- 671
- +13908
姐姐,消失在29年前的黑夜
“姐姐,油棉厂后面发现了一具尸体,快去看看。”1993年3月的一天,一个50来岁的妇女跑进蔡朋娥家喊道。
蔡朋娥大女儿郭桂芳三年前在单位值夜班时失踪,家人四处寻找,发寻人启事,杳无音信。当时,河北邯郸肥乡县很多人知道这事。
蔡朋娥和小女儿慌忙骑自行车,一路飞奔到2公里外油棉厂后的枯井。井边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几十个附近的村民正围着看。
蔡朋娥凑过去,只见遗体蜷缩在井里,裙子、皮带、卷发、身形都和失踪的女儿相似,牙少了一颗——郭桂芳那儿刚好有颗虎牙。她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哭了半个来小时,她们回家叫人,想把遗骨收回去。等再折回现场时,已经没了。围观的人说:“公安局收走了。”
郭家人再没见过这具遗骨。他们心里觉得:这就是失踪的郭桂芳。2015年,蔡朋娥和老伴郭建民相继去世。至死,他们都没搞清:失踪的女儿,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成了盘桓在郭家三代人心口的结。26年了,枯井早已被填平,恐惧、怨怼、隔阂,在这个家庭潜滋暗长。希望看上去越来越渺茫了——直到,2019年4月,12块骨头从这个井中被挖出来。

遗骨
发现第一块骨头的时候,郭会增已经挖一整晚了。
4月24日晚上8点多,他叫来挖掘机师傅,来到1993年发现疑似姐姐郭桂芳遗骨的地方,打算挖井。
26年前,这里还是个沙坑,十几米深、数百平米大。一侧临着河道,另外三边是田地,种着玉米、小麦。一道斜坡由河道伸进沙坑。枯井,就在斜坡半腰,青砖砌成,一米来宽,至少三四米深。

如今,城市的垃圾已经将整个沙坑填平。在灰黄的建筑废料和垃圾碎片中间,蹿出了杂乱无章的野草。
这几年,郭会增经常来这儿转,期盼找到点线索。他自小由姐姐带大,感情很深,姐姐失踪时,他不在家,知道后大受打击。
一个多月前,3月5日早上,他又转到了这儿。回家路上偶遇散步的黄飞(化名),聊起来,发现他竟然是当年发现遗骨的人之一。
黄飞记不太清具体日期了,只隐约记得,那会儿不是很热,穿着长袖。清晨,他和三四个朋友到沙坑玩,摔跤、练拳。一个朋友拿根树枝到处戳着玩,无意间挑开了枯井里的一块小青砖,发现有头发,吓得大叫。其他人闻声围过来,一看都傻了,纷纷往家里跑。
第二天早上,黄飞和朋友一块到离枯井几百米远的肥乡看守所报案。一位民警跟着他们去了现场。
他们壮着胆用树枝将沙土掸开,遗骨露了出来——头朝东、面朝南,蜷着腿,脸还没完全腐烂,头发带卷,一个五十多斤重的大青石压在胸口,身上还残留牛仔裤衩、小皮带头、肉色丝袜。
几个人在井边分析了半天,腿骨一边粗一边细,“不是瘸子就是拐子。”
听了黄飞的话,郭会增很吃惊——姐姐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平时看不出来,跑的时候有点拐。
另一位当年去现场看过的村民回忆,他去的时候,遗骨已经不在了,井边还留着一只带跟的女鞋以及丝袜。围观的人在议论说,“看鞋子像一个女尸”。
26年前,当蔡朋娥和小女儿郭红芳看到遗骨后,她们相信这就是郭桂芳。
郭红芳记得,姐姐失踪那天,穿了件碎花连衣裙,裙上有腰带,脚上穿着丝袜——与尸骨特征一致。
郭家人多次到肥乡公安局了解情况,想确认这具遗骨是不是郭桂芳,一直没有回复。2016年10月,郭会增向肥乡公安局申请公开遗骨的司法鉴定信息。

次年9月,肥乡公安局回复:1993年受理了两起无名尸体案,一是尸长为148厘米、年龄70岁左右的女尸,二是5月9日在一坑内井里发现尸长为168厘米的男尸,特征都不符合郭桂芳,与她无关。因此,没有义务向郭会增公开。
警方的回复没有消除郭会增的疑惑。有传言说,遗骨又埋井里了。他想挖出来看看,兴许能找到点证据。
他找了媒体全程拍摄作证。挖掘机挖了一整晚,他和儿子、儿子的朋友则戴着头灯,用铁锹清开石块,还是没找到井。第二天,在三个目击者帮忙定位后,井终于找到了。12块小骨头,从距井口1米左右的地方相继被挖出。

仿佛有一束光亮穿透迷雾,照了进来。郭会增把骨头小心翼翼收好,放在卧室。那晚,姐姐来到梦里——郭会增很想让姐姐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但姐姐什么也没说。
失踪
失踪看起来毫无征兆。
1990年6月16日,大弟弟郭桂增从老家来县城赶集,郭桂芳留他吃饭。饭后,她送弟弟到路口,说要到单位值夜班。
那年,她32岁,在肥乡县农业局(现为肥乡区农牧局)当团委书记。她高中学历,做过打字员,聪明能干,“年年是先进(员工),要啥啥中”。离婚后带着3岁儿子和妹妹住单位附近。
17日早上,郭红芳睡醒后发现姐姐没回家,急忙和父母到农业局找人。他们找到当晚值班的局长,局长说不在一个屋,不了解情况。遇到了食堂职工,说晚上11点多还看到她值班。
四处不见人,蔡朋娥吓得瘫坐在地上哭,埋怨丈夫,“你把孩子害了”。

年轻时,郭建民是省劳模,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放弃银行工作到村任职,不要工资,事迹多次登报;妻子蔡朋娥曾是全国妇女代表、省人大代表,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在子女的记忆中:郭建民清正、耿直,爱谈家国大事,一说就停不下来;他关注国家形势和反腐新闻,看到电视中包青天审案,会激动得站起来鼓掌。
他“爱管闲事”,看到“不合理”的都要管,为此,有人说他是“精神病”、“不正常”;也有人称他“肥乡包公”,找他反映冤屈。家人劝他,他反驳,“我是党员,我不管谁管?”
有人到家里送礼,被他骂了回去;送来的苹果烂了几个,他买好的补上再退回去。他严厉,脾气暴,家里孩子都怕他;但看到乞讨的人,郭建民自己饿肚子也要分点吃的给他们。
据郭家人回忆,郭建民担任公社书记时,发起了几次反腐行动:1981年举报砖厂贪污群众22万元;1982年揭露当地党代会选举中的反常现象,惊动了中央,三四十名领导干部被处理,落选的县委书记恢复职务;1983年又举报肥乡县工作组在整党工作中弄虚作假、编造政绩……他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先是大女儿郭桂芳,1984年被单位辞退,愤而喝下30粒安眠药、割腕自杀,被抢救了回来,几个月后才恢复工作。之后郭建民自己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停发工资,上访两三年,才调换工作、恢复党籍。妻子蔡朋娥1986年党员登记没通过,被开除党籍、停发工资,还被拘留13天。大儿子郭桂增1986年被抓入狱20多天,挨了打,留下后遗症,经常头疼……
一家人过得战战兢兢。郭桂芳发现有人半夜敲门,心里发慌。郭会增提着棍子去追,发现是因父亲反腐受牵连的人指使的。
但郭建民不怕这些,他一心想为家人遭遇的不公讨说法。
郭桂芳性格和父亲相似,是他的“左膀右臂”,常帮他写举报材料。一次,郭建民在北京上访,身上没钱了,郭桂芳立马把攒了一年多钱买的新自行车卖掉,钱寄给父亲。
寻女
郭家人寻遍肥乡,在电视、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也搭车去过张家口、北京,到北戴河认尸,甚至烧香拜佛,都一无所获。
女儿的意外失踪击垮了郭建民夫妇。蔡朋娥突发心脏病,住了10个月院,整日念叨着“(女儿)被人害了被人害了”。郭建民三次脑出血,后来患上老年痴呆。

他们不愿相信女儿被害了。听说有人和郭桂芳像,哪怕没了双腿的,他们也要跑过去看。他们也找过算命先生,问,桂芳什么时候回来?
女儿的好,女儿的聪明,是最常挂在嘴边的话,“要是桂芳在,多好啊。”说着说着就哭了。
弟弟妹妹们也觉得,“如果姐姐在,生活肯定会不一样。”过去,姐姐经常给他们买衣服、好吃的,家里的家具、日用品,很多都是她买的。
这个家像缺了一角,快乐被抽空了。家人默契地不提失踪的事,一提就难受。
蔡朋娥常埋怨丈夫,“要不是你反腐得罪这么多人,女儿怎么会出事?”
郭建民要么低头沉默,要么反驳,“必须和坏人斗争到底”,他大声朗诵自己写的诗:“风雨交加四十年,为国为民无怨言”“生死规律何辞惧,邪恶面前不低头”……因为女儿失踪的事,两人没少吵架。
郭红芳也接受不了父亲的想法。她高中毕业后,到供销合作社当生活员,后来进入肥乡劳动局工作。领导不让她做重要岗位,她急忙解释,“我不像我父亲爱管事,别人的事情我不管,逼我说我都不说。我不惹事,害怕了。”
“我们心里都埋怨父亲,但是不想伤害他。”郭会增说。四邻没人敢来家里,不敢跟他们走得太近,怕受牵连;周围人一听是郭建民家的人,眼光马上不一样了;找工作时,有些地方不敢收他们,怕得罪人;子女不好找对象,担心女儿嫁过来有危险……“一家三代人都受影响。”
恐惧,像风灌进了这个家。
大女儿失踪后,郭建民屋里常年放根棍子,夜晚12点前没睡过,怕出什么事。他反复嘱咐孩子们:晚上别出门,遇到坏人怎么自卫,在外要注意安全,“看前看后,看左看右”,有时干脆跟着他们出门。
孙子郭伟记得,小学时,晚回家5分钟,爷爷就会紧张地盘问他干什么去了。出去买个馒头也不忘叮嘱,“生怕你突然没了。”
前几年,有一天晚上,郭会增骑着自行车,就被两个骑摩托车的人用铁棍打了。
郭会增听母亲说,父亲偷偷哭过。他能感受到父亲的内疚,痛苦:他整日沉着脸,不再像以前那样拄着拐棍到街里邻坊,大着嗓门跟人唠嗑,一聊大半天。他整日戴着眼镜在屋里写日记和材料,“像变了个人似的。”
寻找女儿失踪真相,成了两个老人余生的信念。
最早,主要跑县公安局等政府部门,向领导反映情况。后来开始向市、省、国家各部门逐级上访,陆续寄了几千封信。
郭桂芳儿子郭超记得,家里以前有个黄色包,装着姥姥姥爷十几年上访的汽车票、火车票、邮票,厚厚地摞着。
两个老人生活节俭,没下过一次饭店,最多吃个面,钱全攒着上访。有时还跟亲戚朋友借钱去,直到前几年才还完账。
郭会增跟着父母去过几次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口排队的人多,有时大冬天,从晚上开始排到第二天早上,下雨也得去。他自己排队,让老人在宾馆待着。
蔡朋娥有关节炎,身子站不直,得被人架着走。她有时坚持要去,站一会儿、地上坐一会儿。郭会增知道,母亲是想亮亮自己全国妇女代表的身份,让领导重视一下。
遗孤

32岁的郭超,已经不太能记起母亲的模样了。对母亲的记忆,依赖于3岁前模糊的印象、家里遗留的照片,以及老人们的念叨。
他隐约记得,母亲那时好几天没回家,他到处找,嘴角都哭裂了。家里人哄他,你妈上班去了。
那段时间,家里来了很多人,气氛紧张。一商量事,就让他出去玩或者去睡觉。他经常哭,问有没妈妈消息。再后来,家里人讨论起骨头和牙齿的事,他渐渐知道,母亲失踪了。
学生时代,他敏感、内向、自卑,不爱说话,也没什么朋友;有人问起他家里的事,他一声不吭地走开。所有母亲会出场的场合——放学后、家长会、运动会……都会让他想到自己的母亲,想起来就难过。
“他在学校经常被欺负,有的同学打他骂他,说他是没妈的孩子,他就哭。”堂哥郭伟和他在一个小学,曾看到有人指着郭超说“他是孤儿,打他没事”。
“现在不知道小时候怎么过来的。不想回忆。一提这事,心里还是会自卑难过。”7月9日,坐在从小生活的屋里,郭超声音很轻,被10岁儿子和2岁女儿的嬉闹声盖过。
打小他跟着姥姥姥爷相依为命。两个老人忙着上访,顾不上管他学习,他也学不进去。读了两年技校后,他去当兵,回来后结婚、生子,到城管局工作,一个月工资两千来块,养家压力大。最近,他请了长假,开翻斗车拉材料,晒得黝黑。
工作后,姥姥常叮嘱他,“在单位干什么事别太出头了,免得招来麻烦。”他心领神会:老人吃过亏,害怕。单位有什么事,他都回避,不参与。单位领导也不敢将重要的事交给他做,“升职都受影响”。
姥姥怕影响他工作,不再让他参与这事。
他不是没埋怨过姥爷,但长大后,好像可以理解了。记忆中,两个老人除了他参军和结婚的时候,几乎没笑过。
他做过不少关于母亲的梦,都是好的——她回来了,一家人一起吃饭。成年后,唯一一次吐露思念,是结婚时,醉酒后一直喊“妈妈妈妈”。他驾驶证里,藏着母亲的照片,翻了又翻。衣柜里,挂着母亲生前爱穿的黑色大衣,姥姥以前经常拿出来晾,后来衣服留给了他。
他有时会想,如果母亲在,“我的人生肯定跟现在不一样。”
更多的时候,他不想,不提。似乎,母亲只是失踪了,他还能找到她。
弟弟
郭会增也有一双儿女,但他已经八年没工作了。家里生计全靠妻子王俊兰做仓库保管、在门诊店上班维持。
初中毕业后,他到县粮棉厂做临时工。父亲因为反腐“惹事”后,他连带受影响,没了固定工作,整日和朋友喝酒、打架。1996年结婚后,他从粮棉厂下岗,开小吃店,卖油,拉煤,做建筑……什么都做过。
姐姐失踪后,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找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姐姐。”
这些年,只要有线索,他都会逐一核实。前年,一个江苏的电话打来,说看到一个人和郭桂芳长得像,他也赶过去看。
2012年,父母身体不行、“跑”不动了,给姐姐讨公道的任务交给了他。母亲说:“家里只有你有能力跑这事,只要你坚持,我相信你。”
这成了他生活的重心:他基本每个月要到北京上访,有时一去上十天。到现在,寄出的上访信已经有几千封了。
没出去的时候,就在家写信、研究材料。厚厚几摞材料,已经刻在脑子里,可以一口气讲出来。

妻子起初不支持他跑这事,郭会增说:“家人被杀,你要是不管,还有没有人性?这样活着没有尊严,我受不了。他们不管,我要管。”
因为这个,两人没少置气。
郭会增觉得没人理解他。有时跟妻子絮叨,她上班累,不想听。于是他经常自言自语,就跟父亲生前一样。
现在,王俊兰已经妥协了:“他愿意跑就跑吧,说他也不听。我不支持,就没人支持他了。”
为跑这事,家里花出去十几万。在北京,为了省钱,他吃最便宜的盒饭,夏天不住宾馆,就到公园长椅上躺到天明,或者包里带个垫子,累了铺开歇歇。
有时没钱了,他打电话问妻子要。王俊兰就找姐妹借,找娘家救济。
和父亲、姐姐一样,郭会增较真。很多人劝他注意安危,妻子、妹妹直截了当跟他说:“你要是出事,家里没人敢替你讨公道。”他头一横:“我不怕。”
但王俊兰怕,她经常告诫孩子要注意安全,“这个家庭和别的家庭不一样”。
郭会增苍老了许多,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眼睛也有些花了,胸口老是疼,整日忧心思虑,睡不踏实。有时凌晨一两点爬起来,边散步边想事。他变得感性,看到悲剧电影,会联想到家人遭遇,刀子扎心般难受。去年在北京上访受阻,妻子打电话嘱咐他在外面要吃好,他在宾馆大哭了一场。
他感觉再跑几年,自己要垮了,“我后半生都毁这里面了”。客厅墙上父亲的照片,他不太敢看,一想起父母是睁着眼走的,想起母亲的临终嘱咐“不管我们遭过多少磨难,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姐姐,要为她讨个公道”,他痛恨又无力。“谁不愿意少一事,平平安安过生活? ”
迷雾
过世前两年,蔡朋娥走路一拐一拐的,还在为女儿的事奔走。
2013年开始,她向肥乡县农牧局申请认定女儿值班失踪为工伤。一年后法院宣告郭桂芳死亡。2014年5月,她向邯郸市人社局申请认定郭桂芳之死为工伤,被否决后,起诉邯郸市人社局。
2015年5月16日,蔡朋娥突发心梗住院。弥留之际,郭红芳对母亲说:“知道你最放心不下郭超。”老人的泪一下就冒出来了。
同年11月27日,郭建民82岁生日那天,郭家人收到了工伤认定的胜诉判决书。那时,郭建民患老年痴呆症,说不了话。郭会增将判决书念给他听,老人半眯的眼睛忽的睁得溜圆,好似听懂了一样。第二天下午,他去世了。
但收到胜诉判决不久,肥乡农牧局提出上诉,否认郭桂芳在农业局值夜班失踪,称之前出具的2份证明材料,为办公室主任私自盖章。此前在一审审判中,这2份证明材料以及3位证人证言,农牧局没有提出异议,获得了法院认可。
2016年8月,二审法院以依据不足为由,驳回工伤认定诉请。

这个转折让郭家人觉得,“太难了,看不到希望”。大哥郭桂增在老家种地,没参与姐姐的事。郭红芳也不想再参与了,她提醒郭会增“别让人家把你害了”。郭超觉得有心无力,“本来应该我出面去跑,现在让舅舅跑,觉得自己有点自私。如果他不跑了,我也能够理解。”
郭会增有些心灰意冷,“压力全在我身上。”父母过世后,这个家更散了。因为工伤鉴定的事,家人间还起过冲突,这让他感觉亲情淡薄。
他在放弃与坚持间挣扎,看不到希望时,想算了;但一想到姐姐的遭遇、父母的托付,觉得就这样放弃,良心不安。“我不能走出去,让别人说我,姐姐被杀了,他麻木不管。”
至今,郭桂芳失踪尚未立案。2015年4月,肥乡公安局政治处主任袁晓雷回复《法制晚报》记者,称该案没立案,是因为已经过了20年追诉期。他没有发现该案报案记录,“该失踪案发生的20多年间,郭桂芳的家人就没有找过公安局。”
2017年9月肥乡公安局回复郭会增时,也称当年没接到郭桂芳失踪的报案,无报案材料及记录。
郭会增坚称,父母当年第一时间就去报案了。此外,2014年10月,肥乡公安局还采集了郭超的DNA,将郭桂芳录入全国失踪人员信息库。
郭会增称,2018年8月,一位警方人士告诉他,“你姐姐是被黑车拉走的,腿还有点残疾”,这些“是从卷宗里看到的”。郭会增认为,有卷宗,说明当年家里报过案,公安局也调查过。
2019年7月11日,肥乡公安局工作人员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肥乡公安已对此事成立调查组,加派警力参与调查工作,其他情况不便透露。
挖出骨头两个月后,6月28日,郭会增在肥乡公安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将骨头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10天后,鉴定中心打来电话,询问是否对骨头做破坏性鉴定。
郭会增先是同意了,又心中忐忑,不停打电话问朋友、记者、妻子,担心骨头一旦破坏,再也没用了。于是急忙取消,只做普通鉴定。
7月16日,鉴定结果显示,“送检检材中未检见人骨”,骨骼大小、形态等与人体骨骼特征不符。

案件再次陷入停滞。
骨头是肥乡公安局工作人员递交的,郭会增想联系其他鉴定机构再做检验。但找了两个月,没有机构做,“媒体不关注,我可能就放弃了,因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但他终究放不下,再次向肥乡公安局递交了郭桂芳失踪重新报案以及公开1993年枯井尸骨的申请书,再借钱请律师。他的微博微信上,隔三差五转发姐姐失踪的信息,向当年的目击者打听情况。
7月7日,他来到父母墓前。那是桃林间一处长满荒草的坟包。郭会增一直想,在完成父母托付后,为他们和姐姐立碑。然后,安顿好儿女,去外地生活。
但眼下,50岁的他,被困在这场笼罩了29年的迷雾里,看不到出口。



- 广场上的鱼:那就期待犯案的人良心发现吧
- 2019-10-24 ∙ 未知16回复举报


- SY695:但愿包公有应,钟魁显灵!
- 2019-10-24 ∙ 湖南24回复举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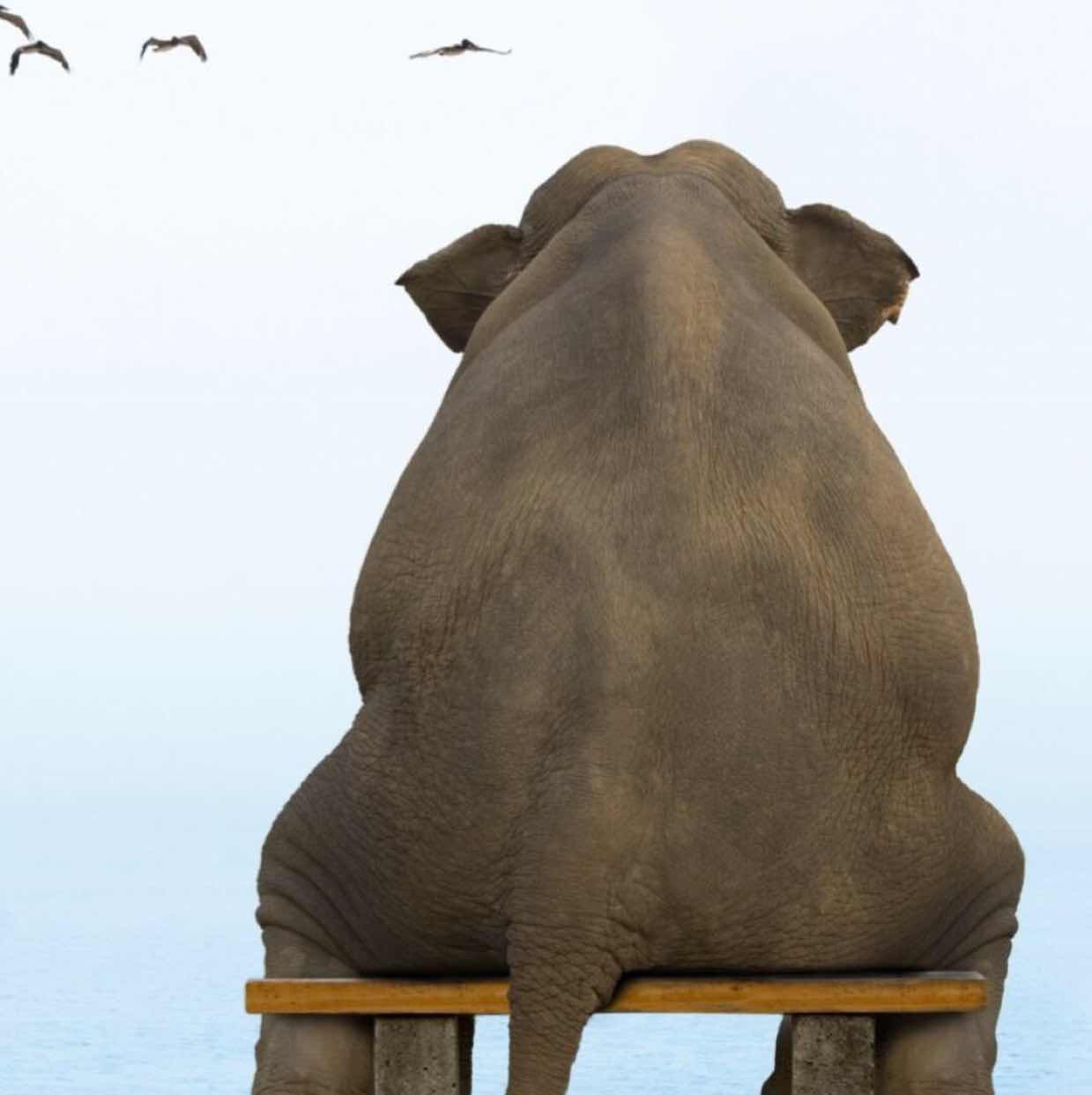

- 谁在把水搅浑
- 服务业扩大开放,多领域明确试点任务
- 中汽协倡议规范驾驶辅助宣传

- 哈佛大学就联邦经费遭冻结起诉特朗普政府
- 伊朗总统:须在保证国家利益前提下与美达成协议

- 国际东方学大师,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
- 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有名句“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