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薄音湖与翁独健的学术渊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明代蒙古史研究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和田清、司律思(Henry Serruys)、萩原醇平、森川哲雄等国外学者,相对元史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学者对明代蒙古史的研究明显不足,且明代蒙古史的研究者多为客串,并没有出现以此为业的学者。这种情况直到八十年代后才改观,出现了薄音湖、达力扎布、宝音德力根等一批研究明代蒙古史的学者,其中薄音湖先生为其中的佼佼者。
薄音湖先生1946年出生于通辽科尔沁左翼中旗,他的祖先是元代林中百姓,祖辈都是普通的农民,父母在他出生这一年参加革命,来到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乌兰浩特,后辗转到呼伦贝尔海拉尔。薄音湖先生1965年考入内蒙古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海拉尔交通部门从事行政工作。在大学时,薄音湖先生大量地阅读了与蒙古民族相关的学术著作,虽然在海拉尔工作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从事的工作与学术无关,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对学术追求,并在“文革”期间通读过《多桑蒙古史》。1978年当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恢复时,他考入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元史三大家之一翁独健先生。

翁独健先生“文革”后首次在社科院招收研究生,其年共有四人,任崇岳先生、罗贤佑先生、薄音湖先生、张承志先生,是年翁独健先生72岁。经历了70多年的风雨,翁先生已不复有当年任燕大代理校长时那样意气风发,而是已经进入古来稀的暮年,张承志先生写到“我认识的翁先生是一位老人,他作为一位老人却拥有着无愧的暮年”。正是这样一位进入暮年的老人,对薄音湖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翁独健先生虽然多年不写文章,但依然关注者学界的最新动向,他敏锐地观察到国内明代蒙古研究很少有人涉猎,于是为薄音湖先生选择了明代蒙古作为研究方向。在师从翁独健先生的三年时间里,薄音湖先生获得了受益终生的谆谆教导和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
薄音湖先生在《青城论丛》后记中说:“只是论文数量不多,质量亦需时间验证,唯略感自信的是,拙文都是努力遵照先生‘重在实证,不尚空谈’的教诲作出的。当年面聆謦欬,先生对乾嘉史学的代表钱大昕,及继承自乾嘉学封的王国维、陈垣诸前辈推崇有家;布置我们阅读的史学理论及方法的著作,则是体现德国兰克史学的法国郎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李思纯译本)、德国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陈韬译本),还有我国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显然,先生是要我们学习乾嘉史学、兰克史学的穷极史料、一丝不苟、求真求实的严谨学风。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唯愿不断勉力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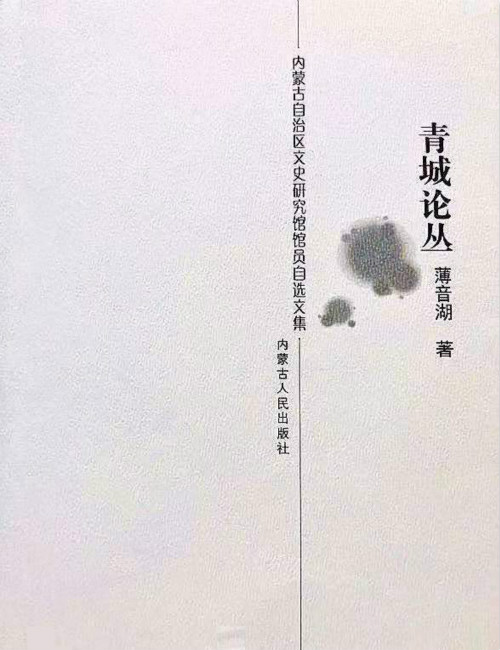
短短几百字,概括了他一生的学术思想及其学术渊源,简而言之即以翁独健先生提出的“重在实证,不尚空谈”为治学的圭臬。翁独健先生早年求学于燕京大学,为洪煨莲先生意门生,大一时他听陈垣先生“中国史学评论课程”,了解我国的历史研究辽金元史较弱,遂决定研究蒙元史。1935年翁独健先生在洪煨莲先生的帮助下到哈佛大学留学,当时的哈佛大学远东语言专业并没有研究蒙元史的合适指导老师,他博士毕业后到了世界汉学的中心,跟随伯希和(Paul Pelliot)学习。在法国期间他学习了波斯文、阿拉伯文、突厥文等与蒙元史相关的语言知识,并掌握了法国汉学的研究方法。翁先生回国后,把洪煨莲、陈垣先生传授的乾嘉史学考据传统,与从伯希和那里学来的建立在历史语言学基础上的法国汉学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风格。清末洋务运动中冯桂芬、张之洞提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寅恪先生及其后学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先生等无不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者。陈先生曾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湘乡指的是曾国藩,南皮即张之洞。
与翁先生有师徒之谊的周清澍先生回忆说:“他认为陈援老是当今乾嘉史学之完美的继承人,邓先生则近似古代文人中的文史兼攻的掌故派。据我的理解,他对二位先生如此评价,后者是指其代表作《古董琐记》、《清诗记事》等体现的路子;前者是认为他具有钱大昕的渊博知识并熟练掌握各种治史的方法,又似赵翼能注意历史的综合研究,并能从札记发展为能阐明重大历史问题的长篇论文专题。”翁独健先生在燕京大学早年受到陈垣先生的亲炙,并推崇其史学方法。刘元珠先生推测翁先生在哈佛的博士论文《爱薛传研究》(AI-HSIEH:ASTUDY OF HISLIFE)在出国前就可能已经打好腹稿,他应该从陈垣先生《元也里可温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得到了启发。
翁独健先生燕京大学早年的学生齐世荣先生回忆,翁先生在西方学者中最佩服的是伯希和,他曾对齐先生说:“伯希和真厉害,《马可勃罗游记诠释》中的一个注,就是一篇考据的大文章。”伯希和去世后,翁独健先生写过一篇悼词,他谈到伯希和的治学方法时说:“然详释先生之著作,其所以能超越前人决疑制胜盖得力于先生精通亚洲,注意版本校勘,与新史料搜求之应用。论者颇有以偏狭为先生之学病;其实先生之治学精神,求精确不求广阔,求专门不求闳通,宁失之狭细,此正为先生长处,奚足为先生病。”翁独健先生从巴黎回国后开展的《元典章译语集释》、《元典章人名考释》研究,正是伯希和治学方法的应用,可惜这些文章大部分没有发表。
薄音湖先生谈起翁独健先生擅长的历史语言考订方法时,常自责地说:“我比较笨,没有学会先生的方法。”其实这不过是先生的自谦之词,《青城论丛》中《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实》、《关于北元世系》等文章无不显示出先生卓越的审音勘同能力,以及具备阅读蒙古语、俄语、日语、英语的语言能力。薄音湖先生常常提及的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注》中对棉花的一个注释,就有好多页的考据,这明显是受到翁独健先生的影响。虽然经历了建国后的无数运动,翁独健先生早年掌握的突厥、波斯、蒙古等多种古代民族语言已经生疏,但他毕竟受过伯希和的真传,历史语言考证的心法他是熟稔于胸的,这在讲课的时候肯定会不经意的流露出来。
19世纪末,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讲求实证的兰克史学在欧洲开始占据了了统治地位。兰克本人是实证史学的一个实践者,在理论上并没有系统整理自己的史学思想,直到1889年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再传弟子伯汉伦(Ern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出版之后,兰克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才被系统的整理出来。1897年法国朗格诺瓦(C.V.Langlois)与瑟诺博司(Ch.Seignobo)合著《史学原论》,这本书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比起《史学方法论》并没有多少创新,但其行文简洁,颇受治史者的青睐。伯汉伦的《史学方法论》通过日本和德国两种途径传入我国后受到极大的推崇,傅斯年、姚从吾等先生在北大授课时主要参考的即是这本书。据杜维运先生研究,在民国流传甚广的梁启超先生《史学研究法》中的许多理论也借鉴自本书。
二十世纪初,翁独健先生留学法国之时,欧洲的历史研究正是兰克史学大行其道之时。他以《史学原论》(李思纯译本)、德国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陈韬译本),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史学理论的教材,正是他在欧洲受过实证史学熏陶的一个例证。齐世荣先生回忆说“翁先生那一辈的学者受实证史学影响很深,最怕著作中出‘硬伤’,似乎一出‘硬伤’,被人抓住,便‘永远翻不了身’”。“文革”后,他曾对齐世荣先生说:“得赶紧写东西了,要不然就来不及。”他夫人邝平章在旁边插话:“你老师太慎重了,看了又看(指看材料),还是不肯动笔。”翁先生一生文章很少,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惜墨如金,几乎不著述,他的弟子张承志先生解释说“那只是被十九世纪实证学术精神濡染的自诫态度”。
翁独健先生在建国后很长时间不著述,主要原因是他所信奉的实证史学并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风气,这种史学方法被列入资产阶级史学而受到批判。他早年对《元史》和《元典章》用功颇深,并对元人文集开始进行研究,可惜这些积累最终化为乌有。

张承志先生写到:“直至一九八一年翁独健、白寿彝等学术泰斗招收研究生时,这场人类认知(尤其是对于历史)的大潮尚不知已处强弩之末,反而以为实证主义因政治条件的改善正欲中兴,前途无限。”张承志先生以历史学家的视野敏锐的观察到实证主义史学正在走向衰落,虽然,这种衰落是在翁先生一辈人故去之后,他并没有看到。中国八十年代史学的掌舵手是深受实证主义史学和传统的乾嘉史学影响的一批人,他们恪守传统,崇尚实证,不务虚言。但当他们及他们的学生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时,所谓的新潮史学终于横空出世,并最终掌握了话语权。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各种西方的理论纷涌而至,历史学研究逐渐人类学化、社会学化,传统的史学方法弃之如敝履。流行于十八、十九世纪的的实证主义史学在西方早已经没有市场,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实证主义史学是显然无法承担这一职责的。
法国实证主义史学的衰微是从伯希和晚年开始的,王静如先生1936年告别伯希和回国之时,伯希和不无悲怆的告诉他:“法国之汉学已呈衰微,能继斯学者,殊不可得,而中国之来学者,当亦渐绝。”在他去世后的不久,以“总体史”为研究目的的年鉴学派成了法国史学的主流,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人的推动下,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潮成为欧美的主要史学流派。即使伯希和的学生塞诺(Denis Sinor)也放弃了伯希和微观考证的方法,以追求宏大叙事以及内陆亚洲游牧社会发展的规律为自己的研究目的。萧启庆先生回忆说:“二战以后,美国汉学和东方学学风大变,历史研究中社会科学方法侵入历史学研究,并占据主流地位,立夫师依然秉承历史语言之方法,不免合者甚少。”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一切都是在向前进化,后来的物种总会在某些方面优于以前的物种,社会科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告诉我们,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但是抛弃实证主义史学,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建立起来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张承志先生所说的那样,“但是新潮派并没有确立自己。他们的办法只不过是把水对稀。他们没有发现,只是听说。他们没有基础,不敢浓缩和朴素化。他们只祈求洋人赐宝,而没有深入中国。他们一窝蜂低价贱卖中国的民俗画,却缺乏对民众的感悟和敬重。新生的这一代智识精华中,只有极少数可能掌握着现代主义;而大多数却可能堕落成投机商或买办。”
在人文学科中对于外来理论的接受,八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学与历史学有着同样的困惑,这从夏鼐先生对二战以后西方兴起的新考古的态度可见一斑。夏鼐先生早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在格兰维尔(S.Glanville)指导下写出《古代埃及的串珠》的博士论文,并受到过埃及考古学的权威皮特里(William Flinders Petrie)的指点,鉴于他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崇高威望和卓越的学术能力,他先后被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日本考古学家樋口隆康说:“他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对于国际上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考古学家,在其晚年日趋保守,在1984年考古学年会上,他否定了由几位理事提出的关于讨论西方最新考古学理论的建议。
夏鼐先生一向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古研究的指导思想,他说:“五四运动时期,历史学方面也有了两个大变化,一个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西洋的史籍考订法和史事考据法。它要比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更无禁忌,更为实事求是。古史辨派便是当时这种史学的代表……中国考古学这个新阶段的标志,首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汤惠生先生这样总结道“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夏鼐眼里更多是一种与乾嘉学派“无征不信”或新史学派以征实为指归并行不悖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原理”。
无论是翁独健先生还是夏鼐先生,他们都在西方著名的学府受过原汁原味的西式教育,他们对西方的思想和理论采用的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对外来学说一味的接受而不知变通。他们同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一样,或多或少受到过清朝中叶以来讲求实证的乾嘉史学的影响,在经过西方的教育后,他们把西方的科学方法与传统的考据结合,从而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写到“盖天竺佛教传入中国时,而吾国文化史已达甚高之程度,故必须改造,以蕲适合吾民族、政治、社会传统之特性”,而当代很多所谓的新潮派以熟稔西方理论自诩,靠套用理论来写文章,以为这就是创新,其实质不过是沐猴而冠。
正如张承志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知识界的弄新潮儿当记一大功,因为他们猛刨了乾嘉学派以来日益腐朽的实证主义墙脚。实证往往证明着虚假,十九世纪连同它的儿子二十世纪都已经结束了。”
翁独健先生逝去了,他的史学思想并没有逝去。1981年翁独健先生对薄音湖先生硕士论文《俺答汗研究》审查时写到:“论文的作者广泛使用了蒙汉文史料,特别是尚未正式出版的蒙文抄本《俺答汗传》,集中就求贡、经略和喇嘛教三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这是前人没有充分做过的。”这不仅是对对自己学生的肯定,而且其中也包含着对未来的期许。
在翁先生去世后的三十二年,薄音湖先生的著作《青城论丛》终于出版,或许可以用张承志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注脚,“十九世纪和实证主义都过去了,也许应当留取的只是考据家们当年追求真实的初衷。发现了《热什哈尔》并为它提起笔来时,我觉得自己第一次可以正视昔日师长的期待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