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寅丽读《爱与圣奥古斯丁》︱重新发现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1929年在她的导师,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这是她登上学术舞台的首部著作,1929年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在柏林出版。受她政治思想吸引的的研究者们很少注意到这部以神学为主题的作品,但在奥古斯丁学界,她大胆挑战这位教父权威的观点却不时受到关注。其实阿伦特跟她的另一位著名导师海德格尔一样,都是从神学转向了哲学研究。阿伦特十六岁就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她高中从文科中学退学后,先在柏林大学旁听了几个学期。在那里,天主教存在主义神学家罗曼诺·瓜尔蒂尼(Romano Guardini)的神学课吸引了她,接着她醉心于丹麦神学家和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从而做出了主修神学的决定。1924年她提前一年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获得大学入学资格,进入了马堡大学。阿伦特在马堡期间也选修过德国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的新约神学课程,布尔特曼以对“新约的非神话化”研究著称。不过阿伦特很快就放弃了神学,转而跟随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所引领的哲学批判潮流。

对于她的博士论文最终为何以奥古斯丁为选题,她马堡时期的同学、终身好友汉斯·约纳斯说,当时以奥古斯丁为论文题目是流行而常见的做法,而且那时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都热衷回应“奥古斯丁的存在主义信息”。海德格尔1921年在弗莱堡大学夏季学期的课程讲授过“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雅斯贝尔斯自己也写过大哲学家导论中的一卷:《柏拉图与奥古斯丁》(英文版1957年由阿伦特编辑出版),这些都显示出1920至1930年代的德国现象学对奥古斯丁式存在主义的热情。显然阿伦特不是把奥古斯丁当成教父神学家,而是当成存在哲学家来阐释的。她声称她的论文对奥古斯丁的解释要“捍卫一种纯哲学的探索”和“避免教条化”,“尝试穿透奥古斯丁自己都未能澄清的幽深之处”。海德格尔的迫人直面的死亡、在世的沉沦,雅斯贝尔斯的“存有”或“大全”,都在论文中清晰可见。另外,她以奥古斯丁最具有标志性的一个概念——“爱”为主题,也是意味深长的,有人认为这与她对海德格尔秘密的、失败的爱情有关。的确,在他们两人1929年前的通信中,“爱”是一个被“实在性”“命运”“生存”等存在主义词汇包裹起来的、两人之间的暗语。但是正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始于对“我是谁”的自我找寻,而终于自我被上帝寻回的道路一样,阿伦特也透过对奥古斯丁这一重要概念的重新诠释,告别了她后来视为私人的、“非世界性”的“爱情”,发展出公共性的“世界之爱”。

重新编辑的英文本
阿伦特从1933年离开德国流亡开始,德文版的博士论文始终带在身边。1962年她和出版社签订了一份翻译出版其博士论文的合同,论文由翻译过雅斯贝尔斯多部著作的阿什顿(E. B. Ashton)翻译,英译稿得到了她的肯定。在她1964年1月13日致乔治·麦克肯纳(George McKenna)的一封信中,就博士论文何时能与读者见面的问题,她回复说:“我博士论文的英译稿已经拿到了,预计今年或1965年出版。我还腾不出时间把译文过一遍,但我想译得很棒。”事实上一拿到译稿她即着手修订,在与玛丽·麦卡锡的通信中她曾简短提及此事(《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1949-1975》,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在1965年10月20日发自纽约伊萨卡城的信里,阿伦特详述了她最近的欧洲之旅和她与雅斯贝尔斯的会面,然后她提到了她修改博士论文的工作:
我给自己找了个荒唐的差事——几年前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要出版我当年写奥古斯丁的博士论文。当时我需要钱(不是很需要钱,但确实有用),于是答应他们了。译文两年前就送过来了,到现在我再没有了借口,唯有仔细看一遍。这真是一种折磨。我几乎是在全部重写,但又尽量不加新的东西,而只是用英语(而不是拉丁语)去解释我在二十多岁时的想法。这样做或许不值得,我应该直接把钱退回去,但现在我又奇怪地着迷于这次不期而遇。我有差不多二十年没读过这东西了。
《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1949-1975》
要尽可能地保留二十多岁时的想法,并用英语重新解释,困难可想而知。阿伦特先是在阿什顿译文的空白处做了多处订正和增补,后来干脆自己在打字机上重打了第一章第一节至第二章第一节,有的地方把原文里的脚注加进了正文,有的地方加入了原稿中没有的文字,以使原来的论证更有力或观点更清晰。但她的重打计划到第二章第一节中间部分就停顿下来了,最终放弃了出版计划。1996年J. V. 斯考特和J. C. 斯塔克(Joanna Vecchiarelli Scott & Judith Chelius Stark)根据博士论文英译稿,以及1964至1965年间阿伦特本人对其所做的修订,编辑出版了《爱与圣奥古斯丁》的英文版。这本书因此囊括了两部分: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一节采用了阿伦特在打字机上重打的内容(B版),导言、第二章中间开始到第三章采用了她对阿什顿译文的修订(A版)。两位编者认为有理由猜测,随着阿伦特在六十年代中期卷入艾希曼审判而引起的空前争议和忙碌,她的博士论文出版计划不得不搁浅了。但其他一些研究者例如卡诺凡(Margaret Canovan)则认为,阿伦特最终发现要重新表述早年思想是无望的尝试,遂在第三卷之前放弃了她重订博士论文的计划。
阿伦特1929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曾在《法兰克福时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奥古斯丁与新教》,作为对奥古斯丁逝世一千五百周年的纪念,那篇文章表明她很早就具有了奥古斯丁对于现代世界的适切性问题的意识。但她的博士论文所代表的早期思想,跟她成熟时期的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却始终是有争议的。实际上,在1931年前,除了博士论文外,阿伦特还写过拉尔·瓦哈根的传记,后者直到1938年才完成最后两章,于1958年出了英文版。由于此书所涉及的犹太人身份和贱民-新贵的主题,同她后来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论述的反犹主义,以及对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批判更为相关,与博士论文的神学主题相比,更易于为对阿伦特的“政治解读”所接受。因为她从1933年逃离纳粹德国到五六十年代作为活跃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写作,都是跟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扬-布鲁尔(Young-Bruehl)在她关于阿伦特的权威传记(《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陈伟、张新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中就断言,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是跟她早期神学观点的决裂。卡诺凡在写作《阿伦特政治思再释》前,研究过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经阿伦特修订的博士论文英文稿,结果是她更确信了极权主义经验对阿伦特思想的决定性作用,她惊讶于青年阿伦特不关心政治,“沉浸在一种特殊的非世界的智识兴趣中”。她得出结论说,显然是来自纳粹的直接威胁,迫使阿伦特放弃了“反政治的神学研究这种无关政治的理智兴趣”(《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陈高华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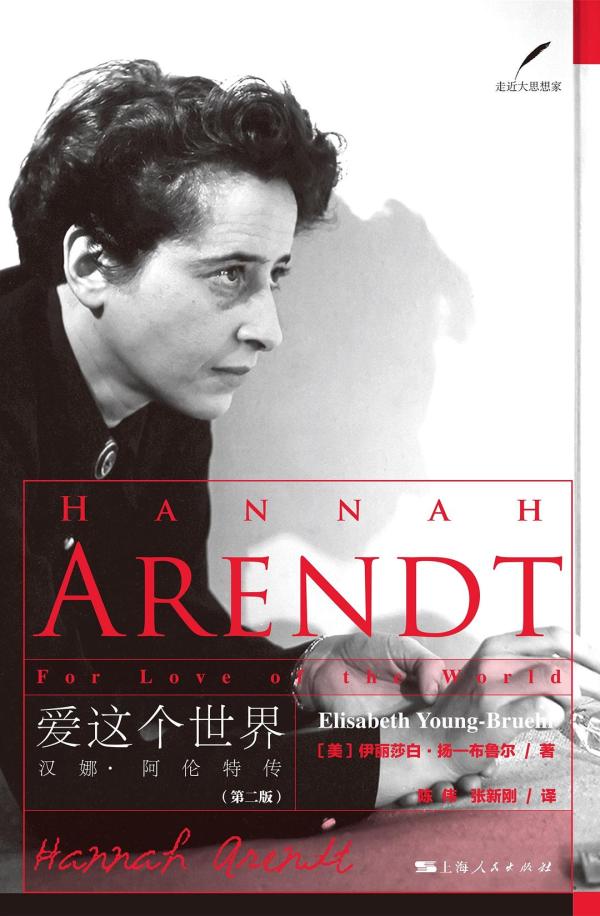
玛格丽特·卡诺凡著《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
也就是说,对于修订稿未能如约出版的原因的猜测,实际上受两种解释态度的支配:斯考特和斯塔克认为,阿伦特的博士论文提供了她从德国现象学、神学到政治思想转变过程中的“缺失的一环”,换言之,阿伦特后来对公共世界的热情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而卡诺凡等主流研究者认为,阿伦特的博士论文与成熟时期的政治思考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是跟她早期神学兴趣决裂的结果。
博士论文的主题
奥古斯丁的爱观,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就是提出了圣爱(caritas)/贪爱(cupiditas)的两重区分:圣爱是对上帝的爱,贪爱是对被造物的爱,前者是“正确的爱”,它“追求永恒和绝对未来”,后者是“错误的、世俗的爱”,它“握住世界不放,从而构造了世界”。前者让人“返回”作为自身存在源头的造物主,后者诱使人离开真实起源而陷入次一级的世界,误以为先于他个人存在的、给定的世界就是他的起源。但阿伦特在博士论文中真正要问的是,在奥氏对爱的两分法中,邻人之爱的位置何在?在论文前两章,她运用现象学方法分析了奥古斯丁爱的概念的两种“概念语境”,第一个是欲望的语境,在此语境下,爱被定义为“欲求”(craving/appetitus),“爱不过是为了自身的缘故对某物的渴求”;第二个是造物主-被造物的语境,其中,爱是向着创造源头的回返,向着过去之记忆的回归。在前一语境中,两种爱的区别在于不同的欲望对象,在后一语境中,两种爱的区别在于时间性上返回到不同的起源(上帝和世界)。她分析的目的是要表明,在这两种论爱的语境中,邻人之爱都是从圣爱中派生出来的,从上帝之爱推出邻人之爱的过程,不仅让后者不具有一个独立的地位,而且造成了对自我的否定和对世界的疏离,从而取消了“邻人”自身的特殊性和他(她)与我们在世相遇的“相关性”。邻人之特殊、切近被消除:“既然我不爱在这世界的归属中成就的我,我也不爱在具体属世的境遇中与之碰面的邻人。”“与我的同伴本人——在他们具体的在世存在以及与我的关系中——的相遇,始终被排除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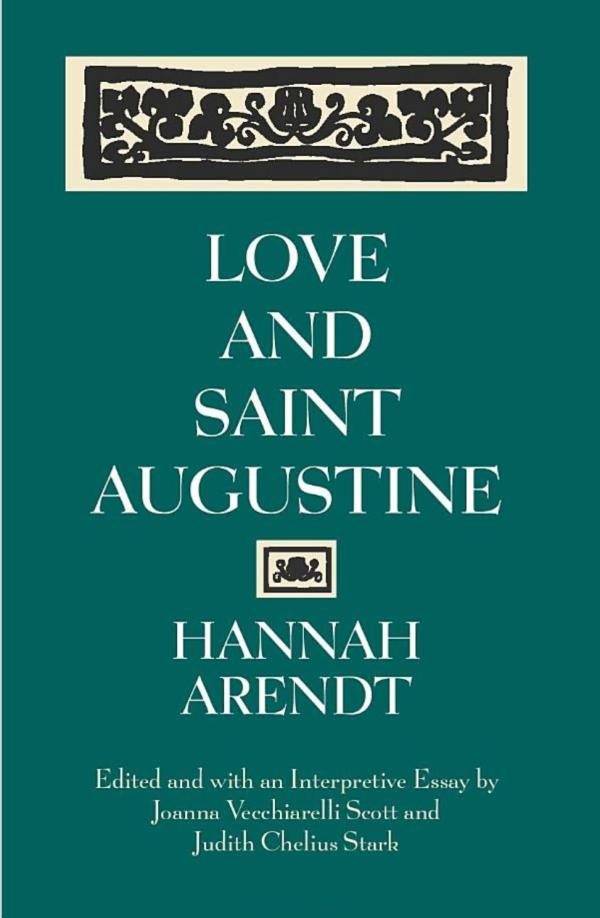
在博士论文中,阿伦特关心的不仅是奥古斯丁神学中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即“邻人之爱是否可能”,更是从“邻人相关性”的角度发问。这个角度就使得她早期对邻人之爱的关注,不再着眼于传统神学的问题,而变成了对“人们之间的存在”和他们开启的共同空间的关注。论文第三章从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转向信仰者共同体,阐释邻人之爱的真正意涵要在信仰者共同体所共享的共同历史命运“世界”中,才得到辩护。即她试图把信仰者共同体(教会)阐释为一个政治社群,而不仅仅是信徒碰巧有同一个信仰。这部分显然跟她后来发展出的公共性思想最为相关,但在原来的博士论文中草草收尾了,而她六十年代的修订工作也从第二部分中间开始就中断了。联系到她后来对“爱”不具有世界性的批评,和把爱与政治对立起来的看法,也可以猜想阿伦特后来放弃重新编辑的工作,并非如两位英文编者所认为的是工作重心的转移,而是放弃了从奥古斯丁之爱来发展人类团结的尝试。例如著名学者理查德·伯林,就因此质疑重新编辑的博士论文在阿伦特研究中的重要性。
超越海德格尔
显然,即使把阿伦特的博士论文放在一边,也不影响对阿伦特成熟思想的理解和评价。但是斯考特和斯塔克编辑的英文版,则提供了一个从奥古斯丁式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理解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可能性。例如,《人的境况》开篇就给出的、使人类活动成为必要和可能的那些人类条件:诞生性、有死性、世界性,她并未解释它们来自何处,仿佛这些对读者来说是预先就有的认识。开篇关于人的复数性、差异性的两段引文都和奥古斯丁有关,几段之后,她又谈到奥古斯丁第一个在哲学上提出了我是谁的问题。从博士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人的时间性生存、意愿等后期思想的主题,都纷纷在博士论文中首次亮相。虽然这些概念明显受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影响,但有两个主题特别反映出阿伦特借助奥古斯丁而超越海德格尔的印记。
一个是关于“诞生性”的主题。B版最后一段对于奥古斯丁区分世界“开端”(principium)和人的“开端”(initium)的讨论,是她在1963年修订时特地加回到原文中的:
奥古斯丁写道:“这个开端以前根本不存在。为了有这样一个开端,人被造出来,在那之前没有人。”……因此,正是为了创新(novitas)……人才被造。由于人能意识到、了解和记起他的“开端”或起源,所以他能作为一个开端者行动并创造人类故事。(B: 033190)
由此凸显出她后来浓缩为人的“诞生性”这一概念在博士论文中产生的语境。这些修订与她在后来其他著作中关于诞生性的讨论相一致,都指向奥古斯丁关于人的创生的隐喻。(关于行动的存在论条件是人的“诞生性”的表述,最早出现在她1958年出版的《人的境况》和同年为《极权主义起源》写的再版序言“意识形态与恐怖”中。她认为,人的出生构成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新开端,行动和带来新意义的言说,可谓政治人类学意义上的新生或“重生”。)在论文中,她也将对于人之诞生的喜悦,对比于她对海德格尔的中心主题——面对死亡的焦虑——的抛弃。“换言之,决定了人作为一个有意识的、记忆的存在者的关键事实,是出生或诞生性(natality),即我们以出生进入世界。决定了人是一个欲望存在者的关键事实是死亡或有死性(mortality),即我们在死亡中离开世界。”“给人的生存以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就是记忆而不是期待(例如,比较在海德格尔进路中对死亡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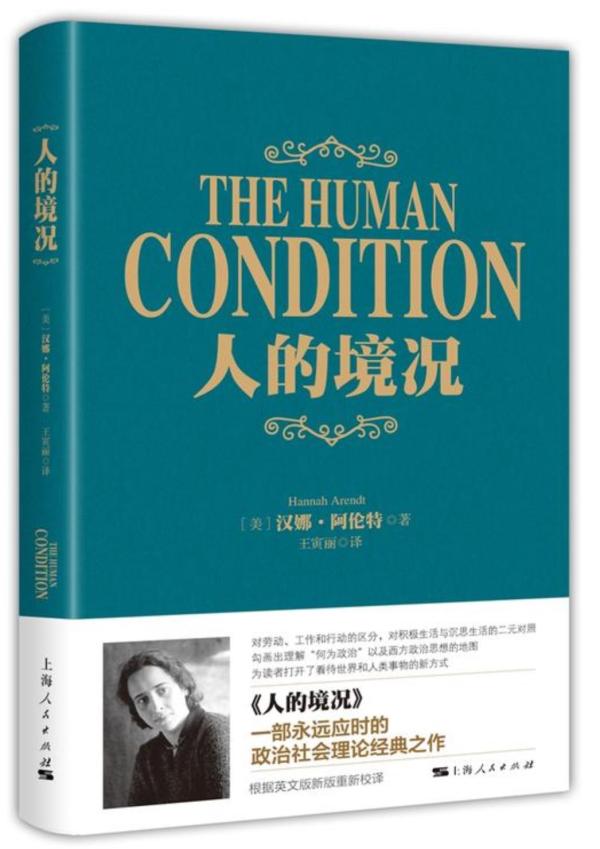
另一个主题是她从奥古斯丁那里吸取的“贪爱/圣爱”模式来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奥古斯丁最常被用作政治文本的《上帝之城》中,他用“爱”来解释“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这两个社群空间的起源和它们在历史中的发展。他理解的爱不是任意发挥的情感冲动,而是所有人类行为、习性、嗜好的心理学根源。即两种根本的人类动机支配着两种社群生活:“两种爱分别造成了两座城:对自己的爱构成了尘世之城,甚至发展到蔑视上帝;对上帝的爱构成了上帝之城,甚至发展到蔑视自我。一言以蔽之,前者将荣耀归于自身,后者将荣耀归于上帝。”(《上帝之城》14:28)自爱促使人们尽力荣耀自己,体现为贪欲和统治欲,它们在地上引起无穷无尽的分裂冲突,但也促使人类出于自保的联合和共同生活的善而建立暂时的和平。而基督徒出于共同的上帝之爱,才能建立真实永恒的“天上的和平”。对于奥古斯丁来说,真正创造共同体的力量是“爱”,对一个共同世界的希望和承诺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出于对安全、个人权利或利益的考虑。在阿伦特的解读中,“爱”成为了一个联系爱者和所爱对象的存在论纽带,不同的爱塑造了不同的人格和世界。“爱(渴求)连结着爱者和被爱的对象,贪爱将人变成了‘爱世界者’(dilectores mundi),也把上帝起初所造的世界变成了欲望对象的世界。”“仅仅由‘爱世界者’所建立的世界是一种恶,仅仅追求这种‘恶’就变成了贪爱。”阿伦特以奥古斯丁的“贪爱-圣爱”模式来解释的双重世界,在《人的境况》中演变成了单纯由“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造成的消费主义的世界和单纯由“技艺人”(homo faber)所产生的工具化世界。而对真正持久共同之物的爱,却转化和更新了这个世界。正是在此意义上,阿伦特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总结为“爱这个世界”(amor mundi),而非海德格尔对“被抛在世”的不安;这种爱也并非马基雅维利所谓的“爱祖国甚于爱灵魂”之爱,而是对人们以言行所创建的共同世界的关爱和葆有之情,正是这个共同世界使人们在世的彰显和行动成为可能。正如罗纳德·贝纳(Ronald Beiner)指出的,阿伦特并非要用“爱世界”来代替奥古斯丁的“爱上帝”,她的世界也不是在贬义上的俗世,而是一种对世界非占有性的爱。
随着阿伦特的奥古斯丁论文重新得到学界的重视,在阿伦特研究中,对阿伦特政治思想的片面“海德格尔式现象学化”和“希腊城邦化”的解读有可能得到纠正。一些政治学者则从公民德性、公民身份主题上,受之启发重新挖掘奥古斯丁政治思想在当代的活力。其中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是已故芝加哥大学教授让·俾斯克·爱尔斯坦(Jean Bethke Elshtain)所著《奥古斯丁与政治的界限》(1996)和现任普林斯顿宗教系教授艾力克·格雷戈里(Eric Gregory)的《政治与爱的秩序:一种民主公民身份的奥古斯丁式伦理》(2010)。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