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狗十三》:静默中的爆裂和重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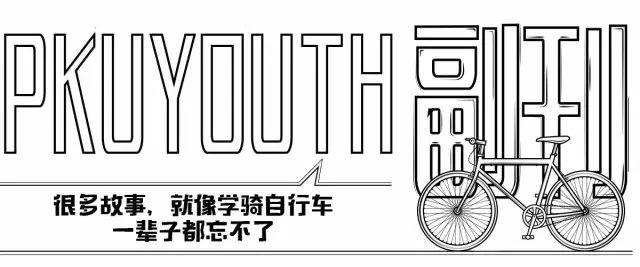
全文共3579字,阅读大约需要6分钟。
本报记者
詹 婧 中国语言文学系2015级本科生
从2013到2018,这是一部尘封了5年的电影。
《狗十三》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一个充斥着堕胎、暴力等因素的类型化青春片逐渐声销的时刻。它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场域,来叙述一个日常的、琐碎的故事。
导演曹保平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时曾表达自己的心愿:希望《狗十三》不被喧嚣的商业市场淹没,希望这部反国内青春片一贯套路的电影,可以触碰到更多人内心复杂微妙的情感。而要触碰更多人,要点亮更多人已经遗忘的角落,叙事就必须谨慎。
影片的故事脉络并不复杂,父母离婚的李玩,被寄养在祖父母家里,慢慢接纳叫“爱因斯坦”的小狗,在“爱因斯坦”跑丢之后慢慢接受另一条“爱因斯坦”,她从与狗亲密到分食猪肝饭,到坦然麻木吃下红烧狗肉。这个不断破碎又重塑的过程之后,她被认为是“长大了”。

△影片剧照,小狗“爱因斯坦”
在面对《狗十三》这样一个少女题材的故事时,擅长拍暴烈风格影片的曹保平态度是审慎的。电影描绘的场景、选择呈现的人物,都尽量保持了克制和静默。纵使是唯一的暴力场景,也并不是骇人听闻的猎奇血腥。相反,它们都显现出日常的样态,像你、像我,像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过的十三岁。
李玩不是一个极端的女孩,她的父亲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暴力分子,他们身上都呈现出了值得玩味的复杂性。

△影片剧照,李玩向镜头展示金属牙箍
她忽略喜欢毛衣和喜欢物理之间的巨大差异,她怀疑自己的长性。她努力为自己的世界里失衡的一切建构合理性,她努力为自己世界中的一切失衡建构合理性,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相处、沟通,她必须将自我意识缩得小一点,再小一点。她需要一套新的规则,来安置那些被放弃的东西。
长成大人的过程是苦痛的,她必须编造无数类似“狗狗去天堂啦”“爸爸妈妈分开是因为妈妈是天使”的善意谎言,来缓解这种生长的痛。喜欢物理、爱读《时间简史》的李玩,她的“谎言”是平行宇宙,用来堆放所有遗憾和不甘。
十三岁的角色,让十四岁的女孩来演,可以称得上本色。张雪迎生就一张寡淡的脸,一单一双的大小眼,坑坑洼洼的额头,还有柔软嘴唇里露出的金属牙箍,带着尚未长成的孩童般的圆钝感,却也开始慢慢长出的少女的精致下巴。
她在镜子前打量自己的牙箍还有正在发育的青涩身体,掀开衬衫下摆,其下是90后女孩最熟悉的“小背心”。和堂堂炫耀的男友高放送的精致、成人化的胸衣不同,母亲这一角色的缺席造成了李玩对女性身份认知的迟缓。那些细腻的、敏感的部分被粗暴略过,女孩对着镜子里青涩的身体微笑的时候,面对那个陌生的自己,她的反应是失望与低落。
她将自己的身体看做“他者”,她对这个“他者”不满。在她的世界里,可以沟通的女性寥寥。祖母非常疼爱她,会因为她彻夜不归而不顾自己对外部世界的陌生出门寻找,会为她布菜,会帮忙调解父女之间尖锐的冲突,但是她不记得李玩不喝牛奶,也不会关心她吃饱穿暖以外的需求,年龄差构成了难以逾越的交流鸿沟;继母更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只在必要时刻展露亲昵,与其说她厌恶李玩,不如说她眼中根本没有李玩;堂堂也许会是一个好对象,但是同龄人所能做到的太过单薄,她不够权威,不足以帮助少女完成清晰的自我认知,两人之间亦敌亦友的关系也在消解着堂堂的权威形象。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李玩和堂堂之间关于身体的打闹,可以想见应该是李玩先提出了相关的好奇,而堂堂从一开始追着她想触摸一直到嚷嚷着愿意出钱摸一下,在这个与性、与身体极其密切的时刻,两个人却都呈现出孩童的一面,气氛走向略具荒诞感的轻松,在影片之前的部分中比起李玩更具有女性气质的堂堂,在这一刻回归到了无性别、好奇的孩童的身份。
李玩的拒绝也值得玩味。她对堂堂的求助和拒绝之间形成了奇妙的张力。她对自己的身体好奇,但除了好奇之外,更多的是难以摆脱的耻感。
这种耻感的极限,在暴力之后爆发。影片的核心矛盾“丢狗”这件事之后,李玩的“不依不饶”最终引致父亲的暴力。脸上的每一个巴掌,身体上挨的每一下,都在打碎少女身体的一部分。李玩在哭着道完歉后奔进浴室,被强烈的音乐填补的应该是哭声,正如现实叙事中应该会被水流声掩盖的哭声,一切的碎裂、重建都必须静默。在这一节点之前会大吵大嚷、大声喊出“这不是爱因斯坦”的少女,在之后的叙事中变得温和而节制,即使是在影片末尾找到有了新主人的爱因斯坦,她委屈的哭泣也是几近静默的。

△影片剧照,李玩在水流下哭泣。
背景音乐中不和谐的尖利噪音暗示着少女内心割裂般的痛楚,她用被啤酒瓶碎片扎破的手指颤抖着脱下衣服,她要冲洗的不是身体,而是那份浓重的耻感。水雾蒸腾之间,艰难站起的背影纤细而脆弱,随着客观远景镜头转向主观近景镜头,李玩已经完成了一次自我重建。羞耻感带来的个体自我意识慢慢消融,她在尝试走向大众行为,做出“正常的”、世俗化的选择。
她坐上了父亲的膝头。不得不说在我看来这是相当滑稽的画面,少女逐渐长成的躯体蜷缩成婴儿在子宫中的姿势,含着胸,驼着背,而这种蜷缩并不能缓解父亲仰头说教的荒诞感。青春期的少女,在看似柔情的话语下,被要求在父亲怀中以婴孩的姿势,成为“大人”。

△影片剧照,坐在父亲膝头的李玩
在这一段之后,影片对于少女身体的描述或者说探索戛然而止。在之后的部分中,紧凑的叙事替代了细腻的情感表达,李玩甚至成为了一个“去性征”的人。外界的压力挤压了对身体的关注,她不再关注身体的变化,牙套也在不经意间消失,她和父亲之间的亲昵举止完全遮蔽了青春期少女本应具有的、对于身体触碰的敏感与焦躁,她在堂堂明显的妒意之中毫无知觉,她忽略高放后颈的纹身,同时也拒绝他的求爱。她的身体消失了。
这种消失在和堂堂的对比中显得极其明显。早期两人的对话关系尚且带有李玩作为少女对于姐姐的憧憬和想象,后期两人却完完全全走向了两条不同的路径。没有遭遇过暴力(至少在影片中没有表达)的堂堂,在酒精、男孩、舞厅多重作用下,长成所谓的“坏女孩”,勇敢对高放坦白爱意,也能在男孩的无意之中坦然和他分手;而曾经认真问堂堂“你爱他吗”的女孩,却已经全然超脱开少男少女的情爱世界,在暴力驯服之下,在酒瓶碎片扎进皮肉之后,成为了一个没有性征的“乖孩子”。
这是一种巧妙的叙事策略。为了完成“触碰”,创作者站在接受者的角度,要尽可能多地嵌入接受者(年轻人们)所熟悉的情节——气氛沉重的家宴、家庭中遭遇的不公的对待、大人们的轻诺寡信,这些必要的情节挤压了少女的生存空间,也同样构建起了和现实的联结,有意识地触碰着那些年轻人,要引发他们的共鸣。

△影片剧照,李玩弟弟昭昭的生日宴会。
所以,在家庭矛盾、学校叙事充斥的后半部分,影片的整体环境得到重构。突然之间,李玩生活的空间变得拥挤而吵嚷,继母、弟弟,诸多亲戚,都出现在镜头之中,我们所见到的李玩,私人镜头变少,她常常处于和他人的交流、接触之中。
寻找跑丢的狗构成了影片的核心事件,围绕这一事件,导演有意展开了多维度的视角分析,除了李玩以外,我们还能看到更多人对于这一事件的看法,影片处于“众声鼎沸”之中。在成年人(祖父母、父亲、继母)看来,能否找到小狗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它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宁可将这份精力用来驯化李玩,让她懂得“接受”“懂事”;而在李玩眼中,丢了就要找,这是天然的逻辑。而且,爱因斯坦对于她而言是有名字的,从让小狗吃自己爱吃的面条,到为小狗专门做它爱吃的猪肝饭并且和它一起吃,通过爱因斯坦——一只柔软的小狗——她扮演了一个付出爱的角色,笨拙地完成爱的习得。

△影片剧照,在爱因斯坦走失后李玩伤心地哭泣。
在整个寻狗事件中,家庭矛盾指向的是两种几乎截然相反的思考角度。李玩无疑是渴望亲情的,她很需要一个父亲,而不是一只用来搪塞的狗,但是她所祈求的父亲与她真正的父亲根本是两个人。父权逻辑之下,不存在换位思考、尊重理解,父与女的关系更多的是上对下的施与、下对上的服从,其核心是稳定。
为了让李玩“稳定”“正常”,有一开始的谎言安抚(“为了你复习中考把狗送走”),有祖父母的苦情劝解,有继母和堂堂的掉包糊弄,诸多方法在影片叙事中全部无效,最终影片选择以暴力终结不稳定因素的挣扎。
暴力过后,一切破碎。李玩在不断碰壁中磨损掉自己的形状,她变得能喝牛奶,能面不改色地吃掉端上来的红烧狗肉,能平静地在弟弟生日的家宴上被忽视,能接受错过的天文展览,能放弃眼前的爱因斯坦。
就像教室里四处乱撞、最终被英语老师拍死扔出窗外的蝙蝠,李玩不想毁灭,所以她选择“长大”,选择妥协,选择重构。
可怕的是,这种重构几乎陷入了一种前仆后继的重复“圈套”。堂堂比李玩早一步,而昭昭又比李玩晚一步。影片的最后,昭昭哭着吐出牛奶,在教练“不许哭,自己起来”的声音中委屈地不断跌倒,浴室里曾出现过的尖利的声音再次出现在背景音里,“我还是不会滑”的求救,逐渐听不见了。
整部影片的格局、体量都不算大,但却在这种有限之中展露出了力量感。静默的日常之下,无声的碎裂、自觉的重构在不断进行之中,回环往复。展现“这样的事以后还多着呢”,触碰、揭开年轻人曾经的伤口,这并不是徒劳无益的。也许变化不能在一朝一夕间见到成效,但是关注和审视本身就构成价值,毕竟,没有人永远十三岁,但总有人正在经历他们的十三岁。
图片来自网络
微信编辑|贺依林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