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佩索阿的每一个异名都不是佩索阿
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是二十世纪欧洲现代主义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生前声名不著。他四十七岁病逝,身后留下一大箱手稿,有两万五千多页,其中一部分得到整理出版,包括诗歌、散文、文学批评、哲学论文、翻译等不同门类,为他在全世界范围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佩索阿出生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五岁丧父,八岁时随母赴南非,与派驻德班做外交官的继父生活,在当地接受了良好的英语教育。十七岁时,佩索阿独自乘“赫索格号”经苏伊士运河回到葡萄牙读大学,两年后里斯本爆发学潮,在混乱中佩索阿退学,实行自我教育。此后三十多年每日上下班,为贸易公司做商业信件翻译,酗酒、写作,基本没有踏出过里斯本周边。期间他曾用外祖母留下的一小笔遗产尝试过开出版社,做过一些商业中介的生意,但都没有结果。
从他的手稿判断,佩索阿写作不辍,几乎一天都没有停歇过的样子,这也许是因为他对自己构建的庞大的写作世界有着紧迫感?佩索阿的文学世界里,绝大部分作品没有署在他自己名下,而是被他分别安在不同的“异名”(heteronym)身上。他的异名,不同于笔名或假名,都是完整的、区别于其“本我”的人,有自己的生平履历、社会关系,有自己名下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有着极强烈的、符合其性格和观念的风格。异名之间的风格互不相同,形成对话、继承、衬托、补充等多种关系,或者完全“没有”关系。这种关系有文本层面上的,也有“真实”生活中的交往,包括会面、互相写信、批评等等。
佩索阿前前后后采用了一百多个异名,或者更多,其中有的是诗人,有的是哲学家、批评家、翻译家,有的是天文学家、心理学家、记者等等,就像孙悟空拔一把毫毛变成了许多化身。不同之处是,孙悟空拔出的每一根毫毛都是孙悟空,而佩索阿的每一个异名都不是佩索阿。甚至佩索阿“本人”也是这异名系统中的一个,是一个异名、真名、本名的统一体(或者矛盾体,两者在此是一回事),考虑到“佩索阿”这个词在葡萄牙语里的意思是“人”,事情就更意味深长了。佩索阿的本人,正如冈波斯所说,“并不存在”,却赫然成为撑起这个庞大的文学世界背后的黑洞或零。这个黑洞或零,最终而言并不是否定的,而是从否定的维度平衡了佩索阿的写作世界。
佩索阿最重要的异名有这么几个:诗人卡埃罗、冈波斯、雷耶斯,写《惶然录》(又译为《不安之书》)的索莱斯等等。冈波斯和雷耶斯都把卡埃罗看作导师,并有私下交往(关于冈波斯和其导师卡埃罗以及其他几位异名的关系,关于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和作品风格,可以参考附录——冈波斯的回忆性批评文章《回忆我的导师卡埃罗》)。把卡埃罗和冈波斯的诗对照参看,会非常有趣。因为他们都是佩索阿的思想投射,有各自独特的哲学本原,是从此本原生发出来的诗人。传统观念认为,文学作品如果只是一种哲学观念的表现,那么这个作品就是失败的,在文学作品中,哲学观念最好是自下而上自然生成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演绎。即使这个观念是对的,佩索阿也肯定是个例外。
事实上,伟大的文学都只能是例外,因循守旧对现代文学来说从根本上就不可行。从实际形态上看,佩索阿的这几个异名的声音都从清晰的哲学观念出发,演绎或呈现出自然生发的活泼形态。不同于他的导师卡埃罗的无目的性、无哲学性的“看”,冈波斯主张“感觉主义”,目的是“感受”一切,其“感”发言为声,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惠特曼影响的功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异名”其实是一个发声的契机,没有它们,佩索阿的声音也许会很狭窄。有经验的诗人都知道,获得一个声音是多么巨大的幸运,因为这个声音就是诗人的一切,有了这个声音,就有了命定的释放。而佩索阿获取了不止一个声音,每一个声音最后都喷薄而出,呈现出一个大诗人的形象。
佩索阿短暂的一生波澜不惊,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惊人事件,似乎连恋爱都没怎么谈过。但他的作品在这样的异名建构下却如狂涛骇浪,横行不羁,繁复多变,完全是另外一番气象。我们通常会说,伟大的作家构建自己的世界,这句话也许同样适用于佩索阿。佩索阿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构建的世界不像别人那样涵盖在其作品集内,把个人、环境和观念融汇贯通于其统一的作品集内部,被批评家从中辨识出一个处于时代中的个人形象——而这个形象通常是一个高度的综合矛盾体,一个抽象的合理化投射。佩索阿也构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体现在其庞杂的写作中,但他颠覆了统一的“作者”的概念,把“自我”分成许多碎片,抛洒在其世界的各个角落,以其自然生活的松散方式形成宏大的“体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抵御这样的“体系”。佩索阿构建的文本因此从本质上、方向上不同于传统的文本,而是与非文本化的世界共时存在,互为异名,平行交错,造成一个根本的悖论。这个悖论是他最伟大的创举,是在现代社会中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洞见。
跟佩索阿生活大致同时代的爱尔兰诗人叶芝一生纠缠于那些折磨自我的“面具”,叶芝的一生就是不断脱去一层层的面具,剥茧式地最后到达“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对叶芝来说是个艰难的蜕皮的过程。但佩索阿似乎并没有感到被“真理”折磨,也没有任何“真理”意义上的焦虑,这也许是因为他的异名虽然本质上也是自我的投射和割裂的部分,却也相应地承担了其分内的问题、对问题的求索和对现实的体验。佩索阿的“本体”得以隐没不见,在他的异名系统里成为一个不在场的维度。这些异名各自为战,有属于自己的完整的人生目的和方式,其实也是一种历时、历史、历世的方式,是统一性的历史观所不能解释的。 当然,有批评家企图从卡埃罗、冈波斯、雷耶斯三位一体的关系中厘定佩索阿“本体”的脉络,这个也能增加我们对佩索阿的认识;但有一点我们需谨记,这只是很多批评构建之一。佩索阿的成功正在于他的世界里没有佩索阿的作者之本体,如果说其本体可以辨识,正如上文所述,那也只是一个黑洞,所有认识之光都被吸引、分解、偏离。作为读者,我们有一种辨识作者形象的惯性,佩索阿的独特之处正在于阻滞我们的惯性,让我们永远抵达不了“作者”的城堡,即使身体已经在“城堡”之中。
和同时期的很多欧洲作家(叶芝、里尔克等等)一样,佩索阿终其一生对占星学有强烈的兴趣,他和著名的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罗利(Aleister Crowley)通信,后者曾到里斯本访问过他,并在他的帮助下设局假装自杀(有趣的是,克罗里和叶芝曾同属一个叫作“金色黎明”的神秘主义组织,两人之间有过激烈的冲突,但除此之外,佩索阿和叶芝应该没有什么个人关系)。佩索阿给莎士比亚、拜伦、王尔德、肖邦等名人绘制过星盘,也给他的异名制作过星盘,据传说,他还大致准确地预言了自己的死期。跟叶芝一样,佩索阿尝试过“自动写作”。虽然从现有的资料很难具体化神秘主义对佩索阿的影响,但很明显,佩索阿的异名写作,是受到了神秘主义、占星学的很大影响。
同在神秘主义影响的背景下,佩索阿的道路却完全不同于叶芝,叶芝在焦灼中企图弥合、超越相互冲突的人格面具,以达到一个经验主义的统一;佩索阿却根本没把分裂的自我当作问题,他任由分裂的自我在世界上回答自己独特的问题,获取各自独立的生命。完整并非一切,这就是佩索阿庞杂的异名分裂对自我、对整个传统和整个世界做出的更为有机的回答。冈波斯在《烟草店》的开头宣布“我是空无”,但冈波斯的感觉主义同时又是一切,是感觉到一切的空无;佩索阿的本我,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平衡了所有一切的“本质上不在场”的空无。
有人说,冈波斯是最接近佩索阿本人的一个异名。不知道这个判断如何得出的,因为从表面看,冈波斯的风格狂放、恣肆,还曾四处旅行,和佩索阿本人“平庸无奇”的狭小生活反差很大。但我对这个判断是赞同的。冈波斯的张扬和恣肆是在精神世界里的,实现于他的梦想,而非实际行动。虽然他去过很多地方,他出发的“行李箱”却永远收拾不好,他的出发永远在“后天”。他对世界的怀疑和悲观虽然深重,但在碌碌无为的“实际生活”中却总缺乏“勇气”,无法贯彻其悲观哲学,总是在指责自己无法踏出行动的第一步。这种深刻的分裂,应该是佩索阿本人的生活。但也很难想象写出冈波斯这样诗歌的人,在生活中会是一个没有分裂的、完满的功利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冈波斯是最为接近佩索阿的异名的判断,也许不需要更多的文本证据来支撑。即使将来有更多日记、书信等传记材料的支持,我们也很难判断这些日记、书信的背后含义,因为佩索阿本人身处文本的哪个层面,是很难确定的。相反,也许常识上的推断会更接近事实。
本书收录的是冈波斯的诗歌,大部分收录的都是短诗,也包括几首长诗,比如著名的《烟草店》和《鸦片吸食者》,但几首篇幅特别长的颂诗如《胜利颂》《海洋颂》等没有包括在内。希望能呈现出一个有着清晰形象的冈波斯,为读者进一步把握佩索阿的庞大写作世界提供一个入口。必须感谢闵雪飞当年的鼓励和帮助,正是在她的提议下,我才鼓起勇气翻译佩索阿,并从冈波斯的声音里辨识了一部分的自我认同,也从中学到了一些具体的技巧,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当中。附录中的小说《无政府主义银行家》署名是佩索阿“本人”,虽是小说,却有苏格拉底对话的风格,其戏剧性来自对一个荒唐理论的层层剥茧的“推证”,又有点哲理侦探小说的味道。最引人赞叹的是佩索阿在推论过程中的重复修辞、不慌不忙的语调,其语调的平衡微妙、反复腾挪,堪比最好的诗歌。
这些诗大部分都是前几年的旧译,除了在网上零星发表过之外,有一组诗曾在高兴老师的支持下在《世界文学》发表。这次编选除了修订旧译,也补充了一小部分新译。译文参考了英译本,凡是有重复的,都用两个以上的译本互相参译。趁这次结集出版,我把所有的诗,除了个别几首没找到原文的,都参照葡语校读了一遍。当年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学过几年西班牙语,后来读博士的时候学过法语,所以借助工具,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问题。纠正的英译本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的意义错误,个别的错漏行;意义偏离较多的地方,啰唆的地方,参照葡语使之简洁化,去掉英译者的添加,尽量直译。凡是没有把握的,一般保留英译的理解,但有时候也根据上下文做出自己的判断;极个别的地方,不同的英译本理解大致形同,而我根据葡语语境,有不同看法的,也做了相应的修改。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诗都有不同程度的修订,相当一部分的译文相对英译底本有很大改动。修改最多的就是标点符号了,英译本把很多省略号改成破折号,我基本都改回原文的省略号,也根据葡语添加或删去了一些空行。虽然做了这些基本的工作,但肯定还有不少错漏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期待有更全面、更专注的译本问世,特别是能参照手稿进行一些版本校正、异文梳理工作的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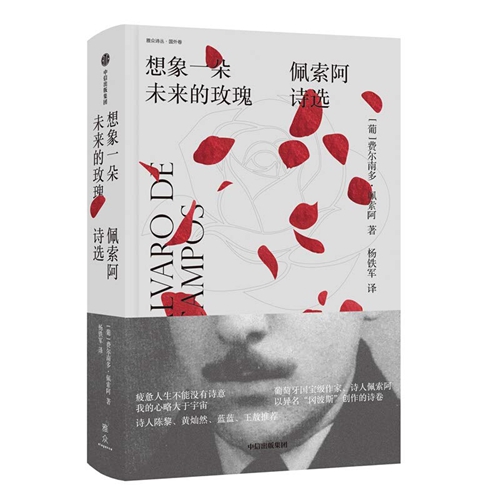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