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郑非评《皇帝圆舞曲》︱一本“过时”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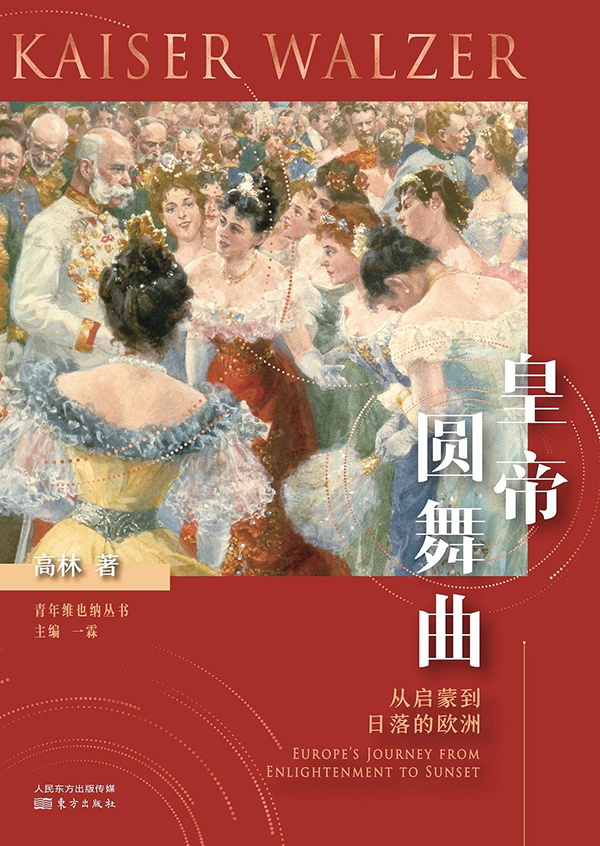
阅读《皇帝圆舞曲》的时候,我偶尔会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作者本人也来自十九世纪的欧洲,多处行文、语气让我想起了茨威格。在那个年代,写成历史文本的语言似乎可以是更华丽一些的。
让这本书“过时”的第二个理由是它所描写的对象:十九世纪。这个世纪有时被人称作“美好年代”,很显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活得有多么畅快、舒适,而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还满怀希望,而这是经历过其后年代的人所不敢拥有的奢侈品。
当然,最能显现本书“过时”的事实是,本书中居然有一篇在认认真真讨论马克思为什么蓄上一把大胡子。这个冷笑话也只有二十世纪后的人才会先疑惑地抬起眉毛,然后咯咯直笑,因为十九世纪的人们只会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自1848年以来,大胡子就跟革命气概联系到了一起。这种思想标志之明显,让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1850年代下了一道法令,规定所有的公务员都要剃须。
这里有幅漫画,讲的是1868年奥地利自由主义改革时期发生的一件趣事——新任内政大臣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着一把美髯。漫画中的大臣走进了一间官员聚集的房间,那群官员惊呼道:“就是他!先生们!一个蓄须的内阁大臣!奥地利完了!”

让法国、奥地利和德国统治者所苦恼的是,他们既不能轻易地把毛发从所有男人的下颌上剃走,也不能忽视国民要求立宪的压力。十九世纪确实是一个美好年代,因为在那个时代,旧制度的统治者虽然把“宪政”和“人民”当成一种威胁,却不会像其后两个世代的继承者那样嘲弄它、戏弄它。
以后人们在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的原因时,往往会指出这么一种观念上的诱因,那就是十九世纪的人对战争持有一种非比寻常的正向观感。他们认为战争犹如森林中的野火,烧去枝蔓,而让树木更健康。如果我们撇去这种言论中所蕴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推断,把它放到十九世纪的历史中去考察,就会发现,当时的人们之所以信奉这种观点,正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真实的。
十九世纪的世界,相对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暴烈,以及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和缓年岁来说,是处于一种低烈度竞争状态中。而正是这种状态让欧洲列国都纷纷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在更严酷的时代,国家来不及进行这样的改革,而在更和缓的年代里,政府没有生存压力也就没有动力来进行改革)。我们能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史上看到这么一个模式一再出现:在一场战败之后,封建特权被废除,个人权利被授予。普鲁士的农奴制是在耶拿会战惨败后被废除的(顺便说一句,黑格尔专门为这次战役写了一本书,称它为“历史的终结”),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改革是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失败后开始的,而俄罗斯专制统治的大松动也起源于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悲惨遭遇。
实际上,不独欧洲国家如此,当时凡有志于自强的国家莫不以立宪为任务。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大做出口加工贸易、靠外资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政治与经济条件,要想增强国力,只能靠国内社会与市场的内在发展。要与列国竞争,就不能不稍假民力。明治维新时日本元老院就在《推进国宪复命书》(1878年)中写道:“(当今世界)以开明兴盛著称的国家均采用立宪之政……不伸张民权,国家则分崩离析,所以君主不能独享其权。因此,欲分享君民之权,使君民之权各得其所,非制定国宪不可。”
既然宪政不可避免,十九世纪的统治者由此进行着一场艰辛的政治园艺工作,企图把它与旧制度嫁接在一起。无论是在法国、德国还是奥地利,都纷纷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最低限度的立宪政体”。这往往意味着有一部被当真的宪法,有一个功能受到极大削弱但仍有一定实权兼吵吵嚷嚷的民选议会,有一个强大的行政机构。这种体制从正面的角度讲,是赋权与政府的自我约束,从负面的角度讲,未尝不可以看作威权人物对政党和人民的某种“驯化”。政治分裂的因子就内含其中。
本书颇具慧眼的地方之一就是指出拿破仑三世、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其实都有某种共通之处,他们既是“最低限度的立宪政体”的设计者与维护者,也都深受其中内含的政治分裂之苦。
比方说拿破仑三世的理想是实现“进步的君主制”。他和他的叔叔虽然都是法国大革命遗产的继承者,但却努力向旧王朝靠拢,做“驯服法国革命的人”。但是帝国的革命色彩让他得不到保守派的支持,皇帝这个头衔又让他与共和派反目。在没有确定社会阶层支持的情况下,皇帝陛下不得不依靠反复的借力打力与政治腾挪。他需要用公决、普选产生的立法团来表示自己受到了人民的拥戴,但又不能真的将之化为政治现实。为了应对这个两难局面,第二帝国需要一个张扬的君主,需要议题政治,需要皇帝陛下用宣传、游行、节庆、城市翻新和外交冒险来吸引他人的注意力,以掩盖他帽子下面那只拿着兔子的手。
作者接着从俾斯麦和威廉二世身上都嗅到了波拿巴主义的味道。
在德意志,霍亨索伦王朝一直有一套防御性弹性改革策略,即主动有控制地进行政治改革,以保证政治的主导权掌握在王室与贵族手里。《俾斯麦回忆录》中有一则故事,是腓特烈·威廉四世当笑话讲给俾斯麦听的。当时俄国同普鲁士还是盟友,沙皇尼古拉找老朋友普鲁士国王借两个低级军官,帮他背部按摩,理由如下:“对于我的俄罗斯人,只要我能盯着他们的脸,就不愁对付不了他们,可是背上没长眼睛,所以我不能让他们到我身旁来。”沙皇本人猜忌其臣民如斯,普鲁士国王无疑引以为戒。俾斯麦自己呢,也否认自己是绝对专制统治的爱好者,他自承,“我一直认为君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应受到一种独立的全国性代表机构的监督”,以免君权肆意妄为。
不过,尽管王室与贵族都承认,有必要让普鲁士——德意志臣民享受一定的经济自由、私权保障乃至政治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决定将政权拱手相让。他们所希望的建立的这个体制,是“君主民辅”。根据1871年帝国宪法,帝国立法机构由两院制议会构成,分成上下两院,上院是联邦议会,由各邦派出代表构成,掌握实权。下院才是普选出来的帝国议会,权能很小。官吏任命、军队统率、内阁组成均不在帝国议会权限范围内。帝国议会的最大权力在预算方面,它可以同意或者拒绝政府提出的预算。不过,即使它拒绝,政府还是可以仍然按照上一年的财政预算获得资金,而不至于断粮,有学者因此讽刺说,帝国议会是一个“没有政府的议会”,此言非虚。
对霍亨索伦王朝来说,帝国议会的真正作用在哪儿呢?它是一条护城河,能够吸收并缓冲德意志人民的政治热情。第一,它让大家能有个念想,消停消停;二,为政府提供合法性;三,最重要的,当时德国社会是很多元的,各邦有很强的地方主义情绪,又有新教徒天主教徒的对立,再加上城乡差别,帝国政府预计将看到社会上多个阶层、集团或组织将为了选票而互相斗争,帝国政府可以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四,它制造一种渐进主义气氛,给政府以从容布局的时间、空间。
“德国就是如此四分五裂,以至于无法形成重要的利益共同体,为有效的政治统治提供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工具性宪政”所蕴含的分割对抗性质,才让俾斯麦有机可乘,可以利用皇帝与议会的矛盾,来让自己数十年大权在握,让威廉一世笑称自己是“在这样一位宰相手下当皇帝”。只有理解这个逻辑,才能明白作者对俾斯麦的下述评语:“(他)背靠君主来压制议会,又反过来用议会控制君主”“俾斯麦满足于依靠帝国议会各党派的的分裂和不团结,利用他们各自的利益矛盾,来操纵帝国议会的票数推动自己的统治时,他就成了一个帝国宰相府里的拿破仑三世”。
至于威廉二世,在作者看来,恰恰也是拿破仑三世的翻版。他的个性与早年境遇并不能充分解释他那些变化不定的决策,那些极富鼓动性质的帝国叫嚣。帝国结构性的政治分裂才更有解释意义。他是个宪法君主,但是这部宪法本身在设计的时候就故意留下冲突的隐患。像俾斯麦那种高手自然可以在这些冲突间游刃有余,乃至利用这些冲突掌握权力。但威廉二世并不在此类高手之列。他应对政治困境的方法同拿破仑三世一模一样:直接跳过现有的政治机制(议会、宰相府与政党)向民意喊话,以民众的真正代表自居。他扑向一切能引发民众支持率的政治议题,做出相互矛盾的表态。于是,在那个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的年代里,他成了帝国主义的推动者与代言者。原因无他,威廉二世和拿破仑三世一样受制于分裂的国内政治结构,只能用表演取代统治。而还有什么表演比挺胸昂首、旌旗招展与外人对抗更鲜明夺目呢?他们的结局也一样,将各自的国度贸然带入了一场并无必要的军事冒险之中,并最终摧毁了自己。
所以,高林这本“过时”的书向我们展示了那个过去时代的一个历史机制——最低限度的宪政机制并不能保障王朝万世长存。俾斯麦有一次给他妻子写信说:“在地球上所遂行的事情,总是有一种堕落天使的特质:漂亮,却不意味着和平;概念伟大,也付出极大努力,亦不表示成功。”此事正是如此。
当然,这本书还讲了其他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我太懒散了,就不赘述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