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莱布雷希特专栏:所有伟大的音乐都在疯狂的边缘摇摇欲坠
1942年8月,当列宁格勒街头遍布消瘦的尸体,德军的枪炮声不分昼夜炸响的时候,斯大林决定了当时列宁格勒最迫切需要的,是听到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这部雷鸣般的巨作几个月前在古比雪夫首演,这是俄国的一个内陆城市,作曲家本人当时被疏散至此。这部交响曲已经登上了英国和美国舞台,分别由亨利·伍德和阿图罗·托斯卡尼尼指挥,两场音乐会通过无线电波响彻各地。而在德军围城之下,在列宁格勒奏响这部交响曲,既是对敌人的蔑视,也是宣传的胜利。
这座城市的广播乐团已经只剩18名演奏家,他们用音乐教师、离职演奏家和业余乐手填补了空缺。这场音乐会由卡尔·艾利斯伯格指挥,于8月9日举行——这是希特勒原定要攻下列宁格勒的日子,演出的实况通过巨大的高音喇叭向德军阵线播出。在这样的音乐下,据说有一位德军军官低声嘟哝:“我们永远无法打败这样的人。”虽然围城又持续了18个月,列宁格勒终未陷落,德军被迫后撤。

几近60年后,一位名叫斯蒂芬·约翰森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了当年参加列宁格勒这场演出的单簧管演奏家,维克托·科兹洛夫,询问他如今听到这首“列宁格勒交响曲”的感受。妻子陪伴在旁的科兹洛夫难以抑制自己的眼泪,他哽咽着说:“这无法表达。”
这一直触事实的体验,促使约翰森先生对音乐作品对其演奏者和聆听者的生活和思想能够产生的拯救性的作用,进行了深刻而个人化的考察。我们可以从约翰森先生的书中了解到,他也深受某种极端状况的困扰。他在一个无法正常运作的家庭中长大,父亲患有抑郁症,具有暴力倾向的母亲患有严重人格障碍。在他的回忆中,童年时“我必须把自己锁起来,才能避开情绪不稳的母亲……如果我当时能够表达出我下意识地对自己反复的教条,那就是:‘我一定不能感受到,我一定不能感受到。’”
他说,音乐,是唯一可以让他放纵的空间。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约翰森先生发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四交响曲》,作曲家在遭受到斯大林针对他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进行的攻击后,将这部交响曲束之高阁长达25年。约翰森将这部交响曲牢记在心——并陶醉于其“可怕的情绪波动”和明确存在的威胁中——使得这部交响曲成为了他骑车上学时脑海里的背景音乐。他身兼治疗师的妻子补充道:“与你的母亲一起生活,肯定就像那部交响曲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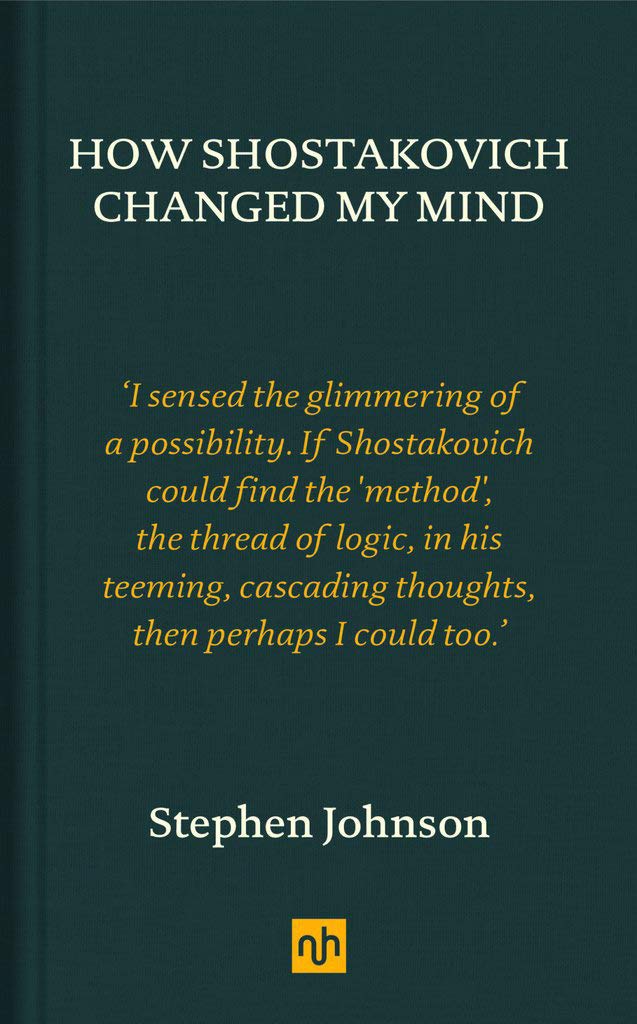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四交响曲》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创作,以保护自己的理智,并隐秘地反映那些大规模的逮捕和杀戮——就像约翰森所说,“与他所反映的情感保持着一两度的距离。”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肖斯塔科维奇曾经为这部名剧配乐)里所说的那样:“虽然这很疯狂,但其中却有一套方法。”作曲家找到了一种为疯狂寻求意义的方法。“如果肖斯塔科维奇可以找到‘方法’,”年轻的约翰森想到,“那么也许我也可以。”
这本书里接下来是对约翰森先生所认定的这位“记录下了一个兼容并包的听众集体体验”的作曲家主要作品的一份非常饶有兴味又高度个人化的分析。音乐中闪现的黑色幽默减轻了悲剧的沉痛。《第八交响曲》中的一段短笛独奏针对的是悲剧时期个体的荒谬。《第十交响曲》创作于斯大林临终之时,在其标志性的主题中包含的暗示体现了作曲家的蔑视和解脱:“我还在这!”
当母亲最终被送进疗养院时,约翰森先生写道,他就像是斯大林去世时的肖斯塔科维奇:“对我的指控都已崩溃。现在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我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即使我再也不会指责自己的空想了。”任何经历过一个充满虐待的童年并得以幸存下来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时刻,此刻救赎终于看似可能,生命终于可以存活。
现代心理学中有一种理论提到“内心的极权主义客体”,在这种理论中,精神借助外在的邪恶来打击自我迫使服从。这样的客体仍然在俄罗斯人中间存在,表现为对于强大的斯大林的隐秘景仰。约翰森对他的疯狂母亲也是感到爱憎交集。
他在反思肖斯塔科维奇《第八交响曲》时写道:“当我回顾我早期家庭生活的奇怪折磨时,我似乎听到音乐在说:‘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责备是一种赋予生命意义的方式,但是它让我们成为了囚徒。”在《第八弦乐四重奏》中,他听到的暗示意指作曲家正在考虑自杀,但在同一个黑暗的地方,它却向约翰逊先生抛出了一根救命的缆绳。
所有伟大的音乐都在疯狂的边缘摇摇欲坠。这位曾经身处困境的作家展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有助于拯救他的精神。他表示,在人生危机中,我们每个人都面对内心深处的一场列宁格勒围城战,而音乐能够成为我们的解脱。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