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 +1152
从斯科特到格雷伯:无政府主义与人类学
在“无政府主义与人类学”这个题下可以讨论的内容有很多。这里所处理的问题,不是作为政治思想的无政府主义与人类学这一学科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关于追求无政府理想的运动的人类学研究。本文的讨论将仅限于对世界各地实际存在着(存在过)的无政府社会,也即“不存在统治者的社会”所进行的研究。近年来出版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相关的人类学著作。或许一些读者有意无意地感到“无政府主义最近好像成了人类学那一挂的关键词了”,这也都归功于这些著作的作者大卫·格雷伯和詹姆斯·C·斯科特。那么,在运用无政府主义这个看似时代误植的词语时,这些作者是如何重新理解那些被他们如此描述的他者的?而通过对这些他者的理解,他们又如何引申出自己所处的社会所具有的可能性?这些便是这篇短文的主题。
人类学史中的无政府主义
首先要指出的是,无政府主义不是最近才成为人类学中的主题的。即便不用这个说法,人类学一直进行着关于现实中存在的无政府社会的研究。与断定“没有国家的社会必然无序”的霍布斯一派政治哲学不同,人类学研究实证地表明,没有国家的社会实际上是可以维持存续的。
无政府主义与人类学的联系并不仅限于个别研究者。要说明这一点,现代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拉德克里夫-布朗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青年时代曾倾心于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家克鲁泡特金,有着“安那其·布朗”(Anarchy Brown)的诨名。但他在成为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泰斗后便沾染上了贵族式的趣味,把名字也改成贵族风的拉德克里夫-布朗了。然而即便他在个人信条上不再是无政府主义者了,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也即认为各要素的有机结合可以保证(作为当时人类学对象的“土著”社会的)稳定统合的观点,仍可以被看作是无政府主义式的,显示了无国家社会的可能性。

明确地将对无国家社会的关注理论化的工作,是拉德克里夫-布朗之后一代的人类学家们完成的。在《非洲的政治制度》(原作初版于1940年)中,福蒂斯与埃文斯-普里查德将非洲的各种社会类型化为“存在政府的社会”与“不存在政府的社会”。毫无疑问,非洲当然也有“存在政府的社会”,其中存在着由权势者、行政和司法所组成的中央。然而在以南苏丹的努尔社会为代表的“不存在政府的社会”中,又是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的呢?埃文斯-普里查德从裂变分支体系中找到了答案。宗系集团内部一分为二,随后再一分为二,以此类推。这样一来,各个层级都分歧为平等的对抗性集团,直至家庭为止,秩序便通过各层级集团间的平衡而达成。不存在下裁决的权势者,纷争的解决由仲裁者中介推动。也就是说,那里存在着的是一种无首(acephalous)却并非无序的“有序无政府”状态(ordered anarchy)。
这样的裂变分支社会不仅非洲有,还存在于其他很多地方。然而,也存在着像大洋洲这样不符合该模型的地域。那里有另一种类型的无国家社会,在其中,无继承制的群众领袖大人物会展开相互竞争。像这样,人类学家在世界各地探索着各种类型的无国家社会。正如格雷伯所言,“人类学家是唯一了解现存没有政府的社会的学者”。
赞米亚的无政府主义者们
那么近些年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在传承过往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什么新内容呢?让我们以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为例来展开讨论。为此,首先要说明一下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的“对抗国家的社会”这个对斯科特影响很大的想法。克拉斯特分析南美原住民社会认为,初看之下这里仿佛是国家“尚未”确立的落后社会,但这其实是积极阻止国家诞生的行动所促成的结果。根据克拉斯特的分析,通过这种并非内部分化而是外部细分化的过程,社会与国家不断展开着“抗衡”。
斯科特以同样的视角,考察了居住在从中国到东南亚的山岳区域(即赞米亚)的山地居民。他指出,这些民族并非是我们落后的“先祖”。他们毋宁说是从国家的统治中逃走,并有意识地选择了与国家体制相对立的生活方式的人们。他们松散地居住在远离国家中心的险峻山岳间,从事着狩猎采集、刀耕火种等便于移动的营生,以此来躲避国家的支配和掠夺(奴役、征兵、缴税、强制劳动等)。除了“躲避国家”以外,为了避免自身社会内部出现类似于国家的阶层结构,斯科特认为这些山民也同时在进行着“阻碍国家”的实践。山民们将以汉人为首的低地居民与自身对照看待,主张“他们有大王,我们有平等;他们被课税,我们不用交;他们像奴隶,我们多自由”,基于这种认识来形成平等主义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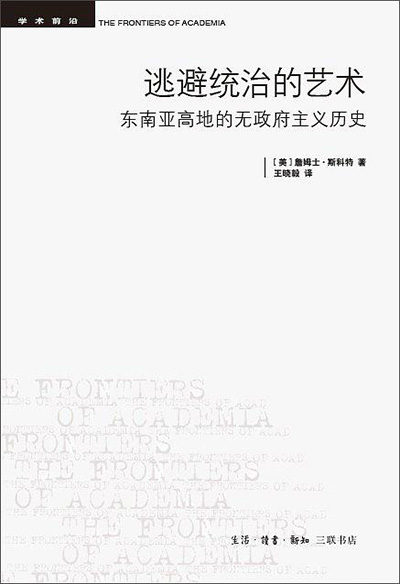
斯科特暗示赞米亚并非个案,这样的生成进程可能存在于世界各地(如逃亡奴隶在加勒比海地区密林中形成的共同体)。就此,斯科特提出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这样一种耳目一新的理解思路:不是像过去那样把这些社会视为愚昧落后,而是认为那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然而与此同时,斯科特又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这类非统治空间已几乎绝迹。他指出现代世界是一个“整个地球都是‘行政空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边疆仅仅在传说中存在”。
格雷伯——无政府主义的连续性
斯科特的观点清晰明快且铿锵有力,引人共鸣。我们或许也会将其与令柳田国男心驰神往的山人联系起来,开始思考日本的赞米亚吧。然而与此同时,斯科特的研究中,“不受统治的他们”与“受统治的我们”被切割开来看待,有种将前者浪漫化为已逝的往昔存在的倾向。如此一来,他们的故事到头来仍旧对我们关于生活方式的追问无甚助益。与此不同的是,格雷伯则尝试对隔开前现代和现代的“思考屏障”实施爆破作业,分析两者之间具有的连贯性。让我们在与斯科特的对照之中,看一看格雷伯在《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里勾勒,并在后来的论文或著作里展开的部分主张。

第一个问题在于,“他们”是否真的是些只知道反对国家的怪家伙?斯科特主张一些人会通过反制国家而形成无政府社会,格雷伯认为这种想法虽然没错,但却不够全面。通过对等级制实行“创造性拒绝(creative refusal)”能够创造出平等主义的社会,对这种观点格雷伯也是认可的。然而在斯科特的认识中,创造性拒绝的运动始终是从国家朝着无政府过度的单向进程。而格雷伯则认为“创造性拒绝的行为有时朝向新的平等理想,有时又导致新的等级形态,又或者向着两者复杂的混合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不仅有反对国家并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也存在着向往并模仿国家的进程。
确实,这种两义性在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中提及的各民族中也看得到。山地居民并非只有抵抗国家的平等主义志向,而是会在等级制(国家)的诱惑与平等主义之间举棋不定。笔者就自己近年来研究的赫蒙族(Hmong)的情况重新确认斯科特依据的文献时,发现他们当中也存在这样的动摇。赫蒙族人虽然确实反对国家的支配,同时却也羡慕有国家体系的支配民族。因此,他们把自己社会的平等主义,看成是由于内部对立而无法团结一致的否定性的状态,并期盼随着领袖人物的出现,当前状态会被克服并建立起“赫蒙之国”。也就是说,赫蒙人的无政府主义并非单方面地否定国家,而是始终摇摆于憧憬和反抗之间。
格雷伯认为,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之中,一直存在着在多种不同选项之间的摇摆。在他与考古学家温格罗共同撰写的论文里指出,石器时代的人们会经历社会的季节性变化(seasonal variations)。也就是说,包括莫斯分析过的因纽特人在内的许多社会,会在夏季与冬季采用完全反转的社会形态与价值观。因纽特人在夏天会散居各地,家长制权威成为绝对的强制性力量,到了冬天则聚居一处,以个人能力而非血统来决定首领,首领的职权仅限于调停利害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夏天是等级制而冬天是平等主义的。因此,生活在这些社会中的人们非常清楚存在着对立的社会形态,以及与此相应的对立的政治及道德价值。因而可以认为,他们是在对政治的多种可能性有着自觉的基础上,不断地对社会形态进行着再编成。
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再说他们从根底里便是平等主义的,而我们骨子里是等级制的,或者说他们生活在没有不平等的黄金时代,而我们已然丧失了那份纯真。对于应当采纳何种政治形态这一知识课题,我们都在踯躅中不断思索着,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相同的。
第二个问题是,世界是否真的由于国家的存在而变成“被统治的空间”了?如前所述,斯科特基本是这么看的。而格雷伯则相反,指出即使国家“宇宙论式地”将自己呈现为支配一切之物,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具备实际统治社会整体的力量。“主权”(sovereignty)作为发号施令并以惩罚相威胁的能力,实际上在很多社会中都在时空范围上受到限制。北美的诸原住民社会中,作为神灵的现身、代理性质的存在(类似于小丑)仅在典礼期间能够行使主权之力,此外的时间中谁都无权这么做。即使是密西西比的原住民纳奇兹人、南苏丹的希鲁克人这类国王看似拥有绝对主权的社会中,权力所及的范围实际上也仅仅局限于很小一部分空间,无法伸展到该区域外人们的日常生活。面对国王那种宛如神明的无常暴力,民众们会借助礼仪和禁忌的手段将其五花大绑,通过“反向神圣化(adverse sacralization)”的方式加以禁锢。
在官僚制度发达的现代民族国家中,情况也与此类似。不同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宇宙论式的印象,无政府空间在事实上是有存续之余地的。以格雷伯做田野调查的马达加斯加为例,在经历1980年代的财政危机之后,市政、警察不再运转,地方上的国家统治系统瘫痪了。尽管如此,人们通过沟通对话的方式决定各类事务,照常维持共同体的日常生活。该共同体对于领导者的命令以及工资劳动关系采取否定的态度,在此意义上,它完全可以被视为无政府主义式的。
这种状态,在非洲等地的后殖民地社会中确实表现得更为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北方”各国与其完全无缘。正如格雷伯所言,很多人的行动没有采取揭竿而起反抗国家这样引人注目的方式,从而并不为人所知,但或许他们也都在千方百计地尝试着形成无政府的串联,并日复一日地创造出全新的组织化生活方式。这么看来,我们不应该以“有”或“没有”统治这样的二分法来思考问题,而是可以用更加细致的方式,连贯地描绘出“他们”和“我们”为保卫无统治的空间而做出的努力。
我们身边的无政府主义

笔者所在调查的法国赫蒙族难民也可以作为与我们相连贯的无政府主义的实例。1970年代后半期作为老挝难民前往法国的赫蒙族们,起初作为工厂里的体力劳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里。然而此后,其中一些人不满于工厂的命令服从制度,在1980年代后期再次移居至法国南部,开始从事农业活动,从而得以保障自己的自由与独立(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些人以非正式的实践来想方设法地逃避国家的干涉,至少“部分地”维持了自律的领域。正如斯科特所刻画的那样,“逃避国家”始终是他们的行为动机所在。同时在共同体内部,他们也始终注意避免等级关系的产生,保持着平等主义。但是这种“阻碍国家”的倾向也并不一定总是受到肯定的。他们也会遗憾地认为“就是因为我们总在相互拖后腿,所以才无法形成自己的国家”,并期盼着足以超越各方对立的领袖人物的出现。
由此可见,就在精神上距离你我并不遥远的地方,在“受国家的蛊惑”和“对国家的反抗”之间的举棋不定中,无政府主义的生活方式今天仍在不断生成。我们不必非得认为这在道德上便是好的。然而通过尝试理解这些他者,我们或许能将自己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放入更广阔的语境之中来加以想象。回想一下便会发现,正如格雷伯与斯科特都在说的那样,无政府主义实践的萌芽,就生长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中。
(原文刊载于『現代思想』2019年5月臨時増刊号「総特集=現代思想43のキーワード」青土社。作者中川理是人类学家,立教大学异文化交流学部准教授。)













- 23人受审
- 外交部回应越南改造我柏礁岛
- 2025稳外资行动方案来了

- 苹果发布iPhone 16e,4499元起售
- 牧原股份声明:未收到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发出的调查通知,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 pH值为7的溶液是什么性质?
- 指在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传播资讯的新媒体,经营者多为普通网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