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张卜天︱《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③:重建伊甸园,统治地球
本文系作者2018年12月4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未名学者讲座”上所作的题为“《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释经学与近代科学的兴起”的讲演,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整理录音,《上海书评》丁雄飞编辑改写,作者审定。全文分三部分发表,这是第三部分。
七
字面主义以两种方式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兴起。除了排空自然物的含义,另一种方式是把《圣经》关于创世和堕落的叙事,理解成人类需要重建对自然的统治。
按照基督教的看法,人类遭受了三大灾难。第一大灾难是堕落。堕落首先导致人类失去了亚当堕落之前的完满知识。据称,亚当堕落之前无所不知,他可以看到最遥远的星系,看清最微小的事物,而堕落剥夺了这些能力。其次,堕落使造物之间产生了冲突和纷争,动物之间开始互相攻击,一个物种以另一个物种为食。最后,地球不再能够产生完美的动植物,人类不得不种植粮食,连地球的土壤也败坏了。

人的堕落为什么会让造物和地球也跟着受牵累呢?难道堕落不是纯属于人的事情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一点可以从《圣经》中找到根据。在《创世记》里,神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3:17)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3:18)……”
后人把这段话解读成地因为人犯了原罪,吃了果子而遭到败坏。《罗马书》也有一些相关的讲法。德国作曲家巴赫有一首管风琴曲的标题就叫Durch Adams Fall ist ganz verderbt:“万物因亚当的堕落而彻底被毁灭”——后半句也可以译成“完全被败坏”。由于亚当的人性堕落,品性败坏,同样的“毒药”为后世所继承。人如果没有来自神的安慰,便不再能够恢复健康。这是西方基督教传统里一个非常普遍的理解。
第二大灾难是大洪水导致的。大洪水使地球的形貌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山脉和裂谷,海啸和地震。大洪水之前的地球是一个光滑的球形,而之后,土地不再肥沃,人的寿命变短,人和动物的身材也下降。我们不是听说古代有巨人,有恐龙这样巨兽吗?

第三大灾难是语言变乱,也就是《圣经》中的巴别塔故事。人类本想建一座通天塔,后来神感觉到了威胁,就把人的语言变乱了,他们至今无法交流,塔便建不成了。语言变乱以后,人类与亚当、与人类先祖的语言联系就被切断了,此后所有语言都是约定的,不再能够从事物名称中读出事物的本性。西方人认为只有亚当说的话才是唯一完美的语言,通过词就可以解读出物的含义。

新教改革家特别重视原罪。马丁·路德说,“亚当堕落后,凭借人的理性是不可能理解自然的,由于亚当的堕落,理性被败坏了”(《布道集》)。加尔文说得更严重,认为“那些在其他方面异常敏锐的哲学家”——他特指没有受过基督教教育的亚里士多德——因为“不晓得人性的堕落”,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堕落是彻底、全面的败坏,它“不止存在于一个部分,而是遍布整个灵魂和它的每一个官能”(《〈创世记〉评注》)。亚里士多德因为不知道人的堕落,盲目相信自己的感官,便轻易地以为重物落得比轻物快。帕斯卡在《思想录》里说:“我们渴望真理,在内心中却只觅得不确定性。……这种渴望留给我们,部分是为了惩罚我们,部分是为了让我们觉察自己是从哪里堕落的。”在重视原罪的人看来,求真、求知并不完全是好事。一个人之所以渴望、追求真理是因为他缺乏真理,是他有缺陷、不完满的体现。
培根在《新工具》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话里指出,
人因为堕落而同时失去了天真无罪的状态和对造物的统治。然而,这两种损失在今生都可以得到部分程度的弥补;前者是通过宗教和信仰,后者是通过技艺和科学。
《新工具》
由此可见,在培根这里,科学和宗教非但不是相互对立的,反而携手并进,服务于几乎相同的目的——恢复人因堕落而失去的完美的状态。只不过宗教恢复的是人的天真无罪的状态,科学技术是为了使人重获对造物的统治。
《创世记》里说,神要亚当“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1:28)。然而亚当在天真无罪的状态下对自然的管理或统治(Dominion),按照中世纪的寓意理解,并不是使万物臣服于他的意志,而是指他掌握万物的多重含义。根据寓意诠释,自然物是有含义的,恢复亚当原有的统治,在于从心灵上掌握自然的神学含义,并且控制、降服人这个小宇宙内部的动物——兽性的激情,从而更好地用理性来思考和生活。但是到了十七世纪,这种理解发生了彻底转变。在培根看来,哲学的真正目的是改变世界,而不是改变灵魂——他从内在转向了外在。培根说:“寻求知识不是为了获得宁静,而是为了恢复和重新赋予人……在受造之初所拥有的统治和权力。”可以说,培根第一次系统地尝试把哲学家的主要关注点,从如何道德地生活,变成如何对自然过程进行理解和重构。他最鲜明地表现出从沉思的生活(contemplative life)向行动的生活(active life)的发展。过去的“统治”是自我统治,而到了十七世纪,它被理解成统治现实的自然界。
于是,与堕落相伴随的物理损失,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弥补。可以说,人的使命有二:一是通过认识世界来模仿神的智慧,二是通过操纵世界来模仿神的力量。这两件事都是为了恢复与神的相似性。或许可以把认识世界、模仿神的智慧对应于科学,把操纵世界、模仿神的力量对应于技术。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些增强人类有限观察能力的工具,在十七世纪被发明出来,并非只是技术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背后还有很深的神学背景:用这些仪器来辅助人败坏的感官,以接近亚当堕落以前完满的感官状态。

与此同时,有人开始模仿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时的饮食习惯。一般认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是吃素的,这就为素食主义找到了某种历史渊源。也有人采用亚当的原始穿衣方式——不穿衣服。英文有一个词Adamites,亚当派,意思就是“裸体主义者”。还有一种弥补堕落损失的方式是通过园艺和农业来治理、修复地球。园艺业兴起于十六世纪,当时许多富贵人家自建园子,自己决定选种的植物,以及植物排列的形状,这就是小规模重建伊甸园的尝试。甚至现代博物馆馆长也以诺亚为原型,将世界各地搜集来的物品置于博物馆内,这亦是试图模仿或恢复原始诺亚的形象。园艺业扩展到更大范围就是农业。在一些人看来,耕种土地可以补救大洪水对地球造成的伤害,而荒野和空地代表杂乱无章,反映了这片土地上居民的堕落。例如美洲大陆的土著,就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土地,致使大片土地荒废,说明他们是“懒惰的民族”。其实对于殖民的主要授权,就是神对亚当的明确命令——“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世记》1:26-28)。我们的教科书里通常把殖民归为资本主义的贪婪,但其背后还有神学的理据——对于《圣经》里治理土地的字面理解。如果原住民没有尽到责任,管理好所属的土地,那就需要殖民者帮助管理。占领、保管和使用土地于是演变成了土地私有化原则,洛克后来在《政府论》等著作里有很详细的阐述。

为了扭转巴别塔之后语言变乱的损失,一些人试图重新发现亚当的语言,或者发明一种类似的符号系统。早期的尝试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征象”(signatures)学说,即认为自然物带有某种标记表明其用途。比如有的核桃长得像大脑,有的豆子长得像肾,它们这样长一定有其含义,好像一种原始的、自然本有的语言符号。但由这种语言可以解读出的内容太少了,这个尝试并不成功。第二种尝试是手势语言。聋哑人听不见,说不出话,发出的声音比较自然,他们的手势仿佛不受人为的干预。第三种尝试是体征语言,它基于人的头颅、面相、手相等自然赋予的特征。除此之外,有人相信亚当说的语言仍然存在于世界的某个地方。其中一种观点就认为汉语是亚当的语言。在一些欧洲人看来,中国特别遥远,或许没有承受巴别塔一事的后果,但后来又有人提出异议:汉语特别难学,一个人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几年,可能也只能学到非常低级的水平,而自然语言不该那么难学,所以汉语绝不可能是自然语言。当然也有类似的认为希伯来语或古埃及语是自然语言的观点。
如果寻找原始语言的希望最终落空了,人们就退而求其次,试图发明而不是发现一种普遍的语言和文字。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一部著作是莱布尼茨的《论组合术》(Dissertatio de arte combinatoria,1666)。在1679年的一封信中,莱布尼茨把他的普遍语言计划称为“伟大的理性工具,它对心灵力量的推动将会超出望远镜对视觉能力的推动”。他又说,“纠正我们推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使之像数学家的推理一样确凿,从而使我们可以瞬间发现错误,当人与人之间发生争论时,我们可以径直说:让我们算一下,看看谁是对的”。在他看来,两千年的哲学史没有解决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概念不清,所以要设计一种理想的普遍语言来避免争论。这一思路也可以被视为计算机的雏形。人类寻求完美的、原始的自然语言的尝试其实是一个极其有野心的计划,旨在彻底地解决一切问题。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世界语——把现有的几百种语言加工成一种最好的、最理想的语言——仍旧延续着这样的诉求。

八
“自然之书”这个概念在十六、十七世纪依然存在,但它的含义已经和过去全然不同。这时的人们强调,自然之书优于人写的书。自然是一个普遍的文本,在编写《圣经》之前很久就有了自然,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族群的人都能读到它。对于自然之书的诠释,也不太有争议,因为所有人都可以面对简单的自然神学,自然哲学家可以扮演祭司的角色。宗教战争在十七世纪异常残酷,围绕《圣经》理解的分歧也是冲突的滥觞之一。十七世纪的许多人相信,“自然”是一个比启示更好的宗教权威。自然哲学家遵循某种意义上的自然宗教,用自然之书取代《圣经》之书,把前者视为最高经典。自然宗教将向所有人开放,易于理解,不会导致宗教战争。
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然无法提供救恩知识,因此才需要在《圣经》中寻找更直接的启示。从自然中只能推断出神的某一些品质,研究自然之书只是“神学的准备”。过去,自然之书和《圣经》之书完全绑在一起,理解《圣经》不能脱离自然,理解自然也不能脱离《圣经》。但如今自然之书和《圣经》之书完全分离了,光凭科学研究找不到启示,推不出神是如何拯救人类的。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点,牛顿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教义,因为从自然之书中读不出这样的教义。三位一体在十七、十八世纪成为流行议题,便与上述背景有莫大的关系。十三世纪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波那文图拉(1221-1274)曾说,“受造世界就像一本书,创造性的三位一体反映、呈现和书写于其中”。但到了培根的《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相关的论述则是:“正如所有制作物都显示了工匠的能力和技巧,而不是它的形象;因此,神的作品也显示了造物主的全能和智慧,但不是它的形象。”所谓神的形象即神的救赎的意志,《圣经》揭示神的救赎意志,自然揭示神的能力和技巧,二者分工不同。这样的理解和中世纪的理解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


福柯在《词与物》里说,十七世纪的知识基础经历了从基于相似性的诠释系统,到基于“分类学”(taxinomia)和“数学”(mathesis)的诠释系统的转变。所谓基于相似性的诠释系统,可以理解成基于寓意诠释和寓意解经的象征世界观;而基于“分类学”和“数学”的诠释系统”,“分类学”可以对应于自然志,“数学”可以对应于(数学化的)自然哲学。于是,现代科学的起源和发展,就是从象征的、寓意的世界观,到自然物失去象征含义后,分成两支——自然志和自然哲学,由它们来重新组织自然物,这二者分别对应于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这两大现代科学的分支。而自然之书的可理解性,亦相应地从关乎自然物的象征属性,变成了关乎分类学秩序和数学秩序。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自然志和自然哲学汇聚在一起,开拓出现代科学的地盘,成就了现代自然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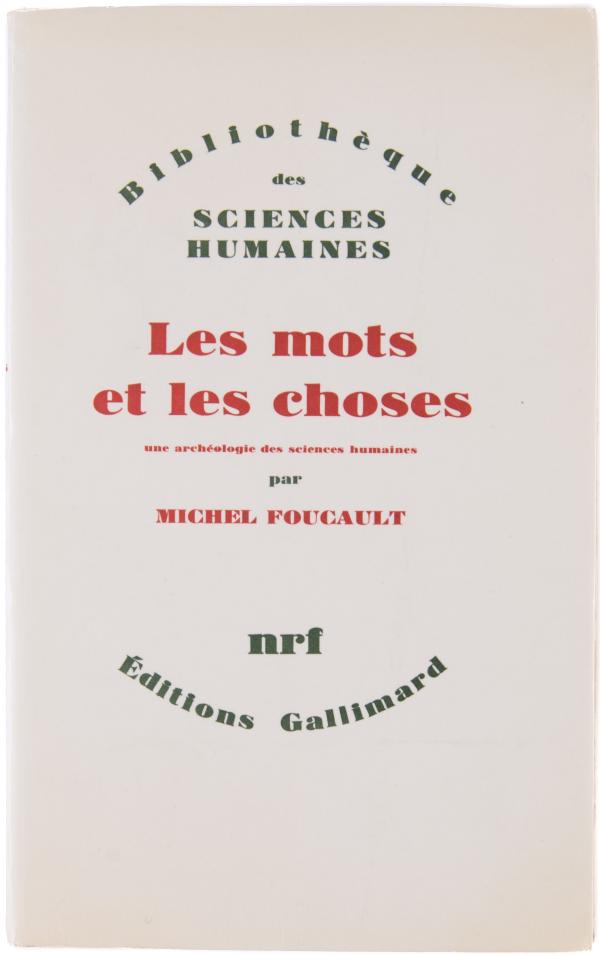
可以说,在新的自然语言中,句法(syntax)战胜了语意(semantics)。“语意”即词的含义,是中世纪的寓意世界观所重视的。“句法”则强调词与词的关系,在现代数学的语言和分类学的语言中,物与物的关系是第一位的,物本身已经失去了含义。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里论证说,从自然事实中推不出价值。这进一步损害了自然的道德权威性。休谟还认为,按照传统的设计论证,从自然的特征中也得不出任何重要的神学结论。一百年后,达尔文说,生物的奇妙机制并不能为一个神圣的设计者提供证词,而是体现了数百万年来偶然事件的最终结果。达尔文之后,设计论证和物理神学便彻底衰落了。这种严厉的推理思路的产生,是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失去象征能力的又一个后果。神及其活动无法直接从自然中读取。
由此可以说,自然之书和《圣经》之书这“两本书”,发展出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牛顿是一位极其伟大的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但他不满足于在这两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反而将大量精力用于炼金术和《圣经》研究,他有志于重新统一词的科学和物的科学,统一科学和《圣经》诠释。人们总说牛顿晚年研究神学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其实牛顿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神学,他想要成就的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事业,这种抱负远非常人所能理解。占星术、命理学、观相术等神秘学思潮总是一息尚存,或在不同的时代经历复兴,这表明人类依然渴望与自然界重新建立起联系。两本书的分离每每搅扰着人心,隐含着帕斯卡所说的最深的恐惧。
我在美国的导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在他的科普名著《宇宙最初三分钟》里说:“宇宙越显得可以理解,它就越显得没有意义。”科学虽然能从宇宙中清晰地解读出许多定律,但却和人没有关系,我们无法从中获得意义,这是每一个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科学思想史的先驱柯瓦雷在《牛顿研究》里写道:
在科学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唯独人失去了位置。于是,科学的世界变得与生活世界疏离了,并与之完全分开,生活世界是科学所无法解释的。……两个世界:这意味着两种真理。或者根本没有真理。……这就是近代心灵的悲剧所在,它解决了宇宙之谜,却只是代之以另一个谜:近代心灵本身之谜。
《牛顿研究》,[法]亚历山大·柯瓦雷著,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出版,453页,79.00元
在科学的世界,尤其是数学的世界里,没有人的立足之地,笛卡尔的学说亦无法安放人的灵魂。人虽然可以解释宇宙万物,可以解释一切,却唯独没有办法解释他自己。帕斯卡在《思想录》里说:“现代人的所有不幸都可以归结为一点:不知道如何安宁地呆在屋子里。”也就是说,在数学的、同质的无限空间中,现代人的心灵无处安住。柯瓦雷和帕斯卡的这两段话最清楚透彻地揭示了现代人焦虑的根源。我们无法解读出自然的意义,那人生能解读出意义吗?一切都失去了更高的意义。虚无主义或许就植根于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疏离,或者说《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的分离。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