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廖涵:探寻明清江西之社会内涵——读《矛与盾的共存》
一
江西,对活在当下的人来说,她给人的印象是经济不发达、人口外流、观念保守,除了绿水青山,似乎别无长处。然而,对历史学家而言,江西却是另一番场景:唐宋时,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名家辈出;在近代,豪情万丈,铁骨铮铮,是共和国之摇篮。明清时期的江西则难以概貌:一方面,经济发达,城市繁荣,文化昌盛,进士及第人数可同江南地区比肩;另一方面,人口剧增,流亡四方,社会涌动,大大小小的地方性叛乱此起彼伏。如何进一步认知明清时代的江西社会,是摆在江西历史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韩国历史学家吴金成教授所著《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简称《矛与盾的共存》)一书,通过多角度的考察,指出明清江西的总体特征是“矛盾的社会”。作为一个韩国学者,吴教授选择明清江西社会为研究对象并无特殊原因,仅是为了深化其早年有关明代湖广的研究。在探索“明代江西地方水利开发与绅士”问题的过程中,他发现,明初以来的江西文运昌盛,与湖广同为中国之谷仓,却也是粮食与人口的流出地区。正是这一社会经济层面的矛与盾共存的魅力,吸引了吴氏的研究兴趣。然而,从事江西区域史研究并非易事,尤其是搜集资料的工作颇多困难,吴教授便遇到了多处江西省内图书馆不向外国人开放的情形,因而怀疑“选择江西作为地区史研究的对象,是不是一个错误”。实际上,这种现象并非针对外国人,不少在外求学并从事江西研究的本地学子亦有类似的感受。在新近出版的《江西省大志》(中华书局,2018)一书的后序中,江西资深学者许怀林教授提及,该书在1987年已完成点校工作,因长期得不到资助,出版事宜一推再推,过程十分坎坷。此间,三名整理工作者有两位已经仙逝,年逾八旬的许教授亦感叹“阎王给的时间不多了”。其文化事业之困境,总归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不只是个别机构的问题。
虽然搜集史料存在困难,但并非不能克服,吴教授的大作便是最佳证明。从近年涌现的研究成果看,江西实是一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善选”。一方面,唐宋以来,江西一直文运昌盛,保存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献。在《矛与盾的共存》一书中,吴教授所用及的史料,不仅有全国性的正史、政书,也有大量江西籍文人和在江西任官的士人留下的文集、笔记、政书,以及相关州县成套的地方志书。除了上述传统史籍,江西还有丰富的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值得深入发掘,包括各村各姓皆有的家谱和充斥文物市场的各式契约文书。曹树基、刘诗古等人整理出版的《鄱阳湖区文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可谓之代表,该套丛书收集了明中叶以来鄱阳湖地区的契约、诉讼文书等多种类的文献,是渔民生产、生活的珍贵资料。区域史研究倚赖地方文献,江西具有天然优势,势必能为开展相关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江西地形复杂,山河相间,省内各地的社会经济情况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北部以鄱阳湖区为中心,地势平坦,开发较早,大量民众以水为生;中部以赣江及其它大河的中下游为中心,交通发达,农业繁荣,人文荟萃;赣南以及边界地区则属山区,经济形式多样,人口流动频繁,也是地方叛乱频发之区。不同的地形特征造就不同的经济形式,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社会,深入考察每一种或许都能丰富对传统社会的认知。
有鉴于此,吴教授将《矛与盾的共存》一书分作三篇十章,先后以人口流动、士绅阶层、都市居民为主题,综合分析明清时代江西各地社会经济中的“矛与盾”的共存与演变,探寻江西明清繁华与近代衰落的历史原因,再透过江西这个中国的缩影窥测明清社会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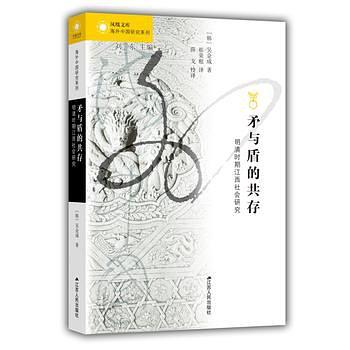
明清时期江西社会中的“矛”与“盾”可谓无处不在,最突出的当是发达的经济、繁荣的文化与不稳定的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历元末之乱,明初推行劝农政策和里甲制度,江西地区社会日渐安定,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至明中叶,江西的经济和文化都有了极大的发展。经济上,耕地不断开发,大量粮食出口至江南、福建等地;经济作物广泛种植,手工业发达,水陆要冲之处的商业市镇日渐发展,陶瓷、造纸、茶叶等行业蔚然兴起。文化上,明代江西继承了宋元儒学的传统,吉州、抚州等地名儒辈出,举业兴盛,进士、高官成群,时有“翰林多吉水,朝内半江西”之谣。与此同时,江西地方社会中的问题也日渐严重。土地向绅士与势豪家族集中,民众的赋役负担不断加重,人口增加引起的“地窄人稠”问题也愈加严峻,迫于生计的小民四处流散,里甲体系难以维系,等等。
流散人口是明中叶以降江西最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总体上说,江西的人口流动有三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地区流向有待开发的山区,二是从经济先进地区(狭乡)流向经济落后地区(宽乡),三是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和手工业地区。人口流向山区,一部分人选择在山区开垦农田并定居,一部分人未能适应山区生活而变成了贼寇,最为典型的当属正德年间的赣南地区。赣南位于闽、粤、湘、赣四省之交,区内地势险峻,人群结构复杂,土著、客民、少数民族杂处,四方而来的流民集结其间,加之国家力量向来薄弱,致使社会治安混乱,是地方行政之大患。为此,王守仁被荐为南赣巡抚,受命平定数省毗邻之区的盗贼。王守仁到任后,先推行《十家牌法》,重整兵制,再镇压贼寇,削其匪首,安插“新民”,新置县衙,后设书院,讲礼义,均赋役,行乡约、保甲之法,巩固社会秩序。在镇压盗贼的过程中,他意识到道德教化的重要性,进而提出“致良知”的哲学命题。
前往经济落后地区的流散人口,一部分人流向省内的边缘地区,更多的人则奔赴外省,他们往往携带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商业观念,促进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抚州、吉安、南昌等经济发达府县是人口外流的主要地区,规模浩大的商人则是江西外流人口的代表。江西商人,亦称江右商帮,主要经营地方特产,如粮食、茶叶、木材,以及陶瓷、纸张、夏布等手工业产品,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进入北方、西南和南部地区的尤多,对湖广、云贵地区的社会经济影响最为明显。江西商人进入西南地区从事贸易,租赁田地和住宅,随即定居,鼓励子弟业举,培育绅士,一面协助地方兴修水利,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一面勾结官府,控制市场,操纵价格,大行高利贷谋取暴利,以致害民激变,危及地方秩序。晚清江西开埠以后,江西商人迅速衰弱,不仅丢失了外省的商业竞争力,连省内的贸易也被外地商人夺去了控制权。
究其原因,除了晚清开埠的客观原因外,自身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从与徽州商人的对比中,或可探知一二:一是江西商人的优势在于人数、活动地域和经营商品种类的范围大,劣势是多为家族式经营,资本规模小,经不起与徽商、晋商的商业竞争;二是江西商人离开家乡后疏于同家乡保持联系,甚至完全断绝;其三,江西商人同官府的关系相对松散,不如徽商、晋商那样敦实,江西商人在外发生争讼时,在朝的江西籍官员视若罔闻。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江西的经济地位越来越弱,活跃了五百余年的江西商人亦一蹶不振。
进入城市和手工业市镇的人口,有商人、雇工、无赖等群体。商人是城市人口的支配阶层,手工业者是城市人口的主体人群,而无赖则是繁华背后的影子,是城市社会的安全隐患。明清时期江西的城市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官府衙门所在的城,一类是工商业发达的市。实际上,工商型市镇的内部差别极大,明清江西的“四大名镇”,景德镇、樟树镇属于专业型市镇,河口镇、吴城镇则是贸易型市镇。位于饶州府浮梁县的景德镇,自唐代以来便是生产瓷器的中心地,故有“千年瓷都”之称,是专业型市镇的代表。明中叶以来,随着工匠制度的崩溃,民窑迅速发展,大量的优秀陶工和外地劳动力接踵而来,至万历间已有十余万人口,城市面积亦颇具规模。在景德镇,大商人控制了窑厂生产和攫取了主要利润,组织生产的窑户多为小本经营,经常与陶工互换身份;陶工的生活十分艰辛,在承受高强度劳动负荷的同时,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以致时常出现陶工罢工、罢市争取待遇的事件。适时,城里的无赖多乘风而起,纠众械斗,从中渔利。位于广信府铅山县的河口镇,地处桐木水与信江的交汇处,是沟通江南与江西、闽粤等地的交通枢纽。河口镇内并无特产,但它背靠茶、纸的主要产地,通过加工和中转茶、纸等大宗贸易兴起,是贸易型市镇的代表。自晚明以降,河口镇商人云集,商品琳琅满目,手工业者及无赖群体蜂拥而来,其居民结构与社会问题,与景德镇相似。不同的是,引领河口镇沉浮的是商人阶层。他们不仅与官府关系敦厚,而且积极进行公益活动,实践儒教修养,不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除了流动人口,影响江西经济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广东贸易体制。清中叶确立的广东贸易体制把江西经济推向了巅峰,而它的废除则将江西经济推下了深渊。在此体制下,从北京到广州的帝国动脉自北而南贯穿江西,江南、福建等周边各地的大宗商品均须经此运往广州,从而带动了沿线市镇的繁荣,如大庾、赣州、樟树镇、吴城镇,等等。不止如此,通过鄱阳湖和赣江的支流,商路沟通江西全境,商人和资本的触角随之而来,拓宽了江西特产的外运渠道,以致乡村市场遍地开花,运输工人、手工业者、流氓无赖等非农业人口奔走竞食,整体上提升了江西的经济水准。
三
江西是王守仁体悟“致良知”的重要场所,也是阳明心学传承并发扬的主要地区之一。追求“天下大同”的王氏门徒,在江西各地为唤醒绅士们的“同类意识”和普罗大众的“良知”而不懈努力。于是,以儒家士大夫自居的绅士,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己任上,又增添了“教化乡里”的职责。
明正德间王守仁在赣南“去山中贼”期间,认识到欲去除小民的“心中贼”必须加以教化,使其回归“良知”,而承担教化职责的自然是较之小民先知先觉的儒家士大夫。为此,王守仁即便军务繁忙,也要及时与门人探讨施行教化的问题,所到之处无不立乡约、设社学、办书院,展开“致良知”的会讲活动。平定“宁王之乱”后,王守仁称病归乡,其教化的精神却在江西生根发芽,人文荟萃的吉安府则是实践“四民异业而同道”的代表地区。嘉万年间,以邹守益、罗洪先、聂豹为代表的王氏门徒,在江西地方官员(如徐阶)的配合下,争相效仿阳明先生,出资办书院讲学、立会社论道,以期“明伦”明而士风变。一时间,白鹿洞、白鹭洲、复真等书院,青原会、惜阴会等讲会,日新月著,四方嘉宾济济一堂。绅士们不但彼此称呼“同志”,还自称“吾党”,相互约束,增进群体的“同类意识”。通过绅士引导普通人,发现每个人心中的“良知”,希冀“满街人都是圣人”。
对江西绅士阶层来说,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天主教。明万历二十五年(1595),由“西僧”变身“西儒”的利玛窦在南昌定居。通过着儒服、讲汉语、翻译汉籍、交结地方士绅、展示西方奇技等手段,利玛窦及其谨慎宣讲的天主教并没有引起地方社会的反感。十余年后,随着利玛窦的离开和接任者苏如望神父的去世,邱良厚、李玛诺等并不精通汉文化的传教士面对日渐增多的信徒,开始购置大房子,公开传教,招致了南昌绅士群体的不满,引发了一系列争讼,是为“南昌教案”。然而,南昌府的判决对提起诉讼的绅士们十分不利。官府认为,传教士们并无违法犯忌的行为,不予以处罚。这将南昌绅士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结果不仅没能限制传教士的活动,反而扩大了天主教的影响,更多的平民加入到信仰天主的队伍。从实质上说,“南昌教案”不过是绅士们遭遇文化碰撞后的过激反应。绅士们认为,信仰天主危及国家自尊和祚命、破坏传统之风俗,威胁到传统文人的优越感;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聚众传教,教会拒绝与绅士合作,严重地削弱了绅士们的社会影响力。因此,绅士们夸大其词无非是想借此强化其内部认同和“绅士公议”的社会权威。
有清一代,江西地区历经明清鼎革和太平天国运动两次兵燹,此间土贼、流寇涌起,社会秩序失控,绅士是战时安抚地方的领导力量。自顺治二年清军进入至顺治六年金声桓败亡的五六年间,江西四境之内,不论是清军、叛军、南明军、勤王兵勇,还是乘乱蜂起的土匪、流寇,凡是携带武器者均是盗贼,无不四处烧杀抢掠,社会治安处于空洞的状态。江西各地一片哀嚎,“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赣南地区的战乱持续时间尤长。明末清初数十年,赣南的闽粤流民以“客纲”为组织,荼毒一方。在生死存亡之际,江西绅士散家财、募乡勇,苟全性命于乱世:从私的层面说,武装自卫能保身家,维护家族成员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从公的层面说,能维持一方安定和生产,又具有防止农民流散、成为的贼寇的功能。待清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江西士绅不再勤王,而是接受新朝的笼络,成为满清统治秩序确立的辅助力量。故曰,清初赣南乃至江西地区的社会秩序恢复和稳定,是清廷的安民之策、州县地方官和绅士协助三者合力达成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江西的惨状较之清初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止是太平军、土贼、流寇等匪类烧杀抢掠,就连大名鼎鼎的湘军也常因军饷不足而劣迹斑斑,与匪类无异。尽管如此,绅士阶层却坚定不移地站在清廷一边。个中缘由非常复杂,既有太平军不用士绅、反对儒教的因素,也有清廷要求地方组织团练的旨令。更重要的是,支持清廷于公于私都有利可图——不仅可以保身家性命,明确绅士作为社会领导阶层的名誉和权力,而且能够增加地方学额,守护名教和国家祚命。
在城市生活中,绅士虽然也是社会的支配阶层,但并非是唯一的权威,因为富商为扩大经营也时常发挥与绅士类似的社会职能,并能通过捐纳科举功名和培养子嗣参加科举而跻身其中。商人没有科举功名,绝对的社会地位也不如绅士,但二者的社会功能并无实质差异,诸如倡建地方公益事业,调停同乡、同业组织间的纠纷,掌管会馆财产、主持祭祀,安抚民变,应对无赖,等等。
总之,明中叶以降,庞大的绅士群体是中国社会的支配阶层,他们不仅承担了辅佐国家权力统治乡村的作用,也为乡村社会代言,在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之间发挥调停的作用。

四
近年各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成果显示,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绅士领导,乃至各种矛盾充斥其间,并非江西一地特有的历史现象。因此,有关明清时代江西社会特征的讨论,有待进一步深化。
当下江西区域史研究日趋细化,考察地域范围多是一府一县,一村一姓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基于上述观察视角的研究成果,虽能“深描”某一区域社会的特殊性,却无法勾勒江西之全貌。因此,我们认识了崇拜许逊的南昌,以水为生的鄱阳湖区,棚民聚集的赣西北,绅士支配的抚州和吉安,以及地方叛乱迭起的赣南山区,却难以形成对江西的整体认识。试问,自北宋天禧四年(1020)设立江南西道起,江西便是中国最高级别的行政单位之一,这片同处鄱阳湖水系的地域,经宋元明清四朝近千年的形塑,就没有形成一套共享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使之构成一个区域共同体?如果有,在“矛”与“盾”并存的种种表象之下,明清江西社会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相较而言,台湾学者于志嘉教授所著《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与《矛与盾的共存》的考察范围完全一致,但选择江西的理由大相径庭:一是因为江西的文献资料容易获取,二是因为,“江西地居腹里,相较于两京或边防、海防地区,其军事地位并不重要,其卫所军役内容相对而言也较为单纯”。综观明清格局中的江西,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其他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既不是中心,也不算边缘,更没有什么离奇的极端情况。故以愚之见,与其主观地将明清以来的江西拔高为中国历史的缩影,不如将之置于“帝国腹里”的位置,分析它曾经的辉煌及近代的平庸,所得之认识可能更加贴近历史实态。
当然,任何单一视角下的研究均不足以洞察一个省级区域的社会全貌,理解明清江西社会的内涵尚需多角度、深层次的持续研究。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