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郭时羽︱献上一瓣心香:赵昌平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
转眼间,赵昌平先生离开我们一年了。2018年5月20日,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至今我仍记得听到消息时那种不可置信的心情。要知道,就在2月过年时,我们还去他家吃火锅,赵先生买了很多菜,一边亲手调配蘸料,一边不无得意地说:“我这可是独家配方,跟外面完全不一样。”那时,我们都觉得他的气色好多了,精神状态大有好转,一切都向着积极的方向进展。却没想到,短短三个月后,竟传来永诀的噩耗。

作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前任总编辑、上海市出版协会原理事长,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全国最著名的学者型出版人之一,赵先生去世的消息,在出版界和学术界引起巨大震动,许多与他年辈相近的学者都第一时间撰写了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我那时几不敢细读,怕眼泪止不住。但心中便隐隐有个念头,我要写一写我知道的赵先生。尽管我只是晚辈,甚至不敢说跟他有多熟稔;但为了赵先生曾经的指点和帮助,为了他言传身教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学者型编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为了他的至情至性,和那些动人的故事……在赵先生离世一周年之际,我想我终究要写点什么,哪怕只是细节,或也可为先生的画像,聊添一二笔自然飘飞的衣袂。
赵先生追悼会那天,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同事发给我一段话:“谢谢那时你鼓励我去跟赵总合影,把我拉到他身边,才有了这张唯一的珍贵合照。”满腹诗书、风度翩翩的赵总编,是上古社多少青年编辑的偶像。而他平时严肃不苟言笑的样子,又让一些年轻人望而生畏,不敢亲近。实则只要跟赵总聊过一次,便会知道他对年轻人十分亲切,总是愿意给予教导和帮助,毫无高高在上的总编架子。正如陈尚君老师所言:“昌平就是这样一个人:重情笃义,做人认真,看似严厉,内心又非常柔软。”
记得大约在2011年,我入社四五年,古籍整理稿之外,也接触到不少学术著作。当时来自国家和学校的各类学术项目支持尚不像如今这样丰富,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十分出色,但由于作者本身资历尚浅,有时难以申请到充足的出版经费。于是,我便初生牛犊不怕虎地提出一个“新锐学术丛书”的构想,希望选取青年学人中真正一流的作品,给予免除出版资助或是仅少量收取资助的待遇,帮助他们尽快出版专著,向学界提供优秀成果。为此还风风火火地跑去跟赵总编请教。他面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的青涩文案,竟毫不以为打扰,饶有兴致地跟我讨论许久,指出难点在于如何确定哪些选题能够入选,我原先设想的由社内资深编辑和学界专家共同组成的评审团,说来容易,实际操作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另外认为“新锐”这个丛书名不好,得换。但总体上,对这个想法给予了肯定,还举出好几位他特别欣赏的青年学者,将他们近期有哪些成果、好在何处一一道来,如数家珍。赵总对青年人的关切与照顾,于此即可见一斑。
而这种行事风格,按赵总自己的话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贯的传统。他曾多次跟我们说起当年的故事:他自1982年入社工作,那时的总编辑是钱伯城先生,无论年纪、声望、学养,还是在社里的地位,都是真正的前辈。钱老曾有一次交待某本书稿给当时年轻的赵先生,但赵先生仔细审读后,觉得书稿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不宜直接出版,便写了长长的意见书,建议退改。钱老无奈,只好退回了稿子。我们开玩笑说,这就类似唐朝皇帝下旨,门下省格回,虽说是制度允许,终究需要下属的胆量和上级的胸襟。又有一次,在一本具体书稿的处理方式上,他和钱老有了分歧,两人你来我往,反复争论,谁都不肯退让。说到这里,赵总呵呵一笑:“哎呀,当时争得厉害,钱老心里肯定是很不高兴的。但也仅止于此事,其他时候的交往,包括后来对我的提拔任用,他都一如既往,完全没有任何要打压的意思。”就事论事,争论是为了把书稿打磨得更好,而非针对个人或“驳了领导的面子”,这一点,上古社的前辈们始终分得非常清楚。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赵先生很快成为编辑室主任、副总编,直至被任命为总编,以卓越的学术与出版成就,成为飘扬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空二十多年的一面旗帜。
去年,赵先生遽尔离世,许多学者在痛悼时,都提到酝酿多年的《唐诗史》未能完成,是学界的一大损失。赵先生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后到华东师范大学读研,师从施蛰存先生,又得上海师范大学桐城派后裔马茂元先生指导,入门之高之正自不待言。他曾任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撰著《唐诗三百首全解》销量已逾十万册,撰写的学术论文更是篇篇珠玑,受到学界高度评价。《唐诗史》若能撰成,无疑是里程碑式的著作。然而,这样一部皇皇巨著需要投入的精力,是难以想象的,对素来严谨的赵先生来说更是如此。作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总编辑,他退休后续聘数年,又担任上海市出版协会理事长,可以说把大半生都投入“为他人做嫁衣”上;否则的话,学术成果一定比现在更为丰硕得多!事实上,尽管《唐诗史》是他多年的计划,但赵先生的学术关注范围并不限于唐代。我的抽屉里一直放着一摞《中古诗学—文章学的思辨形态和理论架构》,是出差参加某次诗话会议前,特地从第十七期《人文中国学报》上裁下来,以便路上学习的。后来跟他说起,还被他笑话了几句。电脑里保存着他的《文献、文化、文学之契合》(《文学遗产》2013年第六期)等文章,都展现出宏大的学术视野。赵先生说过,研究唐诗,而不了解从《文心雕龙》到《诗式》等传承,那只是无根之木;对他来说,也是试图在对整个中古诗学展开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才来书写《唐诗史》,才能成竹在胸,真正阐明其中的脉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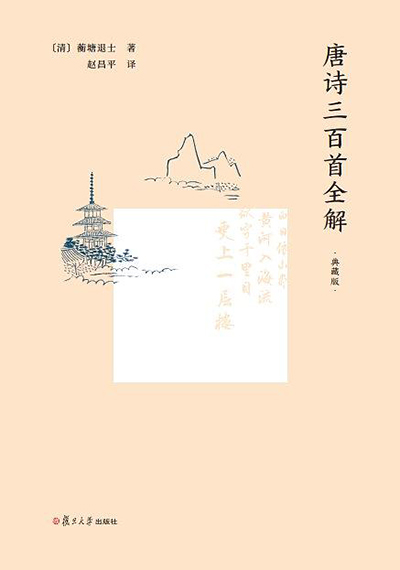
记得2017年的春天,我给赵先生打电话,那时所有的意外都未发生,他心情正好,乐呵呵地讲了不少计划,说等手头承担的《中华创世纪》任务完成,有好几篇文章想写,都是最后可以汇入《唐诗史》的。谁知数月后师母突然病故,哀毁过甚的赵先生有半年时间完全无法写作;直到春节我们去探望时,他买了新的带手写功能的笔记本电脑,说为了完成师母生前的愿望,也要每天强迫自己写一些;可是数月后,他竟也随师母而去了……
最初的震惊哀痛过后,有一个念头不可抗拒地浮现:也许,赵总真的是去跟师母团聚了吧。2017年8月,师母因心脏病突发离世,从感到不适到离开仅一天不到,这样的打击太过于突然而猛烈。我们去赵先生家中拜祭时,距师母去世只短短数天,他竟一下子形销骨立到惊人的地步,后来听说那一个月内瘦了二十余斤。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陆续想拉他出来聚餐,让他松快一下心情,也听说其他师长前辈有一样的想法,赵先生原是那样喜欢与朋友聚会的人,却都婉拒了,说不愿坏了大家的兴致。但微信和邮件中,有时会发来他为师母吹奏的口琴曲,以及彻夜不眠写就的悼亡诗,“馨香一秩诗一挽,和泪书成泣血烧”,真让人欲同声一哭!直至春节那次聚餐,他讲了许多关于师母的梦,有在家中相见的,有回到年轻时居所的,其中一个,是师母身着彩衣,在天女散花中升向天空,还向他招手。大家听得面面相觑,都不敢接口,他却笑着说:“你们不要怕忌讳什么,我是不忌讳的。”回头想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赵先生对师母的思念,直到他去世都未曾淡化过,而那份悲痛,也过度损伤了他的身体。
去年5月26日上午,告别仪式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花篮和挽联布满半个楼面,现场聚集了上海出版界和学术界的半壁江山,更有许多老先生专程从外地赶来送别。师母去世时,墓地是时任世纪集团副总裁的张晓敏帮忙张罗,赵先生发病时,也是他第一时间联系最好的医生,并亲自赶到医院照料。春节一同去探望的朋友,都已先后离开上海古籍出版社,跟赵先生不再有行政上的关系,他自己也常说:“我已经退休了,你们都到了新的单位,大家都是朋友,完全平等相处。”但我们仍习惯性尊称他为赵总。他是以自己的学识、人品和真诚,赢得了众多尊重和真心。作为一个晚辈,我不知道能为赵先生做些什么,只能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写下这些回忆,献上一瓣心香,作为纪念。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