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对谈︱杨念群、李猛、应星:长时段视角下的五四运动
1919年,众声喧哗,革故鼎新,上承清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启现代中国百年激荡转型,回望五四,我们该如何理解和缅怀?2019年4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携新著《五四的另一面》做客单向空间书店,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应星教授,展开了一场对现代中国转型时代的跨界解读,他们试图把五四看作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带有一种立体的,包含各个面相的、非常有意思的系统,从这些不同的面相出发去进行思想碰撞与对话,希望可以深化对于五四这段历史本身的观察。

超越纪念史学:对“五四解释学”的反思
今年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各种纪念活动也应运而生。杨念群先生指出,多年来,中国的史学界有一个习惯,每逢重大事件到百年,或者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一定要大规模纪念或大规模讨论,可称之为“纪念史学”。“纪念史学”讨论的话题可能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讨论五四,肯定要讨论到“民主“、”科学”这些概念,或者它们怎么在中国落地生根、演变,有什么人去推行,民众又怎样去接受,或者它们对中国历史的整个变化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但是,五四已经过去一百年了,我们不能总是讨论一些旧话题,而应该讨论一些新话题。《五四的另一面》一书从新的视角、新的路线,对五四的一些可能被遮蔽的或者说被忽略的面相进行了一些展示,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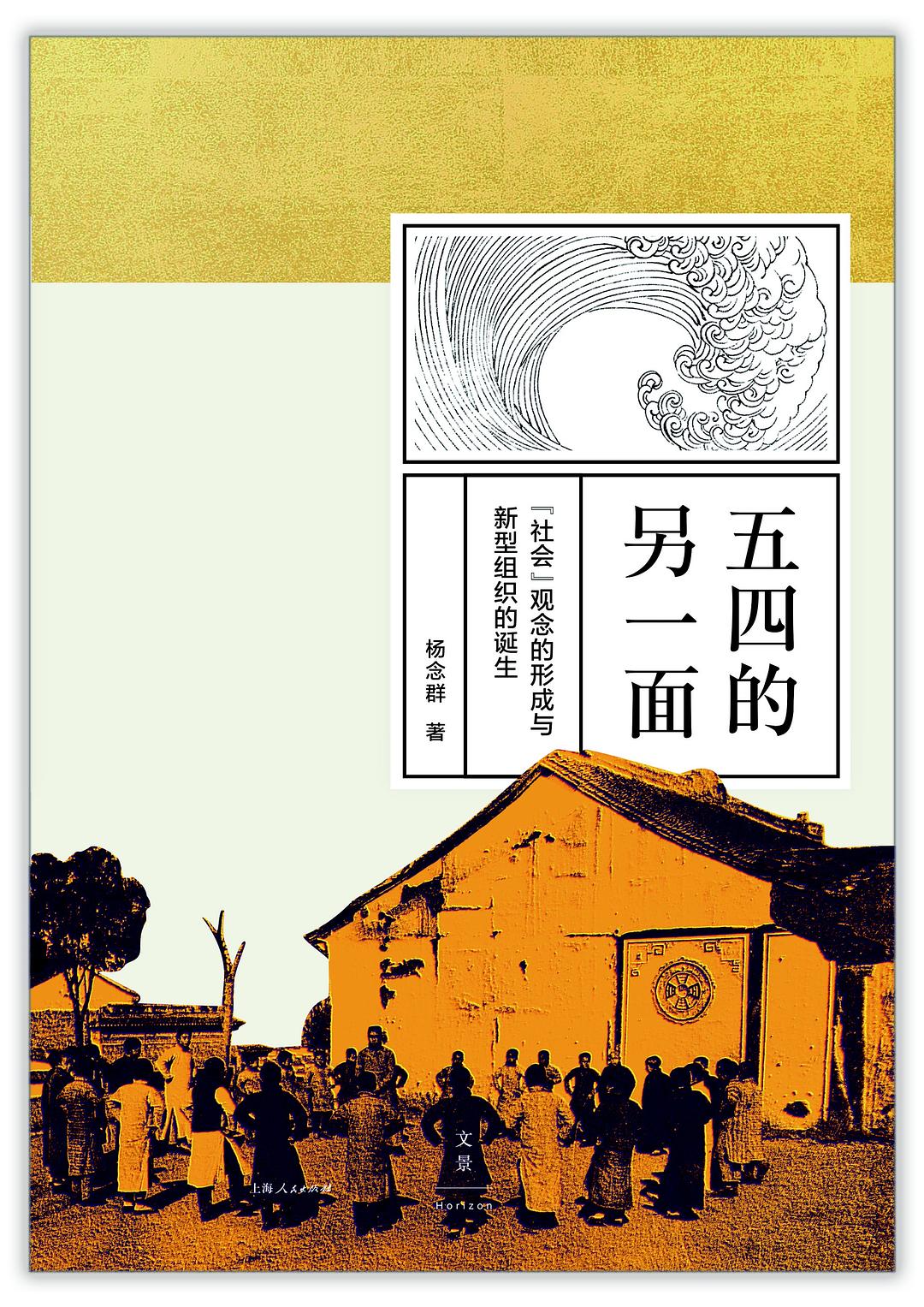
谈到五四,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五四看作一场政治运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引起了国内各阶层的激愤,诱发了一系列的涉及各个阶层的激烈反应。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等等。同时,五四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年轻一代的激进活动家。在主流叙事之外,还有一种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掀起了“胡适热”。我们知道,胡适以及一些当时的知识分子,把五四理解为一场自由主义的运动,把五四定位为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可以用另外一种叙事方式表达出来,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
杨念群先生认为,这两个角度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对立,同时又相互渗透。他还提醒我们注意,五四除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还有一个“莫小姐”(道德伦理革命)。这方面大家注意得不够,同时也一直被“民主”和“科学”这两个非常耀眼的概念所遮蔽。这位“莫小姐”应该有被重新发现的价值。另外,理解五四,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五四这一天,甚至不能仅仅把五四前后的一两年作为解读五四的时间段。而应该把五四看作一个长时段的、更加复杂的一场运动,甚至可以把视野扩展到晚清的变革——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以及辛亥革命。再往后,可以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猛先生指出,纪念史学往往在历史叙事中投入了许多今人的道德和政治立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中就指出了这样一种史学。
应星则是谈了几点感想,他认为《五四的另一面》这本书是个很好的桥梁,沟通了几个方面。书里开篇说是要去挖掘或打捞被思想史、政治史淹没的社会史的维度,但这本书并不是简单地从社会史切入。他回忆说,很多年前,杨念群专门谈到,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的重要性,今天的社会史如果脱离政治史的背景而完全偏向用一种碎片化的方法去做,很多时候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五四的另一面》这本书尝试把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重新联系起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努力,是要在总体史的背景中去安放社会史的位置,力图实现史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的结合。

从后科举时代到现代中国:从长时段来理解五四
杨念群认为,从长时段来理解五四,首先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五四以《新青年》杂志为主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到底是如何产生的?这些身份又与当时的历史状况是什么关系?也即所谓的“身份认同”,他们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这些身份决定了五四的走向,也展示了五四本身的一些独特性质。
如果要谈到五四时期这些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就必然要追溯到戊戌变法前后的年代。理解五四,必须要先看晚清。而晚清,有一个历史事件的节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科举制度的崩溃。科举制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套官僚选拔系统,崩溃之后所产生的后果是什么?要了解五四历史事件的深层原因,还应从所谓的“后科举”时代来进行理解。
杨念群认为,科举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官僚选拔制度。首先,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层制度。考中秀才,就可以成为乡村最有文化的阶层——士绅,但不能离开乡村。考中举人,相当于中层干部,可以当县官。如果考中进士,可以进翰林院,等等。这样就把人才相当精准地分布在了上中下三个层次,官员安排的合理性相当之高。同时,这个官僚选拔制度又是不断流动的。考中举人、进士,有当官的机会,有从地方到中央的机会,而官员退休之后又会回到家乡。这样就形成一个非常良性、不断循环流动的机制。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就产生了另一种人才培养方式——学堂教育。学堂教育培养的人才一般有四种,一种是受理科教育的一批人,很多成为地方官员的幕僚,给他们提供科技知识和辅助;还有一部分人是师范院校出身,到日本进修一年,学到速成的政法知识后回国,进入政府部门;第三种是军事学堂里出来的学生,后来往往成为地方割据的军阀;第四种是海归,很多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学生,回国之后成为知识精英阶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些人接受了系统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训练,但他们的人文素养往往不足。因为科举制终结之后,整个人才教育和选拔机制有了相当大的变化,鼓励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而人文知识占的比例非常小。最重要的是,现代学堂教育,不仅导致了专门化,而且导致了官僚选拔机能的丧失。学堂教育不是为选拔合适的官僚身份,而是通过分散的职业训练,使知识和学问变成了跟政治相脱节的一个教育体系,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乡村士绅阶层的消失。而且,原有的循环系统被打破之后,所有的学堂学生都不愿回到乡村,他们都向城市集中。这样的后果是,乡村大量空洞化——乡村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人物大量流失,导致了中国乡村的空心化。所谓的“后科举时代”,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知识阶层的身份状况。
另外,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实际上都是寻求建立新的政治合法性和新的现代国家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有过很多选择,也遭受了很多的挫折、失败和教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清王朝灭亡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在帝制倒塌的那一刹那,中国人实际上是非常茫然的。
清末民初有南北之争,各种党派之争,导致所谓顶层设计的制度变革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在民国初建的十年之内,甚至不到十年,就已经有很多人对民国的现状不满,对政局不满。一个最大的不满,就是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民国初年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很多的反民国的言论。有一大批人对民国失望,包括陈独秀。他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能否改造国家,从改造社会入手。这种观念把社会看作当时的一个改革的平台和实体,跟“国家”相对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概念。这也是从五四以后,“社会”成为一个关键词的最重要的理由。五四之后,社会改造运动变成了一个主流。不是从上层的政治,不是从顶层设计,也不是从政党政治来讨论中国的命运与改革,而是从社会基层的改造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把中国当作一个新的改革对象,这是五四以后慢慢形成的共识。
李猛总结道,《五四的另一面》一书用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把五四放在从晚清科举废除的后科举时代,到现代中国社会慢慢形成的社会改造、社会建设的长时段中理解,挖掘五四的所谓社会组织的重建这一面的重要意义。另外,杨老师把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放在一起讨论,这是对整体性地理解五四非常重要的努力。因为,如果把五四放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段,即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去理解,那么,中国革命和之前更早的,比如说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相比,可以看出有非常大的差别。

对于现代革命,在中西方学界都有很多争论。和英国革命相比,中国革命可以说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时进行的革命。杨老师在书里也提到,有人会质疑为什么晚清民初,某些围绕现代国家做的宪政改革没有完全成功,这是不是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发展错过的一条可能更温和的道路?其实这样的思路是受西洋史研究中,认为可以脱离社会革命来谈政治革命的思路的影响,英国和美国的革命不像中国革命一样,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紧密结合的一种革命形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的另一面》这本书是通过长时段地挖掘了五四的另一面,即社会组织建设这一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革命某种意义上恰恰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革命,而是一个长时段的,糅合了社会革命的一个二元革命。从长远来看,这对理解整个中国革命有比较大的意义。
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消解
关于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杨念群指出,当时兴起的个人主义实际上跟“莫姑娘”有很大关系。个人在家庭、家族伦理的网络里应该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是要走出家庭,鼓吹个人自由,还是应该投入某个新的组织里,重新把自己认同于这个组织,在当时有很大的争论。但这个争论的出发点就在于个人是否能真正地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并作为个体被加以认识和认知,这是五四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他举例说,我们看早期鲁迅等人的著作,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他们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个人不好,社会也不会好,社会不好,国家也不能好。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没有国家,中国现代的这个国家的体系就建立不起来。但是这个基本的认知后来遭到了相当大的质疑,最后被消解掉。杨念群认为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以个人优先,或者把个人作为独立价值判断的这么一个基础。只有个别的作品如庄子《逍遥游》,偶尔会提到个人自由。但是在以儒家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中,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必须服从于整个家族和家庭的网络以及更大的社会秩序。所谓宋明理学的基本脉络就是由个人推导到家国天下的脉络,个人只是出发点,但不可独立于任何的家国体系。只谈个人,几乎就是不合法的,也是没有合理性的。第二,中国的公私之间的界限非常不分明。从《礼记》来说,就是所谓的“天下为公”。“公”的合理性是理所应当的,是判断任何事情的前提。个人如果在“天下”和“公”里,强调个人和它们正当的对立关系,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但是在五四最早的个人主义言论中,如鲁迅等人,他们大胆提出,个人能不能跟“天下”“公”形成一个对立的、平行的,甚至可以不兼容的关系。但是他们的尝试最终失败了,原因就在于公私之间的界限在传统中国的体系脉络里就是无法区分的。
“公”可能就是“私”的代表,但“私”实际上是变成了“公”的一个部分,融入其中,来体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五四以来力求冲破束缚的最大尝试,但是失败了。一个是它缺乏传统根基。第二,个人的位置,往往是在跟家国天下的互动中来确立的。最大的原因是中国不断受到西方的侵略、干扰,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必须在应对外来的所有因素中保持一个持续的斗争姿态。所以,有人说救亡往往是最重要的,我们任何人,如果要把国家的利益,把抵抗外来侵略的利益放在私人的利益之外,或者把个人放在这样一个姿态之上,就没有合法性。私人到最后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自私自利的、带有很强烈负面价值的导向性的评价。而且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个人主义被压抑到相当狭小的范围之内,最后慢慢趋于消失。这可能是五四时期最值得被重新挖掘出来,加以哀悼和致敬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应星补充道,通常我们去理解五四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面容模糊的思想者、行动者。杨老师强调的“身份”切入了社会史的眼光,因此看到的不是模糊的五四的行动者,而是五四一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制度背景,从科举制废除之后,到新式学校,其中发生的根本变化。第二个,所谓“代”的背景。老一代人,比如像陈独秀这一代,到胡适,再到张国焘这类北大新学生,这是不同的“代”。“代”之间对五四的理解,有很重要的不同。第三个社会史的背景,他们不仅不同“代”,而且带着不同的地域的背景。因此通过这三层,我们就可以看到,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五四行动者面目更加清晰。这是所谓社会史的维度。

最后,杨念群老师作了简要总结,《五四的另一面》这本书把五四放在一个长线的历史脉络里,分别展示出它不同的面相。这些不同的面相,往前可以追溯到后科举时代,往后可以追溯到社会改造运动。对中国历史和政治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有立体感的五四形象。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