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虞云国重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南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

靖康二年(1127)四月初一,宋徽宗、宋钦宗及其后妃、皇子、公主被金军俘虏北上。原宋哲宗皇后孟氏因遭废黜,迁出大内,反逃过一劫,尊为元祐太后垂帘听政,随即下令寻访流亡在外的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建立南宋,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
中兴话题的肇始及其主题词一览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称《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以下此书引文,一般仅注页码)卷四建炎元年四月甲戌,就在半个月前,侍御史胡舜陟建议元祐太后诏告天下,中国依然有君,康王行将继位,“以破乱臣贼子之心”。汪藻在起草这份文告时首倡“中兴”话语:
繇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107页)
汪藻不愧大手笔,以光武中兴、重耳复国等典故熨帖设譬,大意说,赵构出自康王藩邸,继承宋朝皇统,恰如汉朝之厄虽在十代,理应光武中兴,晋献公之子虽有九人,唯有重耳幸存,这正是天意,岂能是人谋!刚经历靖康之变的亡国之痛,朝野上下切盼赵宋中兴,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会诉求与民族心理。
《要录》是记述南宋高宗朝史事最称详赡的典籍,四十年前初学宋史时曾阅读一过。近来得暇重读,发现在绍兴和议前的十余年间,尽管政治倾向各不相同,官僚士大夫议论政事几乎言必说“中兴”。即便从金朝遁归的秦桧,绍兴二年(1132)升任参知政事,也慷慨声称:“中国之人惟当著衣噉饭,共图中兴!”着实令听者“心服其言”(979页)。没有必要繁琐征引群僚奏议与君臣对话中涉及“中兴”的所有言论,不妨将读史所见的“中兴”话题中的主题词作一概括性说明。
“中兴气象”“中兴王业”“中兴规模”云云,议论“中兴”愿景堪称高屋建瓴;“中兴基业”“中兴大计”“中兴根本”云云,关注的是“中兴之业”的基本问题;“中兴急务”“中兴要务”“中兴善政”云云,往往是对“中兴之政”的具体建议。“中兴之世”“中兴之时”“中兴之期”云云,表达了对“中兴”的殷切期待;而“中兴之会”“中兴之运”“中兴之机”云云,对“中兴”祈盼时还强调了机运因素。“中兴之功”“中兴之效”云云,注重“中兴”的功效与实绩。“中兴之盛”“中兴之治”云云,应是对“中兴”目标的终极向往。
在致力“中兴”过程中,无论“中兴之君”,还是“中兴之臣”,首先应立“中兴之志”,同时宜讲“中兴之术”,也都是当时的话头。说到“中兴之臣”,“中兴之相”与“中兴之将”尤为关键,甚至与伪齐暗通款曲的某榷场经纪人也指斥“刘光世非中兴之将,吕颐浩非中兴之相”(1263页)。南宋肇建之初,李纲一再奏论“自古中兴之主”(184页);绍兴二年,张九成对策也大谈“前世中兴之主”(923页);时隔三年,李弥正转对时纵论“古者创业中兴之君”(1485页);绍兴七年,朱松受召见时也曾建言,“自昔中兴之君,惟汉光武可以为法”(1825页)。所有这些“中兴之主”“中兴之君”的话题,仅仅是对宋高宗耿直的规谏与殷切的寄望,并未将其视为心目中的中兴君主。
对南宋高宗朝的中兴语境,已有研究者从历史叙述的视角给以关注:
整个高宗朝廷的政治建设包括皇帝本人都在竭力把持有关“中兴”的历史叙述,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辩护以保障自己的政治前途。(蔡涵墨:《历史的严妆》,中华书局,2016年,30页)
这一论断总体成立,前引宣告宋高宗即位合法性的《告天下手书》也印证了这种历史叙述。但作为一般的中兴话语,其衍变的趋势与面相却是相当丰富与复杂的,仍有深入探究的余地与必要。

大体说来,整个南宋高宗朝,以1142年初“绍兴体制”生效为历史坐标,“中兴话语”凸显出不同的语境与走向。绍兴和议前,朝野士大夫以“中兴”为致力目标,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作一朝“国是”,上奏或面对时频频援引这一观念议事论政。在这一阶段,“中兴话语”仅仅作为一般号召性、具体建议性或相互探讨性的话语系统,即便以皇帝名义颁发的诏书与策问,或者有宋高宗参与的君臣对话,也都呈现这种状态。自绍兴体制确立后,此前那种“中兴”语境虽有短暂的延续,但不久之后,宋高宗与权相秦桧就全面操控“中兴”语义的解释权与话语权,将“中兴”变为具有特定内涵的谀颂性话语,藉此将宋高宗型塑为“绍开中兴”的“中兴圣主”。下面略按年代轨迹来展现中兴语境的这种蜕变过程。
绍兴和议前宋高宗的“中兴”论
建炎二年(1128),南渡政权首次开科取士,殿试策问以皇帝名义发出,援引了宣王中兴与光武中兴等史事,向考生征询消弭内忧外患的方略。绍兴二年科考策问,宋高宗又历数少康、宣王、光武、肃宗等中兴旧迹,要求士子考察前世中兴之主的“施为次序”,哪些仍切用于当今世务,恳切要求他们“悉意以陈,朕将亲览”(《横浦集》卷十二《状元策一道》)。宋高宗之所以在殿试策里一再提及中兴故事,无非向天下表明,他也希望实现与之比肩的中兴大业。正如他在绍兴二年四月一份诏书里所说,“朕寤寐中兴,累年于兹”(933页),不能说这种中兴期待完全出于作秀。这年,徐俯建议宋高宗熟读《汉光武纪》,“以益中兴之治”。光武中兴为炎汉再续近二百年国祚,显然较之其他中兴更为成功,也更应效法。不久,宋高宗手抄了《后汉书·光武纪》一卷赐给徐俯,以示采纳了他的建议。自此以后,以光武故事作比,成为宋高宗朝中兴话语的一大特色(参见何玉红《南宋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光武故事”》,《史学集刊》,2018年第六期)。
绍兴二年八月,宋高宗褒奖韩世忠屡平游寇之功,借此号召内外将官“各务立功报国,共济中兴,以光史册”(990页),表明对内剪灭群盗流寇,确保南渡政权有稳定的立足空间,是宋高宗当时致力的“中兴”目标之一。同月,左相吕颐浩主张在淮东战略要地布防,邀击随时可能南侵的金军,高宗附和右相秦桧“不战何以休兵”的说辞,声言“自古中兴之主,何尝坐致成功”(993页),透漏出其时对金“休兵”在宋高宗与秦桧之间早已灵犀相通;至于他说“朕谓中兴之治,无有不用兵者”云云(1036页),不过是金朝拒绝其乞和之请下的无奈选项。
尽管对内“群盗”仍炽,对外“休兵”无望,“中兴之主”自我形塑的舆论宣传已然启动。宋高宗在应天府即位告天之坛被称为“中兴受命之坛”。李心传没有记及这一尊称何时由朝廷认定,但据《要录》卷四十四绍兴元年五月癸卯条,这天,宋高宗向宰执们展示由他下令新篆的“大宋中兴之宝”,居然比宋徽宗制造的“定命宝”还大上一半,“新刻者其玉明润”(798页),显然为庆贺登基四周年准备的。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宝玺》,其印文为“大宋受命中兴之宝”,让人有理由推断,“中兴受命之坛”的定名或应在其前后不久。绍兴三年,高宗下诏旧相汪伯彦领衔编纂他开大元帅府时的事迹以付史馆,绍兴九年,汪伯彦不负所望,著成《中兴日历》,在同类书中最称详备。绍兴四年七月,汪藻编成《建炎中兴诏旨》三十七册,或是以“中兴”命名的首部官方档案,宋高宗仍诏送史馆存档,俨然认可了“中兴”之说。
以“中兴”命名官方文档既开先河,循例跟进者便不乏其人:绍兴五年十月,右相张浚进呈《中兴备览》,论列亟应着手的要务;绍兴七年二月,提举广南市舶林保献《中兴龟鉴》;次年二月,州学教授李昌进上应诏撰成的《中兴要览》;同年五月,布衣柴宗愈献进《中兴圣统》。这些献书呈文尽管以“中兴”命名,但都是建议如何才能臻于中兴之局的。例如,李昌声称,倘若始终按《中兴要览》做去,将“不止恢复疆土而已”(1903页);柴宗愈在《中兴圣统》里主张夏少康、汉光武可为标准,周宣王、汉宣帝、晋元帝、唐玄宗、唐宪宗可为鉴戒。凡此足见,围绕中兴话语,其时朝野官民仍拥有较充分的言说自由度,高宗还褒赏了柴宗愈。
绍兴八年十月,宋高宗独相秦桧,标志着君相联手打造绍兴体制已是不容争论的最终决策。但鉴于朝野反对之声不绝,宋高宗与秦桧便将与金议和定位为实现“中兴王业”的重大部署,甚至为其抹上祥瑞的色彩。绍兴九年,第一次绍兴和议达成,金朝归还河南陕西地,判大宗正事赵士㒟等奉诏北上祭扫北宋皇陵。五月,还朝复命时,赵士㒟等大肆渲染说,自兵兴之后,皇陵下石涧水久已干涸,礼成之日,竟水流丰沛,“父老惊叹,以为中兴之祥”(2075页)。岂料两月之后,金朝主战派发动政变;次年便公然毁约,派兵夺回河南陕西之地。宋金重开战事,“中兴之祥”也不再说起。

好在宋金实力此长彼消,在东、西战场上,金军不仅未捞到便宜,反而连居下风。绍兴十一年二月,诸路私家军奉朝廷之命,投入柘皋(今安徽巢县西北)防卫战中,发挥了联合作战的优势,最终遏阻住金军的攻势,取得了会战的胜利。三月,金军被迫撤回淮北。但在高宗与秦桧以防卫战促成和议的既定方针下,宋军不仅未挟战胜之威扩大战果,反而奉命退回江南。有学者指出,柘皋会战的胜利,“实质上恢复了朝廷的军事指挥权,在南宋政权最大悬案的收兵权问题上绩效卓著”(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中华书局,187页)。四月,宋高宗断然罢三大将兵柄,为向金求和扫除障碍。六月,他踌躇满志地向秦桧为首的宰执班子自诩道:
中兴自有天命。光武以数千破寻邑百万,岂人力所能乎!朕在宫中,声色之奉未尝经心,只是静坐内省,求所以合天意者。(2255-2256页)
秦桧立马呼应:“陛下圣德,畏天如此,中兴可必也。”君相一唱一和,开始为“中兴”话语蒙上“天命”与“圣德”的光环。其后,宋金战事尽管时断时续仍在进行,这对君相为实现所谓“中兴可必”的政局,一方面紧锣密鼓地频繁遣使推动与金朝的和谈,一方面处心积虑地加紧对岳飞的迫害。十一月十三日,因宗正寺建请,宋高宗下诏续修《玉牒》(次年秦桧以宰相主持续修工程),记载宋高宗朝的《今上玉牒》即动议于此,其目的“以备中兴之盛典”(2282页)。由此可见,宋高宗与秦桧已开始刻意营造盛世修典的“中兴”气氛。
就在同一天,岳飞父子与张宪却以“谋反罪”投入大理寺诏狱。两者对照,触目惊心。说到底,自宋高宗独相秦桧起,这对君相的“中兴愿景”可谓坚定而明确:对外,与金朝尽快达成和议,以确保半壁江山的生存空间;对内,收夺诸大将兵权,让大宋的军队必须姓赵,以紧紧抓住专制极权的命根子。随着当年岁末的岳飞之死与次年岁初的和议生效,宋高宗梦寐以求的“中兴”之局终于梦圆成真,“中兴”语境也随之急遽地蜕变。
绍兴体制下中兴语义的蜕变轨迹:以殿试策论为中心
绍兴和议体制确立了南北和局,却是以南宋彻底放弃中原为代价的。这种时局能否称为“中兴之世”,且不说力主恢复的朝野异议者,即便一般官僚士大夫内心深处也未必真正认同。宋高宗与秦桧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钦定“中兴”的内涵与外延,在垄断“中兴”话语权的前提下,巧妙引导与大力鼓吹“中兴”话题。具体说来,在舆情宣传上,不仅要让朝野普遍接受“中兴之世”因绍兴和议而业已实现,而且要鼓动官民歌颂礼赞这一“中兴之世”,进而把宋高宗形塑涂饰成为“中兴之主”。
于是,在诸多舆情场合,宋高宗对“中兴”内涵进行了煞费苦心的解释与宣传。三年一次的殿试策问,既是皇帝向举子征询治国大计的重要渠道,也是当时政治舆情的主要风向标。不妨仍就此入手作一番考察。

绍兴十二年是绍兴和议确立后的首次科考,尽管此前数月的岳飞冤狱已令政治氛围肃杀凄戾,但质疑和约之声尚未销声匿迹。面对这种态势,这年策问题在评价绍兴体制开局形势时还留有余地:
今朕祗承上帝,而宠绥之效未著;述追先烈,而绍复之勋未集。至德要道,圣治之所本也,而欲未得。散利薄征,王政之所先也,而势未行。
从其承认“未著”“未集”“未得”“未行”云云,说明宋高宗其时尚未自信满满。但接着策问就直斥那些异议言论:
设科以取士,而或以为虚文;休兵以息民,而或以为不武。
最后,他告诫士子说:
子大夫所宜共忧也。其何以助朕,拯几坠之绪,振中兴之业。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从要求举子们助其“振中兴之业”,透露出宋高宗还未公然宣称当下已完成了“中兴之业”,还有提振的必要。
这年状元策作者是陈诚之,他一方面鼓吹绍兴和议是“以休兵息民为上策”,一方面建请高宗“行之以诚一,则振中兴之业,又何难乎?”举子杨邦弼答策说:“陛下信顺以待天下,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2320-2321页)他把吹捧皇上与权相接榫“中兴之功”,也赢得了殿试第三的好名次。总的说来,这年策问与策论中的“中兴”语境已向绍兴体制明显位移,但从振“中兴之业”、冀“中兴之功”的说辞,说明问策与答策都还未直接标榜“中兴之业”与“中兴之功”已然告成,宋高宗的自吹自擂与举子们的阿谀奉承还有所节制。
绍兴体制确立的头两年里,非议之声仍未完全绝迹,整肃力度遂不断加码,不仅任何异议者都被迫噤声,胡铨、王庶与张九成等政敌也遭到更严酷的贬窜。与此形成对照,受名位利禄诱引的阿谀之臣开始为“中兴圣业”唱起了赞歌。绍兴十四年五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葛立方竭力吹捧“中兴大业”史无其比:
陛下决䇿定计,成此中兴。亲迎长乐之銮舆,坐息边陲之烽火,格天之业,夐无前比。
他进而建议朝廷,纠察那些“怀奸”份子,严禁他们“动摇国是”,“煽惑士流”,非议“中兴”决策, 应将他们“流之四裔,永为臣子不忠之戒”。宋高宗下诏御史台“览察”(2436页)。
自秦桧独相,台谏官都是其爪牙鹰犬。一月之后,御史中丞詹大方上奏,先是歌颂高宗“作新庶政,光启中兴”;继而请求“明诏大臣,崇奖廉隅,退抑奸险”,确保“大小之臣,咸怀忠良,中兴之盛,可立而待”(2441页)。宋高宗随即下诏,将这份公开号召整肃异己的奏议张榜朝堂。
五天之后,右正言何若再请甄别君子小人,“如是则一心徇国者,得以辅治,异趣而徇私者,不能以害治”,理由仍然冠冕堂皇:如此“中兴之业,愈久而愈隆矣”。宋高宗随即明示秦桧:“朕任台谏,正要分别君子小人。若小人者,但时察而去之,斯不害治矣。”(2441-2442页)
由此可见,绍兴十四年夏,在动用国家权力迫害坚持异议的朝野士大夫上,宋高宗与秦桧已达成共识,故而在短短四十天里一而再、再三而地唆使或指令台谏,将绍兴体制反对派诬陷为“小人”,再以维护“中兴之业”的名义作为严惩的理由。不言而喻,在宋高宗与秦桧的语境里,绍兴体制与“中兴圣政”是同一政局的不同表述而已,都容不得半点妄议的。
绍兴十五年的殿试策并未直接涉及“中兴”话题,策问的是如何让“入仕者皆知趋向之正”(2467页)。这也表明,尽管政治高压已经酷烈,但在认同绍兴体制上,朝野士大夫远未达到“趋向之正”的地步,故有必要向这些官僚后备队强调“趋向”的重要性。
然而,“中兴之世”基调既然已在绍兴十四年明确敲定,承风希旨之辈便在“中兴”语境上进一步引申发挥。绍兴十七年,殿中侍御史余尧弼奉权相旨意弹劾政敌郑刚中,便振振有词道:“方今中兴总揽权纲之时,而刚中乃尔怙权”(2548页)。
绍兴十八年的殿试策问重回以“中兴之主”为论题,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策问开头仍说:
朕观自古中兴之主,莫如光武之盛。盖既取诸新室,又恢一代宏模,巍乎与髙祖相望,垂统皆二百祀。朕甚慕之。
光武中兴结束了新莽之乱,延续东汉二百年天下,规制与疆域堪比刘邦创立西汉,确实让宋高宗只有羡慕嫉妒的份儿,故而策问接着就追慕光武的话头自圆其说:“愿闻今日治道,何兴补可以起晋唐之陵夷,何驰骤可以接东汉之轨迹。”但绍兴体制既定,中原恢复无望,策问便曲为之解:
夫既抑咸宫之鋭,谢西域之质,则柔道所理,必有品章条贯,要兼创业守文之懿,视夏康、周宣犹有光焉。
“抑咸宫之鋭”,典出《焦氏易林》,强调“恭谦自卫,终无祸尤”;至于“谢西域之质”,则用光武中兴时“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的典故。两者都是宋高宗把屈己求和说成“柔道所理”的自我辩解。他最后腆颜声称:我这“中兴之主”比起夏少康中兴与周宣王中兴“犹有光焉”。
经过近六年的政治整肃与舆情宣传,这次举子在答策时凡涉中兴语义都知趣地指向绍兴和议与绍兴体制。高中状元的王佐热捧道:“况陛下今日任用真儒,修明治具,足以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则光武之治不足深羡。”他不仅把秦桧捧为“真儒”,更将绍兴中兴吹嘘得比光武中兴还了不起。董徳元的答策认为:东晋与中唐的中兴,都“失于用兵故耳”,而光武中兴“固无如是之失也”,将宋高宗休兵求和以致中兴直接媲美光武中兴。陈孺的策论也认为当下“中兴之盛”已超过光武中兴:
今日中兴之盛,以言乎内治,则大臣法,小臣亷,百姓遂其衣食,万物蒙其丰年。以言乎外治,则讲信修睦,中外交欢,边鄙无虞,五兵不试。东汉之事,未足慕也。
而后的任务就是确保“边隙不生,远人益服”,全力维护“中兴之盛”(2553-2554页)。
综观绍兴十八年的皇帝策问与士子策论,不难发现:策问虽仍装模作样地以光武中兴为效慕的标杆,士子策论却径直将宋高宗与绍兴体制的评价攀比或超越了光武中兴。宋高宗与秦桧厉行打击迫害的高压政策,对试图入仕的举子们已显现其强大的震慑力,在这一中兴语境下,他们明白应该怎么顺着说。
宋高宗与秦桧显然注意到举子策论对中兴语境蜕变的顺应与迎合,三年之后,绍兴二十一年殿试策问时索性避开对“中兴”内涵越描越黑的解释与辩护,自信满满地宣告“朕承中兴之运,任拨乱之责”,也就是说,宋高宗已经拨乱反正,担起了“中兴之运”。举人赵逵的对策先是歌颂“陛下以神器之大,方与元老大臣协谋比徳,以缉熙中兴之功”;继而指责“百执事之人,因循旧习,不与圣人同忧”。“缉熙”乃光大之意,也就是说“中兴之功”已然告成;而“圣人”就是中兴圣主宋高宗(2634页)。

至此,中兴语义在内涵上已定于一说,所谓“中兴”即指绍兴和议体制确立的绍兴中兴。
庆典祥瑞虚饰中兴语境
当然,对“中兴之业”与“中兴之主”,无论曲为之解,还是强为自信,宋高宗与秦桧总有点底气不足。于是,铺张隆重的庆典与神神叨叨的祥瑞便大派用场,有关颂辞也都不约而同地与中兴挂上了钩。
绍兴十二年四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与宋徽宗梓宫一起启程南归,她已拘留金国达十六年之久。八月,宋高宗亲赴临平镇奉迎,仪仗队用黄麾半仗两千四百八十三人,生生将被俘的太后还朝搞成一场中兴庆典。韦太后回宫次日,百官赴殿门拜表恭贺,为庆祝皇太后“回銮”,朝野献颂者多达千余人,其中近四百位文理可采者都“推恩有差”。大理正吴㮚之颂号称压卷,吹捧“於皇睿明,运符中兴,绵于肃清,乾夷坤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二十三),直接把高宗歌颂成“运符中兴”的“睿明”之主。
其后,宋高宗与秦桧每年都变着花样举行盛大的礼仪或庆典。据《要录》卷一百四十八绍兴十三年二月乙酉条注引吕中《大事记》,就有如下典礼:
十三年初,谒景灵宫,合祭天地,建金鸡肆赦,班乡饮酒仪。
十四年,作浑天仪,复教坊乐工。
十五年,行大朝会礼。
十六年,制常行仪卫,耕籍田,郊备祭器,设八宝,作景钟,阅礼器,奏新乐。
十七年,祠髙禖。
十八年,图景灵宫,酌享功臣。
十九年,定蜡义。(2383页)
这里,对绍兴十六年的“作景钟,阅礼器,奏新乐”,略述其详。宋高宗下诏铸造的景钟高达九尺,属于绍兴新礼器系列,专供天子亲祠上帝时撞击之用。据《中兴小纪》卷三十二,景钟铸成,宋高宗特命秦桧撰制铭文,“以为万世不朽之传”。秦桧在铭文里吹嘘宋高宗“徳纯懿兮舜文继”,“贻子孙兮弥万世”,在进《景钟铭》表里更不吝谀辞:“中兴天子,以好生大徳,既定寰宇,乃作乐畅天地之化,以和神人。”由此看来,为宋高宗涂饰上“中兴天子”光环的首秀演员还得数权相秦桧,高宗报以“词翰甚美”的点赞。绍兴新礼器全部铸成,宋高宗与秦桧率百官赴射殿行礼如仪,观瞻新礼器,听撞景钟,奏绍兴新乐,一切仿效北宋治世的皇祐故事,借以抬高绍兴中兴的历史定位。
对包括撞景钟在内的系列庆典,晚宋吕中在《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下称《讲义》)卷一《统论·中兴国势论》中评论说:“当神州陆沉之时,而举前世之繁文曲典,以盖其苟安之迹,安能中兴乎?”这一追诘当然一针见血,但倘若借助西方政治学的观点,剖析也许更具穿透力。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梅瑞安在其《政治权力》一书里指出,统治者出于维护其统治权威的政治需要,总是力图唤醒被统治者对自己的崇拜与敬仰之情,这种唤起被统治者内心同感的手段称之为“米兰达”(miranda)。在古代政治里,鼓吹君主乃上帝派遣,能呼风唤雨等神话,或者彰显君主威权的各种仪式与典礼,都可以称作“米兰达”(转引自《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2019年2月16日《年度历史图书选摘》,丸山真男著、陈立卫译《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第二章《人与政治》)。显而易见,在前述隆重的庆典与下述祥瑞的神话中,宋高宗与秦桧正是以“米兰达”来调动与诱导出朝野士大夫与普通民众对“中兴圣主”的崇拜与敬仰,进而拥护绍兴体制的绍开中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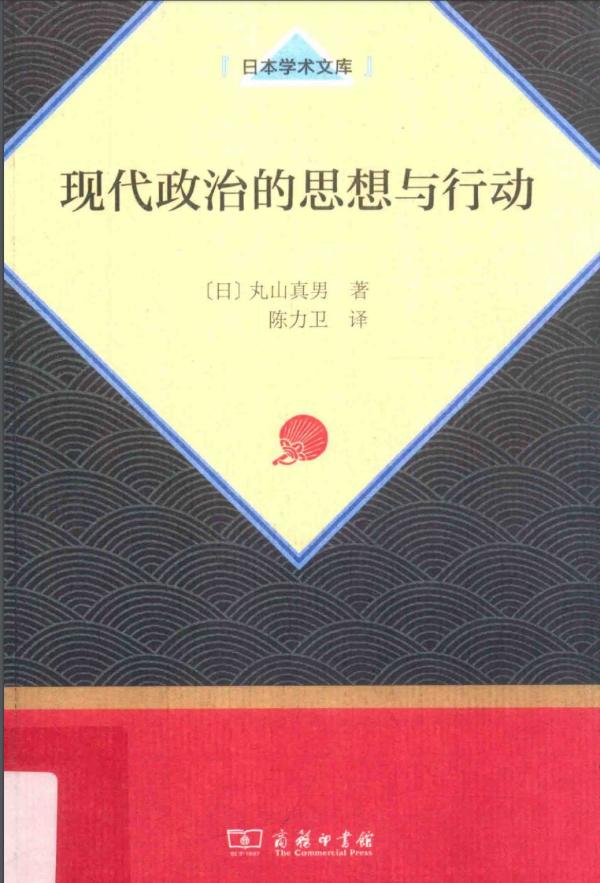
绍兴十八年闰八月,福州奏报盛夏大旱之际忽降大雨,侯官县竹子结实如米,采获近万斛,饥者得食,这是“天子圣德所感,上相爕理之效,实为中兴上瑞,伏乞详酌施行” (2566页),用所谓“中兴上瑞”为宋高宗与秦桧脸上贴金,于是,“圣德天子”下诏将此奏议交付史馆,载诸史册。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衢州通判周麟之上言:
今天子受命中兴,功光创业。近者太庙生灵芝,九茎连叶。此尤瑞应之大卓绝而创见者,宜令有司考故事,特制华旗,绘灵芝之形于其上,以彰一代之伟绩。
宋高宗当即下诏有关部门照此办理。不久,秦桧之孙秦埙与礼部侍郎王珉等权相亲党相继奏请将各地报来的瑞木、嘉禾、瑞瓜、双莲等等,“并绘为旗”,高宗也无不采纳。李心传在记录这些“中兴祥瑞”时,有意转引了何俌《龟鉴》的说法,一切都让秦桧顶缸:“桧乃敢有欺君之心。桧之心直欲掩蔽灾异,缘饰祥瑞,以文中兴,而为固宠之资耳!”(2768页)然而,所有“特制华旗”的诏命分明是宋高宗亲颁的,中兴祥瑞的连台闹剧自然也都是这对君相联手执导的作品。
绍兴二十年五月,专记宋高宗“中兴之迹”的《中兴圣统》修成,隆重供奉在陈列历代宋帝塑像的景灵宫天兴殿之西。“奉安”大典,由秦桧之子、知枢密院事秦熺为奉安礼仪使。礼毕,宰相秦桧率百官拜表庆贺。秦熺、汤思退、周紫芝、林机,孙仲鳌、丁娄明与周麟之等在朝官僚都进颂献诗礼赞中兴。周紫芝颂诗云“礼行廊庙喜书成,重此商周说中兴”(《太仓稊米集》卷三十三《恭进奉安中兴圣统庆成诗》),将本朝中兴比以商周中兴。这种庄重的庆典,旨在借助盛大的仪式让天下臣民对庆典指向的主体与主题形成一种神圣、崇拜与敬畏感,主体当然就是捧为“中兴之主”的宋高宗,主题就是他的“中兴之业”。
从朝野献呈的诗文看中兴语义的蜕变
绍兴和议后,朝野士大夫不时主动进献论表诗颂,其中也颇能折射出中兴语境的移步换形与义随势转。
绍兴十二年,汉州陈靖献上《中兴统论》,以布衣特补右廸功郎。据《玉海》卷六十二《艺文·论》,其书提“三始、五要、八实之说,深明治体,论事之外自为文章”,应该仍属建议性的,未必就是谀颂之作。次年,左廸功郎何俌献《中兴龟鉴》十卷,下诏特迁一官。据《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二引《两浙名贤录》,说他“裒少康、周宣王、汉光武、晋元帝事可施行者,为《中兴龟鉴》上之”,足见也是献策性论著。据此推断,在和议初成的头两年里,尽管秦桧从未停止过对政敌的迫害,但总体态势属于单个定点打击,中兴语义仍未定于一尊。
绍兴十四年四月,宋高宗批准秦桧“乞禁野史”的动议;十一月,秦桧党徒杨愿奏请,必须让“沮讲和之议者”与“腾用兵之说者”,无论朝野都“洗心自新”,不许“窥摇国论,诖误后生”,宋高宗将其奏“揭示庙堂”(2456页)。这两个决定,不啻是一个信号,表明朝廷在朝野上下对和议持异见的士大夫着手全面的清算,也意味中兴语境急遽逆转,言说者再也不能自执己见而各唱各调。自此以后,所谓中兴语义,大体包括确定不易的几层内涵:首先,绍兴和议业已绍开中兴;其次,宋高宗就是中兴之主,秦桧则是中兴之相;再次,绍兴体制与绍兴中兴只是同一语义的不同表述;最后,妄议绍兴体制就是破坏中兴大局。至此,中兴语境已完全蜕变,朝野士大夫在奏议诗文中也随之跟进。
绍兴十三年,权中书舍人刘才邵诗云,“共说中兴似光武,南都赋合继东京”(《檆溪居士集》卷三《早朝行宫奉呈诸同舍》),已将绍兴中兴与光武中兴相提并论。十五年,他以党附万俟卨被秦桧赶出朝廷,出知漳州,为能回朝,他在元旦贺表中将宋高宗捧为中兴圣主:“性由天纵,道本生知,绍列圣之宏规,开中兴之宝运。”(《檆溪居士集》卷三《贺元旦大朝会表》)
绍兴十七年十二月,婺州举子施谔献进《中兴颂》,另上《行都赋》与《绍兴雅》十篇,为绍兴中兴大唱颂歌,宋高宗特许他永免应试证书。
绍兴十八年,歌颂中兴的大合唱渐入高潮。敷文阁待制张嵲赋闲提举宫观,献上了中兴颂歌,序文强调只是为了留下历史记录:
我宋中兴,皇帝陛下得贤圣之佐,成昭明之业,而不被之声诗,荐之郊庙,协声依咏,以乐和平,汗青书策,以示得意,使后世何稽焉?(《紫微集》卷一《绍兴中兴复古诗并序》)
他在颂诗里谄媚宋高宗“过于尧禹”,强调从夏朝少康到东晋元帝的所有中兴,都大动干戈才获致的;“方之皇帝,爝火太阳”,意即比起皇帝您,他们简直就像小火把相比红太阳。宋高宗很受用,下诏嘉奖,岂料他随即去世,无福消受龙恩。
周紫芝进呈了《大宋中兴颂》,序里描绘了一幅中兴盛世图:“寝兵以来,海内清平,文章华焕,考之诗书,皆所未有。”他也另有一套吹功,说宋高宗“方之舜禹,未或远过”;还不忘表态,说作为“寒生均与斯民蒙被圣泽,敢作颂诗以申歌咏”(《太仓稊米集》卷四十三)。
张嵲与周紫芝之流原是草偃风从的无节文人,奉谀献媚无足为怪,史家郑樵竟也来赶场,却令人惊愕。他在《夹漈遗稿》卷一《题夹漈草堂》诗里可自称过“布衣蔬食随天性,休讶巢由不见尧”的,这次赶场却比张、周两位还早。正月十一,年还没过完,他便以草莱之臣上书道:
陛下诚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纵之圣,着日新之徳,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兴,自书契以来未之闻也。(《夹漈遗稿》卷二《上皇帝书》)
他的主旨希望朝廷支持他编成《通志》,倒也无可厚非。但一涉及时政话题,郑樵也显然接受了业已蜕变的中兴涵义,不仅认同君相道合而致的绍兴和议,而且视为史无前例的中兴大业。他最后表态,“微臣遭遇右文之世,宁无奋发之情”,意思说,我遇上了发展文化的大好时代,岂能没有奋发报答之情吗!联系前一年,在《上宰相书》里,他对秦桧也表达过类似见解,“以为宋中兴之后,不可无修书之文”,他是把编好《通志》作为呼应绍兴中兴的文化工程来看待的。作为大史学家,《通志》自有其价值,但在野的郑樵对中兴的表述已与定于一尊的中兴语义完全合拍,无论是自觉认同,抑或是无奈顺应,都足以表明:借助政权强力,宋高宗与秦桧对中兴语境已成功干预了舆论的走向。
权相秦桧与中兴语境之关系
中兴语境的强制性蜕变,秦桧是自始至终主导其间并热衷其事的。他的目的主要有三层。一是通过对中兴内涵的威权性规定为绍兴体制打造合法性;二是进而以维护绍兴体制为借口,严厉清算与整肃对绍兴和议及其权相专政持有异议的所有政敌;三是借助牢牢掌控的中兴话语权,在将宋高宗抬为中兴圣主的同时,也将自己形塑为中兴圣相。他的这些用心随着中兴语境的逆行也都如愿以偿。

绍兴十二年,周紫芝向权相上祝寿乐府,称颂秦桧以和议致中兴,不知怎样才能报答这无上功德:
从来定乱必以战,公以不战为中兴。两朝岁活数百万,报公福禄知难名。(《太仓稊米集》卷二十七《时宰相生日乐府三首并序》)
绍兴十五年,宋高宗为秦桧御书“一徳格天之阁”六字匾额,张嵲向权相献贺诗说,“中兴如问君臣美,万世昭时六字传”(《紫微集》卷一《贺师垣赐御书一徳格天之阁牌》),也以中兴君相来歌颂宋高宗与秦桧。谀媚秦桧为辅佐中兴之相的诗文连篇累牍地送入秦府,其中仍有周紫芝:
南北交欢万国宁,不将黔首比金缯。时人未会新盟意,要与昭陵作中兴。(《太仓稊米集》卷二十九《时宰生日诗三十绝》)
绍兴十八年,中兴颂歌最高潮时,周紫芝上《大宋中兴颂》,特别颂扬高宗“尊用元臣,以扶昌运”,“天子曰都,是任良弼”。张嵲也阿谀宋高宗独相秦桧决策议和事:“与之共图中兴之事,君臣一德,如鱼之有水。”(《紫微集》卷一《绍兴中兴复古诗并序》)
绍兴十九年,秦桧党羽张邵上奏,献媚秦桧是“我朝贤相,道义忠节”,还说在金国时秦桧为宋徽宗起草致金帅的长信,请将其稿本送史馆存档,“以彰陛下任用之当,所以能致中兴之盛”。秦桧借机表白,说信稿证明“讲和本出徽宗圣意”;高宗也自嘘“兼爱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2582-2583页)。在营造以和议致中兴的语境上,这对君相堪称心照不宣。
当然,在中兴话语权上,除了借徒党之口,若有机会秦桧也绝不忘自己发声。绍兴二十二年三月,他对高宗说:“陛下今日中兴,内外无事,所乏者循吏尔!”(2654页)既以中兴太平来粉饰时局,又以任用循吏为自己安插党羽打掩护。他还以中兴的名义提醒宋高宗坚守和议体制。绍兴二十三年七月,秦桧对高宗回顾和议来之不易:
臣伏惟陛下,昨自军兴之初,为宗社生灵计,躬至军前,权与和好,因上格天心,中兴国祚。臣至愚极陋,继亦将命,出于自请。当是时,岂意有今日依乘风云之幸。盖捐躯殉国,万一近似,乃得与今日休兵保邦之大议,非偶然也。(2691-2692页)
据《中兴小纪》卷三十六,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秦桧奉承宋高宗说:“陛下成中兴(国)之功,而知民疾苦,盖兼汉孝宣、光武之事业。”对秦桧的阿谀,宋高宗故作谦虚道:“朕何敢望二帝?然志所深慕。”
对如何掌控中兴语境的话语权与解释权,秦桧尽管主导在前,却完全契合宋高宗的当务之急,他俩不仅一拍即合,也始终配合默契。宋高宗与秦桧君相一体,出于政治需要,管控舆论,夸饰中兴,其后果十分恶劣。对自诩中兴的夸夸其谈,胡寅早在绍兴八年就提醒过:
浅士短识,久诵中兴,智者寒心,方忧极弊。若不及时大有变革,改纪国政,以趋事功,而因陋就简,日复一日,至于智者无以善后之时,正使(张)良、(陈)平复生,不能为陛下计矣!(《斐然集》卷十一《戊午上殿札子》)
其时,宋金议和还是进行时,胡寅就警告:侈谈中兴无异自我麻痹,必将导致“无以善后”。及至绍兴和议确立,为专断中兴话语权,经宋高宗默许与授权,秦桧一方面严禁对绍兴体制发声妄议,一方面诱导对绍兴中兴歌功颂德。李心传《要录》引《林泉野记》描述说:
又命察事卒数百游市间,闻言其奸者,即捕送大理寺狱杀之。上书言朝政者,例贬万里外。日使士人歌诵太平中兴盛治之美,故言路绝矣!(2772页)
于是,在绍兴体制下,和议之前对中兴内涵不同理解与各自言说的局面一去不再,“太平中兴盛治之美”成为不容质疑的中兴语境,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这种侈谈中兴之弊已远超过胡寅当年的警告,其危害正如吕中后来所说:
秦桧始则倡和议以误国,中则挟敌势以要君,终则饰虚文以为中兴,使一世酣豢于利欲之中,奉敌称臣而不以为耻,忘雠事敌而不以为怪,其弊可胜言哉。(《讲义》卷一《统论·中兴国势论》)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虚饰的“中兴盛治”决定了其后南宋国势的总格局。

绍兴更化与中兴语境的定格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权相秦桧去世;宋高宗随即标榜“更化”,史称“绍兴更化”。朝廷将如何定调绍兴和议体制以及相关的中兴语境,尤在朝野官僚士大夫的关注之列。宋高宗罢黜了权相秦桧的亲故死党,但根本不准备全盘清算。“更化”期间,最受倚重的御史中丞汤鹏举,也曾奔走在秦桧门下,高宗却看重他俯首帖耳地听命自己,不久就让他升为执政。由高宗亲擢而继秦桧为相的万俟禼、沈该、汤思退,也都先后趋附过权相,但汤思退居然在相位上待到绍兴三十年岁末。正如后人所说,这一局面完全是“一桧虽亡,百桧尚存”(吕中《讲义》卷十三),这些秦党余孽行事说话完全秉承着皇帝旨意而看风使舵。
对所谓“更化”,宋高宗定见在胸:为强化君权,对权相势力自有必要适度打压;但对秦桧参与打造的绍兴体制却绝不容忍有任何“妄议”,这无异自砸专制极权的通灵宝玉;中兴语境既然与绍兴体制休戚相关,在话语权与语义解释上当然也不容许有任何动摇。就在接报秦桧死讯次日,宋高宗“伤悼久之”,为此明定了基调:
秦桧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2773页)
次月,宋高宗赐谥秦桧“忠献”,据谥法说,“虑国忘家曰忠,文贤有成曰献”。太常寺进上谥议,在绍兴议和与中兴语境上准确传递了圣意:
故太师赠申王秦桧,光辅圣主,绍开中兴,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板荡之后,道德光天地,勋业冠古今,虽备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报之典,严于定谥,尤当先其报国之大节,传道之显効焉。(2776页)
既然宋高宗高度评价了秦桧“绍开中兴”的勋业大节,蛰伏在朝的秦桧余党闻风而动,上言时便延续权相专政时的中兴语境。同月,殿中侍御史汤鹏举献媚道:“陛下慎简群材,鼎新百度,内外莫不欢欣,而和气所以充溢,中兴之治可以持守。”(2781页)但质疑中兴、“妄议边事”者,却颇有其人,他们不仅“鼔唱浮言”,甚至“献章公车”,即公然上书。有鉴于此,次年三月,宋高宗下诏,郑重声明:
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断自朕志,决讲和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议耶?
他严厉警告那些“无知之辈”:“如敢妄议,当重寘典刑!”(2787-2788页)
据《中兴小纪》卷三十七,这年岁末,宋高宗再次下诏,将秦桧去世前不久为御制《先圣先贤图赞》撰写的赞文在国子监勒石上碑,俾其与宸翰亲书的《先圣先贤赞》同“为不朽之传”。正如研究者所说,“赞文计划是企图恢复并巩固高宗对1142-1144年的中兴修辞的主导权”(《历史的严妆》,131页),足见在所谓更化中,宋高宗对中兴话语权不仅从未松动,反而不断固化。

也是这年五月,左相沈该将宋高宗即位三十年来的“玉音”汇编成《中兴圣语》六十卷,作为讨好今上“绍开中兴”的大礼。九月,迁升御史中丞的汤鹏举奏请高宗下诏吏部与刑部,将刑部判刑与吏部用吏的合用条例“修入见行之法,以为中兴之成宪”,从人事任命与刑事法规上为“中兴成宪”保驾护航。显然,沈该与汤鹏举所说的中兴,与秦桧参与设定的中兴内涵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惟其如此,当金主亮毁约南侵戳穿其中兴幻像时,吴璘以四川宣抚使发布讨金檄文,却仍然延续了朝廷规定的中兴语境:
主上绍开中兴,宏济大业,望山河而陨涕,瞻陵庙以伤心,盖卧薪尝胆之是图,宁拯溺救焚之敢缓。然人命至重,佳兵不祥,靡辞屈己以事雠,姑欲安民而和众。(3230页)
直到次年五月,宋高宗与宋孝宗禅代之际,这种中兴语境不仅维持未变,朝野士大夫也都习以为常而安之若素了。据《于湖集》卷二十,张孝祥这年上《贺太上皇帝逊位表》,赞颂宋高宗“巍巍荡荡,繇艰难驯致于中兴,汲汲皇皇,在底定弗忘於無逸”;进《贺今上皇帝登极表》也说:“十一世而益,光迈建武中兴之事,八百年其增,卜侈成周过历之期。”张孝祥虽与秦桧之孙秦埙的同榜状元,后人仍称他“立朝之节,犹有可观”(《讲义》卷十二《科举媚权相》),但在两封贺表里,他也承认宋高宗底定中兴之局,期待宋孝宗作为宋朝十一代国君,功业要超迈汉室第十代的“建武中兴”(建武为光武帝开国年号),也隐然将绍兴中兴譬为光武中兴。
进入孝宗朝,将绍兴和议说成绍开中兴,称宋高宗为中兴之主,在中兴语境中已成定论。据《松隐集》卷三十《崇先显孝禅院记》,隆兴元年(1163),曹勋在一篇寺院记里揄扬道:“绍兴皇帝,执符御宇,光启中兴。”乾道二年(1165),他在《乾道圣德颂》里称宋孝宗“膺上圣之期,继中兴之统”,也确认“中兴之统”开创者是宋高宗。
竟是谁家之中兴?
淳熙十四年(1187),太上皇宋高宗去世,宋孝宗上谥号“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受命中兴”正是绍兴体制确立后宋高宗刻意形塑的自我定位,如今受到继承者的最终确认,他应该满意闭眼的。其后直至宋亡,记载宋高宗朝的档案典籍,冠名“中兴”几成惯例,诸如熊克的《中兴小历》,梁克家领衔的《中兴会要》,留正领衔的《中兴两朝圣政》,太常寺汇编的《中兴礼书》,佚名(一说陈均)的《中兴编年举要》(即《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吕中的《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赵顺孙编的《中兴名臣言行录》,李壁编著的《中兴诸臣奏议》与《中兴战功录》,赵牲的《中兴遗史》,佚名的《中兴御侮录》,陈骙的《中兴馆阁书目》与《中兴馆阁录》等等,甚至连黄昇辑录的南宋词选也名为《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由此可见,宋高宗是绍开中兴的中兴圣主,已然成为毫无疑义的朝野定论。
《宋史·高宗纪》论赞部分比较夏少康、周宣王、汉光武、晋元帝、唐肃宗、宋高宗说,“六君者,史皆称为中兴,而有异同焉”:其中“晋、唐、宋则岁月相续者也”,宋高宗与晋元帝、唐肃宗都维系了王朝纪年的赓续不断;而“少康、宣王、肃宗、髙宗则父子相承者也”,宋高宗与夏少康、周宣王、唐肃宗同样拥有子承父位的得统之正。然而,《高宗纪》却毫不假贷地断言,“至于克复旧物,则晋元与宋髙宗视四君者有余责焉”,即宋高宗与晋元帝所谓中兴,在光复故地上,与少康中兴、宣王中兴、光武中兴与灵武中兴相比,却同样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其论宋高宗云:
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不妨将元代史臣的这一看法与宋季史家吕中评论秦桧作一比照:
今我朝中兴,自绍兴五六年以来,张、赵之议论已叶,张、韩、刘、岳之规模已定。政事日修于一日,国势岁异于一岁。人事亦可谓尽矣。而天理不明,反在晋下。此桧所以为罪人之魁也。(《讲义》卷十)
吕中不可能直斥宋高宗,只得拿秦桧说事,甚至不无偏激地认为,南宋中兴还不如东晋南渡。在《讲义·统论》里,他从中兴规模、中兴制度与中兴国势三方面系统剖析并深入阐述了对南宋中兴的总看法。吕中未必不明白,所谓“绍开中兴”的和议体制都是宋高宗“断自朕志”,再联手秦桧共同打造的,从而决定南宋只能与东晋那样退居东南。
本文宗旨并非研判宋高宗是否“绍开中兴”,即据元代史臣之说,宋高宗也厕身“史皆称为中兴”的君主之列。至于宋高宗与前代中兴之君的成败高下,乃至所谓绍兴中兴的规模、制度与国势,也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我们仅仅依据史书记录,结合绍兴和议与绍兴体制确立前后的政局变动,考察中兴语义在内涵与外延上是如何随之移步换形的,在解释权与话语权上又是如何从相对多元宽松转向彻底专一独断的,通过中兴语境的蜕变来揭示绍兴体制的专制底色。
无论内涵,还是外延,“中兴”原就是一个语义模糊的概念。南宋学者王观国就活动在绍兴年间,他在《学林》卷一《中兴》里为其下过定义:“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也就是说,在同一朝代,能从统治衰坏而中途复振的,就可说是中兴。至于复兴到何种程度,才称得上中兴,即便同时代人,不同的个体、阶层或政派在理解上未必会有完全的共识。惟其如此,宋高宗独相秦桧以前,朝野议政虽然言必称中兴,却各抒己见,未定一说,无宁说是朝政宽松与言路未闭的正常现象;而绍兴和议以后,宋高宗与秦桧以政治迫害为手段,强力干预进而彻底专断对中兴的解释权与话语权,正是专制极权理亏心虚的表现。
宗泽、李纲与岳飞都死于绍兴和议之前,不妨回顾他们当年对中兴内涵的理解。
建炎元年十月,宗泽对宋高宗说:“天下之民,延颈企踵,日望銮舆之归,经理中原,以建中兴之业。”(《宗忠简集》卷一《乞回銮疏》)他无疑是把“经理中原”纳入“中兴之业”的。
绍兴元年,李纲尽管已遭黜赋闲,仍在和诗里宽慰友人说:“旧国故都休怅望,中兴恢复伫旋归。”(《梁溪集》卷二十八《次韵陈中玉大卿》)他也是将恢复旧国故都与中兴奏凯视同一体的。

绍兴十年,岳飞取得郾城与颍昌之捷后进军朱仙镇,准备光复旧京,同时派奇兵深入河东、河北,志在恢复中原。大功垂成之际,却收到强令班师的御诏。他在《乞乘机进兵札子》里恳请宋高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金佗稡编》卷八《行实编年五》)岳飞显然把收复中原视为宋高宗的中兴之机与自己的中兴之功,孰料一年之后,竟死于宋高宗与秦桧之手。而绍兴七年,宋高宗还对他信誓旦旦:“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金佗稡编》卷八《行实编年四》)
宋高宗与岳飞,宋高宗与秦桧,都有过“中兴”的对话,但中兴语境与语义却各不相同。在绍兴体制下,鼓吹绍兴和议“绍开中兴”,那究竟是谁家之中兴?看来只是绍兴皇帝宋高宗的中兴,而绝对不是宗泽、李纲与岳飞夙夜以求的中兴,也决然不是“中原父老望旌旗”的那种中兴!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