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三浦国雄︱日本汉学的“读原典”传统(下)
2018年12月7日,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三浦国雄先生受邀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举办了题为“日本汉学的‘读原典’传统”的讲座,本文即是根据讲座内容增订而成。此为第二部分。
岛田虔次先生与读书

岛田虔次先生(1917-2000)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自觉以成为“读者”(读书之人)为志向。因为某种机缘,先生的藏书全部归韩国的东国大学(校本部在首尔),也出版了厚重的藏书目录。在那里,不仅收藏有专业的汉籍,还有先生年轻时读过的汉籍以外的书籍。前些年我有机会访问东国大学,拜观了岛田文库,发现了一条宝贵的批注。1945年先生(二十八岁)回到故乡广岛期间,读完了文德尔班(Windelband)《历史和自然科学 关于道德的起源》的日译本后,在该书的空白处写满了感想,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即使一生以‘读者’终老,又有何可遗憾的呢?”先生的弟子狭间直树教授(中国近世史)把先生的藏书印交给了我保管,将来我也打算捐赠给东国大学,其中有一枚印“岛田虔次读”,很好地体现了先生的“读者”抱负。近年,在美国出版了傅佛果(Joshua A. Fogel)《岛田虔次:学者、思想家、读者》(Shimada Kenji: Scholar, Thinker, Reader,莫文亚细亚出版,2014年)一书,是择取先生著述中的精华编译而成,著者傅佛果在书名中使用了“读者”(Reader)一词。

从年轻时起,先生不仅嗜读汉籍,也沉迷于阅读欧美的哲学、文学、历史著作。先生擅长英语和法语,因此有时候也直接阅读英、法原著。比如,我确认过的岛田文库保管的法语版《安德列·纪德论》(George Guy-Grand, Andre Gide,纪德是法国小说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先生阅读时画了许多线条作标记。京都中国学有亲炙法兰西文化和法国汉学的传统,小岛祐马(中国哲学,本田济先生的老师)、宫崎市定(中国史)、川胜义雄(中国史、道教史)、兴膳宏(中国文学)等先生都对法国汉学深致敬意。我曾听一位精通法语的人说震惊于岛田先生居然知道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法语。(另外,接下来要提到的入矢义高先生除了英语、汉语之外,还学习过德语,憧憬德意志文化。)
岛田先生从年轻时起就醉心于王阳明和阳明学,熟读《传习录》和《明儒学案》。刚才提到藏书印,先生还有一枚印的印文是“读黄斋”,这也是先生的书斋名,可以想见先生对《明儒学案》编者黄宗羲的崇敬之情。先生曾说几乎读完了黄宗羲的所有著作,在此先介绍关于《明儒学案》的一个重要事实。在先生的藏书中,有一部江户时代后期“阳朱阴王”(表面上是朱子学,本质上是阳明学)的儒者佐藤一斋(1772-1859)手泽本《明儒学案》,该书现在并不在东国大学,而是收藏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且书中有岛田先生的批注。饶有趣味的是,佐藤一斋和岛田先生的批注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斋在栏外自由奔放地写上“痛快”“动静一贯工夫,未必在静坐”等评论意见,而岛田先生一边斜眼看着一斋的批注,一边自始至终参照郑氏二老阁本《明儒学案》进行校勘,用工整的小字记录下文字的异同。在这里,也生动地凸显了先生作为“读者”的一面。曾经听吉川忠夫教授(六朝史、中国精神史)提及,每次见到岛田先生,都会被问到“现在在读何书”?

先生的本科毕业论文也是讨论阳明学。经过我在东国大学的查阅,可以确认论文题目是“阳明学的人概念和自我意识的展开及其意义”(《陽明学に於ける人間概念・自我意識の展開と其意義》),全文大约三万字。这是1941年先生(二十四岁)向京都大学提交的论文。其中有先生的自署:“十三年(1938)入学 东洋史专攻 岛田虔次”。这篇论文的关键词或者说核心是“吾”。以论文标题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人概念和自我意识”。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吾”是作为一切尺度的“良知之吾”(良知的自我)而被发现。这是具备完整的“天理”的“圣人”之“吾”,换言之,就是“肯定现实的原理”“政治道德的最终根源”,所以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吾”和政治与道德——社会不存在矛盾和对立。但是,到了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浸染了“庶民的风气”,主张肯定“人欲”,而与社会=“名教”水火不容。在此,可以看到“自我意识的展开”,而在该“展开”中出现了李贽,他的“童心说”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即与社会矛盾对立的个人的诞生”。这里所谓的“个人”也可以说是“人欲的个人”,但重要的是“个人”是作为社会的批判者出现,岛田先生引入西欧的语境,在这样的自我之中发现了“近代精神”(后述先生的著作则改称“近代思维”)。就这样,先生以“吾”的展开鲜明地论述了从王阳明到李贽的思想史演变。先生的理解方式,并非将“吾”视为自满自足的封闭体,而是不断将“吾”置于社会中加以观察,从与社会的关系中把握“吾”,是一种富有生气的动态理解。先生的这种以“内”(吾、自我)和“外”(社会)的斗争来把握思想史的方法论,与其说在本科毕业论文的阶段就已经出现,毋宁说是作为该论文的框架被使用,令人惊叹。这一框架也运用于《朱子学和阳明学》(《朱子学と陽明学》,岩波书店,1967年)一书,此书虽然是入门书,但作为专业书来说,水平也相当高。

这篇本科毕业论文还有许多值得惊叹的地方。这也关乎根本性的评价。在当时(1940年代)的国际中国学界,基于文献资料追踪王阳明—泰州学派—李贽这一阳明学系谱,并进行再评价的尝试,实属空前的壮举。
这篇毕业论文提交七年后的1948年,先生在任职的地方城市的书斋,完成了《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筑摩书房,1949年初版,1970年再版)一书的撰写。正如先生在序文中所交代的:“扩充了引用的书证,增加了叙述的波澜,至于根本宗旨,则与七年前的论文相差无几”,此书是在前述本科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改订而成,这也着实令人惊叹。不过,本书的分量大增,字数达三十万字,较毕业论文增加了十倍,新增撰写了第四章《一般的考察――近代士大夫の生活と意識》。同时,叙述也精彩纷呈,充分发挥了七年间苦心钻研的水准。更为重要的是公开出版的重大意义。公开出版后,本书给众多的中国学研究者带来巨大震撼,一致认为是必读书,成为战后日本中国思想史、历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强势著作之一。先生的著作大多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如《朱子学と陽明学》,截止2012年已经重版四十多次),近年本书由井上进教授加入补注,作为平凡社“东洋文库”的一种出版(2003年)。“东洋文库”是以日文版的形式收录亚洲各地区的代表性古典名著的一大丛书。岛田先生的著作收入该丛书,意味着成为了今后长期阅读的阳明学研究的“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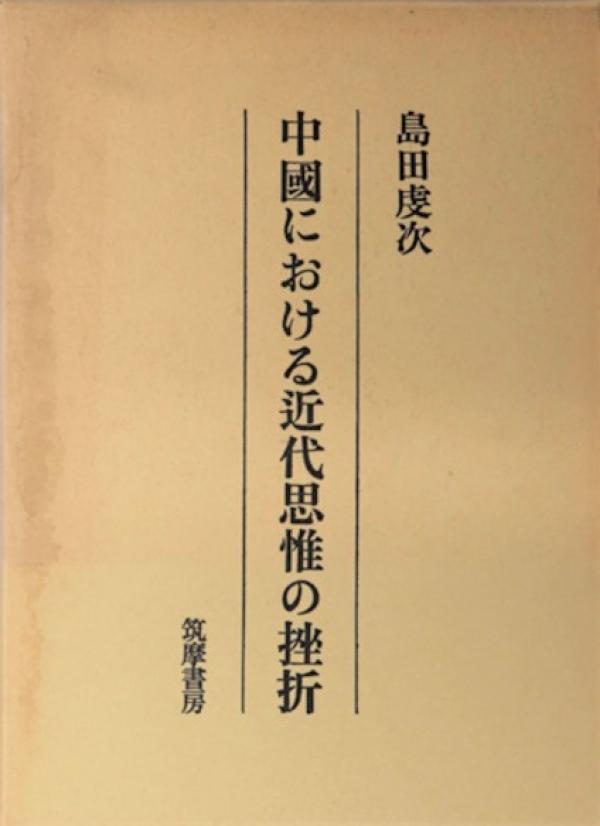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书中使用的“挫折”一词。这是毕业论文里没有而在公开出版的书里才出现的词,应该是七年间先生反复揣摩酝酿而来的观点。李贽作为从王阳明—泰州学派发展而来的“吾”的必然归结,背负着“名教罪人”之名被弹劾,不得不在狱中自我了结。先生使用“挫折”一词,当然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和思想的脉络。对此,沟口雄三教授(中国思想)针锋相对,认为如果按照岛田先生那样以欧洲式的框架来理解这段思想史,确实必然得出“挫折”的结论,但若以“中国本身固有”的逻辑来理解,那就不是“挫折”而是“展开”。除此以外,先生提出了中国史上何谓近代等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种种重要问题,都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入矢义高先生与读书

入矢义高先生(1910-1998)在中国学的诸多领域积累了卓越的研究成果,在此仅从“阅读/读书”的角度出发,重点介绍先生的禅学研究。而先生的禅学研究的起点是俗语(白话)研究。
入矢先生提交给京都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公安派的文学理论研究》(《公安派の文学理論について》),听说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郭沫若,但我都还没有机会拜读。据我所知,1939年先生(二十九岁)进入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工作,参与吉川幸次郎先生主持的元曲研究项目,从此开始了对俗语的研究。据先生回忆,当时与现在的条件完全不同,连便利的工具书和索引都没有,况且元曲这种文学中的小道,更没有注释书和参考文献(只有《西厢记》有明人的注释),从哪里以什么方法入手研究,完全如五里雾中,只能全力以赴一种一种地研究《元曲选》百种。最开始的一年间,先生也不看报,不问白天黑夜,都与元曲为伴,完全是蛮干。

当时研究所除了《元曲选》外,还举办了《朱子语类》(岛田虔次先生也参加了)和韩愈诗的会读会,先生曾说:“读书的快乐是从此时培养出来的。”另外,先生对当时吉川幸次郎先生反复说的一句话印象深刻——“读书除了要把握书中说了什么,同时,还应该理解是怎么说的”(以上根据入矢义高:《自己と超越―禅・人・ことば》,岩波书店,1986年)。
入矢先生的藏书现在收藏于东京的禅寺龙云寺(临济宗·妙心寺派),我去年(2018)曾经前往拜观。但是,这里保管的并非先生的全部藏书,而只是有关禅学、白话研究的书籍,以及先生的文稿、草稿等。这里插一段题外话,在先生生前,弟子们曾私下谈论,如果出版先生的全集,就需要把先生的藏书全部拍照出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先生读过大量的汉籍,并且读过后都会在栏外或者在浮签上以独特的小字写入批注,表达自己的见解。对此,我曾到先生位于比叡平(滋贺县大津市)的住宅实地确认过。
回到先生俗语研究的话题。我在龙云寺发现了题为《元曲语汇》的稿本,是老旧的油印本(俗称蜡版)。虽然说“发现”,但并不是我第一个发现,专家们应该早就知晓此事。根据《凡例》可知,这是将人文科学研究所元曲研究室编制完成的约三万张《元曲选》卡片以注音字母的顺序排列而成,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应该认为是词汇集,而不是例句集。不过,先生照例在该稿本上写满了朱墨笔批注。记得我在人文科学研究所当助手的时候,装着《元曲选》卡片的箱子放置在一个大房间里,经常有元曲专家前来调阅。

除此之外,在人文科学研究所还保存着先生主持编纂的俗语例句集,姑且命名为《近世俗语语汇》。该例句集按照注音字母的顺序记载例句,有时候一个俗语词汇下面还会列举出多个例句,由多达几万张的数量庞大的文稿构成。虽然现在出现了好几种电子辞典之类的检索工具,可以立刻查找到例句,但是,这样的精心力作就此埋没的话,实在可惜。
说先生的脑子里装着所有的近世俗语,也并不为过。先生被称为“行走的电脑”,实际上,我曾经好几次当场目击先生瞬间判断出某个词是俗语还是文言的情景。先生曾以“禅语徒然”(《禅語つれづれ》,入矢义高:《求道と悦楽―中国の禅と詩》所收,岩波书店,1983年)为题,为容易误解的俗语撰写了详尽的释义。题目虽然是轻快的随笔风格,但内容完全不同,一直是阅读禅宗语录的必读指南。比如,先生列举了马祖禅的核心纲领——“即心是佛”和“是心是佛”,指出二者都是“心是佛”的意思,“是佛”的“是”是“である”意义上的系词(文语的“为”),而开头的“即心”和“是心”的“即”和“是”都“具有强烈规定和从正面提出后续名词为立言的主题的功能”,前者(“即心”)可以理解为“心本身”“正是心”,而后者(“是心”)与前者意思虽然相同,但与前者相比语气较弱。我们学习外语,不论如何精进上达,但到最后阶段的“语感”总是难以学到位,而先生则对“语感”的把握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实先生还举了“即心即佛”为例,论述了三者微妙的差异,在此从略。)
只是收入《禅语徒然》的词汇并不多,后来终于满足了学界和宗门(禅宗界)的期待,在古贺英彦氏(佛教学、禅学)的协助下,先生完成了《禅语辞典》(思文阁出版,1991年)的编纂。这部辞典的释义自不必说,例句也有不少颇堪玩味。这里且举一例。关于“只么”,《禅语辞典》给出了明晰的释义:“‘只是……’的意思。‘么’是接尾词,无意义。不是‘只管’的意思。也写作‘只没’‘只物’‘只摩’。”“只没”“只物”“只摩”都分别列举了例句,这里仅介绍“只没”的例句(以下的引用稍有省略):
有一人高塠阜上立。有数人同伴路行,遥见高处人立,递相语言,此人必失畜生。有一人云,失伴。……又问……缘何高立塠上。答:只没立。(《历代法宝记》)
大家不觉得站在山岗上的人“只没立”的回答意味深长吗?一群人结伴同行看到有个人孤零零站在山岗上,有人猜测他丢了牛羊,有人则怀疑他跟伙伴走散了,所以才站在高处四顾寻找。有人直接上前询问,他却回答“只是站着”,并无其他理由。其实这里也反映了思想问题,独自站在山岗上的这个人拒绝自己的行为被赋予任何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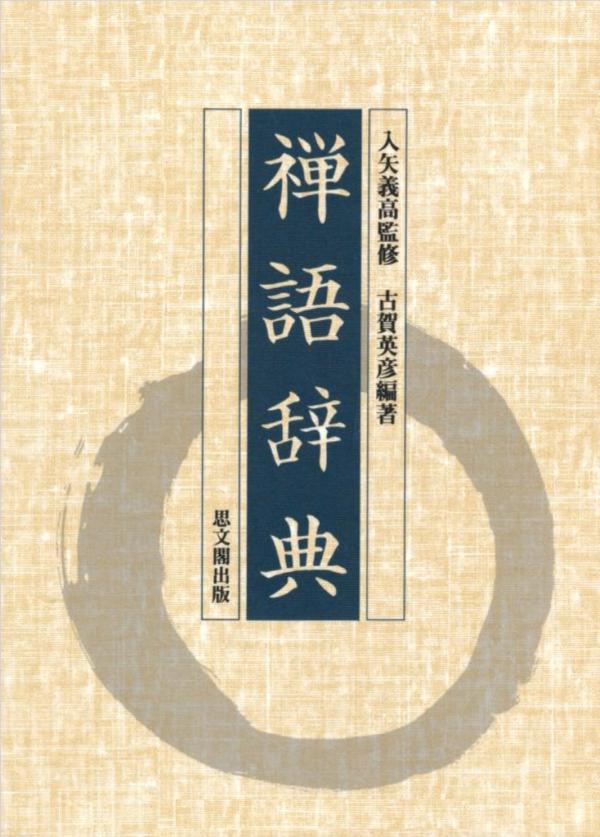
那么,当时在中国的研究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对此,入矢先生曾说:“在中国研究佛典和禅宗语录的语法的学者十分罕见”。先生批判其中著名的语法学家吕叔湘的论文《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对“在”字的词源索解“存在很多不合逻辑和误解的地方”(前揭《禅語つれづれ》)。另外,当俗语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53年)——出版后,先生马上就撰写了措辞严厉的书评(《中国语学研究会会报》二十九,1954年)。
但是,先生的禅宗语录研究决非止步于语言研究的范畴,而是在精准地掌握俗语的同时,上升到把握禅的本质,体现了先生学问的博大与新颖。于是,先生倾注心力重新解读唐代的禅宗语录。众所周知,在日本特别是在禅寺,阅读禅宗语录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日本的禅门缺乏区分俗语与文言的意识,如果实事求是地说,那就是误读泛滥。不过,先生对江户时代临济宗学僧无著道忠(1653-1744)的《葛藤语笺》(“葛藤”指禅宗中难解的语句和公案)却给予了高度评价(讲演录《無著道忠の禅学》,1991年,收入入矢义高:《空花集》,思文阁出版,1992年)。

先生对日本禅门的批判,不止于这种语言学上的问题。日本的禅门理所当然地重视坐禅。日本曹洞宗的开山祖师道元禅师(1200-1253)倡导“只管打坐”,这一教义至今仍然作为禅门修行的要义得到遵守。也许先生针对的不是坐禅的修行法本身,而是反对不坐禅就不能理解禅的观点。事实上,先生曾经这样写道:“奉行‘禅超越语言、文字’的体验至上主义,一直盘腿坐着,并不是真正的禅。”(《禅と文学》,收入前揭《求道と悦楽》)先生所用的不是身心修行的宗教徒的方法,而是通过语言的回路探索禅的真谛。与其说因为先生不是宗教徒而是学者,倒不如说先生识破了禅的奥妙是“语言”。提倡“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其实在结构上蕴藏着矛盾。“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本身就已经依靠语言,唐代以降,禅僧们大量的言论作为语录留存下来。先生将唐代禅僧镜清的“出身犹可易,脱体道还难”(《祖堂集》卷十,又《碧岩录》第四十六则“镜清雨滴声”)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这句话的意思是,“开悟(‘出身’)毋宁说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将开悟本身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脱体’)”。请看先生对镜清这句话的解释:
诚然冷暖自知,但是仅仅是知道并不够,还需要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所知,从而使“知”客体化。经过这个反省的过程,重新确认获得“知”的自己与该“知”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不经过自我检验的锻炼,觉悟和美就不能真正内化为自己之物,也不能向外人表达和展示。(《中国の禅と詩》,前揭《求道と悦楽》所收)
这只是先生用自己的话对镜清的语言作出的解释,不应该认为在这些话背后也有先生如何用语言表达自己悟道的纠葛。虽说如此,我也不认为先生完全是以旁观者或者研究者的身份进行解说。正如上述,先生不是以悟道为目标的宗教徒,而是探究真相的学者,但是,先生通过对唐代禅家表达悟道的语言的分析,与他们的“悟道”产生共鸣,并共享了悟道。正如上述,先生有一部题为“求道と悦楽―中国の禅と詩”的著作。这里所说的“求道”,首先是以悟道为志向的禅家的事业,虽然知道先生不会同意在那里也有先生自己的投影——不过,在该书的序文中先生说:“很有可能被看成是我要把自己当作求道者呈现出来,这让我感到不适”——但是,在我看来,入矢先生只能看成是究明学问的求道者。

虽然已经讲了很多,最后,我想向大家介绍入矢先生对几则禅宗语录的解读来结束我的讲座。禅宗语录确实是匪夷所思的文献,基本上没有注释,只是简短的问答和说法的赤裸裸的集合。禅宗问答从一开始就拒绝佛教教理,等待优等生式回答的是师傅的棒和喝(大声叱责)。那种状态恰似孤身一人置身于荒无人烟之地思考如何生存时的紧迫。在这一点上,即使同样是语录,禅宗语录与在师徒之间共享“理”或“道理”的《朱子语类》就完全不同。日语中的“禅问答”一词,意思是莫名其妙的问答,其实某种意义上可谓切中要害。比如,问师傅“如何是佛”,可能徒弟只会听到师傅“麻三斤”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回答。简直“荒谬”!但是,入矢先生始终想把被“语言”“道断”的空无回归到“语言”。不过,在此请允许我引用比较“有道理”的禅问答吧。
《临济录》是入矢先生年轻时学习中国禅的契机,现在引用其中一段文字,比较旧解和先生新解的不同:
○“你欲得识祖佛么。只你面前听法底是。学人信不及,便向外驰求。”(《临济录·示众》)
【旧解】“你们是想知道祖师和佛吗?你们在那里听说法的那人就是。但是你们对此不够相信,所以才会向外求索。”(朝比奈宗源译注,岩波文库,1935年)
【新解】“你们是想见祖佛吗?现在在我的面前听法的你正是祖佛。因为你们对此不够相信,所以才会向外求索。”(入矢义高译注,岩波文库,1989年)
在旧解中,“祖佛”(不是“祖师”和“佛”的意思)和“你”之间是有距离的。可以确定“那人”是“祖佛”,而重要的“你”和“祖佛”的关系暧昧不明。但是,在此临济想要表达的正是“你”即(=)“祖佛”。这是临济禅的核心,所以必须按照入矢先生的读法进行解读。入矢先生有如下注释:“‘你’和‘面前听法底’是同位语,并不是‘在你面前听法的人’的意思。”

最后,介绍一则令我最为感动的入矢先生的解读。对象文本是《庞居士语录》的下面一节:
○“居士因辞药山,山命十禅客相送至门首。(居)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有全禅客曰:落在甚处。士遂与一掌(打一巴掌)……”(《庞居士语录》)
这里的“居士”是指庞居士(?-808)。“居士”是在家佛教徒的称呼。庞居士被称为“东土维摩”,在偏僻乡村的陋室中与妻子度过了一生。“药山”是药山惟俨和尚(745-828),嗣法石头希迁,是中国禅宗史上的杰出禅僧。
先生的解读如下:
历来将“好雪!片片不落别处”读作“好雪片片,不落别处”,纯粹是误读。“好雪!”是感叹之语,“不落别处”是指一片一片的雪花都恰好落在了应该落在的地方。此时,居士看到雪的所有的一片一片虽无心而似有意般着落于该着落的位置,为这样的精彩感动不已。居士的发言不是针对满地的白雪或者映入眼帘的一色银装素裹的世界,更不是着眼于在清净的“平等无差别”的世界中呈现了雪片的差异。居士看得出神的只是一片一片的雪花宛如神迹般飘落的样子本身。(入矢义高:《龐居士語録》,筑摩书房,1973年)
不管读几遍都让我无比感动。为何可以对短短八个字作出如此出色的解读呢?在此,不仅体现了语言学的、学问的力量,更体现出入矢先生伟大的人格力量。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