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讲座︱夏德明:全球史视野下17世纪的帝国与宗教
全球史起源于美国,于是英语学术刊物所衍生的权威以及英语的全球霸权地位,使得全球史从一开始就烙上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印记,甚至有人将其称为英美国家的外销品。我们不禁要问,全球史最终会变成一种同质化的全球史吗?在这种情况下,就很有必要了解英语世界以外地区全球史的状况。德国,这个始终站在史学理论前沿的西欧国家,近年来就出现了多位享誉世界的全球史家,十分值得关注。相较于英美国家的全球史,德国的全球史有其自身的特点,这说明全球史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述。德国全球史家往往都具有区域史的研究背景,可以视为从边缘来书写全球史的范式,这一点与美国的全球史家相比,就显得更加客观。
德国全球史的标志性人物是康斯坦茨大学的尤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他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C. H. Beck, 2009)是欧陆最重要的全球史作品,影响甚至超出了学术界,被誉为“研究19世纪的布罗代尔”。除了奥斯特哈默以外,近年来介绍到中国学界的还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斯特凡•贝格尔(Stefan Berger)等人。其中,仅2018年中国大陆就出版了康拉德的两部著作,分别是笔者译的《全球史导论》(Global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 C. H. Beck, 2013)和杜宪兵教授译的《全球史是什么?》(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可见,中国学界了解德国全球史状况的愿望,是十分迫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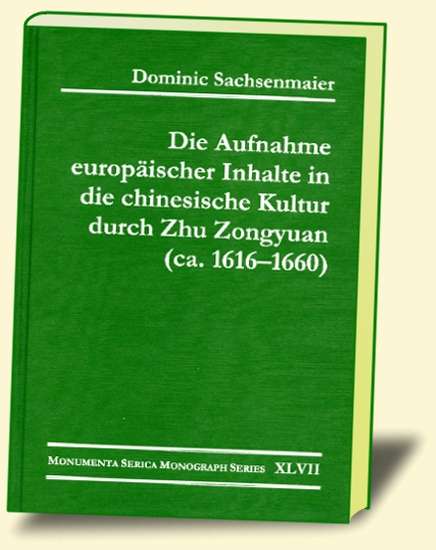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这两年有计划地组织了德国几位著名的全球史家来沪讲座,以便我们更系统地了解德国全球史的研究路径和发展脉络。去年9月我们借《全球史导论》中文版的新书发布之际,邀请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康拉德教授来沪作题为《19世纪“时间”概念的全球性转变》(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in the 19th Century)的报告。今年4月11日,我们又邀请了哥廷根大学的夏德明教授,作题为《17世纪的宗教与帝国:全球与本土的若干问题》(Empire and Religion in the 17th Century, Global and Local Questions)的报告。
夏德明早年在德国南部弗莱堡大学读书,导师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沃夫冈•莱茵哈德(Wolfgang Reinhard),并于1999年完成了有关朱宗元的博士论文《欧洲知识在中国文化中的接受——以朱宗元为例》(Die Aufnahme europäischer Inhalte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durch Zhu Zongyuan (ca. 1616-1660), Nettetal: Steyler, 2002)。博士毕业后,他辗转于美国、中国和欧洲的科研单位,终于在2015年受聘为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汉学教授和东亚系主任。夏德明教授的学术兴趣是历史上以及当下中国的跨国和全球性联系,对全球史在德国的兴起背景和发展现状也有系统的研究。他近年出版了两部英文著作,分别是由博士论文改写的《一位足不出户之人的全球性纠葛》(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 A 17th 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and his Conflicted Worl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和《全球视野下的全球史》(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据夏德明教授告知,这两部英文专著的中文版都将于近期面世,前者的译者是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张旭鹏研究员,后者的译者是同一单位的董欣洁研究员。由两位全球史专家亲自操刀中译,在译文的质量上无疑得到了保证,令人十分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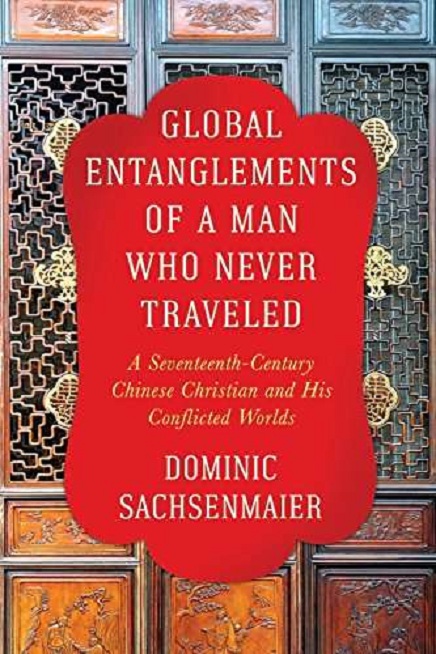
《全球视野下的全球史》
夏德明此番在上海大学的讲座以朱宗元为切入点,探讨17世纪的全球化现象,以及宗教和帝国在全球性网络编织中所起的作用。熟悉全球史写作的人都知道,19世纪是全球史研究的热门,有贝利(C. A. 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Oxford, 2004)和奥斯特哈默的《现代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这两部扛鼎之作,18世纪也有奥斯特哈默的《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Die Entzauberung Asiens. 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 Jahrhundert. C. H. Beck, 1998)这种高水平的作品。相对而言,17世纪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夏德明教授在他的新书中,就是从宗教和帝国两个维度来解析17世纪。康拉德曾在中译本《全球史导论》的“序”里提到,“人们可以预期,在对早期全球史家对‘联系’的狂热有所矫正的同时,网络化的边界和特定地区对全球化挑战的回应,则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夏德明的这部聚焦朱宗元的书,无疑就属于这一路径的研究。
朱宗元约于明万历四十四或四十五年(1616-1617)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士大夫家庭,顺治五年中举人。没有证据表明,他去过浙江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不过,身处明末清初的朱宗元,却有机会接触了许多耶稣会士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并受洗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教名葛斯默(Cosmas)。从朱宗元的著作来看,例如《答客问》、《拯世略说》,他写作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证明基督教是值得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其他阶层人士关注的,于是他主张“天学”(即有关基督教的学问)不仅与儒家传统是不悖的,而且都是通向一个原始的起源。
如果依循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提出的观点,朱宗元身处的明朝正位于全球经济的中心。这不仅意味着全球贸易的互联,而且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在人群、技术、思想都有交换。但同时,朱宗元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乱世。彼时正值明清鼎革,起源于东北的女真人开启了对中华帝国近三百年的统治。从全球范围来看,不仅东亚在17世纪经历着政治秩序的崩溃和重建,欧洲在1618-1648年也卷入长达三十年的宗教战争旋涡之中。可见,17世纪的东方和西方,都处于政治动乱和思想激荡之中,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吗?它们彼此之间有联系吗?对于这一全球性危机,环境史学者指出,17世纪30年代全球范围内经历了一个寒冷期,或许是天气加深了社会的危机。

对朱宗元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明末清初中国的基督教既有全球性的一面,又有本土化的一面。一方面,晚明中国的天主教已经一定程度地本土化了,尤其是在义理和术语上,例如“天堂”、“地狱”、“会长”等词汇都是地道的中文术语。夏德明提到,使用本土化术语,不仅是知识精英之间对话和纯粹义理上取得的一致,更是两大帝国权力体系之间的接触而产生的妥协——彼此都是在谋求霸权的同时却面临内乱。但另一方面,17世纪的天主教会又是一张全球性的网络,通过机制性的通信来保障信息渠道的畅通,再者是通过殖民的方式来搭建贸易网络。夏德明指出,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17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徒是不允许担任牧师的。他分析,此中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基督教徒对拉丁语这一宗教语言的掌握程度,远远达不到主持宗教日常仪式的水平;二是罗马教廷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徒不值得信任,他们只信任“白人”(Bianco,意大利语“白色”的意思)。令人不解的是,同样处于东亚的日本却被视作是“白人”。这一区别对待,说明17世纪天主教知识谱系中对人的分类,不像19世纪的人种学或民族学那么严格,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划分。
分析以朱宗元为代表的知识精英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冲突和矛盾,让我们看到17世纪全球性基督教网络中个体人物的能动性。朱宗元是一位举人,无疑是知识精英阶层的一员。西方传教士绘制的新式中国地图在中国十分畅销,表明17世纪中国的知识精英是乐于接触外部世界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的描述也是充满了想象,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话语都是用来建构儒家理想国的。反过来,欧洲批评家眼中的中国人又是何种形象呢?由于清廷采取了禁教的政策,基督教传教士不得不转战南洋,例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罗宋一带徐图发展,因为那里有许多华人劳工和移民群体。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部分是依据对这些下层人物的叙事建构起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17世纪,不仅基督教在华扩张,伊斯兰教也在南亚扩张,甚至佛教也处于剧烈的变动和转型之中。总之,16-17世纪的世界在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东西方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于是西欧殖民者或传教士不得不尊重本土的文化,亚洲也呈现出文化多元的景象。甚至中国的儒家思想——且不称之为“儒教”,也在经历着改革,出现了李贽、王阳明等思想大家。他们的思想中,都隐含着一种儒、释、道合流的意味。由于时间关系,夏德明教授没有就帝国和帝国主义在17世纪全球网络中的作用,进一步地展开讨论。
在提问环节,笔者提出,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绘制的中国地图实际上只包含长城以南的省份,没有将蒙古、东北、新疆和西藏纳入其中。这一现象,部分反映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政治疆域的阶段性,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西方耶稣会士的“鞑靼观念”。从13世纪起基督教世界就开始把蒙古人以及蒙古帝国在东欧、中亚和北亚的后裔称为“鞑靼”(Tartar),并把内陆欧亚称为“鞑靼利亚”(Tartary)。随着17世纪耶稣会士来华,西方对“鞑靼”的认知有了更新。来华传教士认为,满人也是鞑靼的一支,属于东部鞑靼,并把“鞑靼”想象成一个对抗中国数千年的连续共同体。耶稣会通过书信这一严密的机制,将知识和讯息进行全球互联,一方面从广度和深度上更新了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基督教世界对内亚“鞑靼”人的认知,但另一方面却又沿袭了宗教上的偏见,对西方语境中“鞑靼”(Tartar,与拉丁语“地狱”Tartarus谐音)一词的误写视而不见。这一错误直到18-19世纪现代东方学家群体的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矫正,应当写作Tatar。这一现象,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17世纪全球知识网络中的细节之处。夏德明教授认为,关于17世纪耶稣会士为何没有更正“鞑靼”的写法,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