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卑微者如何能够梦想?|写作大赛作品展示
*原文完整标题:《重述一个时代:卑微者如何能够梦想?》
文|党艺峰
1、引子

那里是我一定要去的!
很久以来,丁文彬的脑子里一直回旋着这句话。自从母亲去世之后,哥哥是这个世界上最关爱他的人,可是,贫穷的底层连发自灵魂深处的关爱也会压迫得被爱者有一种刺骨的疼痛。天天听着哥哥嘴里柴米油盐的计较,他知道,这个家里越来越待不下去。何况他已经从心里厌倦南方的浮薄,他决定到自己记忆中的北方去,到神圣的孔府去。好在哥哥出门去杭州一段时间了,家里其他人不会在意他的存在。
乾隆十八年(1753)四月底,丁文彬拿着一两一钱银子,背着简单的行李,从江南的松江府开始走在仅仅属于他自己的路上。在那个时代,赶路的行人都匆匆忙忙,可在这条属于自己的路上,丁文彬也许是要享受整个生命中唯一的安静,他光着头,打着把破旧的雨伞,慢悠悠地走着,一天只走五、六十里的路程。近一个月的时间,丁文彬几乎没有说话,每天吃一斤多大饼,到了旅店,只是闷着头抽烟睡觉。整个旅途没有一点故事,没有一点奇遇。如果真有旁观者的话,一定会因为这个安静的旅客觉得奇怪。到了五月二十八日这天,丁文彬终于来到孔府的大门口。
一出所谓盛世的“神圣喜剧”就此开始上演。
这出“神圣喜剧”的主人公就是丁文彬,而它的全部情节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一个卑微的人如何梦想自己的幸福。梦想自然是属于个人的,而属于个人的梦想必须在受限定的制度空间中展开,因此,所谓梦想就是发生在个人精神空间内部的一种较量、一场斗争。这较量和斗争的一方是均质的制度空间对人性的强制性塑造,另一方是个体意识深处的渴望,它携带着个体全部的历史性遭遇试图在均质的制度空间中描绘出自己的位置。
对于丁文彬来说,在均质的制度空间中描绘出自己的位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上帝之命总以有德即有位”[1],这无疑是丁文彬全部梦想的根源。德行和权位,是典型的中国式概念。在天人合一的神秘秩序中,在儒教伦理的特殊视野中,德行和权位都关涉到个体幸福,孔子谈到富贵的时候就说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也许我们不能对丁文彬有太高的期望,他不可能如孔子那样洒脱。他已经把自己的梦想埋藏得太久,在决定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时,他将开始为了梦想而斗争。
在整个人类史上,为了梦想的斗争从来都是悲剧性的。只有天才的但丁才敢于期望“神圣的喜剧”,他把自己伟大的诗篇命名为“血统上而非习俗上的佛罗伦萨人但丁·阿利吉耶里的《喜剧》开始”,后来,人们称之为“神圣的喜剧”。在但丁那里,神圣喜剧就是尘世生活的幸福和彼岸的永恒幸福相互结合,因此,“天堂就不只是在天堂里存在了,而且也存在于人间。”[3]丁文彬不是天才,但是他怀着莫名的恐惧,不愿意自己成为均质的制度空间一个无名的点状物,更重要的是,在几乎不能期望幸福的底层,竟然只有在一出“神圣的喜剧”里才能安妥他对幸福的梦想。
当然,最后的死亡已经证明他的失败,在所有人的眼里,他依旧只是一个傻子甚至疯子。然而,这出“神圣的喜剧”还刚刚开始。
2、不是记忆中的北方

乾隆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丁文彬来到孔府的大门口。
那些孔府的门丁见惯了各色达官贵人的排场,他们都有久经锻炼成的察言观色的本领。这个正站在他们面前的人,衣履不整,身材瘦小,满脸是走长路留下的风尘,说着一口南方土音的官话。在炎热的午后,门丁甚至不愿意打量面前的这个人,他小声的请求也根本没有传到门丁的耳朵里去。
丁文彬越来越没有耐心,他开始大声地叙述自己的故事,要求门丁尽快通报孔府的主人——年轻的衍圣公孔昭焕接见自己。丁文彬的声音已经失去控制,近乎咆哮。夏季的午后,应该是最休闲的时候,人们希望能找出一块阴凉,或者希望有点什么故事,让自己忘掉炎热也好,丁文彬失控的声音终于吸引了一些人。
在一个对所有传闻都极其敏感的时代,孔府的门丁坐不住了,他们中的某一个匆匆忙忙地去通报主人。不过,这样做,也许是要求主人能指示如何处置这个让他们恼火的家伙,所以,门丁的通报一直强调丁文彬看起来实在行止可疑。然而,孔昭焕并不完全相信门丁的叙述,他派遣更老成的家人去打探消息。
在孔府的门房里,丁文彬接过那些门丁递上的纸笔,开始写作自己的来历。不一会儿,孔昭焕就看到这一纸墨迹还没有干透的名帖——
“予小子丁文彬,原系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人,予丁父善至祖公世居务农,有叔祖丁芝田在北路教习,曾与先岳老圣公为盟。予小子带府留住数日后,予子回松,荷蒙岳父面命,今在松修道,于己巳年曾有《文武记》二本、《太公望传》一册申付松江学政庄有恭,至今五载未有复命,今续成《洪范春秋》五本,已终帝命,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所以卫圣门之道,敢伸达尊览,余面谈,不暨。”[4]
这样的文字呈现在孔昭焕面前,年轻的衍圣公觉得异常可笑,自己家哪里就会有这样的女婿呢?姐姐早在雍正十四年(1736)就嫁给了松江府的张伯耕,妹妹虽未出阁,但也已经许了人家。笑意也许还没来得及浮上孔昭焕的嘴角,他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可以一笑了之的故事。所谓“已终帝命,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所以卫圣门之道”的事情不是什么人都能随随便便谈论的。
孔昭焕没有犹豫,立即派家人搜索丁文彬的行李。行李里有一部书和它的副本,还有一本丁文彬自己编制的皇历。那些门丁也按照主人的旨意不动声色地控制了丁文彬的人身。到这个时候,丁文彬仿佛置身事外,一点不在乎这些异常的举动,他本来就要将那些文字送给衍圣公的。
那部书摆在面前,孔昭焕不能预见自己会读到什么内容,但一定做好了随时调整表情的准备。现在,他满脸是庄重的神色,手指多少带点迟疑翻开那看起来有些潦草的封面。“大夏”、“大明”、“昭武”、“天帝”、“天子”……这样一些字眼突然撞进他的眼睛,不需要再看后面的内容,孔昭焕立刻就一幅怒发冲冠的样子。当然,怒发冲冠的样子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很快,他又换作暗自庆幸的表情。需要在短时间里不停调整表情是非常累人的事情,但对于孔昭焕来说,这是必须的。
已经平静下来的孔昭焕迅速通知曲阜知县孔传松逮捕丁文彬,同时密函告知山东巡抚杨应琚。做完所有这些,孔昭焕决定出来看看丁文彬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他一定有些失望。等到丁文彬被衙役们带走后,孔昭焕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记录下自己的各种表情,为了这些表情不显得夸张,他也写下自己看到的丁文彬——“状托疯魔,踪疑诡谲”[5]。什么意思呢?孔昭焕只是表达了自己的疑问,他不能理解这个人。不管孔昭焕能不能理解丁文彬,这份奏折都会用最块的速度送达京城。
被衙役送到有些阴森的监狱,丁文彬还不能理解刚刚发生的事情,突然的变故迫使他必须给出一个解释。一个人只能借助自己的记忆理解身外的世界,理解突然遭遇到的事变。丁文彬记忆的北方存在于神话之中,然而,他只能从南方走到北方,没有人能逆反着时间走进神话。现在,丁文彬似乎已经明白,这里不是他记忆中的北方。
3、丁文彬是谁?

接到孔昭焕的密报,正在沿河巡查蝗灾的杨应琚来不及回到济南抚署,命令孔传松亲自押送丁文彬就近赶到兖州。六月初三,丁文彬就跪在了兖州府的大堂上,面对杨应琚的讯问,他开始描述自己。
“父母俱亡,止有一个哥子,并无兄弟,未曾婚娶,没有儿女的。小子从前跟了族叔祖丁芝田到过曲阜,见过老衍圣公讲尧舜之道,辟佛老邪教,曾把两个女儿许配小子的。今年……于五月二十八日到曲阜,公府里门役不传,小子写了说帖送进才取书去看。谁知他嫌小子穷苦,不肯传见,反嘱县官拿住了。”[6]
这是丁文彬描述自己的开场白,他突然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典型的通俗而且庸俗的才子佳人故事里了。
这个才子佳人故事的起因应该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那时,孔府的大小姐嫁给了松江府的张伯耕。二十一岁的丁文彬,只是众多围观这场奢华婚礼的看客之一,由此激起一点羡慕甚至于嫉妒的情绪都是正常的,而对于丁文彬来说,这场婚礼的意义具有别样的意味。丁文彬始终生活在贫穷饥饿的社会最底层,他几乎没有窥视其他等级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这场婚礼提供了一个机会,他看到了用夸张的形式表演出来的其他等级的生活场景。
看过一次表演,就想象着让自己成为同一故事的主人公。丁文彬的想象当然是由这场带有表演性质的婚礼诱发的,但真正的因缘却另有所在。清代的钱大昕在《正俗》中写到: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于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乎其近于禽兽乎!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7]
如果透过钱大昕的道德偏见,我们不得不说他几乎完整地表达出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事业的全部特点——小说必然是世俗化的产物,它的内在机制恰好与现代人建构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基本规则相一致。
虽然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去描画他的阅读经历,但丁文彬一定是小说教中人。因为小说教中人未必一定要拥有阅读史,但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小说家则闭门自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8]在某些时代,闭门自处、离群索居,并非一种个人姿态,它可能会成为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的标识。康熙五十五年(1716),丁文彬出生于杭州。不久,父亲死了,他跟随着做女佣的母亲到处流浪。杭州虽然被称之为“人间天堂”,但它不属于丁文彬。即使在后来的流浪生涯中,他依旧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空间。因此,出生就意味着他必然成为一个异乡人,生活在自己永远不能进入的异乡。在这种境遇中,丁文彬成为一个天生的小说教中人。
作为一个小说教中人,在看过一次表演之后,按照小说的内在机制,按照这个时代的惯常模式,丁文彬开始想象自己的生命,开始把自己安置在一个才子佳人故事里。所有通俗而且庸俗的才子佳人故事都不能仅仅作为简单的浪漫剧理解,它有着需要做深长思考的意味。才子佳人故事的背景是成熟的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在根本上是把可能颠覆社会秩序的底层暴力革命转化为日常的身份革命,因此,才子佳人故事只是发迹变泰的表征符号。不过,故事要达到自己的浪漫结局,主人公必须具有好运气,具有某些可以炫耀的资本。
可惜的是,丁文彬缺乏好运气,也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资本,甚至身材和长相不管怎么看去也不像才子佳人故事的主人公,他必须寻找能够支撑这个故事继续发展下去的可能性。
4、在法官和医生之间徘徊的杨应琚

在六月初三之后的四、五天时间里,杨应琚与丁文彬之间一定有许多较量。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动机和作为——
“丁文彬供词狂逆怪诞,恐系心存捏饰,希图开脱同谋,或别有谋逆情事,诈为支吾亦未可定,是以臣悉心研究,有时严加刑讯,有时用言开导,并又设法遣人诱探,及数日以来终无异词。”[9]
不管丁文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杨应琚首先是一个法官,他不能相信这个故事,他必须怀疑故事背后可能存在的阴谋和危险,因此,他需要按照法律的逻辑揭示这个故事的虚妄。的确,法律可以借助刑罚、劝导、欺骗等各种手段显示自己的尊严,但它如果没有自己的逻辑程序,这些手段的力量一定是有限的。
在某种程度上,法律的逻辑就是在现实和语言陈述之间发现矛盾和裂隙。面对丁文彬的自我描述,杨应琚不断提示着丁文彬的小家出身和形同乞丐的境况,这与丁文彬所设定的自我故事实在不相称。然而,对于丁文彬来说,杨应琚的讯问似乎具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意义,一方面,杨应琚的提示无疑唤醒了丁文彬的记忆,让他回到面前的世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衣食不济,穷困潦倒,经常因为饥饿去乞讨,而另一方面,杨应琚也给丁文彬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无所忌惮地说明、弥补这个才子佳人故事情节短路的机会,即使没有好运气,丁文彬也一定要强调自己拥有进入故事的资本。
当然,在这种较量中,杨应琚已经知道了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时,他开始转换自己的角色。在新的角色里,杨应琚似乎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医生,他写下自己对丁文彬的诊断结果——
“丁文彬乃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稍习陈言,遂自诩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幻想富贵、女色,痴心日炽,结为幻影,牢不可破,辄肆其枭獍之心,狼号狗吠,无所不至。”[10]
这是一份精彩的精神病学报告,对于丁文彬的精神异常状况的成因、临床症候都有清晰的描述。然而,杨应琚突然就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可能存在的危险,他又多少有点迟疑地恢复了作为法官的形象。
“臣观其人猥贱不堪,伶仃偄小,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但该犯气体瘦弱,亟宜早正典刑,仰请皇上速赐乾断,以惩奸慝,以快人心,理合另折据实具奏,伏乞皇上睿鉴。”[11]
在写作这份奏折的同时,杨应琚已经更详细地向乾隆皇帝报告了讯问丁文彬的结果、自己的判决和对后续事宜的处理意见。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准备带着丁文彬从兖州回济南的时候,杨应琚又写了这份徘徊在两种不同身份之间的奏折,他到底要传达什么信息给乾隆皇帝呢?乾隆皇帝在处理文字狱时的残酷态度是一贯的,这自然会影响杨应琚的判断,因此丁文彬被判凌迟处死。死刑判决需要经过中央政府司法部门的审核和皇帝的终审,杨应琚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快一点完成。但是,从清代法律规定看,精神病患者享有司法豁免权,杨应琚又为什么要强调丁文彬的精神病患者身份呢?这其中应该有他要借此推卸责任的因素,但肯定不是问题所在的全部。
也许真正的原因依旧要从丁文彬那里寻找。杨应琚转换角色的时候,丁文彬也同样在叙述中重新设计自己的角色。在讯问开始的时候,丁文彬只是梦想着发迹变泰,杨应琚能够理解这种角色。但是,随着讯问的深入,丁文彬逐步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天启神圣的道德英雄,杨应琚已经无法理解这种角色。对于一个恪守现实秩序的人来说,无法理解的东西也许才是真正危险的,而且对那些试图理解的人充满嘲讽。
5、再问丁文彬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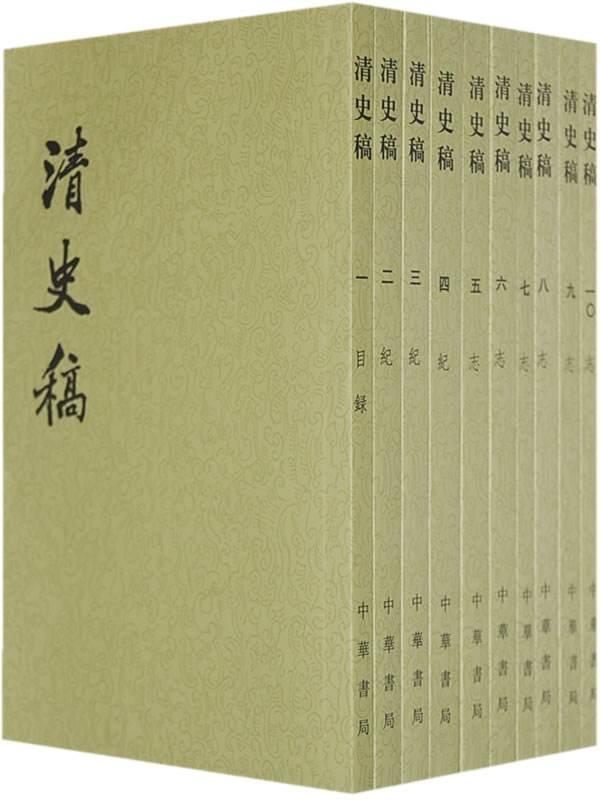
丁文彬的家族里有许多读书人,不过,即使有功名,似乎也仅仅限于贡生,这绝对不是什么名门望族。在这样的家族里,虽然丁文彬强调自己父祖辈务农为生,但至少从他的父亲开始应该已经破产,一家人只能混迹于城市下层艰难谋生。读书人的生涯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和丁文彬没有关系,而事情偏偏会从不可能的地方逆转。父亲死后,母亲有一段时间给同族的丁芝田帮佣,丁文彬因此有机会跟随做塾师的族叔祖开始读书。
和所有接受启蒙教育的孩子一样,丁文彬也是从所谓《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之类蒙学教材开始识字,接着就是读“四书”。然而,刚刚接触《论语》,他就已经觉得困难,不管怎么努力,也没法理解那些熟悉字词的意思,丁文彬的启蒙教育就此结束了。
短暂的启蒙教育没有改变丁文彬的生活道路,但重塑了他的整个精神世界。从清代私塾教育的一般状况看,越是趋于底层,其功利性就越强,越能激发受教育者偏执的想象力。比如说,发动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都曾接受底层的私塾教育,又屡试不弟而充任村塾教师[12],偶然接触到天主教教义,于是就激发出莫名的成仁成圣的情怀。丁文彬虽然没有机会应试,但他的精神世界与洪秀全等人是一致的,只要有合适的触媒,他的精神世界也会爆发出某种异样的偏执想象。
乾隆五年(1740),杭州贡生徐鼎应邀去湖北做张映辰的幕僚,需要雇佣一个能做饭、兼做杂务的仆人。二十五岁的丁文彬,长期跟随母亲在别人家帮佣,也慢慢学会做饭的手艺,经别人介绍,就跟随徐鼎去湖北了。不久,就碰到院试试期,作为幕僚的徐鼎开始帮忙批阅试卷。在这个过程中,丁文彬比平时有更多的闲暇,他对于科举考试也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因此,我们看到了科举时代一幕常演常新的情境喜剧。和丁文彬同时的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经描述过这幕情境喜剧——屡试不弟的周进成为薛家集的乡间塾师,因为乡村的流言和周进的呆头呆脑,将就了一年,就被辞了馆。衣食无着的周进只得跟着姐夫去经商,到了省城,途经贡院,触动他的一番心事,执意要进去看看。刚进贡院,周进就一头撞在板壁上直僵僵地不省人事。同行的商人好不容易把他救活过来,他又是一头撞过去,对着号板依次哭过去,直哭得满地打滚,嘴里流出血来。迫不得已,其他人只得将周进半扛半抬地弄出贡院,他依旧眼泪鼻涕不止,只是伤心。那些热心的商人们决定凑钱替他捐个监生,送他入场考举人去,果然就一路中了举人、进士[13]。
丁文彬没有周进那么夸张的经历,但看着周围那些表现出不同面相的士子,想想自己的处境,痛苦和焦虑还是一下子就把他击垮了,他已经不能正常履行自己做仆人的职责。徐鼎自然不能也不愿意理解自己这个仆人的精神,他很快把丁文彬打发回杭州。
回到杭州的丁文彬继续倚靠逐渐老去的母亲,谋生已经与他无关,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贫穷的处境,是那个时代的所有穷书生的向往,但丁文彬明白自己没有机会,他必须寻找另外的出路。
雍正九年(1731),孔广棨袭衍圣公爵位,“十年,孔林工竟,复开馆,辑阙里盛典”,[14]应该就在这个时候,丁文彬跟随族叔祖丁芝田到曲阜参加了所谓的“阙里盛典”。在丁文彬的回忆中,这个典礼与他似懂非懂的尧舜神话纠缠在一起。乾隆八年(1743)孔广棨卒,但直到乾隆十一年(1746),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丁文彬才听到这个消息。这个迟到的消息仿佛神启,它把早就在丁文彬回忆中纠缠在一起的各种因素——孔林重修完成之后的典礼、含混的神话,甚至被克制的欲望——整理成情节分明的幻觉影像。
“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实应称帝,看小子讲道论德与舜无异,故传位与小子,以儿女妻之,这都是蒙上帝启迪所成。小子闻得衍圣公殁了,就接了位,如今已经八年了”。[15]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丁文彬的内心世界,但是,没有人关心丁文彬的内心世界。
6、乾隆的隐秘内心

在遭遇严刑拷打的过程中,丁文彬已经逐步把自己的角色从才子佳人故事转移为根源于神话的神圣道德英雄。这个时候,乾隆已经看到孔昭焕的密奏,我们不知道在他的隐秘内心里到底在盘旋着什么。
到了六月初七,杨应琚审理完案件,并立即把案情和所有档案都密折上奏,六月十一,乾隆看到密奏并批示。从批示看,他似乎希望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处理这个案件。但当看到杨应琚的另一份徘徊在法官和医生两种角色之间的奏折时,他的态度转变的非常快,不再等候三法司对案件的审核结果,就迫不及待地给杨应琚下达旨意,绝对不允许丁文彬在监狱自然死亡。
“谕:杨应琚所奏审拟造作逆书之丁文彬一案,已交法司核拟速奏,但杨应琚另折有‘该犯气体瘦弱,亟宜早正典刑’之语,此等大逆之犯岂可使其逃于显戮?法司即速行办理,约计部文到东省时亦必须旬余,着传谕杨应琚酌看该犯现在光景,若可等待部文则候部文正法,如恐不及待,即照所拟先行凌迟示众,勿任瘐毙狱中,致奸慝罔知惩戒也。”[16]
六月十四,这份圣旨达到山东抚署。按照皇帝的旨意,丁文彬被匆匆忙忙地凌迟处死,两天以后,终审的判决书才到达杨应琚手里。
面对一个卑微的人,面对一个精神病患者,乾隆的冷酷似乎是不正常的。我希望能够寻找到底是什么东西触发了这冷酷的态度。朱维铮曾经指出,“‘于事无所不通谓之圣’,出自《尚书·洪范》伪孔传的这个界定,起初只是汉魏经学家的自我期许,也涵泳着乱世哲人对君主或执政者人品才能的一种期待”,“满洲列帝都好自命为活着的圣人”[17]。自命为圣人,依旧需要通过权术去改造、渗透儒学,进而驾驭那些儒者。雍正十年,因为重修孔林完工,孔广棨率族人赴京感谢皇帝,雍正给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汝为先圣后,当存圣贤心,行圣贤事,秉礼守义,以骄奢为戒。汝年方少,尤宜勤学读书,敦品励行,与汝族人相劝诫,相砥砺,为端人正士。”[18]
听到这段话,我们不知道孔广棨将如何做他的衍圣公,不过,后来的一件事倒能透露出一些端倪。乾隆六年(1741),孔广棨与曲阜知县孔毓琚在皇帝面前相互攻讦,虽然山东巡抚的调查结果对孔广棨不利,而乾隆则表现出宽大为怀的姿态,只是谴责了孔毓琚就了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激发丁文彬神圣道德英雄想象的衍圣公的确谙熟这个时代隐秘的一面,他绝对不会以圣人自居,甚至雍正所教导的“端人正士”也是做不得的。只有如此,才能凸现“今圣”的形象。
与衍圣公孔广棨相比,丁文彬所遭遇的冷酷正是根源于他在叙述自己时所显示出的神圣道德英雄形象。斯科特指出,“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买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有其共同特点。”而当他们“不再采取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19]与斯科特的观察不同,在丁文彬的时代,神圣道德英雄想象仅仅属于底层,而且是属于最主要的“弱者的武器”,正如我们在这个时代可以看到许多偏执的弱者,他们往往在想象中保持着纯洁的道德情怀。
乾隆毕竟是聪明的,甚至过于聪明,他在丁文彬的自我叙述中看到了潜在的危险。于是,侮辱性的惩罚仪式比消灭这个人的身体变得更重要。
7、三问丁文彬是谁?

乾隆十一年(1746),丁文彬在内心世界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神圣道德英雄形象,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期望着一出类似但丁的神圣喜剧就此上演,可以肯定的是他期望从此能够幸福地生活。然而,就在这之后不久,母亲去世了,丁文彬被寄托在哥哥家里。
哥哥丁文耀已经成家,有四个儿子,他和两个大点的儿子卖烧饼,也在别人的面馆做工,偶然做点其他应时的小生意。即使如此,日子依旧拮据,家里突然添了一个大饭量的人口,他必须找到让一家人吃饱饭的出路。
乾隆十三年(1748),丁文耀终于决定在自己家里开一个私塾,他自然没有大抱负,只是想让弟弟领着附近人家的孩子识几个字,也好收点学费贴补家用。没有多长时间,这个私塾就关闭了,谁也不愿意一个看起来疯疯癫癫的人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私塾关闭了,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松江的街市开始流传着关于丁文彬的种种消息——衍圣公是他的岳父,可直到去世也不给他成亲,也许还有其他吧。不过,人们只是把这些传闻看作笑话,用来打趣丁文彬而已。
丁文彬的生机又成了问题,哥哥托人让他到不远处的董衡山茶馆去烧火。一来到茶馆,他就被那些街市上的流言所包围,而且周围的人会用各种方式诱导他说出更多的东西,然后在一片哄然的笑声中留下他一个人。在这儿,只有董衡山十五岁的女儿不介入这场游戏,或者还多少会安慰一下孤苦无依的丁文彬。不管什么原因,丁文彬终于在这个时候决定要发愤著书了。
“小子幼年读到《论语》,尚不知文义,后来自己苦学,到乾隆十三年住在松江哥子家里教书,才著起这书的,也是上帝启迪,十四年上著完了,都是小子一人著作抄写的,并没有同谋商酌的人。……到乾隆十五年,上帝又命我改作《洪范春秋》,把这书又增添了好些,把书内六十章之后‘丁子曰’都改作‘天子曰’、‘王帝曰’、‘王若曰’,是上帝命改才挖补抽换粘贴的。”[20]
一年的时间,丁文彬写完他的《文武记》和《太公望传》。又过了一年的时间,他把两部书抽换粘贴,合并成《洪范春秋》。
按照他的这种后设叙事,发愤著书是上帝之命。而我总怀疑,在丁文彬的耳朵里,小儿女的温言软语也许已经与上帝的声音无法分辨。因为书还没有写完的时候,丁文彬就急于拿给附近的人去看,米店的老掌柜、已经没有仕途希望的文武秀才,仅仅是偶然碰到的那些识字的人们。那些人看过丁文彬的著作之后,即使不会直接表露自己的鄙夷,但他们一定在背后用很小的声音这样说着:“痴子”。面对这样一群人,丁文彬从发愤著书中激发出的神圣意识依旧处于幽暗之中,无法给他带来幸福的生活,哪怕是微弱的幸福感也没有。相反,只有更深切的挫折,更疼的伤痕,如他所说:
“小子所定礼乐制度皆是按照尧舜之道纂辑,并非杜撰,小子不过遵上帝之命,克守圣道而行,并不是痴子,可恨在家时人人道是小子是痴的”。[21]
丁文彬在自己的笔下用这样几个字描写家人——“兄顽嫂嚣侄傲”,但同时又在想象中封赏哥哥夏文公。他在解释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时说,“他是不明道理的人,常骂我痴子,……只因小子即了位,理应封他”。这种矛盾的态度显示出的是一种厌倦。从厌倦自己熟悉的那些庸人开始,他慢慢也厌倦于自己的想象。
在这个时候,丁文彬突然想起那些留在记忆中的陌生人——曾经做过学政的张映辰和庄有恭,还有衍圣公。在他的想象中,这些陌生人应该能够理解自己的神圣意识。于是,他到苏州去,到杭州去,然而庄有恭早就升迁到其他地方,而丁忧家居的张映辰既不接见丁文彬,也不接受他的著作。我们不知道丁文彬在杭州的其他遭遇,而在苏州,他似乎又回到自己熟悉的那些人中间——
“去年正月到苏州,写对子送各店家讨几文钱,又在青浦讨了几天钱。那南方的人都不明大道,不理小子,没奈何才要把做成这部书,送到孔府要交与圣公传位与他的。”[22]
也许本来就知道这是一次绝望的旅途,丁文彬终于还是决定到自己想象的北方去。
8、从庄有恭到衍圣公

乾隆十四年(1749)三月初三,庄有恭去松江府主持院试,突然听到衙役们的呵斥声,他连忙摸出自己的眼镜,从轿窗望去,看到他们把围观人群中一个衣服褴褛、龌龊不堪的人赶走。可是,等到要进城的时候,那个人不知道又从什么地方钻出,跪在轿前要献上自己的著作。很快,一册看起来不很干净的手抄本拿到庄有恭手里,刚翻开,连串的“丁子曰”就从眼前闪过。
“真妄人,何高自称许乃尔!”[23]
自负的庄有恭说了一句,就把那册抄本随手扔到一旁。不等离开松江,他就把这件事忘记,也不知道这个人叫丁文彬。
可是,丁文彬没有忘记庄有恭,在他的心里,庄有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
“那书共是十本两部,我原写一部送孔府、一部送庄抚台,他还懂得文学,谁知庄抚台不在苏州了,故此没有送都带到曲阜来了。”[24]
丁文彬说庄有恭懂得文学,能使用这个词,大概是他读《论语》留在记忆中的。在儒教语境中,“文学”一词有着复杂的意味,可是,到了丁文彬的时代,这个词的意思也许已经成为某种身份期许。
刘宝楠在注释《论语》“文学:子游,子夏”时说:
“沈氏德潜《吴公祠堂记》曰:子游之文学,以习礼自见。……朱氏彝尊《文水县卜子祠堂记》曰:徐防之言,《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盖自《六经》删述之后,《诗》、《易》俱传自子夏,夫子又称其可与言《诗》,《仪礼》则有《丧服传》一篇。又尝与魏文侯言乐,郑康成谓《论语》为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赞一辞,夫子则曰《春秋》属商。其后公羊、谷梁二子,皆子夏之门人。盖文章可得而闻者,子夏无不传之。文章传,性与天道亦传,是则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观之,是子游、子夏为文学之选也。”[25]
刘宝楠的注释应该能够代表清代理解“文学”一词的平均知识水平,或者说是相对普遍的看法,由此可以看出,“文学”的意味首先是一种谨守礼法的人生形象,而更重要的是在理学之外的另一种道统担当者的形象,这种形象与清代汉学复兴运动的追求是一致的。
丁文彬对“文学”一词的理解绝对不可能超过自己时代的平均知识水平,他之所以要执着地把自己的著作送给庄有恭和衍圣公这些陌生人,原因肯定不是期望得到空洞的赞美,而是寻找道统的担当者。然而,在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必须进入由自命圣人的皇帝们所设置的权力游戏之中,庄有恭和衍圣公都只能让丁文彬失望。
乾隆于十八年六月十一日要求庄有恭呈交丁文彬跪着献给他的手抄本。接到旨意,庄有恭一面表示自己一定会仔细检查,一面强调这手抄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留着。乾隆在这份奏折上写下批示——
“此奏尤属取巧,细查书来,不可终归乌有。”[26]
这批示自然有人会透露给庄有恭,他在七月十五日的第二份奏折中写到:
“臣舟次泰州接大学士字寄,钦奉上谕……随兼程星驰,于六月二十五日三更回署,亲自检查败簏敝箧,搜寻三日,此册竟不可得,臣再四寻思,或临时杂入无用废纸中随时焚去亦未可知,复细询从前随从之仆从,皆各茫无记忆,无可根寻。……臣彼时提督学政,文字是所专责,乃逆犯丁文彬既已拦舆献书,臣谩目左右斥为疯子,……致该犯漏网逋诛者五年,且弃置之后遂即遗忘,又致逆书竟无下落,是臣昏聩纵逆,罪无可逃”。[27]
接到这份奏折,乾隆说道,
“夫大逆不道之词,岂有曾经寓目致令迷失之理?必系闻信查出私为销毁耳。庄有恭受朕深恩,不应狡诈为鬼蜮伎俩至是也,即拿问治罪亦所应得,但天下似此者未必仅庄有恭一人,伊为巡抚尚属能办事,且伊巡抚任内若见此等必早为奏办,当在学政时其意不过以学政司文衡之员,何必多此一事,是其罪不在巡抚而在学政,且欲保全学政俸禄养廉耳。着照伊学政任内所得俸禄、养廉数目加罚十倍,交江南总督请旨,以为徇名利而忘大义者戒。”[28]
庄有恭似乎早就知道最后的旨意只能如此,所以他又一次表示自己曾经抚心顾影,觉得觍然天地,以致不敢自安寝处。当然,天地看不到庄有恭惭愧的面容,乾隆也看不到,就是看到也不会觉得是真的。在这场权力游戏中,乾隆扮演圣人,他必须聪明到知道所有人在欺骗自己但必须甘心接受欺骗,而庄有恭扮演傻瓜,他必须聪明到承认自己傻。因为结果在游戏开始之前就已经决定。
从庄有恭到衍圣公,都是聪明人在玩傻瓜游戏。对于丁文彬来说,他们之所以是陌生人,不是因为从没有相遇,而是横亘在傻人和聪明人之间的距离。
9、丁文彬的多重形象和卑微者的梦想

在别人眼里,丁文彬是一个傻子、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疯子,也是一个叛逆者,然而,这是他所竭力否认的,他有自己所期望的形象。
丁文彬所期望的形象到底是什么,他自己似乎并不清楚。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总是在言语表述中逐步才能变得清晰,但丁文彬从来就缺乏说话的机会,他只能在昏暗中,屏绝周围喧嚣的市声,面对一叠揉得皱巴巴的纸,一笔一笔寻找他所期望的自我形象。如此情境,大概最适合遭遇冥想中的上帝,也最容易激发自我,因此,丁文彬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魏宁格说过,“对艺术家和哲学家来说,自我的激发是对世界的直觉幻想的惟一来源。”而“从自我第一次被激发开始,伟人会一直生活在灵魂中并靠它生活,尽管他们也会因为那种最可怕的情感(即道德感)而犯下错误。”[29]丁文彬不是艺术家、哲学家,也不是天才,但他的确经历了自我的激发。不过,他所遭遇的上帝是已经彻底世俗化的,由此激发出的自我也只能混迹于尘世,他的灵魂里遍布着神魔斗法和才子佳人的鬼影。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他的灵魂深处,在他的想象中。丁文彬不断用虚构的方式上演着一出又一出才子佳人的剧情。一般来说,在母亲的呵护下,一个男孩子更容易养成极端的男性性格。父亲去世后,丁文彬与母亲在流离之中厮守,我们已经很难区别一个慢慢老去的寡妇和一个倔强的男孩子到底是谁更需要对方,是谁在支持对方的生存。但是,这种早期生活始终制约着丁文彬的想象,现实中的那些女孩几乎不能参与他想象中的剧情,他需要一个如同母亲一样女性,因此他把自己的欲望寄托在孔府的女儿那里,当然即便是孔府的女儿也被他改造成神话的主人公。
然而想象中的剧情无法复制到现实之中,甚至母亲也会离开他。不知道确定具体时间,但我们知道肯定是在丁文彬成年之后,他的母亲曾经被人雇佣到江西去了三年。这是母子分开各自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次,在丁文彬的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记,引起他的愤怒。不过,丁文彬把自己的愤怒转嫁到对介绍母亲去江西的那个无名的妇女身上,他终生怨恨这个妇女。我觉得,这种怨恨隐喻的是丁文彬对世界的直觉幻想——这是一个悲哀的世界!
因此,丁文彬的想象开始剧情转换,他要改造这个悲哀的世界。改造世界的想象将会构成一幅新的历史图景,它是由神魔斗法作为基本情节的喜剧。在母亲去世之后,丁文彬终于在纸上写下“太公望”这几个字眼。
丁文彬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他对太公望姜尚的理解仅仅根源于说书人嘴里的《封神演义》,甚至对《封神演义》的了解也是残缺的。《封神演义》的故事从那个叫妲己的狐狸精开始的,终于引出神魔斗法、改朝换代的各种曲折,当然这一切都是命定的,大家实际上从开始就期望着最后封神的喜剧。在丁文彬的生活里,那些惹他怨恨的女人,也许还有其他的细节,终于把他引导进封神的喜剧。在一个幻想王朝中,所有的陌生人都是神圣的,但正如《封神演义》中的正邪神魔同时进入封神榜一样,丁文彬把封赠不仅赐予陌生人,也同时赐予那些熟悉的庸人们。
封神的喜剧已经完成,丁文彬并没有能够走进陌生人的世界,甚至他的神圣感也越来越淡漠,他决定要放下神圣的包袱。就在这个时候,他终于有了一次说话的机会。面对杨应琚这个陌生人,丁文彬开始逐步恢复自己的神圣感,从才子佳人剧开始,到隐秘修道的艰辛,最后秉承上帝之命发愤著书,他用一个虚构的故事塑造出自己神圣道德英雄的形象。
丁文彬似乎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命运——即使在他所期望的能够理解神圣、担当神圣的陌生人眼里,他依旧只是一个傻子,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疯子,一个叛逆者而已。不过,除了遭遇严刑时的疼痛,他也并不关心自己的命运,只是专心讲述自己的故事,让自己的梦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神圣。
10、尾声

故事结束了。
丁文彬又独自一人回到幽暗之中,面对冷冰冰的狱墙,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可以肯定,讲述故事耗尽了他全部的精力。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十四日,杨应琚接到皇帝的旨意,他到监狱里观察情况,丁文彬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杨应琚立即命令济南知府赵之埰尽快布置刑场,中午时分,守城参将万德率领一队兵丁押解着犯人来到刑场。赵之埰、万德,还有他们的上司如山东巡抚杨应琚等,至少表面上看,他们都是小心翼翼、如临深渊的。
过去两百多年之后,我们不知道所有这些人此刻的真实心情如何,然而,当犯人出场的时候,周围的看客一定充满失望。在这森严的氛围中,看客总希望犯人多少能够留下一些噱头,好做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出场的犯人身材矮小,形容猥琐,灰白的脸色和呆滞的眼神显得没有一点活气。也许还不仅如此,对于这个犯人来说,除过突然袭来的疼痛,没有什么能把他从那个封闭的世界中唤醒,他总是留给世界一个背影。这个犯人将被凌迟处死,屠刀已经临近。没有人知道第一刀会从什么地方扎入他的身体,疼痛突然袭来的时候,犯人的脸型扭曲了一下,慢慢地,这扭曲也越来越迟缓,终于连这迟缓的扭曲也没有。
两天以后,丁文彬的终审判决才由乾隆下达,大概还需要三、四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济南。
死去的丁文彬不会知道,松江在几天以后将上演一出夸张的戏剧。江南总兵林君陞这样描述它的场景——
董正坤、周伯爵两位将军“率同各营守备千把等员带领强干兵目,分饬四门加紧防守,复又派拨员弁改易衣履,于各犯住址附近处所四散密布,以防窜逸,并令协同府厅等正在分头拘拿间,随有东省委员兖沂曹道张潮、兖州镇标右营游击富勒和带同把总典史等员至松,而苏松巡道申梦玺同时亦到,文武各员协同擒拿,当获民人丁士麟、丁士贤、王士照、董恒山、蔡颖达、生员蔡玉江、武生徐旭初等。”[30]
不久,丁文彬的哥哥也在杭州被抓获,和这些人一起被押解到济南。八月二十六日,杨应琚对这些人做出判决——丁文彬的哥哥和两个成年的侄子被判处死刑,还有两个不满十五岁的侄子被判入官为奴,其他那些有关的人接受杖刑、流放的惩罚。
【注释】
[1] 《清代文字狱档》,p14.
[2] 《诸子集成(1)·论语正义》,p170-173.
[3] 梅列日科夫斯基《但丁传》,p269-284.
[4] 《清代文字狱档》,p10.
[5] 同上。
[6] 《清代文字狱档》,p12.
[7]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
[8] 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p99.
[9] 《清代文字狱档》,p17.
[10] 《清代文字狱档》,p17.
[11] 同上。
[12] 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塾师研究》p361-363.
[13] 吴敬梓《儒林外史》,p11-12.
[14] 《二十五史·清史稿》,p1527.
[15] 《清代文字狱档》,p12.
[16] 《清代文字狱档》,p18.
[17] 朱维铮《重读近代史》,第185页.
[18] 《二十五史·清史稿》,p1527.
[19] [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p2-3.
[20] 《清代文字狱档》,p13.
[21] 《清代文字狱档》,p15.
[22] 同上,p12。
[23] 同上,p19。
[24] 《清代文字狱档》,p13.
[25] 《诸子集成(1)·论语正义》,p289.
[26] 《清代文字狱档》,p20.
[27] 《清代文字狱档》,p23-24.
[28] 同上,p24.
[29] [奥地利]奥托·魏宁格《性与性格》,p182.
[30] 《清代文字狱档》,p20.
【参考文献】
1.《清代文字狱档·丁文斌逆词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刘宝楠《诸子集成(1)·论语正义》,岳麓书社,1996。
3.梅列日科夫斯基《但丁传》,团结出版社,2005。
4.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三联书店,2008。
6.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塾师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7.吴敬梓《儒林外史》,黄山书社,1994。
8.《二十五史·清史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9.朱维铮《重读近代史》,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2010.
10.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07。
11.奥托·魏宁格《性与性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作品展示不代表最终入围。
大赛投稿请点击链接
或直接发送参赛非虚构作品至nonfiction@thepaper.cn
▍大赛组委会
主办方:澎湃新闻
联合主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今日头条
指导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学术支持单位: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上海大学文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