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夸夸群有让我的生活变好一点吗?
然而夸夸群的生命普遍短暂,建立后不久往往就会归于沉寂。随着众多夸夸群的兴起与退潮,一些关于夸夸群的疑问也逐渐浮出水面。夸夸群的存在背后是什么样的心理诉求?这样的夸奖对于参与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它最终又会给参与者带来什么?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加入了北大夸夸群,并给出了一份体验报告。
自述|唐远
手绘|王雅婷
编辑|谢欣玥
截止到现在,我在夸夸群里呆了14天,感觉上似乎更久。
其实我只赶上了夸夸群在校内兴起的尾巴,当我拜托同学把我拉入夸夸群的时候,我已经是北大夸夸5群的第376位群成员,群里一边水聊,一边不断有人加入。拉我的同学把进群之前的聊天记录转发给我,大家正热烈称赞的是张帆的一条求夸:“脸上被蚊子叮了一个包,求夸”。大家从被蚊子叮这一简单的事实联想到蚊子都青睐的好看皮囊,引申为爱护动物或是舍己为人的美好品质,然后在称赞彼此的胡诌能力中画下句号。在看到那条“血多,夸”的时候,我在自习室里笑出了声。

实际上我已经很难回忆起上次被熟人认真夸赞是什么时候,构想这个场景都显得违和,怎么也不能把熟人的脸与真诚的夸赞放在同一个画面中。在微信聊天记录里搜索“棒”,从夸有意思的推送到网上邻居间的商业赞许,找出一条来自熟人的夸奖很难,难得翻到一条“你棒棒哦”,还是表达鄙夷,但如果搜索“傻”,可以搜到30条到90条不等的彼此挖苦。我开始反思我的社交是不是太不健康。但这已经是被我接受为常态的社交模式,并自以为是地认为朋友之间互相挖苦而非表扬在某种意义上是关系好的标志。
夸夸群的消息不停向上刷,一条求夸底下就看到三个熟悉的头像,都是元培水群的常客,看来各处群聊水群的都是同一拨人。躺在床上玩手机到凌晨一点,睡前点开夸夸群,估计许多人和我一样刚刚加入,互夸的热情依旧高涨。刷到一条“这么晚还没睡,求夸”,我斟酌了一下,决定发出我在本群的第一条夸人:延长生命,夸。基本也是对自己熬夜无所事事的安慰,晚上的时间总像是凭空白得的。一分钟内针对这条求夸已经夸出三条,内容类似,夸友对于熬夜的伙伴都不吝赞美。很快,群内又出现了新的求夸,也不断有新的夸赞的人们。
在夸夸群呆了几天,我才发现夸人十分困难。没有灵魂的夸奖不难,然而要夸出新意、夸出水准,夸得出乎求夸者的意料还是有难度的。我在夸夸群只发过零散几条夸赞,总怕自己夸的落入俗套。
虽然我有对夸夸群兴起的解释,但我其实并不能理解在群里频繁求夸的心理。获得陌生人并不真心的表扬能补足社交中缺少的积极反馈吗?
因此我决定在夸夸群发出第一条求夸,但又对发什么内容毫无头绪。在分析了夸夸5群的求夸记录后,我把求夸分为了三类,对自己感到愧疚或其他消极情绪事件的求夸,单纯为了看看网友能夸出什么的求夸,和真正有所成就的求夸,事实上第三类反而是少数。或许即使在充满陌生人的网络环境中,人们依旧甩不脱强加给自我的对于要求表扬的耻感。
发出第一条求夸需要跨越心理的门槛,因为我心里并不认为求夸能获得什么有意义的回应,同时也处在冷群或者回应寥寥的忧虑之中。加入夸夸群的第7天,我在宿舍楼下没带门卡等着有人开门。抬头正对着宿舍门口站着的一对情侣,毫无进门的意向,我转身来给他们留一些空间,结果台阶下又是一对情侣,我勉强转向介于两对情侣之间。祸不单行,这个方向几米外的车棚里又是一对情侣,他们仿佛七夕短短相会又要久别的牛郎织女,依依不舍。我尴尬的目光终于无处安置,掏出手机,随手刷掉夸夸群最新的消息,带着点打趣的念头发出了第一条求夸:在楼下等人被三对情侣包围,求夸。群里很快有了第一条回复:功率大,夸!还有网友发出了各种表情包,我回复了一个盖着被子哭泣的表情。
求夸的体验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尴尬。这个场景完全可以类比为,你在某个大型社交现场完全无法融入任何人的谈话之中时默默掏出了手机,仿佛一个有着丰富网络社交生活的商务人士。虽然你可能并没有和人聊天,也依旧处于跟身边人搭不上话的尴尬境地,但看手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承担了这些社交压力。这时我对夸夸群的看法稍微有了些改观。
加入夸夸群的第4天,我刷到张帆发的一条自制三明治早餐的求夸,还配了一张她做的三明治的照片。夸友们纷纷夸赞女孩子热爱生活,宜室宜家。之所以印象深刻,可能是因为配图的三明治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可能是因为这是为数不多认真求夸的案例,也可能是因为她被夸完后真诚地回复感谢。
因此我决定和那些同我性格迥然相异的人聊聊夸夸群。

或许和我们级的大多数同学一样,我认识的第一批人中就有张帆,军训的间隙我看到同连一个姑娘在树荫底下唱歌,就是她了。最后军训文艺汇演的时候她是主持人,认识了魔术师辛冠杰,而我搬个凳子坐在几千新生里挥舞荧光棒。这次是我们俩第一次有超过三分钟的聊天,之前每次在楼道里遇到,打个招呼,互相就可见的信息点评二三,然后就各自敲开各自的宿舍。
张帆给我讲了她在夸夸群的故事,我才理解了她说的,每个人在夸夸群都有个自己的故事。
原来我在元培大群里看到张帆问有没有人需要拉夸夸群时,她也刚加入夸夸5群。但她其实已经加入过另外一个夸夸群。“最开始我只是想围观夸夸群,因为我并没有求夸的需求,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夸是一个生活当中稀缺的东西,或许这就证明我平时生活中已经被满足了吧。” 那个群已经到了衰退期,基本都是求夸,夸人质量也很低,围观起来没什么意思,于是她退群了。
如果不是五群的群主辛冠杰找上她,或许张帆不会再对夸夸群提起兴趣。辛冠杰请她拉一些同学进群,最初群里人少,可以通过扫码进入,到达上限后就要手动操作。当晚张帆微信聊天里都是元培的朋友,还有特意加她好友来进夸夸群的陌生同学,她一个一个手动拉人。夸夸群里的同学立刻融入氛围。“群里一个劲儿的夸我,比如老张,他就说黛伊真的太强了,流水线拉人机,夸!” 张帆那天晚上往群里拉了一百多个人。
比较两个夸夸群,张帆觉得不过是自己加入的时机不同。回忆起另一个夸夸群,刚开始的时候同样火热,后来每个群都一样,变成正常聊天而不是夸人,或者用着夸夸体勉强聊天。但聊天情况也在于群里人的质量,“在第一个夸夸群里,我一条求夸都没发过。在这个夸夸群里都是熟人,他们常常会说黛伊怎么样,就不会夸得很尴尬”。 张帆的朋友都会叫她黛伊或者老板娘,刚进群的时我看到这些称谓,还以为错进了元培群聊。
我跟她表示自己担心在群里求夸会冷场,而她觉得没关系,还撺掇我现在就发一条。她将群聊经验与我分享:在任何一个群,只要有几个关系很不错的同学,哪怕损你都不至于冷场,也就没有后顾之忧。“我跟你讲啊,有人损你是件很幸福的事。”说这句话时,她下意识带上了些东北口音。
虽然张帆不觉得自己是夸夸群深度用户,但在夸夸群里她依旧是个吸引注意的人。谈到在夸夸群里常有人加她微信时,她表情自然,而我惊诧不已。有人加她微信,还把她拉进其他的群聊,比如清北美妆护肤群、北大vlog交流群等,她大多来者不拒,也觉得网上的关系和线下的关系没什么分别。
聊天的过程中我随口问她:微信好友上限多少人啊,一千?
她:怎么可能!
我:五百?你是说太多还是太少?
她终于翻到了好友页面的最下,说:“我高三下学期才注册的,好友就有一千多。”
我再次感慨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之大。
后来她也给我讲了那次发三明治照片背后的故事。她先发给了爸妈,为了展示她吃的很健康。“结果他们俩极其敷衍!”张帆开始翻手机,“我拿给你看,六个表情就解决了,而且我爸还是复制我妈发的。”她父母回了玫瑰和拇指的微信自带表情包,六个表情排列整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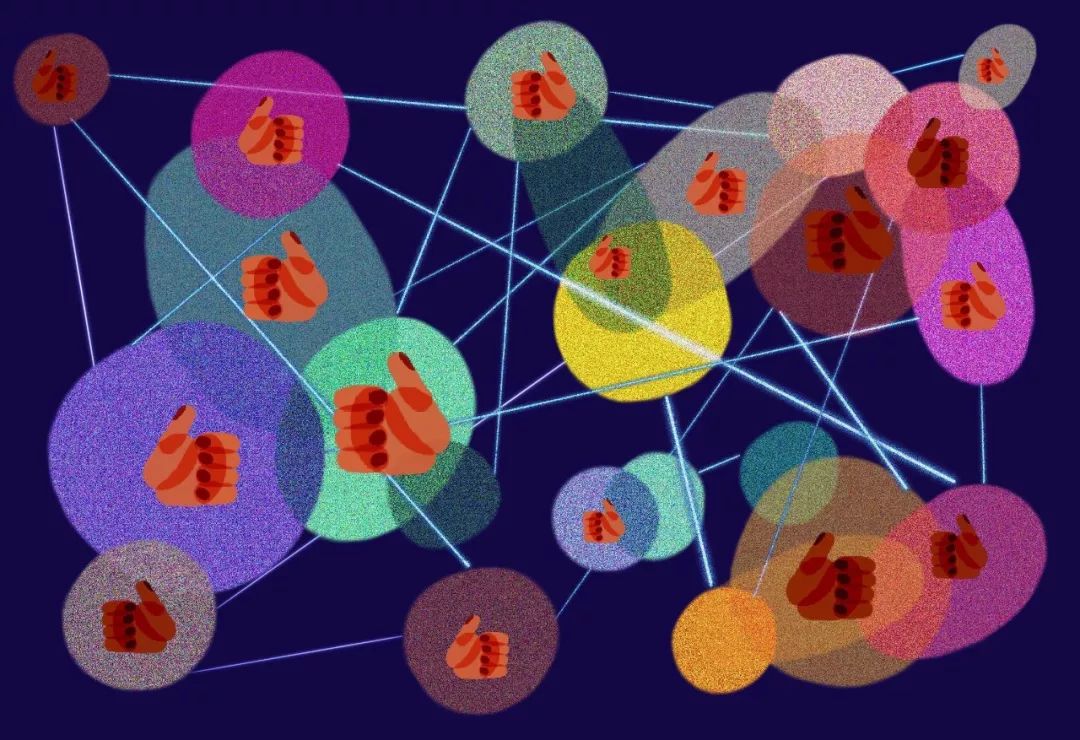
我问她,父母总是相信你是不是也会带来焦虑。她毫不避讳:“高中的时候因为这个也感觉闹心,别的家长什么都管,我的家长完全相信我,后来过焦虑期就好了,反而觉得是好事。”
或许是受父母的影响,她总是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强大的形象,情绪有所保留,尤其是在微信里。好友太多的负面影响是分组很麻烦,她也不喜欢设置分组,朋友圈基本所有人可见,数量在她看来很少,一些最真实的心情会留在空间。她把QQ空间给我看,更新很频繁,评论区有不少互动。
因为QQ空间这样一个安全地带的存在,她觉得自己的人际关系挺舒服。QQ空间里的朋友对她都很友善,熟人也常会留言夸她。
她和建群的辛冠杰从来没讨论过为什么要建夸夸群。我本以为这会是个精彩的故事,但她否定了。“你是不是学哲学的?我觉得这是职业病。” 学新传的张帆这样考虑这件事情,夸夸群是一个场域,大家互相传播资讯,扩大传播量,然后又进入到其他的社交环境里,“网上天天报道夸夸群这件事,好像把它当成一种社会现象,来找到背后的意义,但夸夸群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有意思,如果你非常痴迷追寻意义的话,它就没意思了。”
我们达成共识的地方是,这个夸夸群也开始走向退潮。消息从最开始的99+,到现在有时一条求夸会被晾三四个小时。只是这次张帆不打算退群。
在和张帆聊天之前,我完全无法想象夸夸群竟然还有社交平台的功能。我与陌生人在夸夸群对话的经验只有一次,某次夸人之后有人@我夸我的头像好看,我商业性地完成互夸,点开对方的头像,翻了可见的几条朋友圈,看背景似乎是个挺有意思的人,但并没有点下“添加到通讯录”的图标,也并不觉得自己错失了认识一个人的可能。
后来还有一次,有人在群内问北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推荐了几处密室逃脱,接着我就被拉入了一个密室逃脱局的群聊。群里的人大多是夸夸群里的熟面孔,我发了几个地点的截图到群里,获得了热情夸奖,但群主试图确定时间的时候,并没有人响应,而这只是一个六人的群聊。我空出了周日的时间,然而直到周六晚上,依旧没有人在群里发言。这次不成功的邀约被我看成是某种佐证,我相信大多数网络社交是无谓的,并且相信为此费力不值得。这个六人小群很快被不停涌入的新信息压在底下。
在那段时间里,夸夸群成了少数几个我没屏蔽的群聊之一。加入夸夸群的第八天,群里的消息依旧保持着每日99+。晚上跟朋友在全家自习的时候我跟她讲了我在夸夸群第一次求夸的故事,我对她说:“你觉得友谊能纯粹建立在互相夸的基础之上吗?我觉得可以。” 然后我们打了一个赌,为了得出结果,我们共同编辑了一条树洞来验证我的猜想:单单是互夸的人会拥有友谊吗?
编辑这条树洞有一种订立社会契约的感觉。为了保证不担负新的社交压力,我特意写明了除了互夸之外不需要相互了解。发出树洞,我抱着手机开始紧张等待。当时是凌晨,但依旧几分钟内就有人回应,我精神一振。我们加了微信,第一个难题是如果对方没有屏蔽我,我是否还要遵守洞里写的屏蔽对方呢?思索再三我还是选择了屏蔽。

我依旧把夸夸群,至少我体验到的夸夸群归于生活中的意难平。我还是没能回答最初的问题,生活中的缺失是怎么在陌生人身上找到补偿的?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有一些意外发现。
张帆如此轻松地展示出了夸夸群社交的另一种解法,但我小心翼翼,甚至第二次仔细斟酌,只获得了两次失败和“三而竭”的勇气。我是旧式社交的拥趸,喜欢写信多于邮件,喜欢见面多于微信,也可能因为我在新式社交中惨遭失败。我与新式社交的关系大概是,我曾经发朋友圈抨击它,然后获得了一些赞。网络上的言语有时候比生活中要轻,比如说随口的约定,有时候我们又在其中寻找一些重量来牵住装满消极情绪的自己。
我对夸夸群的态度非常复杂,如果说夸夸群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我会把这当成对我生活价值的贬损,但体验夸夸群,和另一种生活态度的人聊天在某个时间点上还是会改变我的选择,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上。
举个例子,周末回家,我妈照常问我这周过得怎么样。过去的每一周都会有这样的问答,我会说还行,然后掏出ipad插上耳机开始刷剧。我妈会问我怎么没有WiFi还能看剧,我说是下载好的,其实是在用流量。然而这次我猛地吸气,从抱怨手头选题到北大杯分组,讲述我凌晨四点在楼下爆肝被清洁人员围观的悲惨场景,絮絮叨叨从西门开始抱怨直到车走到西单,以最近写稿赶due的辛苦作结。我妈冒着危险驾驶的风险侧过头来看我,问我“是不是真的很累啊?” 我把椅背放倒,合上眼睛说: “ 嗯。”
夸夸群的人数后来总在496、498、500之间波动,总是有人进来,也有人悄无声息地退出。最后停在了499上,不再变动。看到这个数字我想起了夸夸群第一次满员,群主一声令下大家排队型庆贺,还有人担心朋友没法进群。在北大夸夸5群的早期历史阶段,每次夸夸群满员都会有人发一条夸。直到某一个时刻,夸夸群不再有人加入,也不再有人退出,人数停留在了距满员差一点点的不完满状态,就像这个群聊本身因为生活中的不完满而建立。
夸夸群的浪潮已经过去,北大的夸夸群会一个一个沉寂下去,豆瓣的相互表扬小组或许还会一直有人分享,回到登上微博热搜之前的状态。我还是有一点职业病,相互表扬小组也好,夸夸群也好,或许有人会像我一样抱着围观或评判的心情来,获得一点想法乃至意义的碎片,这也挺不错。如果有一天夸夸群死了,我可能会想念它。
新媒体编辑|张漫溪 谢欣玥
责任编辑|张炜铖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