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徐进:如何把握新史学的“感觉”
1919年冬,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得知北大学生林德扬自杀的消息,撰文感慨说“自杀是十九世纪的时代病,我们可以说十九世纪是‘自杀时代’”。这就是海青《《“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与价值选择》(以下简称《自杀时代》)一书主标题的来历。正如李大钊称自杀为“时代”病,“自杀时代”更值得关注的似乎不是自杀和死亡本身,而是自杀所处的时代亦即海青所说的“生活形态”。更有进者,作者笔下的“生活形态”似乎不仅指生活环境,还指向自杀者在特定生活环境中的体验和自我意识。因此,有论者视此书为一部“心史”,且盛赞“此书透过‘知人’来深究世态变化的路径,在未来中国历史的书写中必将具有特殊的典范意义”。笔者在本书阅读中,亦时时感觉到作者笔触和心思之细腻。但也毋庸讳言,如以“深究世态变化”的标准来衡量,作者恐怕尚有大量后续工作要做。另之,海青的导师杨念群教授倡导新史学可谓不遗余力,他声称“今天中国的治史者需要感觉,需要对历史的悟性,不能只是笨夫式的狂搜史料”,且认为“现在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丧失了像司马迁史记那样讲故事的能力”。海青践行老师的新史学宗旨,表示本书就是要“据自己对史料的感悟,讲一个鲜活的故事”。故事如何讲得其深足以“知人”,其趣足称“鲜活”,恐怕是当今整个史学界都亟需解决的问题。那么,海青在此书中做到了吗?
倡导新史学者希望引进与吸收国外社会文化史、女性主义史学、后现代史学,扫除当下中国旧史学只知考据的弊病。读《自杀时代》一书,时时能感受到新史学的新鲜气息。由此亦引发笔者如下思考:“旧”史学“笨夫式的十年苦功”是否真的已不足贵,“新”史学如不建立在十年苦功之上,能否真正形成对历史的有效“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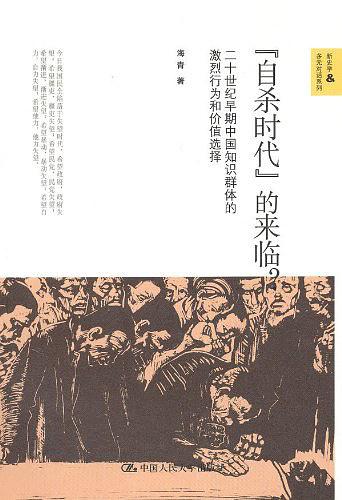
海青自称其研究“自杀时代”所关注的不是自杀和死亡本身,而是自杀所处的时代亦即海青所说的“生活形态”。正如达恩顿在《屠猫记》一书中所揭示的17世纪的法国农民与工匠并非今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意识,这些思想意识无一例外地镶嵌在他们自身所处的生活形态之中。如果此言可取,那么自杀研究应该关心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自杀诱因以及在自杀之后的生活苦难,而是晚清民初以及五四时期自杀背后所独有的生活形态。海青在《自杀时代》中考察了多个案例,摆出了时人各式各样的评论,通过这些相异的史料去努力寻找接近这些自杀者的生活形态的通道。
此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以“新青年”为研究对象,论述了清末到五四时期青年自杀与生命价值的重新解析。中篇则聚焦于“新女性”,再现了她们的爱与死之传奇。下篇则将目光锁定在知识分子群体,以朱谦之和瞿秋白为例解读“自我”的萌现与消解。全书不仅触及了近代中国“知识群体”的内心世界,也展现了这一群体所依存的近代生活形态的波澜壮阔。通览全书,作者文笔与心思之细腻,恰足以匹配关于“激烈行为”的独特选题。
毋庸讳言,《自杀时代》亦有美中不足之处。该书第三章,作者记述的北京大学法律科学生林德扬自杀一事,就颇能揭示作者面对纷繁芜杂史料时的无力感。首先,作者讨论了林德扬自杀的原因,她援引了“一篮子”史料,试图借时人之口解释林德扬的自杀。比如,蔡元培将林德扬的死与姚宏业、杨笃生的自杀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三者都是一种“奋斗失败而自杀”;罗家伦认为,“林君的自杀,原来不是自己杀自己,乃是社会杀了他”,是社会罪恶和不彻底改革的结果;李大钊也从自杀背后的社会缺陷分析,认为林德扬的死,与辛亥以来爱国自杀造成的模仿风气有关……
凡此种种时人的表述类史料,在作者笔下仿佛成为一块块“石料”被堆砌起来,可惜只见平地,不见高楼。“一篮子”史料,也未能“一揽子”解决问题。林德扬究竟为何自杀,作者始终没有给出答案。显然,如果要深入分析林自杀的原因,要与其具体的境遇相结合。具体而言,就是要回归到1919年11月前后这段时间林德扬的境遇进行深入分析。
事实上,作者已注意到,林德扬在自杀前曾经营过一家国货店,他在死前除留给母亲兄弟三封信外,“还留有一纸账单,将自己所欠账单详细开出”。对于学生经营国货的情况,作者引用档案指出,学生卖国货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的学生自陈“原价买来原价卖出,只为增进国人使用国货的观念”,有的学生则说“可以赚几个钱贴补日用”,也有的人说“赚得的钱用作学校联合会会费”。面对学生经营国货店的种种历史样貌,作者并未对林德扬经营情况的“可能”做出评估——林是“赚钱贴补家用”,还是为了增进国人使用国货的观念,亦或是筹措学联经费使然?
如果将思路延伸,一些与此相“关联”的问题便可进入视域。比如,当五四学运的高潮退去,学生组织和学生运动面临常态化的问题时,上海的全国学联曾一度陷入缺乏活动经费的窘境。时为全国学联主席的姚作宾,为“挽救经济上濒于崩溃的学联”四处筹措经费,甚至“孤注一掷”地接触共产国际代表以获取资金。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想象,林德扬也许是为了筹措学联所需的经费而经营了国货店,“欠账”的经营失败,使其“事业”同样走向末路,便构成了他自杀行为的动因。当然,这也只是历史的一种“可能”,林德扬的国货店或许更像是一种自营创业性质。若为筹措学联经费,其身后的报道和纪念理或应大书特书。无论为公为私,学生在读期间经商恐怕不为校方所鼓励,但蔡元培称林为“奋斗失败”,显然也是承认了他的奋斗。考虑到蔡元培一向主张学生应以读书为本,那么这一表态便别具意味。
林德扬经营的国货店是盈利还是亏损?罗家伦最初的文章并未涉及,其所提到的账单也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因为收支之间肯定会有一个时间差。不过为其追悼会所作的行状称“营业殊佳”,如此则林德扬之死当别有原因。然而蔡元培谓其“奋斗失败”,显然又表明国货店经营出现问题。国货的竞争力不佳,适逢运动,民众爱国热情被激发,更可能压倒交易理性而去购买国货,一旦热情消逝,民众便会恢复其理性人常态,国货销路无法与洋货匹敌。林德扬的国货店成立于五四运动发生不久的暑假,但显然民众的热情在此后的日子里持续降温,因此蔡元培的结论或更可信。
很多史实问题之所以无法作结论,是因为史料所限。但所谓“事不孤起”,此处的“空白”,可借由彼处的史料来理解。作者在解读瞿秋白《多余的话》时,便运用了这一方法。如理解其对自身疾病的表述时,参照了方志敏的自述。谈到其知识阶级的自我观照,则引进了茅盾这一参照对象。作者在解读朱谦之的“自杀”与“自我”时,引用了易君左的一段回忆,称本以为朱要公开宣布自杀,到场后朱却宣布要“做和尚去”。由自杀而向佛,这一转变如何解释呢?可惜作者并未抓住这一问题,只是稍后引用胡适的话说“那些佛教徒,其实只是一班懦夫”。其实,如以有相似经历的梁漱溟来参看朱谦之的向佛主张,甚至关注整个清末民初知识界对佛学普遍的炽热情感,便可以展开与胡适这一断语的对话。
对种种相关史料进行分析和评估,从而更加接近所谓历史的“真相”,正是新史学的思考方式。一如新文化史的代表作品《马丁·盖尔归来》所展现的那样,身处16世纪法国乡村的马丁·盖尔,为何会做出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选择?应该如何理解16世纪法国农民的心灵世界?作者娜塔莉·戴维斯在搜集史料、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对马丁·盖尔背井离乡的种种可能进行了“评估”,并以一种“讲故事”的形式完美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而《自杀时代》一书只是像杂货店主般将各式史料如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出来,读者通过书中的叙述一点都看不到作者的分析与估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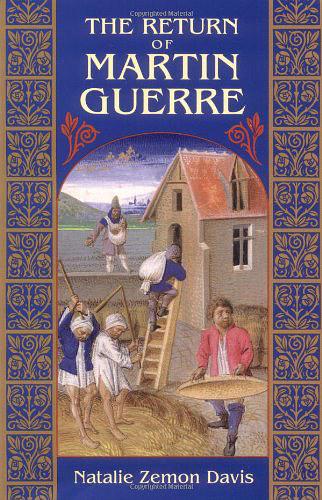
众所周知,后现代史学着力于挖掘过去底层与边缘者的声音。在这一史学潮流引导下西人种族与性别史研究方兴未艾。以中国古代史而论,关于女性的史料记述并不充分,且多为男性以其自身视角描述女性,因此以后现代史学观念观之,治史者要十分小心史料有所“污染”。
自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梁启超呼吁新史学开始,以西方理论参以中国传统考证方法进行女性史学研究案例并不少见,潘光旦所做冯小青影恋研究可算作这类研究中的一个典范。该研究首先考证冯小青其人其作真伪与否,他对论者所作真伪两方面意见依据新出史料分别予以论证。他特别引用后人关于其妹之生平著作论述冯小青确有其人。
如果以上述研究为参照,《自杀时代》一书对相反的史料基本未作处理,只是将各类论述一一列出,读者读后仍然是一头雾水。下面以其研究秋瑾为例稍作分析。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注意到了秋瑾、服部繁子对其丈夫王廷钧的描述大相径庭,也未随意取舍而是保留了两种说法:前者描述其夫阻挠其东渡日本“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而后者则称廷钧“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温顺的青年”,并主动求助其帮助秋瑾留学日本。但很可惜作者却未能根据各种史料的时间和语境以及周遭史料继续分析,给以解答。
无独有偶。秋瑾死后,其密友徐自华悼其“虽爱自由,而范围道德,固始终未尝或逾者也。徒以锋棱未敛,畏忌者半”。而与秋瑾同在日本游学的刘师培则在其文中称秋瑾“公德高尚,而私德或有所亏”。作者似应根据类似相反的史料对这一问题做一个较清楚的考察,使其研究稍稍深入一些。
而稍后对秋瑾王廷钧夫妻关系变化的解读,作者认为秋瑾夫妇关系从绍兴移居北京后由和睦一变为“经常吵架”,是因为1902年秋瑾夫妇二人独立门户,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家事琐琐,参商尤甚”,加之其夫王廷钧捐官户部主事后仕途又无进展。显然,以经济与仕途等因素来解读秋瑾夫妻的破裂,并无新鲜之处,而新史学对事件的解读则是希望开辟一个 “相异的意义体系”,给读者以新鲜的认识。

另外作者前文重点描述所谓秋瑾的“性别倒置”,其男装形象为丈夫所不许甚至毒打,到底在二人关系变化中起何种作用?进一步讲,秋瑾男性化这一角色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应如何解读?其与密友徐自华对话时经常问起自我堪与谁比照,这种自我意识该如何解读?
更有甚者,作者对其与密友徐自华的对话误读明显,先将书中叙述转引如下:
1906年秋瑾自日本回国后,曾在吴兴南浔女校任教员,与校长徐自华结为密友。当时二人都是31岁,一次饮酒闲谈,秋瑾兴起舞剑,问徐自华:“我如古时何人?”徐答道:“子好兵器,刚毅英勇,如孙夫人,未识谁为刘先主?见子战栗而跪乎?”秋瑾拍徐肩膀道:“子工诗文,不亚徐淑,吾为子再觅秦嘉可乎?”徐失笑道:“何出此匪夷所思之语?”秋瑾又笑:“吾与子相等,子可觅秦嘉,吾亦有刘先生。”徐顿悟其言中之味,“知其隐矣!”(第62页)
作者对此的解读为:“丈夫的无能成了秋瑾平生一大恨事……丈夫的软弱让秋瑾感到男性角色缺失的遗憾,这与徐自华玩笑中说刘先主‘见子战栗而跪乎’正相印证,也是秋瑾情感世界的真正‘隐’痛。”(第66页)这一解读固然与秋瑾之夫王廷钧的软弱怯懦形象相印证,但细读之,尚觉不通。
秋瑾问徐“吾为子再觅秦嘉可乎”。徐则“失笑”反问“何出此匪夷所思之语”。秋瑾借用典故声称为有夫之妇另寻佳偶,这在徐看来匪夷所思。联系到刘师培曾言秋瑾私德有亏,应指秋瑾男女关系方面较为自由。而前此史料又多记载秋瑾常女扮男装,并因此而遭到丈夫的毒打,让人怀疑女扮男装之后所寻对象应为女子。与之相应的是,徐自华讳莫如深的“知其隐”,绝非指她本人口中的“见子战栗而跪”的“刘先主”其人及其懦弱,而是出于为死者讳的不便明言之事。
结语
从《自杀时代》一书中,每每能看到作者的心思之妙。如此书主标题为“‘自杀时代’的来临?”,不仅“自杀时代”四字十分醒目,这一设问方式更能勾起读者的好奇心。不过,作者似乎更应交代清楚,李大钊所说的19世纪欧洲的时代病,究竟如何对应20世纪的中国?进而言之,近代中国的自杀时代究竟是否来临?我们当然不能单纯以近代大量的自杀案例来做肯定的回答,因为自杀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的现象。陈天华以来的自杀,到底有何不同?
作者的答案也许是“自我”。作者以“始于自杀,终于自我”为此书作结语,或许意在作出暗示。不过,这也留下了许多暧昧模棱之处。何谓“始于自杀,终于自我”?始与终之间是一种怎样的时间关系,抑或逻辑关系?在结语中,作者先从中国以自杀报复仇人的传统开始,并下断语称这种自杀缺少“主体性”,又以“‘自我’的介入使自杀的形态更加复杂”终。读之似觉传统的自杀没有“自我”,“自我”是近代自杀中特有的东西。那么何谓自我?传统自杀中为何不存在自我?作者可能想绕开这个问题,便以“主体性”替换“自我”。另外一种可能是,如作者在“缘起”中所述,“始于自杀,终于自我”或是自道其学术兴趣和思想的转变,即从关注自杀转向关注自我。从全书的谋篇布局看,作者从陈天华等案例开始到以朱谦之和瞿秋白的案例结束,与人物相关的自述性文本明显增多。这又为读者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正如“自杀”与“自我”均是极为微妙的话题,此书的宏旨也给人一种言犹未尽之感。也许这正是一种新史学特有的“感觉”。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