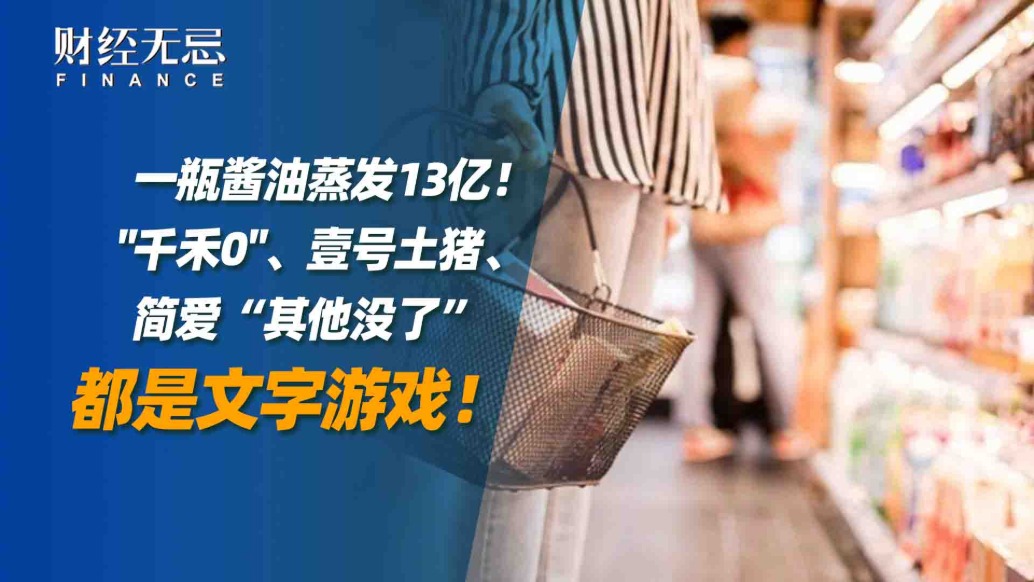- +1
十二段带着水汽的文字,唤醒你潮湿的记忆
天气渐暖,在许多地方,人们处于潮湿的气候之中。许多晦涩的记忆与情感,如一层薄薄的锈,在雨季肆意生长蔓延。
今天,我们精选了12段作家笔下有关“潮湿”的文字。带着水汽的文字会不会唤醒你的某一段记忆?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

01
是个潮湿的春天的晚上,香港山上的雾是最有名的。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融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绿幽幽地,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渐渐的冰块也化了水——雾浓了,窗格子里的灯光也消失了。梁家在这条街上是独门独户,柏油山道上空落落,静悄悄地,却排列着一行汽车。薇龙暗道:“今天来得不巧。姑妈请客,哪里有时间来招呼我?”一路拾级上阶,只有小铁门边点了一盏赤铜攒花的仿古宫灯。人到了门边,依然觉得门里鸦雀无声,不像有客,侧耳细听,方才隐隐听见清脆的洗牌声,想必有四五桌麻将。
——张爱玲 《第一炉香》
02
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霎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扭开收音机,忽然传来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应该出去走走了。然后是一个穿着白衣的仆欧端酒来,我看到一对亮晶晶的眸子。……思想又在烟圈里捉迷藏。烟圈随风而逝。屋角的空间,放着一瓶忧郁和一方块空气。两杯拔兰地中间,开始了藕丝的缠。时间是永远不会疲惫的,长针追求短针于无望中。幸福犹如流浪者,徘徊于方程式的“等号”后边。
——《酒徒》刘以鬯

03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
04
问题就出在搅乱一切的连绵大雨上,如果三天不上一次油连最干燥的机械也会从齿轮间绽放出花朵,而锦缎中的金银线长了锈,潮湿的衣服上则生出橙红色的水藻。环境如此湿润,仿佛鱼儿可以从门窗游进游出,在各个房间的空气中畅泳。一天早上乌尔苏拉醒来,觉得自己陷入一种恬静的恍惚中,叫人哪怕用担架也要将自己送到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那里。就在此时,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发现她后背上密密麻麻全是水蛭。赶在乌尔苏拉的鲜血被吸干之前,她用未熄的木炭烫灼把水蛭一条条揭下来。家里不得不开沟排水,清除蟾蜍和蜗牛,这样才能晾干地面,撤去垫在床脚的砖块,重新穿鞋走路。
——[哥]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05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少女望着流溪林场滴翠的山林思想她的青春。她正是十八九岁,每天在扩音器的催促声中晨起。那扩音器是绑在一根刨得毛糙的杉树原木上、戳进阴沉的黎明天空里的。她竟日劳动、出汗。不久前她落过一次水。一个年龄相仿的林友二话不说扎进翻腾的翠泊、救她上岸。湿润的肉体的质感因情急而未及留意,她和他都是。人家说那个年轻人一直爱她,她只笑笑。她突然爱上十九世纪庄园小说、幻想自己衬着大落地窗和松林月色弹奏钢琴也是在那个年龄——大概率受了姐姐影响,那阵子姐姐正在和一个英语系大学生谈恋爱。
少女望得出神的那片山林我说不出更多,我甚至无法证明少女真的望过、思想过。她的头脑出奇的寡淡,她的一生随之寡淡得出奇——除了最后几年,在一片再也压不下去的混乱中,她好像突然被折断:那也许说明她终于开始思想——她一头撞入只有一圈无影灯高悬的时空;她撞入得太晚了。
我说不出少女的十八九岁,说不出少女活在其中的那片风景。只不过是上一代的事,却已埋葬得很深。我一直想象那是一片滴翠山林,有一种如雨的绿色淡淡地扫,扫得一切将要化了;有一片且傍且依的湖;有一条一往无前奔涌的溪;那种绿色是淋不湿人的。我这样想象只因它在她口中是“流溪林场”。在她还活着的时候,我从未想过去核实那想象。
拿到驾照的〇四年三月,我拉上车门,照着刚买的〇二年版省城地图开,先是朝北开,然后迎着微垂的下午的日头开。我在省咸高速收费站问了一次路,在九〇九省道入口处又问了一次。我把车停进空旷、簇新的收费停车场(倒车时费了好些劲),才发现少女的林场已经变成国家森林公园。我买了一张票。票上印着滴翠的山林、一个湖、一条插入得很勉强的奔涌的青溪。我在愈发黯淡的、潮湿的林间步行,听鞋底碾轧碎石或松针。都是次生林:那些人工种植的、假模假样的、长在原生植被废墟荒冢之上的补偿性二手货。我在假货间穿行。我找到一座湖,浓得发绿。我想象少女就是在此处落水。我掏出叠成方块的她的遗书,展开,搁入湖面。那两页写得密密麻麻、被抚摩得毛茸茸的A4纸先是愣了一下,继而发出轻叹,顺从地拥抱了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甘浓命运。
——林棹《流溪》

06
“这里不能抽烟。”是护士的声音。
“那好吧,”警官说,“很快就会过去的,然后你——”
“再看看吧。”护士说,“给你一分钟的时间。”手术室热烘烘的,因为没有外面的风吹进来,而是机器把房间里的热风抽出去,所以房间里没有刚才走廊里那股掺杂着黑沙子的味道,但是房间里还是有一股风,他不仅能感觉到,甚至能看到这股风,徐徐的。他看到夏洛特的一小缕头发被风带起,不是轻飘飘的,而是黏滞的,头发湿湿地耷拉在她的眼睛和面颊上(医生在她的下颌处用纱布打了一个结,用来兜住她下垂的脸颊)。她似乎变了模样,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下垂的下颌和脸部肌肉以及那条贴在下颌处打了个结的纱布,还因为她整个身体似乎都垮塌了,像是决堤的洪水,不等他看清楚已经往更低的地方冲去。这股洪水冲垮了她的躯体,让她再也无法站起来,再也无法走路,就连躺下也控制不住这洪水的倾泻流动,就连脚上的那双薄纸做的鞋都兜不住这股洪水。他看着那股洪水一直流到地面上,仿佛连平平的地面也兜不住这股洪水,起初它的速度很慢,然后越来越快,直至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消失,完完全全地消失,一点痕迹都不留,被再多也不嫌多的尘土吸收得干干净净。护士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说:“走吧。”
“等等,”他说,“再等一下。”他想往前走几步,但是却不得不往后退了几步。那辆橡胶轮子担架又冲了过来,推它的还是那个没戴帽子的精瘦结实的担架员——头发还是像是用沾过水的梳子梳过,板板正正,熨熨帖帖,一缕头发很自然地打了个弯儿耷拉在额前,模样像是一个酒吧老板,往上翻卷的大衣后摆露出插在他屁股兜里的手电筒——他三下两下把担架推到病床旁边,护士把刚才盖在夏洛特身上的白布重新拉上去。“需要我把她抱到担架上吗?”威尔伯问,“我可以抱她吗?”
“不需要。”护士回答。白布底下的夏洛特的身体看不出任何形状。担架员把夏洛特的尸体从病床上往担架上抱的时候,整个尸体轻飘飘的,似乎一点重量都没有。担架被推着往门口走去,橡胶轮子重新发出吱吱的声音,警官捏着手里的帽子站在门口。随着担架消失在门口,嘎吱嘎吱的声音也消失了,威尔伯依旧站在房间里。这时候护士抬起胳膊,摁了墙上的一处开关,随着“嗒”的一声响,机器发出的嗡嗡声瞬间停了下来,速度很快,像是刚才还无处不在的嗡嗡声被猛地吸进了一个无声世界里,与此同时威尔伯感觉静寂和沉默劈头盖脸地像浪头一样向他压过来,他孤立无援,没有可以抓住的地方,只得听凭自己被那浪头抛起打转,最后大浪咆哮着离开,剩下他一个人站在那里,痛苦地眨着干得似乎要裂开的眼睛。“走吧,”护士说,“理查森医生让你们先去喝点儿东西。他一会儿才回来。”
“没问题,”警官给自己戴上帽子,说,“走吧,莫里森,放松。”
——[美]威廉·福克纳《野棕榈》

07
车子轰隆地驶过一片空阔的地带。右边是片广大的水域,看不到对岸。水面泛着粼粼光波,凉意更盛。挺立在水中的,是一棵棵犹然坚毅的死树。那巨大的水坝,大得像这新世界本身,快速吞噬了大片古老的森林。水面上升后老树逐一绝望地被淹死,但枝干犹高傲地挺立,只有鸟还会在枝干上头驻足、栖息。
山影像巨大的盆沿,盆水盛着绿树的倒影,枯树的前生。
水里盛着的是一个颠倒的世界。
那前生也只不过是回忆。
就好比那回你们决意穿过一座岛,那是座由繁花盛放般的华丽珊瑚礁环绕的、南太平洋上小岛。沿着小径走了一段路,经过一处小甘榜,迎面而来的村人无一不和善地微笑致意,男女均裹着纱笼。
路旁好多叶子稀疏的树上都盘着蛇,蜷曲成饼状。午后酣眠。
流向海的清水沟里,枯木下,淡水龙虾自在地探头探脑。
沿着字迹剥落的路标,高脚屋旁潮湿的小径。你们沿着许多人走过的旧径,反复上坡下坡,两旁是雨林常见的植被,挨挤着、甚至交缠着密密地长在一块。处处是猴子与松鼠,不知名的野鸟。
没多久就置入小岛古老蛮荒的心脏。
——[马来西亚]黄锦树《雨》

08
亚凤把木箱放在货架上,用松紧带固定木箱,让何芸搂着箱子跨骑货架。亚凤踩住脚蹬,屁股往鞍座蹾了蹾。一路上牛奶瓶、生锈的链条和缺油的花鼓喧闹,两人却非常沉默。偶尔他斜瞄一眼身后的她,只看见大胆地微笑着的膝盖。送完一箱牛奶,又回到吉普车送第二箱,如此来来回回,最后一趟亚凤抄捷径,骑上独木桥。桥墩是两根腿粗的盐木桩子,坚定地站在溪水中。溪水暴涨,淹没桥面。自行车碾过桥面时,半个轮圈陷在溪水中,长出两双残破的水翼。脚蹬出水入水,溅起无数落寞的水花。辐丝经过溪水冲击,散发疑虑的光芒。潮湿的链条在潮湿的齿盘上转动,发出吞咽困难的声音。何芸的脚指头蘸在溪水中,在水面划出充满刺梗的线条,抒发着小女生的绮思和神秘。一群母蜻蜓点水产卵,临摹出一朵又一朵整齐浑圆的小涟漪。一棵被连根拔起的小树从上游漂向独木桥,根荄砸入自行车前轮辐丝,车头在桥面顿了一下,自行车哗啦一声落入溪水中。
……溪底很浅,只淹到亚凤胸部。两个路过的庄稼汉跳到溪里,把亚凤和何芸搀上岸,把漂流的牛奶瓶、木箱、溪底的自行车拽上岸。
那天晚上,亚凤梦见自己裸着身体在溪水上踩自行车,轮圈掀起两股水翼像天鹅翅膀。溪水里悠游着蝌蚪、孔雀鱼和两点马甲,水面翱翔着成千上万的蜻蜓。独木桥下没有桥墩,何芸裸着身体站在桥下,好像她就是唯一的桥墩。自行车越过了独木桥,亚凤回头看见何芸跨骑货架上,冰冷的乳房贴住了他的脊椎骨。
何芸没有甘榜女人的圆胸和大屁股,薄薄的,像一只风筝,像随时被强风吹倒的玉米秆。
——张贵兴《野猪渡河》

09
夏至前一天,我从居住的城市出发,往南出城后转东,经过一段弯曲迂回盘旋上坡的山道,翻越大山连绵不断的峰峦之后,从层层下降的山路上眺望远处一片平坦开阔的翠绿田畴,如果天气晴朗,可以一直眺望到海,可以看到浮在海上远看如龟背、凸起于碧波之间的小岛。
旋子,我们预计在傍晚时分抵达岛屿东北平原上一个以温泉著名的市镇,寄宿一夜,第二天清晨绕过东北角的险峻断崖,驱车到东部的海滨。
没想到出发时天色忽然变暗,原来艳蓝明亮的天空飞来乌黑的云团。远方滚动炸开低沉的雷声,好像长久被积郁压抑的愤怒委屈,满溢到了要翻腾激荡,在大气间左冲右突,寻找宣泄爆发的出口。夏日午后热带岛屿雷阵雨前郁闷潮湿、饱含水分的空气,像一块沉甸甸、湿答答、黏腻的布,紧紧贴在皮肤上。
车子在山路上行驶。乌云大片遮蔽了天空,光线迅速暗下来。山壁上倒悬垂挂的蕨类植物的茎叶在风中惊慌地颤抖旋转。窒闷的沉静里听见大点雨滴嗒嗒打在车篷上。开始是点滴响脆疏疏落落的单音,逐渐由疏而密、由缓而急、像点点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嗒嗒嗒嗒,越来越快,最后连成一片,大雨倾注而下,瀑布一样银白色的重重雨幕遮蔽了视线,雨刷疾速左右摇动,雨珠在车窗玻璃上飞溅四散,长久积抑的郁闷似乎终于可以尽情放声号啕大哭。
——蒋勋《大雨》
10
山半腰箭竹林子里,他们并排倒卧,传五加皮仰天喝,点燃大麻像一只魑魑红萤递飞着呼。呼过放弛躺下,等。眼皮渐渐酸重阖上时,不再听见浊沉呼吸,四周轰然抽去声音无限远拓荡开。静谧太空中,风吹竹叶如鼓风箱自极际彼端喷出雾,凝为沙,卷成浪,干而细而凉,远远远远来到跟前拂盖之后哗刷褪尽。裸寒真空,突然噪起一天的鸟叫,乳香弥漫,鸟声如珠雨落下,覆满全身。我们跟大自然在做爱,米亚悲哀叹息。
——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

11
雨开始滴滴答答下起来,雨点愈来愈大,愈打愈急,天空阴云逐渐密布。我张伞要和她一起撑,她推开说想淋雨,我收起伞,两个人坐在白色的双人铁椅上,任雨淋。湖面上急骤的雨点如细箭般漫射进无心的平面,风也刮起一波一波冷颤的皱纹,我看她的长发被水胶合,发末端水沿着脖子滑下,脸更简约地清丽。
——邱妙津《鳄鱼手记》
12
赤道上的雨多是在午后才来的。前半日太阳有多暴烈,后半日的雨便有多凶猛,像是用半日蓄势待发,一举向日头报复,以牙还牙。顾老师说,因为雨下得频繁,人生中不少重要的事好像都是在雨中发生的。那些记忆如今被掀开来感觉依然湿淋淋,即便干了,也像泡了水得书本一样,纸张全荡起波纹,难以平复。
——黎紫书《流俗地》
文字丨作者均已在文中标注
编辑丨楚尘文化编辑部
原标题:《十二段带着水汽的文字,唤醒你潮湿的记忆》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当“雷雨”告别台词
- 东部战区圆满完成联合演训各项任务
- 国防部正告赖清德当局

- 华夏幸福:与保碧新能源公司签约,共同在中东核心地区拓展“产业+新能源”开发业务
- 国内期货夜盘开盘涨跌不一,氧化铝跌超1%

- 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又名
- 文艺复兴时期名画《维纳斯的诞生》是谁的代表作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