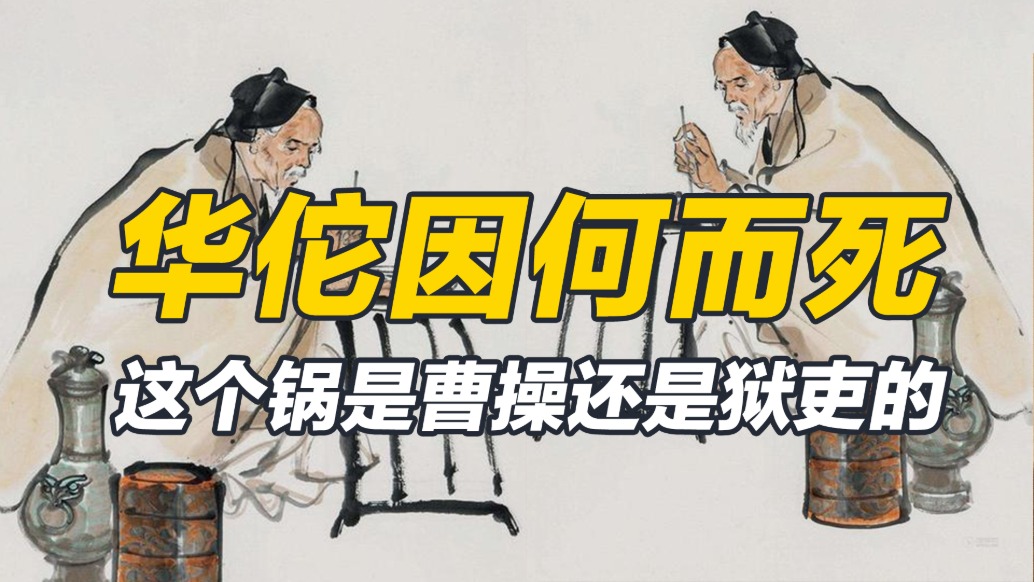- 56
- +1
砚边书影 | 陈世旭:读书人
原创 陈世旭 上海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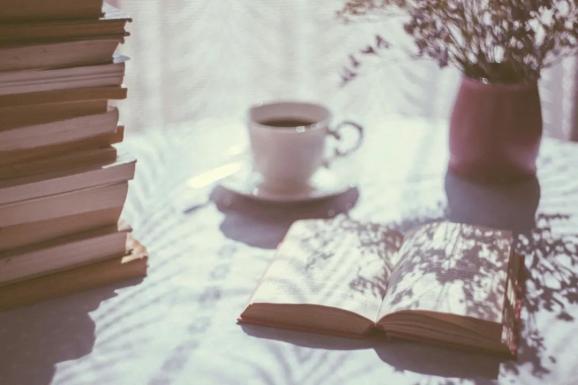
Photo by Freestocks on Unsplash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5年3月号
读书人
陈世旭
一、向书致谢
上小学,听老师讲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用功读书的故事,有点胆寒,似乎读书是一种刑罚。好在家里拮据,除了课本,没书可读。中国明清四大名著,都是放了学,同学在书摊上租了小人书,我在一边厚着脸皮蹭看的。也就只留下了一些肤浅的印象:《水浒传》我喜欢鲁智深,当提辖扶弱凌强,当和尚见佛杀佛。讨厌宋江,为了当官害死了那么多好汉。同情潘金莲,但凡她有一丁点追求幸福的权利也不至于沦为杀人犯。《三国演义》我喜欢关公,千里走单骑,孤独而豪迈!刘备太装,诸葛亮心眼太多,折寿。曹操会写诗,但不是好东西。杨修喜欢卖弄聪明,倒了血霉。周瑜真帅,女孩子为了让他看一眼,琴都弹不好,可惜气量小。《西游记》里的女儿国和蜘蛛洞是我的少年妄想。唐僧是我本家,但我不喜欢他的一本正经。如来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让我从小尽可能远远避开绝对权力。《红楼梦》里女孩多,最可爱是史湘云,傻乎乎的,没心没肺,喝多了酒醉卧花丛。宝钗甜熟乖巧,像女干部。黛玉小性子,谁也受不了。多年后,以写作为职业,接触到中外长篇小说,但我从头到尾读完的只有雨果的《九三年》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读完了,立刻明白我这样的人被喊做“作家”纯粹是一个笑话。
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在陶渊明故里的乡镇务农、工作,算是他的后世同乡。他在自传里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与他有同有不同:同的是“不求甚解”,不同的是不怎么“好读书”。除了忙于生计,跟懒惰、不愿刻苦不无关系。单位分了房子,我十分起劲地做了一整面墙的书架,塞进了一整面墙的书,煞有介事地“坐拥书城”,结果,也就是“坐拥”而已,偶尔翻过几本工具书,借口忙于公务和家务,其他的纹丝未动。将近三十年后,我移居岭南,那些书全数送了亲友。
知道同行中的许多人遍读中外名著,个个成就斐然,很羡慕,但也只能是像唐朝诗人孟浩然写的:徒有羡鱼情。有些年,文坛《红楼梦》热,读《红楼》、说《红楼》、续《红楼》,蔚然成风,我甚茫然,找各种歪理为自己的无知辩解:如果只有读了《红楼梦》才能写好小说,那曹雪芹是读了谁的小说才写出《红楼梦》的呢?参加文学活动,与著名作家刘庆邦同座,我借机请教。他告诉我,他把《红楼梦》仔细读了五遍。惊得我掉下巴。难怪他被称作“中国短篇小说之王”,而我的写作始终原地踏步。
在大学插班学习,一位几乎是晚辈的本科生很怜悯地对我说:你们的出现是得益于历史机遇,缺乏知识根基,走不远的。我一脸通红地认可。
举凡大作家,没有浪得虚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百分百是个认认真真的人:认认真真读别人的书,认认真真写自己的书,他的《向书致谢》充满激情:
“它们静悄悄立在墙边,仿佛都睡着了,可是它们的每个名字又像是睁开一只眼睛在看着你……它们等待着,直到你去把它们开启……在一个夜晚,当你经过困顿的旅途回到家中;在一个中午,当你不胜疲倦地离开人群;在一个早晨,当你昏昏然从睡梦中醒来——只有这时,你才……满怀着甜蜜尝试的享受性预感,走向橱边,上百双眼睛,上百个名字默默地、耐心地迎着搜寻的目光,宛如苏丹宫殿里的女奴在迎候自己的主人,谦卑地听候使唤。”
“书啊,你们是最忠诚、最沉默寡言的伴侣……你们的存在,就是永久的保存,就是无穷无尽的鼓舞……在那灵魂孤独的最黑暗的日子里……你们时时守护着,你们赐人以幻想,并在烦躁与痛苦中给人献上一刻宁静!每当灵魂被掩埋在凡生之中的时候……每当阴沉昏暗的时候,你们总是把我们内心的天空扩展到远方……一旦有心灵触摸了你们……你们的语句就会像驾着烈火的车辆,载着我们冲出狭隘境地,驶入永恒。”
可惜,这些滚烫的文字只能留在我的笔记本里。
唯有读书高
乡塾先生孔丘因为被广泛认为书教得好,被皇帝捧得老高,去他们家,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北宋皇帝赵恒说“书中自有千钟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五经勤向窗前读”,就有可能升官发财,出门有车马坐,找好看的老婆;北宋晚期的汪洙干脆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读书自然就成了自古以来无数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农民家过年,也会贴“耕读传家”的门联。“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白丁”就是目不识丁的人,是要被瞧不起的。学子们读书,几乎就是拼命。《战国策》记录苏秦读书打盹,就用锥子扎大腿,扎得血都流到脚上;《汉书》记录孙敬读书晨夕不休,半夜实在熬不住瞌睡,就用绳子一头绑在自己的头发上,另一头绑在房梁上,一打瞌睡头皮就吃不消;《朱子语录》记录两个宋朝学生去拜见当时的名流,见人家正在打坐养神,便恭立于门外的大雪中,等名流醒来时,雪已经下一尺深了。
古人读书,首在取功名。然而许多人得到梦寐以求的功名,一辈子也差不多走到了头。宋朝有个叫詹义的书生,七十三岁才考中秀才,媒人提亲,问他年龄,他只好自嘲:“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逢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老婆也讨不到,别说出将入相了。
《三字经》说五代人梁灏,考状元时,殿试对答如流,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不如他:“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以此证明只要坚持,无论年龄多大都可以夺魁。可一个人八十二岁了,夺了魁又如何?《三字经》没有下文。
汪洙本人,自幼聪明好学,相传他九岁便能写诗,乡人传为“神童”。一生不仅淹贯博洽,熟悉经史,还写了不少浅显易懂、便于记诵的短诗,被汇编成《神童诗》,与《三字经》等同誉为“古今奇书”,成为训蒙主要教材。人们耳熟能详的“四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等等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诗句,都在这本诗集里。但他自己直到将近七十岁才总算考中进士。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情况,人们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读书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考一个功名,有了功名却什么也干不了。何苦来哉。
好在汪洙后来做了一个州府学的教授,学生众多,有一府之望。一个读书人有这样的成绩,有没有虚头巴脑的功名,也就无所谓了。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大夫”,授正四品衔。对他本人而言,其实毫无意思。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
自古以来,关于读书的教训汗牛充栋,但也有不把这些教训太当回事的。
看到一则徐志摩关于古今读书之不同的高论:“从前的书是手印手装手订的,出书不容易,得书不容易,看书之人也就不肯随便看过;现在不同了,书是机器造的,一分钟可以印几千册,一年新出的书可以拿万来计数,还只嫌出版界迟钝,著作界沉闷呐!你看我们念书的人可不着了大忙?眼睛只还是一双,脑筋只还是一副,同时这世界加快了几十倍,事情加多了几十倍,我们除了‘混’还有什么办法!”
徐志摩是才子。只有才子才有这样的落拓。经历了很多,知道了很多,然后说:“我们除了‘混’还有什么办法!”
与徐志摩同时代的林语堂对读书也取了一种散淡的态度: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称为清高”,倘若“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
“读一部小说概论,到底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书上怎么说,你便怎样答,一字不错,叫做记问之学。”“学堂所以非注重记问之学不可,是因为便于考试,如拿破仑生卒年月,形容词共有几种……事实上与学问无补……要用时自可在百科全书去查。又如罗马帝国之亡,书上讲有三大原因……然而事实上问题极复杂。有人说罗马帝国之亡,是亡于蚊子(传布寒热疟),这是书上所无的。”
“整个世界就是大学堂,在学校里能学到的东西不如从校外所见所闻能得到的知识;只要养成爱读书的习惯,一部字典在手,凭自修,什么学问都能学到。”
“出门、走路、看戏,也乱看乱学,文学乎,不文学也。”
“读书本来是至乐的事。”“读书人每为‘苦学’二字所误。”“人生快事莫如趣,而且凡在学问上有成就的,都由趣字得来。”
“一点没有定规。今天英文,明天中文,今天唐诗,明天聊斋……元曲、《琵琶行》、李白的诗,喜欢就选读,不喜欢就拉倒;庄子与西厢同等看待。韩(愈)文与《宇宙风》同等看待,而且在我看来,宁可少读韩文,不可少读现代通行文章。”“学问之事,是与看《红楼》《水浒》相同,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若不能用看《红楼》《水浒》的方法去看哲学史、经济学,就是不懂得读书之乐。”
“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真正的读书,这才不失读书之本意……读书时,须放开心胸,仰视浮云,无酒且过,有烟更佳……或在暮春之夕……到野外读离骚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
“就兴味与程度相近的书选读……知其书名、作者、内容大概,也就不愧为一读书人了。”
随意,闲适,一派名士风度。的确,读书如果目的性太强,那不叫读书,叫受罪。
这种不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主张,似乎可以追溯到亚圣孟子那儿。他的《尽心章句下》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话,说他对于《武成》这篇书,最多就相信其中的二三页——仁人在天下没有敌手,以周武王这样极为仁道的人去讨伐商纣这样极不仁道的人,怎么会使鲜血流得可以漂起木棒呢?
孟子之文长于论辩,说理畅达,气势充沛,精辟透脱,是那时散文的极品,别人很难反驳。
古往今来,书是无数人膜拜的神物。然而,孟子不仅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且所举的例子是《尚书》中的内容,而《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当时有着极其权威性的地位,岂容怀疑。仅此一点,孟子的独立思考精神,就尤其难能可贵。
当然,“书多前益智”,开卷有益,书绝对是应该读的。深读,浅读,多读,少读,读了总是好的。至于无聊的书,读几页就可以放下。一只苹果,难道非要啃完了才知道是烂苹果吗?
无人处诵经
我知道纪晓岚这个名字,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缘。
一九八二年冬,中国作协受当时的农牧渔业部委托,组织几位作家到海南农垦体验生活,我有幸参加。带队的是当时天津作协的负责人柳溪大姐。闲谈中,她告诉我们,她是纪晓岚第六代孙辈。那时候,我一点不知道“纪晓岚”是何方圣贤,只是隐约记住了这个名字。几十年后,在一本杂志看到作者引述的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个桥段:京城有个老和尚与纪晓岚的高祖后斋公时有往来。有一回,老和尚兴奋地告诉后斋公一件怪事,说自己有天夜里灯下诵经,忽闻窗外窸窣有声,喝问是谁。窗外人答:“他人都是有人处诵经,您老是无人处诵经。”不料,后斋公说:“您以此语告我,也就和那种有人处诵经的‘他人’差不多!”
毫无疑问,“有人处诵经”是装模作样,“无人处诵经”是真的用功,但转弯抹角借“一件怪事”来告诉人家自己“无人处诵经”,这跟“有人处诵经”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世上“后斋公”这样的明眼人多的是,只是总也少不了我这种智商偏低的缺心眼罢了。
早年写文章,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自私,怯懦,没有正义感、责任感、使命感;跑笔会,开研讨会,出全集,写回忆录,建纪念馆;显摆,凡尔赛,不自知,不自重,不检点,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等等。言外之意似乎自己不在其中,清高出尘。
静心想来,其实是因为自己没有那样的资格,嫉妒心理作祟。
东汉书法家崔瑗年轻时意气用事,杀了仇人,只身逃亡。几年后,朝廷大赦,才回到老家。为了记住自己的鲁莽惹祸,作了《座右铭》,原文我记不清了,大意是:不要谈论别人的短处,不要夸耀自己的长处。给了别人好处不要老想着,受了别人的恩惠千万不要忘记。世上的荣誉不值得羡慕,做好自己就行了。凡事问心无愧,就不必在乎别人的诽谤议论。不要使自己名不符实,别人说你愚蠢也没有什么。洁白的品质遇到黑色的浸染也不改变颜色,那才叫宝贵。即使表面上暗淡无光,内心也蕴含着光芒。老子讲过柔弱和刚强、庸人和君子的区别,一个人持久地保持高尚的品行,自会芳香四溢。
崔瑗《座右铭》关于做人的要求,我这样的俗人肯定达不到。但不干《阅微草堂笔记》里那个老和尚拿别人“有人处诵经”来表现自己“无人处诵经”的傻事,应该是可以的吧。
由此,又想起一个与张爱玲有关的话题:
我没有看过张爱玲的书,但从网上看到她的大量语录和对她的评论。给我的感觉,她的确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女作家,高傲与卑微,智慧与偏执,任性与执著,薄凉与深情,集于一身,有无数的“张粉”“张迷”,其中不少人通过引述她的作品来自况。有篇文章引述了《小团圆》中的文字:主人公在乡下看戏,看戏里的人生,二美三美大团圆的金钱名利美女的成功,感叹道:“这些人都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阔度。”而主人公自己——“穿着臃肿的蓝布面大棉袍的九莉,只有长度阔度厚度,没有地位”。
“九莉”的原型是作家本人,“九莉”的这个感叹是典型的张氏感叹。引述者说自己特别欣赏这段话,言外之意含着自己也是“没有地位”但有“长度阔度厚度”的人。
我对这位引述者毫不了解,反对把“有地位”作为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是不错的。但“没有地位”是不是就一定有“长度阔度厚度”,其实也是大可怀疑的。除非你有张爱玲的“长度阔度厚度”,否则这样的自况就难免惹出上面那个老和尚的笑话。
含蓄与不含蓄
看到一则文人旧事:
某次,胡适家宴,徐志摩抱着一本德文书旋风般冲进,大家争看书中插图,胡适不屑: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点含蓄。
让徐志摩和一众文人兴奋的那本书我无缘得见,但因为受命写一位古代画家的传记,涉及中国传统绘画史,对“改七芗”“仇十洲”略知一二。
“改七芗”即改琦,清画家,以《红楼梦图咏》尤为著称,图中林黛玉柳眉杏眼,樱桃小口,弱不禁风,一副病态,为典型的传统古典美人形象。被称为“改家样”的改琦画法,占据了清中后期仕女画主流。
“仇十洲”即仇英,与沈周、文徵明和唐寅并称明四家。
明代仕女画,人们多知唐寅而不知仇英。其实仇英胜唐寅一筹,颇得方家青睐。鲁迅日记有:“七日雨,午后霁。在艺苑真赏社买《燕寝怡情》一本,三元角。”“九日晴。晚以《燕寝怡情》赠增田君。”
改琦和仇英在中国画史上都不是那么“不够趣味”的画家,如果非要说他们“不够趣味”,恰在于他们只讲“趣味”——所谓“只求神似,不求形似”:技法凝固,构图呆板,程式化,扁平化,脸谱化,概念化,符号化,姿态或有不同,表情相差无几,千人一面,缺乏个性。尤其清代文人画把女性病态美作为时尚,在中和、平淡中隐藏对女性美的赞赏。据说这是为了避免引起观者的感官剌激,以保持审美观照所需要的心理距离,渗透了一种理学精神。愚见以为,如此“理学精神”,不过是一种末世的萎靡。
胡适的“含蓄”说,表明的只是他个人的艺术趣味,并不是艺术的唯一标准。况且,即便不是“一览无遗”,即便是通过“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来引人遐想,道学家也一样可以斥之为“诲淫”。所谓“含蓄”不过是虚伪而已。
绘画史上,不含蓄,乃至“一览无余”,同样有的是伟大的艺术。
某年在欧洲看到米开朗基罗和卡拉瓦乔的人体作品,吃惊之余肃然起敬,无论是形体线条还是色彩纹理都极为精确、细致、繁复,以至逼真,艺术家高度的造型能力和精湛的表现技巧,带给人们的远不只是赏心悦目的视觉冲击,你甚至可以感到作品中肌肉的弹性、血液的奔流和汹涌的生命力,其中没有一丝邪恶。作为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压根没有沉溺于追求公众的认可,而是大胆地把“人”从宗教里带回现实世界,赋予了人类生存以无比崇高的尊严和意义。
这是我从“改七芗”和“仇十洲”的画里绝对感觉不到的。划痕
一位朋友给我发来网文《全面评价鲁迅》,拜读后发现,所谓“全面”,其实是全负面。
判断将近一百年前人事的是非真伪,像我这样专业研究者之外的读者,唯一可以依凭的是被“评价”者本人的文字。尽管作家的文字与作家本人并不完全等同,文字自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这价值很难说与作家本人的价值完全无关。
由于时代的缘故,鲁迅的书是我这一代人读得较多的书。我得到的印象是:
一、鲁迅当然不是不可以触碰的偶像、不可以讨论的圣人,他一样喜欢开玩笑、吃零食、上馆子、看电影、肺结核还嗜烟,也打茶围,有旺盛的荷尔蒙,会误会,会偏执,爱发脾气,也容易感动,尖刻决绝,也温情顽皮。
二、鲁迅对传统文化负面及国民性弱点的批判所达到的深度,无人可及。《阿Q正传》三万字,足可使他“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两间”是历史与现实之间,“彷徨”是一个独立思想者必然的寂寞。
三、像所有广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一样,鲁迅难免被消费。《全面评价鲁迅》本身就是一种消费。
总之,鲁迅的文字在中国人的精神史上留下了太深的划痕,这划痕是无法抹去的。
放 下
《弘一法师渡人无数的五句话》在网上流传颇广,五句话的主要意思分别讲万事皆缘,苦乐皆福,得失有因,自在不争,无须执念等,可以归于一个词:放下。
应该说,道理都是不错的,只是因为浅薄冥顽,我还是难免疑虑。
我对李叔同先生的才华很仰慕,早年到西湖,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见到他出家前封印的洞窟,如同埋葬了他前半生的墓穴。后来到福建泉州,又特地寻访了他故世前住的寺院:一座陈旧不堪的小庙,一间狭窄发霉的禅房,一张灰白板床,靠着黄黑破落的旧报纸糊的墙角。想起他临终前的绝笔“悲欣交集”;想起他给昔日好友留下的偈语“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想起后人借“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对他的颂词“如春满花开,如皓月当空”,不免感慨系之。
半世风流半世僧,去世前,他心中应该还是有所念念的吧。
一个人真的放下了,随处都可以放下,何须入空门。身体不过是皮囊,心灵才是精神的故乡。二十多年前游南普陀,见石刻“海天佛国”,心里忽然生出四句:“佛界无佛,空门不空,唯其自心,莫问西东。”我不信佛,无意妄言偈语,只是觉得,凡将“放下”说出的人,其实都是未必放下了的人,放下了的人什么也不会说。
梁实秋有篇文章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
有道之士,对于尘劳烦恼早已不放在心上,自然更能欣赏沉默的境界。这种沉默,不是话到嘴边再咽下去,是根本没话可说,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皆寂然,唯迦叶破颜微笑,这会心微笑胜似千言万语。莲池大师说得好:世间严醯醇醴,藏而弥久而弥美者,皆繇封固牢密不泄气故。古人云:二十年不开口说话,向后佛也奈何你不得。旨哉言乎……言语道断之后,性澄清,心珠自现,没有饶舌的必要。
然而“不饶舌”其实也并不等于“尘劳烦恼早已不放在心上”,“言语道断之后”是不是一定就“性澄清,心珠自现”是大可怀疑的。真正说得透彻的是《红楼梦》里的跛足道人:“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
真正的放下乃是寂灭。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放下,活着就是没有放下。所谓放下,不过是一声无奈的叹息,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自己。
大 家
著名作家张炜介绍过一则文人轶事:
高尔基是跨时代的文学泰斗。他主要写小说,也悄悄写诗,有一次拿给正在诗坛走红的马雅可夫斯基看。没想到后者看完毫不留情地说,这写的是什么东西!不行!根本不管面对的是谁。而让人惊讶并感动的是,高尔基的反应不是我们想象的恼羞成怒,而是让人心疼地呜呜哭了。
老人哭得那么可爱,那是一个大师在文学面前的深深谦卑。他可以不向强权低头,但在文学面前,却低下了高贵的头。
同样,比高尔基年轻二十五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也很可爱。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诗更加神圣的了。为了诗的尊严,他可以无视一切,即便对方是至高的权威。这样的坦率表现出的艺术勇气,真是了不起。
我在早前的拙文中表达过一种认识:只有天才才懂得天才。
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都堪称天才。他们在各自专长的领域都是顶级行家。前者的谦卑是对行家的谦卑;后者的坦率是对行家的坦率。真正的行家一定是谦卑的,因为他知道他面对的同样是一个真正的行家;真正的行家又一定是坦率的,因为他知道一个真正的行家不需要浅薄虚伪的吹捧。
“述”与“作”
“二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跑防空洞躲空袭,见到国文系的沈从文也在跑,喝问:我跑是因为我死了没有人讲《庄子》,你跑什么!
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庄子》专家,认为天下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庄子是一个,他是一个,所有吃《庄子》饭的人加一块是半个。沈从文小学没有毕业,因为写小说出名,进了大学教书。
我的印象中,像刘老师那样,因国学领域某一门学问的精通而俾睨天下的学者不止他一位,他们对专业知识的拥有自然是十分可敬的,但因此就对自己从无涉足的领域无端蔑视,就似乎有点偏颇了。
学问的精通者并不是学问的创造者,没有创造,精通从何谈起?“述而不作”固然是圣人言,但如果没有“作”,“述”从何来?圣人认为“先王”已经穷尽了宇宙真理,后人只要规规矩矩“法先王”就行了。但历史证明这是一种死亡思维。“述而不作”的学者看不起写小说的“作家”,但今天的大学把沈从文小说列为教材,不知刘老师如果在世会做何感想?
文学当然不等同于哲学。姑且不论沈从文小说乃至所有公认杰出的小说有没有哲学的成分,视为哲学的《庄子》开篇就说“寓言十九……”云云,所谓寓言,就是寄寓的言论。《庄子》阐述道理和主张,常假托故事人物,寓言的方法是《庄子》语言表达上的一大特色。而“寓言”,今天的人们一般归类于文学,却是事实。
家 训
中国的“家训”,从周公告诫子侄周成王的诰辞就开始了。社会历经氏族、家族、家庭的变迁,家族顺应王法制度,拟定行为规范约束家族中人,绵延了数千年。自汉初起,家训著作随着朝代演变日渐丰富精深,内容涵盖励志、勉学、修身、处世、治家、为政、慈孝、婚恋、养生方方面面,作为前辈留与后人的处世宝典,治家良策,教子妙方,被许多人当做思想圣经,谨遵奉行,诸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之类,更是受到官方高度肯定。
某年下乡采访,一位从领导岗位退休的干部让我见识到一种极朴素的乡村家训。
说起往事,这位退休干部最欣慰的是自己历尽宦海风波,从没有翻过船。他把最直接的原因归于父亲——在他第一次离乡进城的头天晚上,一辈子种田的父亲叮嘱了他三句话:
一、热闹的地方不要去。
二、钱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
三、有烧香的心才有吃饭的命。
三句话,简单质朴,但让他受用终生。他理解的意思不是胆小怕事,世故平庸,不思进取,而是做人的根本: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实实在在。
头一句,就是遇事心里有数。诱惑越多,头脑越要清楚。
第二句,就是不盲目追求大富大贵,凭本事立身。
第三句,就是有敬畏。心术不正,难说没有饿饭的一天。
不同的时代背景,这三句话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但始终像三脚铁锚一样,让他在大大小小的世事起伏中保持着稳定。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路走来,上级下级,不止一个同事一失足成千古恨;远远近近,也不止一个熟人一念之差沦入万劫不复。
说起这些,老张很痛心。
同样的三句话,不同的人,一样可以有不同的人生内容。
对于我这样写作为生的人,这三句话同样有用:
一,不趋时跟风;二,不把名利看得太重;三,以善为本直道而行。
一位普通农人嘱咐儿子的三句话,比古往今来无数圣人的那些堂而皇之的家训强多了。
河洛之争
整理旧书,见到几十年前在废品店买的《河洛精蕴》。当时读过,做了若干眉批。但印象深刻的却是河洛之外的故事。
《周易·系辞下》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说法,先秦两汉至唐代文献基本持此观点。然而河洛早已失传,至少唐末已不可见。宋以来围绕河洛的真伪以及八卦是否据河洛而画、是有河洛而出《周易》还是因《周易》而造易数等等,形成否定(疑古派)与肯定(图书派)两大派,论争不休。
疑古派视河洛为怪妄,并大张挞伐。其先驱为北宋欧阳修,否定伏羲授河图画八卦,认为河图不在《易》之前。
图书派则极力推崇河洛。代表人物有王安石、苏轼,他们都严词反驳欧阳修的观点,态度十分激烈。
欧、王、苏都是宋代顶级文人,都名列“唐宋八大家”,都是我崇拜的偶像。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欧为北宋文坛领袖,最欣赏的两个人就是王和苏。王科考时,欧对其文采大为赞赏,之后也曾大力提携。至于苏,二十出头参加礼部考试时主考官是欧,他直接就该喊欧老师。三人亦师亦友。他们之间在河洛上的争执,像是神仙打架,让我瞠目结舌。
自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即便是师友,也并不等于所有的见解都必须一致,但河洛之争不是鸡毛蒜皮的事,牵涉到他们同为儒生的立身之本。
欧的经学著作《易童子问》认为《易传》、卜《系辞》以及《文言》《说卦》以下,都不是孔子所作,其中所称的“子曰”,是讲师之言,并不专指孔子。又指《说卦》《杂卦》是筮人之占书,河洛更是“误惑学者,为患岂小哉……王制之所宜诛也”,到了可杀的程度。
对欧之论,王很不以为然,认为河洛是“天地自然之意”,苏附和王:“夫《河图》《洛书》……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正义感爆棚。
以我的学养,无法评判这样的是非,但对几位大家的持论依据颇有感触:
欧是百分百的大儒,却对儒家祖宗并没有唯唯诺诺,其立论看起来避开了孔子,但《周易·系辞下》明明就说“孔子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其实是避不开的。这样的凛然风骨,令人起敬。不过,一个文人不容异见,对学术问题动杀心也够吓人的。
而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和公认聪明盖世的苏却唯权威是尊,并且搬出来压制不同观点,多少出乎我的意外。
将近一千年来,河洛之争绵延不断。直至现当代依然不休。有阐述河洛“发前人所未发”者,有“图书之说,实由道家而来,与作《易》无关”,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河洛者,即使“坚信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画卦”的图书派内部,也有什么是河图、什么是洛书、是“图九书十”还是“图十书九”的分歧……诸如此类,吵得不可开交。
这让我不免心生悲凉:一千年,那么多鸿儒硕学倾注智慧和心血,争的就是这点跟科学思维、社会发展、历史进步八竿子打不到边的所谓“包罗万象的学问”。
幸运的是,中华民族有着许多抬头看世界、向未来、求上进的思想者。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的这段话,让人看到民族成长的希望。
原标题:《砚边书影 | 陈世旭:读书人》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台独”作妖,引火烧身
- 解放军今起位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
- 4月起,这些新规将施行

- 清明节假期全国口岸预计日均210万人次出入境
- 港股医药股震荡走高,康龙化成涨近7%

- 源自西方的一个节日,在每年4月1日
- 杜牧的诗《清明》中“路上行人欲断魂”的上一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