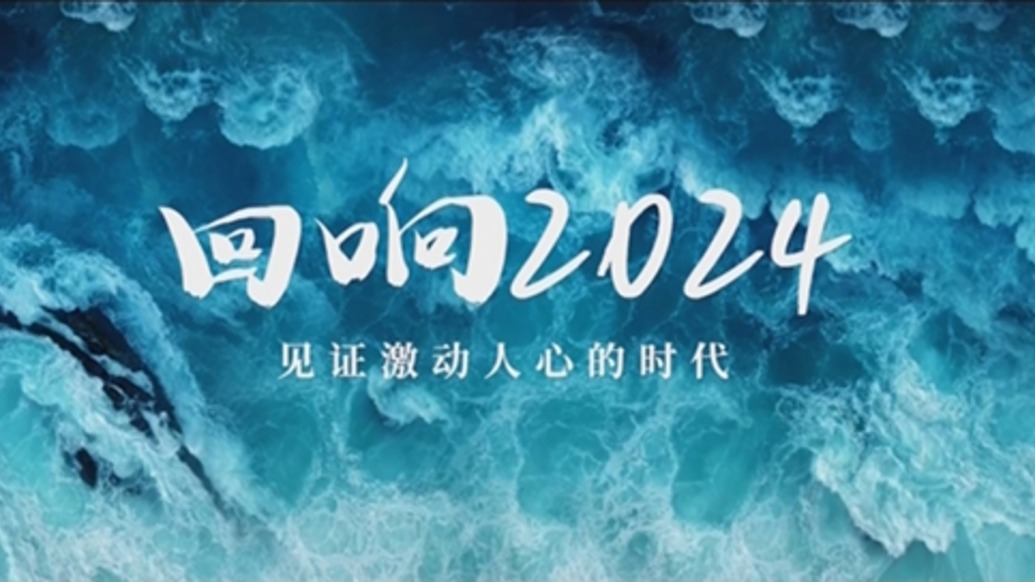- 25
- +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主题争议与发生学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主题争议与发生学
吕纯山
作者简介:吕纯山,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化哲学研究所。
人大复印:《外国哲学》2024 年 12 期
原发期刊:《哲学动态》2024 年第 20247 期 第 65-72 页
关键词:陈康/ 存在论/ 神学/ 发生学/
摘要:陈康在《智慧》一书中提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对智慧(即第一哲学)究竟是存在论还是神学的论述是不成功的,认为存在论和神学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陈康的这一看法或许是出于对《形而上学》文本的误解,对此亚里士多德本人在Λ卷已有合理的解释,即神学是存在论的一部分。《智慧》在阐释《形而上学》时对发生学方法的支配性运用固然值得商榷,但完全忽视这一方法也是不明智的。这一方法并非仅能用于解释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矛盾,而且可以用于澄清一些概念在《形而上学》不同章节或亚里士多德不同作品中的发展和丰富。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并非他本人确定的书名,其内容也非连贯的,而是主题相近的论文集。他本人也没有用过“形而上学”这个词。至于这门学科考察的对象,他称既“关于原因和本原”①,又关于“神”,还有“作为存在的存在”等。(《形而上学》,982a1,983a5-10,1003a21)也正因为存在多种说法,《形而上学》主题究竟是神学还是存在论的问题,在后世尤其是中世纪逐步成了一个著名的争议性问题。到19世纪,这一争议形成了无法化解的矛盾。20世纪以来,耶格尔(W.Jaeger)用发生学方法来解释神学和存在论的关系,他强调亚里士多德有一个从神学到存在论的发展过程,但耶格尔没有展开讨论。(参见耶格尔,第182页)欧文斯(J.Owens)则强调“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普遍性就是神圣实体的普遍性,从而把普遍性和神圣性统一起来。(参见汪子嵩等,第680页)陈康不满意欧文斯的解释,把从发生学立场回答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主题是什么的问题作为其《智慧:亚里士多德追求的科学》(Sophia,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以下简称《智慧》)(参见Chen,1976)一书的宗旨,也首次把“智慧”“我们所追求的科学”“原因”等说法引入这一争议性的话题之中。本文即以陈康的《智慧》为研究对象,讨论他从发生学角度回答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主题争议的得失,并进一步讨论发生学方法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中的必要性和适度性。
一
《智慧》中存在论和神学的关系
作为耶格尔的学生,陈康对其创立的发生学方法推崇备至。在自己的代表作《智慧》一书中,陈康用这一方法重新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思路进行论证。该书的主旨在于回答传统注释中那个著名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主题究竟是神学还是存在论。他接受耶格尔(参见耶格尔,第185页)和罗斯(W.D.Ross)(参见罗斯,第31页)在发生学方法指导下的具体观点,即《形而上学》Λ卷是亚里士多德的早期作品,同时更强调《形而上学》核心卷(ZHΘ)是其最成熟的思想。在他看来,支配《智慧》一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所追求的形而上学思想,即智慧(σοφíα),既是对原因进行考察的神学——这是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同时又是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考察——这是一种普遍的存在论,而两者存在矛盾。如果说以上看法尚与传统看法具有一致性的话,那么陈康的结论则极具特色:亚里士多德全部形而上学思想的追求都是在化解这一矛盾,并且在多次的尝试之后以失败告终。
在陈康看来,亚里士多德从《欧德谟斯篇》《劝勉篇》《论哲学》等著作开始就注重后来被称作“智慧”问题的考察,而这些著作都还有柏拉图哲学影响的残余。他认为《欧德谟斯篇》最早,“智慧”在这一著作中还是柏拉图的“相”论②,而相与努斯等同。《劝勉篇》中所谓的“哲学家的科学”也是“相论”。相比而言,他认为《论哲学》比《劝勉篇》更接近《形而上学》A卷。在《论哲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并不等同于柏拉图《斐多》《理想国》中的“相论”,而是追随《蒂迈欧》《法篇》中的“相论”,即神学。在《形而上学》A1-3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所追求的智慧就是最初的原因,即原因论。这一原因论后来发展为神学,是一种特殊的知识。
陈康对《形而上学》K卷的看法与现代研究者完全不同。现代研究者认为这一卷是学生笔记,而陈康认为是K卷首先提出一系列疑难问题(现代研究者一般认为B卷才是疑难问题卷),并且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最终导致了存在论的建立(在K2,这是存在论的最初形式),即提出它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是Γ2提出了这一观点,并强调了特殊的神学和普遍的存在论之间的矛盾)。陈康与众不同地突出强调了K卷的重要性,认为是K卷造成了智慧既是特殊的神学又是普遍的存在论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在AK卷提出这些相互矛盾的问题之后,马上开始修正存在论,以与智慧是神学的观点相协调:M10和Λ卷就开始修正;而B卷后于K卷,是对后者的疑难问题的一种修订;Γ2是对存在论的修正,Γ3和E1试图统一二者以修正二者的关系。他还认为,亚里士多德调和二者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形而上学》各卷内,也体现在其他多部著作中。总之,陈康对《形而上学》各卷的创作顺序有一个发生学的观点,认为各卷的创作顺序大致是:A;K1-8,1065 a26;M9,1086a21-N;Λ;BΓE 1(E 1=K7);M 10;ZHΘ。(参见Chen,1976,p.93)
在陈康看来,实体是首要的存在,也就是无条件的存在。因此,存在论可以被还原为实体论,或者说存在论与实体论是同一的,对存在的讨论于是转变为对实体的讨论。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后分析篇》《物理学》和《形而上学》Λ卷中提出个别的实体论是被修订的存在论的基础。陈康认为个别实体论有三种形式:逻辑的,即谓述的终极主词是个别的,这一形式在《范畴篇》《后分析篇》中得以表述;形而上学的,即存在的终极主体是个别的,这一形式在《范畴篇》得以表述;原因论的,即形式、质料等原因是实体,这一形式在《物理学》第Ⅱ卷和Ⅷ卷以及《形而上学》Λ卷得以表述。在陈康看来,《范畴篇》中的个别实体论的逻辑形式是柏拉图的相论和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的中间阶段,《后分析篇》中的个别实体论的逻辑形式是《范畴篇》中同一实体论的未完成形式的进一步发展。而《形而上学》Λ卷一方面是《范畴篇》和《物理学》第I卷之间的一环,另一方面也是《范畴篇》和《形而上学》核心卷之间的一环。
陈康认为,逻辑的、形而上学的、原因论的个别实体论,在达到顶峰(即达到不动的动者或神的概念之中的原因论的个体论)的同时,也崩溃了,因为相、质料和个别事物都是个别实体,是一种三重实体。根据组成成分优先于复合物的原则,这些结合在一起时就造成了个别实体论的崩溃。因此,亚里士多德转向对本质的实体论的讨论,进行了新的尝试,在ZH卷提出本质的实体论是存在论和原因论统一的结果。在他看来,本质就是种,同时也是相。而本质究竟是种还是相,视它与不同事物的关系而定。如果它是在与属的关系之中,它就是种差,也就是种;而在与质料的关系中,因为后者是潜在地或现实地具有相,它就是相。这样种和相就是在不同关系之中的同一本质。当现实的中心不再在个别事物即“这一个”之中,而在本质即“是什么”之中时,个别的实体论就发展为本质的实体论。Z卷的其余章节在三个方向上发展了后者,即作为种的本质如何是一个统一体,作为相的本质如何与质料一起构成具体实体,与本质相关的属或普遍物如何不是实体,并由此详细讨论了Z卷各章的主要内容,如本质、定义的部分、定义对象的统一性等问题。
在《智慧》的结论部分,陈康认为亚里士多德调和存在论和神学的种种企图都失败了,因为智慧的主题由永恒、首要的本原组成,是独立自存的,“存在”不是其主题,分离的“神”才是,所以排除了存在论;但是,知识是普遍的,而普遍者不是实体,所以科学对象不是实体,因此智慧也不是神学。这就是存在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中的内在矛盾,在他看来,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有证据同时支持和反对这两种形而上学。陈康最终的结论是:亚里士多德所追求的形而上学的主题“智慧”既非存在论,也非神学,更非统一的科学。他认为这一结论是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Ⅵ卷得出。
二
存在论和神学的关系评述
本文无法关于陈康所给出的《形而上学》各卷以及各著作之间的发生学顺序进行详细评述,只打算讨论陈康对Λ卷和核心卷(ZHΘ)的顺序设定是否合理。陈康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问题上有一个贯穿所有著作、延续一生的矛盾为他《智慧》一书立论的根本,并以亚里士多德最后的失败为结论,然后运用发生学方法展示了亚里士多德对这些矛盾的处理过程。然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是否真的有如此大的矛盾,以至于他努力一生都没有解决,最终造成了体系的崩溃?发生学是否可以用来解释这些矛盾?我们知道,耶格尔在1923年出版他的发生学著作之后,在对罗斯、陈康等多位学者造成深刻影响的同时,就有多位学者对这一方法提出了质疑。如彻尼斯(H.Cherniss)在1935年即认为:“即使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真实作品的每一行的写作时间,我们也应该将它看作一个统一体。因为亚里士多德自己保留了早期和晚期的论述,并将后来的笔记放进早期作品中。我们必须认为,他留下的著作在他自己心目中是一个统一的体系。”(转引自耶格尔,“译者序”第14页)而且,陈康于20世纪60年代完成《智慧》时,发生学方法已经受到西方学者的严重质疑,学者们更多地是系统看待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可以说,陈康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坚持发生学方法,可谓独树一帜。时至今日,系统论依然占统治地位。不过,在当代的研究中,尽管多数学者忽视发生学方法,发生学不仅依然被许多学者用作阐释中的最后选择,一些传统的结论也依然支配着研究者的思想。不过,在讨论发生学方法的适用性之前,让我们先分析陈康的观点。
首先,陈康接受传统解释,并预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存在会最终造成体系崩溃的大矛盾,即所谓普遍的存在论和特殊的神学之间的矛盾。然而,他所理解的存在论的普遍性仍然是传统解释中所理解的,是知识的普遍性。如他所说:“这门科学是一门普遍的而非特殊的科学:普遍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其对象谓述每一事物,并在每一范畴中找得到。”(参见Chen,1976,p.66)“存在论是一门普遍的科学,因为其对象是最普遍的,存在谓述每一事物。”(参见同上,p.73)而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论述“作为存在的存在”,是把它区分为十个范畴而展开的,其中实体是首要的范畴,而且是个别的,是终极主体,就是不谓述任何一个其他事物的东西。因此,“存在谓述每一事物”的说法是不符合亚里士多德原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个别实体论是存在论的基础,也是不确切的。进一步而言,固然在《形而上学》Z卷中亚里士多德在强调形式是个别的第一实体的同时肯定形式是普遍定义的对象。但结合《范畴篇》和《形而上学》Z卷更多文本可知,他对于种属这样谓述个别事物的普遍概念是有明确定位的,肯定它们并非存在论上的实体,而是知识论上的概念。实际上,存在论与知识论在论证中不被区分,或许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那个时代的特征或论证习惯,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四线段学说就同时是存在学说和知识论。如果我们从存在论和知识论、实体和定义的角度分别思考,或许个别和普遍的矛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Z卷的文本而言,亚里士多德强调存在和实体是个别的,而定义和知识是普遍的。尽管就本质而言,它似乎争议大一些,但它终究是定义的对象,更属于后者而非前者。而陈康把相、种与本质概念等同起来,并认为它们在与质料或属的关系之中得以区分,这也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Z卷的说法相矛盾,实际上反而使这些概念更模糊了。毕竟,种属这些类概念是知识论领域的,而形式和质料是存在论领域的。更进一步,在Λ1-5,亚里士多德又把个别实体的个别本原类比到所有的范畴,从而形式、质料、缺失、动力因等成了普遍的万物本原,在存在的领域里实现了普遍化,并不是存在作为谓述的普遍。
其次,陈康在书中也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不同于个别神学的个别实体论,还进一步区分了三个种类,即逻辑的、形而上学的、原因论的个别实体论。而令人疑惑的是,他简单地认为实体论是存在论的基础,却似乎忽视了他本人所强调的存在的普遍性和实体的个别性之间的矛盾,他也没有把个别的实体论与个别的神学联系起来。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把神学的对象作为没有质料的实体来看待,认为它是与核心卷所讨论的可生灭的质形复合实体并列的永恒不动的实体,并在《形而上学》Λ1-5明确了这一点:“实体有三类,一类是可感的——其中一种是永恒的,另一种是可消亡的,所有人都同意,如植物和动物……另一类是不动的,而且有人说它们是分离的……于是,那些[实体]是自然的(因为伴随着运动),这一类是另一种……”(《形而上学》,1069a30-b2)我们知道核心卷以及Λ1-5讨论的就是可感、运动的动植物这样的质形复合实体,而他在Λ8讨论永恒运动的天体,在Λ6-7和Λ9-10讨论分离、不动、永恒的、没有质料的最高实体神,由它保证整个宇宙的秩序。可见,《形而上学》Λ卷未尝没有对核心卷讨论的存在论和神学的关联作出合理的解释,虽然亚里士多德对神学的描述与他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描述在篇幅上不成比例。
Λ卷在传统上一直被称为神学卷,因为大家普遍重视Λ6-10的内容,包括陈康在内的发生学支持者更是把该卷看作早期著作,或者说,正是Λ卷是早期而非晚期的这一设定误导了研究者,使他们忽视了这一卷,尤其是前半卷在实体问题上的重要意义。现在有学者提出这一卷是亚里士多德的晚期著作③,笔者也认可这一看法。在笔者看来,不仅Λ8所讨论的天文学思想属于其生命晚期,Λ1-5对一些重要思想的论证也有总结的意味,Λ6-7和Λ9-10更是给出了成熟的神学思想。而陈康首先预设了神学思想是最早的,是与柏拉图思想关系最密切的。对此我们质疑的是,神学难道不可以是一直在亚里士多德心中、不时地给出零星的说明,并最终在Λ卷给出了虽然简单但完整的论证的思想主题吗?在笔者看来,对作为原因论的神学和普遍的存在论的区分,在亚里士多德文本中的张力并不如《智慧》所强调的那么明显。而且原因论并不必然导致神学,如《形而上学》Z17说形式是质形复合物的原因,实际上存在论的核心实体论所讨论的形式、质料等就是原因。亚里士多德整个形而上学讨论的就是作为原因、本原和元素的形式、质料等,以及对它们的描述。前者是存在论,后者是知识论。陈康“普遍的本质实体论是个别实体论的发展”的看法,或许混淆了实体本身并列的不同含义——作为定义对象的本质和作为存在论上这一个的形式、质料与复合物。前一种意义的本质实体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对“是什么”和定义的追求继承而来的,如上文所言,终究是知识论概念。尽管在后世有“种形式”“样式”等究竟属于存在还是知识的争议,但把这个问题看作个别实体论的发展,就把问题简单化了。
最后,《形而上学》Λ卷是早期著作这一传统设定,或许也误导了研究者对存在论和神学、实体理论与万物本原学说关系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亚里士多德对类比概念的重视,同时也忽视了亚里士多德类比概念在沟通个别性和普遍性上的重要意义。如前文简单提及的,除了所说的知识论上类的普遍性,亚里士多德在Λ1-5还给出了一种类比意义上的普遍性:实体是存在的首要范畴,其他九个范畴都类比于实体而得到阐释(实际上Z卷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论证实体与存在的关系的,虽然没有提到“类比”一词);而形式、质料、缺失和动力因也在类比意义上是万物本原,它们也未尝不是普遍的。而且,基于对质形复合物的详细描述,最高的实体努斯/神才得到解释。换言之,后者也是在与前者类比的意义上得到阐释的。因此,在我们看来,存在论和神学并没有竞争“智慧”的主要内容,相反,神学是存在论的一个部分,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实体理论的一个部分。因此可以说,阿弗洛狄西亚的亚历山大、邓·司各脱和威廉·奥卡姆等学者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参见汪子嵩等,第680—681页)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视野从《形而上学》以上诸卷扩展到ΓEK卷的相关内容就可知,亚里士多德并不含糊地宣称,第一哲学(亦即智慧)不仅包括神学,也包括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说。如他在E1,1026a29—32所说的:“如果存在着某种不动的实体,[研究这种实体的科学]就是在先的,就是第一哲学,并且以首要的方式而是普遍的,而且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是什么,以及依存于作为存在的事物的思考都属于它。”甚至,如他在K7,1064a29所强调的,神学就是存在论,只是其对象分离而已。顺便说一句,从K卷对ABΓE卷相关第一哲学主题及其与《物理学》有关的内容进行了逻辑更为严谨、更为深入的表达看,陈康认为K卷早于BΓE卷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当然,说它是学生笔记也不确切)。相反,作为ZHΘ卷和ΛMN卷两组内容的过渡,已经在暗示后一组文本要讨论的非可感实体问题,这与它目前所处的位置是相符的,创作时间也不会太早。
说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相互矛盾的理论,然后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矛盾,最后又以失败告终,似乎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追求解释得过于悲情了。而如果我们把他的理论追求过程理解为从概念或理论的模糊到越来越清晰的过程,可能更符合他的文本特征。抑或如柏拉图哲学一样,前后有发展,有些许抵牾,却没有大的矛盾,不失为一个系统性整体。
三
发生学方法评述
我们固然不能过分强调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矛盾和发生学的重要性,但如果像当代的研究中过于忽视发生学方法的话,一些文本也是无法获得令人信服的阐释的。鉴于二人哲学的深刻渊源,哪些思想是从柏拉图那里传承而来的,亚里士多德本人是如何发展的,是研究者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吸收和发展,也不应该被认为是一蹴而就的。一旦我们深入亚里士多德哲学文本之中,就能体会到,不同著作中的相同概念有不同的指涉,内涵和外延都有些差异,且有些地方模糊,有些地方精确,即使不一定前后矛盾,但创作有先后、关注或思考的问题重心有所不同是正常的。因此说他的思想是逐步成熟起来的应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陈康的一些具体观点或可商榷,但完全否定发生学方法则是另一种偏颇。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形而上学》核心卷并非亚里士多德最成熟的思想,而是亚里士多德在多个阶段的思考结晶,Λ卷反而可能是其最成熟的思想。
如陈康认为亚里士多德的εïδοζ自始自终都是柏拉图的εïδοζ,都是种,这一看法固然值得商榷,但它是有《形而上学》Z8的文本支持的。④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肯定了同一种下个别事物的εïδοζ是相同的,彼此的不同只是由于各自质料的不同,因εïδοζ此εïδοζ就是柏拉图那里的相,就是种,是普遍的。历史上著名的“质料的个别性原则”就来自这里。我们经常忽视的还有,不仅Z7-9所呈现的εïδοζ可以等同于柏拉图的理念,是种概念,只是它与个别的质料不分离,而且Z10-11的主要文本⑤所呈现的也是一种普遍的形式或普遍的种。这两种εïδοζ都并非在Z卷多处所强调的作为第一实体的个别的形式。而在Z10-11的个别说法和H卷中,明确种属这样的类概念就是普遍的质形复合物。当然,关于同一种下个别事物的形式不同,更有说服力的文本在《形而上学》Λ卷:“在同一种中事物的那些原因是不同的,不是在种上不同,而是在不同个别事物原因是不同的意义上,你的质料、形式和运动者不同于我的,但它们在普遍描述上是相同的。”(《形而上学》,1071a27-29)这样,至少在Z7-9、Z10-11和Λ卷之间,有很明显的发展关系,Z卷中的εïδοζ就有等同于理念的形式、个别的形式、普遍的形式、普遍的质形复合物等多个内涵。而在笔者看来,这些区别反映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不同阶段,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发生学方法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进一步猜测,不仅在εïδοζ理论上亚里士多德是在长期的思考中逐步发展柏拉图的相关理论的,极有可能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理论也是逐步发展而来的。试想,如果他在Z7-9创作阶段或Z10-11的主体部分的创作阶段已经明确个别的人有个别的灵魂,作为种的人是普遍的灵魂和躯体的复合物,而且如Λ5一样明确同一种下的个别事物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具有同一描述,那么Z卷的传统争议或许根本不会出现。当然,还可以证明有其他文本晚于Z卷。如《范畴篇》较之Z13-16对种属是第二实体的明确定位,再如《论灵魂》较之ZH卷对质形复合定义的直接应用等。总之,在笔者看来,如果说逻辑学著作因最接近柏拉图的后期对话而是亚里士多德较早著作的话,《形而上学》Z卷恐怕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思想成熟阶段的文本。相反,这一卷的晦涩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在亚里士多德既在他自己的哲学立场上讨论实体,又在柏拉图的哲学立场上讨论定义,既有对柏拉图哲学的继承,又显示出要突破的痕迹,更多地似乎在与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对话,而非表达自己最成熟的思想。毕竟,根据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方法论,他要证明第一实体是εïδοζ,必然会先批判柏拉图的εïδοζ。当代研究者坚持以系统论方法研究Z卷,事实上也无法合理解释其中的一些抵牾,阐释总是不透彻的。因此,适当引入发生学方法是必要的,当然要适度。
其实对于我们在上文提到的普遍的质形复合物概念,陈康也有不同理解,他用的专门术语是“普遍的复合物”。他不仅在其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参见Chen,1940)中,还在几篇论文中讨论过它。在笔者看来,陈康慧眼识珠,其观点虽有争议,却值得我们单独探讨,因为这一概念是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概念最具创造性的发展。如上文提到的他对《形而上学》Z8观点的重视,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只是把柏拉图的‘相’改头换面,放进可感事物之中,却根本没有放弃它”(参见陈康,第387页),从而认为它是一种实在。因此,在陈康看来,亚里士多德的种属不是普遍的质形复合物,种就是柏拉图的相,比如个别的人就是相和个别的当前质料构成的复合物,而普遍的人就是相和普遍的质料构成的,从而认为个别的复合物和普遍的复合物是双重的实在,而且会造成亚里士多德的属一种一个体的原有体系的崩溃。不过,令人诧异的是,陈康同时也很重视《形而上学》Z10,1035b27-30⑥和Z11,1037a5-7⑦两段文字。但这些文本告诉我们,普遍的复合物并非陈康所说的由相和普遍的质料复合而成,而是普遍地看待个别的形式和质料而形成的。看起来,陈康受传统观点——形式是普遍的,就是种,而质料是个别的——的影响太深,过于强调两人观点的一致性,可能缺少知识论的维度。
那么,亚里士多德的种概念是否就是柏拉图的相呢?普遍的质料是否存在呢?在笔者看来,以上两段文字已经明确,亚里士多德的种概念是普遍地看待个别形式和质料而构成的概念,并非实体,而陈康那里的柏拉图的相是一种实在。或者说,种概念中已经包含有质料而相没有,因此,认为相进入个别或普遍的质料构成复合物,是不确切的。当然,柏拉图那里ïδοζ本来就是多重意义的,既是存在论的,又是知识论的,甚至,柏拉图本人在《泰阿泰德》中已经明确由元素和贯通它们的路径(διεξ/οδοζôδóζ)构成的“可知的复合物(σνλλαβη)”,同时也明确个别事物如人的集合就是种/类概念(ïδοζ)。⑧不过,柏拉图的“可知的复合物”却没有被进一步区分究竟是普遍的类,还是个别事物,比如柏拉图说到苏格拉底和泰阿泰德的希腊语全名是可知的,而单个的字母则不可知。但后来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明确,形式使质料成为个别事物,并称元素为质料,那么贯通元素的路径在他这里就是形式;他还认为可知的不是个别事物,而是普遍的类,即普遍的质形复合物。甚至,如《形而上学》Z10-11所呈现的,质料也有从可感、可生灭的到可思、普遍的发展,前者就个别事物而言,后者就数学对象和描述中的质料而言。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明确了柏拉图的“可知的复合物”就是普遍的质形复合物,就是种属概念。陈康把相放入质料之中的理解方式,是对二人的双重误解。总之,陈康忽视了这一概念的知识论维度,也没有把发生学彻底贯彻下去,而在笔者看来,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ïδοζ概念的丰富和发展或许更符合发生学的观点。
实际上,陈康也承认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H卷中对普遍的复合物概念进行了肯定,并认为属加种差和质形复合定义是两种不同的定义方式,但我们在前文也提到,他更多时候统一这些关系。或许在定义问题上,陈康也没有把发生学方法贯彻到底。而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对定义的对象,还是对定义方式的讨论,亚里士多德一定经过艰苦的探索,体现出鲜明的发生学特征:就质形复合定义的对象而言,虽然都是种,都是对本质的描述,但种的指涉从单纯等同于理念的类概念种,到形式与种的等同,到普遍的形式与种关系的模糊,再到普遍的质形复合物等同于种,其思想是有些变化的。
当然,对于我们以上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或许有人会提出异议。我们要强调的是,亚里士多德那么庞大的哲学体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文本也告诉我们他或许在某个阶段专注于某个问题,在另一个阶段专注于另一个问题,但这并不必然造成大的矛盾,不过是有一点抵牾罢了,他的哲学体系仍然是一个统一体。运用系统论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整体,但在一些具体文本、具体问题上辅之以适度的发生学方法,也许是更审慎、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研究方式。那么,从方法论意义上讲,陈康对发生学方法的坚持反而表现出他卓尔不群的见识。
结论
陈康在传统思想和耶格尔方法论的深刻影响之下进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阐释,并因为对柏拉图哲学的热爱而更强调两个哲学体系的相关之处。虽然有一些观点或可商榷,但他深刻的洞见和广博的问题意识却是不容忽视的。如上所述,即使在我们批评颇多的普遍的存在论学说中,陈康仍然把握住了亚里士多德个别的实体论学说,即使在我们看来他对“普遍的复合物”的看法或可商榷,却必须承认陈康对它的重视本身所体现出的思想的敏锐。在有关“原始质料”这一概念的讨论中,陈康的思想也颇为独特,既像传统解释那样将其看作所有变化中不变的基础,又认为它不与四元素分离,总是潜在地存在,现实中表现为某一种元素。这样,把四元素与最初质料相等同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陈康还有很多类似的观点,既给我们提供了极富洞见的理解方式,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因此他至今仍是值得讨论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最好的阐释者之一。
注释:
①本文所引《形而上学》文本,均由笔者翻译自耶格尔(W.Jaeger)编辑本。(参见Jaeger)
②陈康一直坚持二人的εïδοζ没有不同,应该翻译为“相”,但本文中笔者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分别翻译为“理念”“种”和“形式”“种”。
③伯恩耶特(M.Burnyeat)在第10届亚里士多德学会的一个口头陈述中提出,Λ卷是亚里士多德的晚期著作。(参见聂敏里选译,第356页)
④《形而上学》Z8,1034a2-8:“没有必要把理念(ïδοζ)当作模型来使用……而生成者具有充分的制作能力,使形式因(ïδουζαïτιον)存在于质料之中。而当我们有了整体,这样的形式(ïδοζ)在这些肉和这些骨头之中,[这就是]卡里亚斯和苏格拉底;[他们]因为[他们的]质料而相异(因为[质料]是相异的),但在形式上(εïδοζ)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种[ïδοζ]是不可分的)。”
⑤《形而上学》Z10,1035b33-1036a1:“但是描述的部分只是形式的部分,而描述是属于普遍者的。”Z11,1036a28-29:“因为定义是关于普遍者和种的。”
⑥“人和马以及这样被应用到个别事物之上的东西,是普遍的,不是实体,而是来自作为普遍者的这个逻各斯和这个质料的某种复合物。”
⑦“很清楚,灵魂是第一实体,而躯体是质料,人或动物是由作为普遍者的这二者构成的。”
⑧术语译自希腊文本(参见Duke,et al.),同时参考了詹文杰的中译本(参见柏拉图)。
参考文献:
[1]柏拉图,2015年:《泰阿泰德》,詹文杰译,商务印书馆。
[2]陈康,2011年:《陈康:论希腊哲学》,汪子嵩、王太庆编,商务印书馆。
[3]罗斯,2017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导论》,徐开来译,溥林校,商务印书馆。
[4]聂敏里选译,2010年:《20世纪亚里士多德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汪子嵩等,2003年:《希腊哲学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6]耶格尔,2013年:《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朱清华译,人民出版社。
[7]Chen,Chung-Hwan(陈康),1940,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Inaugural-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Docktorgrades,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zu Berlin.
[8]1976,Sophia,The Science Aritotle Sought,New York:Georg Olms Verlag Hildesheim.
[9]Duke,E.A.,Hicken,W.F.,Nicoll,W.S.M.,Robinson,D.B.,and Strachan,J.C.G.,1995,Platonis Opera,Vol.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Jaeger,W.,1957,Aristotelis Metaphysic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原标题:《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主题争议与发生学》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赛事经济火爆春日
- 中央网信办:增强网络执法震慑
- 瑞丽62所学校完成安全隐患排查

- 多只稀土ETF跌超3%
- 创业板指跌破2100点

- 上海市举办F1的赛车场
- 由海尔集团投资制作的国产动画片,主角是一对不同肤色的兄弟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