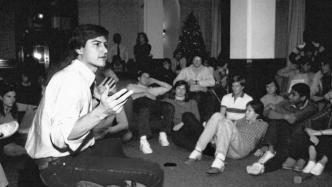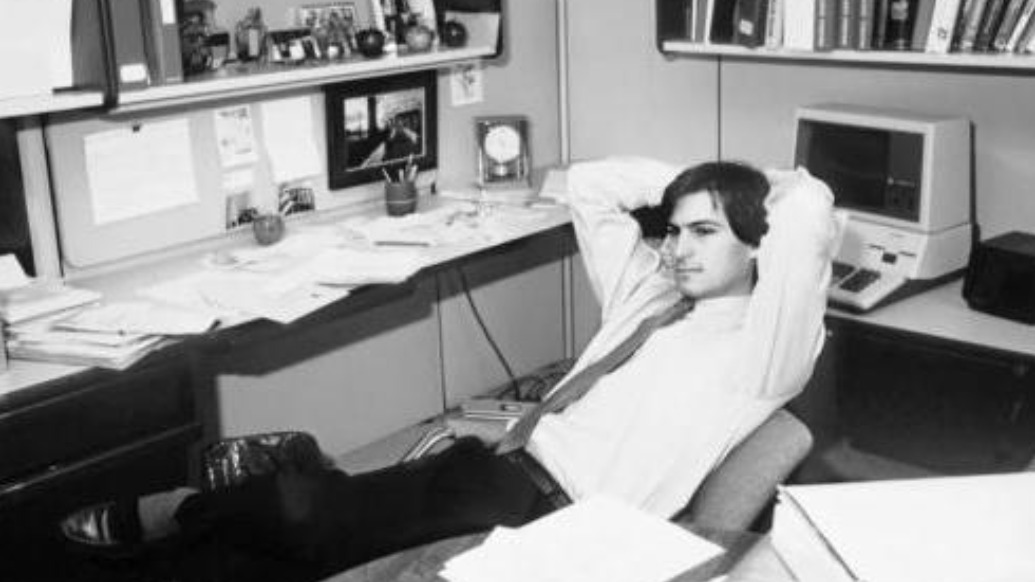- 175
- +1
肖一之:文学播客是赛博空间里燃起的一堆篝火|播客时代的文学波纹
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中文播客呈爆炸式增长。播客逐渐打破小圈层,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据统计,中国播客听众规模在2023年已达1.17亿。《JustPod2024中文播客新观察》显示,至2024年6月30日,中文播客总数已达4.2万档,年增长率约为25.5%。不同于短视频高强度、快节奏的刺激娱乐,以听觉为主导的播客是“慢媒介”,吸引着偏爱长内容,有好奇心和耐心的用户。人们在声音的内容海洋里,主动寻找着打破信息差、拓展边界的可能。

文学与播客的合体,让“收听”成为一种可以被培养的文学行为,也改变着人们接通文学的方式。有温度、有呼吸感和陪伴感的长谈,正是播客的优势所在。节目主播们以声音搭建起流动的文学地图,提供不同的阅读谱系、精神趣味与知识构成。所以,文学播客不仅关乎创作与故事的媒介转化,更关乎“文学中的人”与文学交流阵地的更新互见。
本期邀请于是、张怡微、肖一之、杨毅作为文学播客的观察员。他们是播客的内容生产者与收听用户,其中于是、肖一之曾是“跳岛FM”的常驻主播。他们从多元的参与者视角出发分享了各自的经验与思考,记录下播客时代不同的文学波纹。和一切新媒介一样,播客一边改变着当代人的文学生活,一边也再次让我们思考,什么是文学的本质?它的生命力从何而来?
—— 主持人:刘欣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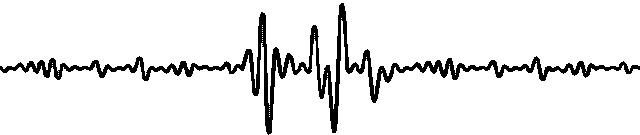

虚空击掌,不亦快哉
文 / 肖一之
其实我不怎么听播客。备课教课之余,我更倾向于让生活在认真和摆烂之间两极震荡。认真的时候,正襟危坐,逐字琢磨,但有所得立时记好笔记,留待未来参考。摆烂的时候,四仰八叉,逐浪网络,只求大脑彻底放空,全无所得便是得。幸好还可以不脸红地说认真多过摆烂,但那不是因为我天性向学,纯粹是因为上班之余能用来工作的时间已是无多,经不起天天摆烂而已。正是因为连读书的时间都要靠挤,但凡道德自律感还能鞭打大脑继续工作,我的首选信息输入媒介还是书籍。毕竟,就单位时间内可以获得的信息密度而言,质量再高的播客也难敌书籍。信息密度不如书籍,放松程度不及摆烂,播客在我的生活里也就只能不尴不尬地在旮旯时间里找到上场的机会。
晨起准备早饭的时候,不妨点开播客。洗碗扫地的时候,不妨点开播客。地铁上仅占得立锥之地的时候,当然只能点开播客。播客于我更多是阅读的替代,是翻不开书却又不甘心彻底摆烂之时的精神安慰剂。套用播客圈的“黑话”,这大概就是播客的“陪伴作用”。可惜我还要坦白一件事,哪怕到了只能靠听的时候,在注意力争夺战里播客节目也未必能拔得头筹。其实我更喜欢听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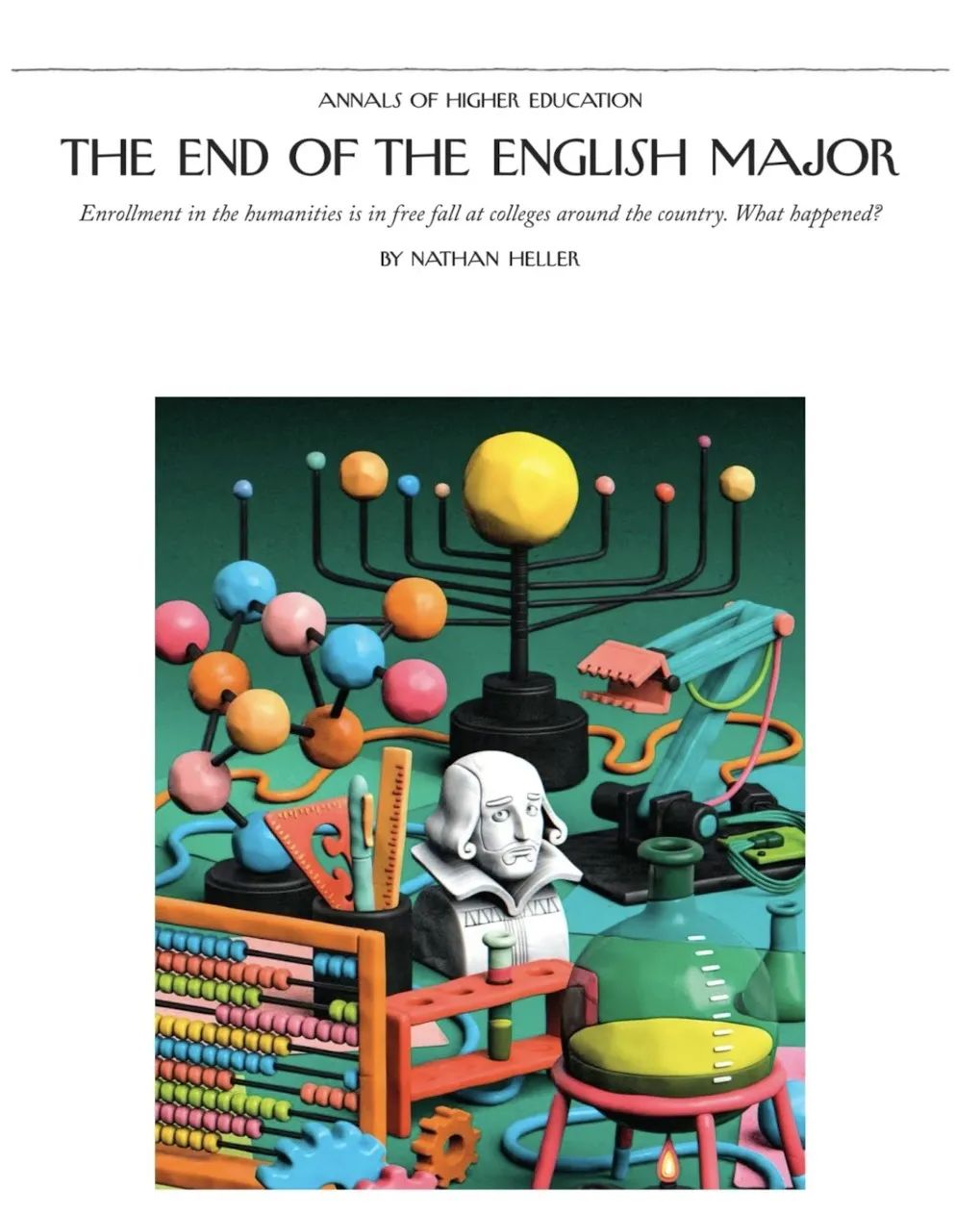
▲ 《纽约客》文章《英语专业的终结》
人人都知道,手机就是我们时代的烂柯棋局,一拿一放之间,光阴打马而过。2023年《纽约客》杂志刊出过一篇大热的报道,讨论了美国英语专业的大溃败,报道采访了莎士比亚学者詹姆斯·夏皮罗,而夏皮罗找到的英语专业不再诱人的原因之一正是手机。曾经一个月可以读五本小说的夏皮罗,在拥有了智能手机一年之后,一个月能读一本小说就算多了。这不是因为他对文学失去了兴趣,而是“因为我要浏览上百个网站。我要听播客”。夏皮罗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自从手机变得智能,不再只是打电话发短信的通讯设备,而是长在我们身上的互联网义肢之后,我们其实就已经生活在了新的媒介环境里。在这个新时代里,注意力是最为稀缺的资源——粘着度也好,完播率也罢,甚至app开屏一定请你先看广告,这林林总总的概念和把戏算计的无非都是我们的注意力——在短视频、直播和游戏面前,播客甚至都排不上号。就此看来,在智能手机的年代,文学遇到播客其实更像个抱团取暖的故事。
但是我喜欢录制文学播客。我和播客的缘起纯属偶然,最初是在几位豆瓣友邻的介绍下,我误打误撞地参与了最早几期“忽左忽右”的录制。此后又在另一位豆瓣友邻邀请下加入了“跳岛FM”成了常驻主播,偶尔也去其他节目串个台,比如到“痴人之爱”或者“惊奇电台”为喜欢的作家摇旗呐喊。这一切少不了有虚荣心作祟,但更多却只是因为乐在其中。准备播客节目,让我可以从日常里切出一两个小时,和同好一起当一个纯粹的文学青年。和新媒体时代的所有创作一样,文学播客的基底也是这个时代喷薄的表达欲,可表达欲不同样正是文学赖以相传的源动力之一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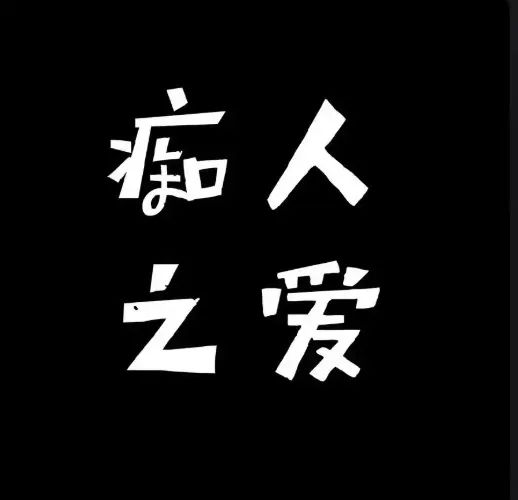

印刷时代的写作是将自身的生活体验转化成文字,再将其投诸世界,期待会心之人纸上寻踪,文字和读者的生活经验互相砥砺,研磨出最亮的镜面照耀生活的幽微之处。但这不是文学阅读的尽头。文学传统之所以存在,依赖的还是代代读者持续不断地阅读,由文字而生感触,接下来或形诸文字,或口口相传,把触动自己的文字传向世间。在播客时代,“我手写我口”已经不够直抒胸臆了,声波传达的是“我口述我口”的干脆利落。在播客里讨论文学,期待的就是凭着一腔热情打动未知之人,制造文学的链式反应。也许1000个听众里只有1个人会因为听到了一期播客节目而打开一本书。但是一条新的文学链条可能就是从这个人开始生长出去,文学作品的生命也就此得以延续。我很喜欢“跳岛FM”的一句口号,“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阅读就是这样,一旦开始文学之旅,面前有的就是走不完的路,看不完的景,一本书从来只是下一本书的序章而非旅程的尽头。不过这句话其实后面还有一句,“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文学史是书的传统,更是一个个由文学作品所串联的人。

▲ 播客线下活动品牌PodFestChina海报
大抵在讨论文学和媒介的时候,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播客也罢,有声书也好,再加越来越便利的电子书,越来越复杂的游戏叙事,文学在新时代的转生形式越多越好。需要打气的时候,我会回忆进化生物学家们提出的假说,安慰自己说,只要有人就会有文学。假定有两个生活环境类似,数目相当,技术水平等同的智人部落。甲部落每日早出晚归狩猎收集,晚上聚众而食,饭后早早休息,以保证明日有充沛的体力。乙部落和甲部落的日程几乎一致,唯有一点不同,他们在饭后不会马上睡觉,而是浪费时间围坐在篝火旁听长者讲故事,良久才恋恋不舍地睡去。假如生存竞争真的只秉持有用这一条冰冷的法则,那么吃饭就是为了饱肚,睡觉就是为了休息,甲部落按理说应该是进化的胜出者,因为他们明显把有限的生命都投入了做有用之事的大业中。但是我们知道,结果不是这样。我们都是乙部落的孩子,在我们的基因里都刻着对故事的渴望。讲一个故事的开头,激荡的血脉会催动我们问出那个最古老的文学问题:“然后呢?”也许未来文学会彻底抛弃文字的形式,但是故事永存,文学永存。
由此看来,文学播客其实也是种复古活动,在1和0搭建的赛博空间里燃起一堆篝火,二三素心人侃侃而谈,每一道声波都是伸向虚空的手掌,等待着另一个人在不知何处伸出手来击掌回应。虚空击掌,不亦快哉。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活动资料、摄图网

原标题:《肖一之:文学播客是赛博空间里燃起的一堆篝火|播客时代的文学波纹》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30℃要来了?
- 外交部:美打压我半导体产业损人害己
- 2024年550余起拐卖案被侦破

- 毕马威:一季度中国经济持续修复,今年货币与财政配合将更为积极
- 阿里万相视频生成模型开源,能在消费级显卡运行

- 指每年的三月和四月,是求职和招聘的黄金时期
- 中国导演霍猛在2025年第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的奖项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