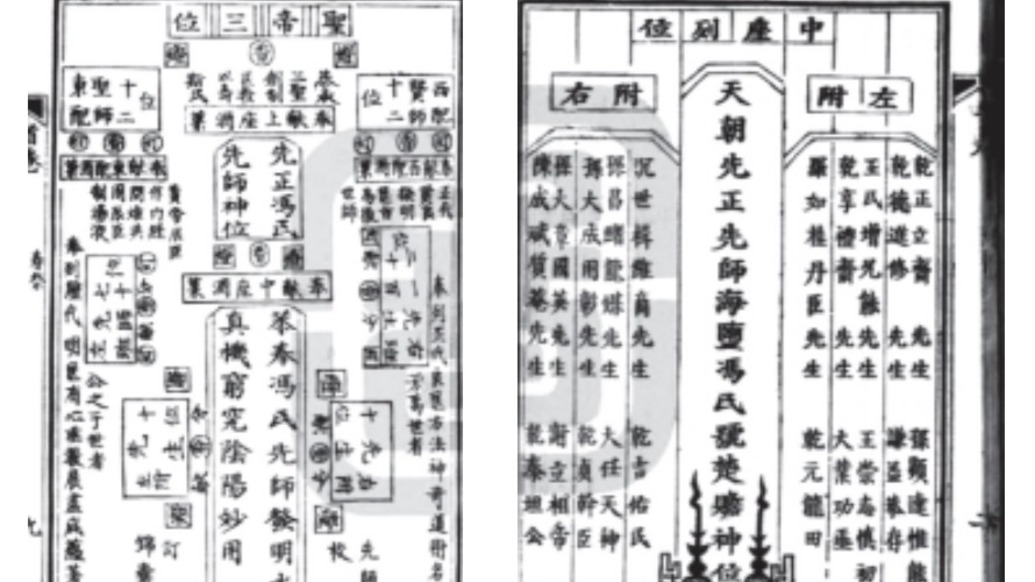- 3
- +142
苏区研究︱石岩:苏联“共产公妻”的谣言是如何产生的?
“妇女国有”
1918年的夏天,美国和欧洲各大报纸上纷纷出现这样的头条:“禁止组建家庭,布尔什维克公妻”“苏维埃实行群婚”“社会主义令卖淫合法化”。这些说法很快就被指为谣言。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辟谣:“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辗转讹传,人又给他们加上了。”
继李大钊之后,刊登于1920年第8卷第6号的《新青年》上的《劳民俄国底婚姻制度》再次辟谣。此文由日人山川菊荣撰写、李达译。山川菊荣考证说:“妇女国有”的消息最初出自美国人阿里夫塞拉的《劳农视察记》。阿氏记录了伏尔加河畔小城萨拉特夫的无政府主义者发布的“妇女国有”的布告,后被以讹传讹,将“妇女国有”归于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

这一传闻的流布极广,中国的报纸也有反应。1918年8月28日《申报》有《俄无政府党之公妻制》一文。从行文看,该文应译自“俄国萨拉土夫(即山川菊荣所谓萨拉特夫)无政府党自由会社妇女国有条例”。报纸的编辑并没有把这则消息太当回事,它没有出现在国际新闻版或要闻版,而是出现在第17版,大标题之前尚有一引题:《四十年后之新世界》,暗示了“妇女国有”是子虚乌有的海外奇谈。
在《劳民俄国底婚姻制度》一文中,山川菊荣援引“巴里特氏”及“普来安女史”的《游俄报告》,驳斥了“妇女国有”的谣言。普来安说:“劳农会通过布告关于婚姻时的集会,我曾出席……这布告采决以前,有一兵士起立,主张政府应限制离婚在三次以下。又有一兵士站起来说,‘我们相信自由,为甚么一定要限定人们结几次婚呢?’讨论于是终止了。最有趣的是,结婚和离婚都与吃一杯茶一样,并无别的道理,可是结婚局和离婚局也并没有应接不暇的模样。”在接下来的篇幅里,山川菊荣转述普来安的观察,介绍了苏俄婚姻法,撮其要者,有以下几项: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期,给妇女以可能的范围内的自由;离婚可由双方同意也可以由一方提出;男女对子女的权利义务平等;禁止重婚,但不制裁奸通和私通;婚生与非婚生子女平等……这些立法精神,被日后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婚姻法》所继承。
从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因俄国革命的成功,本是戏言的“共产公妻”一说,因知识阶层的讨论和苏俄信息的传入,变得越来越真切。“妇女国有”或属子虚乌有,但立法保护离婚自由及非婚生子女权益,不受法律干涉的婚外性关系,在当时以至此后很多年的中国仍属激进之议。与此同时,“共产公妻”的污名渐渐成为达成政治目的之利器。
1920年11月,陈炯明电邀陈独秀赴粤主持教育。初到广东,陈独秀声名甚隆。短短4个月之后,广东高师学生却向省议会提交了驱陈议案,指斥其主张讨父、仇教、公妻、妇女国有。
查同时期的《申报》,陈独秀为粤教育界所不容,似另有原因:“粤人之伦理观念实较强于各省,故办教育者必须道德纯洁,始足起一般社会之信仰”,“谈新文化者必以实学为根底,若无实学则最沦于思想破产而为智识阶级所轻视”。国民党老人黄子凌(黄钺)认为:“陈独秀来粤已及两月,考其成绩不过在报纸上说两句大话”,“以其主义既无彻底之研究,而浮嚣之气已输入于一般青年之脑海,无穷祸害令人悚惧”。就连曾经力促陈独秀来粤的汪精卫也公开说:“今日所谓新文化,注重哲学而不注重科学,专从思想改造未免倚于一偏。须知我国以哲学改造社会已有两次教训:如晋尚清谈、尊老庄,造成一种玄学,卒启五胡十六国之乱;宋人以禅宗参入儒学,造成一种理学,亦不能御女真蒙古之侵入。则今兹之提倡新文化若不于科学注重岂不危险?”
如《申报》所言,陈独秀在广州遭驱除与其激进的主张有关,与保守人士认为他有道德瑕疵有关。对于主张讨父、公妻、妇女国有之说,陈独秀在3月23日接受广州黎明访社记者采访时说:“这些话提起来又好气又好笑,试问父有何可讨?既说是妻不是妓,如何公法?我们虽不主张为人父专把孝的名义来压迫子女,却不反对子女孝父母,更不能说‘孝为万恶之首’。至于‘百行淫为首’,这句话我想除了一班淫虫及讨几个小老婆的大腹买办,不会有这样荒谬的主张。”“又好气又好笑”“荒谬”说明了陈独秀对“公妻”一说的态度。查《新青年》杂志关于妇女问题的系列讨论,陈独秀的几篇文章主要集中于妇女选举权、男女同校、女工等话题。在广东任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陈独秀做过的关于妇女问题的演讲也多属于此类。他虽曾提出“中国妇女解放的要求,不但是精神上的,而且是身体上的”,但“身体解放”针对的是缠足等陋习。陈独秀观点的激进之处在于“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是充实政治革命的内容之一种”。
陈独秀主张“公妻”的谣言一出,不仅陈本人,袁振英、陈公博等,也纷纷在《广州群报》、上海《民国日报》上辟谣。论者认为,1921年9月,陈独秀主动离开广州系因信仰之转变,并非迫于舆论压力。
从陈独秀离粤前后纷纷扰扰的舆论可见“公妻”谣言的“新动向”:与民初政客把“公妻”张冠李戴给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维新派、改良派)不同,到1920年代初,这一污名开始针对具体的人,并且增加了“妇女国有”的新内容。按照传播学的理论,“谣言的力量之一是它的不断重复,人们今天从这听到,明天从那听到,说法不断在变化,添油加醋,去粗取精,越传越像回事”,“谣言和人一样,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也是一种复杂造物的结果,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阐释历史”。“公妻”及其新说“妇女国有”所体现的或正是人们在大变动前夜所特有的“嗅觉”。
大革命时期的“杯水主义”
从“五四”到“五卅”,不过6年,五四青年关于“自由恋爱”的讨论已显落伍。1924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郑超麟把“不闹恋爱”当作对于五四初期“恋爱神圣”观念的一种反动,因为“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
恋爱为何跟小资产阶级挂钩?1920年10月《妇女杂志》一篇名为《性的道德底新倾向》的文章提供了线索。此文作者本间久雄归纳了欧洲“自由离婚派”的观点,将其分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唯物论两大派别:自由派主张“恋爱底自由”,社会主义/唯物论派则主张“自由恋爱”。自由派把恋爱当作目的,主张灵与肉的统一,唯物派偏重“肉”的自由。在唯物青年看来,革命是疾风暴雨,大量的工作有待人做,把时间浪费于罗曼蒂克的卿卿我我,已落伍于时代。蒋光赤就因为跟一个女生通信多年,“两人关系好似恋爱小说里面的”,而被东方大学的同学嘲笑。
如前文所述,“妇女国有”或属子虚乌有,但在1920年代的苏联,“一杯水主义”是确实存在的。1923年,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共福利人民委员、全俄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发表了一篇名为《三代的恋爱》的小说。女主角盖尼娅是坚定的革命者,其情爱观是:“恋爱是非有工夫不可的”,“在这种一切时间都被夺去了的革命时代”,“我们偶然碰到,两个人感到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尊重了这个时间”。当“身上燃起激情时,她决不拒绝生活向她发出的灿烂的微笑……双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当爱的杯盏倒空后,她将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将它扔掉,回到自己的工作中”。“爱的杯盏”大概就是“杯水主义”的由来。
郑超麟们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时候,正是《三代的恋爱》发表之时。现实与小说高度吻合。东方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充满警惕,认为他们身上有很多体现为家庭、乡土、民族观念的旧观念、旧习惯。这些旧习都以感情为纽带,而党要“打破感情的结合”。因此,中共旅莫支部禁绝恋爱,但不禁绝性要求,强调革命者可以有性无爱,且允许相当的性自由。陈碧兰回忆录记录了在1925年举行的一次关于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的主旨是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别开来”,摒弃恋爱至上。陈独秀之子陈乔年在会上发言:革命家的精力、时间有限,“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只有性交”,加上工作流动性强,“工作在哪里,有性的需要时,就在哪里解决,同喝一杯水抽一支香烟一样”。
在苏联,“杯水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容许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柯伦泰的小说成为禁书,但“一杯水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1927年,刘仁静在莫斯科学习时,苏联正风行“一杯水主义”,“许多同学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陆立之1927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秋回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29年我20岁,沉沦在‘一杯水主义’的初恋中……在当时的学校宿舍里,并没有‘家’这个概念。男女间一拍即合,由学校当局提供同居铺位。在大厅堂中安排十几对床位,像船上的统舱一样:两床之间有一小书柜,这是一对野鸳鸯;隔邻的床位用布幕相隔,但生息相通……‘一杯水主义’风行在莫斯科,也很自然地在学校中沿袭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身体力行“杯水主义”的时候,柯伦泰的作品被译介到了中国。1928年,《新女性》刊登了《三代的恋爱》译文,并向读者征集读后感。三个月后,1928年第3卷第12期《新女性》刊出16篇读后感组成的“新恋爱问题”专题讨论。有人认为,“如此种的恋爱中国何尝没有,只不过没有赤裸裸地说出来,造成一个恋爱的概念就是了”。恋爱自由和性爱自由,已不能满足革命青年的需求,有人提出了“性交自由”:“将性交与性爱的必然联署关系打破”,“强制一个人除了爱人之外不跟别人发生性关系,是今日性爱诸种病态之一”,“性爱不必强求只限于一人”。有人主张,“恋爱只是玄学的产物”,而事实上,“恋爱不是神秘的、神圣的、更不是灵的”,“人间的伦理从唯物的历史的解释,皆源于经济的条件”。有人更进一步:“性生活的基础应该从经济制度下脱离开,应该从个人的狭窄范围内脱离开,应该扫除资产阶级所遗存的痕迹,我们应该无产阶级地建立起集团化的性生活。”这些观念与1920年代初的“恋爱自由”有近似之处,但已经走得更远,恋爱本身都已被革命青年视为落伍,恋爱自由在他们看来就更是一个过时命题,必须被“性交自由”所取代。

《新女性》创刊于1926年1月,创办人章锡琛。1912年至1925年,章锡琛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妇女杂志》主编、国文部编辑,并编辑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现代妇女》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刊》。后因主张过于激进,他被商务印书馆辞退。1925年冬天,在郑振铎、胡愈之、吴觉农等人的支持下,章锡琛创办《新女性》杂志社,其办刊初衷之一是“声援五卅”。《新女性》的作者、译者包括陈望道、曹聚仁、顾颉刚、周建人、陈学昭、沈端先、谦弟(安那其主义者)等。
与《新女性》激进程度形成参照的是同一时期的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4日,该报刊出一篇名为《革命青年的恋爱观》的文章,作者提出“废妻”理论:“一天也好,二天也好,一年也好,一生也好,时间的久暂问题,视乎恋爱能否继续下去而定……两人间任何一方对于对方失掉了恋爱的时候,不必经过离婚的手续就可以自由离婚了。这样的恋爱才是真正的恋爱。”“废妻”之说固然耸动,其实质不过是民初无政府主义者“不结婚论”的回响。
大革命时期,各种来源、各种激进程度的性自由主张,在报刊上公开“争鸣”,自苏俄传入的“杯水主义”在此间起到了催化作用。在苏联,革命过后,专制秩序建立,柯伦泰的小说成为禁书。大革命失败后,柯氏的小说却在中国不断被结集出版。在《新女性》译本之后,夏衍翻译了柯伦泰的中篇小说《姐妹》和另一部小说,将其与《三代的恋爱》合编为“恋爱之路三部曲”。1929年,温生民翻译了柯伦泰的长篇小说《赤恋》。1930年,周扬翻译了柯伦泰的《伟大的恋爱》。《开明》杂志第2卷第8期则将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和柯伦泰的《恋爱之路》并称为“两本现代青年男女的必读书”。1930年代,“苏联的性文学”在中国已形成谱系:《三代的恋爱》《姐妹》《新俄大学生日记》《右边的月亮》……流风之及,“杯水主义”也进入了左翼作家的创作。
“耕者有其田”+“多者分其妻”
革命者似乎总是无师自通地把身体作为革命的资源或革命的对象,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五四青年到北伐青年,从清末男子剪辫到大革命时期女子剪短发,莫不如是。徐訏注意到:“在北伐的时代,革命的动乱,性观念又有很大的改变,苏联在革命时代所产生的‘一杯水主义’,也在那时传入了中国。”“中国在北伐时期,性的观念变化与性的行为演变也是很复杂很有趣的。它呈现出最放纵的‘一杯水主义’以及最落后的‘姨太太主义’的现象。北伐的武装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大家‘一杯水’,革命胜利,情有所钟,或若是珠胎暗结,乃谋久合,这是常事。有许多是从北方跑到南方去革命的与女同志恋爱难解难分,可是因为他们在北方家里已有个发妻,等到北伐完成,发妻重会,家有老父老母,岂容随便离婚,女同事也就屈居姨太太了。我们从这些千变万化的形态中,实在很不容易了解性观念在各种道德观点的激冲中,在个人心理上可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变化。但不管我们赞成或反对,那些不同的道德观念,往往会深入我们的下意识,它可以与我们的主张与思想不合,而我们的行为往往被它所控制。”
主张“性交自由”的安那其主义者谦弟曾为共产主义者“正名”:“近来有不少人总是说着共产便联想到公妻,好像‘共产’和‘公妻’是穿上了一条连裆裤不可分离,其实共产与公妻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主张,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没有一个是主张共产必须公妻的,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否定婚姻制度。”《大公报》社评也说:“共产党之称,出于日译,普通社会,初不知共产主义作何解,而就‘共产’二字以释其义,则有类夺人之产以为己有,故共产公妻,相提并论,常人闻之,如洪水猛兽。”
正如徐訏所言,“那些不同的道德观念,往往会深入我们的下意识”。“下意识”若被焕发,往往有更强的“杀伤力”和“动员力”。在1920年代,“共产”与“公妻”成为军阀间互相攻击的武器。孙传芳指责张作霖“任令其子学良小胜而骄妄,以五官中郎将自命,与三五新进少年、绿林枭桀,广招最犷之匪卒,杂以异种之犬羊,蹂躏中原、被同征服、倚官为盗,实行绑票、共产公妻”。张学良的手下胡毓坤指责冯玉祥“丧心病狂宣传赤化、用夷变夏,所谓社会主义、所谓共产公妻,种种邪说倡言不讳”。
北伐既起,“共产公妻”成为“南方赤党”专属的罪名。吴佩孚对日本记者发表讲话,称他与张作霖的联合实为阻挡“赤祸”的蔓延:“彼辈口中之所谓共产,实一种赤色的帝国主义,专共人之产不能与人共产。更进一步倡为公妻邪说,破坏伦纪莫此为甚。”1926年9月,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发出布告:“南方赤党竟敢师出无名,共产公妻主义强迫湖南实行,强夺商民财产、利权划归党人。”面对士兵,“孙联帅”说得更加通俗:“我们为什么要打倒蒋中正,因为他赤化。打倒蒋中正,就是扑灭赤化。何以要扑灭赤化?因为……赤化讲公妻。何谓公妻?就是你的妻,便是我的妻,亦便是他的妻,亦便是天下人的妻……”同一时期,直鲁联军宣讲队张贴的标语这样写道:“你们第一要晓得蒋介石是害人贼;赤党要来抢你财产了,大家赶快起来挡着他;无父无兄与共产公妻,试想世界上行得通么;你的财产,你愿被共产贼党用强抢的手段共了去么?你的妻女,你愿被共产贼党掳掠了去,作他们的公妻么;讨赤即是救国,因为赤党是苏俄的走狗。”
对常见诸报端的“共产公妻”之说,时人常抱这样的态度:“什么‘煽惑’,‘共产’,‘公妻’,‘杀人放火’,‘洪水猛兽’……呵!呵!红帽子多得很,随便拣那一顶戴在他头上就得了!真的,这些都是自孙传芳时代以来的万应杀人良药,是百试不爽的。”“万应杀人良药”说的正是“共产公妻”这一污名的效力。王奇生就注意到:北伐时期,北方的讨赤宣传“用的多是一些大众化的白话,讲的是反对‘共产公妻’的简单‘道理’。这些‘共产公妻’的‘道理’尽管很荒谬,但在当时普通民众的头脑中,可能比南方的‘打到帝国主义’,‘打到军阀’之类的口号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可能更深入人心”。

就连电影导演也要在“公妻主义”的时代活剧中轧上一角。1926年,东方第一影片公司推出由陆剑芬、任爱珠、周空空三大明星主演的电影《工人之妻》。该片大打“劳工与公妻二大主义之冲突”的卖点,实际讲的却是一个相当传统的故事:工人生活困苦辛劳,不足以满足其妻的虚荣心。其妻遂携子与恶徒私奔。后恶徒被捕,妻堕入贫民窟,贫病交加之时写信向夫求救。子被富翁收养,大学毕业后与父亲团聚。父子衣锦还乡,妻在贫民窟孑然病故。导演任彭年此前曾执导“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都市婚恋伦理剧是其所长,“劳工”“公妻”云云,应是打热点议题的擦边球。有趣的是,《工人之妻》的编剧是上文提到的写《佛动心》的王钝根。在《佛动心》中,王钝根对“公妻主义”极尽揶揄,几年之后,他的电影剧本却以“公妻”为噱头。同一时期,《申报》广告版面上打“共产”“公妻”擦边球的书讯、戏剧广告时有所见。
19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从南到北席卷中国大地:勇敢的军事行动、对于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大胆想象、暴力和混乱、豪情和血污、冲决罗网的决心,以及随后的彷徨、幻灭,在短短几年间一一上演。期间,已在报刊上喧嚣的“共产”与“公妻”第一次有了小范围的实践机会。从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武汉三镇到1927年7月武汉政府分共,武汉曾是革命的暴风眼。1927年4月,茅盾接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编辑时,武汉的局面相当混乱。大革命失败之后,茅盾作为蒋介石政府的通缉犯,从武汉逃到上海,在上海完成了《蚀》三部曲的写作。
“三部曲”中《动摇》的情节再次印证了前文引述的徐訏的判断:“那些不同的道德观念,往往会深入我们的下意识”,“而我们的行为往往被它所控制”。湖北某县的农民未必读过《新女性》和广州《民国日报》,对“非恋爱论”“非非恋爱论”等左翼青年的时髦论战谅必也不会感兴趣,但在大革命的风暴中,他们却无师自通地在“耕者有其田”之后加了一句“多者分其妻”,并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召开了一个抽签分妻大会:“去年腊尾,近郊南乡的农民已经有农民协会。农民果然组织起来了,而谣言也就随之发生。最初的谣言是要共产了,因为其时农协正在调查农民的土地。但这谣言随即变而为‘男的抽去当兵,女的拿出来公’……放谣言的是土豪劣绅,误会的是农民。但是你硬说不公妻,农民也不肯相信;明明有个共产党,则产之必共,当无疑义,妻也是产,则妻之竟不必公,在质朴的农民看来,就是不合理,就是骗人。”农民们盘算:在南乡,“多余”的或“空着”的女子不少:一人而有二妻,寡妇未再醮,尼姑没有丈夫…于是,在县农协特派员的坐镇下,南乡的农民在土地庙前开了个大会,抽签分配5个女人。第一个女人还没分完,夫权会冲来砸场。在当地,夫权会是农协最坚定的反对者。特派员见势不妙,迅速转移战场,带着抽签分妻的人打到夫权会。人们旋风一样跟着他,到了村前,把毫无防备的夫权会众全数抓住,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游街。这场闹剧传到县城的时候,国民党县党部成员的反应形形色色。投资分子胡国光希望趁乱有所“作为”;商民部长方罗兰和妇女部长张小姐淡然地将其视为谈资;妇女协会的孙舞阳郑重地将其称之为“妇女觉醒的春雷”。

小说家言与事实相去多远?1957年,茅盾回忆流亡上海时写作《蚀》三部曲的经历:“一时无以为生,朋友劝我写稿出售,遂试为之,在四个星期中写成了《幻灭》。”“那时候,我妻子生病,我是在病榻旁边一张很小的桌子上断断续续写起来的。那时候,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这个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第一次写小说,没有经验,信笔所之,写完就算。那时正等着换钱来度日,连第二遍也没有看,就送出去了。”通过这段自述可以看出,《幻灭》的文体是小说,但作者虚构的成分并不多:一则写作是为了换钱度日,是短时间内的急就章,构思、修改之类都能省就省;二则作者提笔“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所写是真实生活经历的复现。《幻灭》如此,《动摇》也如此。茅盾在《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中交代:《动摇》的构思和写作大概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比《幻灭》长些,可是实在的写作时间,也不过二十多天。
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蚀”三部曲,茅盾有这样一段自述:“(出版社)曾建议我修改其中的某些部分;那时候,我觉得不改呢,读者将说我还在把‘谬种流传’,改呢,那就失去了本来的面目,那就不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我的作品,而成为一九五四年我的‘新作’了。这‘矛盾’似乎颇不易解决。当时我主张干脆不再重印,但出版社又不以为然。结果我采取了执中方法,把这三本旧作,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则根本不动。至于字句上的修改,《幻灭》和《动摇》改的少,仅当全书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分之一。”由此可见:时过境迁,《蚀》的一些内容已不合时宜,但茅盾只做了有限修改,我们今天读到的《动摇》接近1927年春夏之交他在湖北的见闻。
我们能否据此说,“共产公妻”的闹剧确曾在一些地方零星上演?1927年1月9日《申报》上的一则消息似可作为旁证:上海防守司令部公开发表《赤祸侵入湖北后之现象》,声称赤党进入湖北后,武昌县知事公署牌示田产实行三三一制;武昌法院发布公告,宣布废止民法,停止婚姻案受理。公告发布者在“实行三三一制”后打了一个括号,注明“共产”;在废止民法、停止婚姻案受理后注明“公妻”。此公告由北伐军的敌方公布,其真实程度大可怀疑,但此间有一背景值得注意:“北伐”的军事行动是与国民政府的“司法党化”同步进行的。1926年12月底,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徐谦在武昌召开司法工作会议,会议议决:司法改革的目的是在“现在社会制度及经济制度之下务使农工群众减少压迫”;现行民法以前清《民律草案》为蓝本,有与党纲相冲突者,应酌量变更;婚姻问题,根据婚姻自由原则,酌量情形办理;地主及佃户问题,以不违背现在经济社会利益为原则,对佃户采取保护态度。鉴于此次武汉司法工作会议的精神,显易被敌方利用附会以为攻击。
“裸体游行”及其流传时机
大革命的潮汐退去之时,另一则关于“共产公妻”的谣言泛起。
1933年7月20日,《申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两年前作者从武汉初到上海,许多人见面就问,武汉是否常常举行裸体游行。作者因此感叹:“从上海到武汉,只有两三天的路程,而且交通也还便利,然而当时一般人对于武汉的情形,隔阂得竟如不同星球,即是一个毫无使人置信的理由的谣言,也会使人深信而不疑,大家把武汉看作禽兽之邦,为之‘谈虎色变’。”人们之所以信谣传谣,实因“裸体游行”曾是大小报章上轰动一时的消息。1927年4月24日,中华妇女同志会“阅报载汉口妇女藉词打破羞耻,发起免耻裸体游行大会,以天时尚寒,改期端节举行”,在“殊深惊骇”之余,给蒋介石、唐生智发电,谴责发起者及赞成者。滔滔谴责声中,“裸体游行”是否在端午节举行,并没有见诸《申报》后续报告。
比《申报》上述消息更早,4月20日出版的《北洋画报》上刊出《打倒可耻的裸体游行》。作者“诛心”写道:“尝闻古有某吏,得淫妇,褫其裳,缚伏驴上,使游于市,更于鞍间置一突起之木杵……使妇人得尽情发展其性欲……此固裸体游行之先例矣。今日者,天翻地覆之时也,女子裸体游行,在党治之下,固为绝不可少之点缀,而被压迫者则以打倒羞耻心为口号。然武汉妇人,既裸体游行矣,何不干脆‘自动地’骑木驴以当众‘发展其性欲’,岂不更妙也耶?”在这段文字中,“裸体游行”是完成时态的,但在擅长图片报导的《北洋画报》上却并无照片。同一页,北京政府进苏联大使馆逮捕共产党人的消息附了三张图,配发的按语称北京政府的捕人行为“实辛丑以来,外交界空前之创举”。这则消息和“武汉裸体游行”共处一版,无意中呈现了某种历史逻辑。
1927年5月,《新女性》的主编章锡琛在《论礼教与共产公妻及裸体游行》一文中写道:
自从国民党发动清党运动把共产党完全驱除之后,保存礼教的呼声忽然又发动起来……某会首领发出反共党通电,说共产党破坏礼教,提倡公妻,以致女不安室云云……不久前又看到某女子团体通电反对汉口女子的裸体游行……共产党从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究竟有没有做过破坏礼教的工作,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所以无从而知……至于说共产主义主张公妻,那不但维持礼教的人应该反对,便是排斥礼教的我们也绝不敢赞成,虽然我看过直鲁军宣传队所贴的标语,和新近反共产者的通电宣言,说共产党提倡公妻,却至今不知道怎样公法。倘使照一般人的解释以为公妻就是公有物,可以任无论那一个男子去向她泄欲,则现代公然通行的娼妓制度却不见礼教维持者怎样洪水猛兽地看待……
章氏将“裸体游行”之说与“清党”挂钩,虽未给出直接证据,但两事在时间上的接近确实值得注意。周军比对上海、武汉、京津等地报纸,发现“裸体游行”之说最早于3月间出现在上海报刊上,口吻为将来时态。《汉口民国日报》上最早出现相关内容是在1927年4月4日,内容是否定另外一份报纸上刊登的“裸体游行”将于5月1日举行的消息。然而4月中下旬,京津地区报纸对于“裸体游行”的“报导”已经是完成时态的,且各报所载细节多有出入。《汉口民国日报》对“裸体游行”的正式辟谣出现在5月7日和12日。但谣言并没有止息。1932年,鲁迅在为林克多著《苏联闻见录》所作序言中写道:“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苏联越平常,他们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传广东的裸体游行,后来南京、上海又盛传汉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敌方的不平常的证据。”比照鲁迅写作此文的时间,裸体游行谣言的散布时间恰与北伐的兵锋所及同步。
周军注意到,“裸体游行”之说蜂起之时,武汉政府正面临的巨大压力。鲍罗庭曾在报告中写道:“武汉的小资产阶级把国民政府同蒋介石的斗争理解为国民政府试图引进共产主义……小资产阶级根据帝国主义报刊和反动报刊的描绘来想象共产主义,说什么‘将拉着裸体女人满街跑(妇女社会化)’,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等等。”鲍罗庭的报告与章锡琛对“裸体游行”的看法可以互证,与《北洋画报》上的诛心之论中“天翻地覆”“党治之下之点缀”亦可呼应。
这些时论呈现的是武汉“分共”前夕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清洗将至,小说《动摇》中一个测字先生说:“该杀的人多着呢!剪发女子是要杀的!穿过蓝衣服黄衣服的人也要杀,拿过梭标的更其要杀!名字登过工会农会的册子的,自然也要杀!杀,杀!江水要变成血!这就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这样看来,“裸体游行”大概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世界中一个黄色的花边。
“分共”之后,“共产公妻”成为中共的专有罪名。从1927年到1936年,《申报》上《共党蹂躏琼崖之惨状》《江西贵溪县被匪扰害记》《赣省永丰兴国之共祸》一类的报道中,“共产”“公妻”成为攻击革命的高频关键词:“全琼……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共产公妻主义,且更大张告示:男子旅外限期六个月回家,否则焚毁家屋。迫乡民针刺‘赤军’二字于臂上,不从者杀。胁小童老妇驱之放哨、打仗,青年妇女轮流奸淫”,“稍有财产者逃命港澳南洋,贫穷者匿避山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1934年6月,蒋介石以“匪区法制礼俗、摧毁殆尽、男女间尤紊乱、倡公妻邪说、相率营兽性生活”为由制定“收复区婚姻办法”。
也是在1934年,红军政治部翻印的《俘虏工作须知》专门指导战士如何斥责“共产公妻”传闻:“国民党反动派说:‘共产公妻’,这我们可换过来说:只有国民党才实行公妻。苏区里面,婚姻是自由的。在国民党军阀们,每个人霸占几个穷人的女子,强奸、卖淫都是国民党造成的。”
到1936年,《申报》上关于“共产公妻”的消息戛然而止。
从1946年到1949年,随着国共内战越演越烈,“共产公妻”的消息渐次回归《申报》。
(本文摘自《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作者石岩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有大幅删节,原文注释从略。)

- 驰援缅甸
- 外交部发言人就缅甸地震答记者问
- 地球是否进入地震活跃期?专家解答

- 扬子江药业内部公告任命何如意担任药物研究院首席医学官,全面负责临床医学管理体系建设等
- 可免费退改签,多家航司发布针对缅甸航线退改签方案

- 北斗七星属于哪个星座
- 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是澳大利亚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