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安忆《儿女风云录》:“老法师”的故事里,沉浮着多少新旧博弈

文 / 余骏祺
近期,作家王安忆的新作《儿女风云录》出版,以其紧凑情节、各色人物和老练的笔法,串连起“老法师”跌宕起伏的一生和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这部作品不仅是弄堂小人物们的传记,更是王安忆对时代风云的细腻描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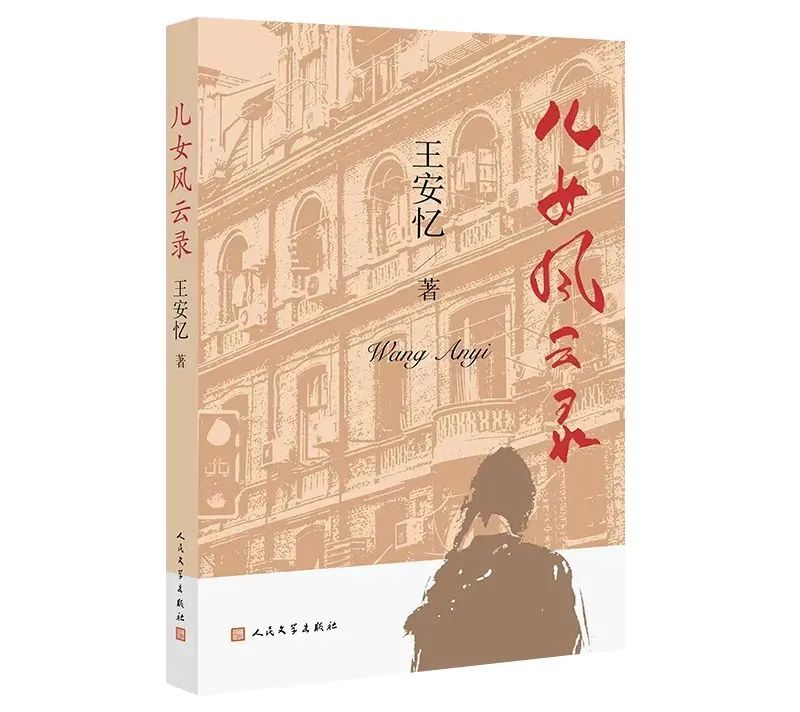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儿女风云录》延续了作家独特的风格,从风云变幻的人世间俯视苍生,将目光投射在了上海地方的“一类人”上,又从这类人中拎出“老法师”这一人物。人间,民间,再到一个人,聚光灯范围不断缩小,最后小到历史的一粒尘埃上。透过这一小人物,折射出半个多世纪的沧海桑田:“历史的残余”是“显学”,“他则是秘辛”。从小处着眼,将时代、历史和人物统一起来,是王安忆一以贯之的写作方式,也是读者始终关注和喜爱其小说的重要原因。《儿女风云录》中的小人物,围绕“老法师”展开,不仅数量多,而且各样:朴实善良的阿陆头、冷静精明的柯柯、眼光锐利的阿郭……这些小人物身上,或携带着历史变化的痕迹,或沾染着时代特有的风气。如何把握这些各异的、在弄堂里游走的男女老少?


《儿女风云录》首发于2024-5《收获》
从代际上看,《儿女风云录》前前后后写了四代人,命运各不相同。第一代如小瑟的祖父母、老太太,他们从斑驳的旧时代走来,在动荡纷争中安然走完一生。第二代人以老瑟夫妇、柯柯母亲、阿郭这代人为主,他们或是时代变迁的亲历者,或是时代变迁的旁观者,但无论如何,都得以善终。小瑟、阿陆头、柯柯和大麦则属于作者着重关注的第三代人,小瑟一生随社会变动起起伏伏,但总体上是于优渥中度过,却又在晚年陡然陷入尴尬困境之中。阿陆头和柯柯同样是时代漩涡中的人物,凭自身力量抵抗周遭际遇。第四代则有卢克、卢馨、如意及阿陆头的孩子,但这已不属作者关注范围。
代际背后,人物又被用“情”区分了开来。四代人,皆为人间蜉蝣,有情人身上多了几分血肉,无情人身上多了几分肌理。老瑟一代人身上没有火热的情感和欲望,对儿子、孙子,不过是按“天命”行事。阿郭从年龄上看当属第二代人,可他分明对小瑟有着不同寻常之情,他的身上有着时代的混杂性。而第三代人各有各的不同,小瑟从未有过情感牵绊,无论对女同学、柯柯还是大麦,都是凡俗因果推着他走。也正因情的作用,同为第三代人的阿陆头,虽也是在朦胧中度日,但却借此拥有自己的立命之处。柯柯同小瑟一样,感情和欲望都不曾占据她的全部,正因如此,她的身上多了几分清醒与精明,从而免于被时代抛弃,在香港寻得一方安稳之地。不难猜测,柯柯去了香港,也能凭着这份理智,从容地适应市场风云和之后的社会变迁。

除了代际与“情”,小说进一步用“新与旧”来重新理解这些人物。阿郭直言道:“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类,一类旧,一类新!”新人充斥着理性与深刻,而旧人浮泛地过完一生,任周遭变迁而流动,不求什么大彻大悟。深刻也好,浮泛也罢,都将这群儿女们引向了不同结局。
在这些新人与旧人身上,散发着不同时代的气息:有的人物身上充斥着陈腐气味,有的人物身上散发新鲜气味,还有人物身上气味驳杂。即便同样是“旧人”,有的能够免于卑琐的命运,有的却被时代无情打击。小瑟,便是众多人中唯一一位在时代面前不知所措之人。小瑟看着“更像禁欲”,但在晚年“好不容易醒过来”,有了迟到的欲望。这种欲望与其说是从底子里油然而生,不如说是被那些“先进的女性”勾起,也就是来自现代的诱惑。小瑟身上的腐味太浓,欲望又太脆弱,不足以支撑他抵抗残酷年代的冲击。当遇到邪恶、复杂的欲望时,他甚至仍沉溺在混沌中,“完全没有觉察危险来临”。终于,他不堪一击,被关进了现代法治的牢笼之中。作家展现的不过是一个旧人,带着旧的生存之道和微弱的欲望,在凶猛的现代文明面前,接受了他的命运。
无论如何,信号灯红转绿,又转红,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王安忆在某一帧按下暂停,展现其中的实况,把这些小人物从历史沼泽中捞起。《儿女风云录》讲述着几十年间的风云变幻和弄堂儿女们的爱恨纠葛,既为读者铺开一幅精妙的时代画卷,也叙说着对社会、历史的深沉思考。径路绝而风云通,天下儿女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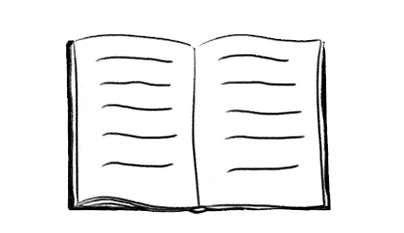
01

上海地方,向来有一类人,叫作“老法师”,他是其中一个。
仔细考究,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舞厅开出日场来了。窗户用布幔遮严,挡住天光,电灯照明,于是有了夜色,还有违禁的气息——舞会的内心。日场结束至多两个钟点,夜场开幕。白天的人气还没散尽呢,油汗,烟臭,茶碱,瓜子壳上的唾液,饮料的香精,胭脂粉,也是香精。窗幔依然闭着,但因为外面的暗,里头的灯亮穿透出去,一朵一朵,绽开绽开,然后定住不动了。
这类日夜兼营的舞厅,多是设于人民公园的旧茶室,关停工厂的废弃车间,空地上临时搭建的棚屋,菜市楼顶的加层。从地方看,就知道它普罗大众的性质。日场的客源以本地居民为主,退休或者下岗,因为有闲;晚场就成了外地人的天下,大致由两部分构成:民工和保姆。价格也是亲民的,五元一人,男宾买一送一,可携一名女客,还有更慷慨的,女客一律免票,没有女伴的也不至落单,初次见面,总要买些饮料和零嘴。无论怎样的舞厅,都是交际场,场面上人不能显得悭吝。所以,最后统算,不赔反盈,渐渐地,一生二,二生三,蔓延开来,成为常规。很快,女多男少,性别比例又失衡。那些女宾们,伙着同乡人小姊妹,自带吃食,孵着空调,看西洋景,占去大半茶桌。没有生意做事小,主要是形象,舞厅,即便普罗大众的舞厅,也要有一点华丽的格调吧,现在好了,一派俗俚。然后,就出现了一种人物,师傅。师傅是跳舞的高手,他们以一带十,只需交付一点费用,一杯饮料的钱吧,饮料是舞厅的标配,同时,也是可见的利润,一杯饮料,可与师傅跳一曲。再淳朴的人,舞厅里坐上一阵子,也会跃跃欲试。音乐所以被古人视作教化,专辟一部“乐经”,此时显现出实效。师傅的带领下,村姑们一个个起身离座,迈开了脚步。
老法师就从师傅中脱颖而出。
顶上的转灯,扫过黑压压的桌椅,零星坐了人,也是灰托托的。不意间,闪出一张森白的脸,线条深刻,面具似的凸起,就有瞬息的延宕,即湮灭在影地里,等待下一轮的光。人们知道,老法师来了。
通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午眠的人醒来,再度过假寐的时辰,拖拽着白日梦的尾翼,恹恹的。勿管舞场论不论晨昏,生物钟这样东西,已经潜移默化成定势,所以,还是生发影响力。原始的时间里,午后的一段就最暧昧,它既是凌晨,白昼开始,又像是子夜,走进黑天。更别说舞场里的人工制造,企图模拟永恒,结果是混淆,生物钟弄不好反而添乱。其实是透支,向夜晚借白昼,白昼借夜晚,借了不还或者多还。舞场里总是亢奋和颓靡两种情绪并存,此消彼长,就是证明!可是,老法师来了,情形就不一样。他自带时间,一个独立的时辰,谁也不借,谁也不还,氤氲中开辟出小天地,小小的生机和小小的循环。
给师傅的是饮料,老法师的是酒,威士忌,白兰地,金酒。就算是这样的舞厅,远远望去,像瓦砾堆,墙上红油漆写着“拆!拆!拆!”,屋顶和墙缝,流浪猫在野合,一包包垃圾从天而降,可也有威士忌白兰地金酒。在吧台里的架上,勿管真的假的,瓶子上贴着标签,曲里拐弯的拉丁字,写着古老的年份,从未听说的酒庄,至少一瓶有货,那就是老法师的特供。有时一人独资,有时几人合资,买下来,理所当然,享有贵宾级别,优先做老法师的舞伴,也可以叫作学生。
和老法师跳舞,生手变熟手,熟手呢,变高手。脚底生风,眼看着随风而去,打几个旋回到原地,脸对脸,退而进,进而退。场上的人收起舞步,那算什么舞步啊,让开去!场下的人,则离座起身,拥上前,里三层外三层。场子中间的一对,如入无人之境,疾骤切换的明暗里,人脱开形骸,余下一列光谱。瞬间一刹那,回到形骸里,再一转瞬,又没了,有点诡异呢?然而,倘若掀起一角窗幔,透进亮,一切回复原形,他是他,她是她,众人是众人。无奈遮蔽得严实,那鬼魅剧越演越烈,进到异度空间,仿佛回不来了。正神魂游离,舞曲终止,老法师将舞伴送到原位,石化的旁观者动起来。
音响送出慢步舞,人们纷纷上场,舒缓地摇曳。这样,老法师垂着手,半合着眼,对面人也是,身体没有一点触及,可是心心相印。他几乎不动,可是全场和着他的韵律。转灯放缓节奏,不那么晃眼,这样,我们就能看他仔细。他呀,至少一百八十五公分,又穿一身黑,目视更要高上三公分,抽出条子,细长细长,顶着一张脸,悬在半空。不仅因为白,还因为立体,就有占位感,拓开灯光的浮尘,兀自活动,打个斤斗,倒置着,再打个斤斗,回到原位,也是骇人。倘若离得近,好比与他舞伴的间距,看得见细部,眼窝、鼻凹、下颌中间的小坑,染了一种幽暗的青紫,刻画出轮廓。舞伴心怦怦地跳,不是骇怕,是震惊,似乎将要被攫住,携往不知什么地方,却又闪过去,放了她。不知侥幸或者遗憾,也让人震惊。灯光亮起来,眼前金箭乱射,箭头上带着一点魂,梦的余韵。就像中了魅,到舞场不就是找这个来的?唯有老法师才给得了这个!
02

舞厅外面,甚嚣尘上。拨开厚布帘子,后面是门,双重的隔离,才有那个谲诡的世界。走下一架铁梯,原本是高炉的上料斜桥,拆了卖了,辗转到这里。透过踏板的空当,看得见地面,夜市将要开张,排档的摊主亮了灯,支起煤气罐瓶,砧板剁得山响,桌椅板凳摆开一片。后面的水泥房子里是菜场,鱼盆里咕咕地打氧气;生蔬底下细细喷着水雾,蔫巴的绿叶菜又硬挺起来;豆制品的木格子大半空了,散发出醋酵味;熟食铺的玻璃窗里,颜色最鲜艳也是最可疑:蜡黄、酱红、碧绿、雪紫。好了,沿街的饭馆上客了,大铁镬的滚水里,翻腾着整只的蹄髈、猪脚、腔骨、肋排;小罐汤在灶眼上起泡;一人高的笼屉里,一层五花肉,一层花椒面,一层炒米粉;酒瓮剪蜡开封……这里有一种绿林气,来的都是好汉!
谁想得到,烟熏火燎里,那一具集装箱似的铁皮盒子,盛着的声色犬马。白日将尽,霓虹灯还没亮起来,灯管拗成的汉字:维也纳美泉宫、罗马天使堡、凡尔赛镜厅,陷在暮色里,蓄势待发,等候闪亮时刻。铁匣子的焊缝,不小心透出一点动静,转眼让汽车喇叭声搅得更散。远近工地的打夯机,水泥搅拌,吊塔三百六十度掉头,也来凑热闹,这城市开膛破肚,废墟建高楼。芯子里的小朝廷,终究敌不过外面的大世界。舞曲和舞曲,乐句和乐句,休止符、附点、延长音的渐弱、跳音和跳音之间,抢进来炝锅的油爆;车轱辘碾过路面的坑;铜舀子打在缸沿;婴儿的啼哭,女人的碎嘴子——细碎却绵密,见缝就钻。可是跳舞的人,是做梦人,叫不醒的。看他们迷瞪瞪的眼睛,微醺的样子,甜蜜蜜的饮料,肌肤的若即若离,分泌着荷尔蒙,哪里经得起老法师的手,轻轻一推,你就滴溜溜转个不停。
时间速速过去,《地久天长》的终场曲里,全体下海,碰来撞去,你踩我脚,我踩你脚。跳舞让人们的心情大好,就起不来冲突,是和睦的大家庭。全家福独缺一人,老法师。
老法师遁走了。街巷的阡陌里,前院墙上爬着夹竹桃的影,后窗向外吐炊烟,主干道华灯初上,漫进一些光晕,绰约透出人和物的轮廓,看不清细部。要有明眼人打个照面,凑了哪里来的亮,就会咯噔一下:外国人!跳舞厅那种场合,本身是个传奇,这身形和脸相就像长在里面,称得协调。日常的生活却是平庸的,凡涉及一点点异端,便跳脱出来。市井中人叫作“外国人”,除此还能叫什么?既是直观的印象,同时呢,还真揭示了实质,那就是非我族类。
03

婴儿时候,叫作“洋娃娃”;长大些,“小外国人”;然后,很奇怪的,具体成“法兰西”;高中和大学,不只国别,还有种族,是“犹太人”!诨号的演变,大致体现本地市民的世界地理常识,是半封建半殖民历史的遗绪,也不排除卖弄的心理。事实上,他三代定居沪地,祖籍宁波,不过是个名头,五方杂居的上海,称得上原住民。沿海地区人口迁徙流动,血缘混交,遗传纷杂,只是发生在概率里,落到个体则渺茫得很。他和他的父母确实不顶像,但是他又只能生在这家里,可能是看惯了,或者这里那里,真有一点隐秘的相像。幼年的他,长一张圆鼓鼓的脸,大眼睛,瞳仁黑得发蓝,浓密的睫毛,扇子一样张开,鼻尖上翘,唇形有棱有角。婴儿肥褪去,骨骼显出来,成了外国电影中的英俊少年。西区昔日的法租界,侨属已经融入市民社会,很奇怪的,有一个群体,就是理发师,被称作“法国人”,他们所操的扬州家乡话则是“法国话”,以上海的地方成见,难免含有歧视。很难追究渊源,但多少可以证明,外国人的在地化。他被称作“法国人”,其中的意味就有些微妙了。随年龄增长,异族人的凸凹有致,渐渐变得粗阔,脸架子拉长,下颚的肌肉发达,接近通常说的“马脸”,收紧眼距,更显得深目高鼻。皮肤依然极白,不是那种半透明的牛奶色,而是象牙的瓷实的白。一头黑发,加上眉睫浓重,真是亮眼,周遭的人和物都黯淡下来。“犹太人”就是这时节喊起来的。老上海大多见过虹口一带的犹太难民,摆地摊,卖自家做的白面包,变戏法,骗走小孩子的零钱,是穷酸的同义词;文艺青年知道典出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犹太人又有了狡诈的名义;沙逊、哈同一流是发财梦里的人物,无异于青红帮,黄歇浦就是个黑社会——所以,就成了个骂名,听见有人叫,是要回敬过去的。
他的出生年月是个谜,按履历表,是一九六六年之前进校的大学生,可是,那一年滞留的在校生总共有五届,贯穿数个年头,就没办法从这里推算了;看职业,他下过乡,还参过军,这两段却又交集在一起,细考下来,原来是军垦农场,时序又乱了;他的档案且一直压在学校人事科的文件柜里,落满灰尘,没有任何就职记录,可谓白茫茫大地,一片萧然!至于户籍簿上的婚姻状况,就是谜中谜。不知道哪一个环节的忽略,单身直接跳到离异,一时上有儿有女,骤然间,又全都没有,仿佛入了道门,无为有处有还无!看外表,最是糊涂,年轻人也比不上他的挺拔紧致,然而,有时候,换一种光线角度,你会发现,他的面颊松垂下来,形成两个小小的肉囊,法令线、鱼尾纹、眉心一个川字,浮出水面,分明是张老人的脸。体态也是,就像现在,向晚的天光里,一身黑外面套了短风衣,接袖坍到肩膀底下,身形就有些塌,髋骨大幅度摆动,脚底却迈着小碎步,嚓嚓嚓的。速度倒不见得慢,很快走进一条短弄。暮霭忽然明亮起来,照出门上的脱漆,脱漆里的木纹理和裂痕,很有些年头了。钥匙插入弹簧锁,俗称“司必灵”的孔眼。这一截三四连排的旧里房子,出于某种缘故,可能是开发商资金链问题,抑或地块所属区域不同,或者只是个人的维权结果,所谓“钉子户”,于是划出动迁范围。眼见得对面日夜施工,打夯机震得墙体歪斜,楼面开裂,吊塔贴着头顶移来移去,倾下砖石瓦砾,像要把它埋了。
......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原标题:《王安忆《儿女风云录》:“老法师”的故事里,沉浮着多少新旧博弈》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