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加缪欣赏的伟大作家们:乔伊斯、纪德、普鲁斯特、托尔斯泰......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让·格勒尼耶与阿尔贝·加缪
1960年1月4日,加缪和密友米歇尔·伽利玛在返回巴黎的途中遭遇车祸逝世。
1968年1月4日,加缪的哲学老师、文学启蒙导师、毕生挚友让·格勒尼耶,于巴黎完成了《阿尔贝·加缪:反抗永恒》这本私人回忆录。在格勒尼耶眼中,加缪一生充满艰辛,却仍怀揣对人类此生意志的希望。
*
这是文学史上的一大悖论。阿尔贝·加缪在文学品位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曾有几年在姨父家借住,那里收集的阿纳托尔·法郎士全套作品成了他的精神食粮。连阿尔贝·加缪自己也觉得惊奇:年轻时竟读了这样一位故纸堆里的作家!这让“熏陶”“师承”方面的专家没了用武之地。
阿尔贝·加缪的姨父阿库先生是位屠夫,开了家叫“法兰西-不列颠”的肉店,据他说,取这个名字是为告诉布尔乔亚们,这里售卖的肉品质上乘。他是个自力更生的男人,个性独特。我认识他时,他应该还不到50岁——精力充沛、满嘴俏皮话,像是拉伯雷书里走出的人物,还是个美食家。他最爱的一道菜是里昂香肠。他曾在里昂生活过。他的青年时光诠释了他对阿纳托尔·法郎士的热衷,那时候,人们视法郎士为最完美的作家,后无来者。
不过,阿库仰慕的不止有法郎士,后来还多了乔伊斯,《尤利西斯》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兴许是为书中幽默而轻佻的笔调着迷吧。我在米什雷大街的文艺复兴咖啡厅和他饮过一次茴香酒,就在他家肉店对面。
阿尔贝·加缪很早便明确了身为作家的使命。早在——尽管时间早晚证明不了什么——阿尔及尔中学读书时,他就与同学迪迪埃(他后来成了耶稣会会士,几年前死于一场车祸)一起办报纸,报纸传阅到二年级或许还有一年级的班上。那年头的中学生爱这样消遣。
事情是在那一天变了性质,我在阿尔及尔的中央邮局前碰到刚结束毕业会考的他,他问我是否相信他能写作——指写出一些值得发表的东西;以及他是否有能耐继续哲学学业!

加缪
18岁的阿尔贝·加缪喜爱纪德,更胜当年的所有名家,他认为《纪德日记》“富有人性”(这是其他很多作品中少有的品质)。
那时候,他没想到自己未来会和纪德在瓦努路的套房里同住上一段时日。在青年作家中,纪德钟爱萨特和加缪,他的评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为公众舆论所印证。1951年,纪德离世,加缪不可谓不伤怀。
*
18岁的加缪,还视普鲁斯特为创造者(对他来说没有比这更高的赞美了),普鲁斯特的作品笔力刚劲、细节入微,二者的反差令他印象大为深刻。他景仰普鲁斯特至极,说自己释卷时内心酸涩。他说,我们在普鲁斯特那儿获得了这么多,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最终会想:“一切都说尽了。再没有能回去说的了。”我在偶然间,在尚不清楚普鲁斯特的世界是否适合他的时侯,给了他《追忆似水年华》这本书,他的这份景仰于是令我更添欣慰。
*
构思《反抗者》时,他希望在精神上做到诚实,于是读了大量的书,并接触到部分19世纪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因为处于时代洪流之外,而很少被人提起。在撰写《正义者》之前,他还读了很多写1905年俄国革命的书。
他始终偏爱“道德学家”的书,比如他曾选取为讲座主题的尚伏。他认为自己也是“道德学家”,动听的“哲学家”称号就留给德国人和他们不计其数的信徒吧。
*
和萨特的关系如人们所知,他们虽然彼此尊重,但性格差异极大。对萨特发表在《南方手册》上的《局外人》文评,加缪心怀感激,他欣赏萨特的解析,认可其中部分批评的合理性、部分意见的洞见性。令他迟疑的是这种“拆解”作品的做法,这篇充满智的文评,没能揭示出作品创作中的本能特质。不过他承认,涉及批评时,规则如此。无论如何,反对萨特的人,必须先和萨特站在一起,这是他的结论。
*
在青年时期,最打动他、也是和他最亲近的书,我想是安德烈·德·里什欧的《痛苦》,以及路易·纪尤的《平民之家》。他从我好友的这两本书里找到了自己。为纪尤的《伙伴》所写的前言中,他陈明自己为什么会被这种书打动:它们以穷困且时而破裂的童年为作品的养分,并在旁人要藏匿和遗忘的东西中发掘出财富。高尔基的天才之处,不就在于永远不忘给他带来巨大痛苦的事物,永远不将不幸美化,仿佛只有通过伤口,美才能进入我们体内吗?
离世前几个月,他在读尼采的书信集。
他说,尼采谈论自己时,仿佛在谈论慈悲上帝,但他可悲不已。他不是慈悲上帝。
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向他推荐过一本化名发表的小书,名叫《尼采的神性》。书本身就是这种神性的强烈印证。我曾经很爱这本书,它远不止是颂词,还是一种信德行为。埃兹的尼采!他当时——以及后来在都灵的自我坦白。
加缪认为这种信德行为是一次赌博,要认真以待,但始终可疑。不过,他理解并为人们对尼采的误解辩护,尼采向来有一种无意识的模仿意愿——比如模仿狄俄尼索斯,比如模仿基督。在加缪看来,尼采模仿这些人,又因为做自己而恼怒。可加缪想,人必须甘心做自己。
他最钦慕尼采的一点,是他持续与身体上的病痛斗争。加缪一言蔽之:“高尚不总是义务。但通常是义务促成了高尚。”这样说起他人,又何尝不是说起另一个自己呢?
文学上——文学和人性是分不开的——他最欣赏融写作与生命为一体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居首(卢马兰的卧室里挂着他的相片),加缪宽宥了他的说教。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他着迷。所有的俄国作家他都感兴趣,就连谢德林的《戈洛夫廖夫一家》,也叫他揪心和赞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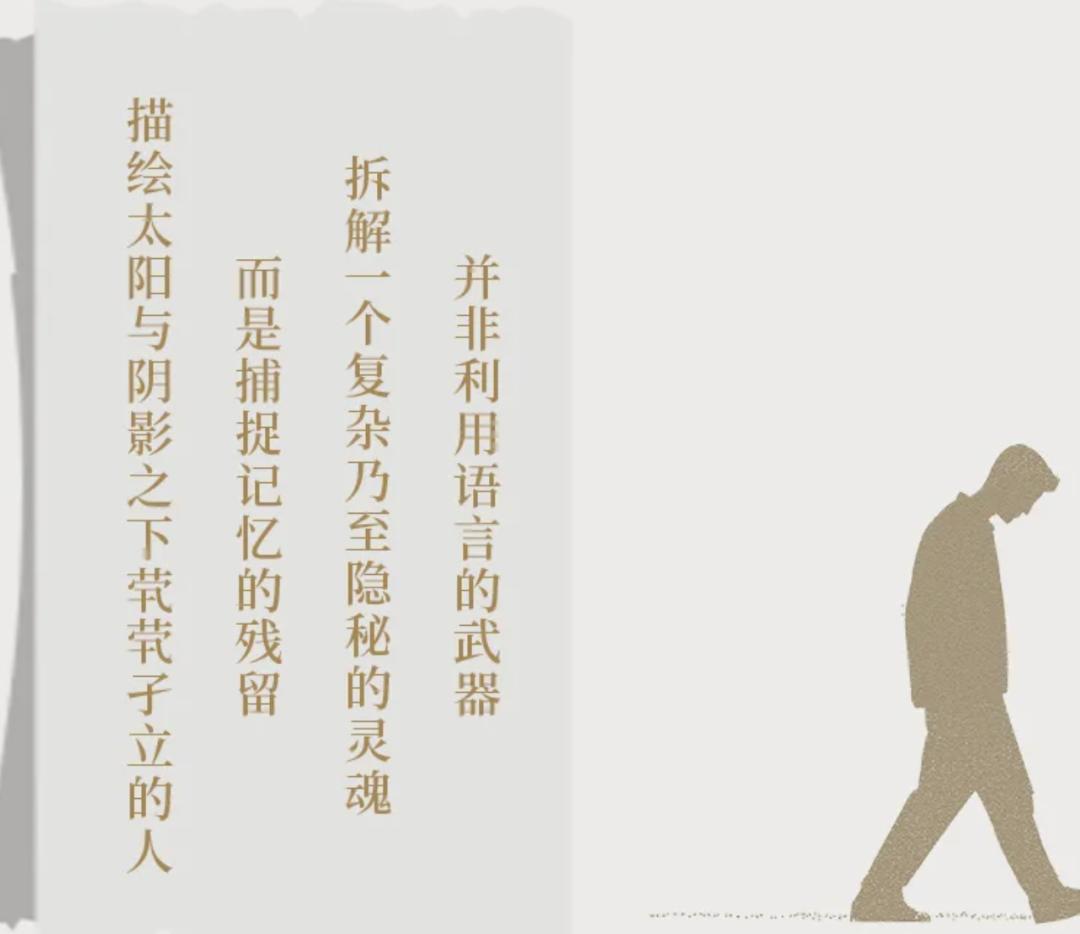
阿尔贝·加缪基本不对名誉抱什么幻想。在他告诉我《夏天集》卖出两万册的那天——他当时才出版过几本书?——他和我讲了这个故事。
疗养院的病患们在圣拉扎尔火车站的图书馆寻觅我的书,未果。那儿的人不认识我。此外,管理图书馆的人和我说,因为您是疗养院读书委员会的成员,所以他们才想找您的书,看看您都写了些什么。
后来还有人和他表示:“啊!加缪先生,您没说过您这么有名呀。不过现在我知道了,我看过您的电影。”(他说的是电影导演加缪。)
他曾因《局外人》鹊起的声名,仅在文学界和年轻人中传扬,而这一次,熠熠生辉的诺贝尔奖让他的名字为天下人所知。阿尔贝·加缪曾获得“批评家大奖”。尔后,他作品的译作越来越多。名望之下,他在海外的讲座愈加引得人们去了解他的作品。诺贝尔奖完成了这种祝圣。更何况作家在获得这样一份人人憧憬的大奖时,还正值壮年。
一次旅行中,我得知斯德哥尔摩的人都在谈论他,尤其是评审团里的新生代作家。由于巴黎报刊的总编们有责任预测重大事件、以免准备不周,于是几年间,他们一直邀请他参与会谈(所谓“采访”),主题是:“您刚刚获得诺贝尔奖。您对此作何反应?”
有的作家乐于提前作答,他们的答案或将永远不为人所知。阿尔贝·加缪拒绝了。他预想刚去斯德哥尔摩开过讲座的安德烈·马尔罗会获奖,也这样期望,加缪从在阿尔及尔改编《轻蔑时代》起,就一直非常崇敬马尔罗。
人们几乎是交口称赞。我说几乎,因为我没想到会出现猛烈的批评声。最恶毒的批评是将他比作苏利·普吕多姆,作为法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普吕多姆的作品已经失去声望。有周刊邀我写一篇关于加缪的文章,阿尔贝·加缪劝我接受邀文,不过他也告诉我,敌视他的人将会比从前更多。
我意不在讲述琐事,也不想写文学逸闻,不想描绘文坛,或为谁画像。我只提一件事,那是阿尔贝·加缪去往斯德哥尔摩的前夕,他的数十位朋友响应菲利普·埃里亚的提议,为他举办了一场友爱而简朴的晚宴。我同样还留存着我们共进午餐的记忆,那是在诺贝尔奖公布后,他动身去阿尔及利亚之前。从他的言行来看,最近的遭遇似乎令他惊愕不已。他倒不是像其他人那样,装腔作势地抱怨;我想,当时的他再次见到母亲和老师,那就像项链的首尾两颗珠子在他手下再次串联一体——这幅我刚刚联想到的画面,是现实再好不过的象征。
内容选自
[法]让·格勒尼耶/著
谢诗/译
拜德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出版社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