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到体制内的第四年,我去医院开了双相的药|三明治
原创 Lavin 三明治

文|Lavin
16号楼跟别的楼不一样,它跟其他楼有一段距离,有自己独立的小院,候诊区虽然是露天的,但抬头看不见天空,头顶都用简易的黑色麻布盖住了,错综复杂地排列着,挡住了所有视线,既遮不了风,也挡不了雨,因为是户外,空气里不会弥漫着医院常见的消毒水味,如果不是偶尔有人被保安架出去或者是在地上打滚,根本不会让人觉得这里是精神科。
不知道等了多久,叫号系统终于大声地喊出我的名字,我深吸一口气,掀开帘子,钻进了有冷气的屋子里。
医生看了一眼我问:“药吃完了?”我点点头。“最近情绪怎么样?”这时我才开始呼气,“还是不想上班。”她点了两下鼠标,“那继续开一个疗程吧。”
这是我第四次来这里开双相的药。

到体制内的第四年,直属领导R介绍了刚回公司的Y带我,她借调的项目临门一脚的时候黄了,回来没了位置。项目的一把手则抓住了机会,升迁后十分照顾当年的旧同事。
Y从不拒绝我的好意,但从不让我参与她的工作。直到跟她走得近的同事提起,她由于性格问题没有晋升,别的没有细说,只提示我“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
渐渐地,R不再提要她带我,我主动要求参与项目的请求也被拒绝,原因是“你还做不了,先让Y负责”,如果再追问下去理由,得到的只有顾左右而言他,我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直到一次找一把手签字,他要我向Y学习,我以为这是暗示,兴奋地跑到Y办公室请教,Y表示很忙要我等一会。一个半小时后再去,她抬起头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我都给忘了,你先回去吧。”
言语之中,我像台球桌上的白球,每一杆都参与,每一杆都碰壁,随着时间推移,桌上只剩我,和摆弄我的杆子。长时间被无反馈的工作消磨,我像戴上拳套却不知往哪攻击的拳击手,只能对着空气一顿乱挥,一无所获,却被不知道哪来的绵针不断地刺痛。身体开始出现反应,每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通过暴饮暴食、反复催吐来发泄没有缘由的焦虑和愤怒。
最终,被边缘化的我成为R的“管家”。我开始为他处理各种琐碎的小事,比如重置开机密码,调整文件字体格式,收发快递等,还要做好随时随地被远程遥控的准备。有一天晚上,他突然给我打视频电话,问我邮箱里的邮件在哪看,当时我坐在马桶上,却还是接了,关掉自己的摄像头,教他点击左上角的收件箱,看着他茫然的脸,耐心和信念一点点崩塌,只能起身远程帮他操作,他才没有继续打过来。
我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
当看到R对我的态度后,部门同事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的“帮个小忙”调整文件格式,跑腿签字,到后来,甚至直接给我安排工作。R对这一切看得明白,有时安排不下去别人做的工作,也会交给我,理由是“别人做事太毛躁,交给你我更放心。”
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段,用赞美掩盖压迫的本质。热爱颁发隐形的、做成枷锁形状的奖杯,直接套在对方头上,当有人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要发自内心露出笑容,“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在掌声之后,它则戴着这座奖杯继续忙碌,直到下一个候选人出现,奖杯会一直传递下去。
戴奖杯的中途一旦推辞或拒绝,就是不识抬举,“领导重视你才把工作交给你呀!”,就是目光短浅,“多做点对你又没有坏处,多在领导面前表现才有机会。”随着拒绝的频率增多,用的词越发宏大,赋予的意义也就愈发深刻,因为如果戴枷锁的人跑了,就要把前任重新召回,由奢入俭可是难上加难。
所以我总是被“捧上神坛”,即使是调格式这样的小事,也会收到句“没有你不行”。听的次数多了开始犯恶心,像被强迫喂下了一只伪善的苍蝇,压抑的源头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我的承受能力也接近极限。

有一次接近午休,同事要我将excel表格的内容调整到一页纸上打印,理由是“我不会操作,下午领导要看”在我调整到只需要他按下打印键后,他还是不满意,“我待会要出去,你帮我调整一下打印出来。”而打印机就在他办公室。
看着那个大小不足10K的表格,网格线好像密密麻麻的小刀,将我最后的底线挑断,我仿佛听见自己的身体在抗议,想把电脑砸烂。我第一次拒绝了他的要求,直到下班,聊天记录还停留在我截图打印键的地方。
几天之后,我请假在家备考没接R的电话,看见来电记录,我选择了无视,出于责任心,还是回复了同事的工作信息。没想到,同事告知R我回复了,于是R的目的就变成“一定要让我接电话”,打了几十个无果后,在晚上11点,他联系我的家人说我请假了没接电话,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以为我出事了。
在父母的焦急和恐慌之中,我停止了这场荒唐又任性的反抗。他们说“为什么不接他电话?跟他好好沟通,别耍小孩脾气”的时候,我说不出话,只是止不住地流泪。
自责和屈辱交织在一起,咒骂自己的愚蠢和无用的自尊心,对被背叛的愤怒像汽油浇在了被冒犯的边界上,极端的想法充斥在脑海。打开通话记录,看到一连串的红色未接电话,我开始不停地抓挠自己的脖子,皮肤表面全是一道道跟未接电话一样颜色的红印。我想把这假冒的奖杯扯下来烧个精光,却怎么都摸不到它,可它明明存在啊,并且越缩越紧,我快无法呼吸,把头埋进了枕头里。
后来得知,他原本是想问我柜子的密码拿一个U盘。返岗后他什么都没说,直到发绩效我才发现少了五百元,同事私底下告诉我,理由是我工作态度消极,不配合安排。
过往的经验让他认识到——领导拥有着围绕着下属的一切,所以要么按领导的意思做,要么甘愿受罚。任何不顺从的人都会受到惩罚,没有人在这种对抗里获得过胜利。成功的经验给了他十足的底气,他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毕竟这比掌握办公软件简单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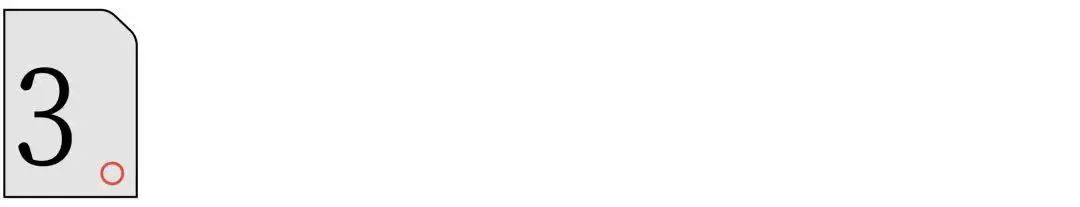
又过了段时间,经历高点买房,考试失利,父母均动大手术之后,与他的对抗确实让日子更难过了,而重要的是,我承担不起离开这里的代价,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
要让渡多少自我才能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没人能给我答案,我好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服从性测试机器,进来的人都被丢进去,通过测试的往上走,没通过则一直留在下面。
而我,毫无疑问是没通过测试的那一批,还是改造失败的最次品。
半年后的某一天早晨,我发现同事提交了3个月的哺乳假申请,第一道流程由我审批,与其说是审批,不如说是通知。我面无表情按下了同意,将流程点给了R。
自我实现的方式似乎单一到了极致,看上去像另一个充斥着童话的谎言。
继半年的产假后还能继续请3个月的哺乳假,并且在这种消磨人的地方,没人会顶替她的位置,这也是吸引人留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她休息的大半年里,领导没有指定谁接替她的工作,领导不提,底下的人也就心领神会。
不指定就是指定,指定就是下意识,而我知道,我就是那个下意识。
她与我同龄,早早地选择结婚生子,理由是“反正晋升没希望不如把重心转移到家庭。”看着她,像在预设自己,是否也只能通过进入复杂又陌生的关系来摆脱虚无,只能通过成为某个人的伴侣、某个人的母亲,才能在极度压抑的生活里获得一些意义。
还是说,追求意义本身就没有意义,我不该再执着于此,而是应该随波逐流,这样反而活得轻松。
自我实现的方式似乎单一到了极致,看上去像另一个充斥着童话的谎言。
把自己放进不合适的评价体系,就像要削掉大脑和四肢,再假装合适地融入,即便已经鲜血淋漓,也要强装自己本就是其中一员。毕竟,这场测试只认结果,并不在乎作弊及其方式。在这里,人像蚂蚁一样被组织起来,一台无所不能的压缩机粉碎了人们的一切个性。
此刻,熟悉又无法摆脱的窒息感突然笼罩了我,我好像被看不见的空气墙困住了,光是想到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我在办公室就控制不住地大哭了起来。不知道如何跟这种忧惧相处,做不到不为还没发生的事情担忧,甚至都不敢问她“这是唯一的办法吗?”不管答案是什么,我都会反复验证直到崩溃。

后来,除了处理R的杂事,我还被安排了项目付款签字工作,一般需要经过三到四个部门审批才能交给财务。这些部门都分布在不同的楼,而线上付款流程由于“不好操作”和“审计风险”迟迟没有运行,每个人在见到我的时候都会对签字的人数高达十位以上表示惊讶,但又都表示理解,“要规避风险嘛,线下也要留痕。”
没有人关心西西弗斯为什么一直在推石头,他们只在乎推石头的是不是自己。
月底的最后一天,有一笔款到了财务却迟迟没有付,R要我盯着流程,避免浪费预算。和会计确认凭证刚做完还没复核后,我向R汇报,“凭证做完了还没复核。”他问是谁复核凭证,我表示不清楚财务的工作安排。“好的,我找他们领导。”他挂断了电话。
十分钟后,会计给我打电话,冷冰冰的语气,“是不是你告状说没有人复核凭证?”当下如同触电了一般,好像突然被推进了导电的漩涡里,浑身发麻。“我没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急得在电话里发誓,“如果是我就被雷劈死。”我拼命地想要摆脱漩涡,但无法动弹。
对方可能被我的激动程度吓住了,告诉我她领导刚刚找她说,有人反映凭证没人复核,她很生气,觉得这种话让领导听到很不合适,想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我向她详细复述了全过程,又向她领导解释了一遍,得知是R说“送过来的凭证没人复核,请协调。”最后把经过告诉她,她回复:“没事,如果我不相信你,我就不会直接给你打电话。”语气轻松,仿佛刚刚剑拔弩张的气氛从没发生过,而走完这套流程,我已经出了一身冷汗。
我明白,即便她一开始找R对质,结果也是一样,因为在三个人里,拿我出气是最成本最低的。一句简单的转述,激起的水花之大令我后怕,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多少次了?可怕的是真正追究起来,我也确实无法证明自己说过的话,“相信你”三个字此刻显得十分可笑。即便有做工作记录的习惯,我也不可能时刻开着录音机。漩涡消失了,但触电的感觉没有,我不再挣扎,渐渐沉入水底。

有一天去签字的路上,我看了眼手里修改多次的表格,这已经是今天来回的第三趟。武汉的夏天地表温度到了四十度,我停在路中间,突然不想继续了,狠狠盯着头上的太阳,希望它能把我烤干。这时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是我的前任领导B,问我站在这里干什么,我没说话,开始往前走,他看了眼我手里的东西,几步走上来与我并肩,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在太阳底下走着,他突然说:“你为什么不去印尼看火山?”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要他再说一次。
“你为什么不去印尼看火山?”他故意凑近大声重复了一遍。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有点无厘头的问题,憋出一句“我都不知道印尼有火山。”
“那你现在知道了啊,请几天假去看吧,特别好看!”
只有几秒,似乎从没有尽头的重复跳脱出来,短短六个字像是在厚重的阴霾里抠出了一束光,我就这样被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宽慰了。
然而宽慰是暂时的。

一天上午接到通知领劳保的电话,这次发的主要是大件的洗衣液,有三十多斤,办公楼没有电梯,我决定把东西放在一楼和A部门一起领,得到了在场人员的一致同意。
我在群里发通知,附上清单,并且口头告知了所有人,尤其是R。他说了句“好的谢谢”,我稍微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因为有电梯的时候,都是把东西分拣好送他办公室,这次是我第一次没有这样做。
过了两天,他还是没有领,我心里开始打鼓了。
第三天下班路上突然接到R的电话,问劳保放在哪里,可能意识到什么,又接着问:“有没有把东西按人分拣出来?”这时我才反应过来他的不满。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种对话,大脑宕机了,只能回答他“没有。”
他继续追问放在一楼丢了怎么办?我没说话。
近百瓶洗衣液该如何在3平米不到的空间分拣出来呢?他以前是A部门的领导,之前放那里也觉得会丢吗?我的工作范围里有物资分拣吗?这次又是我做得不对吗?
我开始逐一复盘这几天发生的一切细节,回想起下午去找另一个部门领导签字时,放在角落里分拣好的物资,恍然大悟,这正是令他不满的地方——他要权力优待,但用道德的外壳掩盖需求。他认为我应该自觉将东西分拣出来,方便他直接拿走,如果我不这样做,他就失去了特权,这是他最不能接受的。
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寄希望于她能多了解我一些,能理解当初我为什么会不接R的电话。说完之后,她回复了我。
“你太傻了,应该单独帮他拿到办公室去拍他马屁。”
“他就是要摆这个谱,你能拿他怎么样?”
……
一开始,我还在解释拿不动三十多斤的东西上楼,忽然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自证漩涡。
重要的不是是否具备拿的能力和条件,而是有没有拿的意识并且付诸行动让领导看见。自我厌恶涌了上来,幼稚、愚蠢、可笑,不计其数的负面词汇从四面八方飞来,嘲笑自己居然渴望得到她的安慰。
不想再复盘那些琐碎得要命的细节,不想再复述任何人的话,重现当时的场景,不想再进行无谓的自证了。反正结果都是一样,每次都是一样,为什么就不能干脆点,直接告诉我,这次也一样就好了啊。
脖子上的枷锁又加了几只无形的手,在此时狠狠地按住了我的头。在我稍微表露出一些自我的时候,那些手就会突然施压,把我按进无法呼吸的真空里,时刻提醒我,不要把自我排得太靠前,尤其是领导前面,不要去挑战不成文的潜规则,尤其是默认的特权。
她见我沉默许久,问我是否听懂她说的话。
怎么会听不懂呢,我不懂又怎么生存到现在。我笑了出来,故意讽刺道“是不是该多做一步,帮他直接拎到他车上去,送到他家里去?”
几乎没有停顿,她回答,“对啊,就该这样做。”
刹那间,封闭已久的开关被打开了,对这个地方的恨意瞬间全数涌了出来,将按住我的手被悉数砍断,枷锁被生生扯开,我再也无法掩饰了。
她话音刚落,我瞬间拿起手边的东西往地上疯狂地砸,控制不住地开始一边流泪一边尖叫,把目之所及的全部砸了个粉碎。她之后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尖叫打断,在我大叫“我受够了,我不要再忍了”之后,她终于留下一句“你冷静一会儿就好了”,把电话挂断。
此时我看了眼房间,已经无处落脚。

我又回到了16号楼。
不知道等了多久,叫号系统终于大声地喊出我的名字,我站起来直接冲了进去。
医生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问:“最近情绪怎么样?”
我盯着她,“我昨天砸了很多东西,边砸边哭,哭得停不下来。”
她手上动作停了几秒,“那就换新药吃吧。”
跟一年前相比,头顶上的黑布变多了,厚重到光需要找缝才能钻进来,新的循环开始了,像《彗星来的那一夜》,每次开始,我都会走进同一家医院,拿着不同的药走出来。
我走在黑色麻布的阴影里,在不同时空的混沌中,与过去的自己相遇。有的满面愁容,分散地坐在露天的候诊区,朝着头顶的黑布发呆,努力想透过它们找一点天空,有的见五分钟医生就跑出来,抱着一堆药匆匆离开,有的出来的时候一脸茫然,手里还拿着医生给的咨询师名片。
“够了,不要再继续了,不要再开始了。”我走到每一个自己面前大喊。
可没人理我。
瓢泼大雨毫无征兆地浇了下来,我被淋得透湿,顶着肿着的大眼泡漫无目的地走,雨越下越大,模糊了视线,我看不清眼前的路,停了下来,抬头望天。
“对家人乱发脾气的自己真是糟糕透了,”我想,“跟同事领导叫板也是毫无作用的情绪发泄。”有一点后悔,剩下的是内疚。
“可我已经这么做了。”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我也是。
宏大叙事,优绩主义,我曾经奉为圭臬,每一分钟都异常关键的成长路线,我走得战战兢兢,但最后还是到了这里。
我早晚都会来到这里。
望着灰蒙蒙的天,湿淋淋的地,我第一次觉得,放弃也没关系。
我决定请半年病假。即便是有短暂逃离的可能性都好,只要能松一口气就能骗自己再坚持一会。
想到这里心情轻松了一些,随便走进一家店躲雨,我是唯一进来的人,索性就坐下吃点东西,本以为下雨天生意不好,吃完转身发现已经座无虚席。
可能我要做的只是转身而已,就算坚持不下去又怎么样呢?望着灰蒙蒙的天,湿淋淋的地,我第一次觉得,放弃也没关系。
写作手记
故事最后的砸东西情节正好发生在开班的前一天,也算是送上门的素材了(苦笑),翻看了上一次的短故事和这两年的记录,发现我处在一个巨大的循环里,并且越陷越深。带着愤怒和恨意敲下事情的经过,把能记得的细节都写了下来,像是发泄,可发泄完之后陷入了自我怀疑,这些细碎的痛苦有没有记录的价值?
我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写下去,自我消化完那些情绪后,似乎又能坚持下去了。可又能坚持多久呢?坚持到下一次崩溃吗?我又要在短暂的放松后忘记那些处于无助时刻的自己吗?想到这里,我还是把旅行后快乐的自己拉回桌前,熬了几乎通宵写完了。回到情绪里是痛苦的,因为我不能阻止循环的开始,但这次作为旁观者,我能给痛苦的自己一个停靠的地方。
原标题:《到体制内的第四年,我去医院开了双相的药|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