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60年前,他就受够了上班

24岁的他,生活总是笼罩着一层忧郁。每天上班,对他来说就是一场无休止的煎熬。他总是和同事们格格不入,友谊昙花一现,他常常感到自己是个孤独的异类,而同事们则是一个紧密的整体。他总觉得同事们用一种厌恶的目光审视他,对自己的形象和存在感到深深不满。他害怕自己看起来可笑,因此奴性十足地遵从一切成规惯例,生怕自己做出任何标新立异的举动。这一切让他感到极度痛苦,每天下班回到家,他都需要大量时的刺激来平息内心中不断累积的愤怒。
他,就是陀思妥耶夫记《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早在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位主人公就已经对上班办公深恶痛绝——“以致达到如此地步:许多次我下班回家,竟像大病了一场。”
那时,我才二十四岁。当时,我的生活就已经郁郁寡欢,杂乱无章,并且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不和任何人交往,甚至避免跟任何人说话,越来越深地龟缩进自己的角落里。在办公室上班时,我甚至极力不看任何人,我也十分清楚地发现,我的同事们不仅把我当作怪人,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这样——似乎还用某种厌恶的目光在看我。我不禁深思:除了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感到别人是用厌恶的目光在看他呢?
在我们办公室里,有个同事形貌丑陋,满脸麻子,甚至似乎还颇有强盗相。要是我长着这么一副有碍观瞻的面容,定然不敢抬起头来看任何人一眼。另一个同事,身上的制服又脏又破,一挨近他身边就能闻到一股臭味。然而,这两位先生中竟然没有哪一位感到不好意思——无论是因为衣服,或是因为尊容,还是因为品性方面的什么问题。无论是这一位,还是那一位,都不会想到,别人会用厌恶的目光看他们。而且他们即使想到了,也毫不在乎,只要不是上司如此看他们就行。
而今,我完全明白了,由于自己那有加无已的虚荣心,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己的苛求,因而对自己不满到了极点,进而由不满发展为厌恶,于是,就在内心里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了每一个人。比方说,我对自己的脸深恶痛绝,觉得它丑陋不堪,甚至还怀疑它上面有某种下流无耻的表情,因此,每次上班时,我都要停辛贮苦地让自己摆出一副独立不羁的姿态,使别人不致怀疑我下流无耻,同时也尽可能让脸上的表情显得高贵一些。“脸长得不美就让它去吧,”我心想,“不过,要让它显得高贵,表情生动,而最重要的是极其聪明。”然而,我确切又痛苦地意识到,所有这些优点永远无法用我这张脸表现出来。而最为可怕的是,我发现这张脸真是蠢笨不堪。但我心里还是完全能够容忍的。我甚至可以承认脸上的表情下流无耻,只要别人同时认为我的脸聪明绝顶就行。
自然,我憎恨我们办公室的所有同事,从上到下,概莫能外,而且鄙视所有人,然而与此同时,我又似乎害怕他们。常常,我甚至会忽然认为他们远远高于自己。那时不知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我时而鄙视他们,时而又认为他们远远高于自己。一个富有修养、作风正派的人,如果不是自己对自己无尽无休地求全责备,并在某些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他就不可能产生虚荣心。可是,鄙视他们也好,认为他们远远高于自己也好,我在遇到的每一个人面前都会低下目光。我甚至做过实验:我能否经受住某个人射向我的目光,可总是我第一个垂下目光。这使我痛苦得几乎发疯。
我生怕自己显得可笑,甚至害怕到病态的程度,因此我奴性十足地崇拜有关仪态举止的一切成规惯例。我真心喜爱循规蹈矩,并且打心眼里害怕自己有任何标新立异的行为。然而,我又怎么能熬受得住呢?
我是一个病态的富有教养的人,就像当今时代所要求成为的富有教养的人那样。而他们大家却全都浑浑噩噩,而且彼此就像羊群中的羊那样何其相似。也许,在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常常觉得自己是胆小鬼和奴才。而这正是因为,我是个富有教养的人。不过,这不仅是感觉,而事实上也果真是这样:我是个胆小鬼和奴才。我这么说,并不感到丝毫的不好意思。当代任何一个作风正派的人都是,而且应该是胆小鬼和奴才。这——才是他的正常情形。我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生来如此,老天就是这么安排的。而且不仅在当代,也不仅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总的说来,在任何时代,一个作风正派的人都应该是胆小鬼和奴才。这是世上所有作风正派者的自然规律。如果他们中偶尔有谁麻起胆子干了什么事情,那可千万不要以此自我安慰并沾沾自喜:因为他在别人面前终究会心虚胆怯的。这是唯一而永恒的出路。只有蠢驴和他们的低能子孙才会硬充好汉,然而,须知这也只有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如此。对他们无须关注,因为实在不值一提。
当时还有一种情况让我苦恼不堪,具体地说,就是没有一个人与我相似,我也不与任何人相像。“我只是唯一,而他们是全体。”我思忖着,接着便陷入深思。
由此可见,我还完全是个小顽童呢。
也时常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形。须知有时我甚至对上班办公都深恶痛绝,以致达到如此地步:许多次我下班回家,竟像大病了一场。可是突然之间,又会无缘无故地升起一股疑神疑鬼、漠不关心的情绪(我的情绪总是变幻不定),于是我自己也嘲笑自己的过于偏执和吹毛求疵,责备自己沉醉于浪漫主义。我时而不愿跟任何人说话,可时而又不仅要跟他们畅所欲言,而且恨不得和他们相互视为知己。所有的吹毛求疵会突然之间无缘无故地云消雾散。谁知道呢,也许我从来就不曾有过这种吹毛求疵,而只是装腔作势,从书本上照搬的?我至今还没有搞清这个问题。有一次,我甚至跟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开始对他们登门拜访,和他们一起打牌,一起喝酒,谈论职务升迁……
当然,我和同事们的友谊没能保持多久,我很快就和他们吵翻了,而且由于当时年轻气盛,没有经验,甚至见了他们连招呼都不打了,就像是从此一刀两断了。不过,这种情况总共只出现过一次。总的来说,我一向都是孤身独处的。
在家里,首先我主要是读书。我试图用外来的感觉抑制住我内心中不断累积的愤懑。而对于我来说,外来的感觉只能来自阅读。阅读,当然对我大有助益——它使人心潮起伏,使人心花怒放,也使人痛苦不堪。不过,有时也使人感到乏味至极。我毕竟想活动活动,于是便突然陷入阴郁的、地下的、卑劣的状况之中——并非放荡,而是堕落。我的情欲由于我经常的、病态的愤懑而变得异常劲悍,十分炽烈。时常歇斯底里地发作,还伴随着热泪滚滚,浑身痉挛。除了阅读,我无处可去——也就是说,当时在我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尊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吸引我。此外,苦闷又日益深重,于是歇斯底里地渴望矛盾、对立,就这样,我便放纵自己荒淫起来。我现在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可绝对不是在为自己辩解……然而,不!我在撒谎!我正是试图替自己辩解。先生们,我记下这些,是为我记下这些,是为自己立此存照。我不愿说谎。我做过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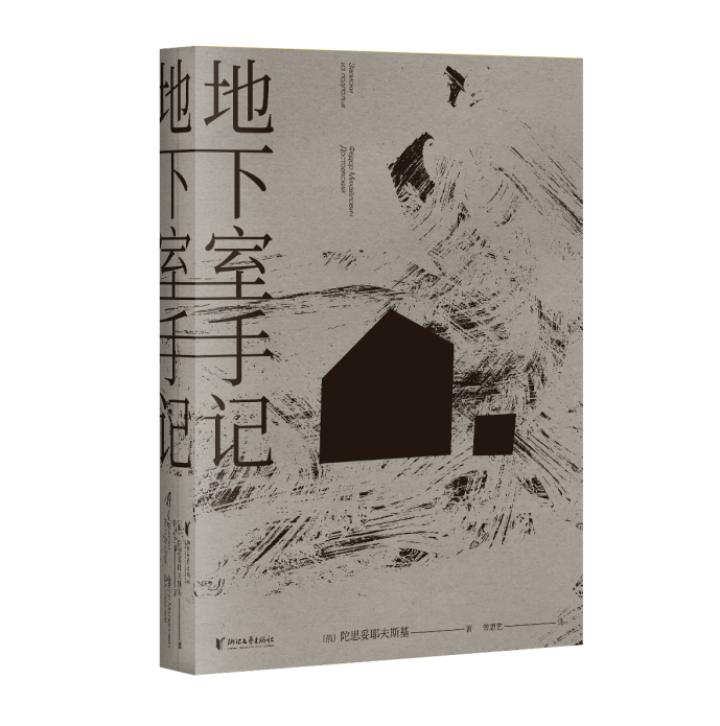
节选自《地下室手记》浙江文艺出版社|
果麦文化 2020年5月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曾思艺 译
文字与图片获浙江文艺出版社|
果麦文化授权
原标题:《160年前,他就受够了上班》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