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侯旭东:打捞被遗忘的北朝村民世界

侯旭东
远远地看上去,戴着两千多度近视眼镜的侯旭东,让人错觉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位终日埋头在故纸堆里的老夫子。如果近距离观察,56岁的他甚至比实际年龄还要显得年轻。红蓝白三色格子休闲衬衣,外套一件藏青色V领毛线背心,眼前的侯旭东,肤色白皙,温文尔雅,一副书生模样。初冬的阳光从阳台窗玻璃照进来,整个客厅里都暖融融的。2024年10月底,因为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的《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以下简称《北朝村民的世界》)一书,我采访侯旭东,地点就在他的家里。

《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收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时的封面
2005年,作为何兹全主编“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的新成员,《北朝村民的世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十年间曾几次重印。2022年,经专家论证和审核,该书收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再版,一年后又旋即加印。一本纯学术著作,能有如此不俗的市场表现,无论是出版方还是作者本人,都算得上是一份殊荣。侯旭东的学术履历显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史,兼及秦汉”。实际上,除了这本《北朝村民的世界》,《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以下简称《宠》)《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等书也为他在学界和读者中带来了极大声名。其中,《宠》于出版当年入选中华读书报年度十佳图书及国内多家重要媒体图书榜单,《什么是日常统治史》收入罗志田主编的“乐道文库”,同样受到众多读者喜爱。

《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2005年初版时封面
出生、成长于大学校园,从本科到博士10年的学术训练,中国社科院12年的研究生涯,2008年调入清华大学工作至今,历数下来,侯旭东的人生轨迹可谓非常简单,其重心始终是围绕学术,生活的场域也基本没脱离过高校。虽然在农村生活的时间屈指可数,但要了解中国和中国历史,不能不关心农村,这是他研究北朝村民世界的一个重要初衷。“这对我来讲是个挑战,因为我基本上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但是做研究需要不断地突破自己的界限,包括生活经历上的界限,知识上的界限,要抓住历史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去做。”
别开生面的中古乡村社会研究
公元439年—581年,存在于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个朝代,被后世史家总称为北朝,与南方地区的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四朝合称南北朝(420-589年)。作为中国中古时期的社会生活史著作,《北朝村民的世界》中讨论的时代距今将近1500年,追究这么久远的事情,资料匮乏是最大的难题。“此前的无数岁月里,无论是在历史研究还是现实研究中,‘村落’始终是中国学术界相当薄弱的一环,基本处于学者的视野之外。”侯旭东说。
历史上,关于乡村的描述,其鼻祖或可上溯到《诗经》中的农事诗,如《豳风》中的“七月”。此后,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为世人留下了许多对古代乡村生活的浪漫描述。“尽管如此,总体上无论是士人还是朝廷,都缺乏了解乡村的兴趣。”在《北朝村民的世界》开篇文章《从田园诗到历史——村落研究反思》中,侯旭东指出,“田园”只是文人,特别是失意文人,闲情逸志的寄托,借以抒发他们的心境与追求,表现的重点是诗人的个人情感,而不是细致描绘乡村生活的实景,难以从中发现乡村的精确画面。历代朝廷统治的对象主要居住在乡村,历代也有过关于乡村的许多官方记载,如各种性质的地方档案,除了极少数由于各种原因残存至今,或经现代考古发掘而重见天日,绝大部分都被主动销毁或毀于兵燹战乱、自然消亡。
在侯旭东看来,历史上的每个时期都存在过多种声音,只是由于历史记述者的取舍,给后人主要传达了一种,而忽视、压制了其他声音。相对于众声嘈杂的过去,突出其中一种声音而压抑其他声音是带有歪曲的效果的。“今天的学者有义务、有责任挖掘出那些被抑制的声音,展现过去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的工作只是在这方面做的一点努力。”
原本,侯旭东也没有想到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从硕士开始,他学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史专业。读博期间,他读到《东晋南北朝的佛教结社》(郝春文)和《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刘淑芬)这两篇文章,由此注意到造像记(记录各种宗教石窟、神龛等像的制作的文字)。博士论文即是利用造像记来研究当时北方民众的佛教信仰(1998年,论文以《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为名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集造像记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侯旭东注意到这些造像记题名中包含了不少乡村生活的内容,从村名到村内居民的姓氏构成、家庭关系、村内景观的表述,等等,加之“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乡村做过长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且与中国中世社会形成这样的大问题联系在一起,使得村落研究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但侯旭东注意到,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很少利用造像记,他希望借此来推进中古乡村,特别是北朝乡村的研究。
学者胡宝国在评价该书时认为,与传统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有很大不同,侯旭东研究的重点是北朝时期的基层社会。由于研究观念、史料等方面的限制,传统北朝史研究的重点还是在朝廷、国家,而本书则是有意识地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基层社会,从而为我们描述出了一个十分生动、丰富的北朝基层社会图景。在诸如“村落”的性质、时空分布、“宗族”的含义、“三长”的地位、乡里与村民空间认同,“市”的多重意义等等许多方面,都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
而其书名副标题中的 “生活世界”(Life-World)一词,最初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后经奥地利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加以发展,其涵义为“包含人所牵连的种种日常事务的总和”。侯旭东借用这一概念,用以概括由朝廷、州县和村里三者构成的考察范围。如他所言,其基本研究单位是“村落”,主要对象是“村民”,同时也关注村民日常生活涉及的村外世界,两者之和构成他们的生活世界。“既分析村民的活动,也涉及他们的观念。最后试图从中提炼出理解中国历史的新分析概念与新解释。”
在豆瓣《北朝村民的世界》的内容简介下面,是长达数页的读者评论,既有几千字的规范书评,也有几行字的心得体会。有人说,学界对于乡村社会史的研究,鲜见中古时期基层乡村的研究。这本书充分利用现存可见的各地造像记,对于村里、村民生活及国家认同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别开生面。也有人表示,这本书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材料的一网打尽、全面掌握。这位网友还表示,“自己最近也在写论文,不少地方都可体会、借鉴这本书”。
史学研究不能止步于考证事实,还需构建解释

集安丸都山城遗址考察时留影
“抓住历史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去做。”从做北朝乡村研究开始,侯旭东便有了这种明确的意识,至今他一直都有这样一个追求,那就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或许,这样的学术理想,在他童年时期就悄然埋在心底了。因为父母在北师大工作,侯旭东从小在北师大校园里出生、成长。周围邻居中不乏知名的学者教授,因为父亲在教务处工作多年,还曾担任过陈垣校长的支部书记,他很早就以父亲熟人的身份听闻过白寿彝、启功、刘乃和、龚书铎这样的史学大家,钟敬文则是父母的老师,很多历史系的老师也是父亲的朋友与同事,没有什么仰望的畏惧。加之先天性遗传,从小眼睛深度近视,学不了理工科,父母又认为他中文没学好,于是选择了历史专业。高考时,侯旭东考了班上第一名,但北师大给生活补贴,加上离家近,他最终放弃北大选择了北师大。从1986到1996年,这一读就是十年。
1990年夏天,本科毕业的侯旭东本想报考自己喜欢的中国近代史专业,但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当年硕士考试暂停,只能保送本校。有人建议他学魏晋南北朝史专业,因为这个专业有硕士和博士。于是他一路读了下来,最后从何兹全先生门下博士毕业。侯旭东初涉史学的1986年,被称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元年”。当时,史学危机的阴霾弥漫学界,而社会史的蓬勃兴起,成为那些年中国史学最瞩目的变化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侯旭东多少也感受到了这种新风气与新变化。大学四年,他读了很多介绍与研究西方新史学的书,也修过相关的课程。1995年暑假,还在读博的侯旭东旁听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虽是短短的21天,但于他而言却意义深远,得以“初识文化人类学的门径,给了我观察现实与过去的另一只眼,受益无穷”。
博士毕业,他去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在完成初期的北方民众佛教信仰研究后,便投身到北朝村民生活研究。回溯自己的研究轨迹,上世纪90年代邓正来先生致力推动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民社会的含义与适用性这一学界热点,成为他学术研究的契机与起点。这之后,他与学界友人在思想上相互砥砺、碰撞,尝试提出“村里”概念,意在反思“社会”一词,寻找更为恰当地表达古代中国百姓基本生活场所的概念;概括出朝廷、州县与村里三层构造及关系,参照造像记中佛徒们的表述,希望借助“主位观察”的视角,提炼一个更切近古代中国的分析框架。于他而言,这也是“对邓先生有关追问的一个回应”。
“史学研究不能止步于考证事实,还需要构建解释。”侯旭东知道,这条路很漫长。对中国学界而言,首先要从基本概念的重新厘定开始。这些概念不应是盲目照搬西方,而要立足过去的事实潜心归纳与定名。他深深服膺历史学家黄宗智的名言:“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只有立基于此,才能逐步构建出关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种种解释。
侯旭东说,表面看来,每个学者是“直接”面对由各种资料组成的“客观对象”来从事研究,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错觉”。我们都是在自己所接受的前人研究所积淀下来的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的指引下展开工作。能意识到这一点,就有可能通过注意到前人的界限而自觉地走得远一些,能突破一些具体的框架,提出新视角,发现新问题;如果对此茫然无知,可能会落在前人设定的具体框架内,工作的领域或是前人不曾涉足的,但分析的方法与问题意识难以跳出已有的藩篱。
在侯旭东这里,做学问难得的不仅仅是获得新的材料和方法,问题意识才是更深层、也是更可贵的驱动力。尽管时隔多年,他仍然非常怀念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的那段时光。他与同事孟彦弘一起发起组织“史学沙龙”,十年间举办学术讨论会70多次。每次的沙龙上,大家一起讨论各自刚写完的论文,包括他自己《北朝村民的世界》中的大部分篇章,都在这里接受同仁们的批评和建议。此外,他们也请一些学界名家来座谈,如葛兆光、李零、巫鸿等。“历史所这12年对我学术成长非常重要。”在他眼里,这相当于第二次读博士,为后来的学术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那时候,他和孟彦弘、胡宝国、陈爽、吴玉贵等人每周的返所日几乎都成为交流学问的聚会。这几位好友中,吴玉贵是孙毓棠与马雍的弟子,孟彦弘乃宁可的高足,陈爽出自田余庆门下,胡宝国则是史学大家胡如雷的公子,父子二人都师从周一良(胡如雷是周一良的开门弟子),学术背景各异。胡宝国从小耳濡目染,对北大的那些老先生都很熟悉。就像自己小时候对启功、刘乃和这些史学大师们的认知一样,因为从小就认识、接触,取的是一种平视的视角,并未将他们看作不可逾越的权威。比如胡宝国,他和田余庆关系密切,对田先生学术上的问题和得失都能够指出来。这些,是侯旭东在“史学沙龙”之外获得的更为隐性的教益。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青年史学沙龙。左起依次为:杨宝玉、黄正建、关树东、侯旭东、张彤
承上启下的转折点

侯旭东在整理课上要使用的今人书写简牍册书
1999年8月,侯旭东赴南开大学参加会议,提交的论文即是《北朝村民的世界》中的《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得到与会的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学濛的鼓励。另外一篇论文寄给台湾“中研院”的邢义田先生,同样得到邢先生的肯定。千禧年前后,他到哈佛燕京学社访问一年,开拓视野的同时,发现在当时中国接触到的学说与美国大学里流行的学说基本同步,没有太多的落伍感。此间,他将书中另一篇《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的要点,向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华琛(James Waston)请教,后者建议他翻译成英文,后来在JA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再就是,侯旭东曾送过一本《北朝村民的世界》给美国学者南恺时(Keith Knapp),南氏因此邀请他参与《剑桥中国史·六朝卷》中 “地方社会”章节的撰写。长期以来,六朝史是海外汉学较薄弱的领域,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人选很少,除侯旭东外,另有三位汉语学界的学者受邀参与,其中两位来自“中研院”史语所,另一位是北大的荣新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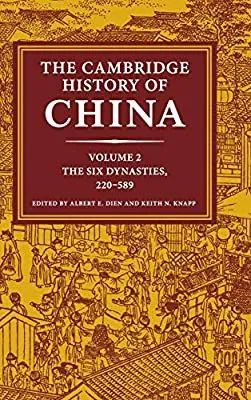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The Six Dynasties, 220–589
作为历史学者,史料之外,侯旭东同样关注理论问题的探究。《北朝村民的世界》中那篇关于北朝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的个案研究,受到读者关注和好评,令他颇感意外。2001年8月,在结束大同召开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后,他取道太原至阳泉,再打车到平定县开河寺石窟,进行实地考察。此前他注意到有考古学者在调查开河寺石窟后,显示造像基座上还有题名,但这位学者没有抄录。侯旭东此行的目的,是想对石窟的造像题记进行更全面的整理,但因为没有掌握打制拓片的技术,只能望石兴叹。为完成这篇论文,他还特地通过社科院考古所开具介绍信,到国家测绘局买了四张平定县1:5万的地形图。不过后来地图也没有派上多大用场,只是用来画了一幅当地的地图,用在文章中。
这些年,他的兴趣不断漂移,关注的重心上移到秦汉,更多地转向研究国家统治的展开。当被问及这本书在其学术版图中的位置时,他给出的回答是“承上启下”:上承博士论文关于造像记的研究,下启国家和王朝的研究。由此,他开始借助西方理论逐步尝试提炼概念,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此后,他更自觉地返回历史现场,开展多侧面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出土文书简牍的研究,从走马楼三国吴简起步,现在更多的是研究汉代的文书简牍。“乡村社会研究给了我一个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即便后来花费不少精力来研究朝廷,我始终也不是就朝廷论朝廷,就皇帝论皇帝,而是能跳出来,从基层、民间角度来观察朝廷与皇帝。这种多样化的角度是这本书带给我的。”
做北朝乡村的研究期间,他的另一收获是处处感受到古人(包括身处底层,看似天高皇帝远的村民)生活中皇帝与朝廷挥之不去的存在。有些是直接的,如造像记中对皇帝与百官的祈愿;有些是间接的,甚至迂曲的。“这些不仅使我重新思考强调贵族自立性的六朝贵族论,更使我意识到皇帝与朝廷在古人生活中的份量,进而引导我去关注皇帝、朝廷与官府这些所谓老生常谈的话题。”
虽然《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自成体系,但是其中那些问题又成为原点,各自发散,成为他新的研究方向。
“国家研究”三部曲

2022年夏,和景跃进、蔡乐苏等参加北京社科联组织的考察活动,右一为侯旭东
“现在的问题就是时间少。”虽然清华的工作量不算多,但他带的学生比较多,上课占去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加上学校的各种“杂事”,开学后基本上做不成什么完整的事情,只有假期里才能静心从事自己的研究。不过,侯旭东表示自己倒也没那么着急,他现在的想法是,不一定要写那么多论著,还是以少胜多,抓住比较重要的、前人想不到的问题去做。
眼下,他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早期国家的运行机制和形态,时段上基本不出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近,他刚刚完成一篇文章,探讨十六国时期的汉赵国,即匈奴贵族刘渊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非中原居民的国家,藉此来重新思考中国的民族史。这也是他计划中“国家研究”三部曲中第二部的内容。
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2018出版的《宠》,梳理不同类型的“宠”来研究君臣关系,关注的是王朝内部在官僚制之外支撑国家运作的机制。第二部,即研究非中原居民国家的建立及其对后续历史的影响。按照他的规划,不是仅仅将此放在断代史、国别史的脉络下,而是将从汉赵国与十六国、辽金西夏、元与清代这些非中原居民建立的国家,前后联系起来进行贯通性考察,同时也和秦末的南越国,以及习称的“农民起义”放在一起思考。侯旭东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一类是中原居民建立的国家(从秦汉到明),另外一类就是所谓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最早出现的汉赵国构成了中国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从疆域上看,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基本上稳定,奠基于秦代,但在东北、西部以及西南方向疆域不断伸缩变化,很多都是和这些非中原居民的统治有直接关系,汉赵国是其起点。他希望由此来反思民族史及其背后的民族国家观念。
至于第三部,侯旭东笑称已准备了11年,甚至连书名都取好了:《做主》,但就是迟迟没能完成。不同于《宠》讨论人和人(主要是君臣之间)的关系,《做主》是讨论人和物之间,尤其是在国家的支配下,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和物的关系的展开。
如果有足够的精力,他还计划了解一些其他国家的情况,比如罗马。最近,他和其他学者合作研究第一波斯帝国——约存在于公元前550年到330年的阿契美尼德帝国。有学者发现,和中国的秦王朝的许多做法相类似,波斯帝国也是中央集权国家,所以他们怀疑秦的很多做法可能是受波斯帝国的影响。对此,侯旭东给出的一个佐证是,在甘肃天水一带,考古学家在战国时期秦国墓葬里发现了一些带有波斯风格的器物,说明至少存在一些物质文化上的交流。“所以我们想做一个工作坊,把中国史的学者和研究波斯帝国的学者,包括西方学者聚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侯旭东说,这些以前都是孤立的研究,比如秦的很多做法就是在自己内部去讨论,没有思考它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对其他帝国的情况了解不够,以前也不太注意制度层面有无可能是受外来影响,主要关心的是器物层面的交流。中国史往往还是就中国论中国,现在随着中外考古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可能。
“史学研究,要有一个断代作为基础,熟悉基本史料,以传世文献为主,但同时也要清楚还有什么其他资料,也要有所接触。细读史料的能力是基础。断代之外还应有跨断代、跨国家的努力,才能收获更精准与更通贯的把握。”在研究方法上,侯旭东强调要有“通贯”的视野,对学术史要有充分的把握,不止是具体问题的学术史,还有整个断代史的学术发展史,以及这个断代在20世纪以来中国史演进中的位置,包括对中国史本身的反思,从论断、问题意识,到基本概念、分类架构等,要将自己研究的具体问题和这些看似宏大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样才可以将问题由多变少。为此,研究者需要有宽广的视野与多学科的训练。
他始终记得当年读博士时,年过八旬的何兹全先生总是强调“做学问要像跑马圈地,要有自己的领地”,反复叮咛他“研究大树不要研究到树杈上”。导师的话虽然简短,但却形象精辟,自此深深刻入他的脑海。“为此,我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分析上也更求细致、深入,力争超过这一领域成果卓著的日本学者。”2011年,何兹全先生以百岁高龄辞世,在纪念导师的文章中,侯旭东在深情追怀往事之外,也表达了自己在史学研究上的追求和雄心。而在研究之余,他自谓日常生活平淡无奇,无非是埋首饭浆瓢饮、游走超市菜场。“没有成就出良庖佳厨,但时时感受到单调重复却稳健顽强的生活意义。”
(中华读书报记者 陈菁霞)

原标题:《侯旭东:打捞被遗忘的北朝村民世界》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