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张治读《蛋先生的学术生存》|我和“蛋先生”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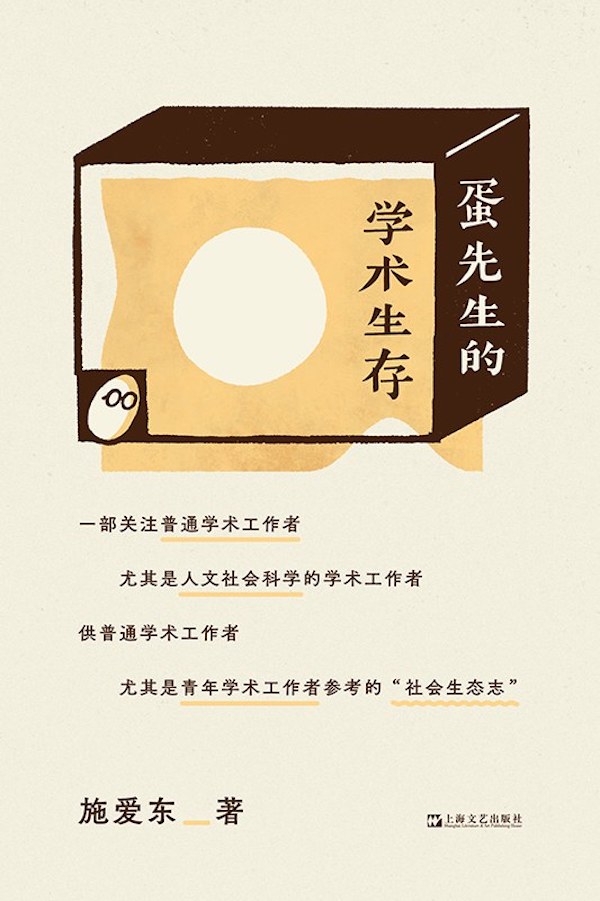
《蛋先生的学术生存》,施爱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400页,68.00元
也不知是不是“围城”的道理无处不在,反正自从我博士毕业,获得了进入学术界的“敲门砖”“入场券”,就无时无刻不想要离开学术界。据说,好像还真有些人能做到,无非三种情况:其一,自己宣布退出学术界,主动、公开地表示谢绝一切学术活动;其二,比较纯粹地消极躺平,另谋生计或是家里有矿,彻底变成“三无”人员(无项目,无论文,无著作);其三,更无可奈何:去世。我仔细揣摩过一番,能说自己是退出学界的,只能是少数有影响力的大佬,人家能那么讲话,必然先在学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何况醉翁之意本不在酒,以退为进,也许效果更佳。至于躺平,我也做不到,不仅因为别无生计,而且家里没矿。第三种情况更不用说了,那本来就是这个时代“无声无光”的悲剧,谁会愿意抛妻弃子、饮恨吞声?纵然天堂里没有体制考核和项目申报,但尘世里还有我买在高点的房贷,需要一直还到我退休后的某年……
这么一想,就是铁定离不开了。好在我也还很乐于做些什么研究和发表些不上不下的东西,结交一些和我同样纠结的学界中人,报团取暖,一起自嘲。因此,也还不算特别痛苦。在单位负责一点科研管理的工作,接触才毕业不久的青年学人机会比较多,也包括平日出差开会遇到的新晋助理教授、副教授,不管前途是否光明,我都觉得他们更加地苦不堪言。名牌高校作为理想的学术界生存场所,现在都在无上限加码地进行高强度考核。很多青年学人博士毕了业就一边要应付备课,一边要拆博士论文拼C刊发表,还要从自己熟悉的那个领域里变出一个新题目来申报项目。如果收获不多,就是“非升即走”;如果成功了,下一步还有新的困境在前头等着:原来的题目做到头了,接下来再写什么成了难题。回想自己的道路,庆幸早生几年,在第一处工作单位度过了我从三十到四十岁的光阴。工作头几年没有什么压力,自己心血来潮,一直搞不在行的翻译和得罪人的书评,被学科同行讥为不务正业,且没有属于自己的代表性成果。后来新领导说不积极申报职称就要清理冗员时,才发现自己连“核心期刊”是啥都不知道,连国社科项目什么时候申报都弄不清,而拿到的项目,又因为看不懂、理不清财务处报销经费的大小规则,索性就不报账,甚至我天真地以为职称的升迁是单位赐予的,而不是申报的。但那时我还算很快乐,非常清楚自己未来要读什么书,积累了很多的想法和研究经验。承蒙师长朋友们关心提携,算是有了一点成果,一次性升了职称,换了工作。被新单位给予太多信任,居然要我管理科研,逼不得已,为了服务他人,才算把各种体制里的门道摸个明白。现在虽然没有了危及生存的压力,顺从于学术研究的尊严和读书育人的志趣,仍会继续努力,但我也不免时时感到些许的悲哀,体会到青壮年时自己身上那种别有追求的气概在渐渐消退了。
以上,是我读民俗学家施爱东老师新书《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产生很多共鸣的一个原因,虽然这些感受不是此书的主题。在我眼中,这部新书不能算是内封里戏言的“儒林葵花宝典” “学术丛林守则”这种类似“黑幕”文学广告词,而应该就是一本民俗学的学术专著。只不过它研究的恰好就是通行言说学术界之崇高与卑下的一种“故事”模本罢了。这原来就是施老师这些年治学的一贯思路。我还清楚记得当年在微博上,他和做当代文学研究的杨早师兄讨论,大意是说,当代民间文学应该有个新视野,就是今天的民间在哪里,比如那时候的微博或是豆瓣,就是民间文学创作的“田野”(参看374页、382-385页)。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关心网络“谣言”的发生机制、豆瓣书评的“一星运动”、微博上限制字数的学术“清谈”,也有样学样地将之视为一种类民俗现象。早在《中国龙的故事》里,施老师就曾设立“‘龙图腾’是学术救亡的知识发明”一章,用社会学、民俗学的眼光考察学术活动某些突出现象背后的通行母题了。其中关于“拿破仑睡狮论”的捏造与流传,有一句总结非常老辣:“故事都是不可靠的,但都是老百姓喜欢听的”。假如你还读过他写的《故事法则》,肯定知道这一切和此书的中心观点大有关系:所有的故事套路,都是特定功能相互制约的最优结果。每一则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都是特定语言游戏中的最优玩法。正如《蛋先生的学术生存》甫一问世就常被人们征引的开篇那节文字(第3页)所说:
传统学术史多为思想史、发展史或者编年史。当我们借助“发展”和“进步”的眼光来回望一个学科的学术历程时,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常规预设,比如:学术发展是在传统继承基础上的学术创新,学术发展是沿着一条从低往高、后出转精的道路不断前进的,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与他的学术贡献大致成正比,等等。在这些预设之下,成王败寇,能够进入学术史大门的永远只是极少数知名学者,而绝大多数普通学者都被排斥在了学术史的大门之外。
可是,只要我们换一种眼光,参照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思想方式,把学术研究看作一种特殊的行业类别,就会发现,作为“学术工匠”的普通学者,他们的行业习俗以及他们所处的学术生态,一样应该得到我们的讨论。
可知此书关注的是普通学者,不是那些真正有资格进入学术史、思想史的伟大人物。这意味着,你不能把学术界里的芸芸众生自我标榜的那点儿发现或发明,当成是评价他在学术上真正成败与否的理由,这在每年因国社科获批项目发榜时刻真实表演着“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有些人看来,自然都会有些扫兴。但我们就此理解了自己在这学术江湖的摸爬滚打、兴衰成败,竟然就如同民间故事里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或是扫灰娘凭借独特的鞋码嫁给了王子,或是种了魔豆的杰克打败了可怕的巨人,虽然没那么起伏跌宕,却一样有着某种可复制搬用的通关套路。也许,认清自己的渺小和普通,比在申报书上写一万字强调自己研究的价值、意义、创新性、前沿性更重要吧。
举个例子,书中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有意义的研究题目却没人去做?道理很简单,“绝大多数学者都只会选择有经济利益的课题、有助于获得学位或晋升职称的课题、能让成果得到顺利发表的课题、能提升学术声望的课题;少数学者会选择那种纯粹带给自己身心愉悦的有趣课题;几乎没有学者会为了一幅理想的民俗学蓝图而选择那些对个人没有多少实际收益的‘有意义’的课题”(33页)。比如“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这种题目,“耗时长,见效慢,枯燥无趣”,高成本,低收益,谁也不愿自讨苦吃。这令我读到此处颇感惊讶,因为我见识过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六大卷《民间文学母题索引》(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以为丁乃通、祁连休诸先生开启山林后必然大有可为呢。如此来看,这种现象恐怕也并非孤立的,想必也常见于其他很多学科领域。
这么一来,什么学术研究的神圣光圈,就都不那么可信了。如同把大到天王老子、下至城隍土地一众神明的崇拜仪规、典礼法器,都视为一种民间约定俗成的话语和习俗一样,学术行业的“祖师崇拜、学术赶集、资辈亲疏、派系与行规、控制与反抗、顺从与革命”云云,不也就是一套某个圈子里的新民俗嘛。作者说,“祖师崇拜”,首先就是一种“半强制性的群体仪式”,其作法的神坛就是“学术机构”,由于共同信仰和仪式将不同代际和存在竞争关系的芸芸弟子团结起来。内部存在竞争,但更重要的使命是抱团对外,使这个神坛得以维持下去,维护着在此传统荫庇下大家的共同利益。令人神往不已的学术之“薪火相传”,往往不过就是“世世代代传香火”的一厢情愿美好祝福。作为扩充学术机构影响的重要手段,学术会议也就首先是一种仪式,用以编织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长幼尊卑排序,很像是武侠小说里的门派大会,确立某种程度团结性和排他性的“圈子”。
门派需要领袖,仪式需要偶像。一代代更替,一代代传承,也一代代的焦虑和反抗。“圈子”自然有其意义,不见得就是树立门墙、固步自封、党同伐异。施老师此书最被人津津乐道、截图转发的,可能要数对当下典型的 “师门微信群”各种现象做出的概括了(122页),他讥之为“丁春秋的弟子群”。但《蛋先生的学术生存》的宗旨并非在于揭露黑幕,我们看到,作为民俗学科富于成就的学者,更是作为这些年关注当代学术生态的知识分子,施老师更在意的,是将这种存在时间不久的门派圈子,区别于具有牢固学术传统的学派圈子,以及由跨学科学术精英长期互动而形成“无形学院”的流派圈子,最后这种圈子是具有理想意义的学术共同体。对此,我深感赞同。我自己虽然也有师门归属(甚至在不少人眼中,我们还算是根柢深厚的大门派),参加师门活动,但从来不喜以赞美自己导师言辞思想为核心话题的圈子生存方式。我引以自豪的是,也结识过好几位来自不同行业、学科而都有真学问的师友,也形成了几个不太一样的日常交流圈子。他们会在我风光的时候来一句冷言冷语的讽刺给我降降温,也会在我低落的时候给以着实温暖的鼓励。拈断数茎须而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难,会受他们一句话而豁然开朗。虽然不常见面,但时而有微信群里的日常对话,不论晨夕省定,兴之所至,不断涌现各种充满智慧的戏谑、调侃机锋,以及深入体己的关怀。不必担虑自己忍不住分享的新发现会被这些师友抢走先写论文,也不会因为臧否人物的直白不讳而被别有用心地截图散播。我想,这应该类似于施老师所说的那种有正面意义的学术圈子了。
除此之外,还有如何宣传造势(学术推广的四种方式,见29页),如何为自己的学术品格立人设,如何搞理论建设、为自己的学派建立合法性,如何设定学术领域的边界,乃至如何进行学术写作,从施老师的专业角度来看,无疑也都是在学术界建立或遵守风俗的手段。他提醒新入行的年轻学者千万小心头顶上压着的学术机制两座大山——“量化管理机制”和“学术评价机制”,此外还有一座隐形的大山,名为“学术创新机制”,前两者损害学者个人健康和幸福生活,第三座大山会损害学术发展本身的正常进程(39-40页)。由此可见,学林的风俗、习俗与种种风气,不免与学术机制自身存在问题的畸形发展方式有些关系。我们当然知道,学术史大浪淘沙,终会将无价值的学术成果全部淘汰出局。但这并不意味着从事服务工作的管理层有资格来充当裁判乃至行刑人,以一刀切的条条框框来敦促、监督乃至审查、核算学术生产的数量、质量、价值、意义,等等。因此,《蛋先生的学术生存》还有一章专门写“学科建设”,其实主要涉及的是关乎学术意义上的软件建设,最可贵的就是一种在合乎学术规范和学科共同体认可前提下进行自由发展的路径。而这种自由的获取,除了依靠管理者高度的领导智慧,也需要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学者的积极行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我们往往都专注于自己论文、著作的炮制,缺少对同行成果的关注和讨论(除非是别有用心的原因)。而之所以普遍呼吁减少对每个人学术产出的量化要求,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学者其实需要互相对话,包括出自真心和实用的互相引用、互相批评。施老师曲终奏雅,在全书的最后环节畅想了各种不同层次学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再次申明那种“无形学院”的圈子理想,使我们相信,即便是人文学术,也不可独坐书斋抱残守缺,而形式上的团队建设其实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没有优秀学者的杰出成果,没有年轻学者的研究热情,没有众多学者的平等交流愿望,那么我们看到的学术界,终将还是会辜负“蛋先生”的一片苦心。
我读后深信,志向远大的青年学者绝不会将此书当成是“学术界登龙术”的引导习得工具。只要这些早被过来人“看破”的规则成为你知我知的共有知识,只要这些共有知识变成了“看破又说破”的公共知识,就可能出现打破常规、破除旧习的希望。因此,我觉得《蛋先生的学术生存》具有《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小孩子把大家心知肚明的真相说出来、说清楚的意义。如此,才有可能去除学术界的神圣光环,减少有损害的影响,回归学术生活所追求的本真目标上去。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