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看人 | 谷川俊太郎专访:“祖母的宇宙快要破碎了”
“祖母的宇宙快要破碎了”
谷川俊太郎专访

谷川俊太郎(1931-2024)
问:首先,我想听您讲一讲您开始写诗的最主要的动力,以及您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格调清新,但内容常常玄秘,又带有一些哲理性的诗风?我知道在日本,您的风格也是独树一帜的,我所读过的西方神秘主义诗歌,就算晦涩难解,也都能看出一个宗教背景之类,而您的诗风非常难以分类、描述,也很难分析,只是给人一种富有东方色彩的感觉。
答:我形成这种风格,完全是无意识的,或者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当然,和我的家庭环境,和日本的人文环境有关。我父亲是个哲学家,我则是家里的独生子。不是说独生子孤单,所以我喜欢一个人思考,而是说,独生子就不会和兄弟姐妹吵架、打架,我的生活里没有纠纷。
问:为什么您专门强调“纠纷”?
答:我不涉入纠纷,和我后来同他人,同社会、组织、集体、集团保持某种距离有关。

问:好像您的母亲是基督徒,您受过基督教影响?
答:不,我母亲不是基督徒,但我父母送我去基督教会的幼稚园,我的确受过影响,那种影响也是无意识的,不直接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基督教里说的“天国”和“地狱”这一对概念。还是小孩时,我每晚睡觉前都会对上帝默默地祈祷,但这也不是因为虔诚,只是出于模仿,老师教什么我就学什么。我后来也从没去过教堂。
关于宗教,你知道日本人大多数信佛,我母亲老家有佛坛,遇到一些节日时,比如在八月十五,一家人都去烧香,这种我都记得。在小学里我还读过希腊神话。如果说宗教的话,那么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都对我的心智的形成起过作用。
问:但您是无神论者?
答:我们家都是无神论者,不过在二战期间,家里曾经贴过一个日本神道的标记,这是因为当时东条英机做首相,命令每个日本家庭都要表达对天皇的忠诚和尊重。

问:战争期间您也接受了很多军国主义教育吧?
答:当时学生都经历了真枪实弹的军事训练,我在班里的成绩非常好,还是班长,但因为胸膜炎,因祸得福,避开了这些训练,也没有上过战场。我父亲是坚决反战的,他在报纸上看到学生低着头向天皇致敬的照片,就骂“真他妈的混账。”后来他还曾经被东京的秘密警察列入了黑名单,这种事都无形地影响了我。
问:所以您也没有关于战争的直接体验吗?在您的诗中看不到战争的影子,而您也没有写过任何相关的回忆文字。
答:是的,我从来没写过战争,像原子弹爆炸这种事,我不在那边,没有体验,可以说跟它完全无关,所以没有资格来写。

问:您的第一本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就奠定了一种基本思路,把人类和地球摆在了一个宇宙中的沧海一粟的位置,我在这部诗集里读到一种急切的超脱的欲望,您好像不希望人们在您的诗中发现具体的历史和时代背景,您的诗,都是“无所指”的,甚至经常是即兴“漫唱”式的。
答:我不想在社会的进程中进行诗歌创作,我要超越它,想触摸、表现宇宙的进程。但是宇宙并非总是遥远的,很大的,就是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所能看见、听见、触及的最近的东西里,也存在着人同宇宙的关系。这是我要写的。
问:我对您的写作过程非常好奇,您似乎是不用构思,事后也不加修改,而全凭灵感创作的。尤其是一些极简诗,例如《Minimal》中的那些。我在田原先生的文章里看到您曾在飞机上用很短的时间,拿圆珠笔写完一首诗。
答:正是为了让你感受到这些,我才努力地、反复地修改。我写完一首诗的底稿,一般沉淀一个月后修改,一直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才发表。在飞机上写的那首诗,修改不多。底稿完成后就拿去发表的情况不多。我修改的基本上都是助词,日语是被助词束缚的语言,助词决定一句话的命运,修改之后不只节奏有了变化,意思也大不一样了。
《Minimal》里的诗很短,修改都很少。你说觉得我写得轻松,我很高兴,一个写作者不应该把他的痛苦艰难都表现在最后的作品之中。最理想的状态,一首诗是一朵花,我们看到鲜花的样貌,心头一亮,但我们不知道它从花苞开始开放的漫长的、艰难的过程,这是我写作的梦想。

问:在《自我介绍》这部诗集中,有12首一组的《少年》,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组诗,我在其中读到一些朦胧的主题:首先是成长,在许多岔路面前彷徨,然后有同母亲的关系,然后爱上音乐,然后有友谊,然后恋爱,等等,最后有个象征性的“告别”,但是每个主题都是若隐若现,不那么明确的,可以请教您写这组诗的动机以及创作过程吗?
答:我很在意这一组诗,你的理解都对。我的写作动机来自音乐,一支曲子,这是一位朋友,作曲家中川俊郎,给一个中国茶的广告作的曲子,没有歌词,在听完这个曲子后,不可思议地,我就创作了这一组诗,先是三四首,两个月后成了十二首,在这之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写作本身也是无意识的。这组诗发表在一个月刊上,十二首发表了一年,这本刊物是筑摩出版社的社刊,名字就叫《筑摩》,读者有限,我的诗主要发表在《现代诗手帖》这本专业诗歌刊物上。
我受音乐的印象很大,主要是西方的古典音乐,贝多芬之类。在我开始写诗时,我都没觉得诗能跟音乐相比。
问:在《少年》组诗之11中,您写到“纵使天才也不会创作音乐/他们只是对意义堵上耳朵/却对源自太古的静谧/谦恭地竖起耳朵”。这四句很有感染力,您是不是将做诗也与音乐等量齐观,认为它们都是对神秘的谛听,而不是穷追意义的创造行为?
答:是的,我对诗歌的定义是:一种超越语言的语言。日本有位诗人兼评论家大冈信,做过这么一个精彩的比喻:诗歌就是一个磁铁,放在桌子下面,你看不见,而只能看到外面的铁屑游动、转移、汇聚、飞舞。

问:另一首我喜欢的诗是《自我介绍》,它与希姆博尔斯卡式的哲理自嘲诗十分相似,您有没有受过她的影响?您有一些风趣的讽刺诗,比如2009年创作的《再见》,用犀利的自嘲,审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瓦解人类自己赋予自己的崇高地位。您在写作讽刺诗时通常会有怎样的构思?
答:我写所有诗基本都不分类,不会把这首看作抒情诗,把那首看作讽刺诗。你说的两首诗都是我比较在意的。我没有受过希姆博尔斯卡的影响,但是在偶尔读到她的诗时,心里会想:嗯,这个诗人离我比较近。
问:您受过西方诗人影响吗?
答:两个法国诗人:普雷维尔和弗朗西斯·蓬热。普雷维尔的诗很通俗,像儿歌,日本人都爱读,蓬热的诗在日本影响一般。我写过一本《定义》,就是直接受到蓬热影响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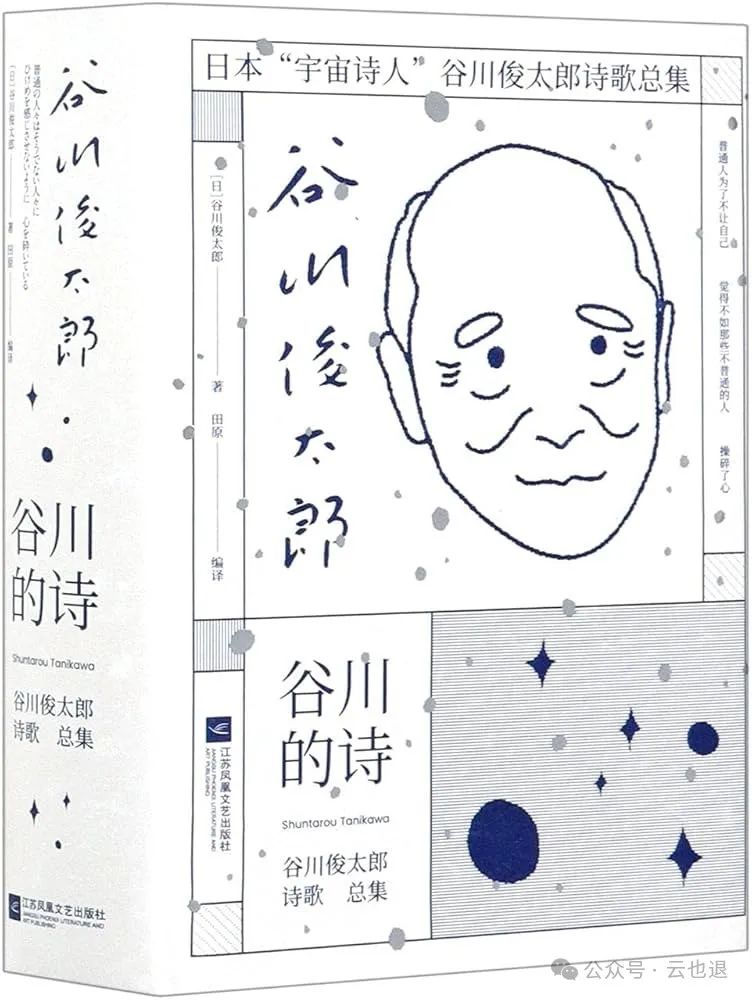
问:在日本,儿歌、童谣是否流行?有许多的儿歌诗人吗?
答:教育界有人写,诗人写得少,你说的儿歌,往往作为绘本来卖。写的人很有限。我出版过300多本绘本,我写文字,别人绘图,我的生活主要靠绘本的版税收入来支持,比其他诗歌赚得多。儿歌是个专业性的写作,有固定的对象,我在写的时候,并没有过于强烈的“我是为孩子而写”的意识。
我写儿歌,念起来朗朗上口,是为了让语言回归其音律性。日语是不能押韵的语言,通过儿童诗的写作,扩大日语书写空间,也设法让母语押韵。但这个努力其实是失败的。
问:《自我介绍》这部诗集中有太多的佳作,《在纽约东二十八街十四号写下的诗》以奥登开头,后边写到了电视、收音机、玛丽莲·梦露,从“在游客支票上/一次次签下自己的名字”联想到“人如果老是现在的样子/还能获得拯救吗”,接着进入两段思辨,最后一段又来了个大转折,做诗人从想入非非之中回到现实。您是怎样写这首诗的?
答:这真是一首“纪实诗”,是在1970年代末,我应邀参加了纽约诗会,日本一共有三个人,另两人一个是田村隆一,荒地派的重要诗人,我在诗中都提到了,另一个是片桐。纽约诗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诗歌活动之一,请来的都是大诗人,比如诗一开始写到的W.H.奥登。我写奥登的动作都是纪实的,在我的旅馆房间里有个小电视,在里面我看到了梦露。
“人如果老是现在的样子/还能获得拯救吗”,这句诗是一个提升,从现实提升到灵魂的高度,至于怎么写出来的,我答不上来。

问:《语言的胎盘》这首写给北岛的诗,是2010年9月在香港凯悦酒店完成的,您用十分婉曲的笔法写出了北岛和《今天》在汉语艺术上的贡献,但似乎又暗示他可以做的仅限于语言的边界之内。这首诗是在怎样的机缘和心境之中写的?您和您的老朋友大冈信似乎也都是北岛的好友?
答:我知道北岛的名字很长时间,但碰面的机会不多。诗歌本身就是语言,无法抵达语言之外的地方。十一年前,北岛到东京,邀请我和大冈信,以及白石甲寿子同他同台朗诵。2010年,首届“国际诗人在香港”邀请了我,在那里我跟北岛有了交谈。
问:可否请您简单介绍下您所写的史诗?您有没有写长诗的计划?
答:我写过长诗,比如《临死船》,也已翻译成了中文,长诗是有故事性的,但是不多。写一个关于死去的人坐的船的故事。这首诗同日本传说什么的都没关系,完全是自己的想象。我要探讨的是:人死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呢?

问:您说过,中日两国的诗歌创作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缺少读者,缺少创造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首鼠两端。就您对中国诗歌的了解,中国传统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与制约,与日本传统诗歌对日本现代诗人的影响与制约,哪一个更大一些?
答:我不识中文,对中国诗歌太不了解。不过现在,中国诗歌的情况与日本诗歌完全一样,都受到西洋诗歌的巨大影响,也都有一些诗人在设法结合本土和西方;日本现代诗人中,就有少数同时写现代诗和俳句,设法把短诗、俳句与西方诗融合起来。而且,中国的唐诗对日本的影响很深远,现在还有几位诗人和小说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延续那种古老的传统。
新书《作家酒馆》上市:

草婴读书会·云也退的“作家酒馆”共读群
(欲参与者可于我公微私信)
当下共读1.卡罗尔·希尔兹《拉里的家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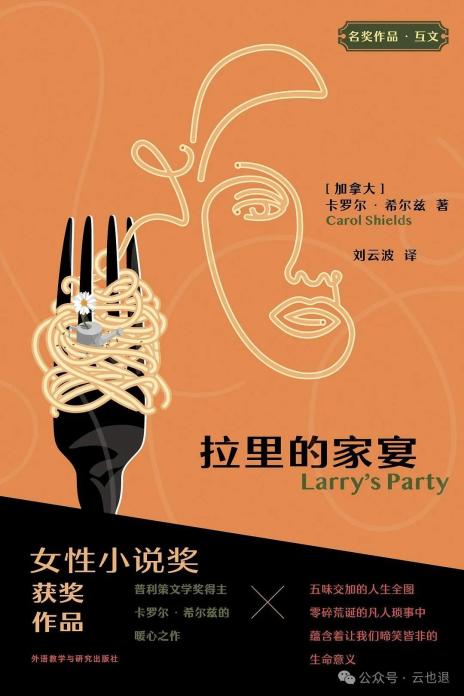
当下共读2.君特·格拉斯《铁皮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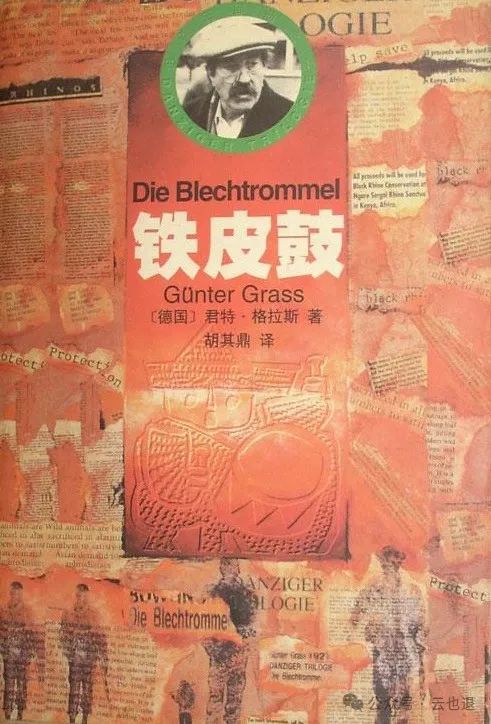
原标题:《看人 | 谷川俊太郎专访:“祖母的宇宙快要破碎了”》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