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停更三年后回归,我们仍向往李子柒式的生活
11月12日,停更三年的李子柒,终于更新了一段制作漆器的视频,仍然是熟悉的风格,三年过去,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

出自:李子柒视频
不变的还有她在全网的影响力。新视频发布没多久,微博上的播放量超过1亿。不只在中国,停更的三年里,李子柒在YouTube上的订阅增长了500多万,超过了2000万之多。
要知道,她发布在YouTube上的视频,都是中文字幕,没有翻译。即使这样,也挡不住全世界网友对她的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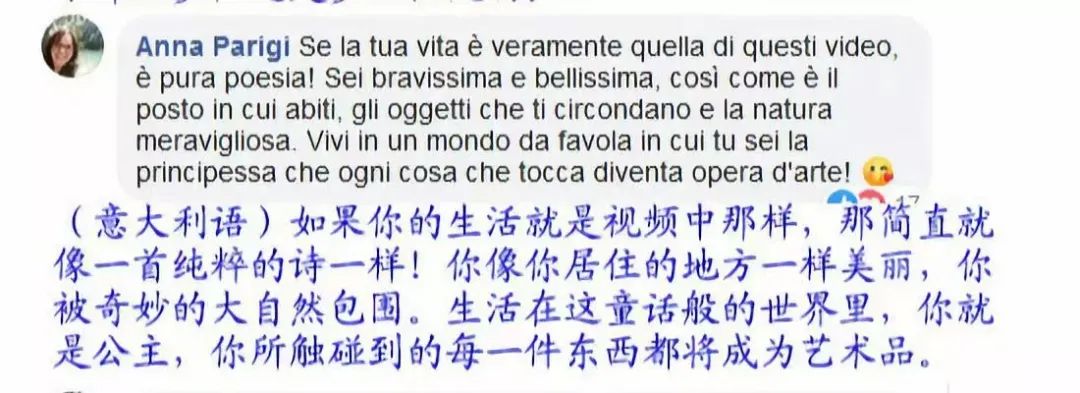
图片来自网络
为什么几年过去,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的情绪与关注点也发生了转变,李子柒仍然是无法替代的呢?
原因恐怕相当之多,但一定有这么一项:那种远离喧嚣,专心生活、专心劳动的姿态,不论在任何时代,都是人内心所向往的一片桃源地。
在工具理性横行,利益驱动一切的城市里待久了,人就容易忘记世界上还有各式各样的活法,容易变得失去耐心,无法长久地沉静在一件事物中。
但那样的生活仍存在于世间。今天我们给你分享一个造纸的手艺人的故事。这恰恰是一种“李子柒式”生活的代表。他们认可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从做工中得以获得真正的价值认同感和意义感。也是一种值得一过的生活。
下文选自《纸上》一书,篇幅所限有所删减。
01
如果一张元书纸开口说话
它发出的一定是水的声音
十月,霜降。
阳光从天窗倾泻而下,像一场金色的雨,落在富阳元书纸古法造纸第十三代传人朱中华身上。站在浙江图书馆地下一层古籍部金色的雨里,隔着一层玻璃,他看到另一些金色的雨,落在阅览区的仿古书柜和桌椅上。影影绰绰的光亮,清晰的怦怦怦的心跳,都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
一双戴着白手套的手,将乾隆版《四库全书》中的一函在他眼前徐徐打开,两百多年前的旧时光呼啸而来。两百多岁的书,新得跟婴儿一样,闪烁着玉石般的润泽。

出自:李子柒视频
鼻尖传来一缕熟悉的气息,是他已闻了四十八年的气息,空谷、阳光、雾气、溪流、毛竹的气息,一张竹纸的深呼吸。
朱中华手心发热,耳朵里嗡嗡作响,眼前飞速交叠着一些幻象——龟甲、青铜、竹简、丝帛……荒野中,一个无名氏从一张破竹帘上轻轻揭下一层被太阳晒干的纤维物,惊异地发现可以在上面写字……灯影下,一个叫蔡伦的男人,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原料,挫、捣、抄、烘,成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真正的纸……船一样的纸,承载着唐诗宋词书法绘画,悬浮在浩浩汤汤的时光之河……一千多年前的某个元日,北宋皇帝庙祭,风轻拂真宗手里的祭祀纸,散发着竹子的清香。这张从江南富阳跋涉千山万水抵达京都的元书纸,在风里舞蹈,召唤着祖先、神灵,以及大地上的一切……
“我能把手套脱了,用手摸一下吗?”
一段短暂的沉默。
“好。亲手摸过,说不定您真能把修复纸重新做出来。”
轻轻触及纸页的一刹那,食指中指和拇指指尖上传来丝绸般的凉滑,轻轻摩挲,则如婴儿的脸颊,细腻里又有一点点毛茸茸的凝滞。
“的确是清代最名贵的御用开化纸,洁白坚韧,光滑细密,精美绝伦。”
《四库全书》从修成至今已有两百余年,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其中文澜阁本屡经战火,后递经补抄,基本补齐,就是此时此刻眼前的这一部。然而,当年所用的开化纸,世上已经没有人能做得出一模一样的了。
可他觉得,这张消失在历史深处的纸离他无比的近,像他失散多年的一个亲人:是一个婴儿,也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
“它离我不远,我会把元书纸做得像它一样好。我尽力。”
富阳大源镇朱家门村,逸古斋古法造纸坊。四十八岁的朱中华站在站了四十八年的纸槽前,听见隔壁传来淅淅沥沥捞纸的水声,回响了一千多年的水声。
“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曾经,富阳的山山水水里,镶嵌着无数手工纸槽。元书纸古称赤亭纸,是以当年生的嫩毛竹作原料,靠手工操造而成的毛笔书写用纸,主要产于浙江富阳,北宋真宗时期被选作御用文书纸。因皇帝元祭时用以书写祭文,故改称元书纸。又因大臣谢富春倾力扶持,又被称为谢公纸或谢公笺。
朱中华家族中最辉煌时,是抗战前,太公朱启绪拥有八个纸槽、五十个工人。而此时,曾经日夜回响着淅淅沥沥捞纸声的朱家门村,朱中华成了最后的、唯一的坚守古法造纸的人。

出自:李子柒视频
朱中华从裤袋里摸出一盒烟和一只打火机,点燃了一根烟。阳光从屋顶的塑料棚布间漏下来,将一个中年男人不高但很壮实的身影投到积水的地面上。深秋的寒意从脚底升起,他只穿着格子棉衬衣和单裤,却一点都不觉得冷,这几乎是他常年的衣着,砍竹、捞纸、晒纸、送货、谈生意,都这么穿。
其实他最喜欢的是那套米色的唐装,穿起来站在纸堆里写字,很像一个文人,但他怕村里人“晕倒”,从来不穿出门。烟雾绕上他长着老茧的食指和中指,绕上鬓角的白发,绕上紧皱的浓眉,挡住了他看向纸槽的目光,如时常挡在他眼前的一个个“难”。
朱中华相信纸是会呼吸的,有生命的,甚至相信,纸是有灵魂的。据《天工开物》记载,从一根竹子到一张纸,要经过砍竹、断青、刮皮、断料、发酵、烧煮、打浆、捞纸、晒纸、切纸等七十二道工序,耗时整整十个月,像孕育一个胎儿。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便承载着生死悲欢、沧海桑田,那么重,那么痛,那么美,它怎么可能顽同木石?
朱中华所有的努力,就是想用竹子做出世界上最好的纸,让会呼吸的纸、让纸上的生命留存一千年、一千零一年、更多年。
可是,很难。如今的人们,往往只关注纸上的字,关注是谁的画谁的印章,是否有名,有谁真正注意过一张纸本身,它来自哪里?如何制造的?能活多少年?谁在担心一张纸会永远消逝,一门古老的手艺将无人传承,一种珍贵的精神将永远绝迹?
如果一张元书纸开口说话,它发出的声音,一定是水的声音,水声里,是比古井更深的寂寞。
《四库全书》的触觉还在指尖萦绕,他掐灭烟,将双手慢慢伸进纸槽,看到遗失在时光深处的老精魂,在纸浆水里渐渐醒来。
02
“洁白的纸上,
会长出一轮一轮的年轮”
五月,小满。
穿过荒草的时候,九岁的朱中华和双胞胎弟弟朱中民同时瞄见了三颗鲜红欲滴的覆盆子躲在一棵毛竹的根部。覆盆子的鲜甜同时抵达两个男孩的舌尖时,他们听到了小满节气后父亲的第一次砍竹声。
当当当当当……
一共十刀。
唰啦啦唰啦啦……
一小片天空被毛竹梢搅动了几下,随着一棵毛竹慢慢倾斜、倒下,一小片天空就大出了一点点,预示着一棵毛竹在天空中消失,投胎到大地上做了一张纸。毛竹倒下时伸出绿色的手,和其他依然挺立的家人说珍重,然后砰砰砰投入了山涧——朱中华的父亲和伙计们早已铺设好的竹道上。

出自:李子柒视频
“斩竹漂塘”是《天工开物》中古法造纸的第一步。芒种前后上山砍竹,每根竹子截成五到七尺长,然后就地开挖水塘,将竹段在水里浸一百天,取出时用力捶洗、软化。竹子与木材造出来的纸张,最根本的不同是,木材纤维中的木质素会氧化,纸张会泛黄,添加酸剂则更严重,而竹纸纤维密实,薄如蝉翼,柔如纺绸,易着墨不洇染,写字则骨神兼备,作画则神采飞扬,耐贮藏不招虫,这些特性,使竹纸成为纸中上品,得誉“纸中君子”“千年寿纸”,是文人墨客的最爱。
小满前三天,九岁的朱中华兄弟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看见父亲不高但很壮实的身影穿过细密的雨丝,很快消失在一大片绿色的寂静里。父亲同样穿着蓑衣戴着斗笠,脚上是草鞋,绑腿的布袜是母亲用厚实的布条子细细缝制的,防止荆棘和蛇虫。
古老的造纸图谱上,砍竹人都是壮年男子。砍竹是有诀窍的。有经验的砍竹人,要提前看山势,为毛竹快速顺势下山找好一条路,用几根老毛竹铺在坡上,方便竹子滑动。砍竹时,第一,要找那种竹梢刚冒出笋头的嫩竹,如果青叶都长出来了,竹子就老了,胶质包浆少,纸的紧密度就不够;第二,砍竹时,每一刀都要均匀,竹根要砍平整,硬纤维都要砍断,否则刮竹皮的人是要骂人的,不仅要花工夫清理,还会伤手;第三,要让竹子往一个方向倒,方便集堆打件;第四,打件时,要仔细,上面一人砍,下面一人将三四根竹梢头捆在一起拖向山脚,如果打不好,竹子滑到中途就散掉。
矮矮壮壮的父亲放下砍竹刀,走到溪边,双手掬起溪水喝了几口,抹了把脸,向山脚张望了一眼。晌午到了,该是女人们送饭上山的时辰了。从小满到夏至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无论阴晴,朱家门村的后山上一直会回荡着当当当当的砍竹声。一个月里,父亲身上没有一天是干的,或被雨水淋湿,或被汗水浸透。家里穷,只有两套衣服,夜里等炭火烘干,第二天接着穿。
覆盆子的酸甜里,朱中华兄弟年年跟在父亲身后做小帮手,但没有想到,父亲当当当的砍竹声在他们十二岁那年戛然而止——在一场农事中,父亲不幸触电,留下妻儿撒手人寰。
十六岁,兄弟俩师从二伯做纸。从此,村里人说起双胞胎兄弟,眼前会浮现日夜穿梭在造纸坊的壮实身影,还有两双一模一样的、黑亮的、忧郁的大眼睛。
十九岁,兄弟俩一人砍了一万斤竹子,自己刮皮,自己做纸,借用别人家的纸槽、晒纸房,做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一批纸。
多年后,朱中华陪同中国科技大学专家考察浙江民间手工造纸时,在温州泰顺一个很深的山坳里,突然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那个和他同龄的造纸人,一个人砍竹,一个人刮皮,一个人捞纸,一个人烘纸,所有的工序都只有他一个人在做。空山寂静,朱中华站在远处点起了一根烟,静静看着夕阳下那个弯腰捞纸的剪影,就像看到了自己,眼眶渐渐湿了。

电影《小森林 夏秋篇》
“老哥们,多吃点酒多吃点酒!”
大年初一,堆满元书纸的厅堂中央,摆了一张圆桌,圆桌上堆满丰盛的菜肴。一桌年纪与他相仿的砍竹人围桌而坐。朱中华线条圆润的国字脸上堆满了笑意,一手香烟,一手一碗自家酿的葡萄酒,一扬脖,酒碗就空了。春寒料峭,他仍然只穿着格子棉布衬衣。
如果朱中华是海底的拳击蟹,这些人就是被他牢牢“抓”在手里当拳头用的海葵。是砍竹、刮皮的伙计,也是几十年的兄弟。农历新年的第一场酒,只是个起头,一年里要请他们好多次,过年吃一次,开工吃一次,上山前吃一次,上山后天天吃,家里做好酒菜,碗筷酒盅全套备好连同一人三包香烟,一拨送到山上,一拨送到山脚。
朱中华脸上的笑,是真诚的,心里却是酸的。此时,在他左手边吆喝着划拳的四个同村兄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说是来挣钱,其实是来帮他。砍竹的壮年人越来越难找了,兄弟们也都年已半百,一人一天只能砍一两千斤。而技术性更强的捞纸、晒纸,会做的人更少了,工人工资越来越高,人越来越难找。也有年轻人想来当徒弟,过来一看,村里别人家都造了高楼别墅,朱中华兄弟俩还住着旧楼房,觉得没啥前途,说“再说再说”,就再也不见踪影了。再过几年,恐怕连给竹子刮皮的人都请不到了。
一场酒接着一场雨,第一场春雨后,头一茬新笋一冒头,朱中华就得挨家挨户找人了。嫩竹越来越少,有的竹林长久没人打理,春天一来,笋就被挖掉了,能长成嫩竹的寥寥无几,同样面积的竹林,能用的嫩竹只有从前的十分之一。有的竹林主人以为朱中华挣大钱了,便不肯按平常价格卖给他。
求人,全是求人。
有什么办法吗?有。降低要求,批量生产,成本就少了,钱就能多赚一点。可是,怎么能眼睁睁把会呼吸的纸做成死的纸呢?不行,要做,就做最好的纸。
二〇一七年小满前三天,朱家门村后的山里,又一次响起了砍竹子的当当声,又有一些竹子,将带着一种使命滑向山脚,如同多年前双胞胎兄弟曾经采摘覆盆子的那棵竹,只剩下一截短短的竹根。再过一个月,山谷会安静下来,更多新鲜的断竹根会和它不远处很多枯黄的断竹根一样,在竹节里盛上一场雨,映入整个天空和竹林,像一只只深情凝望的眼睛。
一棵竹,在一个个深情凝望里,经过整整十个月的孕育,将以一张元书纸的生命形态重新启程。洁白的纸上,会长出一轮一轮的年轮,在许多生命无法抵达的时空里,继续延绵一千年,一千零一年,更多年。
03
“请您继续做下去吧”
江南的大寒节气,通常并不像这两个字眼那么凛冽,然而,假如冷空气从北方长驱直下,到了夜深人静时,隆冬就会在每一个村口提前降临。
都睡了,连狗吠声都已潜到夜的深黑处,而一场三个人的煮料大战正如火如荼。

出自:李子柒视频
朱家门村石桥下,二十五岁的书画专业硕士生朱起航双手紧紧抓着破裂的橡胶水管,感觉到十个脚趾正传来一阵阵刺痛。从煮料皮镬里抽出来的水不时从破裂的水管里喷出来,已将他一身运动服浇透,灌满了球鞋,在零下两度的严寒里开始结冰。他的平头短发上停满了水珠,像一丛雨后的剑麻,白皙瘦削的脸上,是比脸色更白的嘴唇,一对黑色的眸子在黑夜里闪闪发亮。每一秒,他都想将水管扔掉,飞奔回家冲到热水龙头下。可是,不知为什么,水管像长在了手上。
他咬了咬嘴唇,一声不响,就像平时跟伯父朱中华学捞纸、晒纸时一样。
《天工开物》中制竹纸的第二个步骤是“煮楻足火”,将竹料去皮,拌入碱性的石灰水,发酵后,一捆捆码在巨大的锅中,足足六层,蒸煮八个昼夜,除去木质素、树胶、树脂等杂质后,放入清水中漂洗,再浸入石灰水,再蒸煮,如此反复进行十几天,直到竹纤维逐渐溶解。
在朱起航的伯父朱中华眼里,纸质的根本不同,就在这发酵和煮料里。
“酿酒”,是伯父常用的一个关键词。像酿酒一样,古法造纸也有极高的科技含量,比如烤竹料时,温度不超过九十度,要花三天三夜慢慢烤熟。发酵时,需天时地利,更需虔诚之心,就像小时候,奶奶只准他将耳朵贴在酒缸外听,不能出声,不能惊动酒神。
他常看到水汽弥漫的竹料池边,伯父掀开一层层塑料薄膜,满脸喜色地掰开一团竹料,抽出一瓣竹片,在阳光下举起——一团洁白的、毛茸茸的菌丝,慢慢舒展开身子,像一个婴儿第一次舒展手脚。他说,这就是纸的胚胎,纸的精灵。
他看菌丝的眼神,像看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比看他这个侄儿、看他在外地读书的两个亲儿子的眼神更加温柔。
“玉化”,是伯父形容一张手工元书纸生命过程的另一个关键词。机器做的纸和手工做的纸,到底哪里不同呢?机器造纸,没有经过石灰水的浸泡,是不含钙的,而手工竹纸经过石灰水浸泡,纸浆用手工一下一下打出来,使得纤维帚化,产生叉状的不规则花纹,形成活性状态的碳酸钙,于是,一张纸便会呼吸,便会产生光泽,一个生命体就活了。而追求效益和利润最大化的机器造纸,是造不出这样的纸的。“纸寿千年”说的就是手工纸。

出自:李子柒视频
伯父说,一粒捞纸房的灰尘里,就有一万个生命体、一万个宇宙,一门古老的技艺里,有难以言传的玄妙。越钻进去,他就越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可是,“就算只能做两刀纸,也得用完整的古法技艺做出来!”
伯父对朱起航说这些话时,有时正蹚在溪水里翻洗竹料,有时正挥汗如雨地斫着竹料,有时就站在大雨里一捆捆码竹料,有时在纸槽前捞纸,有时正往炉火里扔一块柴。
水抽完了,朱起航抬起冻得发麻的双脚,跳进了两米多深的皮镬,像跳进一口井,抬头看见了一个浑圆的天空,天空中出现一双手,捧夹着一捆竹料向他递过来。仰头,伸臂,接料,弯腰,码料,如此反复,整整五层,一层五十三捆或五十七捆,要先盘算好,一圈一圈码紧,否则煮的时候会散掉。两个伙计递料,他码料,要一整个半天,近五个小时。腰、手臂开始痛的时候,朱起航忘记了脚痛,也忘记了自己还是个大学生。
皮镬下第一朵火焰舔上锅底时,朱起航像被这个寒夜唯一的暖意舔了一下。煮料的火是要持续的,先烧六个小时才能将水烧开,这六个小时里,人不能离开,要弓着腰不停地往炉里添柴。
伯父朱中华让他守的这团火,曾经熄灭了整整一年。
原材料不够、人手不够、经费不足、了解手工竹纸的人太少、市场太小,都是朱中华的一个个“难”。一年忙到头,产出的手工竹纸只有五百刀、五万张左右。
六年前的初夏,朱中华天天淋雨砍竹子,终于病倒了。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再次回到朱家门村,朱中华的脚步在捞纸房前犹豫了片刻,转身往家里走。家在一个斜坡上,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脚步被什么扯住了,很重很重,把心都扯空了,走几步便停下来,手撑着腰大喘几口气。太难了,太累了,算了,不做了。
那一年,朱中华总觉得自己的耳朵出了什么问题,夜深人静时,耳边会响起一些声音:当当当当,唰啦啦唰啦啦、叮叮咚咚、淅沥沥淅沥沥……暗夜里坐起,点燃一根烟,没有一丝风,长长的烟灰会突然断落,他想,那些声音是真的来过。
一年后,在一家光线暗淡的素食馆里,一个比朱中华小五岁的兰溪男人坐到了他面前。两个人吃了简单的素食,喝了很多茶。朱中华聊纸、聊茶,兰溪人聊文房四宝,聊自己白手起家的建筑业,谁也没有提“帮”这个字。
朱中华说,我的祖宗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才将火烧纸变成文化纸,却从我手里断送了,我也不想,但真的做不下去了。
兰溪人说,我从小喜爱文房四宝。一幅字画能传得久远,首先纸要好,但现在多少古字画都只有摹本了,太可惜了。文化是要靠实物传承的,比如纸,比如建筑,假如我造的房子,最多只能存活一百年,那我岂不是罪人?
“请您继续做下去吧。”他说。
不久,这个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帮”字的兰溪人,将一笔经费打了过来,请他定制一大批元书纸。此后,他们每次见面依然淡淡的,并不亲近,但朱中华觉得生命里多了一个兄弟。
弟弟朱中民从南京打来电话,说:“中华,经费有困难,我来。找人有困难,我把儿子起航交给你!”
砍竹声再一次在朱家门村后山响起。
又有一天,来了另一个外乡人。中国科技大学历时九年调研中国传统造纸术的汤院长,让朱中华又一次深切感到“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幸福。在浙江几十个纸种的调研中,朱中华免费给他当司机、翻译,车开了四万公里,他循着那些叶脉一样的公路,慢慢触摸到了古人留在大地上的根,找到了造纸术百变不离其宗的奥秘。而汤院长在他眼里,是老师,亦是兄长。

出自:李子柒视频
在朱中华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支撑他的,还有一帮意想不到的“兄弟”。一个秋天的下午,他自己设计的晒纸用的烘缸从外地运到了村里,三千多斤的钢板,从路口运到老房子里,有五十多米的距离,需要在地上垫四根钢管当滚轮用,几个人分别扶着烘缸两边,其余的人在后面往前推进。这是一项很危险的活,如果用力不均,三千多斤的钢板便会倾斜,砸到人,以前出过这种事。
那天朱中华叫了六个伙计一起,心里有点担心人手不够,但还能叫谁呢?烘缸从拖拉机卸下时,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正在村口闲聊着的同村人,呼啦啦一下子拥了过来,有七十多岁的老人,有二十多岁的小伙,一共十五个人,都过来相帮了。两个老哥经验丰富,在前后指挥,其余的都卷起袖子,六个人在两边扶,七八个在后面推。这些人,平时跟他并不亲近,好像有时还能感觉到他们目光里的鄙夷。五十多米的路,烘缸艰难地挪动着,朱中华感到眼眶一阵一阵发热。
烘缸安放好了,朱中华招呼大家留下来吃饭。他们摇摇头笑笑,说,不用,你忙。
水终于开了,朱起航感觉特别饿,从柴火堆里扒拉出一块烤红薯。火光映照着袅袅的白气和红薯瓤的美丽纹理,让他想起儿时记忆里一张最美丽的纸——堆满元书纸的堂屋前,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兄弟,同时将手里燃着的香烟搁到了烟灰缸上,四只长满老茧的大手,一起徐徐铺开了一张大纸,竹纸晶莹剔透,薄如蝉翼,纸下的图案一清二楚,而纸的表面在窗口透进来的微光中,闪烁着玉石般的光泽。
“这张纸起码有四十多岁了,当年有人临摹《兰亭集序》,用的就是这类纸。”伯父朱中华说着,将鼻子凑到离纸一厘米的地方,深深吸了口气。
“我能做出来。”父亲朱中民说着,也将鼻子凑到离纸一厘米的地方,深深吸了口气。
他们嗅着纸,像两个犯了烟瘾的老烟枪。
他们谈论纸,如同在酒桌上谈论一坛刚刚启封的陈年佳酿。
本文摘编自

《纸上》
作者: 苏沧桑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十月文化
出版年: 20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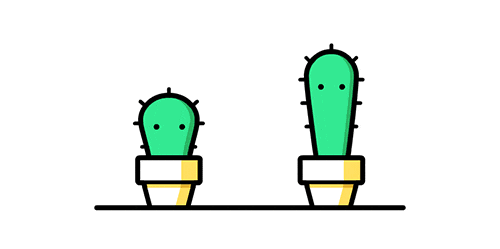
编辑 | 轻浊、飞起来的各种东西
主编 | 魏冰心
原标题:《停更三年后回归,我们仍向往李子柒式的生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