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曹寅评《海洋、岛屿和革命》丨非东非西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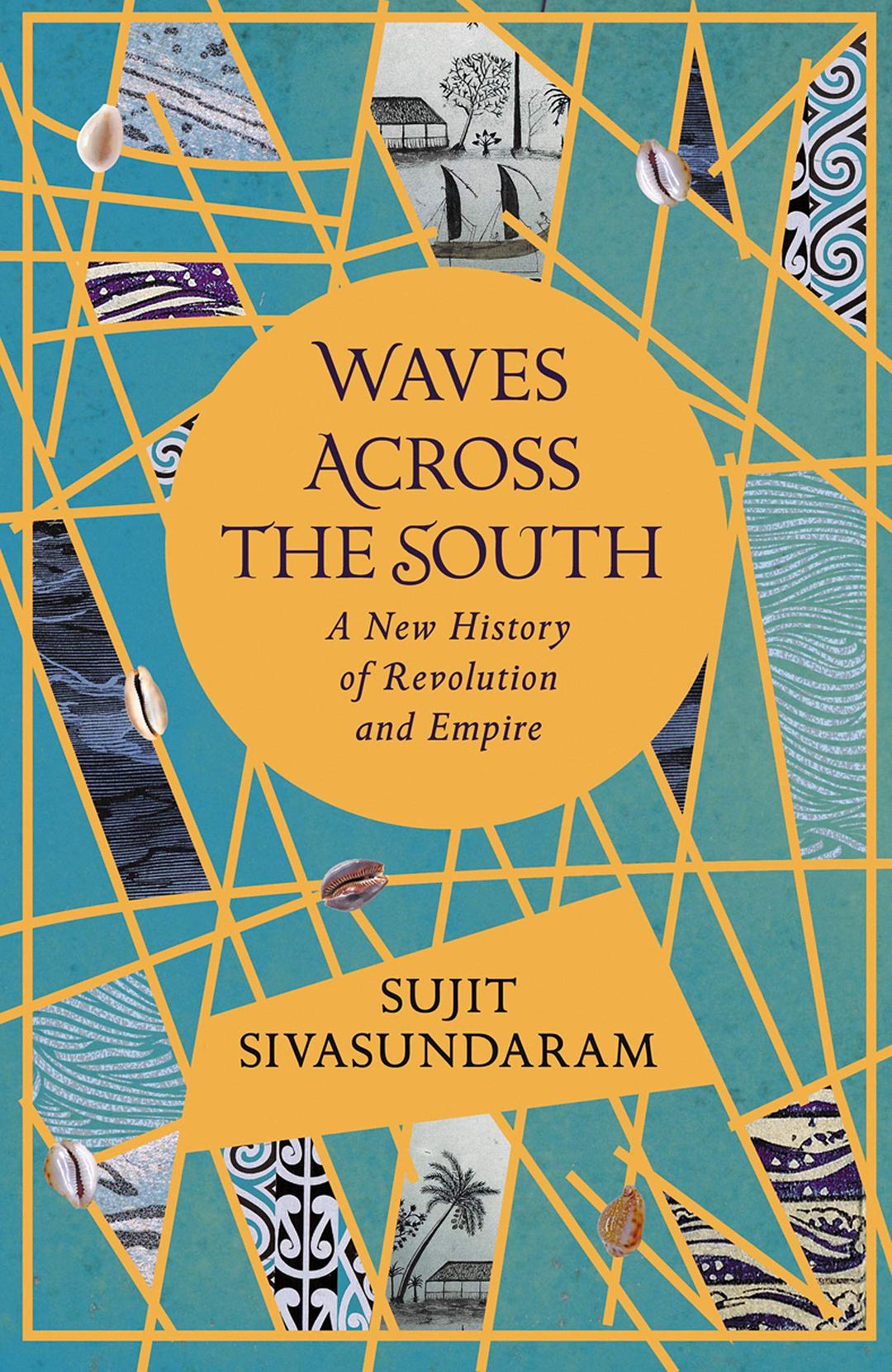
Sujit Sivasundaram, Waves across the South: A New History of Revolution and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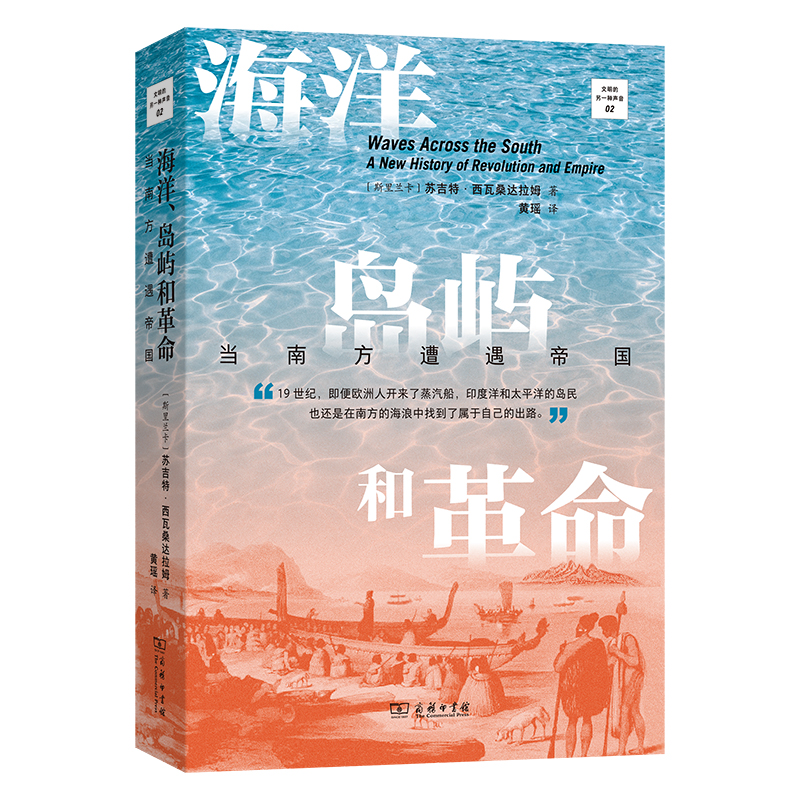
《海洋、岛屿和革命:当南方遭遇帝国》,[斯里兰卡]苏吉特·西瓦桑达拉姆著,黄瑶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9月出版,477页,95.00元
2024年9月,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博士生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分享了她的博士论文。报告人的研究主要涉及十九世纪初智利铜矿向亚洲的出口。她用非常翔实的数据展示了智利出产的铜是如何参与到中印两国的贸易之中的。在交流互动环节,有听众指出以往关于近代中印贸易的研究大多局限在中印两地的商品(鸦片与茶叶),智利铜的研究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联结印度洋、南中国海和南太平洋的全球贸易网络。同时,大家也认为如果能在纯粹的数据之外,增加一些航行在这些大洋上的商人和水手的故事,那么会是一个更加精彩的研究。
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西瓦桑达拉姆(Sujit Sivasundaram)在其《海洋、岛屿和革命:当南方遭遇帝国》(Waves across the South: A New History of Revolution and Empire)一书中就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788年,一位名叫彼得·狄龙(Peter Dillon)的爱尔兰人在法国殖民地马提尼克(位于加勒比海的一个海岛)出生了。成年后,他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并参加了1805年的英法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狄龙作为一名私商,开始前往太平洋寻找商业机会。他在1808年至1809年期间居住在斐济,与周边的太平洋岛民建立了联系,并学习了他们的语言。之后,他便往返于澳大利亚悉尼和印度加尔各答之间,向太平洋岛民兜售西方武器,同时为加尔各答的欧洲人提供南太平洋上的香料和木材。
到了1820年代,狄龙决定将他的生意范围扩大,参与当时利润极高的智利铜贸易。狄龙租下了一艘名为“圣帕特里克”号(St Patrick)的商船,将其注册为智利籍。1825年,“圣帕特里克”号满载智利铜,从智利港口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出发,驶往加尔各答。这艘船上的乘客包括了二十名英国水手。这些英国人之前曾经作为雇佣兵,参加了智利的独立战争,因此宣称自己是归化了的智利公民。此外,当“圣帕特里克”号驶经新西兰和其他南太平洋岛屿时,陆续有十一名土著岛民自愿加入了这趟旅程。这些土著怀着各自目的,希望这趟前往加尔各答的旅程能够为他们带来财富、先进的武器,以及政治地位。在西方人利用岛民的航海和捕猎知识进行殖民扩张的同时,这些岛民也在利用西方人的远洋航行工具来为他们自身的经济活动、政治野心,以及知识生产服务。
在庞大的智利-印度-中国三角贸易中,“圣帕特里克”号只是一艘极其普通的商船,但其船员的生活轨迹却可以帮助我们窥见那个革命时代的一些重要特征。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和革命加速了全球化,生活在南方大洋(包括了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土著利用这一轮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思想、商品、制度来重新想象和规划自身的信仰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西瓦桑达拉姆认为土著们并不是在革命年代被动接受了自由、理性、进步等理念,而是通过自身传统思想对其进行了再发明。这些杂糅性的思想和制度无不体现了岛民土著的主体性。至于土著岛民们在革命年代体现出的主体性为什么没有延续下来,并会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被遗忘,西瓦桑达拉姆则将矛头指向了英帝国及其历史书写者们。
在中国传统的世界史教科书中,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世界史主要是在讲述大西洋两岸的政治(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文化(启蒙运动)、技术(工业革命)和经济(资本主义)变革。学生的潜意识因此被不断地灌输这样一种思维:那是一个由西方主宰的时代,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和人群在那个时代都是可怜的配角,被无可奈何地裹挟着进入了现代。在这两个世纪当中,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无疑是最为激荡人心的时代。霍布斯鲍姆将这一时代称之为“革命年代”。“革命年代”的故事围绕着大西洋展开,由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拉丁美洲革命构成。有关“革命年代”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无需赘述。但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都带有“大西洋中心”色彩,甚少有研究“革命年代”的学者关注该时期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的水域(西瓦桑达拉姆称之为“南方大洋”)中发生了什么。
《海洋、岛屿和革命》一书试图将革命年代故事的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南方大洋。西瓦桑达拉姆认为十八至十九世纪大西洋世界的变革(政治、技术、经济、文化)并非非西方地区变革的唯一范本和动因。相反,这一时期南方大洋也发生了诸多非西方版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变革。这些变革本可以为现代世界带来一些不同于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单一历史发展逻辑的其他可能性。但这些变革却被抱持着保守立场的反对革命的英帝国所压制了。在西瓦桑达拉姆看来,英帝国是在镇压南方大洋各地革命力量的过程中才得以形成和巩固的。吊诡的是,反革命的英帝国却将自己塑造成了保卫自由贸易和促进政治进步的革命力量,并进一步在之后的历史书写中抹去了南方大洋土著在革命年代的创造性变革。西瓦桑达拉姆开启这项研究的目的则是要揭示英帝国崛起过程中的反革命本质,并重新确立南方大洋土著在那个关键时代的主体性。
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南方大洋各地的土著开始广泛接触西方殖民者带来的商品、制度和思想。土著们对这些新事物加以改造,并引为己用,从而引发了南方大洋的革命年代。毛利人的空间知识生产模式、汤加土著精英的集权国家建设、南非科伊科伊人的千年末世论信仰、波斯湾的伊斯兰教瓦哈比派改革等都是那个革命年代的产物。西瓦桑达拉姆强调,这些发生在南方大洋的革命远非冲击/回应范式所能解释。太平洋土著、阿拉伯人、帕西人、爪哇人、缅甸人、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和西方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相互交融、冲突和借鉴塑造了南方大洋革命年代的性质和特征。
西瓦桑达拉姆发现英帝国在十九世纪的崛起与革命年代南方大洋的土著们息息相关。南方大洋的土著政治精英利用革命导致的混乱局面谋求自身的利益扩张。英帝国在扑灭革命的过程中,也遏止了土著精英的扩张企图,为南方大洋带来了一种反革命的霸权稳定。这种霸权稳定是建立在高度排他性和等级化的种族、族群和性别概念基础之上的。这些由英帝国散布在南方大洋各地的身份政治理念为二十世纪各地出现的政治危机埋下了伏笔。

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西瓦桑达拉姆(Sujit Sivasundaram)
该书作者西瓦桑达拉姆专长于十八至十九世纪的英帝国史,尤其关注英帝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殖民扩张中的自然科学实践。他的第一本专著《自然与神圣帝国:1795年至1850年太平洋上的科学与传教》(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揭示了十九世纪欧洲殖民扩张中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协同关系。他的第二部专著《孤岛:英国、斯里兰卡与一个印度洋殖民地的边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将研究重心转向印度洋,从港口基建、种植园产业、泰米尔劳工移民和上座部佛教传统等角度剖析了现代斯里兰卡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海洋、岛屿和革命》是西瓦桑达拉姆对其前两部作品的综合和总结。他将印度洋与太平洋世界整合为南方大洋,并努力尝试复原这些地区的土著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革命年代所展现出的主体性。这是一部反西方中心主义和揭露英帝国反革命性质的全球史作品。由于其打破了大西洋中心的“革命年代”叙事逻辑,并致力于将开普敦、毛里求斯、波斯湾、孟加拉湾、塔斯曼海以及南太平洋群岛等地的变革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加以联系和比较,美国世界史协会于2022年授予该书本特利图书奖(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Bentley Book Prize)。
尽管该书自出版以来获得了非常多的国际关注,但中国学术界对其却鲜有提及和讨论。这种沉默体现了国内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界在早期现代时段研究中存在的脱钩现象。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书在国内史学界可谓是家喻户晓。许多中国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书中的“大西洋中心”叙事逻辑,并默认这些“革命”是世界史——甚至仅仅是西方史。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大多数中国读者看来,近现代世界史约等同于西方史——的范畴。中国的欧美近现代史学者对革命年代中出现的思想、文化和制度变革展开了非常系统的研究,但少有人愿意将目光移向南方大洋。开普敦、霍尔木兹海峡、科罗曼德海岸、马来群岛、塔斯曼海这些陌生的地名既在其知识范围之外,也在“主流历史发展潮流”之外。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革命年代正是中国清代中期。中国史学者对这一时代的关注仍然以中国核心地区(华北、江南、华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变迁为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清代中国边疆(东北、新疆、云南、福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和互动。但是,鲜有中国史学者愿意去想象远在大西洋的革命会对乾嘉时期的中国有何影响。
《海洋、岛屿和革命》一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革命年代并不仅仅是大西洋史的一部分。与旧制度决裂的变革浪潮席卷了从毛里求斯到汤加的广袤地区。那么,那些在1800年代前后来到中国沿海活动的西方人又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革命年代的影响?当时的中国人是否感受到了世界的剧变并给予了回应?革命年代在南方大洋留下的余音又如何与中国内部变奏曲形成共鸣,奏响了十九世纪中国社会剧变的浩瀚篇章?这些问题如此令人着迷又如此紧迫,但我们现有的英美近现代史和明清史学者都无法在各自既定的研究领域内回答这些问题。全球史方法——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史方法并非仅执着于批判西方中心观,而是对各类中心观的批判性方法——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促使我们走出西方史/中国史二元思想牢笼,在一个非东非西的位置尝试新的历史思考方式。
不过,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我们也产生了一些疑惑。该书的主要论点在于强调恢复南方大洋土著的主体性,其对话对象则是十九世纪盛行一时的英帝国史书写。但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西方学术界已经对传统英帝国史书写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展开了系统的反思和批判。二十一世纪以来,尝试探索非西方世界族群主体性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因此,西瓦桑达拉姆用如此巨大的篇幅重述这个已经被学术界所共知的观点,其研究的创新性就显得些许薄弱。此外,西瓦桑达拉姆在书中一再强调土著主体性(indigenous agency),但他所提及的土著几乎都是岛民土著中的精英群体。那么这些人彰显出的主体性是否也代表着庶民的主体性呢?这些政治精英在彰显自身主体性时,是否会在其社会内部造成新的不平等或者暴力呢?换句话说,西瓦桑达拉姆所谓的“土著主体性”在内涵上是空洞的,他并没有解决“谁才是土著”这个问题。而一味浪漫化这种空洞的“土著”概念则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尽管西瓦桑达拉姆指出“高贵野蛮人”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和臆想,但空洞的“土著主体性”概念又何尝不是“高贵野蛮人”这种东方主义思维的当代变种呢?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土著如何对革命带来的思想和制度进行利用和改造,但革命浪潮的源头始终是在西方,南方大洋的岛民土著作为这一浪潮接受者的角色并没有在本质上被改变。西瓦桑达拉姆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太多岛民土著对革命的反应如何在本质上影响了西方历史进程的案例。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所宣称的要打破传统帝国史叙事中冲击/回应范式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达到。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