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凯蒂·恩格尔哈特:关于生死的特别报道
199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了2起分别来自华盛顿州和纽约州的协助死亡案件。在这2起案件中,大法官们一致决定不推翻州一级禁止医生协助死亡的法令。大法官们指出,医生协助死亡并不是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一项受到保护的权利。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死亡权,也没有尊严死的权利,或者用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的话来说,甚至也没有“普遍的‘自杀权’”。最高法院把这个问题退回了“各州的实验室”。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在由他执笔的多数意见书中,强调了各州在“保护弱势群体——包括穷人和老弱病残——免受虐待、忽视和错误伤害”方面的权益。他也提到了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反对死亡权思想支柱的滑坡论,即一旦承认有限的死亡权,就不可能对其加以控制,这项法律会势不可当地一再扩大,将越来越多的病人都包括进去:生了病但还没病入膏肓的人,精神上有病但身体上没病的人,老、弱、残。批评者警告说,最后一定会出现滥用,滥用在穷人、不情愿死去的人、妥协了的人、感到害怕的人身上,就连害了单相思的16岁男孩都可能会卷入其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就曾指出,任何给定的原则都有“扩大到自身能够推而广之的极限……的趋势”。
然而,在其他地方,立法者对神圣性有不同的看法。1995年,澳大利亚北领地拟将安乐死合法化。尽管该法律在2年后被联邦政府废除,但全球格局正在慢慢发生变化。1998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自杀游客”开始在瑞士死亡。在那里,协助死亡已经合法化,苏黎世附近的一家新诊所开始接收外国病人。2002年,荷兰和比利时都将安乐死合法化了;后来,卢森堡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小小的比荷卢地区成为医生协助死亡的全球中心。
大约在同一时间,英国的一项法律挑战未能推翻该国对协助死亡的禁令。这个案子是由来自卢顿的43岁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的戴安娜·普雷蒂引起的。黛安娜说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她做不到,因为她脖子以下都瘫痪了。她说,这样一来,她无法自杀,而这是她的合法权利,法律剥夺了她尊严死的权利。
黛安娜想让她的丈夫杀了她——她想确保当他这么做时,他不会因为谋杀而入狱。她先向英国法院提出诉讼,然后又向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诉讼。2002年4月,在最后一次上诉失败的那天,戴安娜在伦敦通过语音模拟器对一群记者说,“法律剥夺了我所有的权利”。一个月后,她在数天的极度痛苦中死去。《每日电讯报》报道,她“以她一直害怕的方式”死去。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在其著作《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未来》中指出,允许协助死亡的法律只要存在,就会给伦理道德带来极大腐蚀,让我们一头冲向毫无价值的死亡和强制的杀戮。戈萨奇写道,没有比美国死亡权运动骇人听闻的早期历史更好的证据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自愿安乐死”四处奔走的人,有些也同样支持优生学,支持强制“愚笨的人”绝育,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还秉持“种族改良”的思想。戈萨奇警告称,未来的道德败坏,只能通过维持“反对由私人有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毫无例外的社会规范”来防止。生命必须保持神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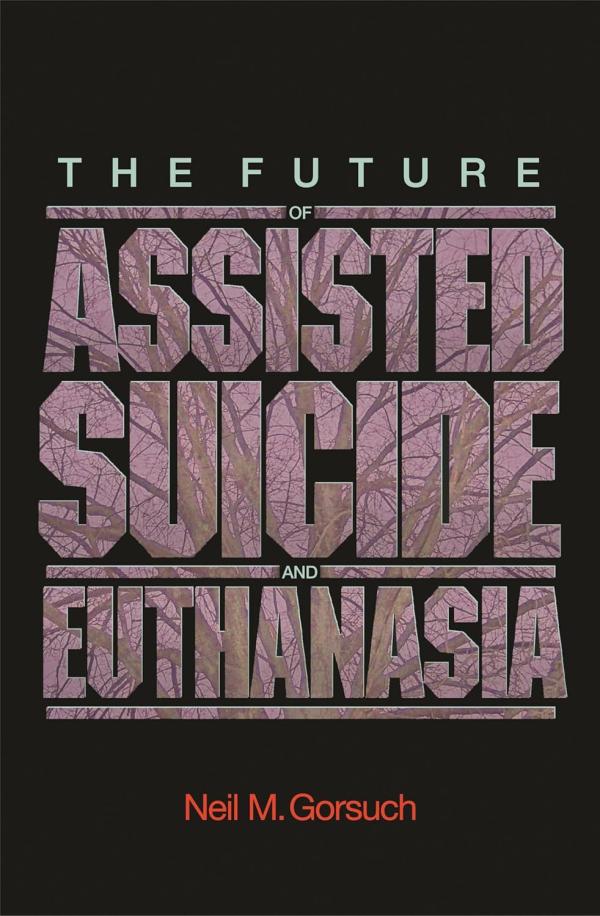
尼尔·戈萨奇《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未来》
一直到2008年,才有第二个州跟上俄勒冈州的步伐,就是华盛顿州。随后是蒙大拿州(通过司法裁决,而不是立法)、佛蒙特州、科罗拉多州、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特区、夏威夷州、缅因州和新泽西州。这些法律各有各的名称,各自采用了不同的委婉说法:《生命终点选择权法》(加州)、《“我的护理我做主”法》(夏威夷州)、《病人在生命终点的选择和控制法》(佛蒙特州)。今天,超过1/5的美国人生活在对绝症病人来说医生协助死亡合法的州,他们对此也乐见其成。2017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73%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医生应当被允许“以某种无痛的方式”结束病人的生命,只要这是病人自己想要的,而且该病人“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不过,在问题变成“如果病人要求自杀”,是否应允许医生帮助病人时,这一支持率下降到67%。语言反映了思想,语言也影响了思想,“自杀”这个字眼仍然很有分量。
在俄勒冈州,这一数字仍然很小:大约每1000人中有3人以这种方式死亡。2019年,290名病人得到了致命的处方,188人通过摄入致命药物死亡。根据该州披露的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关于这些人的一些事实。绝大多数人都患有癌症,而其他人则患有心脏病、肺部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肌萎缩侧索硬化(ALS)。患者通常都是65岁及以上的白人中产阶级,已婚或是丧偶,受过一定程度的大学教育。他们在精神健康测量方面的得分都很低。他们基本上都有医疗保险,也基本上都已经住进了临终关怀病房。最近,精神科医生、学者琳达·甘齐尼在一次演讲中对一群公共卫生专家开了个玩笑:“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在医学当中,我们一直很担心的一种情况或者说情形原来是,风险因素一直是富有、白人和有医保。”甘齐尼指出,需要临终援助的病人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专注于控制”死亡。为此,他们在需要挑战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时,在需要同根深蒂固的重重障碍折冲樽俎时从不退缩,他们有时间,有秉性,也有资本,可以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并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其他学者还提出了另外一些理论。他们指出,非裔美国人通常都不太可能在生命终点得到照护,比如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并推测这些差别也同样延展到了协助死亡方面。致命药物价格昂贵,一般医疗保险也不会包括这一项,所以有时候他们根本买不起。学者坚持认为,有些群体对老人的照护比其他群体更加周到,因此那些群体中想要自杀的老人估计会比别的群体少。他们把这些都归结为宗教信仰、集体归属感和道德价值观的差异。
在那些协助死亡合法的州,我们确实知道是什么促使病人选择早死。在查看俄勒冈州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时,最让我惊讶的是,大部分要求死亡的人据说并没有处于可怕的疼痛之中,甚至也不是因为害怕未来会遭受怎样的痛苦。绝大部分人都声称,他们最关心的临终问题是“失去自主权”。也有一些人担心“失去尊严”,失去享受生活中的快乐的能力,以及“失去对身体机能的控制”。在将疼痛纳入考量时,他们说的都是害怕未来的疼痛,或是想要避免即将到来的疼痛,再不就是因为此时此地并不知道未来还会有多少痛苦到来而在精神上感到的苦痛。是能好好死去还是会不得好死?这个问题中的不确定性让它变得迫在眉睫。俄勒冈州的病人必须身患绝症才有资格申请协助死亡,但到最后他们选择死亡却更多的是跟生存有关的原因,是对现代医学既定边界之外的痛苦做出的回应。
本书融合了医学、法律、历史和哲学,但并不是一本关于论辩的书,也不是对美国或任何地方的死亡权运动的全面描述。实际上,本书主要是故事、对话和思想的集合。我的工作从2015年的伦敦开始,那时我还在维斯新闻当记者。那一年,英国议会要投票决定是否将医生协助死亡合法化。我就这个主题做了一些报道,还跟几个同事合拍了一部纪录片。我一直在关注这场全国性的辩论,很激烈,也可以预见。支持者说着“个人自主权”,讲述着病人和垂死之人因为受到的痛苦而被迫以可怕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样的故事让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反对者说着“生命之神圣”,警告说没有能够保护弱势群体的保障措施。到了投票那天,抗议者聚集在议会大楼外,互相冲着对方的脸尖叫,剑拔弩张。一边的牌子上写着,“给我比死亡更好的选择”。另一边的牌子上写的则是,“小心滑坡效应,不要伤害”。后来,议会投票否决了这个议案,而我在那之后还在继续自己的研究,先是在英国,后来也涉及协助死亡已经合法的地方: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和美国的一些地区。我想知道,立法规定一种全新的死亡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似乎对我们如何理解生命的意义,以及理解我们觉得自己有义务遵守的社会契约,都至关重要。
我在转而关注美国及其《尊严死法》时,发现能找到的数据比我预计的要少得多,让我很惊讶。在比利时和荷兰,安乐死监督委员会发布了年度报告,但几乎没有披露使用法律的个人相关信息。协助死亡合法的美国各州要求医生就每个完整的死亡案例提交一些书面文件,但这些文件都是医生填写的,而不是由将死的病人自己填写,病人自述的想法和情感从来没有被医疗系统记录下来。而且出于保密的考虑,并非所有州都会收集大量数据,更不是所有收集到的数据都会公布于众。有些研究人员因为永远都不可能知道所有跟那些不寻常的病人有关的情况而哀叹——他们的特定地理分布,他们的精神健康史,他们的家庭关系是什么样子,他们的银行账户在什么量级,等等。在整个世界,关于医生协助死亡的系统性研究也很少。甘齐尼博士在这个领域发表的文章挺多的,她告诉我:“这是有原因的。这样的工作很难拿到资助。这是……怎么说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会保持警惕的那种研究。”我知道,我如果想了解这些病人,就需要找到他们,和他们一起度过他们用来策划自己如何死亡的生命片段。
但并不是这样就够了。随着我对类似俄勒冈州那种尊严死法律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些法律从哲学角度来讲,并不像我之前所想象的那么激进。毕竟,这样的法律只适用于那些本来就会很快死去的病危患者。这些法律让那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加快,但并没有加快很多,而且不会改变这个过程。我后来遇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病人:即使在医生协助死亡合法的地方也并不满足法定标准,但仍然想死的男男女女。他们说,他们都有绝对合情合理的原因。他们得了慢性病,他们很痛苦,他们年老体衰,他们正在变得精神错乱,他们不想活得像他们的父母那样久、病得那样厉害。这些人彼此之间大不相同,但他们似乎都在说着同样的话。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们会说到“理性自杀”,这种终结生命的方式至少在理论上并非出于冲动,也并非由精神疾病所激发(后文有时候叫作“绝望自杀”,是自杀的绝大部分原因),而是在经过极其冷静、清醒的数学计算,做了成本效益分析之后的决定。在将一切都考虑进来之后,再行决定是活着还是死去。
很多人都跟我讲,他们遇到了法律的限制,于是只能在法律之外寻找解决方案,也确实找到了。有时候,他们得到的帮助来自亲友。也有时候,人们通过互联网得到一些小型但往往组织严密的秘密团体的救助,有些活动家称之为“地下安乐死”。我头一回知道这些网络的时候,觉得非常惊奇。我不是也读过在罗诉韦德案之前的那些年提供堕胎服务的地下女性团体的故事吗?我不是也知道,只要法律不到位,人们就会想别的办法吗?我决定让这些人成为我的报道焦点,成为本书的主人公。

凯蒂·恩格尔哈特
4年间,跟我交谈过的有好几百人,他们跟协助死亡有各种各样的关联,有的在法律范围内,有的则在法律之外。我采访了病人、医生、护士、研究人员、坚持不懈的支持者、坚定不移的反对者,以及一个痛苦万分的母亲、一个义愤填膺的父亲,还有一个在我前去询问关于她孙子的一些事情时,把自己锁在地下室的老祖母。我接触过一个住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里的萨满,接触过一个读过《老子》的墨西哥毒贩,接触过一些从网上订购致命药物的老年人。我还接触过一个在全美各地传授如何用气罐和塑料袋结束生命的人,他以前在某企业做高管。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考虑活下去的动力和死去的冲动,以及这些倾向互相影响的方式。我对政客在州议会唇枪舌剑的经历,以及出于神学立场反对安乐死的宗教人士都关注极少,因为他们的故事让人厌倦,也太一目了然。
每天我都能读到关于医生协助死亡的新闻报道,讲述的故事整齐划一,无外乎俄勒冈州或加州或比利时的某人生了重病,在接受诊断结果后,作为对肿瘤、肺部疾病或是神经功能衰竭的直接回应,做出了痛苦但清醒的选择。然而我碰到的很多人,他们的故事都比这些新闻报道更复杂,也更缠夹不清。我碰到的那些人想死当然是因为他们生病了,但也同样因为精神上的痛苦、孤独、爱、羞愧、很久以前受到的创伤,或者渴望脸书上的粉丝认可自己。有些人的动机是因为钱,或者说因为缺钱。也就是说,我遇到的人都不是清一色的。他们并非都讨人喜欢,并非都容易相与,甚至感情上也并不总是清晰可辨。在面对死亡时,他们并非都很勇敢。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并非都能给他们周围的世界带来有意义的经验教训。有时候,他们虽然极度痛苦,却毫无意义。
我的报道并不容易。在一些案例中,我知道那些人打算在实施医生协助死亡前就结束自己的生命——独自在家里,不要医生的帮助,也不需要知道该怎么做——而我没有干预。这件事情从伦理道德角度来讲非常棘手。我常常感到不安,感到不确定,无论是作为一名记者,还是作为一个人。随便哪个记者都知道,只要自己带着笔记本和录音设备出现,故事就会变化,无论自己有多低调,也无论自己在引导故事发展时有多小心翼翼。我永远不希望某个人的生命因为我的出现而被推向死亡,我不想让任何人因为一个故事而死,更不用说因为我的故事而死。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于我要见的人,我精挑细选。如果有可能,我会跟他们的家人、朋友、医生、治疗师和照顾者都谈谈。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他们,他们不欠我什么,我也并没有期待什么。他们想跟我聊多久就聊多久,聊完了告诉我一边待着去都行。他们可以直接不再理我,如果这样会让事情简单一些的话。确实有些人这么做了,我便没再找他们。
这些年来,我总是在晚宴上、在工作场合、在人满为患的酒吧里聊到这本书,然后就会有人来找我,私下招认一些事情。似乎每个人都有故事,也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讲出来。为什么?素昧平生的人描述了他们亲眼见过的生命如何结束的可怕场景:难以控制,十分缓慢,让人难堪。另一些人则跟我讲述了提前计划好的死亡。有位朋友说,他的祖父囤了好多心脏病药物,想用来自杀。还有一位朋友则描述了她姐姐怎么把镇痛药碾碎,掺入一位年事已高的姑姑的酸奶中。有位同事告诉我,他90多岁的老父亲选择做一个毫无必要且很有风险的手术,满心希望自己能死在手术台上。那位老人太虚弱了,没法自杀,于是寄希望于让医生杀死自己。
这些都在说明什么?在生命行将结束时,对绝对控制权——或者可能只是一丝丝控制权——的这种渴望,以及对有时用来维持毫无生机的一具躯壳的机器的这种反抗?这些都关系到免遭病痛折磨的渴望,关系到自主权。在美国的法律传统中,还关系到隐私权,以及不被干涉的消极权利。但对我遇到的大部分人来说,选择在计划好的时间去死,最主要的还是关乎“尊严”。
当然,尊严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有些哲学家对这个概念挑出了好多毛病。他们认为,尊严这个概念往好了说是多此一举,只不过是表示尊重选择、尊重自主权的另一种方式。也有些人对于把这个概念用在这场战斗中表示愤慨。他们问道:难道不是所有人都早就被赋予了与生俱来的尊严吗?以此推之,难道不是所有人在死去的时候都是有尊严的吗?临终医疗援助的支持者将这个词纳入囊中,放在语带委婉的口号“尊严死”里,并声称只有他们才能用这个词,但反对者也有自己的关乎尊严的诉求。2008年共和党的政治纲领中就有一个段落题为“让人类生命保持神圣和尊严”,其中写道:“我们反对安乐死和协助自杀。”对另一些人来说,尊严并不在于逃避肉体上的痛苦,而在于面对痛苦时保持冷静、勇敢和自我克制。在他们看来,尊严体现在镇定中,并通过忍耐赢得。
我在为本书采访病人和垂死的人时,有时会问他们一些关于尊严的问题。我承认,我发现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期待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超凡的智慧,就好像他们会因为特别接近死亡,而以一种我无法做到的方式去理解世事人情。我采访过的很多人都把尊严等同于控制括约肌。他们说,到他们把屎尿拉在裤子里,或是必须让别人来帮忙擦屁股的时候,他们的尊严也就丧失殆尽了。真的就这么简单。看来,就算人们难以准确定义尊严究竟是什么,在有什么事情让他们觉得有失尊严时,他们内心还是知道的。对他们来说,为死亡做个规划往往是为了避免失去尊严。他们认为,没了尊严会让他们感到羞愧、屈辱、无力、压抑、自私和丑恶,无法再举止端庄,经济开支也会高得离谱,还会觉得不堪重负、不合理或不真实。
“这事儿我该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任何人来说,无论多大年纪,都几乎不可能想象自己会如何死亡。”贝蒂说。我们在她的餐厅里,坐在木椅上吃着水果沙拉。她刚跟我讲完她自己的墨西哥之旅、那些药品,还有她们关于自杀的约定。“曾经出现过的意在让人们加入基督教的各种想法中,复活算是最好的一个了。”但贝蒂并不相信复活。她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也是唯一她能通过计划做到的,就是“平静地死去”,她希望能通过缩短生命的最后一程来实现。她宁愿在病得特别厉害,或者精神错乱到迷失自我之前就死掉。服用过量巴比妥酸带来的深度睡眠似乎能帮到她。
贝蒂想着,人类到生命终点时会被扔在那里受苦受难,而狗狗却可以通过打上一针来脱离苦海,真是奇怪得很。同样奇怪的是,让狗狗脱离苦海还会被看成一种仁慈。人还不如一条狗,真够奇怪的!死亡权支持者有一句口号在网上广为流传,贝蒂也很喜欢:“我宁愿像狗那样死去。”
在我的新闻报道工作中,这句话我听了无数遍。我随时都能听到这句话。很多人跟我讲起,生了病的宠物会被好心的兽医实施安乐死。他们问道,为什么他们不能得到同样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在一个人均医疗费用较高的国家,却在祈求自己能得到兽医的垂怜。
本文摘编自《不愿活下去的人:关于生死的特别报道》,为该书引言的节选,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后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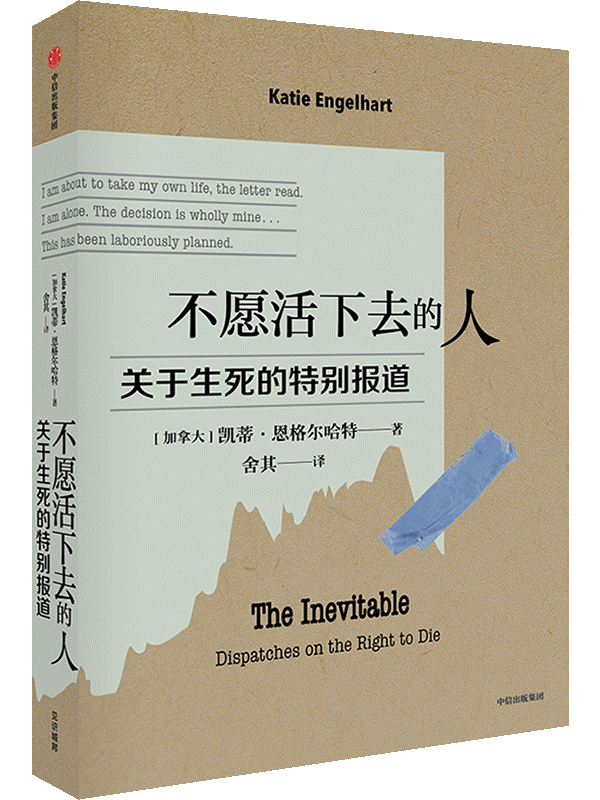
《不愿活下去的人:关于生死的特别报道》,【加拿大】凯蒂·恩格尔哈特/著 舍其/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23年8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