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讲谈会|文心新雕——《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为纪念王运熙先生逝世十周年,顾易生先生诞辰百年,2024年10月25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文心新雕——龙学回顾与前瞻”学术讲谈会于光华楼西主楼1001室举行。本次讲谈会由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杨明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左东岭教授、澳门大学中国文学系张健教授主讲,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陈引驰教授主持。以下为讲谈会实录,经讲者审定。

陈引驰
陈引驰:老师同学们好,很高兴各位能够到场,也很荣幸第二届《文心雕龙》青年学术沙龙将于明天在复旦召开。20世纪以来,龙学在文学史、文学批评、专书研究等方向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天的主讲人都是龙学专家,杨明老师的研究最具王运熙先生之风,极为精细;左东岭老师现任《文心雕龙》学会会长,他师从罗宗强先生,发展了罗先生对《文心雕龙》的很多精彩看法;张健老师师从张少康、吴组缃先生,也是古代文学批评领域的专家,曾就龙学的许多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那么先从杨明老师开始吧?

杨明
杨明:如果序齿的话,我就只好抛砖引玉了。就像陈老师刚才说的,《文心雕龙》研究很多,也很深入透彻。得到通知要参加这次讲谈会,我很高兴,想了很久该讲些什么。今天我想谈谈,《文心雕龙》研究能否跟写作联系起来。
《文心雕龙》虽然谈及很多理论,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刘勰的本意是谈写作的基本知识、文章作法,这一点为老先生们所公认。我们今天主要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但就像范文澜先生所说的:“《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刘勰切实地把写作门道告诉读者,让读者能够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王运熙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强调刘勰的本意是谈写作。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也开宗明义地讲:“《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讲写作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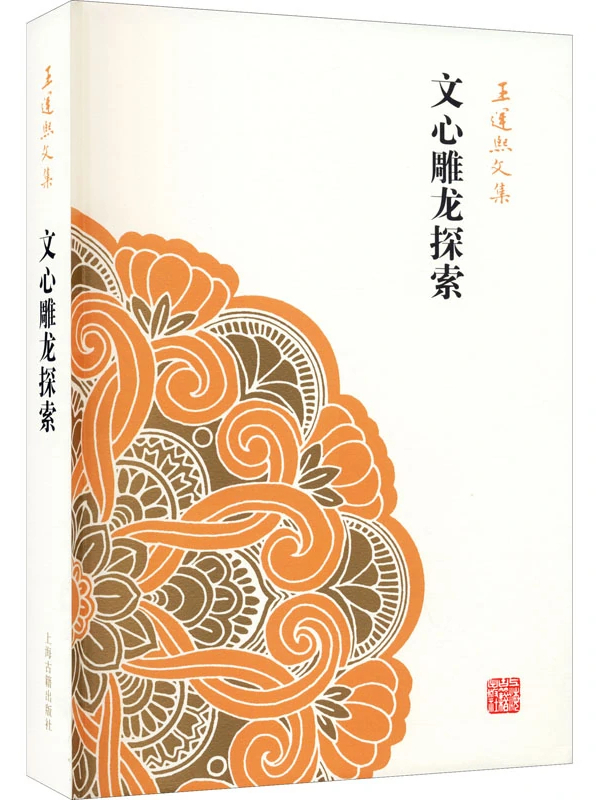
《文心雕龙探索》,王运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4月版
先说刘勰称为“文之枢纽”的首五篇,这五篇的基本观点就是,写文章应一手伸向儒家经典,一手伸向楚辞。在刘勰看来,学习作文要以儒家经典为主,这说的是学习儒家经典的雅正文风,而非强调儒家著作的思想内容;学习楚辞,是由于光有雅正的文风还不够,在此基础上要发展、新变,要更加绚丽。这就是“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骚”。刘勰所谓雅正文风,对文章写作的规范化提出了要求。今天写文章,也要合乎语言文词的规范,才能被广大人群接受,在此基础上再去求美、求新、求变。
在论文体的二十篇中,文学意味较强的主要是《明诗》《诠赋》,此外很多篇目讲的是应用性文章,从皇帝的诏命、臣下的章表,甚至到零碎的药方、户口登记等,都算在“文”之内。许多文体今天已经不用,但在这二十篇内,仍能体会到很多与写作相关的东西。首先,不仅文学创作,即使是普通应用性的文章,也要讲究文辞的运用,刘勰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可见儒家经典也很重视文辞之美,而各种文体的美又有所不同。这或许是中国文学的特点,外国的东西我不太了解,但曾有一位日本社会学学者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写文章很慎重,很注意结构、条理等等,我们写文章常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这样看来,讲究文辞表述或许能说是中国文章的一个特点吧。第二,写应用文章要讲究文辞,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得体”。每种文体有自己的规格和风格要求。王运熙先生非常重视古人论“体”。“体”的含义很广,其中风格这一点非常重要。钱钟书曾评价梁元帝萧绎的《劝农谕》,这篇文章是为劝导农民耕作而写,作为皇帝下诏,应该是很严肃的,但萧绎为了追求文章之美,加上了很多描写自然风景的漂亮文辞。这篇文章虽看起来漂亮,但钱先生说,作为帝王下诏,却写得像士女相约游春的小简,并不得体。这对今天的写作也有启示作用。
所谓“创作论”的部分也是如此,比如《神思》论构思,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偏于文学性强的作品的,但其实该篇所论也包括应用性文章的构思。对于作文思路怎样才能畅通的问题,陆机在《文赋》中就有讨论,他认为灵感很神秘,灵感之来和去都是作家无法控制的,“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便是他的切身体会。而对学习写作的人来讲,这就有点让人挠头了。该如何保证思路的畅通呢?刘勰在《神思》里讲得很切实:一方面,需要下好平时功夫,即“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积累文辞、典故,研究和思考各种事理以增加才力,并从写作的角度研究古今作品,阅读、欣赏和体会别人的写作之法;另一方面,是临文之际的功夫,刘勰强调写作时应“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集中思想,摒除杂念,这是将先秦诸子论述心理活动的语汇运用到写作上面。这些话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对今天仍有启发作用。《风骨》也和写作有关,该篇主要谈的是文风问题:“风”指文风要明朗,让读者能看懂,这样才能使读者感动;“骨”指的是文辞要精炼、准确。刘勰说“结言端直”,强调的并不是思想的端正,而是文辞运用的规范化,不应为求新变而损害文辞,这也是古今相通的。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主席曾在内部讲话中谈到,工作汇报应讲究文风,要有鲜明性、准确性、生动性。后来召开了座谈会,郭沫若、老舍、冰心等作家都参加了,专门讨论文风问题。毛泽东所说的这三性,其实也与刘勰讲的“风骨”相通。还有《定势》中,刘勰特别谈了“讹势”,也就是“反正”,故意与规范唱反调,如“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的写作方式,刘勰指出这是由于一些作者“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他对此现象很不满意。讹势的现象自古就有,但主要是从南朝刘宋时开始盛行,尤其是鲍照和江淹,他们甚至在诗和文章中故意生造词语,这是刘勰非常反对的。这也可能是《文心雕龙》“针砭时弊”的重要内容。今天有些文章为求新鲜,或故作高深,也会不顾文辞表述的规范,生造词语,违反语法规则,形成一种晦涩的文风。这需要注意。
具体讲修辞手法的篇章,更与写作有直接关系。如《练字》提到,《尚书大传》中“列风淫雨”一句,因流传中的错讹变成“别风淮雨”,而有些作者明知有误,却为求新奇故意使用错字,比如东汉的傅毅和南朝的王融。又《指瑕》谈到,“赏”原指赏赐,却在使用中增加了欣赏的含义。这个意思我们今天觉得很自然,但在刘勰的时代,却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用法。“抚”本来是一个动作,却逐渐被用来指体会和感受事情,比如后来杜甫曾写“抚事煎百虑”。这样看来,刘勰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似乎比较保守,强调语言文字要合乎常规;但也不能就此将他批评为保守派,因为语言的发展就是在既要守规范、又要突破规范的矛盾中前进的。今天的许多网络语言都突破了规范,但它们以后是否能进入现代汉语的宝库,也是我们无法预料的。但就写文章而言,基本的倾向还是要遵守规范。
总之,《文心雕龙》主要是从文辞运用的角度谈写作,它的许多内容实际上并不高深。我们今天之所以感到高深,主要是由于时代远隔、对骈文形式相对陌生,但究其道理,其实是很明白的,关键在于能否落实到写作中。对《文心雕龙》的进一步研究,最好跟当今的写作联系起来。刘勰作《文心雕龙》的目的之一是纠正当时的不良文风,而今天倘若能借鉴这种做法,分析社会上的文病,也是有意义的工作。
陈引驰:谢谢!杨老师的发言可谓一气呵成,胸有成竹。今天龙学研究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角度,我印象里,早期研究各有不同,可能主要是结合秦汉以下的创作来谈文学史的问题。如罗常培所记刘师培口义两篇,就是讲论《颂赞》《诔碑》的,而刘氏《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也多对照《文心雕龙》文本,以更清晰地阐述汉魏文学的发展。20世纪后半叶,学者对理论多予关心,如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就是从理论方面深入,且与西方理论相对照。总的来说,当今龙学研究较少考虑写作问题,但从本原上讲,指导写作或许才是本书的宗旨。杨明老师的发言既把握住全书的篇章结构,对词句细节的理解也很深入,从各层面扣住了《文心雕龙》的本意,且联系到术语、文句等具体的情况,为本次讲谈会确定了基本的方向。那下面有请“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左东岭老师发言。

左东岭
左东岭:杨先生将《文心雕龙》定性为一本指导写作的书,我非常同意。现在《文心雕龙》学会在做一个课题,叫做“新时期《文心雕龙》研究学术思想检视与中国学派建构研究”,所以我最近几年也在做研究史相关的工作。这次在复旦举行的《文心雕龙》青年学术沙龙,名字叫“源流与通变:《文心雕龙》研究再出发”,所以今天我想讲讲我在罗宗强先生门下学习《文心雕龙》的心得,还有一些新的想法。
罗先生硕士阶段就读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他最早发表的龙学论文,是1978年的《非〈文心雕龙〉驳议——评〈学习与批判〉上的一篇文章,兼论批判继承我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反驳那篇文章关于《文心雕龙》的思想是唯心主义,尊崇儒家思想与温柔敦厚审美原则,以及批评六朝形式主义是复古倒退等三个方面的观点。这篇文章罗先生后来似乎并不满意,没有收入他的文集中。集中体现罗先生龙学学术思想的,是评论毕万忱、李淼《文心雕龙论稿》这本书的文章《读〈文心雕龙论稿〉随想》,发表于1987年。罗先生认可《论稿》表现的“一种力图按刘勰的思想原貌来把握刘勰思想的认真努力”,指出它“与支离掇录刘勰只言片语,而附会以现代文学理论、滔滔游谈者异”,这后来衍生为他的“历史还原”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罗先生提出了“《文心雕龙》究竟是一部什么书”的问题,他很认可王运熙先生的观点,即《文心雕龙》是论文章的。这个提法现在尽管已不太新鲜,但在当时非常重要,后来的重要学者如张少康等,都承认《文心雕龙》首先是一部文章学著作,其次才是文学理论著作。而在王运熙先生的基础上,罗先生指出,这还涉及“什么是文学”的根本问题——古代文论家所理解的文学都包括些什么?有什么特征?他们的认识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他们给“文学”总结出了什么样的“普遍规律”?罗先生一辈子都在想这些问题,他认为,刘勰所处时代的“文学”,跟现在的“文学”太不一样了,因此《文心雕龙》应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框架中理解。罗先生后来对这篇文章也不甚满意,没有收进自己的文集。但我认为这篇文章实际上奠定了他研究文学思想史的基本学术理念。
罗先生有两部书,分别体现了他研究《文心雕龙》的两种特点。第一部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其中对刘勰和《文心雕龙》的研究,在十章中占了三章。罗先生在《后记》中非常感慨地说,有三四年时间,他都在《文心雕龙》上徘徊,反复思索该书与六朝文学思潮的关系问题。此前学界曾经认为,《文心雕龙》与六朝主流文学思潮异趣,是反唯美主义、反形式主义的;但罗先生在深思熟虑后得出,《文心雕龙》所表述的文学思想,实际上与当时的文学思潮一致,只是刘勰在承认文学发展的前提下,又对过度的形式化提出了批评。罗先生在《刘勰的文学思想(中)——刘勰的文学观》中,特意设置了两个小节,分开来谈刘勰的杂文学的观念、刘勰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这就是要处理刘勰文学思想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刘勰的杂文学观念》主要谈杂文学、文章学方面的内容,甚至延伸到文化这一更大的框架,指出刘勰在认可杂文学观的前提下,特别强调了诗文写作和审美艺术;《刘勰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则主要谈刘勰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他的主导思想还是突出文学审美,和六朝文学思潮是一致的。罗先生在谈整体的理论问题时,往往先分析每一篇的架构和行文,再分析篇章之间是如何勾连起来的。他并未打碎材料来分析、归纳,而是回归到作者如何写的问题,按照《文心雕龙》的本来面目进行讨论。我认为古代文学和其他学科的重要差异,就在于文本分析;个案研究和文本分析,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看家路数,我们要把文本当文章读,而不是当材料读,要在读懂文章的基础上提炼问题,否则就成了无根之木。关于这个观点,我曾经写过《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文体意识》,这篇文章就源于罗先生研治龙学的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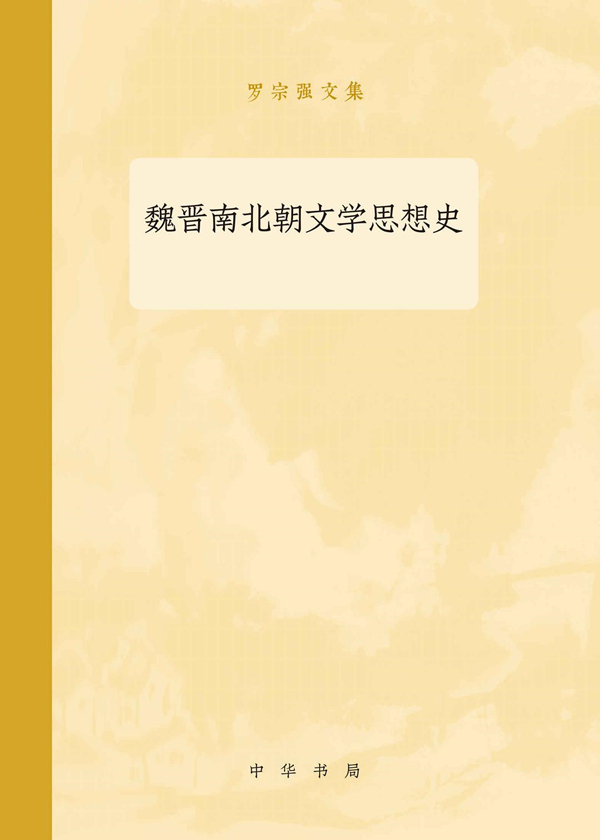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罗宗强/著,中华书局,2019年7月版
第二部书是《读文心雕龙手记》,这代表罗先生的另一种研究方式,即抓住关键词语、重要范畴,从小处切入,结合全篇阐述,再扩大到文论史——典型的“小题大做”方法。书中《释“文之为德也大矣”》《释“惟人参之”》《释“辞来切今”》《释“五言流调”》《释“入兴贵闲”》《释“阮籍使气以命诗”》等,皆由一字或一句切入,扩展开来研究。我深受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以前写过论文《“风骨”之骨内涵再释》《文体意识、创作经验与〈文心雕龙〉研究》等,都学习了罗先生的治学方法。《文心雕龙》是一本非常宏大的书,每次读都能有新收获,关键在于要认真体会由字到句、由句到篇的含义。总的来说,罗先生对龙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将《文心雕龙》放在六朝总体的文学思潮中,观察该书与时代的关联,这是“面”的研究;二是对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这是“点”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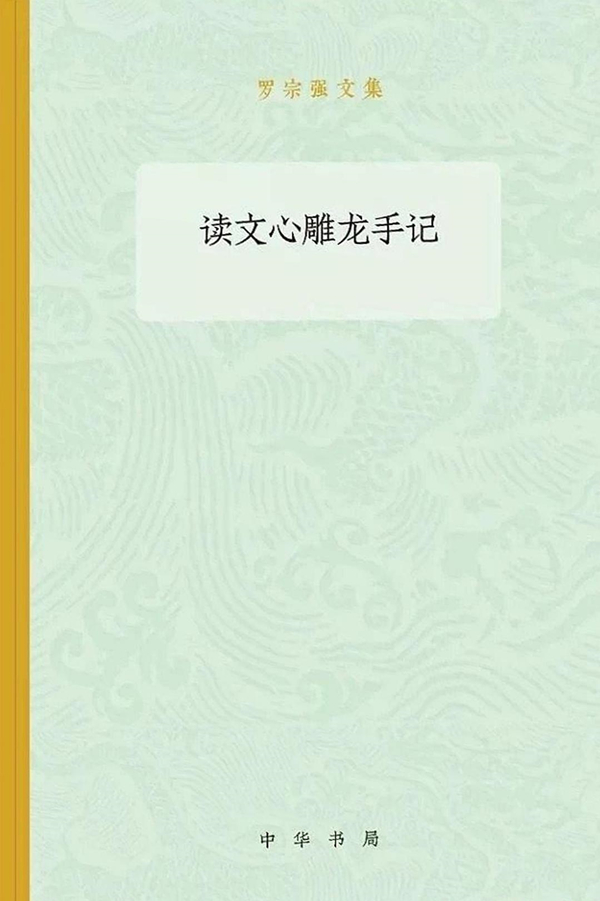
《读文心雕龙手记》,罗宗强/著,中华书局,2019年7月版
《文心雕龙》研究大致有两个方面可供我们继续探索。首先,当我们探讨《文心雕龙》的核心问题文体观念时,实际上还可进一步落实于“体要”。“体”也就是“大体”,是文章的基本内容与主要功能,“要”即“关键”,指主要的表达手段与体貌特征,“体要”包括文体的体式、体貌、创作目的、创作手法、能够达成的效果等,是一个综合的范畴。体要是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核心,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显现于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在研究时必须结合写法来谈,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体特点,与西方文论重分析的特点有所不同。在《文心雕龙》以后,再未出现如此宏大的理论作品,能够与它的整体性相匹敌的,或许仅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我们可能要问,体要既然如此重要,为何刘勰没有单独写一篇呢?我想这大概是由于刘勰将它贯穿在全书之中了。倘若我们在研究中,能将文体研究落实于体要上,或更能突出《文心雕龙》的综合性和实践性。
第二个可供进一步讨论的方向,是关于思潮史和经典的关系问题。罗宗强先生认为,《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倾向和当时的文学思潮是完全一致的,这的确是重要的学术发现,也符合历史的实际。但如果进一步看,只谈一致性可能还是没能真正揭示《文心雕龙》的思想史价值。伟大的作家、批评家,往往有超越时代的一面,他们与时代的关系并不是完全重合的,而往往具有纠正时弊、倡导新方向的意义。刘勰超越同时代普遍思潮的地方,主要体现于“折衷”的观点,他能将各种观点容纳于一个系统中,也就是所谓的“弥纶群言”。《文心雕龙》理论之宏大、思考之严密、内含范畴之广泛,超越了它的时代。罗先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求真”的目的,但思想史的写作,还可以进一步分层次研究。王汎森先生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提出了“分层的思想史”观念,他认为,一流思想家、作家的思想,一旦进入实际的运行,效果是会打折扣的。我们的思想史往往只关注一流思想家的高度和深度,却很少关注思想的实际运行状态。这就需要考虑:刘勰的文学理论,在当时的文坛上究竟落实了几分?是通过谁来落实的?要探讨《文心雕龙》的接受情况,只研究刊刻、版本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读文学作品、读其他文论家的理论,许多时候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文心雕龙》,却汲取了该书的营养。《文心雕龙》对文坛实际的作用与贡献,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陈引驰:左老师讲得非常精彩。罗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既有对于字句作出的非常精细的讨论,也延伸到整体的问题,贡献非常大。左老师阐发了“体要”的问题,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我们既要看到《文心雕龙》与时代的相关性,也要看到它超越时代的地方,对当时、对后代有何影响。英国文豪本·琼森(Ben Jonson)曾说,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时代(was not of an age, but for all time);宇文所安在盛唐诗的研究中,也说李白、杜甫等,在盛唐诗坛中只能算是边缘人物,却有无限的可能性,身后逐渐成为文坛中心。同理,讨论《文心雕龙》时,不仅要注意时代背景,也要注意其特出之处。这是否有点像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能不了解古希腊的悲剧、史诗,但仅此也远远不够,还应看到它对后来整个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有请张健老师。

张健老师线上参与了会议
张健:谢谢各位老师。感谢陈引驰教授、陈特博士组织召集这次会议。我要先向王运熙先生和顾易生先生致敬,我本科时曾给王运熙先生写信,请教如何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王先生回信建议我读《文选》和丹纳的《艺术哲学》,我一直铭记。我曾经跟随祖保泉先生、张少康先生学习《文心雕龙》,后来也一直关注这部书,开设相关的课,也试图写一本关于《文心雕龙》的书,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学习了王运熙先生、罗宗强先生、杨明先生等前辈的著作,以及现代的研究著作。我原来打算在书的绪论中谈谈《文心雕龙》的现代研究,今天我也从这个问题切入吧。
刚刚杨明老师和左东岭老师都提到,《文心雕龙》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对于这个问题,王运熙先生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章学著作,主要目的是谈写作;罗宗强先生认为,《文心雕龙》是一种杂文学的理论。这就引发我想要往前追溯这些问题的来源,也就是:所谓“文章学”“杂文学”等范畴是如何产生和兴起的?这牵涉到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如何建立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王文生先生曾讨论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史问题,他指出,中国文学批评这一学科,是在五四以后,具体来说则是1927年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后才正式成立的。王先生认为,五十多年的研究大致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做了大量的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并拿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中国古代文论;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以后,用正确、科学的文学理论,即马列文论,来指导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有更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建立民族的文学理论。从学术史角度看,这段话说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现代研究,就是拿西方理论来整理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在王文生之前,朱自清早已注意到拿西方文学批评范畴整理中国诗文评的现象,这就是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主流倾向。
现代龙学研究的历史也大致是如此,但问题是,为何一定要拿西方理论来研究《文心雕龙》呢?这实际上涉及所谓普遍的文学观念,即认为世界的所有文学是统一的,这是西方所认定的现代思想的基本特征。在这个观念之下,产生了普遍文学原理的认定。然而,谁代表普遍的文学观念?谁代表普遍的文学原理?很长时间内,西方文学理论被认为是普遍的文学原理,王文生所概括的五十年学术史,正是这种观念的显现。
像这样拿西方观念看《文心雕龙》,自然产生了王运熙先生、罗宗强先生等关注的问题:《文心雕龙》是不是文学批评?是不是文学理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接受西方文学理论时,文学观念就发生了分化,产生“纯文学”和“杂文学”相区别的问题,其依据是英国19世纪批评家德昆西(De Quincey)对“力的文学”(即“纯文学”)和“知的文学”(即“杂文学”)的划分。德昆西的观点最早被日本接受,日本文学理论家太田善男在作于上世纪初的《文学概论》一书中,提出“纯文学”和“杂文学”的观念。这种观念在1910年代引进中国,很快,学者杨鸿烈在论文中,就提出《文心雕龙》所论究竟是纯文学还是杂文学的问题,从“纯文学”“杂文学”二分的视角看待《文心雕龙》的价值。杨鸿烈认为,从先秦到六朝,中国的文学观念是朝向纯文学的观念演进的;至唐代古文运动,恰恰混淆了纯文学和杂文学观念,变成复古倒退。这一观念,后来成为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对整个批评史历史线索的基本判断。杨鸿烈说,《文心雕龙》分文、笔,这是纯文学观念的体现;但又讲“原道”,容纳“非文学”的内容,包含复古思想和杂文学观念。讲“纯文学”的理论,后来被称为“文学理论”;讲“杂文学”的理论,后来被称为“文章学”,今天的文章学,如果要在西方找源头,要追溯到修辞学。然而,倘若不用纯文学、杂文学的观念来看文学,而像M.H.艾布拉姆斯一样,将修辞学等讲文章作法的内容,归为实用批评,从而纳入文学理论,那么王运熙先生等所讲文章学和文学理论的区别,实际上就不存在,《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还是文章学的分别就失去了观念基础。
我举两个例子,来说说现代学者用西方普遍文学原理研究《文心雕龙》时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徐复观先生的研究,他相信普遍的文学原理,深受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的影响,认为文学有思想、媒介、艺术三要素,其中艺术是文学区别于其他类著作的分界。徐先生在此基础上,认为艺术就是形相性,集中体现在“style”(“文体”)。他受到日本学者的启发,认为“style”一词不应译成“风格”,而应译成“文体”,而文体恰恰是形相性,故是文学的基本特征。他从文学三要素的角度看待《文心雕龙》,认为该书论述的核心就是文体问题,即形相性问题、艺术之为艺术的基本特征问题,从而得出《文心雕龙》抓住了文学的基本特点,有极大的现代意义。徐复观把文体分成体制、体要、体貌三个次元,体制是最基本的,体要是内容,体貌是各人写作时形成的独特特征,即现在所说的风格。在他看来,《文心雕龙》讲文体的突出特征,就是与人密切相关,认为人决定了文章的体貌,这与18世纪法国布封《论风格》中“风格就是人”的观点有共通之处,而中国却早于西方一千多年。他就是这样通过比较中国和西方的理论,来认定《文心雕龙》的价值。
第二个例子是王元化先生的研究。王先生不仅相信普遍的文学观,而且相信进化论,认为文学理论也是进化发展的。他在西方现实主义的基本脉络下讲《文心雕龙》,如认为《物色》所论“物色”,相当于西方的“生活”,刘勰讨论文章和物色的关系,也就是西方讨论的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站在进化论立场上,王元化先生认为西方的现代理论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而《文心雕龙》只处于萌芽状态,而用现代理论研究《文心雕龙》,就像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低等动物一样。我们说王先生的观点当然有特殊的语境,但在进化论角度讲《文心雕龙》,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刚才讲到徐复观,徐先生就反对用进化论来讲中国文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徐先生的看法比王先生更可取。王先生曾提出,要在《文心雕龙》的基础上建立民族的文论,但他的论述和口号有基本的矛盾:如果《文心雕龙》只是科学的文论的萌芽状态,还有必要以它为基础建立民族的文论吗?如果它的价值仅在于部分符合现代的“科学”文论,那么有何研究的必要呢?这一百年来,我们用西方文论研究中国文论,却又提出建立民族文论的口号,就导致了非常困难和现实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同样存在于美学领域,像朱光潜提出要建立中国的民族的美学,但倘若先认定西方的美学是科学的美学,那么如何建立中国的民族的美学呢?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想也是在讲《文心雕龙》研究的当代意义时,必须面对的问题。至于将来应该怎样研究,刚才杨明老师和左东岭老师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我很受启发。
陈引驰:谢谢张老师的精彩报告。张老师的《借镜西方与本来面目: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这本书,分析了传统诗文评如何转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讨论得非常精细,分析也很绵密。张老师今天也是在这样的脉络中谈《文心雕龙》。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学术价值,涉及古、今、中、西多个维度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在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领域,研究者都需善于反省前代学者的观点,同时也应注意自身学术观念的历史性。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持有的学术观念,都包含特定时刻的历史因素。

陈尚君老师也参与了此次讲谈会
在讨论环节,几位老师就《文心雕龙》中最重要的文体为何展开了讨论。陈特老师认为,《文心雕龙》的核心是诗、赋等“艺文”,如创作论部分就主要是围绕诗、赋来谈,在刘勰心中,诗、赋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掌握了相对困难的文体,其他文体就不在话下。张健老师强调,这个问题也应分层次看待,《文心雕龙》讲所有文章的基型,一定是儒家经典,而在讨论带有“文学性”的文字时,诗赋应是最重要的。杨明老师认为,诗、赋确实是南朝时深受重视的文体,如《文选》就以赋、诗起首,但很难据此判断对诗、赋的重视已超越了其他实用性的文体。曹丕所言“经国之大业”,主要就是指实用性的文体。在《文心雕龙》所谓创作论的部分,有些比较偏重诗、赋,如《比兴》《夸饰》,但很多篇章,我们今天并不能确断它们都针对诗、赋,这是因为在南朝时期,实用性文章也非常讲究艺术美,如《情采》所论内容和文辞之美间的关系,无论诗、赋还是实用性的文章,都必须重视,《镕裁》《声律》《章句》《丽辞》《事类》《练字》《指瑕》等篇,对实用性文章来讲也很重要,刘勰往往是将诗、赋与实用性文章打通了来讲。左东岭老师指出,《文心雕龙》的基底仍是诗、赋、骈文,但不会脱离经典,刘勰对文章之美和实用功能的认识很复杂,他认为文章无论多华美,也不能损害实用功能,但另一方面,在尊体的基础上,也要争取写得华美。至此,本次讲谈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黄佳敏/整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