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穿越巴尔干的旅程:我看见人类曾经彼此交融、相互残害

图源:视觉中国
【编者按】
没有一个地方的爱与恨,比这里更浓烈。“巴尔干”,一个沉重的地理名词。整个20世纪,这片土地上爆发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屠杀、种族清洗、难民潮和人口交换。巴尔干的故事,关于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关于两次世界大战,关于冷战和南斯拉夫,关于危机、崩溃、分裂和重生。对于旅行作家刘子超而言,巴尔干更像一个形容词,充满伤痛、挣扎、求索和希冀的复杂含义。
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民族主义如燎原大火,以极其暴烈的方式,重新勾画了欧洲的版图,势不可挡地推动着民族的建构:意大利和德国相继统一;奥匈帝国解体;巴尔干半岛上的诸国相继崛起——它们纷纷要求摆脱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基于民族原则,成立主权国家。
如果说在德意志和意大利这样的新国家里,民族主义打破了中世纪小国的各自为政,使其能够结合成符合经济理性的大单位,那么在巴尔干,结果却恰恰相反。“巴尔干化”一词应运而生,用来形容一个昔日帝国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分崩离析的过程。
在的里雅斯特的一间酒吧里,浙江温州来的酒保、克罗地亚来的管道工、塞尔维亚来的建筑工、斯洛文尼亚来的妓女,他们聚集在一起,共享着昏暗漫长的雨夜。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东北部的港口城市,地处亚平宁半岛通往巴尔干半岛的交通要道。
这间小小的酒吧,也是作者刘子超穿越巴尔干的旅程开始的地方。他的目光如一只猎鹰在高空盘旋,视线越过灰色山岩,俯瞰意大利与斯洛文尼亚的边境——在那里,在巴尔干,不同的民族、文化曾经彼此交融、交锋,甚至相互残害。
以下文字选自《血与蜜之地》,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在此鸣谢出版方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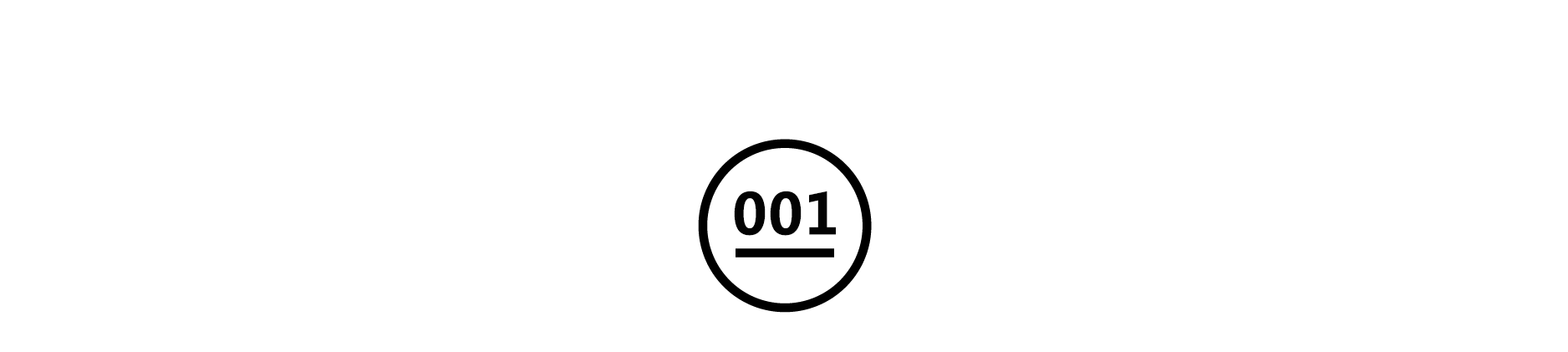
这里的冬日并不凛冽,但一整天都很冷。天空阴沉,飘着丝状冬雨,湿漉漉的街道披上了一层光滑的水膜。树木早就脱去了叶子,光秃秃地立在那里。猛烈的布拉风,从喀斯特高原扑向港口。几只海鸥像被撕破的纸片,发出凄厉的叫声。港口外,亚得里亚海如一面凝重的镜子——波浪前后追逐,披着铅灰色斗篷。
我坐在的里雅斯特一家酒吧的桌边,试图写点笔记,却只是写下了日期。我不时抬起头,抿一口廉价的白葡萄酒,目光望向窗外:连绵的阴雨扰乱了我的心绪,也为眼前这座意大利城市平添几分边陲之感。
这家酒吧位于巴尔干人的聚居区。店面开在一楼,是一栋不起眼的土黄色建筑。上面的出租公寓里住着巴尔干来的工人——这从住户的名牌上可见一斑。酒吧附近,有一所斯洛文尼亚语中学,还有一座建于19世纪的斯洛文尼亚天主教堂。从喀斯特高原下来的斯洛文尼亚农民,正在教堂外面的空地上贩卖香肠和硬质奶酪。
酒吧看上去已有年头,灯光昏暗,墙壁斑驳,靠墙处摆着三台布满划痕的老虎机。一个穿着卡其色背心的男人正沉迷于老虎机游戏,一个留八字胡的老人坐在角落里,安静地阅读报纸,桌上放着一瓶克罗地亚啤酒。
长条形的吧台后面,有个亚洲青年在忙碌着。他的寸头略显蓬乱,似乎已有月余未剪,开始变得率性不羁。墙上挂着一柄绘有“双龙献瑞”的折扇,为这家小酒吧增添了几分不太协调的东方氛围,同时也透露出青年的文化背景。
于是,在点第二杯酒时,我就顺势用中文和他攀谈起来。
他是温州人,1997年出生,十一岁那年随父母和姐姐一起移居意大利。一家人最初在威尼斯的老乡家借宿,后来才搬到这座被斯洛文尼亚环抱的小城。他们做过各种小买卖,直到十二年前开了这家酒吧。客人大多是住在附近的巴尔干工人——因为意大利需要体力劳动者,而工资又远比巴尔干高。
小伙子告诉我,那位沉迷于老虎机的是一位塞尔维亚来的建筑工,而留八字胡的老人是克罗地亚来的管道工。
“他是这里的常客,总是赊账。”
“赊账?”如今,这个词听起来简直有一种古典气息。
“他是按日结算的工人,干一单能赚几十欧元,挣了钱就花光,再去找下一份工作。”温州小伙子说,“意大利本地人的酒吧不赊账,只有我们中国人的店才会这样。所以,他就成了这里的常客。”
温州小伙子望了那人一眼,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些巴尔干人,跟咱们中国人的想法不一样。”
“或许他没把这里当家吧。”我说,“你了解他的情况吗?”
“不太了解。我只是卖酒的,最多提醒他别在这里喝醉。”温州小伙子说,“看样子他应该不是有钱人,不然也不会这把年纪还出来打工。听说他们国家的工资水平很低。”
这时,一位裹着貂皮大衣的女士优雅地走进酒吧。她走到吧台前,点了一杯掺了气泡水的葡萄酒,从皮夹中抽出一张五欧元的钞票,示意不用找零。她转身离去后,温州小伙子低声对我说:“她是斯洛文尼亚人,以前是妓女。”
“这份工作让你知道了不少人的秘密啊!”
温州小伙子笑了:“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从不主动打探。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是把我当外国人。”
“那你觉得自己的家在哪里?”
“当然是中国。”他说,“不过上次回国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温州小伙子说,靠着这家酒吧,父母把他们姐弟俩养育成人。姐姐一年前回国成婚,而父母还留在这里,但一直念叨着落叶归根。他们在的里雅斯特生活了这么多年,意大利语依然讲得不太流利,出门办事往往需要依赖儿子帮忙。
“我在这边的大学里学习土木工程。当时有传言说,中国企业会接手这里的港口。我想着或许能找到一份工作。后来,因为政治原因,港口的事一直没有进展,我这才决定来酒吧帮忙。”温州小伙子拿起抹布,擦了擦吧台,“这里的工作机会没有国内那么多。”
“那你考虑过回国吗?”
“经常想。可回去又能干什么?现在国内的竞争太激烈了。”
这时,克罗地亚管道工步履蹒跚地走向我们,腿脚显然有些问题。他戴着厚底眼镜,脸上的皱纹像风琴的琴箱,双手骨节突出,如鹰爪般枯瘦。他又点了一瓶啤酒,依旧是记在账上。“我们都担心他哪天回去了。”温州小伙子说。“回克罗地亚了?”“不是,死了。你能看出他身体状况不太好吧?他跟我提过,他的腿是在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中受伤的。”
我轻轻点点头,目光追随着那位克罗地亚管道工。他的身影像一辆风尘仆仆的旧汽车,身后是蜿蜒在巴尔干山间的道路——我即将踏上的道路。

图源: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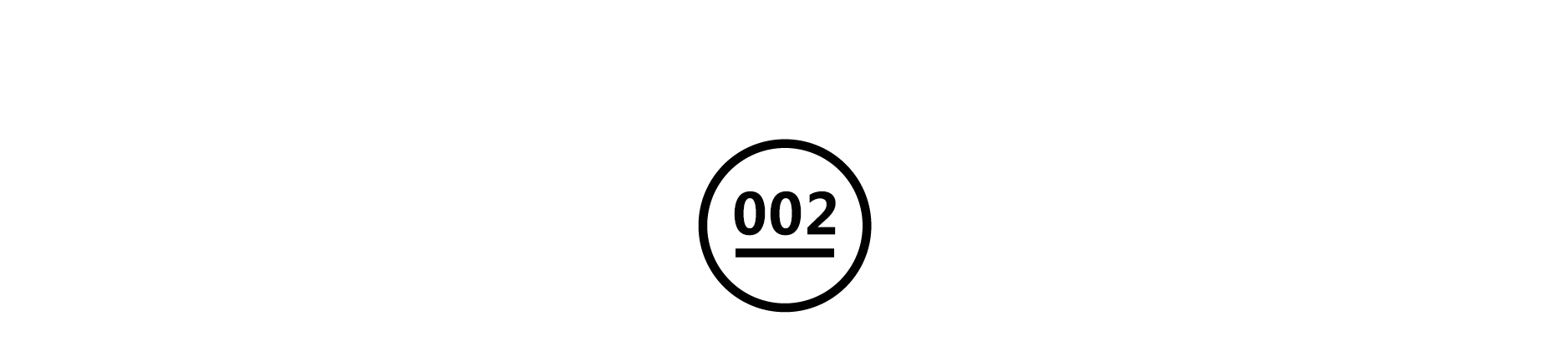
巴尔干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故事;关于暴力和战争的故事;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关于冷战和南斯拉夫的故事;然后是危机、崩溃、分裂并最终走向重生的故事。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这些故事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我时常面对世界地图,紧盯着巴尔干半岛,想象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上演的地点。对我来说,巴尔干似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更像一个形容词,充满伤痛、挣扎、求索和希冀的复杂含义。
现代意义上的巴尔干,其实是近两百年才形成的概念。从15世纪到19世纪,巴尔干半岛最普遍的地理称呼是“欧洲的土耳其”或“鲁米利亚”,即奥斯曼帝国征服自原来拜占庭帝国的“罗马”土地。
那时,民族的概念还未成形,人们的身份认同几乎完全依附于宗教信仰,而非民族身份。这种缺乏民族认同感的前现代状态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当携带着民族主义火炬的活动家们踏入现今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时,他们惊诧地发现,混居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只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对于“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的民族标签茫然无知。
“民族”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思考世界的方式,让我们得以理解周围的环境和历史,但人们并非天然地从属于“民族”。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并非人类心理的固有成分,也不根植于我们的生物学本质。
人类对于拥有血缘关系的小社群容易产生归属感,但要让人类对数以千万计的陌生人产生同胞之情,则需要社会建设的巨大努力。这种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思潮,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显现了。
在的里雅斯特郊区,有一条历史悠久的“拿破仑大道”,就见证了军事征途和思想交融的历史。这条五公里长的步道,从的里雅斯特的奥比齐纳镇一直延伸到著名的起泡酒之乡普罗塞克村。它沿着喀斯特山脊延展,远离海风的侵袭。的里雅斯特的居民喜欢在这里散步骑车,享受休闲时光。
在启程前往巴尔干之前,我特意踏上了这条步道。因为正是拿破仑的军队,像播撒种子一样,将民族主义的理念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某种意义上,拿破仑大道是一条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路线。
1793年,面对反法同盟的进攻,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呼唤人民团结一心,捍卫家园。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释放出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而它的理论源流可以追溯至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启蒙学说。
拿破仑对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的入侵,直接刺激了当地民族主义的产生。在伊利里亚地区,即今日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也开始出现一种斯拉夫民族的认同,最终蔓延为泛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
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民族主义成为欧洲社会政治思想的巨浪,势不可挡地推动着民族构建。它如一场燎原大火,以极其暴烈的方式,重新勾画了欧洲版图:意大利和德国相继统一;奥匈帝国解体;巴尔干半岛上的诸国相继崛起——它们纷纷要求摆脱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基于民族原则,成立主权国家。
在很多欧洲自由主义者眼中,巴尔干的现实很难符合他们心中民族自决的理想。如果说在德意志和意大利这样的新国家里,民族主义打破了中世纪小国的各自为政,使其能够结合成符合经济理性的大单位,那么在巴尔干,结果却恰恰相反。
从这时开始,“巴尔干”的称谓开始获得更广泛的使用,其负面含义也随之凸显。“巴尔干化”一词应运而生,用来形容一个昔日帝国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分崩离析的过程。

图源: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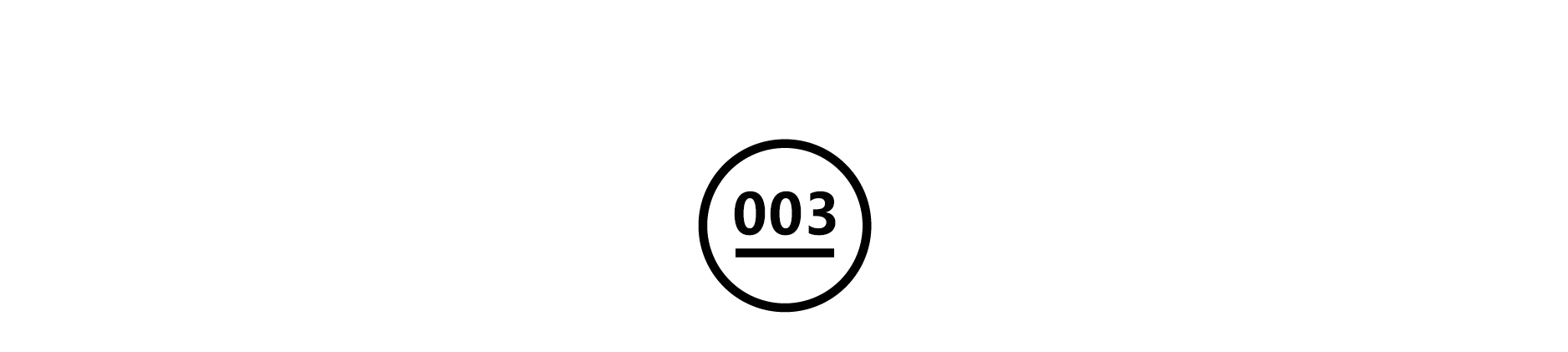
巴尔干的暴力时代由此开始。整个20世纪,在这片土地上爆发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屠杀、种族清洗、难民潮和人口交换。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因此写道:“在这些人民中引入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结果是造成屠杀……那样的屠杀其实只是相互依存的邻邦,被致命的西方观念煽动而进行的极端民族斗争。”
到了1990年代,巴尔干继续呈现它的故事,此时的我已经成为这些故事的见证者。记忆中,每当《新闻联播》临近尾声,那些远在巴尔干半岛的声音就会短暂地传入耳畔:南斯拉夫的解体与内战,流离失所的难民,残酷的种族清洗和大屠杀,还有北约“外科手术式”的轰炸。播音员的音调平静而稳定,仿佛所述之事与我们并不相干,而是发生在遥远的星球。
然而,1999年5月7日,北约的五颗精确制导导弹从不同方向击中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三名记者牺牲,数十人受伤。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天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走上街头,高举横幅和旗帜,抗议北约的野蛮行径。那一幕,让当年的我想到了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历史似乎在某个瞬间重演,而同样的情感穿越时空。
从那一刻起,巴尔干在我心中不再是遥远的异域,而是变成了一片我决定日后踏足的土地。时光荏苒,二十余年转瞬即逝。2022年冬天,巴尔干再度浮上心头。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奥地利格拉茨的美术馆,看到了波黑艺术家塞拉·卡梅里奇的作品《波斯尼亚女孩》。在这张黑白照片上,女艺术家身着白色背心,目光直视前方。照片上叠加着对波什尼亚克族女性恶劣的诋毁言论,内容源自一名荷兰士兵的涂鸦。
1995年7月,这名荷兰士兵所属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未能阻止塞族军队进入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最终导致大约八千名波什尼亚克族人遭到屠戮。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严重的一起种族屠杀事件。
接着,在维也纳的陆军历史博物馆,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展览再次让我深受触动。展示柜里陈列着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时所穿的天蓝色制服。领子右侧是一个直径仅几毫米的破洞——正是这枚破洞,在不经意间引爆了民族主义的火药桶,推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帝国的坍塌与千万生命的消逝。斐迪南大公的遗体先是从巴尔干腹地运抵的里雅斯特港,再由铁路运回维也纳。这让我想到,或许可以循着这一路线,从的里雅斯特出发,开始我的巴尔干之行。
走在拿破仑大道上,我一边听着阿尔弗雷德·卡塔拉尼的咏叹调《我即将远行》,一边幻想着即将开始的旅程。
亚得里亚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透过松林和山毛榉,可以看到镶着金边的云朵在海上聚拢。一辆货轮划破海面跳荡的金币,缓缓驶向港口。
喀斯特岩壁上,两个女孩在练习攀岩。一只猎鹰在高空盘旋,目光越过灰色山岩,俯瞰意大利与斯洛文尼亚的边境——在那里,在巴尔干,不同的民族、文化曾经彼此交融、交锋,甚至相互残害。
民族原本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这种抽象的想象驱使无数人为之杀戮或赴死。我甚至觉得,当西方给予这些国家定义其民族的方式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让它们毁灭自身的武器。
往事像年深日久的油漆,缓缓剥落。2013年,我初次抵达的里雅斯特时,对穆贾村并未太过留意。那是意大利与斯洛文尼亚边境附近的一个宁静渔村,位于的里雅斯特以南五公里处,一条边境线从穆贾的喀斯特高原上横穿而过。
午后,我走出旅馆,乘公共汽车前往穆贾。我要从那里启程,一路穿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波黑、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希腊,最终抵达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雅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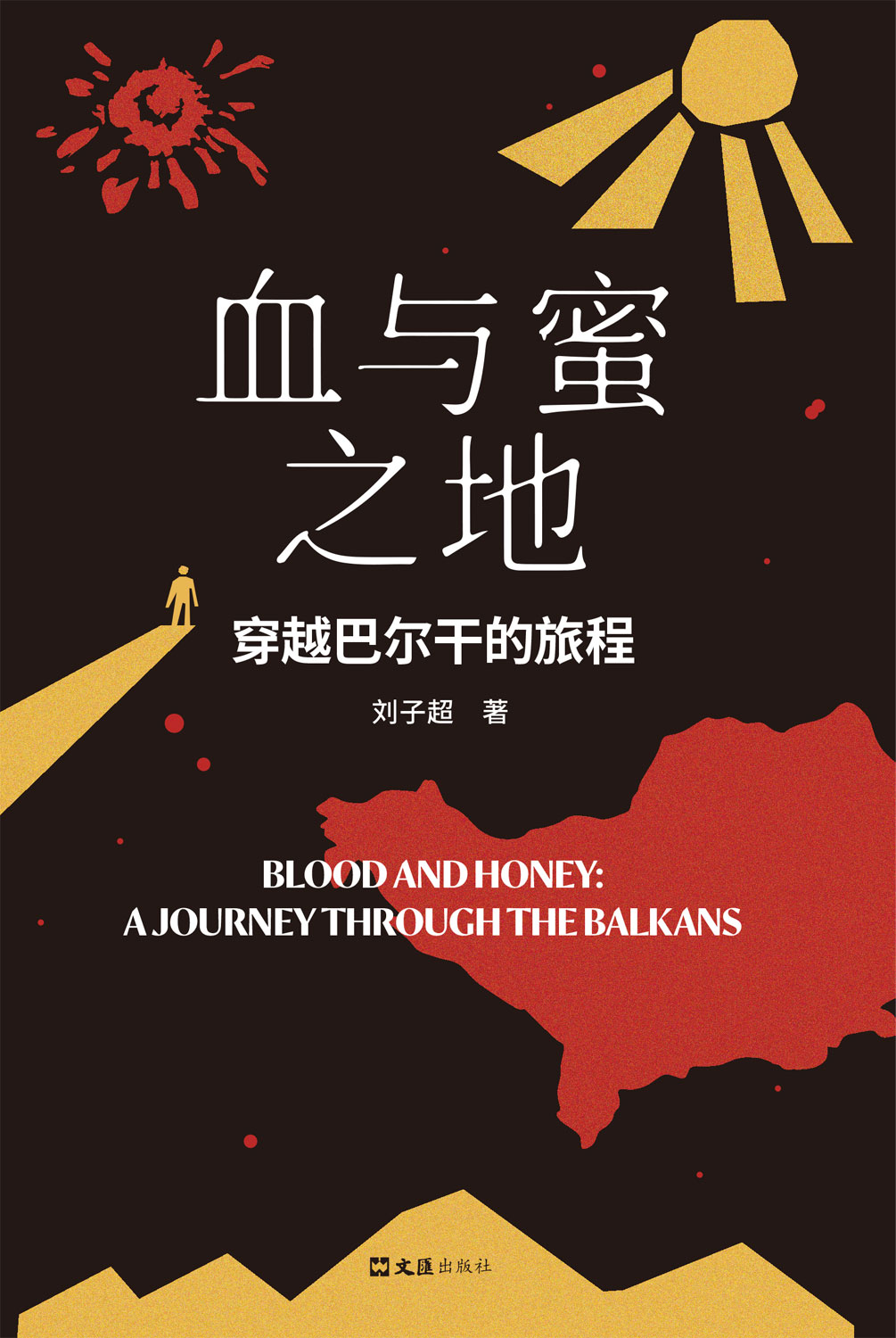
《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
作者:刘子超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品方:新经典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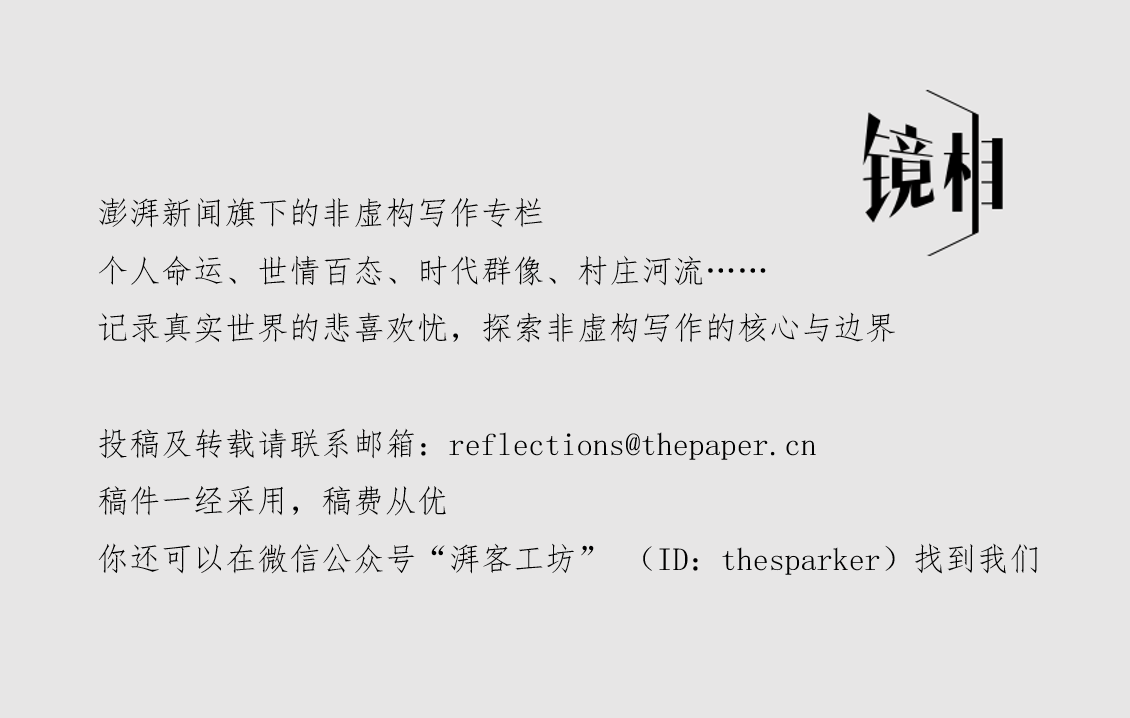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