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读丨城市作为理解社会的窗口——《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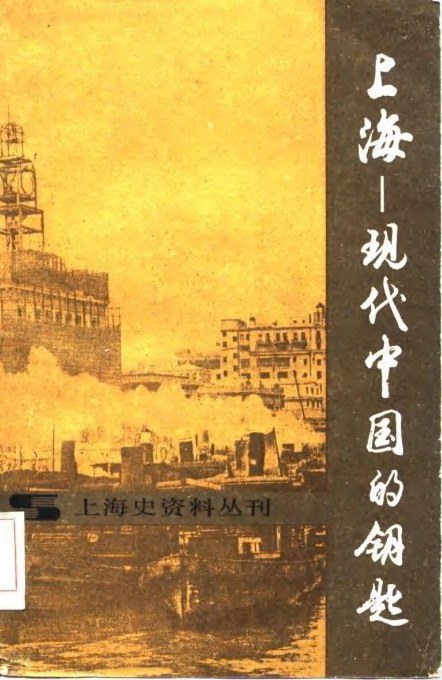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中国学家罗兹·墨菲在中国政局动荡、世界局势变化莫测之际写下了一部经典的上海史著作——《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1]。墨菲在序言中直陈其主旨,是希望在几乎所有有关上海和中国的讨论都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下,“尝试在上海和近代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去论述这一主题,就可以不管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或可能发生的变化,使研究同样具有意义和启发性”[2]。因而,此书更倾向于将上海城市视为一种经济地理现象,并着重探究地理因素对于城市发展的作用。
然而,就目力所及,笔者发现国内学界对这部著作的书评和引论,多意在强调墨菲对上海之于中国意义的判断,但是却忽略了该文本最鲜明的特征以及罗兹·墨菲由上海研究牵发的亚洲研究。罗兹·墨菲是一个从上海研究出发,继而进入中国、亚洲研究的美国学者。墨菲在上海研究中引出的问题意识,随后也成为他进行中印比较研究以及亚洲研究的出发点,并在对上海和亚洲主要港口城市研究的基础上构筑了以城市为中心的亚洲论述。而他的亚洲研究,则鲜明地体现了城市作为理解不同文明社会窗口的特点。
鉴于此书在国内外上海史领域内的广泛影响,本文将首先梳理其中译本的翻译状况,然后将该书置于西方学术以及墨菲整个学术研究的脉络体系中考察该书的意义及价值,最后尝试指出墨菲城市研究的进路及其意义和价值。
一、《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译本翻译状况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译本是经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仲礼教授推荐,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章克生、徐肇庆、吴竟成、李谦所译,最后由章克生校订、加注、定稿。张仲礼教授昔日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因此对于海外中国研究比较熟悉。1984年张仲礼升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时,分管历史所,悉心关注历史所的工作情况。当时历史所承担的有“上海简史”“上海工人运动”“上海史大事记”三个上海市重点项目,张仲礼副院长曾多次听取项目负责人的汇报,并提出许多指导性的改进意见。[3]张仲礼院长的留美背景以及在主持工作时对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视,让他对国外学术研究状况颇为关注。因此,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向历史所的研究人员推荐翻译罗兹·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而后该书中译本于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至于为何推荐该书。从国内的背景来看,概主要出于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实现现代化成为国家目标。现实环境的改变致使学术视角随之改变,学术研究开始关注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而城市现代化则被当作典型进行研究。再者,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步伐加快,也是重视城市研究的重要背景。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研究上海近代化的问题,可以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所借鉴和启发。而从学术研究上看,“上海由一个普通的海滨县城,发展成一个多功能的世界闻名的大都市,近代东方第一大港” [4]的起因,也即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当时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张仲礼教授曾在1988年首次举行的上海史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谈到自己非常赞成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的观点,即其中既有国际因素、租界因素,又有地理因素、人口因素。[5]
此外,张仲礼教授似乎与罗兹·墨菲也有一些交集,中译本译者在卷首语中言张仲礼院长跟墨菲是昔日的同窗,而张仲礼院长也称呼墨菲为自己的老同学[6]。根据两人的履历来看,罗兹·墨菲于1946年进入哈佛大学,1950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1952-1964年间在华盛顿大学教授亚洲研究和地理学。而张仲礼院长1947年进入华盛顿大学,1953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而后于1953-1958年底在该校经济系、远东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副教授等职。可见,两人求学时间大致相仿,1952年之后更是同处华盛顿大学。《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1953年出版,并在当时就引起广泛关注,相关书评多达十余篇。考虑到此时张仲礼教授和罗兹·墨菲同在一所学校而且具有共同研究对象,两人可能由此进行过更多相关学术交流和探讨。因此,随着1980年代译介西方经典作品的兴盛,张仲礼教授在关注上海史研究的过程中,推荐翻译这本由自己的老同学所撰写并曾在西方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上海城市研究作品,也是十分自然。
从《钥匙》中译本翻译的质量上看,译文清楚、流畅、准确,基本上没有删节、误译、漏译。这跟本书的译者之一章克生先生有很大关系。章克生先生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学术委员、编译组负责人。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长期从事编译方面的专业工作,精通英文,通晓法文、俄文,并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古汉语造诣也较深。[7]在历史编译工作中,他认真严谨。而且他认为“作为一个历史专业的编译人员,除了政治条件外,在业务上要做到:一、透彻地理解外语原著,译述时忠实反映原意;二、熟练地掌握汉语,译文务求通顺、畅达,尽可能表达原文的体例和风格;三、通晓专业知识,译文要符合历史专业的要求”。[8]毫无疑问,《钥匙》中译本确实达到了上述要求,而且译者费了很大功夫对原文中的历史事实、数据进行了考订和修改,这让《钥匙》的中译本相比于原著更少有错误,也更能为中文世界所接受和认可。
具体而言,译者对原文中许多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的内容进行了考订、修正,并在译文中直接呈现出来。比如:《望厦条约》签订的时间,原文是1843(p16),译文修正为1844(p18);泥城之战的时间,原文是1853(p16),译文修正为1854(p18);上海特别市的成立时间,原文1928(p17),修正为1927(p19);道路委员会设立时间,原文是1845(p29),译文修正为1846年(p34);长江流域的面积,原文750,000,000平方英里(p45),译文修正为750,000 平方英里(p55);三角洲地带面积,原文200,000,000平方英里(p45),译文修正为 20,000平方英里(p55);黄河从河口溯流而上可航行的水道,原文是25英里(p47),译文修正为250英里(p56);英国政府撤销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独占权,原文是1834( p111),译文修正为1833(p130)……这类修正据统计约有二十多余处。
另外,译者也对原文内容进行了补充,并根据历史知识作了若干修改,比如,永定河和大清河在天津注入的河流,原文是白河(pei river)(p54),译文修正为海河并将原文未说明的永定河和大清河标识出来(p63);陇海线的终点,原文是海洲(Haichow)(p54),译文修改为连云港(p64);1930年代连接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三条河流,Siccawei,Soochow,Woosung creeks(p92),译文修改为肇嘉浜、苏州河、蕴藻浜(p109);1936年,沪宁、沪杭线铁路里程,原文是753公里,占中国本土铁路总里程的8.3%(p90),译文修正为612公里,占中国本土铁路总里程的6.3%(p108),同时,译者还将该原文注释中笼统的数据来源信息补全。如此种种,可见译者对于这本书的准确性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不仅如此,中译本还增添了大量译者注。译者注不仅详细注释了文章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同时也表达了不同于国外学者的观点。这种在不修改、删节原文内容的情况下,同时保留原著的风貌和表达不同见解的做法,则更体现了译者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
然而,该译本也不免有一两处疏忽,比如原文福均估计苏州、南京、宁波的人口各为50万(p66),译文则错写为500万(p82)。同时,在翻译上也有若干的错误和语句不连贯,比如第十一章,墨菲评价共产党对待上海的态度上,认为“当共产党置身局外,袖手旁观时,对上海提出指摘,那是自然……”(p202),而译文则误译为“当共产党置身局外,袖手旁观时,人们对他们提出指摘,那是自然……”(p245)此外,中译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呈现原著本来的章节结构布局,而这一缺陷让我们无法从整体结构上把握墨菲主要论述的主题,从而忽视文本本身的立论起点。原著的章节结构布局主要展现在目录上,目录除第一章“序言”外十章内容,被原著者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环境(The Setting),包括二至六章的内容,处理了上海人口、地理条件、历史发展、特殊政治等问题;第二部分是关键功能(Key Function),包括七至十一章的内容,处理了交通和内陆腹地、贸易、粮食供应问题、工业等问题。在论述上海是现代中国工商业中心这一论点上,两大部分各有不同的侧重点,而这些不同侧重点呈现了1920年代以来美国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发展的若干特征。中译本未将原著的章节布局展现出来,留下一些缺憾。
二、风起海上:上海之于中国的意义
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而此前有关中国城市的作品,多为游记、指南、年鉴及其他描述性的著作。[9]近代以来,上海作为五大条约口岸之首,所以有关上海城市作品也名目繁多。早期如福均、裨治文、麦都思等人的游记和见闻记录以及之后出现的各种城市漫游、指南、年鉴等其他作品。[10]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城市研究开始有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性著作出现,这主要是几部有关上海城史著作:兰宁和库寿龄合著的《上海史》、梅朋和傅立德合著《上海法租界史》、卜舫济著《上海简史》[11]。此外,还有各类通俗性的介绍、旅游指南以及有关上海各方面的研究。其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是传教士、行政官员、商人、记者、冒险家等,他们居留上海多年,有对上海最直观的观察与了解,但却很少有专业的学术性研究。
二战结束之后,随着美国中国区域研究的兴起,有关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开始不断涌现,其中也有少数以上海为主题的学术性论著。其中《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即是代表之作,该书至今都是海外上海城市研究的经典作品并对国内产生很大影响,其关于上海之于中国意义的出色分析至今仍被学者引论。但仔细阅读文本,不难发现该文本的立论起点、研究取向、分析方法与同时期的上海史书写模式并不相同。从一方面看,相较于二十世纪20年代以前的描述性文献资料,它更是一项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从另一方面看,相较于纯粹的史学研究,它更倾向于历史地理研究。这表现为,虽然从时间跨度而言《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论述了上海自开埠之后的百年历史变迁。但不可忽视的是,它也在研究中采用城市地理学取向,关注城市的选址、位置、交通、城市与腹地关系、城市格局等方面。并且在更广范围内,“把城市视为经济现象并连带关注其社会、政治方面,以在城市发展或衰落的过程中寻求定义城市的功能或者城市在它所服务更大区域的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12]
因而,《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不仅是一本对上海城市进行宏观论述的学术性分析著作,同时墨菲也采取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上海城市社会进行综合、立体的分析性解释。美国地理学家、亚洲区域研究专家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S. Ginsburg)曾从地理学以及城市研究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过评价,他认为“这是美国首批对中国大城市进行地理研究的著作之一,它的出版为原本很少有学者涉足的中国城市化研究贡献了一本杰出的著作。对地理学家而言,本书以上海为例阐明了研究外国城市的方法论问题;对非地理学家而言,本书有助于展示地理学方法对城市化研究的有效性和实用性。”[13]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最受到广泛认可的是,作者从经济地理角度论证了上海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而墨菲着手从事上海研究,则是源于他对上海崛起为世界第五大城市这一异常现象的困惑。墨菲在其自传中提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在中国从事救援工作期间曾两次到过上海。第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两周后,他去探查上海是否需要紧急救援,特别是被日本人关押在城市西郊大集中营内的平民收容者是否需要帮助。然而,他第一次到上海时就感受到,“我一点都不喜欢上海。在刚看到铺砌的街道、有轨电车和西式的饭店之时,会有一瞬间的兴奋。但是,对于刚从中国西部森林地带出来的我而言,上海看起来更像西方而不是中国,而且是一个低级版本的现代西方。”[14] 1946年初,墨菲第二次来到上海,他感到上海似乎被令人厌恶的商业贪婪、商业化性交易所占据,并为此感到困惑。
因为,从西方观念来看,世界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是行政中心,一是高度整体化和商业化经济体制的中心。[15]而上海却在中国“现代铁路网尚未兴建,全国性市场尚未形成,中国国内其他商业大都会尚未出现以前,在短短一百年期间,从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组织中发展成长……为世界主要都市工业中心之一”。[16]这着实让人感到诧异,而当时中外学者对于上海崛起原因的解释,多强调租界、外国主导势力主导上海发展的看法。这也让久处于中国西部地区、一直通过运输物资接触中国交通系统的墨菲深感疑惑,如果从中国内陆看上海,上海是另一个中国吗?如果是,上海对于中国又有何意义?上海又是如何发展现代化?
墨菲基于其二战期间来华的经历和地理学学科背景,从他非常熟悉的陆路交通运输入手,选择地理学取向论证上海城市的经济发展及转型。这种视角在当时却是独树一帜。因而,墨菲在对上海近百年历史演变的阐述中,着重从地理角度解释上海之所以能在开埠之后迅速超过广州等早期通商口岸,一跃成为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心、工商业中心。在具体内容上,墨菲主要阐发了三个主要观点。
第一,墨菲指出,虽然上海的地质条件不理想,比如具有地基不稳、排水不利、泥沙淤积等问题。但是,上海的位置条件却是极好:面向陆地,上海位于富饶平坦的长江三角洲、长江入海口处,长江及其支流把流经中国物产丰饶的核心地带的水源收容下来,最后都倾泻到黄浦江口;面向海洋,上海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以及位于往来北美西海岸、日本、中国以及东南亚之间世界环形航线之西不到一百英里之处,所有西太平洋的主要航道都在那里汇合。[17]上海所兼具的陆地和海洋优势,让中国沿海的多数港口城市无法与之匹敌。随后,墨菲通过海关贸易数据等资料统计和分析上海在不同时期各项贸易指标的数值及其所代表的意义,以此论证上海在开埠后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获得迅速发展,经历了从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到全国工商业中心的转型。
在大多数人认为上海近代发展主要是受外部冲击影响的情况下,墨菲独辟蹊径分析论证地理因素对上海近代发展产生的更根本性影响,这种不同的视角和解释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和赞誉。英国东南亚研究专家费舍尔(C.A. Fisher)指出,“中国一旦卷入世界贸易潮流之中之后,按照地理逻辑可以确定在中国两大自然公路(长江和沿海航线)上定会出现一个主要港口。墨菲支持这一论点的证据是有力的。”[18]其次,由于中西方城市发展的起源不同,西方城市的发展基于农业技术的变革以及机械化交通的扩展。因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许多西方学者对工业革命之前是否有地区可以发展出或能支撑一个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抱有疑问,因为工业革命之前各地先天的本土技术和主要的交通运输系统可能无法支持这样规模的城市。墨菲有关上海粮食供应的论述,有力反击了这一质疑。证明了一个拥有三四百万人口的城市,粮食可以通过距上海不超过100公里的内陆腹地提供,而不需要依靠国外进口。[19]上海也成为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用以表明水道在向大工业城市提供食物、原材料和市场,以支持大工业城市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无论地理因素在上海崛起中占多么重要的位置,政治因素,特别是西方势力在上海崛起中产生的影响却始终是无法绕开的一点。墨菲也没有忽略上海崛起过程中政治因素的影响,他认为“外国控制所提供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安全保障在上海早期发展成长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但一旦长江流域根据条约对外贸易开放,地理位置的因素就在现代上海的成长发展中,起着支配全局的作用。……即使外国侨民从他们现代化房屋搬走,回到家乡,它依旧是一座大城市。”[20]甚至在二十世纪40年代末上海处于封锁状态时,墨菲仍对上海的未来抱有乐观的预测,认为“一旦东亚恢复和平之后,上海经济地理上的优势,同样会使上海在未来的日子里重新繁荣昌盛。”[21]
在对政治因素的具体处理上,墨菲把西方势力在上海崛起中所发挥的作用,放入上海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来解释。他认为西方势力在上海早期发展曾起过决定性作用,是上海早期发展的原动力,并且在之后的发展中也从中获得助力。然而,一旦上海地理逻辑背后的经济优势显现之后,即使没有政治因素的加持,它也仍会继续成为一座大城市。墨菲的分析一部分符合西方当时主流观点认为西方殖民势力在亚洲殖民/半殖民港口城市崛起中发挥重要影响的认知。而另一部分有关地理因素在上海未来所能发挥作用的解释,考虑到当时中国政治环境的影响,不少西方学者对上海在1949年之后的发展,地理因素能否仍起决定性的作用抱有很大的疑问。现今,上海再次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国际化大都市,也就印证了墨菲所强调的影响上海发展内在因素的重要性。
第三,墨菲清晰而有力地指出上海之于中国的意义,这在当时并未被西人所认识到。墨菲指出,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西方人才注意到中国长期进行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上海才是推动现代中国变革的最大功臣。他断言,事后的认知将会揭示“上海在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和经济变革上,在给中国讲授西方贸易、科学、工业课程上、在提供该项课程可能作出成就的榜样上,上海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23]也即现代中国在这里诞生,上海包含着变革中国的种子。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24]墨菲的这一论断,将上海之于中国的意义清晰有力地概括出来,为此后国内外上海研究学者所认可。
当然,也有西方学者对墨菲的这一论断表示质疑。芝加哥大学亚洲城市和地理研究学者诺顿·金斯伯格教授的批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没有人会毫无保留地赞同墨菲有关‘上海及其发展模式是现代中国的缩影’,或‘中国的经济革命和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样在黄浦江边建立了最初的现代化根基’,‘或中国人错误地认为二十世纪的上海主要是由外国人所创造’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上海像孟买、加尔各答和香港一样,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来性,但上海众多人口在很大程度上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一小群外国精英需要他们的服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开始转向到西方的商业主义。直到外国人被迫退出之后,上海才变得中国化”[25]。又或者,“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所在地可能是广州,甚至是香港,而不是上海。诚然,民族主义的种子是落在上海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但上海更主要是由富裕的上海地主组成,他们是现代中国的企业精英,而且相比国家意识,他们更具国际化的思想”[26]。“同样的,墨菲认为上海是一座置于农业文明之上的城市,这种说法也具有误导性。上海的意义可能更在于它作为西方直接扩张的产物或飞地而出现,然后通过置身于中国之中,连接中西之间的贸易。”[27]
诺顿·金斯伯格评论主要指向的是上海的性质问题,他认为上海的意义更在于充当沟通中西的桥头堡,是西方的飞地。上述观点,其实代表了当时西方学者、作家的一种普遍认知,即认为上海是西方帝国主义者用于剥削中国其他地方的堡垒,是一个中国的西方城市。不仅如此,民国之后,随着民族主义的影响日益增长,中国政界、学界的重要人士在论及上海时,都较为强调上海作为道德堕落、天堂和地狱同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本营等罪恶的方面。如,李大钊和戴季陶就以通商口岸为具体的例子谴责城市的堕落和寄生性;傅斯年、郭沫若、周作人等也多为谴责上海社会道德堕落。因此,国内外的评论者都将关注点聚焦在上海的殖民特性上。
墨菲则认为即便当时的中国两个主要政治势力——国共两党都曾谴责上海因外国统治而带有的西方特质,但即使在外国统治最为鼎盛的时期,上海也并非完全属于西方。它既是由外国人创建,同样也是由中国人创建的城市。直到中共掌权之后,它才在政治和经济上成为中国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李欧梵指出,上述认为上海是一个西方城市的观点,暗含有后殖民理论中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有绝对权力的假设。[28]但这种理论假设来自非洲和印度的殖民经验,上海与之不同,上海人并没有把自己视为殖民者的“他者”。中国和印度的经历也很不同,中国遭受了欺凌,但从未完全被西方国家据为殖民地。
三、“另一个中国”:由上海性质问题引发的讨论
墨菲有关上海是现代中国钥匙的论断深受认可,以至于二十年后,当墨菲在《外来者:西方人在印度和中国的境遇》[29]中从更宏观背景中进一步探讨上海之于中国意义而阐发不同观点时,却引发学界的一些争论。
法国中国学家白吉尔教授首先在1977年有关上海的会议上,指出墨菲对上海在推动中国现代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观点发生了转变。[30] 也即是墨菲曾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信誓旦旦地告诉众人,上海通商口岸近百年来的历史变迁是近代中国的缩影,它通过自身的示范效应将西方模式传达到中国广大的内陆腹地,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和催化剂。然而,《外来者》却推翻了上述结论,转而认为上海作为西方渗透的桥头堡,它对中国近代发展几乎没有起多大作用。西方人在中国建立的殖民港口城市不过是中国广大海洋中孤立的小岛,而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就好似在一片汪洋之中掀起一阵风浪,只在中国边缘的通商口岸地区激起阵阵涟漪。白吉尔教授认为,墨菲偏离了以前的正确认知,上海并非孤立于广大中国海洋中小岛。
国内学者也有相应的回应。比如,熊月之教授也认为墨菲在《外来者》一书中修正了此前上海对中国近代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论断,前后观点差异悬殊。“对于西方的回应,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上海不是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没有改变中国,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31]曾对墨菲《外来者》一书有过评述的张笑川也认为,两部著作关于上海的论述有显著差异。“《局外人》强调通商口岸与中国经济的隔阂,指出上海并不能代表中国。这一结论一反其早年著作《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认为上海是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的论断”。[32]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对于墨菲前后观点转变的讨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上海在推动中国现代化所发挥作用(或者是有效性上),对于这一问题,墨菲的判断从来都是一致的。即上海在推动中国现代化方面是不力的。比如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他认为,上海对乡村的影响几乎为零,“传统的中国绵亘,差不多延伸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在乡村,人们看不到上海影响的任何迹象”[33]。张仲礼教授也指出墨菲认为“同西方城市相比较,中国传统城市封建色彩浓厚,到了近代尽管有上海这样的城市兴起,中国城市也不能担当起现代化的重任”。[34]在《外来者》中,墨菲进一步检视其原因,他指出一方面中国传统体制如生产组织、社会运行制度、文化传统在以上海为代表的通商口岸中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使上海展现出两种体制并存的现象;另一方面从通商口岸与其内陆腹地的关系看(贸易),上海对于其内陆腹地产生的影响也较小。如此,上海不仅自身的现代化都出现问题,更不用说在推动中国现代化上不力。
另一是,由通商口岸在中国现代化不力,引出的上海性质问题。墨菲认为,上海作为西方势力渗入的前沿阵地,如果它本身以及它在推动现代化方面不力,那么上海通商口岸代表了一个与真实中国分离的世界。白吉尔教授对此并不认同,她指出,上海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是一个与中国隔离的地带,主要是由于1949年之后上海模式的终止。西方学者通常由此出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虽然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发展工业化,但在他们眼中上海代表着受外国人支配的殖民地发展类型,而且上海消费品工业盛行、忽视原材料和燃料产地、依赖进口、局限本地市场等特征,都说明上海没有与整个国民经济融合在一起。如墨菲所言,它是中国广大海洋中孤立的小岛。[35]
然而,白吉尔教授却认为,上海作为西方模式的输出口,它对内陆地区的影响,可以随着不同的时间发生改变。她认为此前关于上海性质的研究,不管是如墨菲所设想的上海是一个同中国隔开的外国地带,还是上海是两种互不让步的文化进行接触的一个享有特权的地方,或者如费正清(J. K .Fairbank) 所说的, 这是一个两种社会的价值和习惯部分地融合在一起的共管的中外基地,多数都是通过制度和经济的研究来探讨这些问题的。而且研究的时间通常集中在19 世纪后期和20 世纪早期,这段时期起初是上海模式正在形成,后来就正常运行的时期。而通商口岸地位下降的时期,也即是1919-1949时期却很少有学者研究。白吉尔认为通过对这一期的研究,指出西方介入上海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一直都在延续,比如上海的工业化以及同时发展的外国技术继续存在,上海与世界市场的相对结合使它能逐步了解的国际事务相协调、几代中国实业家通过与外国专家接触,增加了才干,扩大了眼界。这些及其他在上海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所留存下来的特点,继续留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之中。
其次,白吉尔还指出一些学者认为,如果上述这种进步仅局限于通商口岸,或者这种进步仅加重了上海与中国其他省份之间的二元结构。在通商口岸与乡村之间截然对立的观点下,人们认为当传统的经济制度阻碍了革新力量扩展时,由通商口岸制造或进口的货物在内地扩散就毁灭了农村中能工巧匠的技艺。这样,在通商口岸发展与农村悲惨境况之间存在一个精确的关系:每一次灾荒、每一次内战,就毁坏了农村一方;同时给通商口岸带来进口、人口和活动能力的增长。但是,条约口岸与农村之间,一个被摧毁,另一个才能获得发展。这是在战争期间显示的状况,在和平时期农村和通商口岸之间更多地互相连接和依赖。如此,墨菲仅依靠短期数据分析来阐释并推断上海的性质,在白吉尔看来并不站得住脚。
在白吉尔看来,上海同农村一样是确确实实的中国,只是它代表的是中国非正统的商业阶级的传统,是一个少数人的中国,但确实一个真正的中国。然而,白吉尔也认同了墨菲将上海视为一个与中国其他地方切割开来的外国区域。只是,白吉尔更为强调上海现代性的延续,从更长时间段评判上海性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上海性质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围绕墨菲和白吉尔的争议,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在时间上,不能以1949年或1978年之后中国现代化发展状况,来判定历史上的上海。其次,墨菲关于上海研究,主要是随着研究主题、研究范围的扩大而展现出更具有层次的中国图景。墨菲侧重于关注上海城市本身的现代化发展,并且他是在认为西方现代化典范有效性的认知上,判断作为中西首要接触点的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缩影。如此,他判断的依据是西方现代化的普世性。然而,在《外来者》中,墨菲更多地是从反思西方现代化普世性的角度,通过考察中印两国殖民/半殖民港口城市对两国现代化发展作用,来讨论中印两国对西方冲击的不同回应,或者是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选择。因而才看到通商口岸城市是本质上与中国深刻、稳定变化潮流无关的东西,深刻而稳定变化潮流才是决定了近代中国命运。[36]最后,如同叶文心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从更具体的研究来看,有关上海性质的讨论似乎已经变的不那么重要,因为无论上海的国籍是什么,一个城市总免不了兼容各种异质文化。[37]
四、城市是理解不同文明社会的窗口
在《外来者》中,墨菲有关上海与中国关系的新阐述虽然引发一些争论,但他在这部著作中进行的中印比较研究确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并对比较不同区域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墨子刻曾赞誉该书为“第一本成功将近代中国历史置于第三世界和世界历史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38]其中,城市依旧是墨菲进入不同区域文明的有效途径。
不得不说,墨菲选择进行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非常具有亮点的主题。1970年代,西方关于亚洲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个区域,忽视区域间的比较研究。而且,即便在比较研究中,人们也因为日本、苏联与中国有更多的相似性而更倾向于关注中日、中苏的比较研究。因而,从整体上看,当时的西方中国研究者可能对日本、欧洲的知识有一些了解,因为这些知识可能与中国更相关。但他们忽视了另外一些相关的连结,即由殖民帝国(英帝国)勾连起的亚洲各殖民地之间的关联。正如后来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当然不是孤立存在的,或者说,不是单独存在于印度与作为宗主国势力的英国的关系中,它还参与到一个定义整个英帝国的更大的关系网络中”。[39]
墨菲则认为,“印度是西方人侵扰中国的主要基地,殖民印度的已有经验使他们认为,他们也可在中国以同样的模式满足他们的野心”。[40]因此,“通过在文化和经济层面比较中国和印度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以及这种回应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成功或失败”[41],人们可以从两个地区截然不同的境况和随后不同的发展中了解亚洲的历史与未来。由此,墨菲以殖民/半殖民的港口城市为切入点,将中国和印度置于统一的帝国主义背景下,从内部环境解释中国和印度对帝国主义的不同回应。
这里我们能很明显地捕捉到墨菲对于城市路径的重视,而墨菲整体的学术研究也可以概括为以城市为中心的亚洲研究。具体而言:其一,墨菲在上海城市研究后,就开始致力于从中西方城市比较中思考城市的不同作用。墨菲也根据中西方城市的不同特征,初步将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条约口岸城市与西方城市、中国传统城市区别开来。[42]墨菲的这一倾向使他在更大范围内的亚洲研究中,力促将亚洲 “殖民港口城市”归为一类,并希望通过它们了解亚洲多元文化和社会。其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墨菲曾着力推动和倡导亚洲殖民港口城市研究,并提出“殖民港口城市”分析框架解释西方冲击对亚洲的影响以及西方与亚洲之间的互动。殖民港口城市,也由此被作为检视西方对亚洲影响的一个重要场域。其三,由城市进入中国和亚洲区域研究。
墨菲的学术研究也因此展现为点、线、面的层层递进。其中,点是单个城市研究,线是基于亚洲主要殖民港口城市研究形成的殖民港口城市分析框架,面是城市/港口城市所在的区域研究、区域比较研究以及亚洲整体区域研究。城市作为理解社会的窗口,也是墨菲最为核心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他尝试从城市角度解释中国、亚洲历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比如墨菲从城市角度解释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回应了五十年代美国中国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即西方在中国推行的现代化为什么失败?以及海内外学者至今仍在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曾使欧洲成为世界仲裁者的那种革命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在墨菲看来这个问题换个问法也可以是:为什么中国城市不似欧洲城市,成为变革的中心?虽然,关于中西分流的问题,中西学者已经从各方面讨论过,即使提问的方式也有修正,但从城市视角进行比较研究仍是一个可资借鉴和尝试的视角。而在亚洲区域研究中,他对于亚洲殖民/半殖民港口城市的研究促使人们关注前殖民时期亚洲海上贸易的悠久历史,这些研究正在一点点修正人们关于亚洲历史图景的认知。
——————————
[1]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章克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 1953.
[3] 张仲礼著,马军编:《我所了解的国际汉学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222页。
[4] 张仲礼:《借鉴历史经验 重振上海雄风》,《文汇报》1998年10月11日。
[5] 张仲礼:《借鉴历史经验 重振上海雄风》,《文汇报》1998年10月11日。.
[6] 同上。
[7] 关于章克生先生的介绍,参见马军编著:《史译重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翻译事业(1956—201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469页。
[8] 马军编著:《史译重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翻译事业(1956—201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470页。
[9]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印永清、胡小菁主编:《海外上海研究书目(1845-200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朴尚洙:《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之回顾与瞻望》,任吉东译,《城市史研究》第12辑,2013年,第250-270页;马润潮:《西方学者看中国城市——社会科学及历史学的文献回顾》,《城市规划》2006年(A),第69-74页。
[10] 印永清、胡小菁主编:《海外上海研究书目(1845-200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1] [英]兰宁、库寿龄著:《上海史》,朱华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版。该书分两卷,是第一部翔实记载19世纪上海租界历史的英文著作,主要使用了工部局档案、《北华捷报》、时人记载等资料;梅朋、傅立德合著:《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本书主要讲述了上海法租界从1849年形成到1943年被撤销的近百年历史,细致入微地从上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现象描述了法租界与外界冲突、争端和交融的过程。卜舫济(F.L.Hawks Pott, D.D)著《上海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是一部简明的上海租界史,大体按时间顺序,叙述上海的社会变迁。F.L.Hawks Pott, D.D,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Kelly & Walsh, Linmited,1928.问题n t﷽﷽﷽﷽﷽﷽﷽﷽﷽﷽뿯ꃎ䩀꛶儀꛶슌綨﷽﷽﷽﷽﷽﷽﷽﷽
[12] Preston E. James, Clarence F. Jones ed., American Geography: Inventory and Prospect.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 1954.p143.
[13] Norton S. Ginsburg, “Review”,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45, No. 1 (Jan., 1955), pp. 142-144.
[14] Rhoads Murphey, Fifty years of china to me: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1942-1992,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 Studies,1994, p. 93.
[15]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17]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18] C. A. F., “Review”,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21, No. 1 (Mar., 1955), p. 98.
[19] Norton S. Ginsburg, “Urban Geography and ‘Non-Western’ Areas”, in The City in Newly Developing Countries, edited by Gerald Breese; Englewood Cliffs, 1969. p.429.
[20]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105页。
[21] 同上,第249页。
[22] C. A. F., “Review”,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21, No. 1 (Mar., 1955), p. 98.
[23]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24]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25] Norton S. Ginsburg, “Review”,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45, No. 1 (Jan., 1955), pp. 142-144. bid,. for Asia Studies,1994, pp﷽﷽﷽﷽
[26] Norton S. Ginsburg, “Review”,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45, No. 1 (Jan., 1955), pp. 142-144. bid,. for Asia Studies,1994, pp﷽﷽﷽﷽
[27] Norton S. Ginsburg, “Review”,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45, No. 1 (Jan., 1955), pp. 142-144.
[28]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9] Rhoads Murphey, The Outsiders: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30] Marie Claire Bergere, “‘The Other China’: Shanghai from 1919 to1949”, in Christopher Howe, eds., 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pp. 1-34.
[31] 熊月之:《上海通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32] 张笑川:《本土环境与西方冲击互动中的通商口岸——<局外人:西方人在印度和中国的经历>评述》,《史林》2006年第1期。
[33]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34] 张仲礼:《关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的回顾——在中国近代城市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上的发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1期。
[35] Marie Claire Bergere, “‘The Other China’: Shanghai from 1919 to1949”, in Christopher Howe, eds., 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pp. 1-34.
[36] 鲍德威著:《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张汉、金桥、孙淑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37] 叶文心:《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时报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5页。
[38] Thomas A. Metzger, “Review”,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8, 1979, pp. 381-384.
[39] 托马斯·R.梅特卡夫著:《新编剑桥印度史—英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李东云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0] Rhoads Murphey, The Outsiders: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 p. 2.
[41] 同上。
[42] Rhoads Murphey, “The City as a Center of Change: Western Europe and Chin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44, No. 4, 1954, pp.349-362.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