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哈罗德·布鲁姆最后的文学记忆:文豪过眼,最大的对手仍是自己

近期,当代美国极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生前最后一部著作《记忆萦回:布鲁姆文学回忆录》,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可以说是年近九十岁的布鲁姆对他一生阅读体验的一次回顾和总结。书中,作者遵循阅读的记忆,选取了超过八十段他从小就熟记于心的经典作家的文本,为读者带来精炼、睿智的解读。
书中,布鲁姆的论战对象不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阅读此书,就好比跟随作者经历一段从童年到晚年的精神之旅,读者将有幸看到当代最伟大的批评家从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的杰出灵魂中汲取养分的过程。书中选入的西方经典自布鲁姆幼年时代就萦绕在他心头,至今它们依然鲜活:从莎士比亚到约翰生博士;从斯宾塞与米尔顿到华兹华斯与济慈;从惠特曼与罗伯特·勃朗宁到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从托尔斯泰与叶芝到德尔摩·舒瓦茨与艾米·克兰皮特……其中不少作者他都在之前的著作中论及过,但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将它们重新加以诠释,依然会给读者带来新鲜的观点。
回
忆

译作选读

我喜欢普鲁斯特,可惜不具备他的智慧。他是巴黎的荣耀,也应该是法国的欢乐。有时在晚上,我会梦到我的父母。他们已过世三分之二个世纪。阅读普鲁斯特时,我想领悟到心灵的间隙,但我做不到。但丁认为,最好的年岁是八十一岁,九个九。但丁死于五十六岁。如果他活到八十一岁,他是希望一切都圆满,但事与愿违。我记得我八十一岁那年,因为背伤,有四个月住在医院。我今年八十七岁,最近动了几次手术,正在努力恢复。有时,我忍不住想,如果我到了九十岁,我会不会开始明白至今我还不明白的许多东西。遗憾的是,我只是一个读者,一个教师,不是上帝。维柯说过,我们只知道我们创造的东西。
普鲁斯特的知识尽藏于《追忆似水年华》之中。我反复阅读了七十年,仍然不能完全把握其中要义。重读普鲁斯特,如同再次经历但丁、塞万提斯、蒙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乔伊斯。普鲁斯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主要人物夏吕斯、莫雷尔、阿尔贝蒂、斯万、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圣卢小姐、弗朗索瓦斯、奥黛特、希尔贝特、布洛克、马塞尔的母亲,以及所有未曾指名但最终表明都是马塞尔的叙事者,对我来说,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笔下的伟大角色。《追忆似水年华》中的视角像在走马灯。我们看见和听见夏吕斯男爵,这样一个文雅的贵族,最终沦为受虐幻想的可悲牺牲品。有时他看起来荒诞不经,有时又能感受到他残余的辉煌。如今重读,在我曾经觉得深为同情的地方,我不禁潸然泪下。
我意识到,我现在仍然徘徊于激情和浑噩之间。在《重现的时光》结尾,当叙述者和马塞尔融为一体,作者的声音抵达了澄明之境:
坐在椅子上的德·盖尔芒特公爵,我望着他,钦羡过他,尽管他的年龄比我大那么多,却并不见他老多少,我刚弄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了。一旦他站起身来,想要站住的时候,他便颤颤巍巍,两腿直打哆嗦,像那些老迈年高的大主教的腿脚,年轻力壮的修院修士向他们大献殷勤时,在他们身上只有那个金属十字架仍是牢固的。当他要往前走,走在八十四岁崎岖难行的峰巅上,他非颤抖得像一片树叶不可,就像踩着不断增高的活高跷,有时高过钟楼,最终使他们的步履艰难而危险,并且一下子从那么高摔落下来。我想我脚下的高跷恐怕也已经有那么高了,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力气把拉得那么远的过去继续久久地连结在自己身上。如果这份力气还让我有足够多的时间完成我的作品,那么,至少我误不了在作品中首先要描绘那些人(哪怕把他们写得像怪物),写出他们占有那么巨大的地盘,相比之下在空间中为他们保留的位置是那么的狭隘,相反,他们却占有一个无限度延续的位置,因为他们像潜入似水年华的巨人,同时触及间隔甚远的几个时代,而在时代与时代之间被安置上了那么多的日子―那就是在时间之中。(出自《追忆似水年华》第七卷《重现的时光》,徐和瑾、周国强译,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

普鲁斯特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每次起身准备走路,总是怕摔倒。我好几个朋友都是这么离开人世的,我自己也严重地摔了四次。普鲁斯特结尾的这段话在多个层面上打动了我。除了个人情感的层面,它还使我不禁想到自己渴望继续教书和写作的心愿,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普鲁斯特寻找失落的时光的一个例子。普鲁斯特的母亲虽然是犹太人,但在我看来,他既不是基督信徒,也不是犹太信徒。他的智慧是他自己的智慧。他像莎士比亚一样,游离于基督教和犹太教。我认为,他事实上更接近印度教。这里有一个奇怪的难点。普鲁斯特笔下的一切始于情欲关系,但这一切立刻又被弃绝或抛弃。话说回来,没有这些情欲关系,《追忆似水年华》也不可能创作出来。正如马塞尔说,阿尔贝蒂用不幸浇灌了他。
反复阅读之后我们会发现,普鲁斯特本质上是一个伟大的喜剧家。他认为友谊“介于身体疲惫和精神厌倦之间”。他还认为恋爱“就是惊人的明证,现实对于我们可有可无”。他颂扬“完美的谎言”,认为这是我们揭开惊喜的唯一机会。他说,死亡治愈了我们对于不朽的渴望;这让我醍醐灌顶。
克里希纳在《薄伽梵歌》中的最后教诲,是教导勇士阿周那人和神所具有的自然品性:
阿周那,何为快乐?
找到快乐有三条路
只有勤加练习,
才不会再有痛苦。
一是澄明的快乐,
来自平静的自知,
起初看来像毒药
最终看来像珍馐。
二是激情的快乐,
当感官碰到对象,
初看起来像珍馐。
最终看来像毒药。
三是浑噩的快乐,
好似蒙头在大睡,
懒散马虎不努力,
从头到尾在自欺。
世上没有这样的人,
天上没有这样的神,
可以摆脱这三种境,
它们都是自然品性。
(英译,芭芭拉·斯托勒·米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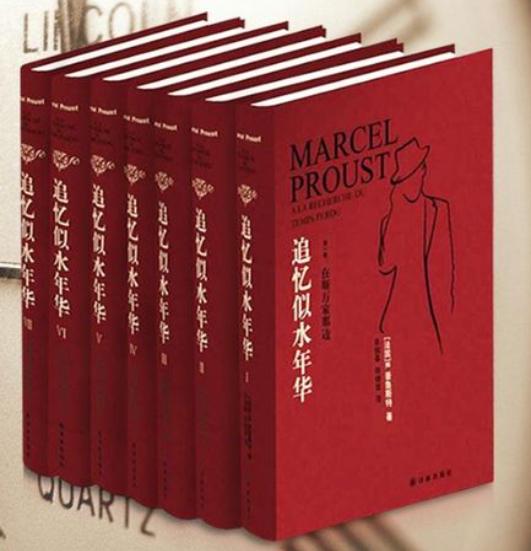
显而易见,这是普鲁斯特的核心。但是,如果我们把马塞尔的成长,看成是从浑噩与激情的交织,到明确无疑的惊人的澄明,这 既是洞见,也是盲视。因为普鲁斯特笔下那一群人物,许多并不遵循这样如此明晰的模式。马塞尔终将成长为普鲁斯特,但我们永远不能准确看到他到底是如何走出自我的迷宫。
我教莎士比亚六十多年,我经常觉得或情不自禁地想,我对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些重要角色,如哈姆莱特、福斯塔夫、克利奥帕特拉、李尔、伊阿古和麦克白,既了如指掌,又一无所知。我虽然从来没有讲授过普鲁斯特,但我一直在读他,思考他。那么,对于叙述者马塞尔、夏吕斯男爵、斯万、奥黛特、希尔贝特、阿尔贝蒂、圣卢小姐、马塞尔的母亲和外祖母、弗朗索瓦斯、布洛克、贝戈特、科塔德、埃尔斯蒂尔、盖尔芒特公爵和公爵夫人、诺布瓦、莫雷尔、维尔迪兰夫人和维尔巴西斯夫人这些人物,我又知道多少呢?尽管不能说一无所知,但对于他们至关重要的一切是谈不上了解的。
普鲁斯特的研究者们往往都认为,要理解其人物,心理还原毫无用处。这是普鲁斯特很像莎士比亚的重要特征之一。用普鲁斯特式的方式解读弗洛伊德,比用精神分析法研究夏吕斯或阿尔贝蒂更有成效。我找不到任何字眼来形容莎士比亚对于他笔下人物的立场。你可以说他客观公正,但那种客观公正是非常有限的。普鲁斯特热爱他的人物,甚至热爱夏吕斯男爵。《索多姆和戈摩尔》第一部分中就有雄辩的一段:
他们的名声岌岌可危,他们的自由烟云过眼,一旦罪恶暴露,便会一无所有,那风雨飘摇的地位,就好比一位诗人,前一天晚上还备受各家沙龙的青睐,博得伦敦各剧院的掌声,可第二天便被赶出寓所,飘零无寄,找不到睡枕垫头,像推着石磨的参孙,发出同样的感叹:“两性必将各自在不同地方消亡。”在遭受巨大不幸的日子里,受害者会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就好比犹太人全都倒向德雷福斯,但一旦不再倒霉,他们甚至再也得不到一丝怜悯——有时被社会所不容——遂被同类所唾弃,暴露无遗的真实面目引起他人的厌恶,在明镜中原形毕露,镜子反射出的不再是美化他们真相的形象,而是把他们打心眼里不愿看到的各种丑态和盘托出,最终使他们醒悟,他们所称其为“爱”的玩艺儿(他们玩弄字眼,在社会意义上把诗歌、绘画、音乐、马术、禁欲等一切可以扯上的东西全称其为自己所爱)并非产生于他们认定的美的理想,而是祸出于一种不治之症;他们酷似犹太人(唯有少数几位只愿与同种族的人结交,嘴边总是挂着通用的礼貌用语和习惯的戏谑之言),相互躲避,追逐与他们最势不两立,拒绝与他们为伍的人,宽恕这些人的无礼举动,被他们的殷勤讨好所陶醉;但是,一旦遭到排斥,蒙受耻辱,他们便会与同类结成一伙,经历了类似以色列遭受到的迫害之后,他们最终会形成同类所特有的体格与精神个性,这些个性偶尔也惹人高兴,但往往令人讨厌,他们在与同类的交往中精神得以松弛(有的人在性情上与敌对种族更为贴近,更有相通之处,相比较而言,表面看去最没有同性恋之嫌,尽管这种人尽情嘲讽在同性恋中越陷越深的人们),甚至从相互的存在中得到依赖,因而,他们一方面矢口否认同属一伙(该词本身就是某大的侮辱),而另一方面,当有的人好不容易隐瞒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却主动揭开假面具,与其说是为了加害于人(这种行为为他们所憎恶),倒不如说是为了表示歉意,像大夫诊断阑尾炎那样刨根问底,追寻同性恋的历史,津津乐道于告诉别人苏格拉底是他们中的一员,就好比犹太人标榜耶稣为犹太人,却不想想,如果连同性恋也是正常的事,那么世间也就不存在不正常的东西了,无异于基督降生之前,绝不存在反基督徒;他们也未曾想过,唯有耻辱酿成的罪恶,正因为它只容许那些无视一切说教,无视一切典范,无视一切惩罚的人存在,依仗的是一种天生的德性,与他人格格不入(尽管也可能兼有某些高尚的道德品质),其令人作呕的程度远甚于某些罪恶,如偷盗、暴行、不义等,这些罪恶反而更能得到理解,因此他更容易得到普通人原谅;他们秘密结社,与共济会相比,其范围更广,效率更高,更不易受到怀疑,因其赖以支撑的基础是趣味、需求与习惯的一致,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最初的尝试,掌握的学识进行的交易,乃至运用的语言都完全统一,在他们这个社会中,希望别相互结识的成员凭着对方一个自然的或习惯的,有意的或无意的动作,就可以立即识别同类……

普鲁斯特画像
第一句话中提到的那个诗人是奥斯卡·王尔德,他是一个惊人的天才、永远的殉难者。把王尔德形容为在加沙地带推着石磨的参孙,这种意象引用自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愤怒的参孙》:“两性必将各自在不同地方消亡!”普鲁斯特认为,两性并无区别,即便在不同地方消亡。
普鲁斯特逐渐相信,在时间的毁灭和创造中,他找到了自己对意义的求索。理解死亡,就是理解他作为小说家的职业。他立刻看到,精神是在爱与痛的融合中呈现。如叔本华,普鲁斯特抛开了纯粹的观念。维特根斯坦以叔本华的方式指出:“唯我论者说的是错的,但他的意思是对的。”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普鲁斯特才是唯我论者。他追求的是作为意志和观念的世界,创造的是作为表象的新世界。
(《记忆萦回:布鲁姆文学回忆录》哈罗德·布鲁姆/著,李小均/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8月版)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历史资料

原标题:《哈罗德·布鲁姆最后的文学记忆:文豪过眼,最大的对手仍是自己|夜读·倾听》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