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余华|我的鞋带从来没有松开过,一直是系紧的
你有想要逃跑的时刻吗?余华在新出版的随笔集《山谷微风》中讲述了一个关于鞋带与逃跑的故事。每次见到库斯图里卡,余华都发现他故意没系鞋带,有一次活动中,现场观众问了库斯图里卡不系鞋带的原因,他说,“这是为了表明他身心放松,如果系上鞋带,表明他处于紧张之中,准备随时逃跑。”
由此处展开,余华讲述了他少年时一个想要逃跑的时刻。余华在文中写到“我们的少年里不会缺少逃跑,不会缺少心惊胆战,而且逃跑和心惊胆战如影随形,追随我们一生。”
下文摘选自《山谷微风》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库斯图里卡的鞋带
我与库斯图里卡相识于七年前,贝尔格莱德进入春天的时候,一个小范围的会议,塞尔维亚文化部长主持,库斯图里卡是会议的主角。在这个七人会议上,一位八十多岁的塞尔维亚老作家认真参加会议,不参加晚上聚餐。

库斯图里卡,塞尔维亚导演、编剧、演员、作家、音乐家,是当代为数不多在戛纳、威尼斯与柏林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的导演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俄罗斯作家扎哈尔·普里列平,他曾经是特种兵,参加过车臣战争,他是从顿巴斯来到贝尔格莱德,他和家人居住在顿巴斯。这位光头作家发言时像是一个军官在参加军事会议,为此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表情严肃地看着他,开玩笑说:谢谢你没有背着AK47来开会。这位普京的朋友(他自己这么说的)差点让乌克兰特工干掉,去年五月六日在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州的公路上,他乘坐的汽车被炸,司机炸死,他炸伤。
会议进入最后一天,一位法国作家来了,他不知道前面两天我们说了些什么,我们说话时他插不进来,他整个下午都在迷惑地看着我们,到了晚餐的时候仍然孤独,我们互相熟悉地说话,他像个陌生人坐在那里,后来他端着酒杯坐到我身旁说:
这个会议很奇怪。
我是在贝尔格莱德街上第一次看到库斯图里卡没有系鞋带,那时候我们走在一起,他穿着一双黑皮鞋,走去时鞋带自由地甩来甩去,起初我以为他不知道鞋带松开了,提醒了他,他点点头继续走着,没有一丝停下脚步系鞋带的迹象,我以为他是懒得弯下腰去,松散的鞋带并不妨碍他的行走。
后来的两天,我注意到他仍然没有系鞋带,于是他的鞋带出现了两种表情,他开会坐下时,鞋带垂头丧气耷拉在那里,他起身行走时,鞋带生机勃勃甩动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系鞋带,显然他并不讨厌鞋带,如果讨厌的话,他可以去穿没有鞋带的鞋,我当时想这可能是他的个人嗜好。

此后不到一年时间里,我们又见了两次,一次是在上海,他带来了新电影和无烟地带乐队。
下午我们在宾馆见面,我看了一眼他的鞋,鞋带还是散开的。
晚上在剧院看他和无烟地带乐队演出,他弹着吉他在舞台上蹦蹦跳跳,自由的鞋带“野蜂飞舞”了。
另一次是在塞尔维亚靠近波黑的木头村,二○一八年一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在一个山顶木屋里吃了烤牛肉,外面白雪皑皑,傍晚时分我们走到户外,在寒风里观赏落日在白茫茫中降落的壮观景象。
第二天他开车带我去波黑塞族共和国的维舍格勒,他的双脚踩进厚厚的积雪,走向他的SUV,我跟在后面,看着他的鞋,鞋带仍是散开的,鞋带和鞋一样沾满了积雪。我至今难忘那里冬天的美景,山势层层叠叠,树林也是层层叠叠,树上结满了霜,一片一片的灰白颜色波浪似的下去又上来。
就是这次塞尔维亚与波黑之行,我去了萨拉热窝。
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萨拉热窝是一个传奇城市,两部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曾经风靡中国。萨拉热窝也是南斯拉夫时期的艺术之都,那里文艺人才辈出,库斯图里卡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他在萨拉热窝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成长,可是他经常与一伙不良少年混迹街头巷尾,他自然也是不良少年。他少年时期的玩伴后来都进了监狱,如果没有对电影的热爱,他很可能会在监狱里与玩伴们相聚,电影把他拉了出来,让他去了布拉格。他从布拉格学成归来时,已经是崭露头角的青年导演。
我在萨拉热窝时去了他少年时期生活的街区,我站在路边看着行驶的车辆,心想这哥们少年时干过的坏事和眼前的车辆一样多。
南斯拉夫解体后,不同民族之间煽动仇恨,现在巴尔干的穆族和塞族很难共处,库斯图里卡无法回到他的故乡萨拉热窝,这是一座属于穆斯林的美丽城市。他思念故乡的方式之一,是请居住在波黑塞族共和国的朋友去萨拉热窝时拍一些照片发给他。
我离开萨拉热窝,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后,也就忘记了库斯图里卡的鞋带。
今年四月二十五日,我们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见面,我也没有去看他的鞋带。电影节组委会的郝洁邀请我参与库斯图里卡的大师班讲座,讲座进入尾声的时候,他抬起脚,让台下的听众看看他浅棕色皮鞋上散开的鞋带,我这才重新注意他的鞋带。
我和在场的听众得到了他的回答,他解释为什么不系上鞋带,这是为了表明他身心放松,如果系上鞋带,表明他处于紧张之中,准备随时逃跑。很好的解释。
紧张还是放松,都是生活给予的,什么时候给予什么,是生活的意愿,我们没的选择,只有接受。
库斯图里卡散开的鞋带是一个姿态,并非他现在已经远离紧张,紧张仍会经常找到他,但是他知道如何对付了,他已不是少年库斯图里卡,他已是老江湖库斯图里卡。我觉得库斯图里卡散开的鞋带是对自己少年经历的警告,这个曾经的不良少年如何逃跑的经验丰富多彩,我相信他有过很多心惊胆战的时刻。
我们也一样,我们的少年里不会缺少逃跑,不会缺少心惊胆战,而且逃跑和心惊胆战如影随形,追随我们一生。

我少年时期的紧张,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的口吃,这是童年时觉得好玩,觉得结结巴巴说话别具一格,当我成为一个正式的结巴后,想改已经晚了,改不过来了。我应了那句老话,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没有早知道。我口吃的表现因人而异,与父母哥哥还有同学在一起很放松,说话比较连贯,虽然时常停顿,总还能把那些词汇艰难地说出来;与不怎么熟悉的人说话时,就会无端紧张起来,说话不再是停顿,而是卡住,停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卡住才要命,卡住如同一座高山挡住了我的去路,怎么也翻越不过去。那时候我只能低下头,满脸通红地站在那里,用点头或者摇头来回答对方的问话。我的口吃也因天气而异,有个说法,下雨天容易口吃,太阳天不会口吃。不知道真是如此,还是心理作用,每到下雨天我说话总是断断续续,太阳天说话明显流畅一些。
我上小学时的一个夏天,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在屋外乘凉,我父亲想起医院工作上的一件事,让我去给他的一个医生同事传话,传什么话我忘了,我不愿意去,对父亲说,让哥哥去。我是担心自己的口吃,站在一个陌生的门口,面对父亲的同事,我有可能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父亲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他对我说,就是要你去。我继续说,就是不去。我父亲沉着脸进屋拿着扫把出来,他还没有把扫把举起来,我连声说,我去,我去。我听到父母和哥哥在后面的笑声,我父亲好像还说了一句敬酒不吃吃罚酒之类的话。
我生气又委屈,走出我们当时居住的杨家弄,走上大街,口吃担忧症的症状开始出现。我在紧张的感觉里沿着城里的小河向父亲同事的家走去,先是在心里默念那句话,在心里说的时候还算流畅。我尝试小声说出来,第一次比较顺利说完,第二次出现停顿,接下去一次不如一次,后来几乎每个字说出来时都是停顿后拉长,而且越拉越长,像是唱出来的音节。路上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心不在焉地看他一眼,好像是我的同学,他笑着问我自言自语哼的是什么。我面红耳赤,没有回答他,继续走去,我不敢再发出声音。我恍惚起来,路上认识的人都是好像认识。
我走到父亲同事家门口时,另一个担心出现了。他住在河边的房子里,我站在他的屋门外,我担心敲开门之后出现的不是他,是他的家人,我就要多说一句话,问他的家人,某某叔叔在不在家。我担心这句询问的话会停顿卡住,声音拉长了唱歌似的才能说出来,要命的是之后面对父亲同事还要说一句话,一次唱歌变成两次唱歌。

就在我的担心转化为害怕时,屋门打开了,我父亲的同事正要出来,好像是要倒垃圾,他见到我站在门外怔了一下,随即笑着说,是余华啊。他的出现让我猝不及防,正是这样的突然,担心害怕瞬间消失,我流利地说出了那句话。
我沿着河边回家时心花怒放,感觉傍晚的天空从来没有这么好看过,云彩在落日和晚霞的映照里闪亮,长长的拖船驶去时河水掀起层层波浪,我觉得波浪很快乐。见到认识的人我主动叫出他的名字,遇到同学时说几句话,我发现自己说话流畅了,几乎没有停顿卡住的时候。这个经历对我口吃的治愈立竿见影,我说话时不再畏首畏尾,而是敞开交流了,虽然还会出现停顿,也是小小的停顿,很少有卡住的时候,不影响我的正常说话。
我说话顺利了几年后,一次经历把我打回原形,那是我口吃史上登峰造极的时刻。
我上高中,当时县里每年几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我们海盐中学的操场上进行。因为我作文优秀,学校推荐,上级同意,布置我写一个死刑犯的批判稿,而且让我站在公判大会的台上念自己写的稿子,这对于少年的我是光荣和梦想。我认真看完这个死刑犯的罪状,写出批判稿,里面充满了《人民日报》上每天出现的革命语句。批判稿顺利通过审查,接下去我只要站在台上,用义正辞严的腔调念完,我就大出风头了。公判大会的前一天晚上,因为激动睡不着,我脑子里一遍遍想着明天的风光时刻。
这时候一个不合时宜的念头出现,明天公判大会上口吃了怎么办。情绪急转直下,从兴奋激动的高峰跌入心虚胆怯的谷底。担心像雾一样弥漫开来,忐忑成为我心跳的节奏。虽然我给自己壮胆,让自己放心,明天会把稿子顺利念完,可是担心忐忑不时袭来,我在自我鼓励和担心不安的拉锯战里昏昏入睡。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对自己口吃的担心不仅没有离去,反而更加清晰强烈,这个要命的感觉占领了我头脑,驱逐了其他想法,让我怎么也摆脱不了。我忘了自己是怎么去的学校,只记得海盐中学的学生搬着他们的椅子来到操场的情景。学生按年级和班级分片坐下,我手里捏着批判稿,站在操场讲台的一侧,与另外三个拿着批判稿的人站在一起,他们三个说说笑笑,我心慌意乱,看着熙熙攘攘的学生乱糟糟入座,我知道上台的时间快到了,心里越来越紧张,身体开始僵硬。
公判大会的开始,是我们武原镇派出所的所长宣布的,四个五花大绑的犯人被六个民兵和两个解放军战士押上讲台,他们胸前挂着大纸牌,上面写着他们各自的名字和罪行。死刑犯只有一个,就是让我念批判稿的那个,两个背着步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在死刑犯身后,另外三个犯人后面站着手握标枪的民兵。死刑犯是最后一个宣判,所以我是压轴的。前面三个犯人的批判稿是我们镇上其他单位的人念的,他们都是革命积极分子,他们嗓音洪亮,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出来的声音,铿锵有力地从高音喇叭里喷射出来,的电流声伴随他们的声音。
他们说了什么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我正在担心害怕的煎熬里试图咸鱼翻身。如果让我第一个念批判稿,或许能够完成,中间会出现几处停顿,我相信自己能克服过去。偏偏我是最后一个,前面三个的批判稿写得冗长,他们的声音像是吃坏了拉肚子那样没完没了。我在紧张里待得越久,就越紧张,我仿佛踩上了紧张的西瓜皮,滑过去摔一跤,滑过来摔一跤。感觉过去了很长时间,他们三个才念完批判稿,他们的声音没有了,的电流声还在响。我的身体不是哆嗦,是僵硬地走上台,我似乎不是走过去的,是把自己搬到麦克风前。如果可能,我肯定逃之夭夭,可是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力气逃跑,我懵懵懂懂无依无靠站在那里,心里喊了三遍毛主席万岁,指望毛主席保佑我顺利念出第一句,再顺利念出第一段,这样我有希望顺利念完批判稿。
我站在麦克风前不出声的时间有点长,台下的人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寂静无声看着我。要命的是我往台下看了一眼,不看还好,这一看,看到他们的目光整齐划一地射向我,我听到自己念出批判稿第一句的声音颤抖。第一句出现一个停顿,第二句出现几个停顿,这是唱歌的趋势,我听到下面有咝咝的笑声;第一段也就两百多字,我卡住了三次,这是唱歌的调子,下面的笑声响亮起来。我知道自己完蛋了,停顿卡住的频率越来越高,我自己听到的不是说话声,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歌声,极其难听的歌声,结结巴巴地响起。台下的笑声浪涛似的起伏,我无助地向下面看了看,看到不少人笑得站起来,又捧着肚子弯下去。老师们也都站起来了,他们摆着双手,正在制止学生的笑声,可是老师们也在笑。

我在公判大会上用不着调的歌声念完了批判稿,时间比预定的长了两倍,在浪涛似的哄笑声里走下台,竟然感觉解脱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那种解脱。班上的几个男同学哈哈笑着向我走过来,我看着他们也笑起来,反正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样。
此后的几天里,女同学看到我就会捂住嘴笑着走开,男同学们围着我,拍着我的肩膀笑,说他们很久没有过这么高兴,他们告诉我,台上那个死刑犯也是笑得浑身抖动。有一个同学补充说,死刑犯身上绑着的绳子都笑得抖开了,绳子一头掉到了地上。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这可是用绳子套住脖子绕到背后反剪双臂的五花大绑。我不知道这是成长里的至暗时刻还是高光时刻,后来每次的回想都会定格在死刑犯笑得浑身抖动的情景里,我给一个行将结束生命的人带去了最后的快乐。
中学时期公判大会上名噪一时的表现让我达到了口吃的巅峰,之后不断回落,有高峰必然会有低谷,我开始进入了漫长的口吃低谷期,说话会有停顿,但是都能说完。
三十多年前,莫言在《清醒的说梦者》一文里描述我说话“期期艾艾”,那时我二十九岁,我们两人住在鲁迅文学院的一个宿舍里,我正处于说话会有停顿的口吃低谷期。后来因为国内国外很多的采访和演讲,我说话时越来越放松,似乎告别口吃了,或者说忘记自己的口吃,偶尔会出现停顿,也是越来越少,当某一个词汇卡住时,我会脱口而出另一个近义的词汇。
可是写下这篇文章以后,不祥之兆降临了,我突然感受到一些紧张,担心这篇文章可能会召回我的口吃,让我重返结巴的高峰,因为我的鞋带从来没有松开过,一直是系紧的。
本文摘编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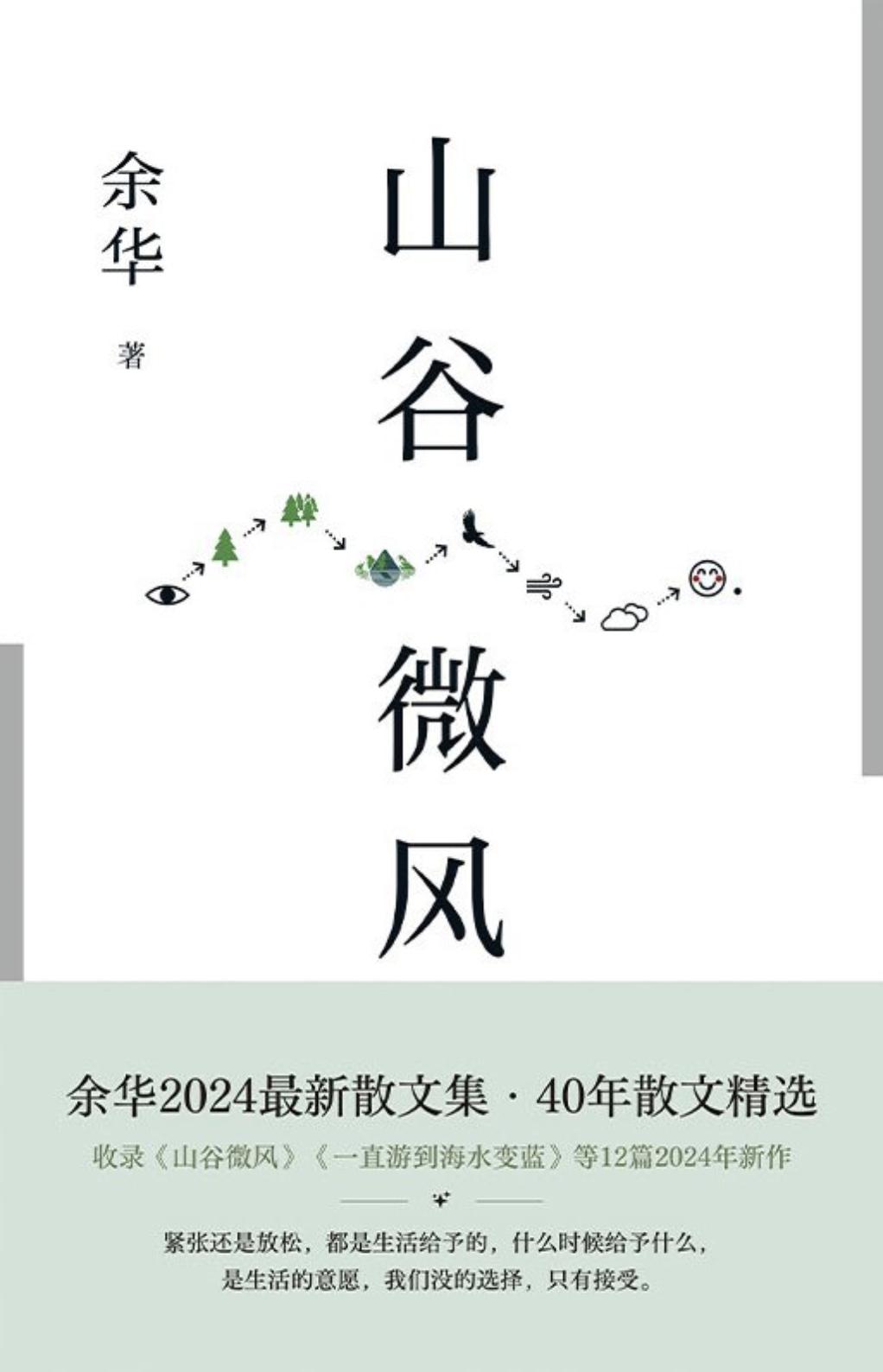
《山谷微风》
作者:余华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新经典文化
出版年: 20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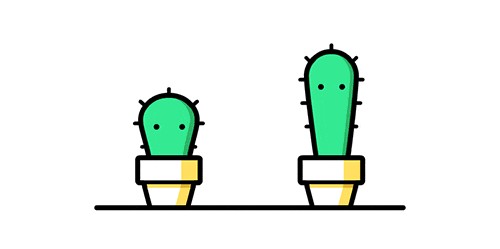
编辑 | 飞起来的各种东西、轻浊
配图 | 《小鞋子》《岁月神偷》
主编 | 魏冰心
原标题:《余华|我的鞋带从来没有松开过,一直是系紧的》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