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书展|如何读懂中国画?《中国画品评史绎》首发
“品评”是一个伴随中国古代绘画史发展重要的艺术观念,是一个可以把中国绘画的全部理论贯穿起来的线索。自最早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起,至今产生了无数品评著作。
澎湃新闻获悉,8月20日下午,“如何读懂中国画:《中国画品评史绎》”新书首发式将在上海书展世纪活动A区展开, 该书作者邵琦梳理了历代品评理论的具体内容及核心思想,以图文并茂形式解读中国画的品评历史。澎湃艺术特选摘《余论》章节,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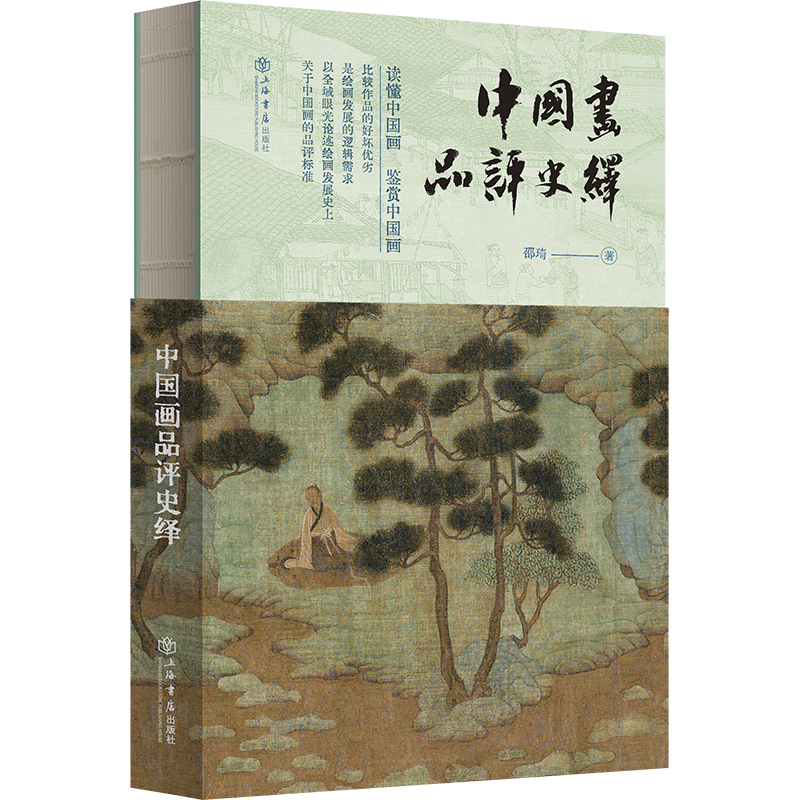
《中国画品评史绎》书影 上海书店出版社
如果说,远古的绘画描绘各种神灵,是为生民的生存而祈福;中古以来的绘画描绘圣贤忠节,是为建构百姓有序的社会生活;那么,晚明以画中烟云供养而多寿,则可以看作是对远古祈望的一种时代呼应。
或许,正是缘于此,董其昌等人的“南北宗”,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就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新论,而且成为规导其后近四百年的范式。自此以后,清初恽寿平、四王以至扬州画派到海上画派,无不执其旗,循其轨。近四百年来,只有在这条轨道上走得不尽人意的,而没有能超越其规范而提升的。
在绘画实践上是如此,在理论品评中同样如此。晚明以来有关书画的著录、论说十数倍于清以前的总和,除了翻抄、记录,或有所论,亦不出董其昌的权威之论外,以至于现代以来,各级博物馆对书画的藏品的定级也无不以董其昌的定论为是。而出版的无论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写就的书画史著作,所执持的基本史观亦无不以董其昌的眼光为基准。

《中国画品评史绎》书影
因此,只要孩童还把书画当作学习规范的手段,老人还把书画当作养生长寿的途径,那么书画就始终有着循依初心,永葆发展的生机。
进入清代以后,品评一道渐次式微。标明为品评著作并传世的仅黄钺的《二十四画品》,这部仿《诗品》而就的著作,一如李开先、王穉登的著作,仅可看作其传世文章而非可以评骘画家或作品的标准。究其缘由,还在于绘画整体功用已经转换,而他们的认知依旧。石涛的“一画论”,倡言“我自有我法”,堪称戛戛独造,然而他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只是成就了他自开面目,以中国绘画史的历史尺度和眼光来看,依然不出董其昌的范式之外。即便画面面目比石涛更独特的八大山人,其山水也是直接师从董其昌而成就,更不必说得董其昌亲炙的王时敏、王翚等“四王”派系。而整个清代山水画坛又从“后四王”到“小四王”为主流,诚如方薰《山静居画论》所谓:“海内绘事家,不为石谷牢笼,即为麓台械杻。”这一现象毁之者以为代代相同,了无生气,而实不知其前赴后继,正在于不惜努力实践着董其昌所开列的课题。因此,如何看待清代绘画,乃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不过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四王”及其传派,未能抵到董其昌所希冀的高度,当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四王”及其传派在主观与实践中都是董其昌纲领不折不扣的忠实信徒;其二,除了王原祁、王翚作为公务参与过《南巡图》这类歌功宣传之作外,绘画在他们几代人身上都没有退回到人伦教化的时代。
因此,无论是面目独到又不无市场狡黠的扬州画派,还是恪守成法而又各具面目的四王画派,都以各自的实践验证着绘画私人化的发展纲领。
能否寄乐于画,这无论对画家还是对观者,都是难以精确计量或准确判断的事,而绘画品评的式微,也正缘于此。因此,探究步入私人化发展期之后,绘画是否还有可资共同执持的品评指标,也就成为清代画论的关注点,而系统地厘清指标,自然是从底层的技法开始,在这一方面,《芥子园画传》前后接力完成,功不可没。作为中国画的标准教材,在技法层面上秉持打通门墙,南北并重的原则,将各家各法分解示范,为后学的登堂入室和融合创新奠定了基础。这部教材的出版付梓,并在其后三百年不断再版,是中国画从文人化、职业化走向平民化的桥梁,对中国画技法的普及和观念的普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且不仅在文言的清代,即便在白话的当今,依然承担着中国画入门的职责。
因为《芥子园画传》是风行时间最长、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画教材,因此,它的选编标准,在无形之中,也就成为最深入人心的。尽管在综述文字上严格秉持了苏轼以来的文人画传统,简要摘录了最主要的各家各法的观点,但在具体示例示范图的选用和排列上,十分明显地偏向了南宗。如在《成家》一章中:
自唐宋荆、关、董、巨,以异代齐名,成四大家;后而至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为南渡四大家;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为元四大家;高彦敬、倪元镇、方方壶,虽属逸品,亦卓然成家。所谓诸大家者,不必分门立户,而门户自在。如李唐则远法思训,公望则近守董源,彦敬则一洗宋体,元镇则首冠元人,各自千秋,赤帜难拔。
尽管在“元四家”的人选上用赵孟頫替代了倪瓒,但其目的并不是要将赵孟頫列入“元四家”,而是要为专列的“逸品”找一个带头人。因为“元镇则首冠元人”,这一句话完全可以看到选编的绘画意趣指向。当然,由于是基础技法,也为求历代技法的完备,在画家选择上还是以每种技法的创建者或最优者为代表。

《中国画品评史绎》内页
《芥子园画传》立足在技法层次上的对中国画的梳理,在一般民众那里成为认识、了解中国画的标准件。换言之,《芥子园画传》是董其昌推行的“寄乐于画”的绘画私人化谋略中率先完成的技法教材实施部分,与此相随的是:由于这一技法教材所实施的对各家名作的解析,使得中国画的学问门槛大为降低,在客观上又完成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文人画普及。甚至从学习的人员数量来看,已经改变了原先文人画家精英化的历史状态。
《芥子园画传》造就的文人画普及化或者说平民化,核心是将文人画的技法作程式化分解,致使文人画从精英阶层迅速稀释到平民大众之中。由于难得一睹真迹而高还原度的复制品又极为有限,因此,技法用笔的诸多精微细节被省略或遮蔽,尽管数量猛增,但质量下滑,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积壳与俗赖——因缺少基本的文人修养而徒摹其形,因此,从绘画本体的发展而言,是滞塞的,甚至是退化,但就文人画的观念的普及而言,则是卓有成效的。晚清以后,对绘画的反思中出现的种种诟病,或皆源于此。
也是由于数量上的猛增和信息获取的有限,致使对绘画的品评丧失了可能性。当无法比较全面地掌握和了解绘画实际情况时,基立在整体比较之上的优劣铨量,也许失去了可行性与必要性的前提。所以,此后的品评大多限于一时一地或一人一派,这显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品评了,而只能与既往的题跋相当,或者白话语境中的所谓“评论”“批评”。评论或批评,作为现今时代的一种评述,往往与私情和利益相纠缠,且其指向往往在当下,鲜及过往与未来。
关于“肖像不像”
肖像不像,是中国画深被诟病的“落后”原因之一。
肖像,一定要逼真吗?在今天这个问题或许应该被禁止,因为太常识了,以致这样的问题一出口就给自己贴上了愚蠢的标签,或者是在故意捣蛋。肖像不像,还叫肖像吗?
当然,这里的像与不像,是相对于西方的肖像标准而言,在文言文的时代,不问这样的问题,或者说很少问这样的问题,似乎总在理所当然中。
然而,一旦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提问者的关于肖像的标准也就显露出来了。那就是肖像的基本衡量标准就是:形似,真实或逼真。无疑,从最根本的层面来看,肖像的职责就是存留下对象人物的容貌,于是就又有了是不能画逼真?还是不愿画逼真?似乎这才是根本。
我们从唐代的人物画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刻实逼肖的人物形象并不是不可为的,再从宋代帝后肖像图来看,也可以看到“逼真”完全不是技术的问题。但从人物画史来看,人们更愿意说中国画中人物形象不是写实的、具体的人,而是观念的人物,这一观点道出的却是事实,同时也是人物形象不求逼真的根由。
至晚春秋战国时,屈原观祭祀先王之庙、公卿之祠中的壁画而喟然有叹,写成了名篇《天问》。《天问》中所提到的这种壁画,在汉代仍能看到。《汉书·成帝纪》记载:“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应劭注:“画堂画九子母。”又《汉书·叙传》:“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可见,西汉时还有各种壁画、屏风,其所画题材与《天问》的“女歧九子”“王纣之躬”是对得上的。当然,这些画面上的人物,都是用来宣教相对的观念的。
如何表达对先王、圣贤、公卿等这些人物的敬重、庄严,便成为一个问题了。祭祀的场所是庄严肃穆的,这种氛围需要所有进入这一场合的物件都不引发轻蔑傲慢心绪,这是常识,也是礼制。

《中国画品评史绎》内页
不能引发轻慢心绪,就首先要寻找引发的源头或原因。就与绘画相关的部分而言,用逼真写实的图像来表达固然可以,但这就需要极为高超的造型能力。然而在照相机发明之前能做到的恐怕极其有限。对于一个统一的、幅员广大的族群来说,礼制,不仅仅是文明的象征,更是连接的纽带。因此作为礼制的一个重要元素,便是要有可复制性,且是保持统一规则的复制,如果复制走样或失误,也就意味以此为代表的秩序的散乱。因此,在这种场合是不适宜选用这种高技术含量的图像的。当然,这还仅仅是从绘制角度来看的。从观看的角度来看,高度写实的逼真图像,是最通俗的,因为对图像与物象之间作还原度,是人的视觉器官的自然功能,亦即人们比较图像与物象之间的还原程度是无需经过特别训练的,只需调用生活的日常经验即可。画家当然也可以通过细微的观察来真实地表现,但现实的情况是:画家一个人的观察与众人的经验之间必然会有不能涵盖的部分,一如戴嵩画《斗牛图》,以牛尾高扬表现勇猛激烈时,却被老农嘲笑不合常理。因此,逼真写实的图像,即便逼真度很高,也会因为动作姿态的不合,而让人产生轻慢的心态,如果逼真不高,那么,就更会让生活经验不是很丰富的人也产生轻慢心绪。
存形用的图像尚且如此,作为被祭拜的对象,要求当然就会更高而不能低。缘于此,也循于礼制规范,就出现了我们现在依然可见的一个传统:越庄重的场合,装饰图像越抽象。这样做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阻隔视觉把图像向物象的还原,不能完全还原,则生活的经验无法被激活、被调动起来,那么,就可以保证参与祭祀的人沉浸在现场应有的氛围中。对被祭拜的对象——祖先来说,写实逼真的图像还有更多的问题。首先是画祖先什么年龄时的形象,如果画儿童期,显然不合适。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去拜一个稚气的孩子,这种场景怎么能庄严?那么画一个老人形象,众所周知,一个人过了七十、八十岁固然是耄耋之年,可以令人景仰,但垂垂老矣的龙钟之态,如何给子孙以精神的振作?再者,写实逼真的老人,更容易让人产生的是可怜的心绪。而更容易让人头疼的则是:不是每个人都长得同样标准的。如果祖先生而有缺憾,那么一个残疾样老人又如何让子孙们产生自信与自豪?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便会有真切感受。倘若是隔了几代的子孙根本没有机会见到祖先生前的模样,他们在祭拜过程中,要搜寻的是我从哪里来?这种终极问题、终极思考。如果面对一副形象丑陋或有残疾的形象,又在如此庄严、无法选择的场景之中,能得出什么样的答案?
因此,如何来解决这一难题,才是真正的难题。因为这难题的困难程度远超出绘画写实技法之上。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观念的问题:即祖先对子孙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希望留给子孙的是什么?子孙当从祖先那里继承什么?而这才是作为画像的首要议题。毫无疑问,一个人的容貌是父母给的,是天生的,亦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一个人是否受人尊重,则是由他的行为决定,这是人为的,是人的意志体现的。因此,行为比容貌更代表一个人。当我们把时间的尺度,从一个人的生死,拉长到一个家族的兴衰时,那么,孰重孰轻就高下立判了。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用图像来表现一个人的行为。
这显然是比画得逼真写实更难的事。东汉王充甚至说过更极端的话:
人好观图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
因此,以程式化为基础,只是约略地体现人物的形貌特征,无疑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
程式化,其重要的是:表现人的基本形貌,忽略大部细节,这就是把我们通常用来判断一个人容貌漂亮与否的细节,做弱化处理,降低对容貌本身的期待值——亦即降低对表像的期待,提升对言行的关注度。因此,理智而高妙的做法是:太漂亮的画得一般些,有瑕疵的顺势忽略或减轻些,这种中庸的手法或观念的实施,就是我们今天翻阅历史与故物时所看到的:不太写实,大致相类。而在这背后,不仅体现了“死者为大”,对先人的宽容与对生命的敬畏,同时,也体现了直系于人本的平等观念。祖先给予我们最根本的是“由所而来”的生命,在这层面的平等,是最为紧要的、基础的,剔除了血缘的贵贱之后践行的人人平等。而这种初始的平等乃是生命平等观的实践,同时,也把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落实到后天的言行之中。
缘此之故,即便不是供奉在祠堂里,而是作为家藏,也是如此,程式化的形象,可以最大限度减弱官能欲望在观看中引发的功利评价,而将对先人的缅怀,导向言行等后天功德。
人生一世,能恒久传留的是言行,而不是皮囊。
皮囊是父母给的,我们不能责难父母,所以,只能感恩。
皮囊是天生的,我们无法选择,所以,天性平等。
皮囊是临时的,我们无法使其不朽,所以,言行才是生命的本质。
因此,轻容貌,重言行,背后是一种人本精神,平等精神,中国文化的精神。
轻容貌,可借助于程式;重言行,则依赖于传神。
以形写神之神,与人的后天修为相关,亦是你之为你的根本。因此,画像要真正画出某个具体的人,则要由形象传递出神气。
形以神为主,服从于神。故顾恺之可以在裴楷颊上凭空添加“三毛”,这无中生有之笔,要写的便是裴楷之神气。换言之,适度的增减是被许可的;适度的夸张变形,也是被许可的,但这夸张、变形、增减需符合一个原则:这便是能表现其神。
要表现对象人物的神,就要首先了解表现对象这个人。通常的肖像画,往往是让这个人坐着当模特儿,且还不能动。如此,形象是逼真了,可精神却不见了。因此中国画写像则推崇默识,如宋人陈造《江湖长翁集·论写神》云:
使人伟衣冠,肃瞻眂,巍坐屏息,仰而视,俯而起草,毫发不差,若镜中写影,未必不木偶也。
西洋式的写生肖像画法,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就已经被讥笑了。因着近世对西方造像技术的引入,而陡然成为先进科学,实在是不肖子孙之为。
陈造认为正确方法应当是:
著眼于颠沛造次,应对进退,颦頞适悦,舒急倨敬之顷,熟想而默识,一得佳思,亟运笔墨,兔起鹘落,则气王而神完矣。
看,仔细看,全面看,看熟看透,默记于心,让对象人物在心中丰富起来,活动起来,一笑一颦,喜怒哀乐,烂熟于心。然后,遇到佳想妙思,落笔酣畅,则人物的气神可以生动于纸帛上。
而宋人陈郁则认为,倘若仅仅是面对面的描摹容貌,有时不仅是徒劳的,甚至是无益的。
写照非画物比。盖写形不难,写心惟难,写之人尤其难也……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否则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贵贱忠恶,奚自而别,形虽似何益?
“何益?”这一问的背后,实际上说的是:仅仅满足了视觉还原的官能愉悦,激发的是官能性的欲望。而这种激发对观者并无益处。亦即低级的官能快感,于世并无益处,有时甚至还会产生负面的作用。
元代画家王绎,曾和倪瓒合作为杨谦画过《杨竹西小像》他在《写像秘诀》中对现今通行的写生式肖像画,有过同样的评价:
近代俗工,胶柱鼓瑟,不知变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传写。因是万无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吾不可奈何矣。
在他看来,肖像的秘诀是:
凡写像须通晓相法。盖人之面貌部位,与夫五岳四渎,各各不侔,自有相对照处,而四时气色亦异。彼方叫啸谈话之间,本真性情发见,我则静而求之。默识于心,闭目如在目前,放笔如在笔底。
本真性情,即便在官能欲望得到最充分肯定的宋人那里,肖像写真,还是重在性情。
不过从陈造、王绎的言词中,我还是可以发现,当时以求逼真肖似为目标的“俗工”并不是没有的,或许还是很普遍的,只是那种与西洋肖像做派一般的画家与作品,在中国绘画史上,只能是不记姓名的“俗工”而已。
所以,关于肖像,首先是为何要绘制肖像?也就是目的是什么?具体到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原由,如果觉得这个问题过于开放,那么,我们可以把问题缩小些,变成:给谁看?这样就把问题的答案指向归纳了。无外乎三种:一是自己看;二是子孙看;三是社会公众。
其实上述所有问题归结起来,只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既是肖像画主的,也是画家的,这就是给人看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否一个有效的解答,自我检验的方法是对这个问题注入时间:往上三代,往下三代。
你想见到你的高祖留下来的是什么?你想给重孙留下的是什么?这个时间打通了,问题的正确指向也就获得了。
当然,上述问题的语境是在照相机技术普遍使用之前,有了照相技术以后,像与不像就不是现实的问题了。然而,对于了解肖像画,了解中国人物画及其背后的中国文化依然是有效的。
关于皴法与描法的命名
对技法进行分类,就涉及类别的名称。命名,也就成为技法分类研究的直接成果。
技法分类的前提是技法有一种以上,亦即出现了比较丰富多样的技法才有实施分类的可能。其次是各种技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亦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比较显著。
皴法与描法,是用笔和线性层面上的基础技法,是构成画面的最基层元素,在个人风格的建构中,比造型、构图更重要、更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事实上,人物画的风格分类和山水画的风格分类,都是以描法和皴法这一最基本的技法特性为依据的。
因此,认知与鉴别基本技法,也就成为理解风格的基础。而对技法特性的认知与鉴别程度,又直接体现在对技法的命名上。所以,关注对技法的命名是一件有必要的事。
绘画中的描法与皴法,大致相当于书法中的笔法。故,亦可用“绘画笔法”或直接用“笔法”来指称描法或皴法。亦即描法是人物画的笔法,皴法是山水画的笔法。
绘画中笔法的分类完善于明代,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绘画呈现代流派风格的发展时期。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绘画从晋唐公众性人伦教化的成熟发展,经过两宋的醇化至元明已经演化为私人性的心性修养之径,成为社会精英人群——文人的雅逸之事,亦即到元明之际,与书结盟的绘画乃是世界万事中,最为文雅的顶尖之事,但对绘画笔法的命名,却以一种俗之又俗的面目呈现,这种雅俗的强烈反差,显然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不合理的。那么,为什么五百多年来,代复一代的画家、评论家都没有提过任何疑义,直至沿用到今天。
先看描法,明周履靖的《夷门广牍》、汪砢玉的《珊瑚网》和邹德中的《绘事指蒙》都有对皴法的记载,而以邹德中在《绘事指蒙》中的记载最为完备:
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种。一曰高古游丝描,用十分尖笔,如曹衣纹;二曰如周举琴弦描;三曰如张叔厚铁线描;四曰如行云流水描;五曰马和之、顾兴裔之类马蝗描;六曰武洞清钉头鼠尾描;七曰人多混描;八曰如马远、夏圭用秃笔撅头钉描;九曰曹衣描,即魏曹不兴也;十曰如梁楷尖笔细长撇捺折芦描;十一曰吴道子柳叶描;十二曰用笔微短,如竹叶描;十三曰战笔水纹描;十四曰马远、梁楷之类减笔描;十五曰粗大减笔枯柴描;十六曰蚯蚓描;十七曰江西颜辉橄榄描;十八曰吴道子观音枣核描。
清人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中统计古今山水皴法计有十六种:
古人写山水皴分十六家。曰披麻,曰云头,曰芝麻,曰乱麻,曰折带,曰马牙,曰斧劈,曰雨点,曰弹涡,曰骷髅,曰矾头,曰荷叶,曰牛毛,曰解索,曰鬼皮,曰乱柴。
如果说,“行云流水”“琴弦”“竹叶”“荷叶”“雨点”等,还略微显得文雅一点的话,那么“钉头鼠尾”“撅头”“折芦”“蚯蚓”“乱麻”“斧劈”“骷髅”“鬼皮”“乱柴”“马蟥”就不仅没有一点雅趣,只是粗鄙而已了。甚至有人可能见到“马蝗”“骷髅”“鼠尾”之类词眼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吧。
那么,究竟何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当然,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这些技法的称谓并不是一时一刻发明或出现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积累下来的。后人只是将其收集记录而已,这固然是一种观点,却显然是不够的。除了事实上确有的这样一种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外,更主要的大抵还是为了命名的能指和技法的实指之间有更直接的对应——亦即通过命名更生动、具体地揭示笔法的特性。如果结合邹德中配的插图,或者对照《芥子园画传》的示范图例,就可直观地体会到不同笔法下的不同线性的特点。比如说“高古游丝描”和“铁线描”,就线形上看是很近似的,但由于毛笔的强大表现力,使相近的线条可以表现不同的质感和动感,灵动活泼的游丝和端庄严谨的铁线,就可以通过命名的文字和其实指的对象给人的不同感觉中直观地体现出来。而“斧劈皴”的质感和“雨点皴”的组合,也是借着命名可以得到充分解说的。亦即,线条除了有粗细长短,轻重快慢,浓淡干湿,造成的形状的不同外,还有柔顺平滑,尖锐爽利,凝重厚实,轻盈飘逸,以至于平和安详,激越亢奋等落实在感觉中的线性。因此,画飞天仙女可用“行云流水”,而画观音菩萨则宜用“铁线”,虽在笔法上都是粗细均匀,平柔流畅,但用笔上快慢轻重的些微差异,所呈现的意趣则是不同的。这对后人的学习来说是大有裨益的。亦即借用现实生活人们熟悉的事物来命名,便可调动起日常积累的关于该事物的认知和体验,使原本抽象的线形与具体质感相关联,而这种具体的质感,恰是用笔手感的来源。也正是因为执笔画线的手有应对事物的质的赋能,线条才有了自身独立的表现可能与价值。
当然,线条自身的表现与形象匹配,则可以达到强强联手、事半功倍的成效。
因此,选择一种人们熟悉的事物来命名笔法,不仅是必要的,且是必须的。这种抽象事物具象说的传统,在书法中有更早的体现。魏晋时期就有了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山坠石”的类比。所取的喻义,也正是人们日常可知可感的具体事物。只是书法中的这一传统,到了绘画变得更自由、更夸张、更无所顾忌而已。
绘画之所以能如此随心所欲,不顾鄙陋地命名,与中国文化自春秋以来的去神圣化进程是一致的。今天的我们之所以会觉得绘画中笔法的命名显得鄙陋,是因为我们执持了西风东渐而来的“艺术是神圣”的观念。当我们给“艺术(绘画)”戴上了“神圣”的光环,那么,笔法命名的鄙陋也就是一个逻辑的判断。相反,倘若我们能回到中国文化的时状语境中,看到绘画自秦汉以后,渐次由祀礼神灵而人伦教化而心性修养的功用演化的进程,那么,笔法的这种命名就不是鄙陋,而是日常。
其实,绘画中笔法的这一命名方式背后所呈现的观念完全可以借用明代王艮的一句话来说明:“百姓日用即道。”
日用即道,投身于日常生活,这是晚明的思想,其实也是更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的演化指向。秦汉以来,绘画的笔触之所到遍及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画忠烈,也可以画圣贤;可以画贵妇,也可以画赌徒;以至于引浆卖流,贩夫走卒,锦鸡芙蓉,芦麻鼠虫,可谓无不可。而这正是日常生活,对中国画而言,不仅是可以,而且是必须的,因为自两宋以降,描绘神灵圣像之类,主要不是画家们的职责,而是画工们的工作。
不再依附神灵,亦不再攀附权贵,把生命落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便是文人画。
绘画笔法的命名,正是在绘画最根本的层面上,把人们引向全部生命意义所在的日用日常。
我们可以说绘画笔法的命名是鄙陋的,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都是鄙陋的,因为,绘画也好,文化也罢,都是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站起来。
当你站起来的时候,一切都是低矮的。
关于“美盲”
“美盲”,也是一个现在被常常使用的词汇。提出这个概念的吴冠中也因此而得了大名。“美盲”显然是由“文盲”衍生而来的。因此,可以循依着“文盲”来解读“美盲”。
文盲,是指不识文字,面对“文”(字)犹如盲人一般。那么,“美盲”便是面对“美”,犹如盲人一般。在一般的语境中“美盲”就是指不知美之为美。这种话出自美术专业人员,似乎极有批判性,当然,这是一种类比的说法。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真正的“美盲”。认不认字,可以客观检验的,知不知美,则显然是无法客观检验的。因为,“美”本身并不是和“文”(字)一样是一种客观知识,美是一种主观判断。当然,这种对美的感受、感知和判断与文化的熏陶、知识的积累有关联,这一点上和“文”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具有和“文”一样的客观性。
这里能不能认知或感受到“美”,就涉及了什么是美的?亦即关于美的标准。如果执持的标准不一样,那么,就无法获得统一的结果或结论——成为俗话所说的“鸡同鸭讲”。 因此,当一个评判者没有亮出自己的标准时,而人们也不清楚他的标准为何时,他的判断也就只能对他自己有效,而不具备公共性。亦即和呓语、臆测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也不排斥是别有用意。
因此,作为提出者吴冠中的关于“美”的标准的有效性,也就决定了“美盲”一词的有效性。
吴冠中关于“美”的表述,主要并且完整地体现在他的《绘画的形式美》。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形式美”似乎就和吴冠中关联了起来,并且对“八五新潮”等一批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誉为“号角”“领军”。
如果说当时的“形式美”,是“红光亮”语境中发出的一种对绘画本体的反思与回归,那么,这种回归的有限性是由其功用性的扭转所决定的,亦即吴冠中对形式美的倡导,其实质指向是当时的绘画的功用,而不是本体。换言之,是借“形式”来指摘“功用”。因此,他所谓的“形式美”就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是关于形式的基本构成要素的复述,这当然只是常识,只是因为有了针对“功用”的语境指向,其复述也就成为其扭转功用的证据,亦即并不是客观的形式要素的梳理,而是将客观的形式要素作为其主观意愿的论据而已。其二,他所谓的形式美的依据其实就是他留学欧洲得来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倡导,亦即既不是他自己的感悟,也不是循依历史文化的研究,而是一种拿来主义的挪用,尽管这种方式是简单且粗陋的,但在当时却是十分受用的。
这些落实在油画中的各执己见对于那些对油画并无全面认识的人来说,既是新鲜的,也是深刻的,吴冠中也因此而成了中国现代绘画的“导师”。如果仅限于油画,那么,吴冠中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当他开始对中国画也施以同样的手段时,他的简单与粗鄙就暴露出来了。当他甩出“笔墨等于零”的时候,他对中国画的无知便无法掩饰了。
从倡导“形式美”到“笔墨等于零”,可以看到吴冠中的投机逻辑。“形式美”的潜台词是绘画不应该强调“教化”功能,而“笔墨等于零”的潜台词则是:没有“教化”功用的笔墨等于零,强调的是“教化”功用。在形式与功用之间的飘移,说明并不是他不懂、或无知,而是见风使舵,或者最客气的说是为了制造话题,提升关注度。但值得关注并不是自相攻讦的矛盾,而是这矛盾背后的心态。
当然,也可以为吴冠中作如下辩护:因为倡导形式美,导致过于浮于形式表面,故而有必要再次强调内容(教化)的地位。这种将其抬到一言九鼎、左右画坛的崇高地位的辩护,似乎合于文字的逻辑关系。但是,若将他的另一句大话联系起来,那么,情形或许就并非如此了。吴冠中曾有“一百个齐白石不如一个鲁迅”,在这里“齐白石”无疑是“形式”的指代,“鲁迅”则是“教化”的指代。
众所周知,鲁迅的杂文是匕首和猎枪,齐白石的画则是花花草草。如果这个观点是成立的,那么崇拜鲁迅的吴冠中的画,做不了匕首与猎枪至少也应该是一根木棍或石块,遗憾的是他的画,几乎没有一幅堪称棍棒,甚至连一枚针都算不上。当一个人的理论观点和他的实践作品对不上的时候,又应该更相信哪一方呢?
如果依照孔子所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那么,吴冠中的话不仅是不可靠的,且很可能是别有用意的。
这中间还有一个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这种不忌惮的大话都是在中国画中说,对油画却是不敢多置一词的。这大概也源于他对观众的尊重。他说过他有两位观众,一位是西方大师,一位是中国老百姓。老百姓大概率都在“盲”的范畴内,因此,西方大师就重要了。
其实,单独看,吴冠中说的似乎都在理,甚至连“画院美协如同妓院”之类,话虽糙,却也不无道理。之所以如此,在于很多时候人们只看了他的评说结果而没有追问他评说时状现象时执持的标准。评价标准,往往是一种潜在状态。虽然,通过其评价结果,可以略窥一斑,但未必能尽见全貌。直到后来吴冠中推出他的“书法”时,之前的谜面才有了准确的答案。
书法,顾名思义是遵循法度的书写。而这书写的“法度”,已经经过了至少两千年的传承和检验,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法度”都是不证自明,共同执有的。因此,任何人,只要沾上书法,那么,其笔墨功力,文学功底和品鉴修养便可高下立判。对照吴冠中的“书法”,那么,他说的“笔墨”指的是什么,“形式”指的又是什么,也就清晰可见了,至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原本潜然于绘画中的问题都浮了出来。
正是借着书法这面镜子,我们才清楚:假如吴冠中不是“美盲”,那么,不能欣赏吴冠中“书法”之美的,便是“美盲”,亦即吴冠中的“书法”是清晰、简单的判断是否“美盲”的标准。
我们不清楚吴冠中何以会使出这种自戕性的“回旋镖”,把自己定性为“美盲”?
倘若不是这样,那么,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只有认同了吴冠中指定的美,才不是“美盲”;如果不认同他的指定,便难逃“美盲”的判定。这确实很适合西方的现代主义逻辑。
现代主义的蛮横逻辑,往往在遇到书法时会出现这种不堪的矛盾,相反,所谓从事书法的人一旦遇到了现代主义,倘若不能弄清楚其逻辑与标准,那么,同样难免落入不知所措的境况,典型的例子便是“丑书”。
“丑书”者的之所以要丑书,其潜在的评判标准并不是通常标榜的创新,而是不知所措境况下的盲从。这种盲从的前提是放弃书法既有的标准,代之以舶来的现代主义的观念。
书法的本体被弃置,降格为表述现代主义观念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因此丑书,本质上是反书法的。
“丑书”之所以要被打上引号,当然是表明“丑书者”并不以为是丑陋的,不仅可以拿“天然”“天性”“率性”“童心”“自由”等等高尚且高级的词汇来注释、辩说,甚至还可以用“审丑过敏症”来诊断:如果你认为那些“丑书”真的是丑陋的,那么,你已经得了“审丑过敏症”。
由此可见,“丑书”之所以能以其“丑”而行于世,并不仅仅是因为有了一批为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为我所用、不及其余的批判家的帮忙,也有着手握“审丑过敏症”之类“美学”理论的支援。因此,“丑书”的能大行其道,就不仅仅是因为有“丑书”的作者,更有其理论和观念上的支撑。这就不是个别的问题或某个环节的问题,而是系统性的问题了,亦即从作者到批评到理论的完整闭合链。
这也就意味着,单从“丑书”本身来看是不够的,也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丑书”之所以敢“献丑”,是因为背后有一套“审丑”的强大理论支撑。理论对于“丑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是生死攸关的。“丑书”之所以用“丑”字来指称,在于其弃置了技法、法度。书法,本立根于“法”,既去其法,则无生根立命之所。于是,言说、辩护、推广之词,便成了“丑书”的救命稻草,亦即对“丑书”的解说之词,乃是“丑书”的立命之基。而原本以美为旨归的理论,何以成为“丑”的资生者?这当然不是“丑书”者所能做的,而是“审丑”者的需要,亦即从大的因果关系而言,并不是因为有了“丑书”才有“审丑”,相反,恰恰是“审丑”理论的需要,助生了“丑书”的张扬。
泛化“审美”和泛化“民主”是同样的伎俩:寻求并建立的霸权。
20 世纪 80 年代,美学热潮退去后,“审丑”或“丑学”就开始登台了,将“丑”与“美”作等量齐观的同时,也就消解了“美”与“丑”的边界,原本被抑制、排斥的“丑”就此登堂入室。潘多拉之盒打开了。
美学之所以作为一门学问,得以成立在于它能提供一系列鉴别美的标准——所谓的审美,是对美的鉴定,而这一系列标准中最基础的,也是最核心的标准是美与丑之间的界分。换言之,消解其作为一门学问存身立命的根基:帮助人们认识生活中的美与丑——判定美丑的标准,无疑是一种自戕行为。设想一下,如果科学取消了“真与假”的标准,还成其为科学?伦理学取消了“善与恶”的标准,还成其为伦理学?“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标准的确立,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得以建构的基础。尽管在某些极个别的场合,“真与假”“善与恶”的边界会有模糊或权宜,但在总体上是清晰而明确的。而之所以不能消除真假、善恶的评价标准,是因为这些标准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与否。
所谓“文明病”的说法,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标准失落的诊断。而当今世界依然能维持的原因,并不是这些标准可以可有可无,而是被金钱所取代,亦即建立在金钱之上,其表现就是:价格。除了大部分真假的判定以外,善恶、美丑的判定事实上已经让渡给了金钱。文学、艺术,以至于哲学、伦理等,在很大程度亦已沦为了标价的解释者与鼓吹者。即“审丑”能够被提出来,不是丑有值得申扬的价值,而是被标价的缘故。
“丑”之所以被标价,在于其独特性质。丑作为美之外的或对立的一面,其呈现的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是由在对美的规定的时候给定的。一如与“真”相对“假”的呈现是多样性的;与“善”相对“恶”的呈现也是多样性的。因此,“审丑”,实质上是配合标价的理论推销。将多样性中不可比的因素抽出来,正是垄断价格得以逻辑合理的必需。在这一意义上,“审丑”是“暴利”的帮凶,然而,比较可悲的是因为从“审美”转向“审丑”,并不是受暴利获得者“雇佣”的。因此,在此过程中,所获之“暴利”,往往与“审丑”理论者鲜有关联或了无关联。因而,“审丑”者便又有了酸葡萄心理,甚至忿然不平。这种既失学术之本,又不得现实之利的行径,显然是有病了——所谓“文明病”或便是对这一类现象的诊断。

《中国画品评史绎》内页
夫子有言,攻其异端,其害也者已。美学之自贱与自戕,正源于其专攻“审丑”之异端。将“审美”偷换为“审丑”,其根本在于“丑”的多样性,而将多样性与独特性作等量齐观,再将独特性与创新性关联,最终封上“创造性”的桂冠,“丑”便战胜了“美”。如此,此刻你依然认为那是丑陋的,那么,另一项帽子也正合适你了:“美盲。”
“美盲”一如“色盲”,是一种诊断。那么,什么样的人有这样的权利?诊断“色盲”要有完备的医学知识、经验和手段,当然,更要有有效的标准。那么,诊断“美盲”呢?当然也需要有相应的知识、经验。但是,在没有客观的手段,尤其是连标准都缺失时,所谓的诊断无异于臆断。当专业的知识、经验不构成公认的标准,那么,诊断的真实依据,便是个人的好恶与胆量:所谓撑死胆大的,指的便是这种现象。于不合我的好恶口味,便是“美盲”,便是“这个时代出了问题”。以一己之私心,充任一个时代,这种近乎疯子的言行依然有其市场,说明我们的时代真是有了足够的“民主”:不管是一个正常的“民”,还是病态的“民”,都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主”。
由此可见,“美盲”或者“审丑”之类均是私欲膨胀下的失本、失节,跌落到寡廉鲜耻境地的既是作为理论的当代美学,也是作为实践的当代艺念(术)。唯其如此,方能信口雌黄,以一己私欲,僭越为时代判官。
(作者邵琦曾任上海书画出版社《朵云》编辑、编辑部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8月20日下午13:30,“如何读懂中国画:《中国画品评史绎》”新书首发式将在上海书展世纪活动A区展开,嘉宾包括新民晚报高级编辑李天扬、书法家刘国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