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因治疗绝境求生:孤注一掷的罕见病患者
2018年11月26日,yoyo(化名)迎来了她8岁的生日。母亲秦可佳早早就下班回家,给她买了生日蛋糕和一顶皇冠。戴着皇冠的yoyo四处跑动,一边拍手一边叫喊着,看起来十分高兴。
早在一岁半的时候,她能叫爸爸、妈妈、奶奶,可如今她只能“咿啊”地叫着,不知面前的蛋糕为何物。为了不让女儿打翻蛋糕,秦可佳从后面抱住了yoyo,母女俩一起拍了张照。

秦可佳从不把女儿生日的照片分享到朋友圈,“从yoyo出生开始,她的生命就在倒计时”。yoyo体内的一个基因出了问题,导致她患上一种罕见病,她的身体、感官和智力都在不断退化。
为了打破这个“死亡沙漏”,秦可佳多年来奔波于国内外寻医问药,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基因治疗。但就在生日聚会后,她在新闻上看到,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已经出生。
尽管罕见病基因治疗与基因编辑婴儿有本质不同,但后者引发的巨大争议还是让基因治疗蒙上一层阴影,也让努力了五年的秦可佳平添了几分担忧。
致命基因
今年38岁的秦可佳与大自己一岁的宋涛结束了十年爱情长跑走到一起,硕士毕业后两人来到北京投身于航天事业。婚后两年,女儿yoyo出生了。
刚出生时yoyo就有一头浓密亮泽的头发,脸蛋柔软嫩白,秦可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之中。两岁之前,yoyo和别的孩子一样,一步步学会翻身、坐爬、站立、走路。只有一样让秦可佳感到隐隐担心,yoyo的语言功能迟迟没有进步。

尽管如此,看到yoyo萌萌的样子,秦可佳与宋涛并没有多想,直到发现慢慢长大的yoyo有些异样——
“她总是到处乱跑,没有主动叫过谁,对一切事物感到好奇。”听不到一声“妈妈”,这让秦可佳十分着急。
2013年5月,秦可佳和宋涛奔赴靶场执行神舟十号发射任务,期间只和yoyo通过电话联系。电话里yoyo总是笑着,秦可佳感到女儿很想说话,却不会表达。
等到7月任务结束回到老家,秦可佳进门就想抱抱女儿,yoyo有些冷漠,抱完转身就走了,仍然没有主动叫妈妈。
5天后回到北京,夫妻俩直接带着yoyo去到首都儿科研究所。初步检查显示,yoyo的发育商偏低,判断智力发育迟缓;一周后,核磁共振显示yoyo的大脑出现了脱髓鞘病变,这是一种常见于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的症状。
秦可佳回忆,当时她就跟疯了一样,她不明白女儿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夫妻俩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医院,只记得一位医生说,他从来没见过这病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出现。
9月的北京骄阳似火,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秦可佳形容自己的心和冰窖一样冷。她和宋涛被医生喊进了办公室。在此之前,她得知女儿患上的可能是一种叫做黏多糖Ⅲ型溶酶体贮积症(以下简称MPSⅢ)的遗传代谢病。但此时,他们仍然希望能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然而那一整个下午,秦可佳哭着听完了医生的话。
“你们要有心里准备,孩子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慢慢失去所有功能,包括记忆、理解、语言、行动甚至吞咽,他们大多活不到青春期……”
301医院小儿内科副主任医师孟岩告诉秦可佳,yoyo的病是由一种单基因缺陷引起的罕见病。基因缺陷导致yoyo体内天生缺少一种酶来分解黏多糖分子,导致黏多糖在全身细胞内堆积,随着时间的推移破坏脏器、骨骼、神经系统……
孟岩形容黏多糖病,“如同一个房间,垃圾堆得越来越多却无法清理,最终人无法入住。”
其中Ⅲ型直接病变于中枢神经系统,yoyo的大脑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萎缩,失去所有功能。孟岩说,Ⅲ型黏多糖无药可治。
而所有黏多糖贮积征的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一,根据发病率计算,中国至少有1000人患有这种病。
回去的路上,秦可佳强忍着泪水。yoyo走着跳着,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一无所知。

“生机”与“绝望”
这不是孟岩第一次接触“黏宝宝”(黏多糖溶酶体贮积症患儿)。早在7年前,郑芋带着女儿飞飞(化名)从西安赶到北京,想为女儿寻找一线生机。
在飞飞4岁半的时候(2001年),郑芋送她去上舞蹈班,老师反映飞飞的脚常常使不上力气,直到在医院拍片后才发现飞飞的骨骼异常,原因不明。
“当时医生说可能是黏多糖,我还以为是糖尿病之类的毛病。”这是郑芋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走了七八家医院后,医生告诉她,飞飞患的是Ⅳ型黏多糖贮积症,“孩子长不高了,一般10多岁就没了,给孩子吃好喝好吧。”
“哪怕她缺哪个器官我给她,只要能救我女儿的命,但这种病我想给也给不了……”为了给女儿治病,2005年底郑芋辞去工作,只身来北京,“我就不信女儿只能等死。”
正如郑芋所说,并非所有的黏多糖患儿都毫无生机可寻。
2005年10月,一个叫健健的男孩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接受了中国首例黏多糖患儿骨髓移植手术。负责这台手术的血液科主任王玲介绍,黏多糖病十分复杂,根据基因的类型以及所编码酶的不同,至少分为7种大型和16种亚型,每种类型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都不相同。
当时根据基因检测和酶学结果判断,健健属于Ⅰ型,国内出现较多的是Ⅰ、Ⅱ、Ⅳ型,发病率均为十万分之一。
健健的手术很成功,移植两个月后“天门”完全闭合、身高92厘米、肝脾恢复正常,智力发育指数也慢慢升高。
2010年,健健的母亲王秀群接受成都商报回访时说,健健现在活泼调皮,正在上幼儿园。他很爱吃,个子也长得快。最近一次测身高,健健是1.2米,在幼儿园里算中等偏上。
2006年,当郑芋得知骨髓移植是唯一的治疗手段时,她灰暗的世界里亮起了一盏灯,“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把房子卖了,为了救孩子,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但这盏灯很快就灭了。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欧瑞明介绍,从2005年至今,二院仅做过两例骨髓移植(包括健健),第二例经过基因检测后发现也是Ⅰ型黏多糖患者。即使到今天,专家认为只有Ⅰ、Ⅱ、Ⅵ型的患者适合做移植,这其中还要看患者局部受损的情况、骨髓提供者的状态等等,条件十分“苛刻”。
多年后王玲在一篇博文中写道,骨髓移植的效果也取决于众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移植时的年龄最好在18个月以内,赶在过度积累的黏多糖给组织和器官带来不可逆性损害之前实施。
而对于Ⅳ型患者来说,身体器官和骨骼的变化较慢,不一定适合骨髓移植。前世界最矮男子何平平身高仅74.61厘米,他也是一名Ⅳ型患者,终年21岁。
郑芋从医生那里得到的答案是——飞飞不适合做骨髓移植,失败的概率很高,而且飞飞的发病过程稳定,不会损害到大脑,即使进行骨髓移植,效果也并不一定理想。
郑芋犹豫了,她选择了保守。
和yoyo不同,飞飞知道发生了什么。9岁那一年,飞飞突然问郑芋,为什么我长不高?郑芋只能安慰她。
女孩都爱美,因为腿脚不便,飞飞上楼梯要么由爷爷背,要么自己一步步爬。她觉得自己上楼的姿势难看,所以每次都让郑芋走在前面,不让她回头看自己。
在母亲郑芋眼里,飞飞多数时候是乐观的,但她也跟奶奶说过类似“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话。
女儿患病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郑芋不会笑也不社交,整天埋头搜索关于黏多糖的资料,到处寻医,却发现有些医生对罕见病知之甚少。
绝望笼罩着她。和秦可佳一样,面对疾病,两个母亲必须和时间赛跑,却不知希望在哪。

“孤儿药”困境
2017年10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在《中国小儿血液与肿瘤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黏多糖贮积症儿科专家共识”的文章。里面提到,目前MPS的主要治疗方法为酶替代治疗(ERT)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
酶替代疗法的原理很简单:人体缺什么酶,就从外部进行补充。这不仅可以改善部分患者的临床症状,同时也降低了并发症。
秦可佳和郑芋早就了解到这种疗法,几乎所有黏多糖患者的家属也都知道,可很少有人能够用上。
欧瑞明解释说,酶替代的药物大多在国外研制生产,目前在国内没有上市。“没有国家药监部门的批文即会被认定为假药,如果在国内销售就是违法的,就像电影《我不是药神》里的那样。”
北京协和医学院遗传学家黄尚志2013年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分析,从生产角度而言,与常见病相比,罕见病人群相对较小,而投入药物生产研究过程耗费较高,药厂回流的钱就会少。因此这些药被形象地称为“孤儿药”。
目前,国内只有极少数“孤儿药”被个别省市纳入了医保。如果患者自费购买酶替代药物,每年花费大约在150-200万人民币左右,且需终身用药。
郑芋身边仅有两个家庭在国外买过药,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是商人,五年花费近千万。每次买药直接给美国药厂汇款,药厂人员将药品转运到香港,购买人再去香港经中间人取药。
“56万元人民币,订购了40支注射用药,每支14000元。这是孩子4个多月的用药量。什么时候钱没了,孩子也就没了。”
尽管多年来医学专家、学者都不遗余力呼吁将黏多糖等罕见病纳入医保范畴,但截至目前收效甚微。
黄尚志在采访中说道,“相关部门多将财力投入在多发病、常见病,以及非典、H7N9等对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疾病上。而诸如黏多糖等相对罕见的病症,关注度不够。”
秦可佳的困境在于,即使她有这个经济能力,yoyo也无药可用——由于Ⅲ型发病集中在中枢神经系统,酶作为大分子被注入人体后无法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酶替代疗法对她“关上了大门”。
yoyo在5、6岁的时候特别多动,喜欢摇晃椅子和门。由于逐渐失去感知外界的能力,她只能通过这种的方式刺激自己,比如摔东西。
“家里的碗已经换了几批,电视机换了三个,手机已经数不清几个了。”秦可佳说,yoyo甚至会把手指咬破,为此她曾经不得已给女儿带上特制手套。
如今yoyo已经8岁,进入到病症中后期。她不再多动,行动能力和吞咽能力进一步下降。2017年做的24小时脑电监测显示,她的睡眠波出现严重异常。
yoyo经常在半夜里醒来,秦可佳唯一能做的只是抱着她,直到她疲倦睡去。“不论女儿变成什么样,我永远会给她毫无保留的爱。”但她清楚地意识到,留给女儿的时间不多了。
再过几年,yoyo就会失去吞咽功能,那时就要在她胃上开一个洞,用导管将流食注入体内;接着脑萎缩会让她癫痫不断发作,呼吸能力也会变差,她的生命随时可能终止。
希望的曙光
秦可佳不上班时,几乎24小时守着yoyo,防止她摔倒、磕伤。除此以外,她经常一个人在家附近的肯德基查资料、写文章。也许女儿永远也无法像餐厅儿童乐园里的孩子一样嬉戏玩耍,但她没有放弃寻找希望。
2014年,她通过美国临床试验数据库(ClinicalTrials.gov)找到了一条关于MPSⅢA的记录。一家名为Lysogene的法国公司在2014年发布了一项临床试验,标题的最后写道“Gene Therapy”,也就是基因治疗。这是秦可佳第一次看到这个词。
在这份公开记录中,已经有四名MPSⅢA患者进行了药物注射,直到今天,临床试验仍处于1/2期。
秦可佳立即联系到这家公司的CEO,一位46岁的法国妈妈Karen Aiach。Karen说,自己的女儿Ornella也是一位MPSⅢA患者,已经用药2年多,目前状态稳定。
此时秦可佳并不明白什么是基因治疗,也不知道试验是否成功,但她在绝望中看到一丝转机。至于风险,“我没得选,哪怕是希望渺茫我也会去找。”当时秦可佳在国内的搜索引擎里输入“基因治疗”,只有一条相关信息,除此以外找不到任何报道和文章。
秦可佳说,根据Lysogene公布的数据,一期临床试验的安全性已经得到验证。
而Karen在2015年接受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采访时说道:Ornella依然是一名MPSⅢA患者,只是从6岁起开始了治疗。从过去三年的情况来看,她好转了许多,不再过度活跃,睡眠也很好。这改变了她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我有一个会笑的孩子,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秦可佳习惯用详实的数据和资料来分析判断,基因治疗是否可靠。
2016年3月,美国Abeona公司在临床试验数据库发布了一项试验,对象同样为MPSⅢA患者,参与人数为16人。
在Abeona公司官网上,可以查询到更多关于临床试验的数据与内容。其原理可以概括为“基因替代”(Gene Replacement),即通过基因载体(通常为改造过的病毒)导入一段有独立功能的基因进入体细胞,代替已经发生突变的基因进行独立表达,发挥其原本应该有的功能。
这个案例让秦可佳眼前一亮,其中一位受试者美国女孩Eliza比yoyo大一岁,也是Ⅲ型,这更让她感到希望就在眼前。然而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罕见病医保,对方拒绝了yoyo的试药申请。

但此时秦可佳确信自己找到了方向,她把yoyo最后的时间都押在了基因治疗上,“我要研制出自己的孤儿药。”
正如黄尚志此前所说,由于市场太小,鲜有人愿意将精力和金钱投资于罕见病药物研发上,秦可佳只能自己寻找科学家、自己募集资金进行研发。“最困难的是资金,光一只模型老鼠的费用就高达上万元,一只用于试验的猴子甚至需要30万元。”
只有当基础研究、动物试验等前期准备工作完成,针对yoyo的项目才有机会进行学术和伦理审查。即使通过审查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yoyo也只能被称作“受试者”,对她进行的并非治疗,而是试验,仍然有失败的可能。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疯子,认为我病急乱投医,但正因为研究过国外公开的资料和案例,它给了我希望和努力的方向。路再难,我也要拼一把。”
正如Eliza的父亲格伦·奥尼尔在同意女儿接受试验之前说的那样,“这是她唯一的机会。”(It was her only shot)

“我是航天人,基因替代就好比火箭搭载卫星进入太空。火箭是病毒载体,卫星是起作用的正常基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基因,就利用病毒包装好这个基因送进人体细胞。在这个过程中,火箭是运输工具,用什么卫星我们说了算。”
秦可佳打了个比方来解释基因治疗的机理,她深信未来这会成为治疗罕见病的主攻方向。
哈佛大学医学研究所成员田禾在此前发表于澎湃新闻的《基因疗法解题①》一文中解释道,自然界中有一种善于跨域细胞膜的微生物——病毒。科学家想到,如果将需要添加的基因片段插入病毒的基因组中,也许可以依靠病毒将基因片段带进活体细胞中。
然而病毒不是细胞,不能独立分裂,要寄生在宿主细胞内才能自我复制。这种复制是以自身健康为代价的,免疫系统会与病毒展开搏斗,宿主会出现炎症反应。
所以天然存在的病毒是不能作为运输载体的,病毒需要经过改造,失去细胞内复制的能力,还要尽可能避免触发免疫反应,危及宿主生命。
过去20多年,基因治疗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波折。
199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詹姆斯·威尔逊开发出一种腺病毒载体(Adenovirus),并开展了一系列临床试验。其中一项试验针对一种罕见的代谢疾病,患者缺少尿素代谢的一种酶,大部分无法活到14岁。少年杰斯·格尔辛基已经与这种病搏斗了18年。
研究人员把制造酶的基因装进了被“腾空”的病毒载体里,约1万亿个载体被注入格尔辛基体内,导致他产生了激烈的免疫反应。几天后,格尔辛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8岁,这是第一个死于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者。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药学院教授肖啸解释道,格尔辛基因为急性免疫反应而死亡,静脉注射高剂量腺病毒是威尔逊的致命错误,当然还有一系列违规行为。这其中就包括之前在猴子身上进行的类似试验时,已经导致实验动物死亡,然而临床试验并没有及时叫停。

这是基因疗法历史上的一次惨痛教训,随后威尔逊被美国FDA禁止十年不许涉及临床试验,而这期间大部分基因疗法的临床试验均以失败告终。
直到18年后,美国监管部门才批准了一项关于遗传性视网膜病变的基因治疗,并诞生了首款在美国获得批准的基因治疗药物。根据FDA官网数据,截至目前全球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大约有2000多例,已批准上市药物有6个,尚无安全性事件报道。
这其中,腺相关病毒(Adeno-associated virus,简称AAV)成为了新的“火箭”。肖啸介绍,和当年所使用的腺病毒不同,AAV是脊椎动物病毒中很少见的非病原性病毒,也是先天性缺陷病毒,本身不能复制,需要在其它致病性病毒存在时才能复制,同时抑制那些病毒。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好”病毒。
尽管如此,即使选对了“火箭”,“火箭”的量应该控制在多少等一系列问题仍然需要缜密研究。
田禾说,格尔辛基的悲剧提醒着所有医学研究者,在试验新疗法时,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绕不开的伦理问题
原国家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规定:“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配子、合子和胚胎进行基因操作”;《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也明确规定,不得将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它动物的生殖系统。
2018年年末的基因编辑事件在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基因编辑技术权威、CRISPR基因编辑专利持有人张锋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多数科学家都认同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是不道德的。
在yoyo生日的那天晚上,秦可佳不停地收到来自身边医生、朋友的询问,起初她没有在意,“这起事件很明显与罕见病的基因治疗是完全不同目的和结果。“
肖啸也指出,现阶段基因治疗主要有基因替代和基因编辑两种方式,不论哪一种均用于治病救人,只作用于体细胞而非生殖细胞,这与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有本质不同。
但秦可佳担心,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起的连锁反应会使国内正常的基因治疗被迫收紧,“如果这样,等待救命的罕见病患儿就没有希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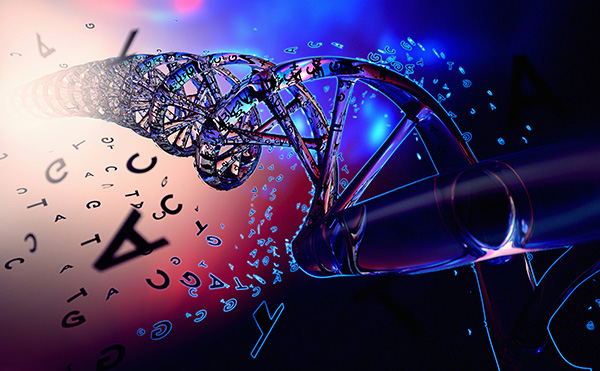
在这次风波前,我国的基因治疗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办的微信公众号“新叶社”在《基因治疗的国内外研究进展》一文中提到,我国基因治疗研究及临床试验与世界发达国家几乎同期起步,目前已经有3个基因治疗产品上市,此外还有20多个针对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遗传性疾病的基因治疗产品进入了临床试验,其中在临床试验网上登记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方案就有70多个。
秦可佳反复强调,罕见病用药与常见病不同,“首先是极大的迫切性,其次是患者子样少。目前已发现的罕见病7000余种,90%左右无药可治,很多孩子自出生就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对他们而言,有药可用才是最重要的。”
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伦理学家邱仁宗对众多媒体表示,不管是针对体细胞进行的基因治疗,还是用CRISPR对生殖细胞进行的基因编辑,都应该安全可靠,严格按照程序来走。
中国孤儿药创新联盟发起人郑维义介绍,在进行临床试验前,找到治疗疾病的化合物等基础研究就需要约3-4年,罕见病药物临床试验需要2-3年,整个周期十分漫长。
秦可佳觉得自己等不起了。yoyo的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她期望女儿有机会,哪怕只是维持住现在的状态,而不是等到她无法进食、只能靠呼吸机生活,药才迟迟出现。那时候,再救她反而是种残忍。
“如果我私下找个诊所给yoyo用药,那跟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性质就没有区别,整个行业发展会被搅乱,伤及无辜。”秦可佳说,在经历过那么多挫折后,她变得更加理性。
“母亲的呼吁”
秦可佳从来就不是一个柔弱的女性,这一点郑芋深有体会。
早在2012年,郑芋牵头成立了北京正宇黏多糖罕见病关爱中心,但秦可佳认为仅仅“关爱”还不够,罕见病更需要的是被社会关注,通过社会力量推动政策和科研进步。
2015年秦可佳建立了cureyoyo网站,帮助MPS患儿家庭提供护理指导和研究信息;随后,她牵头发起了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SF罕见病专项基金。2018年,基金向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定向捐赠110万用于MPSⅢA基因治疗研究,以推动药物早日进入国内的临床试验。

秦可佳希望,有关部门能区分用于治病救人的基因治疗与违背伦理的基因编辑,不因为个别违规事件,导致罕见病患者失去救治机会。
她也期待,国家能够尽快出台孤儿药鼓励政策,从医院到药审建立罕见病绿色审批通道,宽严并济推动国内基因治疗良性有序发展。她呼吁,参考美国NIH对孤儿药的做法,在罕见病临床试验的伦理评审中增加患者家庭(或组织)代表发言,保障那些严重危及生命却无药可治的患者的生存权。
对秦可佳来说,每天醒来还能看到yoyo的微笑,看到她欢快地跑来跑去,已经很满足了。
yoyo的父亲特地买了一台单反相机,记录女儿长大的点点滴滴,亦或是,最后的时光。秦可佳却不敢翻看这些照片,每次她都会忍不住流泪。“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停留,再给yoyo多一点时间。”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