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70
鲤鱼洲往事|镜相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作者 | 路明
编辑 | 吴筱慧

天色阴郁。七月,乌云低沉,像吸饱了雨水。洪水浩荡而来,吞噬其它色彩。站在堤坝上望,满目浑浊昏黄。近处漂过几绺水草,他问老白,像不像一锅咖喱牛肉汤。
小猢狲还在关禁闭。出早工时,三连的“狼狗”嘲笑小猢狲娘是资本家姨太太。小猢狲垮着个脸,一声不响。中午收工,各班围一个圈,坐在地头吃饭,小猢狲悄无声息绕到狼狗背后,一脚踹去。狼狗爬起来,抹一把嘴,反手操起锄头。两人被勒令写检讨,外加禁闭三天。回来的路上,老白捅捅他,上次探亲,带回的咸肉还剩半块。他心领神会。咸肉洗净切片,闷进柴火灶,大火猛蒸。二十分钟出锅,肉呈半透明状,白萝卜般晶莹剔透,香得张牙舞爪。他和老白猛吸几鼻子,各自夹了两片,剩下的压在饭底,送进禁闭室。
他们三个从小相识。一道在弄堂里闯穷祸,又一道上的苏联制实验小学,共享“皮大王”的声名。那是中苏蜜月期,常有苏联及东欧代表团来校访问。小朋友都会几句俄语,布拉吉哈拉哨,打仗冲锋喊乌拉。别的小学读六年,苏制读五年,等于跳一级,直接汇入初中。以至于当六九届“一片红”大潮汹涌而至,他们都有点蒙,觉得自己何德何能,赶上了这惊天动地的伟业。
阿姐大他一岁,读的是普通小学,也是六九届初中毕业。阿姐插队去安徽蚌埠。他一心想当兵,于是报名去了江西,那里是军垦农场,好歹跟解放军沾点边。老头子在大学教古汉语,此时下放劳动,姆妈在单位集中学习,都没能来送他。那一天,他吃了泡饭和萝卜干,汰了碗,背上背包,拎着被褥去学校。一进校门,看见操场上停着十几辆披红挂彩的公交车。大喇叭歌声雄壮,一旁有人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离开。公交车发动,人群缓缓后移,他想,就是这个时候,要记牢。往后的漫长岁月,深夜茅舍黄昏地头,辗转反侧或是忧愁袭来,他会掏出这个时刻,像掏出一片陈年红薯干,反复地咀嚼。
火车两天一夜到南昌,换解放牌卡车,一路风尘颠簸。不知过了多久,前面人喊,到了到了。他跳下车,一个趔趄,差点跪倒在地,腿酥麻了。眼前是操场、旗杆、一排灰扑扑的平房,再远处,大片农田铺展开,几座草棚点缀其间。视野之外,是浩渺无际的鄱阳湖。这地方叫鲤鱼洲,原本是一片滩涂。1965年,响应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口号,南昌市组织四万劳力,大干快上,围垦出十二万亩农田。当年冬天,又修筑八十里大坝,隔开农场与湖水。报纸上热烈宣传了一番,叫“人定胜天”。
他、老白、小猢狲,每人领到一身军装,没有军章帽徽,胸前硕大的“农垦”二字。他们是光荣的“兵团战士”,主要任务是种棉花和水稻。此外,冬季加固大坝,夏季抗洪救险。听老兵讲,每年七八月汛期,鄱阳湖倒灌赣江,鲤鱼洲低于水面十几米,等于在湖底。大坝是生命线,鲤鱼颤动的背鳍。一旦溃堤,那就是灭顶之灾。
主食是籼米饭,硬硬的一坨,咽起来扎嗓子。此外有绿豆、黄米和小米,一个礼拜吃一次肉。虽然在鄱阳湖边上,平时很少能吃上鱼。除了辣椒炒冬瓜皮,最常见的蔬菜是蕹菜,就是当地的空心菜,个头硕大,坚韧到难以下咽,诨名“无缝钢管”。
老白说,别的都能忍,洗不了澡太难熬。场部有集体浴室,一个礼拜轮流洗一次。夏天好弄,收工后,井水一冲。冬天汗水捂在棉袄里,裤腰上一圈白花花的盐渍,肉都咸了。加点蒜薹、干辣椒,下锅一炒就是一盘好菜。
老白家解放前开混堂的,老白的爹是有名的“老虎灶小开”。后来混堂改公私合营,再后来,小开讲了句怪话,被警惕性高的群众举报,押送西北劳教。老白跟营长申请,能否多洗几次澡。营长是个赣州老表,脾气火爆,左耳在朝鲜战争中失聪。营长说,就你们上海人娇气,穷讲究。不洗澡咋了,老子一个月洗不到一次澡,老婆也不嫌弃。
一天夜里,营长起床小解,迷迷糊糊正打算回去接着睡,猛地瞥见厨房有火光。
营长一个箭步冲进厨房,只见炉膛里柴火熊熊,上面架一口大锅。锅里还飘出歌声,是《铁道游击队》的插曲: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老白脱得一丝不挂,坐在大铁锅里,一边唱着歌一边擦身。好家伙,也不怕把自己煮熟了。
第二天清早,老白出列。“啪”一声,营长丢下一整条肥皂——给老子刷锅去,不把这块肥皂擦完不许停。奶奶的,全营这么多人,都吃你洗澡水不成?
农场边上是清华大学的五七干校,下放教师在此接受劳动再教育。秋收时,教授们割不来稻子,营长带他们前去支援。他挥动镰刀,一马当先割过去。两三个老先生在一旁端茶送水,递毛巾擦汗,一口一个“小将同志”——小将同志辛苦了,小将同志歇会吧,小将同志喝口茶。他听了心里难受,想到正在吃苦头的老头子。
一年半后,政策变化,加之血吸虫病泛滥,干校撤销。集体返回北京前,教师们宰杀了所有的猪和鸡,开了三天三夜的“百鸡宴”。耕地、宿舍、牲口圈、自建的砖瓦厂,包括所有农具,由军垦农场接管。这是后话。
他,老白,小猢狲,并排坐在大堤上,六条腿晃荡。旱季,湖水下落,露出大片滩涂。几只水鸟出没于芦苇丛,为这天地间的寂静增添几许生气。老白突然说,假如有一天离开这里,你们想做什么?他诧异道,不是说扎根一辈子吗?老白说,我说假如。小猢狲说,我要开一家大饭店,卖无锡酱排骨、南京盐水鸭、扬州狮子头、镇江水晶肴肉、宁波醉蟹、六月黄炒年糕……老白说,停,停,不要讲了,馋痨虫要勾出来了。他问老白,那你想做什么?老白说,听我表哥讲,香港有一种人,专门帮人打官司,口才好,收入高,每天西装笔挺——小猢狲抢着说,我晓得,就是绍兴师爷,写状纸的。老白笑,对,就是师爷。他望着湛蓝平静的湖水,怅然道,我无所谓的,只要能回上海,叫我做啥都情愿。
老白得了痢疾,一下午跑十几趟厕所,人快虚脱过去。老白刚病愈,他又染上打摆子,身上一阵冷一阵热,夜里高烧到抽搐。小猢狲借来一辆板车,跟老白一起,送他去场部卫生所。值班医生老朱,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一口慢条斯理的川普,主治跌打损伤,兼任农场兽医。老朱摸摸他额头,把了下脉,摊手说,卫生所很早就没有奎宁了。小猢狲说,那就等死吗?朱医生说,也未必噻,我这里有个偏方,你要不要听一下子。小猢狲说,啰嗦,赶紧讲。朱医生说,找个晴天——刚好,这两天就不错——正午日头下,寻九亩菜地,绕着走九圈。能走下来,病就会好。第二天气温直冲四十度,他摇摇晃晃走下来,大汗淋漓,一头栽倒在地。老白和小猢狲赶紧冲上去,又是掐人中,又是灌凉开水。他迷迷糊糊睁开眼,觉得自己像块烧透的木炭,正在一点一点地熄灭。卫生所里搭张床,每天供应一顿青菜肉丝烂糊面。亏得年轻,躺了一个多礼拜,居然慢慢康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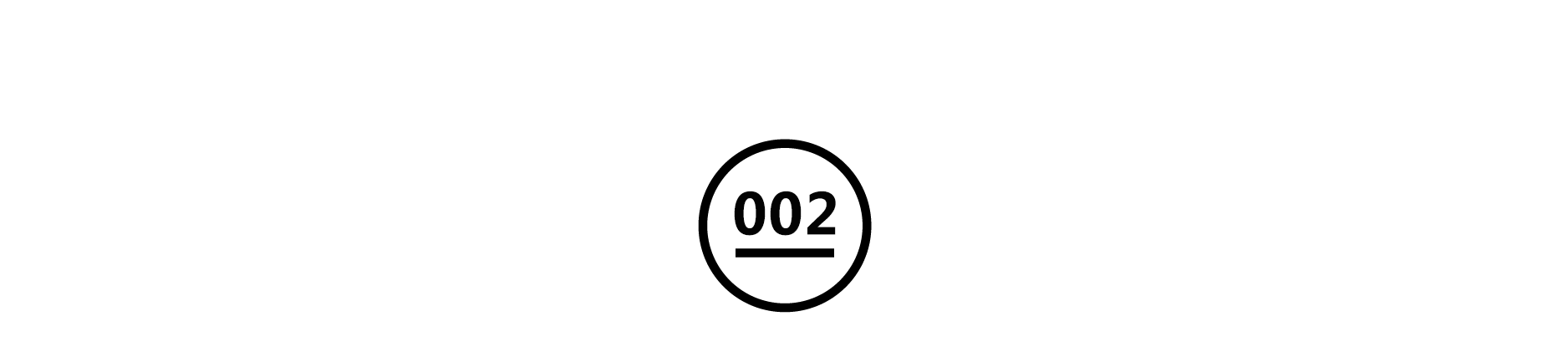
那年春节探亲,他给老头子买了两瓶四特酒,1块6一瓶,他记得很清楚。老娘吃香烟,那么带一条安源牌香烟。又去天子庙称了一斤金丝蜜枣,阿姐喜欢吃枣。给小弟不知道该买啥,想来想去,买了一挂炮仗。

《归来》剧照
列车于清晨抵达上海。地平线微微发红,车窗凝结着冬日的露珠。农田、工厂、新村飞速掠过,带着温暖的色调与旧日的气息。这是上海。他眼眶一热,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小弟一大早在月台等他,凭电报可以买站台票。车还没停稳,小弟已经冲到窗边,大声喊,阿哥,阿哥,行李给我。他和小弟一起把行李捆上自行车,自己去搭41路公交。太久没坐公交了,他一身绿色军棉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总觉得别扭。推开家门,小弟和阿姐已经在了。阿姐瘦了一大圈,皮肤黝黑,颧骨高高凸起。他叫了一声,阿姐。三个人都笑起来,仿佛分别只在昨天。阿姐给他下了碗面,加两个荷包蛋。下午,老头子和姆妈都回来了,姆妈一见他就哭。小弟赶紧迎上去,姆妈,做啥做啥……今朝要开心嘛。
阿姐带回花生和绿豆,他行李里有十斤大米和一桶菜籽油,都是外头要凭票供应的物什。小弟买来烤麸、素鸭和熏鱼。老娘炸了花生米,用午餐肉罐头做了个罗宋汤。老头子调了清色拉。一家人美美吃一顿,兄弟两个还跟老头子喝了点酒。晚饭后,小弟摆开行军床,招呼阿姐,阿姐来睏,我跟阿哥打地铺。半夜他醒来,耳旁是小弟的鼾声,脚边摆着两个痰盂。跟“广阔天地”比起来,家是如此逼仄狭窄,像个小小的避难所。他翻个身,又睡着了。
初七一过,阿姐就要回安徽了。阿姐愁眉不展,一天天数着日脚。终于到那一天,他和小弟去送阿姐,站台上,阿姐哭得接不上气。他搀起阿姐,心中惨然,晓得再过几天,自己一样要踏上这远去的列车。小弟抹眼泪,阿姐莫哭,阿姐莫哭。阿姐穷哭。
来农场的第四个夏天,接连下了一个月雨。半夜,一声尖锐哨响,全营紧急集合。暴雨如崩,大坝被洪水冲出一个缺口,随时有溃堤的危险。营长拎一瓶52度三花白酒,大吼一声,会游泳的,向前一步!他、老白、小猢狲齐刷刷往前跨。苏联制小学,游泳是必修课。十几个人的敢死队瞬间拉起来。 一人一口三花酒,凶,辣,烧喉咙。衣服一脱,闭着眼睛往下跳,水一下子没过胸口。洪水裹挟着泥沙,浑浊中蕴藏蛮力,像某种巨兽的血液,带着一股子腥味。敢死队员手挽手站成一排,搭成人链。拦不住洪水,但能挡一挡汹涌的浪头,为身后抢修的队伍赢得时间。装满鹅卵石的蒲草包一袋袋扔下去,填不满那张贪得无厌的嘴。一个浪打过来,他脚底一滑,趔趄了一下,手肘被老白紧紧箍住。雨水一刀刀砍下,逼得人睁不开眼睛。他努力望向远方,分不清天和水,只有大块浓重的黑暗。他想起金训华的故事。金训华是杨浦知青,插队到黑龙江逊克,为抢救两根电线杆被山洪卷走。连环画里,战友们流下悲痛骄傲的泪水。他忍不住想,要是我牺牲了,阿姐能调回上海吧。
天一直没亮。闷雷滚滚,自远方来。浪头一个接一个,无穷无尽。他迷迷糊糊,不知是梦是醒。只晓得,一旦松手,这辈子就此完结,尸骨无存。
九八年抗洪。女儿看见他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视新闻,肩膀一耸一耸。他们有救生衣,他们还有冲锋艇……他无声恸哭,我们有啥……屁都没有!

《归来》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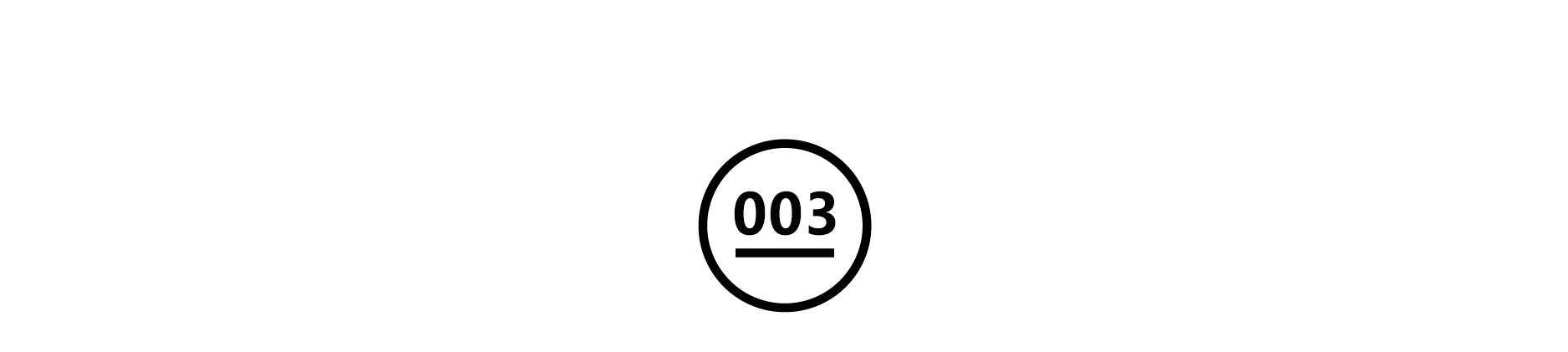
三十三岁那年,他动过一次手术。手术本身并不大,过量的麻药使他迟迟无法苏醒。妻子哭着喊他的名字,化为天边隐约的雷鸣。世界是一场大雨。他起身,行走在雨中。水没过脚踝,渐渐淹到膝盖,汇成一条地上的河流。许多事物漂浮起来。路边站着几个面目模糊的人,雨势太大,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也无法与之交谈。他终于醒来,病床边是妻子的泪眼。他感到无比的疲惫。后来他做过许多关于暴雨、河流和故人的梦。在梦里,时间流速加快,出现分叉和交错。而现实的时间较为黏稠,有咳嗽糖浆一样的质感。有时是逐渐醒来,现实一步步侵蚀梦境,最终吞吃干净。有时醒得很突然,像跌进更深一层的梦境。
老白和小猢狲来看他。老白刚回上海的时候,分配在里弄加工厂,业余时间读夜校。凭着自学的英语,通过几轮面试,进入外资单位,坐进玻璃办公室。小猢狲奔走南方,倒卖录像带和牛仔裤,后来盘下一间当街铺面,开起小饭店。上了点年纪后,见面都称胡老板,毕竟小猢狲尚显可爱,老猢狲就有点难听了。他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在报社当副刊编辑。工作之余,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小说,却从没发表过一篇作品。写了撕,撕了写。一道墙堵在面前,绕不过去。他承认,自己是个笨拙的小说作者,逻辑混乱,情节矛盾,只一味耽于想象,出于某种不可言说的原因,不得不写下去。
时间一长,同事们发现他有些神叨叨,时常自言自语,与空气对话。单位的年轻人背地里笑话他,当伊神经病。好在工作没出过差错。终于做到退休,他一声招呼没打,麻利收拾东西,悄然离开。
退休后,他把自己埋在书桌前。妻子拍他的肩,说,陪我去旅游嘛,喏,普吉岛四天三夜,蛮好的。他抬起头说,要么你跟女儿去,问佳佳啥时候能请假,我帮你们订旅行社。妻子嘟囔,就晓得,从来都是这个样子。他只好抱歉地笑。等我写完这部小说,他说,写好就陪你出去。

《归来》剧照
退休第九年,他失去了妻子。发现已经迟了,胰腺癌晚期。最后几个月,妻子基本失去意识,陷入无边无际的昏睡。监护病房没有窗,日光灯二十四小时亮着,隔绝了黑夜与白天。他习惯于坐在妻子身旁,监视器屏幕闪烁,替代妻子的表情。阿姐刚做完手术,小弟一家移民海外,倒是老白和胡老板来过几次。三人站在楼下小花园,沉默着抽一会烟。妻子去世,来不及悲痛,一大堆事汹涌而至,需要他立刻做出决定:寿衣款式、灵堂布置、出殡时间、医院结账、吊唁名单……他昏头昏脑,简直被一条龙的人牵着走。众人散去已是深夜,他对女儿说,你去睡吧,我来守着。女儿说,你年纪大,你去睡。他说,没事,一会老白和胡老板会来陪我。女儿不再说话,叹一口气,默默走回房间。
等妻子落葬,入土为安,他陷入巨大的空洞与悲伤。妻子的音容笑貌,温存或是拌嘴,洗发水的味道,连同在医院最后的记忆,一起消失。唯有相片前三柱香,昼夜不熄,成土成烟。他昏昏沉沉,作息紊乱,饿了煮点速冻水饺,困了就阖上眼睛。时常恍惚,不知身在何处。有一天,他忍不住跟老白和胡老板讲,想去鲤鱼洲。胡老板说,啥。他说,鲤鱼洲,军垦农场。老白点头,这么多年了,是该回去看一看。
到了约定的日子,他开车接上老白和胡老板。导航显示,全程八小时十七分钟。距离上次离开,正好五十年,宿命般精准。上高速,途经大江、田野、滩涂、丘陵,世界后退,三人讲讲笑笑。
黄昏,抵达鄱阳湖边。天气晴好,湖面是无边无际的灰蓝,巨大水体的一角。习惯了城市的拥挤逼仄,视线骤然释放,飘荡至远方。初夏,湖边树木茂盛,满目葱茏。当年开辟的十几万亩农田完全不见踪影,眼前是一大片湿地公园。几千人,仿佛集体做一场大梦。他们坐在堤岸边,脱了鞋,把脚伸进微凉的湖水。一个大浪打来,来不及躲闪,衣服湿透了。他一个冷战,突然清醒。环视左右,孑然一身。天色暗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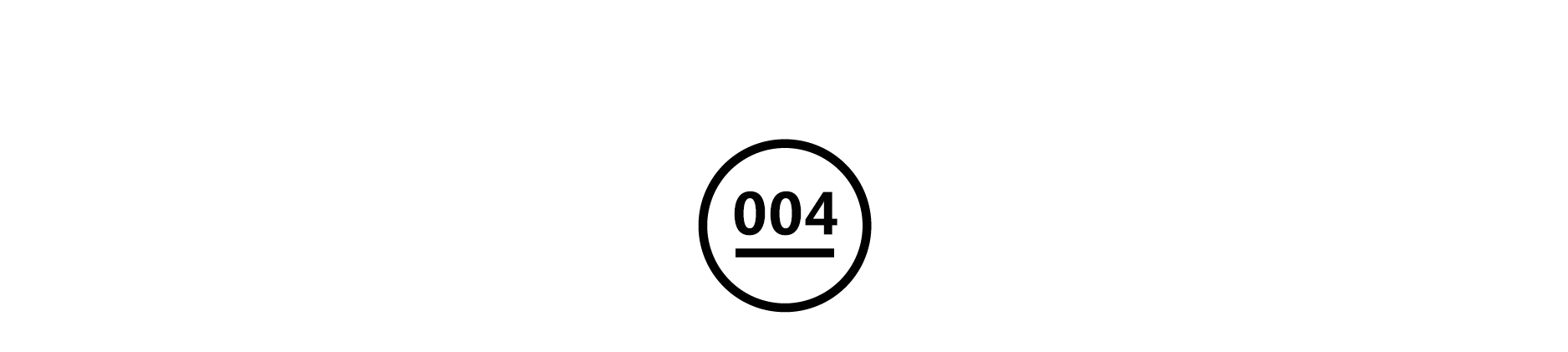
人链断了,三个人被洪水卷走。混乱中,他被救了上来。眼前一片模糊,只记得世界颠倒,大雨倾盆,手电筒光柱乱晃,有人大声叫卫生员。他苏醒过来,头顶是昏黄的灯泡,指导员坐在身边。他问,老白呢,小猢狲呢? 指导员沉痛地握住他的手,白同志是英雄,胡同志是英雄,金训华式的英雄,咱们营出英雄了。他不知所措地看着指导员。一道闪电劈下,他突然反应过来,英雄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喉咙一紧,一个浪头迎面打来,又晕了过去。
老白说,头伏个油麻,二伏个栗,三伏个绿豆好煮粥。小猢狲说,鳑鲏跳一跳,猫咪笑一笑。他问,你们干嘛去了,快到饭点了都。小猢狲嘻嘻一笑。老白突然说,糟了,没带衣服。小猢狲说,要什么衣服,你看,这里有一片鳞……
几日后,指导员找到他,希望他回忆一下英雄救人的具体经过。他摇头,不记得了,实在是不记得。指导员耐心启发,想想先烈们的光荣事迹,再想想胡同志和白同志,落水的那一刻,他们是怎样奋不顾身、舍己救人。他惶恐道,是要我编造吗?指导员笑了起来,帝修反那一套才叫编造,我们宣传英雄,用英雄的壮举激励广大群众,是革命的需要。指导员做一个手势,可以再深挖一下,比如两位英雄平时一贯要求进步,积极学习语录,心向红太阳。他站起来说,指导员,我,我做不到。指导员正色道,你不愿意出来讲,白同志和胡同志就可能评不上烈士,评不上烈士就没有抚恤金,他们不就白白牺牲了吗?你怎么跟人家爹妈交代?他僵住了。指导员表情缓和下来,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也是你表现的机会。我们每年有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到年底,上海的复旦大学,师范大学,都会来招生。指导员语重心长,你的表现一向很好,觉悟也很高,组织很器重你。这一次,希望你站稳立场,好好把握。
礼堂贴着大红标语——向白XX胡XX烈士学习!聚光灯雪亮,气氛肃穆而热烈。他一身军装,胸戴大红花,上前一步,深深鞠躬。忘了是第几场,台下坐满新兵,要么是新来的知青,或者当地中小学生,天真的崇拜的脸庞。他定了定神,开始汇报演讲。先从平常的一点一滴、一针一线讲起。穿插几件趣事,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洪水席卷而来。当讲到战友为了救他而献出年轻的生命,他的声音哽咽了。他再也讲不下去。他转过身,开始掩面哭泣。全场情绪达到最高潮。他就站在那里,被灯光灼烧,战栗着,等待迎接暴雨般的掌声。

《归来》剧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配图来自电影《归来》剧照)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远亲不如近邻”
- 央行最新例会:择机降准降息
- 金正恩会见绍伊古重申对俄支持

- 尚德机构:2024年净利润3.4亿元,同比减少46.6%
- 胡塞武装称袭击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及美航母多艘护航军舰

- 一位知名华裔男演员,主演电影《旺角黑夜》等,最近因为推出英语网课而爆火
- 《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的下一句是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