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柳向春︱读《陈乃乾日记》笔记三则
陈乃乾先生是书业耆旧,自早年即拥书阅市,日与旧籍为伍。见闻既广,眼光尤其独到,曾影印罕见文献多种。晚年则入中华书局,为古籍整理事业也是贡献攸多。对他的日记,我早就关注有年,但拜读之后,却也稍有遗憾。一则是晚年日记记录甚简,有用信息不很多。再则是因保存不善,1959年7月22日至1965年10月之前的日记因手稿褪色,未能整理行世。但虽然说是有遗憾,日记中还是有不少有趣的信息可供品味,今举其与上海博物馆所藏相关两则及其编辑《李慈铭读书记》一事,略为陈述,以为一脔之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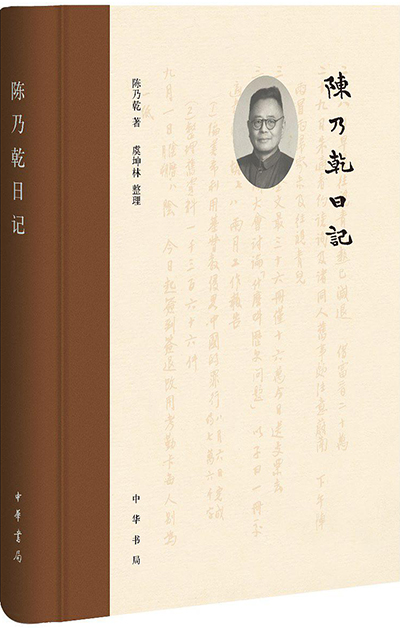
《嘉靖上海县志》
1929年12月5日《日记》(14页):“余所得嘉靖《上海县志》,为绝无仅有之孤本,昨日已见售于越然,惟尚未取去。今振铎必欲争得之,颇为难。”此书后来应该还是归于周氏言言斋,据1930年1月8日《日记》(20页):“以《上海志》送交越然,得二百元,聊以济急。”此书见录于《言言斋藏书目》卷二,著录云:“上海县志八卷,明郑洛书撰。明嘉靖三年刊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栏。前有嘉靖三年徐堦序及洛书序,又上海县境图、上海县市图各一叶。又目录。后有高企书后。收藏有‘曾为徐紫珊所藏’、‘汲古阁’、‘封城开国’、‘秀谷亭续藏书’、‘吴城字敦复’五印记。卷末旧面有徐紫珊手跋,附录于后:□庵农部修县志时,以未见此书为恨。余从嘉兴吴氏得之,为绝无仅有之本。渭仁记。”此书现藏上海博物馆,为1960年9月24日市文管会所拨交者。言言斋之藏目,未知编者是否周越然本人,其中“封城开国”一印,实际当作“彭城开国”,当係虞山钱氏之印记。上博于此书著录为四册,白棉纸。四册皆有水渍,第四册尤多。徐渭仁手跋页残破,首一字残。可见正是言言斋旧藏之物。再检两种《西谛书目》,均无《上海县志》。则当年西谛虽然“必欲争得之”,但却始终未能藏有上海志书。
陈乃乾曾经写过一篇《上海三志》,收在《海上书林》中(《陈乃乾文集》, 110-112页)。在这篇文章中,他写到:
《嘉靖上海县志》也同样只有一部流传在世上,正是汲古阁的旧物……乾隆初年(1736)是杭州吴氏瓶花斋收藏的,道光中上海徐渭仁在嘉兴买来,咸丰十年(1860)蒋敦复始据以参校嘉庆志异同,作《官司迁居表》等数卷。同治修志的时候,就根据蒋稿补入,却没有见到嘉靖志原书。
但在其《善本经眼录》(《陈乃乾文集》,413页)中,陈又认为:“‘汲古阁’(朱方,伪)”。事实上,此汲古阁印可能并不伪,此印的形制,又见于传世典籍多处,如万历间刻本《(万历)青阳县志》六卷,也钤“汲古阁”、“彭城开国”、“吴城字敦复”、“稽瑞楼”及“铁琴铜剑楼”等印记。而陈氏曾有多篇文章言及这部嘉靖志,都没有提到此印为伪作。实际上,毛氏汲古阁拥有多枚“汲古阁”印章,详勘其旧藏诸书,即可知晓。陈文说的蒋氏曾校阅此书,据今《同治上海县志·凡例》第七条:“咸丰十年,知县刘郇膏觅得郑志,延宝山蒋敦复与旧志参校异同,作《沿革表》、《官司选举表》、《宦绩人物传》若干卷……”现在上博所藏这部书中,还有签条三帧,想来就是敦复当时校阅所得。这位“海天三友”之一的宝山蒋敦复,与书中钤有印章的瓶花斋吴焯之长子吴城,名、字正好相同,也算是巧合之极了。
陈乃乾《上海三志》一文中还提到了这部志书的流传情况:“嘉靖、万历两志,我在二十年以前已经见到了。八一三事变的前几个月,上海正举行着盛大的文献展览会。当时我很想把这两部书介绍归市通志馆或博物馆储藏。但当时的代价要一千元,即等于一百二十担米的代价,使市通志馆和博物馆都没有方法可以应付。后来这两部书就离开了上海,转到青岛和北平。经过抗战的苦难以后,此书居然没有毁损,而且依旧投到了市通志馆的怀抱,这是一件值得喜悦的事。”这里他没有提及早在1927年他就曾将此书售给周越然之事,想来是因周氏后曾落水,所以不便言及。不过,陈氏与周其实交往甚密,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周越然的言言斋被毁,此书幸而无恙。陈乃乾遂将此书与《正德金山卫志》同时影印,以《松江府属旧志两种》为名行世。至1937年的上半年,这部嘉靖志再次流入市场。据陈氏此文所言,此书曾在辗转青岛、北平后,于陈氏撰文时的1946年7月,被上海通志馆收藏,后来转入上海文管委而拨交上博。但陈乃乾在《上海地方志综录》三《嘉靖上海县志》(《陈乃乾文集》,881页)中则又说:“原书卷前有毛、吴二家藏印及渭仁题记,咸丰以前流传之迹,班然可考。近百年间,则始终未出上海境外,但若隐若现,令人想望,是可异也。”所以,此书到底是否曾流出上海,现在并不能确定。
再据民国时所修《上海续县志》,其卷末存总纂姚文柟跋:“忆余弱龄,馆太平丈贾季超先生家,曾见案头有郑志,仅四薄本,惜当时未知注意。今先生之孙叔香闻余言,遍检家中旧籍,已不可得。”则这位贾氏收藏这部嘉靖志时,应该是在刘郇膏之后了。综而言之,此部嘉靖志的藏源流大概为:汲古阁毛氏-秀谷亭吴氏-春晖堂徐氏-刘郇膏-贾季超-陈乃乾-言言堂周氏-上海通志馆-上海文管会-上海博物馆。

《梅花喜神谱》
又1931年1月15日《日记》(31页)载:“晚至来青阁,知今日售去宋刻《梅花喜神谱》。”但此条甚为可疑。宋本《梅花喜神谱》传世只有一部,今藏上博。此书自光绪十二年由文登于昌进子彤侯售于吴县潘祖荫滂喜斋,再由潘祖荫弟祖年于1921年正月十三日灯节(2月20日),以独女静淑三十虚龄,转赠其女,归吴氏梅景书屋收藏,数十年间,一直未曾外传。以现在该书卷末题跋而论,在陈氏日记之前,头一年有陈曾寿观款:“庚午秋八月,蕲水陈曾寿观于梅影书屋。”下钤“陈印曾寿”白文小方印、“苍虬”朱文小长方印。在这段日记之后,有次年初吴湖帆自己的记载,据吴氏《丑簃日记》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四日:“赵万里来,观吾家《梅花喜神谱》及《淮海词》。”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宋本《梅花喜神谱》安然珍藏于吴湖帆府中,并无外流的可能。陈乃乾家学渊源,又自少阅市,且曾专门设肆售书,学识既丰,见闻又广,按道理是不可能看走眼的。那么,陈乃乾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录呢?
以我的浅见,日记此处可能是漏写一“仿”或“影”字,盖以陈乃乾的阅历,绝无将此书错认的可能。那么,如果仅仅是仿刻或者影刻,有必要特意在日记中郑重记录下来吗?在1928年,中华书局曾有一个《梅花喜神谱》的影印本,其卷末可见底本藏家高野侯之跋:
宋器之《梅花喜神谱》宋刻孤本,为述古秘籍,黄荛圃得之,珍如拱璧,题咏至再。又以袁寿阶影摹本付古倪园沈氏翻雕,由是著闻于世。咸丰中归斥山于氏,既为吴县潘氏所有,什袭而藏,遂不复觏。古倪园影摹本雕印绝精,红羊劫后,流传亦极尠,值兼金未易得也。比来藏家旧籍转鬻于肆,中有是谱,沈刻初印也,亟论值购之。
这一嘉庆十七年的刊本,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也有记载:“松江沈绮云所刻宋本《梅花喜神谱》颇为博雅君子所赏鉴。沈氏家本素封,有池亭园林之盛,改七芗尝居停其处,《谱》中梅花,皆其一手所临,印本今尚有之,……”黄裳认为,沈氏这一刊本,“为沈绮云倩黄荛圃用袁寿阶手摹宋本重刊,刻手精妙,然终未能与原书毫发悉合,版心题字亦各不同,影摹收藏图记亦有朱白文之异。然系此书重刊之第一本,初印用开花榜纸,墨色晶莹,由士礼居黄氏为之经营,遂成精本”。 虽然未能与原书“毫发悉合”,且为近代所刻,但此沈氏刻本流传甚罕,正如高氏所言:“红羊劫后,流传亦极尠,值兼金未易得也。”因此之故,陈乃乾日记中所言,很有可能,就是此本。
《越缦堂读书记》

李慈铭可谓是清末一大读书家,其所作《越缦堂日记》1920年影印出版之后,便被视作文献富矿,有多人曾从此试图窥见李氏读书要领。1921年,越缦弟子孙雄从这部日记中辑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至光绪十五年李氏所撰诗,编为《杏花香雪斋诗》十卷,由云龙也从此日记中辑出光绪元年至十年的越缦诗,编为《越缦堂诗续集》十卷。1927年,北平图书馆收得越缦堂遗书,由王重民予以整理,结合日记辑成《越缦堂读史札记》三十卷、《越缦堂文集》十三卷,由该馆铅印。又录有《越缦堂读书记》二卷,连载于《北京图书馆月刊》;《杏花香雪斋诗二集》十卷,未刊。除此之外,尚有缪荃孙、金梁等人或摘抄、或索引重编,都以此日记为学问掌故之大集。1959年,商务印书馆在由云龙早年所辑《越缦堂读书记》基础上,将其分类增编出版,1963年中华书局再加重印。现在常见的中华书局本、上海书店本及辽宁教育的《新万有文库》本,全是源出于此。再后来,又有王利器《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及《越缦堂读书简端记续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问世,虽然并非取材于日记,但观其书名,就知道也是受到了之前“读书记”的影响。但由氏所编仍有遗珠,故而,据傅璇琮《濡沫集?热中求冷》(京华出版社,2013年,64页)中说:“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能觉得需要一个助手,也或许看我刚被从大学贬出,得收收心,就叫我帮他做这一项事,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并再从李慈铭的日记中补辑旧编所漏收的部分。”虽然最终未曾成书,但也可见李慈铭日记之吸引力,虽数十年而仍不衰。
而《陈乃乾日记》中,还记录了当年另外两部《越缦堂读书记》之事,可见当时学人对这部日记之重视。据1931年1月15日《日记》(31页):“去年剪碎《越缦堂日记》弃置久矣,今始为之排比。”同月的20、21日、23日,则分别记录器编《越缦堂读书记》的“集部”、“经部”、“史部”之事。2月7日,又有(34页):“以《古学汇刊》本《越缦堂日记抄》加入所编《越缦堂读书记》中,竟日未出门。”7月15日(45页):“以所辑《越缦堂读书记》稿共九百卅七种售于富晋,得三百元。”从以上所引可知,陈乃乾于《读书记》一事,动意于1930年,而真正动手则在1931年,费时约半年。其所编《读书记》与由氏不同之处,就此处之简单描述,是直接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来编排。而在《新万有文库》本的整理前言中,按照四部来编排这一点是首先作为该版本特色与优点来说明的。可见,陈氏于书籍毕竟斵轮老手,出手便是正道。
再据1938年4月6日《日记》(71页):“从来青阁取得张见阳刻《饮水诗词》、朱梁任辑《越缦堂日记抄》。余昔年曾刺取《越缦堂日记》中读书之作,分类排比,成《读书记》二十卷,其稿为富晋书社取去,至今七载,迄未付印。今得亡友梁任之稿,与余乃不谋而合,惟未分四部耳。”6月20日《日记》又言(77页):“余尝辑李莼客日记中读书之作,为《越缦堂读书记》十二卷,以稿交富晋。忽忽十年,迄未付印。今见亡友朱梁任辑《越缦堂日记抄》五册,与余书大旨相同,惟余书依四部编次,朱则随原文校录,斯为异耳。日记中有数段拟倩人摘抄,录目备忘。”后又抄录十四种书目,则仍念念不忘,当为仍想补足旧作。朱梁任(1873-1932),名锡梁,号纬军,一字君仇,晚号夬膏。同盟会早期成员,南社发起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后回国鼓吹革命,曾任苏州《正大日报》社长、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江苏分会委员。1932年11月12日,朱梁任携子去甪直参加保护保圣寺罗汉塑像活动,不幸途中翻船,父子遇难。据陈氏此记,朱氏也曾摘录越缦日记中与读书相关部分,排比成书。其编排次序则当与由氏相同,也是随原文顺序,一一摘出。自陈乃乾当日所见至今,又已七八十年,陈、朱二人所辑,未知还尚在天壤之间否?读之令人念念不忘。
陈氏日记中可供钩沉之事尚多,于以正见日记、手札之类一次文献之价值,虽只言片语,如能结合其他材料,都可发掘佚事,考镜史实。即便偶有所误,也都有迹可循,非汗漫之谈者可比。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