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 +11129
游荡在美国:真实唐人街,定格在昨日|镜相

宰也街(摄影/丁海笑; 海报设计/白浪)
作者 | 丁海笑
编辑 | 吴筱慧
编者按:
惠特曼、菲茨杰拉德、伍迪·艾伦……一代又一代艺术家都曾为纽约这座炫目的城市心醉神迷。加缪在1947年还这样写道,“这么多个月过去了,我对纽约依然一无所知,我是置身在此地的疯子中间,还是世界上最理性的人中间……”
从曼哈顿唐人街到时代广场,从百老汇到布鲁克林大桥,本文作者丁海笑以背包客视角打量着纽约的过去与现在,或置身于嘈杂的地铁,或漫步于令人狼狈的雨中,不断审视一张张流动的面孔,同时试图记录下21世纪初的纽约图卷。
当通过流动的透镜看纽约,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海笑说,他在这里找寻到了安东尼·波登笔下那个流动、热烈、不羁的纽约。
(澎湃新闻·镜相工作室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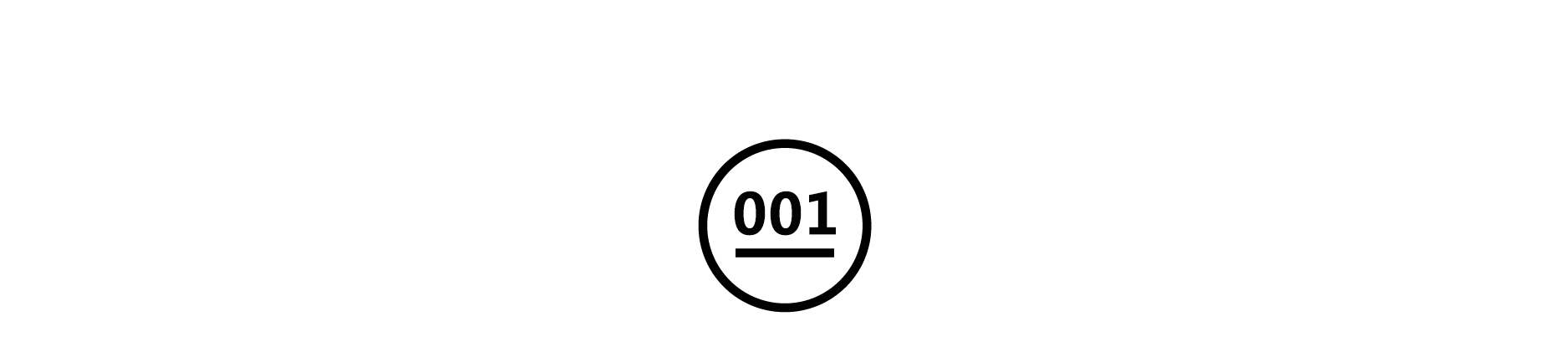
移民之殇
早在移民到来以前,曼哈顿的居民是岛上的美洲原住民。岛上过去遍布着山丘与河流,原住民对他们的岛屿倾注了很多名字,其中的一个就叫做“山丘之岛”。1626年5月24日,荷兰人从美洲原住民的手中买下了曼哈顿,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笔欺诈的交易,因为在原住民看来,没有人能够买走祖先之地。而持有另一种立场的学者则把它归咎于印第安人缺乏契约精神。随着城市人口增长,曼哈顿岛的山地与河流逐渐被填平。
曼哈顿拥有不同的移民社区,各族群像拼图一样地分布着,宛如树木的切面。下东区的唐人街(华埠)、小意大利、小德国是纽约最老的移民社区之一,也曾是犹太人的生活中心,数座犹太教堂就夹在中餐馆和杂货铺之间。
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我参加了菲尔的“下东区移民”City Walk。下东区是菲尔妻子的外祖父母生活过的地方,他们是波兰裔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来到纽约,当时的波兰尚在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几乎在一夜之间,纽约的樱花全开了,分散在各个公园与街道,映衬着新古典主义的建筑,让纽约忽然充满了生气。
City Walk从Rogers Partners大街的一座Loft公寓开始,这里离苏豪区不远,过去也是曼哈顿的纺织工厂,所有房间皆有着明亮的大橱窗,一楼用以展示,楼上是车间和仓库,曼哈顿的制造业逐渐外迁后,纺织工厂纷纷搬到了新泽西等地,廉价的厂房被艺术家租下来,改成艺廊和工作室——“艺术家喜欢落地窗”,也诞生了Loft这一住宅概念。随着房租的持续上涨,这些Loft后来又变成了咖啡馆、精品公寓和商业办公室。
下东区唐人街活像一块香港或者南洋的飞地,脸孔更多元化,却又更杂乱无序。时光仿佛在此停滞了,这里的华人活在过去,像是一块块活化石,不再富有朝气。街上所呈现的是好莱坞电影里的东方形象——一对阿公阿婆站在大街上用福建话唇枪舌剑,他们可能来自某个贫穷的闽北小镇,我同时想到外婆的家庭,也是这样吵个不休。
菲尔站在宰也街的中国戏院前面,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斧头帮的故事。宰也街被称为“血角”,这里曾是纽约最血腥的角落,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两拨华人帮派在这条街上相互仇杀。当年的故事已经成为半神话,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那些唐人街的传奇人物只留下了一串奇怪的拼音。

宰也街
老菲尔对唐人街知之甚少,且明显带着成见,但他却表现得自信十足,透着一股西方人的傲慢。他区别不出西边的老广东和东边的新福州,更不知道在皇后区还有一座更大的华埠——法拉盛,那里聚居着“新大陆人”。1930年后,后起的移民逐渐从下东区转移到皇后区,如今法拉盛的华埠已远远超过了曼哈顿的华埠,被称作新唐人街。
曼哈顿大桥穿过唐人街,路过时我想到年少时听过的一首老歌——张洪量的《情定日落桥》,标题中的“日落桥”正是眼前的这座。“游客们全都涌向布鲁克林大桥,而没有人来走曼哈顿大桥,这座吊桥通地铁,走在上面体验并不好,附近也比较乱。”菲尔说道。


曼哈顿唐人街
美国号称“种族熔炉”,这种族群的抗争与融合持续了上百年,时至今日也未能完成。无论是非洲人、爱尔兰人、犹太人,还是东欧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因为不同的理由来到纽约,过程中难免被驱逐、排挤,都有一段血泪史。美国一度颁布过排华法案,也同样地打压过爱尔兰人,历史总在重复,这在菲尔看来是一种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
曼哈顿唐人街的前身是一个被叫做“五点区”(Five Points)的贫民窟,电影《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讲的就是这里的爱尔兰移民故事。美国的爱尔兰裔人数众多,占到美国人口的约六分之一,爱尔兰节日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s Day)这一天整个美国都会变成绿色的海洋。“如今,美国的爱尔兰人比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还多。”
关于爱尔兰人远渡新大陆的原因众多,菲尔向我们提供了其中的一种:爱尔兰移民的历史可追溯至欧洲移民拓殖时期 ,大规模移民潮则始于1840年左右。当美洲的土豆作物传入爱尔兰岛之后,带来爱尔兰人口的爆炸式增长,1801年,爱尔兰被英国吞并,1845年,马铃薯青枯病席卷欧洲,在爱尔兰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或背井离乡。
“横渡大西洋至少需要两周时间,路上就会死很多人,这些去美国的船被称为‘棺材船’,甲板下面几乎都满载货物,为了赚钱,船主将船上塞满了人,只提供给他们勉强维生的食物。”
“最初来到美国的爱尔兰人大多没怎么受过教育,除了农业之外没有其他的生存技能,且大多是天主教徒……”这些爱尔兰人在美国饱受歧视,他们被冠以“野蛮”、“酗酒”、“罪犯”等标签而遭到排挤,只能做一些底层的体力工作。
小意大利与唐人街毗邻,它在19世纪末形成规模。早期的移民主要来自意大利南部,比如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在19世纪初期,一群意大利的年轻人来美国,等他们攒到足够的钱后,回到村庄接济他们的家人,村庄的人们会称呼他们为天使,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村庄将无法维系下去。随着年轻人长大、结婚,他们中的有些人决定留在纽约,于是我们奇迹般地有了‘小意大利’……”
“当意大利统一后,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爆发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在1880年至1924年期间出现意大利移民大潮……到了1924年,美国通过了《移民法令》,于是关闭了意大利、希腊和东欧移民的大门——我们定期就会这样做一次……”

小意大利
小意大利与唐人街一带曾存在一个庞大的犹太社区,美国是犹太人第二多的国度,而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生活在纽约。犹太人的社区遍布纽约各处,许多大厦的基石上就刻着希伯来文,一些地方还能见到星条旗和以色列的六芒星旗同时飘扬的场景。
前一个周末是犹太人的普珥节(Purim),我恰好路过布鲁克林的一处犹太社区,大街上灯火通明,犹太人盛装打扮,如同参加化装舞会。普珥节与犹太人反抗波斯帝国的屠犹计划有关,庆祝的方式是施舍与馈赠,因此许多小孩会扮成小丑来向过往的路人要钱。人们行色匆匆,步伐快得跟跑步似的,我仿佛来到耶路撒冷的某处街区。

犹太人的普珥节
一位德国姑娘对菲尔讲解的犹太历史尤为感兴趣,而且她的英文出奇的好,只有她能全程跟得上菲尔,菲尔虽是一位志愿者,但也可以随时转换成一名布道者,不经意间他已带着我们去了埃尔德里奇街犹太会堂、加尼那犹太教会堂和卡茨熟食店——电影《当哈利遇到莎莉》的取景地,现在是纽约最网红的餐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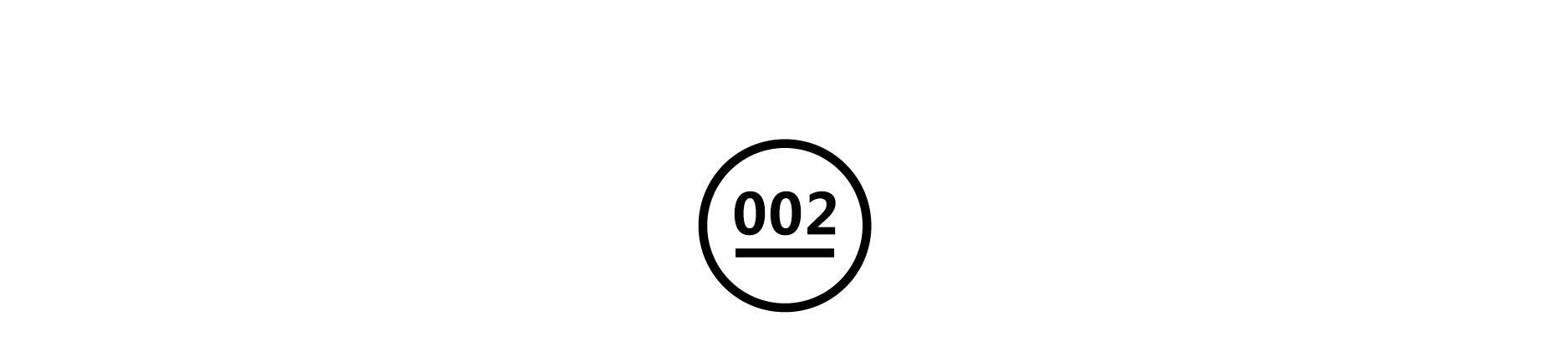
“你是哪里人?”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果园街的廉租公寓博物馆(Tenement Museum),这里被认为是美国移民故事的佐证,聚集了下东区最多的City walk旅行团。果园街97号建于1863年,这里曾居住过超过20个国家的数以千计的移民,果园街103号建于1888年,这里也陆续住过上万名移民,历史学家通过公寓里的一些日常物件与文件碎片,构建出百年间不同微小移民家庭的历史,他们是德国人、非洲人、爱尔兰人、俄国人、意大利人、波多黎各人、华人……
纽约在一位旅居英国的朋友眼中是:“伦敦翻版,只是少了几百年的历史。”纽约的历史不长但足够丰富,这里的历史学家着迷于微观历史的研究,大到一条街,小到一间餐馆甚至一座路桩都能成为研究课题。
曼哈顿下东区更像是美国梦的一条样板街,不同族群、宗教、语言、习俗的移民聚居于此,最终自发地形成一种共通的美国价值,听上去就很世界大同。但这种价值正在面临着自我瓦解,族群问题只是被街区化了,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平权运动在美国正走向极端。

下东区著名的犹太贝果店Russ & Daughters
近年来,身份政治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主党执政的纽约,“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愈演愈烈,非洲裔美国人一跃成为第一族群。就连“黑人”一词也变成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提法,正在逐渐地被改称为“非洲裔美国人”。
在大多数的美国博物馆,非洲裔美国人专柜通常会占据其最主要的位置,就连最倡导“艺术自由”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处处充斥着政治立场。2020年,古根海姆博物馆通过了一项纠正其体制内种族主义倾向的计划,到我去的时候,博物馆已经整改完毕,负责安保的雇员几乎全部被替换成了黑人,持续半年的主题展是一个叫做“Going Dark”(走向黑暗)的展览,除了一个面积不大的常驻展厅用以展出爱德华·马奈、保罗·高更、马列维奇、巴勃罗·毕加索等名家名作,其余大部分艺术展品均来自黑人艺术家。我在场馆里能明显地感受到逆向歧视,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公平感。

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黑人教堂虽然在名义上对不同族裔开放,但由于频发的黑人教堂遇袭案,教会成员对一切非我族类都充满警觉。我曾误闯过一间芝加哥的黑人教堂,保安将我拦在了门外,他嚼着口香糖,摆出一副嫌弃的表情,朝我扬了扬头,我会意地解释了一番,但直到我参观完道谢离开,他嘴里都没有吐出宝贵的一字。芝加哥有几家开在白人社区里的黑人酒吧,里面从雇员到顾客全是黑人,跟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酒吧不同,这里是将白人隔绝在外。
毋庸置疑,美国社会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而对亚裔的仇恨也在逐年加剧。亚裔美国人被视作“永远的外来者”(Forever Aliens),“外来者”一词在英文中本身就带有歧视属性,被定义在黑白种族关系之外。脱口秀演员Brian Kim是一位在纽约长大的韩裔美国人,他曾分享过每次当他路过时代广场的时候,总是会被人问道:“你是哪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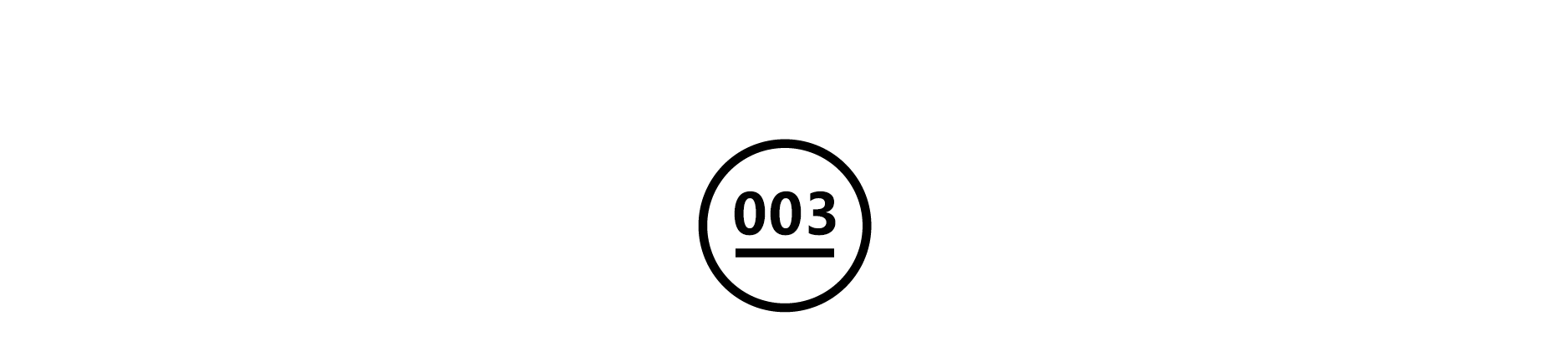
美国背包客
本世纪初的巅峰时期,全美共有136家国际旅舍(Hostelling International)——那也是菲尔们的“好老日”(Good old days),疫情加速了它的关店潮,现在仅存14家。菲尔们的志愿精神源自对全球背包客浪潮的缅怀,曾经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少不了美国背包客的身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青年越来越少地踏出国门,甚至在北美旅行也极少碰到背包旅行的美国年轻人,唯一一次是在火车上,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小伙子说他正在过间隔年,在一家医院里做义工,忙得根本没有时间旅行。
虽然有诸多原因导致Z世代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热衷于背包旅行,但经济压力绝对是主要原因之一。飞涨的物价让美国国内旅行的成本与日俱增——在芝加哥车站枢纽的Hudson News零售店买一瓶500毫升可乐税后要5美元(约合人民币36元),纽约青旅的一张12人间床位平季的价格是每晚74美元(约合人民币536元),旺季则不低于每晚100美元(约合人民币725元),这还是在享受非营利组织免税的基础上。
疫情之后,即便是像纽约国际旅舍这样一家异常火爆的青旅,仍然在勉强地经营着,甚至刚从倒闭危机里缓过来。旅舍的住客有一半来自中南美洲,他们到纽约的感觉就像是过来朝圣,我碰到一群哥伦比亚的青少年,十七八岁的年龄,个头都不太高,其中一位蓬蓬头的哥伦比亚少年在谈到纽约时情绪有些激动:“我不敢相信这里的人可以在夜晚出门,我多么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像这样……”虽然纽约的治安已经饱受诟病,但对于一位在哥伦比亚长大的孩子来说,从未感觉到如此安全,他说自己所在的家乡非常混乱,他甚至不敢在大白天一个人上街。
国际旅舍也有许多年过花甲的背包客,其中一位韩国老太已经80多岁了,称自己背包旅行了40年,去过两百多个国家。她佝偻着身子,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口齿也不太清晰,难以想象她是如何到达这里的。她对纽约的食物无比失望,跟我要了一些老干妈香菇油辣椒,吃完以后赞不绝口,一定要我告诉她在哪里才能买到。
在旅舍的欢迎派对上我认识了一位印度博主,叫做斯芬克斯,和开罗的狮身人面像同名,他与法老之间唯一的关联可能就是都剃了光头。斯芬克斯给人的印象是超级热情,且无比自信,他主动加了每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建了一个群,邀请大家第二天从布鲁克林大桥徒步去丹波,我其实已经去过一趟大桥了,但没有走到丹波,于是就跟着一块去了。

丹波和布鲁克林大桥
人都是斯芬克斯组织的,只招到了清一色的男性,斯芬克斯对自己的目的也不避讳,就是让大家为他的Instagram新拍一组照。从旅舍出发之后,印度人便自动进入了指挥官的角色,不仅路线得听他安排,就连大小便也得统一行动——“上桥之前,我得保证所有人都上完了厕所。”
美国的公共厕所极少,游客找厕所颇为麻烦,你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餐饮店的最里面,期望那里没有密码锁或者由柜台遥控的开关,也得同时提防没有保安过来把你赶走。斯芬克斯有一种找厕所的嗅觉,他总能通过自己的同胞打听到附近的厕所,再佯装那里的顾客或者附近的邻居,从服务员那里套到厕所的密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被安排轮流进入一家小店,上完出来后跟每个人击掌庆祝,脸上挂着一副做坏事的表情。
斯芬克斯四十岁左右,在他身上有着部分上个时代背包客的气质。他一边出差一边旅行,去过不少地方,也来过两次纽约,留下了他的光头与世界各国地标的合影,效果就像AI生成的一样。他喜欢三不五时地提到中国,也习惯在气势上压一压我,譬如他会向所有人科普:“印度人口在去年已经超越了中国。”他还强烈安利中国的一加手机,并称它的拍照功能无与伦比:“在印度,有一半人用中国手机,另一半人用其他手机。”可惜在纽约,没有人会关心龙象之争。
我想在丹波看日落,斯芬克斯却一直催促着我们赶路,我刚架好机位,他便从远处朝我扬手,头也同步地朝外昂,意思是快跟上,我只能示意让他先走,他又朝我昂了昂头,表示会意。
“你在哪?怎么回事?”第二天一大早,斯芬克斯就追着问我照片,睡眼惺忪的我火气正大,说我正在出门,我不得不爬起来往外走,没想到又在电梯撞见他,他抓着我索要照片,语气像是我的老板。
日本的谅子也是我在欢迎派对上认识的,旅舍的东亚面孔很少,她一进来就找我说话。她在加州的一所大学里做交换生,研究的是国际关系,我们聊得不错,感觉有挺多的共同话题。她在后来的Pub Tour中不辞而别,被热情好胜的丹麦小伙拉森叫走了,走之前她留了我的联系方式,推荐我一定要去联合国总部看一看。
在纽约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我拼命地按着快门,想记录下21世纪初纽约的图卷,怕它会转瞬即逝。我改签了车票,决定在纽约多待几日,继续辗转于不同的线路,往返在曼哈顿与布鲁克林,有时也尽享欢乐,却很难交到朋友,所幸在纽约根本不需要朋友,有太多可以忙的事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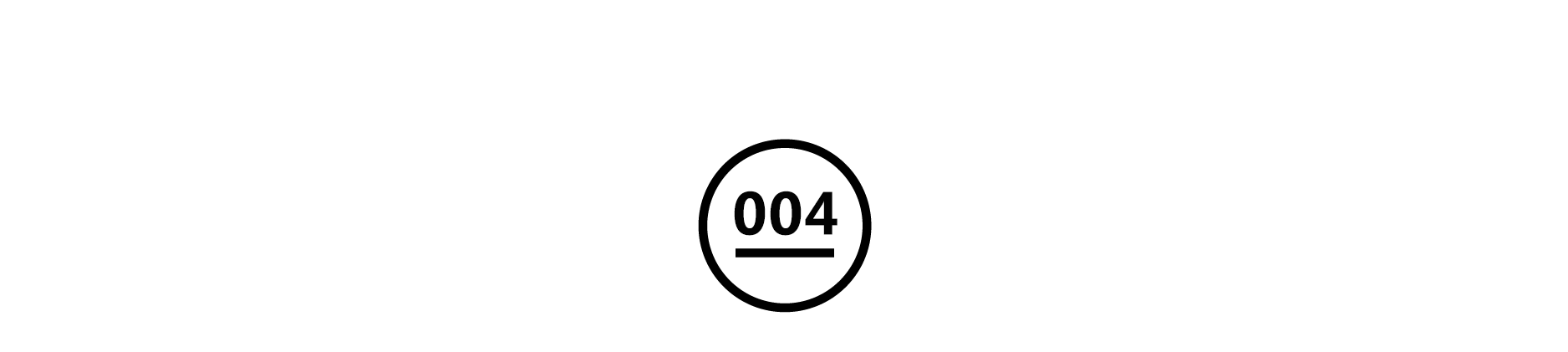
纽约的一个雨天
那天清晨从BASEMENT回到曼哈顿,通宵未眠,想接着再去“哈林区City Walk”,无奈在床上睡着了,眯了有两三个小时,收到了谅子的信息:“其实我今晚要走了,如果我们能再见的话,我会很开心。我为那天的突然离开感到抱歉,如果你今天有空的话,给我联系,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见。”日本人总是很客气。
谅子在中午有个佛教讨论会,我正好想去凑个热闹,结束后已是下午三点,我提议去古根海姆博物馆逛逛,今天是免费开放夜,而谅子对看展有些兴致索然,她说最后一天了,还没尝过纽约的精酿啤酒呢。
美国是精酿啤酒文化的一大发源地,仅在纽约就有300多个啤酒厂牌,我从西海岸一路喝到东海岸,品尝过无数的精酿啤酒厂,逐一记录下不同地方的小气候、口感及精酿文化差异。从下午就开始喝酒,这个计划听上去很疯狂,但当我们到了布鲁克林才发现,纵然外面大雨滂沱,各个啤酒屋都已经座无虚席了。
一路上雨下得很大,雨水冲刷着这座老旧的城市,让我想起罗马大雨中那只被冲掉的鞋子。纽约一半是雨天,一半是晴天,纽约的天气带火了伍迪艾伦的《纽约的一个雨天》,成为来纽约必看的城市漫游指南,因为总会碰上一两次下雨嘛。雨越来越大,鞋子完全湿透了,我俩像是踩在水塘中跳舞。

纽约的下雨天
EBBS啤酒屋是我挑的,据说是布鲁克林最火的精酿啤酒屋之一,啤酒屋的一面墙上挂着“布鲁克林第一IPA”的张贴,沽酒客挤满了整座空间,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氛围很燃,音乐越大声,人们彼此说话就越热络,吧员也手忙脚乱的,我们要了IPA和皮尔森,找了个靠墙的角落碰杯。
啤酒是美式文化的代表之一,酒吧、啤酒与男人的画面被反复地投影在电影银幕上,这种黄金液体也随着好莱坞文化的扩张而走向全球。我到美国还是第一次尝试在白天喝酒,但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又破了记录,从一大早就开始跟人干威士忌。
第二家啤酒屋我让谅子来选,她挑了布鲁克林啤酒厂——纽约精酿的鼻祖之一,历史悠久。当我们走出EBBS,雨逐渐变小了。“如果不喜欢纽约的天气,只需要等一等,没多久就会变天了。”我想起了老菲尔的话。布鲁克林啤酒厂离东河不远,河畔的风很大,雨伞不断地被吹歪,我们在几个街区之间差点迷路。
布鲁克林啤酒厂已成为纽约旅游通票的一处景点,这里的精酿啤酒中规中矩,唯一有意思的是角落里有一台可以玩任天堂游戏的街机。我们接着去了Other Half——同样号称“布鲁克林最佳”,里面正在举办婚礼,把整个啤酒屋都包了下来,我们只好去下一家叫做Talea的酒馆。
路过一家贝果店时,我买了一个烟熏三文鱼贝果,贝果被称为纽约人的早餐,最初也是由犹太人传入纽约的。一个橱窗边的白人男子对我们说了些亚裔歧视的用语,谅子在我们走出贝果店后才告诉我,我原本有些愤慨,但转念一想,也许这就是美国旅途之始朋友所说的“扔掉滤镜”吧。
布鲁克林已逐渐沦为了中产社区,随着房租上涨,属于布鲁克林风、亚文化的酒吧也在不断外移,许多已经从威廉斯堡搬到了布什维克——布鲁克林与皇后区的交界处,那里多了些老布鲁克林的气息,少了通货膨胀的网红店、板着脸的服务员和一些装腔作势的文青。我们从威廉斯堡一路喝到了布什维克,体验不同“地层”的精酿工坊,几乎覆盖了整个纽约精酿史。
谅子的故乡是北海道的札幌,札幌最有名的物产就是“札幌啤酒”(SAPPORO),许多外国人可能不知道札幌市,但几乎都听过“札幌啤酒”。 在札幌人人喝酒,谅子说她从来不知道喝醉是什么感觉。十几年前在亚美尼亚,我碰到过一个环球旅行的札幌人,她当时在伦敦大学念历史地理学博士,每到一处,就会喝掉当地所有品牌的啤酒,看得出她是真的爱喝酒,民宿的冰箱里装满了她买的酒,每天不喝一口就睡不着觉。
最后我们去了布什维克附近的一家古董酒吧,是我在去BASEMENT的路上无意间发现的,这里的消费便宜到不像是在纽约,只收现金,没有小费。酒吧仿佛是美剧《瑞克和莫蒂》的外星人狂欢派对,全是穿着“奇装异服”的皇后区怪人,有来自中世纪的巫师,有高更的大溪地少女,还有把自己装扮成动物的人。这里的舞曲更加自由无国界,是酒吧,也是跳蚤市场、占卜摊……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皇后区是美国本土族裔最多元的地区,古董酒吧的宾客几乎都是外来者,来自阿根廷、黎巴嫩或者某个加勒比海上的小岛,有的人可能才刚蹲完移民监(用来比喻等待获得美国身份的过程)出来,我却在这里找寻到了安东尼·波登笔下那个流动、热烈、不羁的纽约。我们是里面唯一的东亚面孔,他们见到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在一群没有故乡的人中间彼此取暖。
凌晨两点,我们踏上了地铁L线,夜班车要统一绕到百老汇交汇车站,再从那里换乘A线回曼哈顿,刚好路过高街车站,谅子说没去过布鲁克林大桥,于是我们即兴地决定跳下车,往大桥方向走去。路上要穿过一些黑布隆冬的隧道和公园,一个行人都没有,路边的樱花却在黑暗中开了,预示着纽约的春天已提前到来。
当我第二次来到布鲁克林大桥公园,眼前是曼哈顿的璀璨夜景,身后是简的旋转木马,空无一人的置景让人产生了不真实感,像坠入19世纪的巴黎。曼哈顿所有的大楼都在夜空中点亮了,谅子问我:“难道纽约人也像东京人那样通宵工作吗?”后来我问了菲尔,他比我更熟悉大楼的事情:“那些不是在写字楼上班的人,因为清洁和维修工作只能在晚上进行,工人会把每层楼的灯都打开,走的时候无意或者故意留灯,这样做一点都不环保。”

布鲁克林大桥公园

布鲁克林大桥公园简的旋转木马
“我从没想过我会有机会来到美国。”谅子感叹道。她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母的工作一直不稳定,从出生后便不停地搬家,从最西边的九州到最东边的北海道,搬过十几次家。因为工作压力,谅子的父亲患上了抑郁症,开始沉迷于一些旁门外道,整个家庭后来一直在靠母亲支撑着。“我都不知道我的父亲现在在哪……”谅子的语气里透露着绝望的悲伤。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经历了失落的三十年,疫情之后,日本经济的衰退加剧,跌出了全球第三的座次。日元的贬值使得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赴海外就业,在加拿大旅行时,我碰到了大量日籍的外劳,在当地做司机、厨师甚至保洁工作,这是我过去十几年旅行中极少碰到过的事情。
谅子在凌晨四点过打车去机场,飞往洛杉矶。我又在纽约晃荡了几日,坐跨夜的火车前往印第安纳的布鲁明顿,见了一对十年未见的老友,我们从早上就开始喝酒,在森林里燃起篝火,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仿佛昨日重现。原来最后只有我在流浪,他们从未散落天涯。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无缝衔接上帆时间
- 廊坊4.2级地震,京津冀有震感
- 一批房产类“自媒体”被禁言

- 有色金属板块活跃,合金投资涨停
- 陈亦伦、李震宇领衔,它石智航完成1.2亿美元国内具身智能最大天使轮融资

-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是
- 敦煌莫高窟的主要艺术形式是雕塑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