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和文凯:为什么现代财政国家制度没有在近代中国出现?
2024年5月30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于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共同举行题为“深度比较历史分析的贡献与局限——《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的读书会。会议由《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一书的作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和文凯作引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长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杜宣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策、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崔金柱进行评议。限于篇幅,本次读书会文字稿分三篇呈现,本文为和文凯教授所作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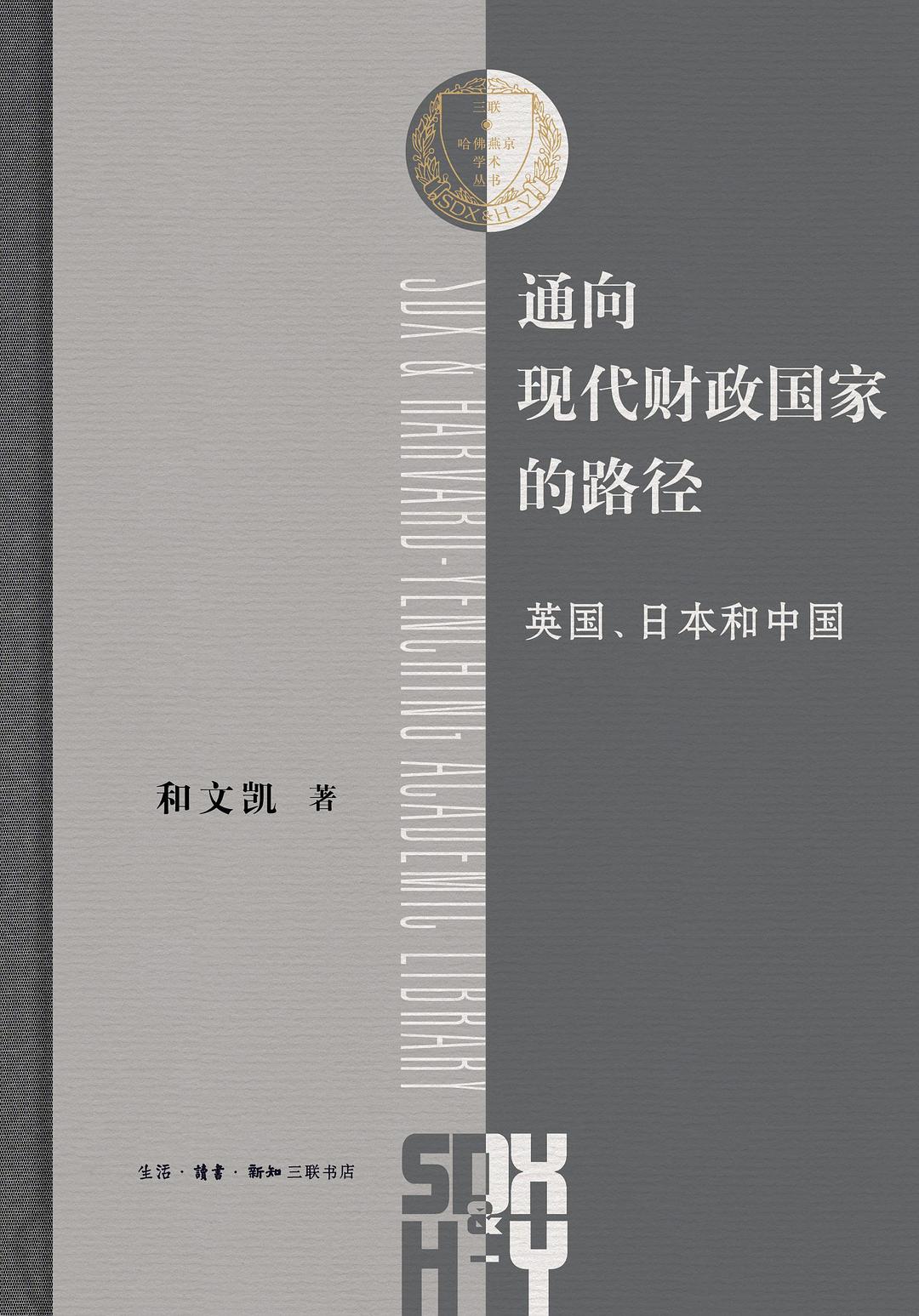
《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英国、日本和中国》,和文凯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2月出版
这本书的研究是要回应社会科学的若干议题,特别是关于制度的形成、建设及巩固。这在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包括制度主义)中都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做研究不能拿制度的功能去反推制度的产生过程。当然,这种功能主义的做法已经被现在学界逐渐所摒弃。制度的产生及演变,实际上涉及历史过程的问题。如果简化处理历史进程,我觉得是对历史研究的不尊重。但是如何将历史学的研究尽可能地带到制度形成与制度发展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脉络中,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类研究最大的一个挑战便是——既能让历史学家满足,也能使社会科学家接受。
从源头来说,我最早关心的是晚清财政金融的问题。学习晚清财政金融的时候总会想,它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对清代财政制度的很多研究,带着很强的事后视角,特别是从甲午战败往回看,这实际上脱离了特定的历史情境。其实,许多批评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是不成立的。如果要真正地理解晚清的财政制度运作及其特点,比较的角度将会提供一些新的发现。
最早的一批理论文献会强调英国有地方乡绅的自治传统,地方自治体有向王室政府谈判的能力,通过交税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利,进而有强化国家能力的结果。这是社会科学里比较经典的解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财政制度,明显存在一个过于中央集权的问题。地方势力或地方的代议权难以进入中央财政的运作过程,因此,中央财政的运作具有很强的专制性,这进而又会影响到国家能力的提升。就像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言,国家看似强大,实则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非常薄弱。我之前一直是在这一框架下去理解清朝及其财政制度。另外,将清代跟日本去做比较,既有的很多文献会强调日本明治政府的主动性及能动性,即日本能够将非常崭新的现代化的措施强力地施加至社会,实现社会经济的转变。相较而言,清代国家好似就缺乏这样的能力。
然而,后来在读英国财政史的过程中,读到了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的《权力的支柱》,当时对我的震撼非常大。布鲁尔认为英国政府财税的主体并不是地方乡绅控制,甚至也不是来自一些大的金融家和贸易商,18世纪英国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来源,是从普通消费者征收的消费税,比例超过40%-50%。其中最重要的是啤酒税,大概占政府年收入的20%-30%,具有相当高的比例。在整个征收啤酒税的过程中,国家靠的不是地方士绅的合作,而是中央政府自身建立的高度官僚化的征税机构。这部著作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我们可能低估了英国官僚制度所发挥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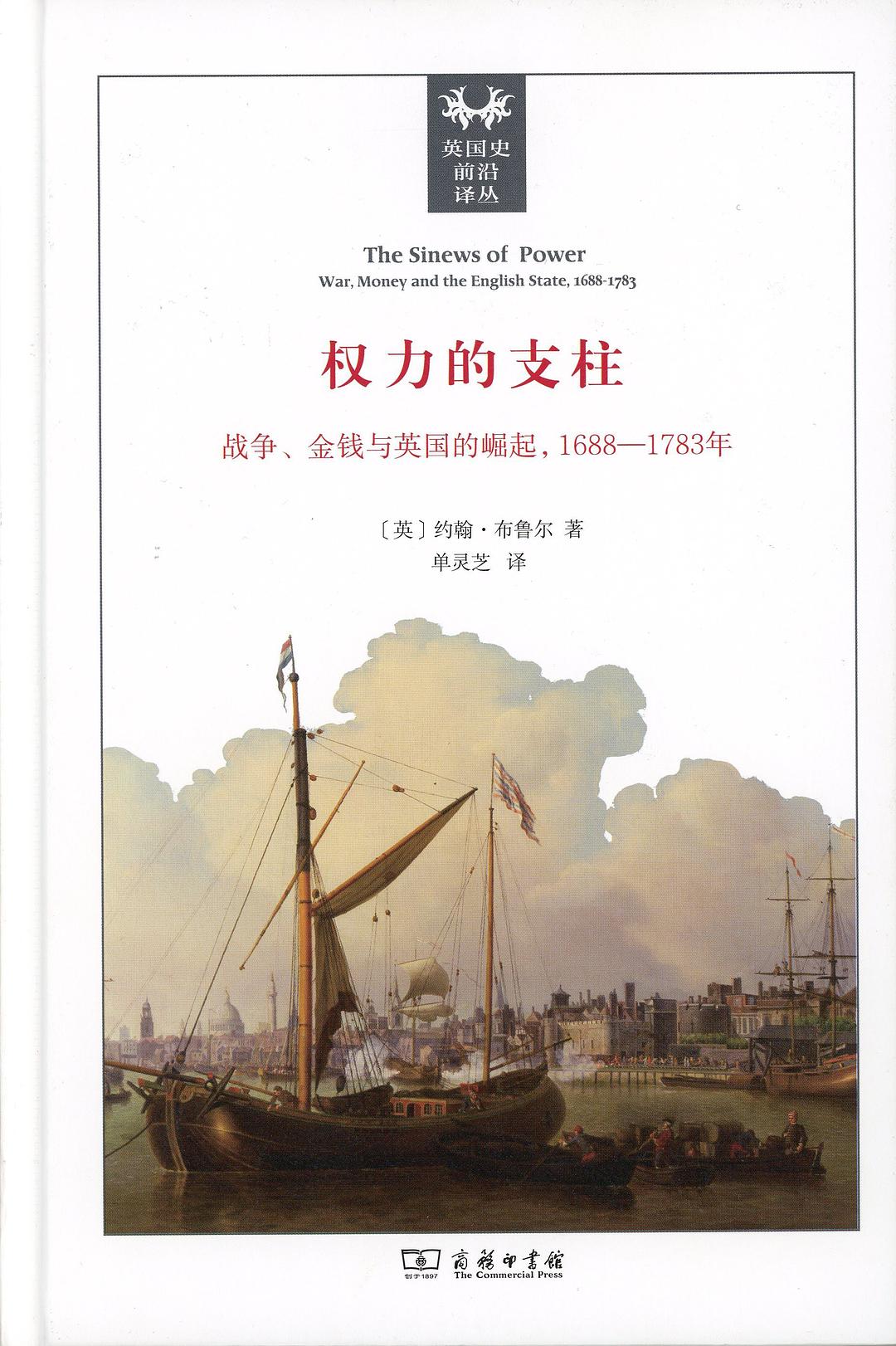
《权力的支柱:战争、金钱与英国的崛起,1688—1783年》,约翰·布鲁尔著,单灵芝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4月出版
上述思路还有一些新启发,即土地税并非最重要的税种,消费税或厘金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之前研究清代财政制度,包括研究晚清和民国财政的变革,重点都放在土地税,基本都是用国家政权缺乏社会渗透能力来解释晚清国家能力的薄弱。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路,重点不放在土地税,而是放在增收更具弹性的消费税,再用比较的视野来审视厘金,那么就会得出不同于传统史学的解释。厘金本质上是一种消费税,英国和日本主要是在酒类生产的场地征收,虽然中国缺乏类似生产规模的大众消费品,但在大宗物品的运输途中,有很多难以躲避的关卡要道。在这类交通要道处去征收厘金税,其性质与英国和日本是一致的。
即便如此,单单从财政收入来理解国家能力,亦不足够解释晚清的财政困境,因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家怎样使用这种财政收入。如果把中央集中管理的财政收入作为一种资本,参与金融市场,调动长期性的金融资源,那么对当下的国家支付能力将有极大的提升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比较视角。日本通过国内发行长期公债的方式,把未来20年到30年的税收用到了1894年之前海军、陆军的军备扩张。而且,日本铁路的修建主要也是依靠民间债券和中央政府发行的铁路公债。相较而言,晚清中国缺失这一层面,无论是新式海军的建设,还是铁路的修建,仍然依靠的是每年非常有限的财政盈余。这就显示出日本和晚清国家能力的巨大差距。
我这本书主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财政国家制度在英国和日本出现,而没有在中国出现?我没想用“失败”一词来描述清代的财政金融制度,而只说它没有建成现代财政国家的制度,但后来许多解读将其理解为“失败”,实则将我的观点极端化了。像英国和日本这样长期的公债制度,是靠间接税来做信用担保,这样的制度有没有可能在清代出现?其实这一问题可从两个层次来讲。第一是在政治制度层面,即清代的执政者和官员是否会接受这样的制度?第二是清代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能否支撑一种完全靠间接税为担保而发行的国家的长期公债。
本书借鉴了众多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当时商品经济的规模,足以支持以间接的消费税为主导的制度。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即便地方有很多隐瞒的陋规收入,但是中央层面控制的税收额每年有八千万两,如果只用关税和间接消费税,也就是厘金,也能有三千到四千万两。如果是用这一规模的财政收入来调动长期国债,那么清代的整个财政运作及国家能力,包括铁路与军备的现代化局面,都会为之一变。因此,如果有这一制度,清代的官员应该会很欢迎,那么这么好的制度为何不去建设呢?回答这一问题,就不能拿事后对制度的理解去回推制度的建设,而是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从历史人物的立场去讨论制度的走向。
我在对英国和日本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之后发现,这一制度产生的初期,甚至到中期阶段,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这种长期国债是可行的,反而出现了诸多反对意见,像日本的政治保守派对很多西化财政政策持有非常严厉的批判态度。有趣的是,在如此情形下,英国和日本为何依旧会朝这一方向努力呢?结合当时历史情境和具体历史人物的分析,我们才能够厘清现代财政国家形成的机制和动力。这个动力不是我们从外部强加给历史人物的,也不是事后为历史人物做理性假设所提供的,而是这些历史人物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下时刻面对的压力。我将当时这些国家面临到的财政困境和财政压力称之为“信用危机”。“财政危机”主要是指入不敷出;与之不同,“信用危机”主要是指国家在超额发行的信贷工具之后,如何去维护其商业信用的问题。
从英格兰来看,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巨额的短期债务,使得国家难以承受如此重负。问题的解决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将债务转变为较低利息的长期性国债,国家承担的负担将会减轻很多;另一个是让英格兰银行把这些国债转化为资本,相应而言,作为交换条件,国家则需要赋予英格兰银行发行银行券的垄断权。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推翻幕府的军事行动中,既缺乏军费又没有财政基础的明治政府,在新政权建立的前三年,大量发行不兑换的纸钞来应对财政支出。这些不兑换的纸钞最后又被国家强加到整个社会上,变成在全国流通的纸币。纸币的可兑换性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它不单是政治信用的问题,也是经济信用的问题。英国和日本在解决信用危机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财政制度的中央集权化进程。
这部分我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以契约理论的包税制、分税制、官僚制等概念来解释英国消费税制度与明治时期日本财政制度的诞生。我认为,如果缺乏这一压力,制度难以走上这一特定的发展方向。按此来说,晚清没有走上现代财政国家路径,有其合理性。因为在甲午战争之前,晚清的财政运作其实有成功之处,它解决了很多内忧外患的问题。这些成功使得晚清缺乏建立新型财政金融制度的迫切性需求,特别是通过发行长期公债来解决问题的需求。因此,本书的解释框架指出,正是缺乏“信用危机”,制度建设才失去了向特定方向持续发展的动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这一惰性简单地视为清朝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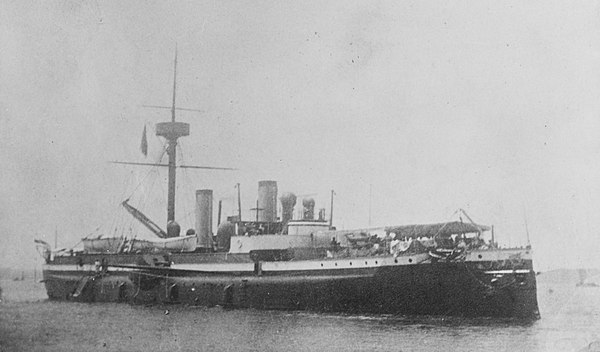
来远舰
研究清朝的财政制度,要特别谈到地方(督抚)和中央的关系,比如到底有多少收入是被督抚瞒报的。回到档案会发现,其实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是相当强大的,像之前刘广京教授和何汉威教授的研究也都指出,中央政府具有非常强的政治和财政控制能力。通过历史档案来考察晚清的财政运作,我发现有趣的一点是,在分散管理的财政制度下,督抚的财政运作主要靠户部的指拨,但是在户部指拨本身缺乏清晰数字支持的情况下,督抚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各个款项之间的挪移,来处理中央指拨的紧急任务,比如偿还外债、军费支出、购买军舰等。这些属于紧急款项,无论如何都要去完成。在许多重大的民生工程上,比方说黄河决口之后的维修经费,督抚也尽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来满足户部指拨的需求。但是在非紧急款项的指拨方面,地方上则是能拖就拖,或者象征性拨解部分的经费,或者干脆视为具文,比如督抚应付户部和海军衙门指拨给北洋海军的日常经费便是如此情形。
可见,这一财政制度确实有相当大的惰性,一方面能处理许多面临的急迫问题,另一方面在非急迫的问题上,财政拖欠也不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谈清代的财政制度运作惰性。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清代当时的金融制度发展规模,到底能不能支撑现代财政国家制度建设。我用甲午赔款的赔款方式,来推断这一反事实的假说。清朝通过向英国、俄国、德国和法国的银行借债的方式,来偿还日本索取的赔款,需要在确定的时间将每年的债息送到江海关,如果清政府当时缺乏强大的行政能力令督抚将这笔钱按时送到江海关,那么它连借债的利息都承受不了。但在档案里看到的情况是,每年近95%的费用都能按时送抵。这说明了清政府其实有这个能力来发行长期公债,只不过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没有紧急事件迫使其往长期国债的路径去走。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时中国的民间投资人、商人到底有没有购买国债的欲望和能力?或者说,他们对国债到底有没有信任感?我在书中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稍微粗放了一些,如果只是从假设的角度来说,如果清政府每年按时支付债息,投资国债的人是受益的,清政府本身从国债的收入里也会获益很多。从这个角度讲,清政府没有任何违背信用关系的动力。同样的情况,如果看英国和日本,在国债发行的初期信用也是不稳定的,一直要到它们能够做到以稳定的税收来支撑不断增长的国债之后。因此,在我看来,民间商人对清政府的信任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总的来说,这个比较研究的框架涉及许多国别史的问题,我个人已经是尽己所能,收集和运用了很多一手的档案资料,特别是在日本史和中国史部分,英国部分主要借鉴英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现在回过头去看,英国部分还可以做得更细致一些,当时应该花个半年时间到英国去做一些档案研究,这样一来,可能这本书的论证会更严密些。今天有国别史的三位专家在,我非常希望听到从他们的角度来评析这种历史个案分析的解释框架、本研究的不足与可以继续精进的地方。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