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沙龙︱女性、食物、海与鱼:柳田国男笔下的日本民俗
2018年12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北京大学日语系副教授王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日语系讲师史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岳永逸在三联韬奋书店举办《柳田国男文集》沙龙——“用心感受,每个人都是生活里的民俗学家”,谈谈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和新近出版的《柳田国男文集》。
王京是《柳田国男文集》的主编,也是文集中《食物与心脏》一书的译者,史歌是《海上之路》一书的译者,岳永逸则专长于民俗学,沙龙主持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宋旭景,她是这套书的策划编辑。

生活里的民俗世界
主持人:我们这次沙龙的题目叫“用心感受,每个人都是生活里的民俗学家”,我把它发到朋友圈的时候,就有人评论说,其实可以改为“每个民俗学家都是生活里的人”。柳田先生的书中所有叙述的内容,都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不会注意到的事情入手,比如说家里的灰尘,比如说大家吃的食物,包括像我穿的棉质的衣服。柳田有一本书叫《木棉以前》,他会跟你讲在棉花诞生之前大家穿什么?为什么现在着装会有这样的变化?接下来几位老师可以详细聊一聊书里具体的故事。
王京老师翻译的《食物与心脏》里有很多关于节日或者叫民俗性的东西,其中有一些也发生在我的生活里,比如“送膳”。小时候我的舅舅或舅妈大概在麦子要熟的时候会来城里给我家送吃的,其中有一样是油条,每年这时候我妈就会说,她(指舅妈)是来“送膳儿”的。其实我不懂是什么,但是我看了这本书,我想到这件事,可能这之间有一些相似性?
王京:提到“送膳”,与食物相关。食物是和我们每天的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所以往往能较为突出的体现比如历史、制度的安排,或一些信仰层面的东西。《食物与心脏》这本书集中收录了柳田论述食物的文章。刚才提到的“送膳”是什么呢?柳田通过他的研究,认为食物不只是用来裹腹的,它本身是有灵力的,它里头有一种灵的力量,这个灵的力量是和人的社会紧密结合的。在农村,比如说盖房子,以前因为都是茅草顶,隔几年要换,是非常大的工程。或者像收割的时候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时候需要很多人来帮忙。在别人来帮忙的时候,主人需要专门做一些吃的,在室外犒劳大家。这些食物除了犒劳之外,还有确认社会结合的含义。既然是社会结合,意味着有时候本来应该在场一起食用的人,虽然因为特殊原因没有到场,但也是其中一分子。这些人没吃上怎么办?那就专门留一份,然后把这一份给你送去,虽然是隔着时间和空间,但还是能够通过食物这一媒介联系在一起,完成这个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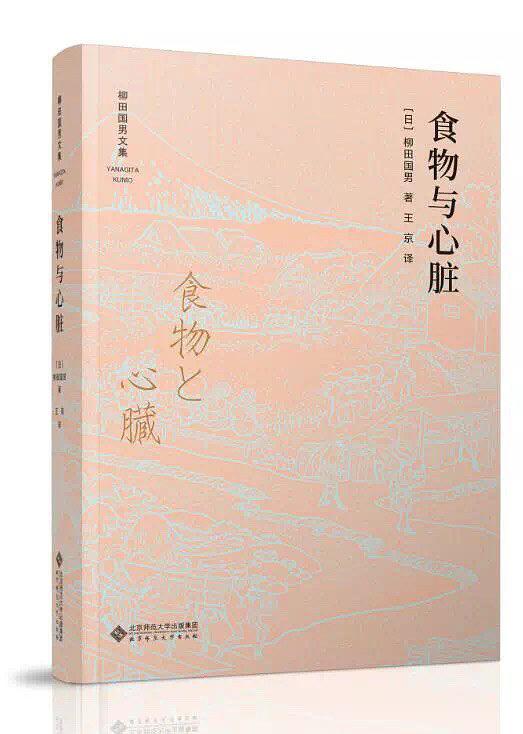
主持人:当时我并不懂他们为什么每一年都来送,可能也是因为我妈还是家里的一分子,所以即使她不在、收割的事儿也跟她没关系了,但是以此来表明他们依然有关系?
王京:在民俗里面,这种情况很多。虽然人不在,但是你的功能、你的位置还是在那儿,一切都按照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式来进行。因为民俗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圆和、比较美满、比较完善的形式,“送膳”也是这样一种填补的方式。
岳永逸:作为读者,我特别有感于在《木棉以前》里面那篇《女性史学》。王京提到柳田国男是学者,但更是一个文人,他的文字始终有着暖意,有着理性的思考。柳田对女性的善意、暖意与敬意,不是我们当下的“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等等那种声嘶力竭的呐喊,这些激进甚至极端的革命性,在柳田国男的文字里面没有位置。福田先生很敏锐地注意到柳田对女性始终有的善意、始终有的温暖的目光。
以我们中国人都熟悉的“分家”来说,我们说“分家”就是分灶。现在,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年实行,基本不存在“分家分灶”的问题了。但是,过去一家有几个儿子的话,肯定结婚了以后就要分家的,“分家”就是“分灶”。“分灶”就是自己开始要烧火做饭了。这时候,分家都是强调男性在干什么,是从父子这个链条而言的。柳田国男在《女性史学》里勾勒出日本女性在整个社会当中的重要性。
首先,我感触很深的一点,柳田指出,男性喝的这个酒不光是家庭主妇酿的,而且家庭主妇也控制着男性喝的酒。酿造技艺是她的,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只有在酒宴场合,男性才能喝酒。
我们中国人都习惯说以前所谓的“旧社会”,女性苦大仇深、苦不堪言。俗话说“三年媳妇熬成婆”,熬成婆有什么标志?好像都说儿子娶了媳妇,地位就升了一辈。其他,很少有具体的研究与呈现。但是,柳田国男给我们提供了日本女性社会地位变迁的细节、标志与仪式。在日本,女性似乎才是家庭生活中的主体。当媳妇升格为家庭主妇,掌管家庭事务时,婆婆会把一把勺子、一个锅盖,仪式性地给儿媳妇,说今后家里的煮饭的事情都由你来做了。此后,婆婆退居二线。在这个日常生活层面,如果没有那种对女性的善意、对史料的广泛的阅读和理解,柳田是很难从琐碎的层面勾画出日本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不可缺失的重要性。
虽然我们有很多学科、很多研究也都在做这些东西,但是很难有深入到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面临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柳田国男最难学的地方。王京刚才说,柳田之后的日本民俗学者感觉到巨大的威压,说一步前面有他,十步前面还是有他。在我看来,对中国学界而言,可能走了五十步之后,前面还是有柳田国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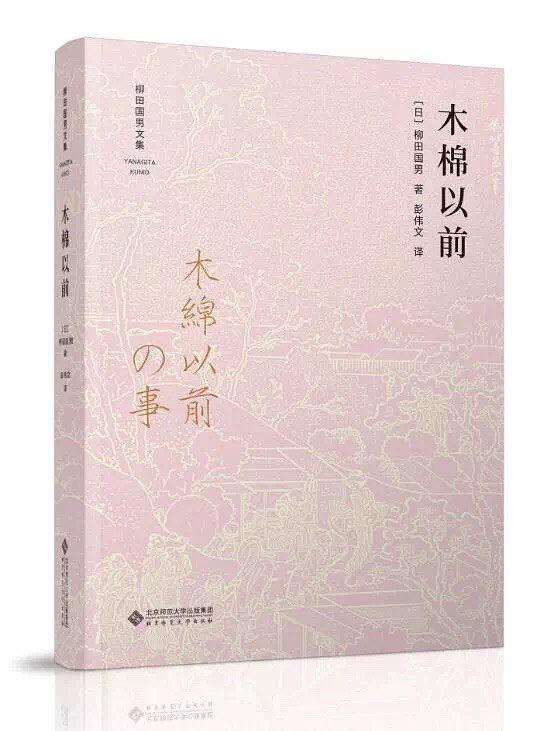
主持人:《女性史学》这一篇我印象也很深,这本可能读起来是相对最轻松的。柳田国男明确提到,他说我也有女儿的、我身边有很多女性的,我也得替她们说话。但是他在这本书里也提到,他其实是比较鼓励在当时那个日本社会,鼓励女士从事比较适合女性的工作,但是他又怕人家说他提这个就好像有歧视女性的意思。其实他还是相当重视女性在社会当中的地位的,包括岳老师刚刚谈到的喝酒,其实柳田国男的书可以帮我们厘清一些对于日本文化以前认识上的偏差,比如现在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吃日料相对来说比较洋气一点,日料店都会挂“居酒屋”的牌子,但是他说 “居酒”这个事儿,在日本一开始不是特别好的,就是如岳老师刚才说的,是要在特定的节日由女性端出来大家一起喝,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一个人独自饮酒。一个人独自饮酒在什么情况下呢?出现在这个人是家里的仆人或者下人,主人给他喝,他就一个人拿着喝,或者他无地可去,有这样的酒馆——这样的酒馆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开的,叫“居酒”。
王京:居酒屋这个“居”,从中文角度看起来像是居住,但在日语中就是“待在那儿”的意思。所以“居酒”就是“待在那儿喝”。按照柳田国男的说法,酒原来是和家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家的管辖范围。柳田国男认为在家的范围之内,劳动是男性负责,负责人称为“家长”,劳动之外,包括衣食住的安排、调度、获取、制作等等这些全都是由女性来掌管的。我们说“男主外女主内”比较抽象,他说的比较具体,认为家里的事,除了劳动之外都是女性在管,因此提出一个叫“主妇权”的概念。当时学界老是提家长、家长权,都是男性,给人的感觉是家里什么都是男性说了算。但柳田认为不是。他认为跟生活最密切的这些事情都是主妇在管,男性是不过问的,完全按照女性的意思来。甚至有时候,比如说我一个主妇张罗这个家的时候,有时候挣的钱不够使怎么办呢?我去娘家要,从娘家那儿获得一点帮助来渡过难关。女性在操持一个家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实不只是酒在女性掌管下,但酒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外在的标志。酒应该是在过年过节,或者有重大庆祝,或者说婚丧嫁娶这样的机会才会出现。饮酒首先得酿酒,而酿酒所需要的器具、材料都是女性来掌管的。

王京:《关于婚姻》这本书专门谈家庭到底是怎么演变的。跟《都市与农村》也有关系,随着城市的发展,其生活状态和原来农村的生活状态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本书专门讨论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还有一本是《女性的力量》。《木棉以前》是从生活角度来谈,而《女性的力量》是专门就女性这个主题展开论述。这是第二辑的内容,敬请大家期待!
不断发问的“人”学
史歌:很多史料,或者说很多事实,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参考的事实,这些事实有可能是形成文字的文献,也有可能是口口相传的传承,也有可能是人的身体,也有可能是祭祀表现等。这种作为研究资料的东西,我们怎么样把它用一种范式、使它成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这个可能是有柳田国男的过人之处。我就是在想,这些史料都摆在大家眼前,所有的学者都可以看得到、查阅到,有些史料也是被嚼了很多次了,也被翻阅、查阅了很多次了,但是怎么样把它排列组合起来,能够发现新的问题,或者说用一种新的叙事的形式来进行对一些日常现象进行表述,我在思考这是不是有柳田国男和其他民俗学者最不一样的地方。
王京:对于柳田国男,其实他未必一定要说自己的学问是“民俗学”,他所做的,就是为了“人”的一个学问,只不过是当时称为民俗学而已。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战后柳田把自己的藏书捐献出来,成立民俗学研究所,面向社会开放,而他的弟子就成为研究所的研究员,以这样的方式继续研究。当时他们的工作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柳田组织弟子们编撰“社会科”的教科书。日本的小学中学里有一门课叫做“社会科”,是关于社会的科目。语文、数学、英语之外,比如政治、经济、法律,只要是关于社会的,基本都是社会科的范围。柳田编的教科书,有着非常强烈的一个编纂思想,就是绝不是自上而下的,比如先讲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再讲到人的消费,他绝不是这个眼光。他是从人开始,第一课就是日常生活,让孩子们先去了解自己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自己每天过的生活变成一个观察的对象。观察完自己生活,再去了解别人家的生活、身边的邻居、自己的村子、旁边的村子、我们和自然界的交道等。实际是从人真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并延伸下去。他认为是因为人想要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所以才有了社会。即使到现在,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一般的教育方式还是从上往下,从社会往人,也许记得了制度但很难看见人。
可惜的是,柳田最后失败了。因为教科书是否被使用,在日本需要竞争,而他这个教科书跟别的教科书放在一块儿,明显会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教科书没办法考试,没办法出考点。对生活的通过身体的了解怎么去机械的考核,最后给一百分?不像从上往下的教科书,比如三权分立啊制度什么的,容易设得分点。这也许正是现在的这种教育和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重新反思的东西。教科书这个尝试是失败了,但是这个事情上比较明确的反映了柳田对生活的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是他学问的出发点。

主持人:岳老师肯定有话说,关于“人”,所有的研究当中其实应该都是围绕“人”。
岳永逸:作为外国人,我们还在今天谈柳田国男,这可能本身也是柳田国男成功的地方。柳田国男过世后,甚至过世前,他的学生辈们为了自己的“活路”,就开始有意识地批判他。然而,柳田最成功的地方是,刚才王京说了立足于人。这五本书我阅读的感受,就是柳田国男他那种温婉的批评,很老道、很厚道,他绝不会轻易否定一个什么东西,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新生的,他始终有着最大的慈悲心。
《孤猿随笔》周先民老师译得也非常顺畅,甚至把中国的一些俗语融了进去。该书中,有一篇是写柳田国男自己养的狗。这只狗名叫“毛利”,毛利在日语中是“守卫”的意思。这个狗很小一点就领养来了,是日本的一种很忠诚于主人的本地犬——秋田犬。结果,同是秋田犬的毛利似乎有着变异。在其长大时,它的个头比一般的秋田犬大了一倍,而且脾气暴躁,很爱咬人,咬邻居,咬这个咬那个。这使得作为主人的柳田不得不经常给人赔礼道歉。后来,毛利把柳田的女儿也咬了。虽然是这样,柳田还是去咨询。他说我想把它送走,但是我送它去哪里呢?又不忍心!最后,直到毛利把柳田自己咬了之后,柳田才经过中介,将毛利送到一个养鸡场去。后来,养鸡场也没有了。在这种状况下,柳田还是对他的毛利念念不忘。他一直想弄明白,毛利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持人:他甚至研究这个狗为什么特别爱咬人,是因为中介的人告诉他,这个狗的妈妈就特别爱咬人,是基因问题。在自己的生活所有方方面面,他都会去问一个问题。
岳永逸:他都会娓娓道来。对柳田而言,这些不是琐事也不是小事!这跟我们文人的“学而优则仕”之逻辑很不一样。柳田国男完全是相反的路径。他本来做了高官,“裸退”了,来做学问。做学问在很多国家都跟民族主义捆绑在一起。柳田并非没有民族主义的情结,但他始终都是从最普通的人及其日常生活这个点出发。这样,柳田的民俗学跟中国民俗学在一开始就分岔了。柳田对民俗语汇,就是我们平常常用的口语关注很多。
对口语,我自己有一次感受深刻的经历。18年前,我跟朋友坐火车从北京到拉萨。在火车上,面对车窗外越来越多的白杨,我们两个畅聊起来。看到白杨树,我们自然就会用到茅盾“绝不旁逸斜出”之类的表述。坐我们对面的是一个打工的大姐。大约一个小时后,那个大姐实在受不了了,说:“你们两个可以说点人话吗?”我们两个当时镇住了,我说:我们没说“人话”吗?她说:“你们说的我一句都听不懂!”显然,我们在座诸位熟悉的我与我这位朋友的交谈,已经远离了更多人的日常语汇。
一个中国人看这套译丛如果有阅读障碍的话,那就是柳田格外重视的日本的民俗语汇。不仅如此,柳田自己也花了很多力气,编辑民俗语汇词典。民俗语汇都是大家在说的,不光是哪个集团的事情。所以,始终以普通的人为出发点,这是柳田民俗学最成功的地方。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总是在急迫否定。我们好像是在关注弱势群体,我们好像在要求这个社会快点变,但是我们一直在否定,我们到今天还是在否定。
我想,在座朋友有兴趣的话,在读柳田的文字时也是可以体会到的:他总是在启发你问为什么,就像一个老人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说到《海上之路》,我还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不光是柳田国男这样的大家,日本人其实一直有一个始终在追问我是哪里来的民族情结。2008年汶川地震。我是当年5月底去的汶川。我在几个村寨走的时候,当地有人告诉我说,地震前几个日本学者刚刚走。我问日本学者干嘛呢?老乡们说,这几个日本学者待了快半年,说羌语里面的很多口语和日语的音相近,他们在分析日本大和民族是不是跟羌族有关系。当时听了我就镇了一下。因为我本身学这个专业的,我也听到过很多关于大和民族族源的说法。从海上的漂浮物出发,《海上之路》同样委婉地表达着“寻根”从而安身立命的情结。
经过“二战”这样的历史事件,日本到今天也没停止追问这个话题。在《海上之路》等著述中,柳田国男经常说:我只是一种推测,我猜测、我推测、我觉得,等等。这种严谨、坦诚,不像我们国内的很多学者经常说肯定就是这样子,我说了就是这样子,其结论也好像逻辑严密,还有很多量化的统计数据分析。但是,大家都知道,其结论好像跟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少关系。所以,尽管时境过迁,我几乎是如饥似渴地来读这套译丛的。
史歌:你说的那个我体会特别深,因为日语当中暧昧表现非常多,出现这种“我认为、我觉得”或者“也许、可以”类似这种表述特别多,这跟日语本身的特点有关系,但是确实是柳田他的论述非常严谨,就像您说的,他很少有直接的这种批判,也很少有自己的这种直接的断言,基本上都是用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刚才岳老师提到日本人经常会问自己从哪里来?因为给学生讲课经常讲到日本人和大海的关系,日本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的,日本人他们对大海的这种情结肯定和内陆的国家,或者像我们中国这样仅有一半、不是完全四面环海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其实书上也提到在很早很早以前,大概在绳纹时代的时候,发现日本很多贝塚,就可以看出来那时候日本主要是以食用海里面的海物为主,那么这个贝塚层层的堆叠起来像年轮一样记录日本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大海实际上给日本人提供了食粮,但实际上它也是一道屏障,日本毕竟在海的中央,它如果想走向更远的地方必须要克服一定的困难,日本人本身对大海这种情结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日语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那种跟海有关的,用我们中文很难去描述出来的一些词汇,包括一些景色、包括一天当中不同的时刻,都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关于大海的很多很多描述,都是在日本人对于海洋的非常细致的思维当中慢慢产生的,慢慢孕育出来的一些词汇。一说到日本就想到岛国,岛国文化,我们喜欢说岛国文化对吧,从世界上看日本,和日本人站在他日本的土地上去看海洋、看世界,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通过翻译《海上之路》,我也大概能够体会到海洋对日本来说,它既是一种外在的、向外走的一种渠道,那么同时它也是一种让自己反省自己深层结构的,因为他好像是被困在孤岛上的一群人,那他们可能有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去审视自己。那么现在航海技术都非常发达了,日本走向世界现在已经是克服海洋这道屏障,现在完全不是问题了,日语当中有一句话日本人经常会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受恩于海洋的国家”,就是受到很多来自海洋的恩惠,柳田在他的书中也提到过很多漂流物,就是海洋给他们带来了很多丰富的物产。日本人对海洋的思考会比一般的国家或者其他民族的人会更加细腻一些,更加多一些。
王京:关于海,肯定在日本人心目当中有着非常浓厚的一种情结,也是跟他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一种东西。比如柳田在谈食物的时候提到,在日本,特定的时候一定要吃“荤腥”。日语原来有一个词,我把它翻译成“荤腥”,但是他这个“荤腥”不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佛教的那个吃“荤”的概念。因为他说的“荤腥”不包括一般的肉类,“荤腥”特指海产品,尤其是海鱼。非常限定,首先它只能是鱼,第二它还得是海鱼。他举了一个例子,在深山里头的村子,大家觉得日本小,其实日本也不是那么小,也有深山老林,深山里面的村庄离海非常远,但在过年的时候或者有一定特殊需求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弄一点“荤腥”。
除非是家里有人去世的情况下是不用的,其他的情况下都必须有,这个“荤腥”对日本文化的意义就非同一般。柳田在论述的时候,当然他没办法直接证明,他就说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来自海上这种记忆还深深地留在文化的底层,所以在我们赠答的时候,早的时候需要附有一个鱼干,后来不用真鱼干也得画一个。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