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圆桌|王笛、何其亮、陈丹丹:历史的微声——城市研究与微观史
近日,全球学术平台“全球研究论坛”(globalstudiesforum.com)展开了一场围绕“城市研究”和“微观史”问题的圆桌谈。主讲人是澳门大学讲座教授王笛,与谈人则是香港树仁大学教授、历史学系主任何其亮。圆桌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陈丹丹教授(也是“全球研究论坛”创始人和本场活动召集人)主持,参与讨论的还有河南大学博士生何元博。以下为本次圆桌谈之汇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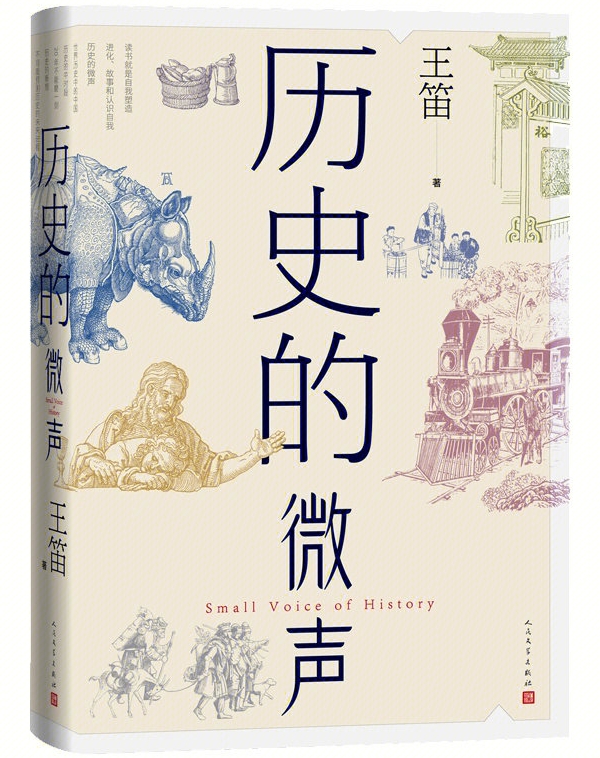
《历史的微声》,王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一、为什么选择做城市研究
陈丹丹:我们在去年6月份有过“全球城市·长安与洛阳”系列讲座的第一季第一场,当时很受大家欢迎,所以很高兴半年之后能继续我们的“全球城市”系列讲座。今天有幸邀请到王笛教授和何其亮教授。王笛教授是城市研究的大家,研究包括有成都、长江上游地区以及城市空间诸如茶馆等。何其亮教授研究的是上海及其城市文化、杭州及城市空间比如西湖。我个人也是研究城市的,研究的是民国初年上海的清遗民,还有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城市文学。
今天的圆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先谈城市研究,中间加入我们三人对各自的家乡、各自当下所在地域的讨论;第二部分我们就切入到微观史,会谈到王笛教授的作品《历史的微声》《街头文化》《茶馆》,还有《袍哥》等。现在先开始城市研究部分,请问二位专家为什么要选择做城市研究?
王笛:我真正开始城市研究是1991年在美国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有三个题目,其中两个和城市史有关,分别是成都街头文化、茶馆,以及和城市研究关系不大的袍哥。最后我选定了成都的街头文化。我选择城市史主要是基于我当时对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些思考。
首先,研究生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城市史研究成果,发现关于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上海的研究特别多,但是对内地的研究相对薄弱。第二个问题是重乡村轻城市,我看到很多关于区域的研究,几乎都是以农村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当时城市史的研究,上海之外的如罗威廉的《汉口》这样的著作并不多。国内的城市研究几乎也是集中在主要的大城市,特别是上海。由此,我感到整个西方对中国城市的研究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而且我认为上海其实不能代表中国的城市,上海是一个西化的港口城市,是在近代贸易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它是中国,但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国,甚至不是典型的中国。像成都这样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城市,其实更能代表我们称之为的中国城市。所以我提出要研究一个全面的中国、另外的中国,只知道上海是远远不够的。同时我并不是研究整个成都,而是研究成都的某一个方面——街头文化。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内地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中,去发现一些我们通过上海或北京所看不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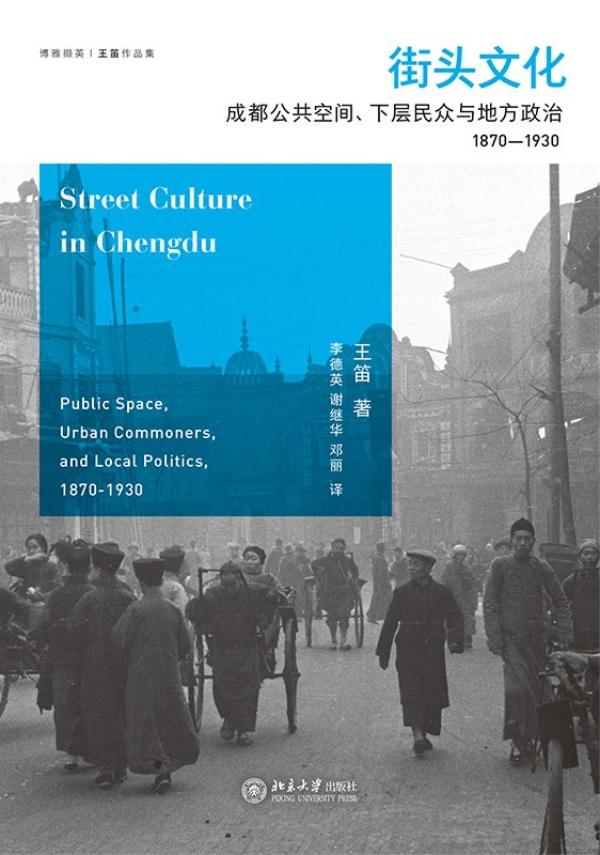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1870-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版
何其亮:我觉得自己其实并不能算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者,因为我的研究路数其实还是以文化史为主。我的学术其实比较任性,体现在我的学术跟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我做上海史是因为在我26岁去美国前,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上海市的黄浦区。其实那里不光是一个店铺林立的商业中心,也是娱乐场所的集中地,有很多戏院、电影院等等。所以我后来做戏剧、电影,就是受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但当我到美国读了一些美国的上海史专著后,发现其实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看上海,这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太熟悉的东西,我反而要从遥远的大洋彼岸的角度去重新认识。
现在我搬到香港,又给我提供了一个回看上海的角度。所以我说生活的经历跟学术息息相关,对学术是有帮助的。我非常支持王教授刚才说上海不是一个有代表性城市的说法。我在自己的一篇博士论文里写过一句话:上海不是a representative city of China,上海是a city of representations。对我来说,城市除了城市管理和基础建设等物质上的东西,还代表着一种想象。这种文化想象会脱离物质一直存在。比如我每次到杭州的孩儿巷,脑海里便会浮现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到了香港,从小看港片长大的我也会有意去寻找看过的电影电视里的场景。这是我研究城市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跟我的研究方法也有关系。
陈丹丹:我回应一下王笛老师关于上海研究的问题。我开始研究上海时,正好是李欧梵老师写《上海摩登》的时候,大家都在谈上海是一个很摩登的地方,但我的研究主要是写上海不那么摩登和现代的部分。所以我研究的民初上海的清遗民是前现代的,我写张爱玲也是写她呈现上海比较传统中国的一面,其实是在挑战当时的一种上海叙述。所以我比较关注上海十里洋场之外的部分,比如王安忆作为共和国的女儿,其作品经常强调上海的边缘地带,《长恨歌》之后的作品也是一直探索上海本身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部分。
我在北大读书时,我的导师陈平原教授当时正在进行北京研究,他提出这个北京研究其实也是为了回应上海研究,所以有这样一个学术的脉络在。王教授您说到您做城市研究是受您的导师罗威廉教授的影响,在他的那本《汉口》中,他回应、挑战了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研究——韦伯认为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所以我觉得王笛老师的这部著作其实也呈现了这么一个学术脉络,即除了研究日常文化,我们也会思考一些历史的宏观取向,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欢迎大家待会儿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二、城市研究中最感兴趣或让自己兴奋的地方
王笛:的确,我在写《街头文化》时,罗威廉出版《汉口》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如你所说,他回应了韦伯关于中国的看法。韦伯认为中国没有发展出城市共同体,中国人都是把乡村视为真正的家,而只视城市为一个谋生的地方。我记得1990年代,魏斐德和叶文心编了一本论文集,叫《上海的寄居者》,可能也是来自这种思考。但罗威廉的《汉口》提出这是不对的,出版以后影响很大。虽然我写成都街头文化并非以此为出发点,但我后来在阅读成都资料时发现了很多实例。成都市民在清代就把自己看作是成都人,不断强调成都是成都人的成都,有完整的Community,有土地会。过去说中国没有城市的概念是因为缺乏纪念碑式的建筑物,但进入城市的研究后可以发现,民国初年成都就修建了四川保路死事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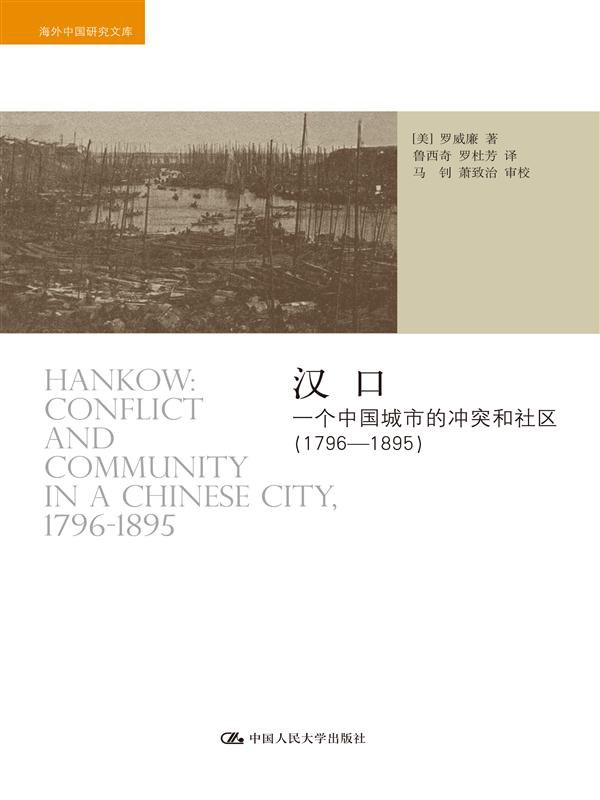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版
当我读了新的资料,对过去大家很困惑的问题有了一点新发现,这就能支撑我把一个课题做五六年,甚至十几年。再举一个例子,成都的茶馆有一个功能,在晚清民国时期,人们有了纠纷就到茶馆里去“吃讲茶”,好多纠纷就在茶馆里解决了。黄宗智有个重大的发现是为什么在清代很少有民事诉讼,他认为好多民事诉讼在县一级里经过调解就解决了。但他没有提到在成都甚至江南,绝大部分的纠纷在民事诉讼前已经在茶馆解决了。所以为什么在民国时期有人说茶馆是“最民主的法庭”,地方的司法权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民间像袍哥这样的组织分化了。当时我在思考这些时觉得这些重大发现远远超出了茶馆问题的范畴,涉及到了中国的司法系统、社会自治等大的问题,这就是让我很兴奋的地方。
何其亮:历史研究的确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事情,特别像做侦探。我前两天和一些研究生说,研究做得多了,内心会产生一个跟外部世界有联系但又隔绝开的第二世界,那一刻你会觉得许多东西都似乎是身外之物,没有那么重要了,你内心世界的那种满足是无法形容的。
我刚才说了我做学术比较任性,很多研究和我的日常生活是有关的。比如我做上海(研究)时,脑子里已经呈现了一幅地图。较明显的是2005年我在上海档案馆搜索盛宣怀出殡的档案,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描写盛宣怀家属必须走工部局规定他们走的那条路径。我当时特别兴奋,因为工部局文件规定的那条出殡路线就是我生活过的地方,让我感觉特别亲切。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一个人坐在美国南卡罗来纳的办公室里,当时我脑子里的世界已经超越了周围的环境,是在走那条路线,因为我太熟悉那个城市了,我想这就是现在所谓的city walk吧。这就是我为什么写东西特别兴奋、有愉悦感。
三、为何选择成都、杭州、茶馆、西湖
陈丹丹:何其亮老师写过上海,当时怎么又选择杭州?刚才我们提到茶馆,王笛老师书中有写到各地不同茶馆的比较,提到过成都茶馆的独特在于农业的影响。如果成都茶馆文化是受农业文化的影响,那其它城市会不会受到更多商业文化的影响?比如说现在阿里巴巴在杭州,比如说明清商品经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考量?此外茶馆和西湖都是公共空间,就联系到我们城市研究的一个经典话题:公共空间,请问二位对此有没有什么观点?
何其亮:杭州是我特别喜欢的城市。1993年我第一次去杭州看到西湖时感觉惊为天人,似乎见到了梦中情人,这种感觉是萦绕在我心头30年一定要把它做出来的,所以2023年我出版了西湖的书。我一开始想做景观史,因为高峥教授的《接管杭州》珠玉在前,我想有一些突破,于是想到西湖景观。但后来我越做越往环境史、非人类史靠拢,不过还是在杭州城市研究范畴内。西湖有一个特点是它城乡结合。1912年前西湖是城墙外的一个郊区。后来城墙拆了,西湖从城市以外变成城市的中心地带。刚才丹丹老师提到杭州这样的城市是不是和商业有关,因为成都是农业有关,有点像芝加哥,有一本名著讨论了芝加哥和中西部农村之间的关系。杭州绝对跟大运河有关系,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和杭两个城市的意义其实就在大运河运输的关系里。所以城市发展和传统时代的商业是密切相关的。后来我还看了一些徽商的书,我发现杭州是徽商离开徽州山区外的重要一站。所以杭州的发达肯定和商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陈丹丹:你在香港待了这么久,对各地饮茶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何其亮:香港有属于有闲阶层的饮茶文化。但茶餐厅和饮茶不一样,茶餐厅是去吃一顿饭,很快可以回去接着上班;而饮茶可以社交,也可以独享这个空间,一个人在那里静静地坐一下午也没事。扬州也有早茶,我觉得像成都、扬州、广州、苏州等地区,不管是商业文化还是农业文化影响,只要有钱有闲人聚集的地方就会有茶馆,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
陈丹丹:对,很有意思,就是扬州饮早茶的习惯还在持续,但在南京,这种早茶文化就不是很浓郁,上海那当然是咖啡馆了。大家有没有新的见解?
何其亮:我说一下上海咖啡的问题,这要分两方面看。一方面,中产阶层、白领阶层兴起,有喝咖啡的习惯是正常的,我们经常会看见白领手上拿一杯咖啡匆忙赶到公司上班;另一方面,上海的咖啡文化是被刻意渲染出来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我去了韩国发现那里咖啡馆的密度比上海高,其实不见得咖啡在上海有什么特别大的特色,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有意制造出来的城市象征。
王笛:把喝茶作为日常生活,据我观察,现在也就是四川成都、重庆了,可能是整个20世纪的变化。上海在晚清有好多茶楼,20世纪开始越来越少,我觉得主要还是生活节奏和商业化的影响。像广东虽然过去茶馆也很多,但演化到今天就是吃早茶;在北京,我们所知的老舍笔下的茶馆也早就没有了。我想这还是和地域的生活节奏有关,成都要慢一些,因此它不仅能提供茶馆发展的环境,咖啡馆也多。在成都,大家不是像刚才其亮描述的,咖啡拿在手上匆匆忙忙去上班,而都是坐在那里慢慢聊,一杯咖啡喝一两个小时。所以茶馆是根据地区的生活习惯、节奏发展起来的。
最后我要强调一点,由于城市大拆大建,小街小巷逐步消失,街头文化、茶馆文化也随之消失了。成都现在的茶楼和我们过去概念中传统的那种茶馆还是有很大区别,而那种真正表现过去茶馆文化的,大家坐下来没有什么隐私随便聊天的茶馆,在成都也越来越少。所以我在这里推荐大家去成都市内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以后这种传统的茶馆会越来越少。

鹤鸣茶社
陈丹丹:王教授提醒我了,像南京的六朝烟水气,就是《儒林外史》中著名的那段,挑粪的人他们也会相约去看夕照,这一点特别有意思。我们从明清时期开始,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了,所以我想也可以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元博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何元博:我小时候家门口附近就有一家茶馆。大概十年前,西昌城市里还有三家老式的茶馆,但现在经过各种旧城改造、消费升级,可能只剩下一家了。那个茶馆和成都茶馆还不太一样,西昌的茶馆里很多是做工、骑摩的的社会劳动阶层,他们会在那个茶馆里坐上一整天。在茶馆门口,也形成了一些产业,就是摩的产业。因为我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外地或山上的少数民族,如彝族,他们来到这个城市里后,可能会去从事摩的等行业。他们很喜欢在茶馆里聚集,可能一坐一整天,几人坐着喝茶,围着打牌,这是我感觉西昌茶馆一个蛮特殊的地方。
陈丹丹:这个摩的文化挺有意思,我想到了现在从咖啡馆出来的打车文化,王笛老师书中也提到了黄包车。
四、喜欢哪些城市研究的著作
陈丹丹:接下来的问题是,二位喜欢哪些城市研究的著作?王老师您写作的时候是以哪些著作作为榜样?
王笛:我一直强调学术研究一定要大量的阅读!不仅是阅读和自己的研究专题有关的,很多阅读其实是间接的。阅读的思路一打开,你在写作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将从其他研究方面得到的启发用于分析自己的问题。我在写《街头文化》时,想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地方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冲突,其实已经超越了成都城市的问题。我在写《茶馆》时,第一卷解决的是: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冲突,也超越了成都城市本身。
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不关注现代城市,但现在城市的大拆大建,城市的发展对城市文化的影响,不能只是让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去研究。《茶馆》的第二卷,写1950年到2000年,就进入到了过去我们历史学很少涉及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城市。我作为历史研究者,要回答历史的问题,不是说只能读历史研究的成果。人类学、社会学通过田野调查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城中村的研究,对我来说非常有启发,我们历史的研究也可以和他们进行对话。
最近二三十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科在互相交叉跨越。像《茶馆》的第二卷实际上解决的是社会学考虑的问题,包括公共领域的问题。但这些超越了历史学的讨论一定是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跳出自己的领域,阅读始终是开放的、不分学科的,始终是要超越自己研究课题的本身。
陈丹丹:我之前研究城市比较像文学的手法,把城市作为一个文本、一个意象,会用到比如说齐美尔、德勒兹的理论,比较文本化。我觉得历史学家们就好像给我们打开了另一个世界,比如您说到茶馆背后有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然后需要研究到税收、各种档案、各个阶层等。跟我们文学的研究完全不同,我们文学做城市研究时用理论的话,通常会用文本化的文学理论来研究。接下来我们就交给何其亮老师,就是你喜欢哪些城市研究的著作?对你的影响,可结合经典理论、空间理论来谈。
何其亮:《上海摩登》对我影响很大,它解答了我在博士时期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现代性。《上海摩登》给我们解答了现代性的两面怎么结合起来。它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城市基础建设等物质层面,另一部分讲的是那些作家如新感觉派、张爱玲等,是一种文化表达、美学叙述。《上海摩登》对我来说,不光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上海的问题,而是怎么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不过我认为书中作者选择的小说家要具有代表性。如果1930年代都没人看这些作者的作品,你凭什么说他就代表了上海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太研究精英阶层的作家,我喜欢做大众流行的,比如鸳鸯蝴蝶派。
有一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就是《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其实里面描写的和《上海摩登》有点像,比如写奥斯曼改造后的巴黎,导致像波德莱尔等一些法国作家的心态发生改变。所以我一直比较喜欢这种写法,即外部环境的改变,如何改变人的感觉和人的表达。这些对我影响比较深刻,我现在的研究很多时候回答的都是这些问题。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版
五、“城市研究”在全球语境与中国语境中,现今的瓶颈在哪里?还能怎样突破?未来的研究方向?
陈丹丹:我也想到《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还有《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文学完全是把城市作为文本,再去细读一些文学文本,我习惯了这种研究后,看历史学家的著作,会觉得又打开了一个更宏大的世界。
王笛老师刚才提到社会学、人类学,现在我觉得我们进入了一种社科的时代。社科的进路特别多,比如政治经济学、数字平台、外卖骑手等。不知道您现在是准备往社科化方向,还是往探索普通人心灵的方向发展?还有怎样突破现有的城市研究,比如当年想突破《上海摩登》,我所做的尝试是研究上海不现代的方面,社科的做法好像又跟人文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他们会比较印度和中国的城市管理等,不知道我们应该是去结合社科,还是继续人文路径?因为我们人文要突破的话需要新的理论,但其实继本雅明、列斐伏尔等等之后,理论突破似乎也越来越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现在更社科化了?所以请问二位:城市研究该怎么突破?我们现在城市研究的瓶颈在哪儿?怎样面对社科化?
王笛:我的第一本书《跨出封闭的世界》是社科化最深刻的,里面几乎任何问题都要量化,让人觉得非常枯燥,很难读。所以我后面的研究有意识地要回归人文,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学的转向,这种转向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在那之前,历史研究的社科化确实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但是也造成了历史的著作越来越远离大众。
海登·怀特写了《元史学》(Metahistory),对整个西方历史学都有很大影响。我在美国读博时也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我的第二本书《街头文化》里没有一个统计表,就是有意要回归人文。开始去关注个体,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从精英转向普通民众,这样的转移一直持续到今天,茶馆也好袍哥也好,都是以人为中心。其亮刚才说到环境史,环境史是把人放在环境中,也有人,但我这里强调的是要有个人的故事,个人的经历。
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就在它的多元,任何学术的研究只要做出了学术贡献,那就是它的价值,不可能都像科技发展比如ChatGPT那样有重大的突破性的。现在到了年底,要开始各种年度学术热点等等,我经常收到这样的邀请要我提出什么热点,但我从来都不参与。去找热点学术是没有意义的,其所谓的热点就不是学术,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课题积累,才能有进步。哈贝马斯这样的大学问家非人为可造,但有了千千万万个踏踏实实做课题研究的,他自然会就会涌现出来。如果大家都去找热点的话,100年以后都出不了大家。
何其亮:我回应一下社会科学的问题,我在做一个结合了社科但不完全社科的课题。我以前做流行文化、大众文化较多,这次结合了这两者,是电影院兴起和上海城市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因为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城市环境的改变会造成人认知的改变,电影院的兴起对城市的管理产生了极大的挑战,我希望把urban studies和film studies这两个东西融合在一起。
另外一个问题是瓶颈如何突破,我觉得城市研究有好多东西还没做,比如还没有完整论述过城市是谁的城市。这个问题在我研究上海时便感觉到了,也有人提出来:为什么一些在上海的外国人和上海华人,或者说不同的作家(比如说鸳鸯蝴蝶派或左翼),他们写出来的上海不一样?谁有权利可以把城市描述出来?王笛老师在书里指出,刘大鹏的日记十人去看十人写出的东西都不同,我印象很深。那不同人生活在上海,写出的东西也不一样,这是谁的声音的问题?比如打工人、外卖骑手,是否有一个真正的平台可以去写出他们的经验、感受、对城市的看法?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
现在人类学、社会学的人做得比较好,当然历史学也有很多这样的做法,比如北京的黄包车夫,老的经典著作如裴宜理《上海罢工》,讲了好多工人阶级。所以我觉得很多题目都可以丰富着继续做下去。
六、城市研究中公共空间的消退与网络虚拟公共空间
陈丹丹:谢谢,其亮老师说的电影院其实也回应了我们之前所说的公共空间。1980年代时去电影院对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你看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约会不会在电影院了,所以有一种公共空间的变化。而且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公共空间的消退?因为网络的虚拟的公共空间更蔓延。
王笛:目前很多年轻人有了社恐症,但眼下正是我们要回归日常的时候。虽然网络也可以叫公共空间,但是它是虚拟的。现在不管是城市还是文化、历史、社会学等等的研究者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创造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空间。
陈丹丹:王教授提出的公共空间的回归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我觉得也和当下的数字时代有关系,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什么E人I人,即外向的人和内向的人,就是当代灵魂比较迷茫,我觉得在这背后也存在数字时代的危机。我们刚才其实讲到的是一种公共空间的变迁,以前1980年代电影院是很重要的公共空间,但现在好像已经不是这样了,所以其亮老师,你觉得现在实体的重要的公共空间是什么?
何其亮:其实电影院不是一个完全的公共空间,它的环境是黑的,是一个半私密的公共场所。电影院还有一点做梦的感觉,因为漆黑的环境里有一束光在隧道前面,我对这种说法印象很深。
我们说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人的原子化,即人的关系很碎,不能在公共空间聚集。这是技术发展、互联网兴起的一个趋势。现在看电影的方式越来越多了,慢慢开始有网上观影,全家老小买饮料爆米花去电影院这种仪式似乎在渐渐消失。所以王老师说要回到公共空间有它一定的道理,是我们怎么和时代妥协的问题。技术发展到这一步,我们确实不需要离开家就可以看电影,但人是社交的动物,有这个需求。如何回到这种社交状态也是一个难题。而且我觉得不能把互联网作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因为互联网上充分交换意见的功能比较弱,它产生了信息茧房,只是重新确认你想知道的东西。因为智能推送,人接受的信息变成已经挑选过的,这非常可怕,把人困在了一个幻想的世界里。这是我一个粗浅的看法。
七、对微观历史研究、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的互动的感想
陈丹丹:回到公共空间的话题,我觉得电影院其实像一个喻体,让我想起蔡明亮的电影《不散》,他拍了一个倒闭的电影院的空间,里面有一位残疾女性每天从其中走过,她其实是在跟时代告别。那现在我们就从城市研究切入到微观史吧,王老师您做微观史,其实肯定有宏观的抱负吧?您刚才所说的第一本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我不觉得是枯燥的,我觉得有一种朴素的美感,好像打开了一个宏大的世界。王老师刚才也提到了一些他很喜欢的作品,如《奶酪与蛆虫》《蒙塔尤》《屠猫记》,还有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一些作品,不知其亮老师有哪些心头好?你觉得你研究的是微观史吗?有没有非常喜欢微观路径?有没有心仪的微观史著作?
何其亮:昨天准备时我特地想了一想,我的研究肯定是微观史,都是非精英阶层的普通人。作品的话,Ladies of Labor, Girls of Adventure这本书对我影响很深,写的是美国纽约移民女工的生活方式,她们喜欢流行服装,喜欢化妆,看现在被我们称为爽文小说的东西,里面都是灰姑娘遇到白马王子或底层年轻女性遇到了有钱人就完成了阶级跃升这样的情节。这些小说都是地摊上卖的流水线产品,故事有套路,除了人物名字不同,情节其实都差不多。我当年印象很深,这本书最后把这些细节凝练到纽约移民女工的政治斗争上去了。女工们看了这些小说后产生了ladyhood的自尊,觉得自己也是有价值的人,也希望在劳资关系上争取权利。这种自我尊严就是从看这些小说追求fashion中来的。这本书对我影响比较深刻,我经常把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东西和普通人的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当然我这种复制不一定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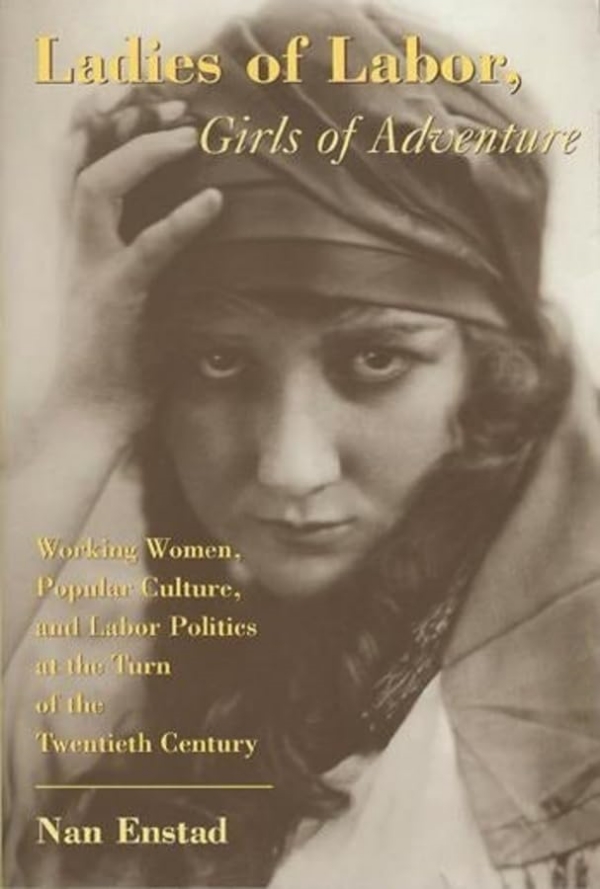
Ladies of Labor, Girls of Adventure,南·恩斯塔德/著
陈丹丹:王笛老师您有没有要补充的?您微观史做到现在,有没有觉得哪里存在局限?
王笛:局限肯定是有的。我当然希望写一本书,既能回答微观的问题又能回答宏观的问题,但这两者是很难兼得的。做得比较好的微观史能通过一个个案、一个人的经历帮助我们认识宏大的问题。如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它展示的是法国大众文化、工人阶级等大的问题,虽然屠猫事件本身不那么重要,但他能把这个事件提炼出来,观察后面文化的东西,我觉得做得比较好。
我在《袍哥》一书中,把雷家故事讲出来,好多人读了觉得你去讲其他的干啥?可能我表达得不够好,让有的人觉得有些内容是不需要的,但其实我的重点是要通过这些看后面地方社会的暴力秩序的关系。
最近读了一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叫做Stranger In the Shogun’s City,写一个农村妇女逃到江户去谋生。这本书非常有意思,这个妇女的父亲是庙里的,她逃到江户以后写了大概好几百封的信给家里,就在庙里留下来了。这些信里有她闯江户城的经历,一家一家的打工,怎样生存等。江户时期的一个普通妇女就这样被记录下来,写得非常好看,像读小说一样。个人的经历背后展示了整个江户城的画面,刚好又是马修·佩里的黑船到达前后的日本转折时期,各种因素交汇在一起。这样的微观的著作就是写得非常好的。
陈丹丹:谢谢王教授,之前有一些观众提到他觉得社科也有局限,就是可能缺乏对美的感知,我觉得像这种微观史做得好的,其实它还是来自于一种个人功力吧:对历史的感知、怎么去把握那个精神世界等。然后让我们何元博同学来介绍一下你刚参加的法律史的尤陈俊、杜正贞等几位教授的读书活动里,他们觉得《蒙塔尤》对他们研究的影响是什么?
何元博:几位老师的学科不同,对于《蒙塔尤》这本书也有不同的看法,比较统一的一点是大家从里边学到了一些方法论,包括它的一些研究视角。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蒙塔尤》是怎么用宗教裁判等档案,去构建起那么细碎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杜老师说,她也想用中国的一些档案文书去做明清时期中国一些村落的研究,希望能从中获得一些借鉴。仇鹿鸣老师现在做的也是用墓志铭去复原唐末五代中下层一些人士的社交网络,还有基层生态,这和《蒙塔尤》有一些异曲同工的地方。《蒙塔尤》是乡村社会史,像王笛老师得《茶馆》《街头文化》,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其实是城市史的话题。那么可以思考,乡村史和城市史,虽然都可以用微观史或者新文化史来统摄,但两者在具体做的时候,是否有一些区别联系或者分别有什么特征?以及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八、乡村研究和城市研究在使用档案上的区别
王笛:元博这个问题,其实微观史的兴起还是从研究乡村开始的,乡村比城市的流动性小,人类学所关注的人类行为保留的完整性比城市高得多。城市的特点是移民人口的流动,人类学所要回答的问题在城市中很难找到,这也是为什么早期城市研究的著作很少。
现在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城市也能像乡村一样进行微观史的研究。问题的关键在于微观史研究最重要的特点:它取决于资料。做微观史研究千万不要先选好题目再去收集资料。比如我的《茶馆》两卷本,第二卷就搞了整整12年,太累了,完全不推荐这种做法。写微观史需要先看哪些资料有做的可能性。现在乡村的档案被逐步发现,华东师大、北大、上海交大等都成立了相应的文献中心,这些文献中心逐步从各个乡村、生产队里收集大量的资料,在座的老师同学如果要写微观史的著作,要先去翻这些资料。像中山大学的邱捷老师,是把中山大学历史系保存的南海县知县杜凤治完整的日记整理出来,并写出了很好的研究著作。我觉得司法档案资料是以后写中国微观历史的一个主要途径,但很多地方档案馆由于仓库库存满了,会把存不下的资料拿去化纸浆,我们一定要能抢救一点算一点,这都是我们以后微观史发展的珍贵资料,一定要珍惜。
何其亮:研究近现代中国史没有档案肯定不行的,而且档案和公开发行出版的资料有本质性的不同,它更接近于人的真实感受,更准确描写当时环境中人的想法。虽然档案也有一个谁是作者、谁是读者的问题,也有个人偏见,但档案确实因为当时不公开,写的东西比较真实。
在我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时候,档案的作用非常巨大,没有档案基本上无法准确地反映那个时代。我做评弹时做了很多访谈,但口述历史中间出现的信息误差太多了,档案的存在补充了访谈者在记忆上的一些缺失。有时也会出现档案缺失的问题,比如做民国史时,因为当时可能没有保存档案的意识。香港也有这个问题,香港1990年代是电影的黄金年代,但很多材料居然是没有的,就是因为当时没有保存资料的意识,拍完电影大家散伙,资料全当废纸丢掉了。所以做历史跟做电影一样是遗憾的艺术。档案资料有的话我们就尽量保存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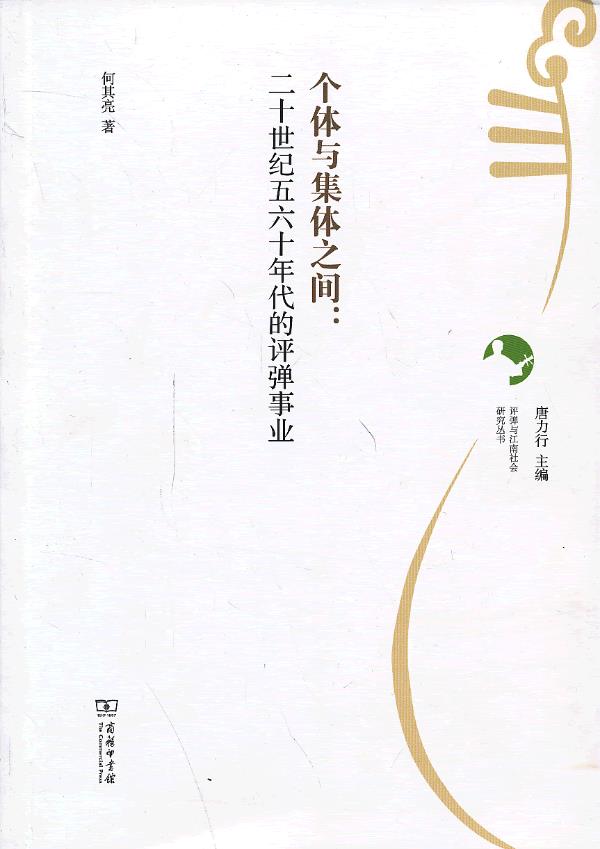
《个体与集体之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弹事业》,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版
陈丹丹:这边有一个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的意见,他是做地理学、建筑学视域下的城市研究。大家知道现在地理在搞GIS,这位同学就觉得社科现在有两个转向,一个是计算社会科学与理工科的结合,另一个是关注精神认知层面,即物质环境和精神认知的相互作用关系。然后我觉得《历史的微声》这部作品是给大家的一个读书指南,其中提到了很多可作为范本的经典书籍,还提到罗威廉老师写陈宏谋,就通向18世纪中国精英意识,我们怎样通过做一个人的研究去通向整个世纪?王教授还提到了一本书可以作为英文写作的范本,就是《中华帝国的过去》,不知道何其亮老师读《历史的微声》还有什么心得?
何其亮:一开始看到王教授读书不易的那段,我觉得挺感动的,那是时代造成的。想读书但没有书的感觉,这在我那个时候已经好很多了。在微观史上,如今大家都指责的学术碎片化,王教授讲得非常好,尤其是年轻学者不可能上来就做个通史出来,都是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做,那你怎么回答碎片化的问题?王教授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我们如何关心日常生活,非精英的小人物生活,这不光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一种人文关怀。历史是人组成的,哪里可以天天空谈大结构。我们研究法律史时就知道,黄宗智教授的一个基本理念,是成文法和法律实践是两回事。所谓法律实践就是人在做法律,判的人审的人被告原告都是具体的人,不能只做大的结构而不做具体的。这就是我的一些感想。王教授帮我们解答了很多问题,不管是在实际工作层面上还是人文关怀的哲学层面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陈丹丹:虽然王教授非常强调微观史,但我觉得他其实是通向宏观的。就像王教授不断地强调微观史不只是在说一个故事,而是要关注到后面社会经济、政治上的问题,最终通向一个宏大的世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从微观的窗口进去,去思考、解决一些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抱负是不是?
何其亮:从现实意义上说也因为每一次你写的东西,人家会要你讲这个案例有什么意义,那肯定要讲你的重要性。我以前美国史的老师总是跟我说significance,意思就是反正我也听不懂你们中国史研究的什么,你得让我听懂你学术重要性在哪里。他这么说让我印象很深。
陈丹丹:元博你作为一个正在学习的博士生还有什么意见吗?
何元博:没有什么意见了,我对于微观史也是抱着一个学习并感兴趣的态度。对我来说有个难点,因为我现在做的方向是断代的宋史,可能想做微观史的研究难度会大一点。也许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如敦煌,或材料相对丰富的长安、洛阳,凭借墓志铭能够做一点相对微观的讨论,但可能在唐宋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去展开一些相对微观的研究和论述,这可能是我遇到的刚才王笛老师说的材料的限制。
九、接下来的研究计划
陈丹丹:有资料的匮乏,但我觉得其实还是需要一些大的手笔的研究,比如说我们之前组织的唐宋变革圆桌讨论,还有大分流和现代世界的兴起。
接下去交给我们王笛老师,您是不是有几部作品的写作出版计划?是不是通向一个比较宏大的世界?
王笛:我刚完成了《中国记事》,花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关于美国媒体从辛亥革命一直到1928年的新闻报道来看中国,其实就是China through Americans’ eyes,已经全部完成了,上下两卷。一些美国人在民国初年在中国的观察和经历,是非常好的材料,但过去很少受到关注。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出的两本书都是修订重印的,一个是《走进中国城市内部》第三版,今天讨论的一些问题,包括公共领域、马克斯·韦伯等都有所涉及;另一本是《消失的古城》的增订版。我现在正在写的,还是我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袍哥历史研究,目前第一卷快要完成了,写的是袍哥的起源,书名叫《开山令》,大概在今年可以完成,是我现在花时间最多的一个课题。
陈丹丹:我在看您说的《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这本书,其实您一直思考的都是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地方和国家的关系,民生、官僚和地方政治,还有袍哥的饮茶、吟诗之中的力量角逐。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面向我们还没有提到,就是文史结合,因为王笛老师说他读了很多文学作品,也从中吸收到很多,所以作品也很多,很像是重新构建出了一个文化的世界。那其亮老师你除了刚刚出版的两本著作,下面就是研究电影院和管理是吗?
何其亮:我今年可以的话,把电影院、电影和上海城市管理这本书写出来。第二个任务是《人民的西湖》中文版要出了,但因为“人民”两个字我感觉在书里没有解释得特别清楚,将来会另外出一本关于“人民的电影”的专著吧,这是后面的写作计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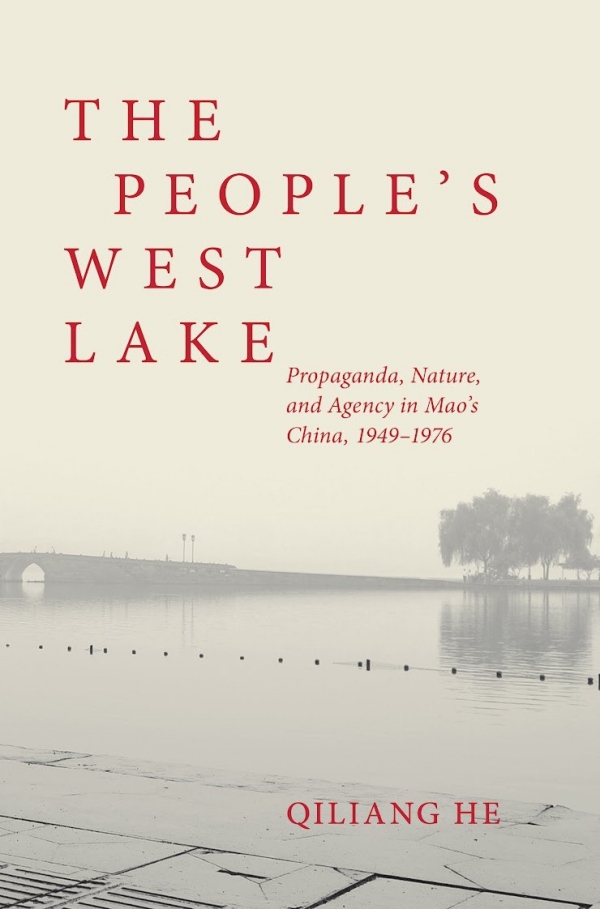
《人民的西湖》英文版
十、对城乡问题、城乡关系的看法
陈丹丹:我觉得王笛老师《历史的微声》这本书里面关于市民的部分,可以跟其亮老师关于“人民”的研究有一个对话。然后这边有个问题,是刚才那位研究生同学,他提问社会变迁对文化的影响、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我觉得可以读一下雷蒙·威廉斯的著作。我其实研究张爱玲和王安忆时一直在思考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我写的是她们的城市书写之中城市比较乡村的一面。王安忆有一部作品里面写到了农民在城市中受到屈辱,本雅明也有城市是一个堕落的自然史的观点,不知道您二位对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有没有一些思考?像齐梅尔他写到大都市会生产一种倦怠的精神生活,后来韩炳哲也提到当代人是倦怠的。倦怠好像是一种城市的心灵。还有我觉得在当代社会,城市和乡村在数字生活上好像在某个层面,差异已经被大大地抹平了,大家都是一样地在看抖音,但同时在物质生活中,乡村和城市又存在差异,不知道二位怎么看?
王笛:过去市民和农民是有直接交往的,在我们小时候和改革开放初期,农民都可以直接把自己的产品运到城市里的农贸市场和市民直接交易。但现在没有了,哪怕菜市场的小商贩,都是通过物流批发的菜。过去几千年形成的城乡交往模式,被现代物流彻底改变了,农民和城市人之间也被隔断了,这对城乡关系的影响非常之大。整个乡村的日常生活在发生变化,刚才丹丹说到的,从相当程度上来说,好多农民虽然还居住在农村,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逐步的接近,比如上网、看电视、刷抖音,他们也淘宝、拼多多。这对于城乡关系的影响肯定是深远的,值得社会学研究。这种城乡关系隔断是怎么发生的,在以后我们历史学研究的课题里也都是要思考的。
陈丹丹:我还想到土地的问题,最近陶然老师有一本书叫《人地之间》,讲土地变革,周飞舟老师有一本《以利换利》,也讲了地方和土地。我就想到研究城乡关系应该也要涉及土地关系。谢谢王笛老师的意见,现在把城乡的问题和人工智能的问题交给何老师。
何其亮:城乡问题我虽然思考过,但对此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就用大卫·哈维的一个说法,世界上没有城市,只有城市化。以前的扩张是通过物理方面,比如把乡村的农田变成街道、建筑设施,但现在这种扩张是通过一种虚拟的方式、生活的方式,比如抖音、淘宝等,甚至有些高铁几乎已经修到了乡村里,这些扩张都让农村的生活方式得到改变。但我觉得城市的扩张是必然的,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个办法。
人工智能的问题,我对人工智能倒不是很担心。我觉得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工具可以,但是缺的数据、材料这些都还需要人去做发掘。人文的工作者需要灵感,人的认知不是大数据或者AI训练就能学会的,我不觉得人工智能会对我们有什么冲击,有也是好的冲击,因为做研究确实比以前方便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这是好事吧。
(本文由张芊芊整理,何其亮教授修订,王笛教授审阅,陈丹丹教授最终定稿。)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