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学能成为拯救人类精神的最后归宿吗
编者按:日前,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上海高校学者共同发起了“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系列活动工作坊。6月28日,由同济大学中文系主办的第一期工作坊“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教育与文学阅读”在同济大学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澎湃新闻·上海文艺等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的30余名与会者参加工作坊,围绕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本文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王宏超在首期工作坊上的主题发言稿。
2014年,八十五岁高龄的米兰·昆德拉在“沉寂”十年之后,出版了一部中译本只有三万五千多字的小说:《庆祝无意义》(La fête de l'insignifiance)。老人的作品多少总有些遗嘱的影子(其实所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昆德拉这部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小说,以谈论女人的肚脐开始,最后却在说:
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我的朋友,呼吸我们周围的无意义,它是智慧的钥匙,它是好心情的钥匙……[米兰·昆德拉著,马振骋译:《庆祝无意义》]
昆德拉并不是第一次在讲“无意义”了,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始,他就在说:“如果生活中的第一次彩排便是生命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他在《帷幕》中又说:
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难道不就是无意义?我们的命运难道不正是无意义?而如果是的话,这一命运究竟是我们的不幸还是我们的幸运?是对我们的侮辱,还是相反,是我们的解脱,我们的逃逸,我们的田园牧歌,我们的藏身之所?[米兰·昆德拉著,尉迟秀译:《相遇》]
昆德拉为什么反复在强调“无意义”?人类难道不是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是悬挂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的动物吗?昆德拉是在表达虚无主义吗?

昆德拉在《被贬低的塞万提斯传承》中,提到胡塞尔在1935年所做的几次有关欧洲人文危机的演讲,此即《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昆德拉总结胡塞尔的说法,欧洲所面临的危机对欧洲命运攸关,“危机的根源在现代(les Temps Modernes)初期就已经出现,在伽利略和笛卡尔的著述里,在欧洲科学单边性的性格里。欧洲科学将世界缩减为技术与数学探索的单纯客体,将具体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die lebenswelt)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人在理性世界里,处在“存在的遗忘”的状态之中,而人的生活世界,“也没有任何值得注意之处:人的具体存在被预先遮蔽,被预先遗忘了。”
伽利略与笛卡尔代表的是启蒙现代性。笛卡尔、黑格尔等将“思考的自我”(ego pensant)理解为一切的基础,追求绝对真理。胡塞尔说:
从笛卡儿起,一种新的观念支配了整个哲学运动的发展……首先是数学(作为几何学和作为关于数和量值的形式化的抽象理论)被委以普遍性的任务,这种任务在风格上从原则上说是新的,是古人所不知的。[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
古希腊虽然有对经验的数的理念化,有欧几里得几何学,形成了系统地一体化的演绎理论,“但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和一般的古代的数学只知道有限的任务,它们只是有限的、封闭的先天原理……古人到此就止步不前了。但是停留在这里就失去了把握无限任务的可能性。”
近代的哲学和数学在柏拉图的基础上前行,通过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自然成了数学理念化的对象。
通过在时空的形状方面观念化物体的世界,数学创造出观念的对象。数学从没被规定的普遍的生活世界的形式中,使空间和时间及其在它们之中可想象的经验上可直观的形体成为一个真正的客观的世界。这也就是说,数学创造出一个在方法论上普遍地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可清楚地规定的观念对象的无限的总体。这样,数学最早向我们表明,用一种先天的普遍的方法,可以使原先主观地相对的、只是在一种模糊的一般观念中可想象的对象的无限性成为客观地可规定的,和真正地按其自身的规定性设想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对于这种无限性可以事先在其一切对象及其对象的性质和关系方面加以规定和决定。[《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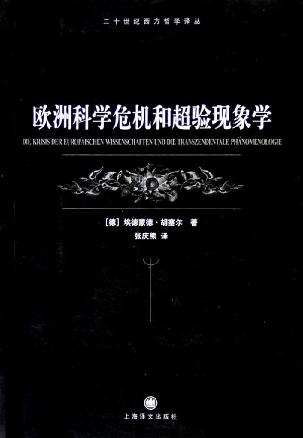
生命充满着偶然,我们却用必然性来解释事件。必然性令人踏实,人接受不了生活被偶然性所支配的事实,这令人不安。在理性的世界中,可经验的事物都是被因果律所决定。“一切在这个世界中所共同地存有的东西,都是通过一条普遍的因果律,直接或间接地相互依存。由于这种样式,世界不仅是一个万有的总体(Allheit),而且是一个万有的统一体(Alleinheit),即一个整体(尽管它是无限的)。”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提到了尼采的轮回观。轮回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建立起了一种存在的链条,以因果律作为连接的逻辑。人害怕失去确定性,失去意义,需要一个因果的链条来赋予人的存在和历史以意义。若是纯然单线的历史观,人就难以找到过去与未来的关联,也就找不到意义所在。因果的必然性是理性所赋予的,那种坚实的必然性给人以厚重的生活根基。
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建筑在莱布尼茨的句子上:nihil est sine ratione——没有任何存在之物是没有理由的。科学受到这个信念的刺激,热烈地检视着一切事物的为什么,好让一切存在之物看起来都是可以解释的,所以,也是可以计算的。人,希望自己的生命拥有某种意义,他会放弃每一个没有原因和目的的行为。所有的传记都是如此写下的。生命看起来像是一道因、果、成、败的明亮轨迹,人则是一边以焦急的目光紧盯着自己行为的因果链,一边继续加速向死亡狂奔而去。[米兰·昆德拉著,尉迟秀译:《小说的艺术》]
启蒙理性的核心是科学化,科学成为真理和秩序,人成为科学理性下的机器,人类的生活、知识、情感、审美都可以放置在科学的眼镜下进行观察,人文学科及文学艺术,也需在科学理性的框架才能呈现其意义和价值。理性解释了世界,同时也遮蔽了世界的复杂性。思想的反思要从理性本身开始,所以海德格尔才说:“只有当我们终于认识到,被颂扬了几个世纪的理性,其实是思想最顽固的敌人,只有这时,我们才有可能开始思想。”
受到启蒙理性的影响,人文学科亦视科学为榜样,追求准确与清晰。哲学与伦理学在进行判断,“人总是期望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因为在人的身上有某种天生且无法驯服的欲望,让人在理解之前先行判断。种种宗教和意识形态即建立在此欲望之上。宗教和意识形态无法与小说和平共存,除非它们能将小说相对和模糊暧昧的语言转化为它们必然的教条论述。”
科学化的理性,简化了世界。世界原本是模糊复杂的,但理性哲学需要清晰的世界,这种清晰的世界是简化的世界,丰富的生活世界被简化了。昆德拉说:
简化所统领的白蚁大军长久以来一直啃噬着人类的生活:即便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会被简化成一副由淡淡回忆组成的骨架。但是现代社会的特性像恶魔似的,又强化了这个诅咒:人的生活被简化为它的社会功能;一个民族的历史被简化为几个事件,而这些事件又被简化成一个戴着有色眼镜的诠释;社会生活被简化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又被简化为仅仅是地球上两个强权的对立。人置身于一个真正的简化的漩涡里,在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宿命式地黯淡了,存在堕入了遗忘之中。[《小说的艺术》]
笛卡尔的哲学把主体作为核心,近代哲学是主体哲学(a philosophy of the subject),以确定性和真理为基础。
理性传统的问题不在于它主张理性,而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理性优先、理性唯一”的传统。“理性优先”表现在“一切对真理和合法权威的主张必须提交理性之法庭”,而且这个理性据称有客观性、普遍性和绝对真理的权威。“理性唯一”在于它排斥了人性中的欲望、直觉、无意识、想象、意志等,视所有这些为“非理性”。[尼采著,黄明嘉译:《快乐的科学》]
尼采说:
你们以为对世界的解释只有一种是正确的,你们也是以这种解释指导科学研究的,而这种解释仅仅依靠计数、计算、秤重、观察和触摸啊,这种方式即使不叫它是思想病态和愚蠢,那也是太笨拙和天真了。[《快乐的科学》]
科学对于人生问题,根本是无能为力的,科学的精神化,使得人成为物的奴隶。“所谓‘科学地’解释世界实在愚不可及,荒诞不经。本质机械的世界也必然是本质荒谬的世界。”科学所追求的客观和真实,其实是一种欺骗,因为“科学也是以某种信念为基础的,根本不存在‘没有假设’的科学。”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的目的便是审视科学:“当时我要抓住的是某种可怕而危险的东西……它就是科学本身的问题——科学第一次被视为成问题的、可疑的东西了。”他希望在艺术的基础上反思科学,他把《悲剧的诞生》“立足在艺术的基础上——因为科学问题不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被认识。”尼采对于科学以及理性主义的反思溯源到希腊哲学,尤其是苏格拉底那里。他认为苏格拉底就是后来强调理性、知识和科学思想的源头:“我们整个现代世界被困在亚历山大文化的网中,把具备最高知识能力、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视为理想,其原型和始祖便是苏格拉底。”尼采在对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悲剧精神和歌剧文化的分析中,深刻地解释了西方思想在苏格拉底处的转型,酒神精神的没落,歌剧文化取代悲剧精神,成为西方文化的一场“悲剧”,这导致了科学思想的强势,却恰恰是对真理和生存的遮蔽。
悲剧毁灭于道德的苏格拉底主义、辩证法、理论家的自满和乐观吗?……甚至科学,我们的科学——是的,全部科学,作为生命的象征来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全部科学向何处去,更糟的是,从何而来?怎么,科学精神也许只是对悲观主义的一种惧怕和逃避?对真理的一种巧妙的防卫?用道德术语说,是类似于怯懦和虚伪的东西?用非道德术语说,是一种机灵?哦,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莫非这便是你的秘密?[尼采著,周国平编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修订本)]
作为拯救之道,尼采提起了艺术,希望用艺术拯救人生。他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尼采哲学的核心在于“强力意志”,对于强力意志的解释就是以艺术为起端的。“如果说对于尼采来说,在把一切发生事件(Geschehen)都解释为强力意志这样一项任务的范围内,艺术具有一种突出的地位,那么,恰恰就在这里,关于真理的问题也必然起着一种首当其冲的重要作用。”艺术因为关涉人的存在而关涉真理,从而关涉人的生活本身,从而,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压抑下,艺术有了拯救的力量:“艺术,无非是艺术。它是生命的伟大可能性,是生命的伟大诱惑者,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

生活是陷阱,人是被抛进这个世界的。理性在言说着生活的合理性,但却掩盖不了生活的非理性与荒谬。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说:“小说不是作者的告白,而是在这已然成为陷阱的世界里探索人类的生活。”何以说世界是陷阱呢?昆德拉在另一处说:“生活是一个陷阱,关于这个,人们从来就知道:我们不曾提出来要求就被生了下来,被关在一个我们不曾选择并且注定要死去的躯体里。”
现代的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对理性主体进行了解构,在心理分析看来,人是受非理性支配的存在。“弗洛伊德说,他有两个基本的发现‘足以触怒全人类’。一是发现有意识的思维活动底部还有一个广阔得多的‘无意识’存在;二是发现‘性本能’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核心。”
在理性的思考中,在因果逻辑下,人类是严肃的,一本正经,但不知生活的趣味。在昆德拉看来,拉伯雷有一个被人忽视的创造,那就是发明了一个新词“扼结乐思忒”(agélaste),这一源自希腊语的词,意为“不笑的人,没有幽默感的人”。这种人不懂文学的智慧,生活的乐趣,令人害怕。这些人“从来不曾听到上帝的笑声,他们相信真理是清晰的,他们相信所有人的想法都应该相同,他们相信自己和心里所想的自己一模一样。然而人之所以成为个人,恰恰是因为他失去了对真理的确信以及其他人的一致共识。小说,是属于个人的想象天堂。在这片领土上,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安娜不是,卡列宁不是,在这里,所有人都有权力被人理解,安娜有,卡列宁也有。”小说有着与哲学不同的智慧和逻辑,“小说的智慧和哲学的智慧是不同的。小说并非诞生于理论的精神,而是诞生于幽默的精神。”
启蒙现代性让人类陷入到“存在的遗忘”之境遇之中,是文学承担了寻找存在的责任。“一门伟大的欧洲艺术因为塞万提斯而成形,而这艺术,正是对被遗忘的存在进行的探索。”在米兰·昆德拉看来,塞万提斯与笛卡尔同为现代的奠基者。塞万提斯将世界理解为一团模糊暧昧、相互矛盾的存在,在乎的是“关于不确定事物的智慧”(sagesse de l’incertitude),追求相对真理。

王宏超在工作坊上发言
人的价值观、欲望、情感、审美,是难以被启蒙理性进行简化的。由此,有了美学的现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来对启蒙现代性加以反思。“美学判断除了非功利的特质,还将理性、想象、直观、欲念融为一体,形成更为成熟的判断,因而不同于以理性为唯一特征的体系现代性。没有20世纪之前现代经典文学的美学积累,我们未必能明辨现代体系的问题所在,也就没有直逼要害的眼力。”
而文学的使命是什么?是去体现哲学思考,成为历史的片段吗?若是这样,那文学仅是一种传声筒而已。昆德拉传述赫尔曼·布洛赫的看法说:“发现那些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事,这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发现一件至今不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奥威尔的小说虽然优秀,但他的作品讲述的东西和一篇论文与评论中所言的内容是一致的,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事”,才是小说的使命所在。
小说的智慧与哲学的智慧不同,“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但是在简单快速响应的喧哗之中,这样的真理越来越少让人听见了,喧哗之声先于问题而行,并且拒斥了问题。对我们时代的精神来说,要么是安娜有理,要么是卡列宁有理,而塞万提斯却向我们诉说着知之不易,告诉我们真理是无从掌握的,可他老迈的智慧却看似笨重累赘又无用。”
小说作为这个世界的模型,奠基于人类事物的相对性与模糊暧昧,小说和极权的世界是互不相容的……这种不兼容,是本体论的(ontologique)。也就是说:根植于唯一真理的世界与模糊暧昧又相对的小说世界,是用全然不同的材料捏出来的。极权的真理排除相对性,排除怀疑,排除质疑,这真理与我称之为小说精神的东西也就永远无法和平共处。[《小说的艺术》]
黑格尔用理性来解释战争,“在荷马的作品里,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战争拥有十足清晰可辨的意义:人们为了美丽的海伦或为了俄罗斯而战。帅客和他的同袍走向前线,却不知为何而战,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此没有兴趣。”海德格尔把战争看作是“追求意志的意志”(volonté de volonté)。“为什么昨天的德国、今天的俄国想要统治世界?为了变得更富有?更幸福?不。这种力量的侵略性对此完全没有兴趣;没有动机;它只想追求它的意志;它就是纯粹的非理性。”

同哲学一样,“过去的小说家试图在奇异而混沌的生活材料里,抽出一条清晰、合理的线索;在这些小说家的透视法里头,可以合理解释的动机产生了行为,行为又引起了另一个行为。冒险则是一连串的行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清楚楚。”因果是简化世界的方式,真实的生活世界中,许多事情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但现代的文学还原了世界的非因果状态,“在那儿,因果之间的桥梁被摧毁,思想在无所事事的甜美自由里游荡。存在的诗意……它处在离题之中。它在无法计算的事物之中。它在因果关系的另一边。它sine ratione——是没有理由的。它在莱布尼茨的句子的另一边。”
在昆德拉看来,《安娜·卡列尼娜》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阐明了人类行为的无因果性、无法预知的甚至神秘的一面。”因果关系可以解释维特的自杀,但却无法解释安娜的自杀。
安娜去火车站迎接情人弗龙斯基,她乘坐火车到达了车站,被生活与情感折磨的安娜,总算摆脱了火车上遇到的一对虚伪聒噪的夫妇:
她在站台上停下来,竭力回想她干吗上这儿来,打算来干什么。她觉得以前能够办到的事,如今却变得如此难以揣摩,特别在这群吵闹得不让她安宁的、胡天胡地的人中间。[列夫·托尔斯泰著,高惠群、石国生译:《安娜·卡列尼娜》,下同。]
但安娜只是等到了弗龙斯基草草的一封信,他还没回来。安娜的内心又遭受了一次羞辱性的致命一击。
“不,我不会再让你折磨我了”,她暗自寻思,既不是吓唬车夫,也不是吓唬自己,而是吓唬那个使她受尽折磨的人。
她走在站台上,却不知道走向何处,感觉周围的人在议论她,“一些年轻人不让她安宁。”
“哦,天哪,我要到哪里去呀?”她这么想,一边沿站台越走越远。
安娜的心绪很乱,她何止不知道该走向哪里,她也不知道人生该走向何方。她像浮萍,难以把持命运的航线。正在这个极度迷茫的时刻:
蓦地,她想起她与弗龙斯基第一次相会那天被火车碾死的那个人,顿时明白,她该怎么做了。她迈着轻捷的脚步从水塔那里走下台阶,来到铁轨边,在行驶的列车的跟前站住了。
安娜的决定并非一系列理性思考的结果,尽管有迷茫、悲伤、屈辱、绝望,但这些现实中的事件似乎也不必然引她走上铁轨。昆德拉说:“她扑到火车底下,并非事先做了决定。应该说是这个决定抓住了安娜。”
安娜似乎也有理性的思考,“我要惩罚他,我要摆脱所有的人,要摆脱自己。”为惩罚别人而自杀,这是一个自杀的理由,但很难说是个合乎理性的理由。人很多时候似乎就如此受到非理性的情绪左右,所做出的决定比理性更坚定,或许也更合乎自我之期待。安娜在那一刻时归于了内心的平静:
这时候,类似游泳入水前的那种感觉攫住了她的内心,于是她画了十字架。画十字的习以为常的动作,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这时笼罩着她周围一切的那片黑暗突然划破了,她眼前刹那间又呈现出昔日生活全部美好、欢乐的光辉景象。
昆德拉的小说不再讲述“光荣、荣誉、勇气或神圣”(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说:“我总是为神圣、光荣、牺牲这些字眼的滥用感到难堪。”),他选择讲述轻、快、精确、形象和繁复,讲述孤独、无聊和虚无,他选择跟随了塞万提斯、塞缪尔·理查森、福楼拜、托尔斯泰、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在宗教、哲学、科学不能庇护人类之后,文学成了拯救人类精神的最后归宿。
文学,在摆脱了理性的钳制之后,不正是被用来拯救被遗忘的生活的原初意义吗?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