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田野与星空:访华侨大学吴小安教授
伴随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承担起日益重要的责任,加强对域外国家和地区全貌的综合性认知成为当今中国发展的战略性需求。2021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之后,学术界关于这一新兴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问题展开了热烈且深入的讨论。“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建构”曾入选“2022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近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文编辑部专访华侨大学讲席教授兼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吴小安教授介绍区域国别学相关研究及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吴小安教授
吴老师,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曾在北大工作了二十余年,在海外十几所大学也有十四年的研修工作经历,您能否谈谈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北大、加盟华侨大学?
吴小安:喔喔,该来的还是来了,谢谢。这个问题单刀直入,值得认真思考后,诚实地作答。不是周旋,请允许我先说句题外话,如果我依然在北大,我应该是不会接受采访的,因为这是我当初加盟北大时给自己定下的一条规矩。所以,中央电视台、《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国内外媒体,曾经多次提出采访邀请,我都一一婉拒了。
可以说,在我职业生涯中,北大无疑是最重要的。这不是客套,也不是煽情。在燕园,我从一个人都不认识,到逐渐融入、认同北大,这是学习的过程,也是适应、提升和改变的过程。北大高手云集,自由、宽松与包容,这是优点,也是压力和动力。当初决定离开北大,很突发奇想;潜意识里,部分地可能与我个人性格有关,主要想看看离开了北大之后,自己到底能不能生存下来。回过头看,这其实是很幼稚、很任性的,也是非常冒险的。
从2002年金秋十月进入北大开始,我始终很清醒、很自觉:心里一个声音说,不要躺平,不能躺平,无法躺平,需要不断努力学习、提升和进步;心里另一个声音则说,必须要继续向外走,设法让自己再动起来,同时要主动适应新环境,积极认同新单位。没人可请教,没人来指点;很幸运,在北大,我最终生存下来了。所以,真的感恩北大的同事们接纳了我,虽然我个人很性情,讲话很直率,好在自己始终善良。
燕园一个显著特征是,表面看,园里林子大,好像很野(wild),几十年前尤其如此,根本没有现在这么精致;未名湖很深,好像上海滩,反而比以前热闹喧嚣许多。骨子里,燕园却是博雅的,内心奔放,有文化、有胸襟,是有关怀的,是很讲理的。事实上,北大历史学系,确实对我一直很支持、很包容,印象中我记得好像没人给我穿过小鞋。所以,在北大,除了幸运,我始终是心怀感恩的。
在课堂上,我时常对学生说,你们在北大读了四年本科,理论上已经足够了,该学的可能基本都学到了;如果要继续读研,最好不要选择继续留在北大,而应该或赴海外,或者到国内其它985高校深造。只有离开了,才有超越;只有在新环境适应了,才能欣赏。如果非要留在北大读研不可,那么最好不要留在本系,最好转到外系读研。这是因为在本地四年该学的套路可能基本都熟悉了,不大可能有更大的、质的改变;到外系跨专业、跨院系则不同,适应了就是蜕变与大幅度提升。
那么,反过来,作为教师,自己该怎么定位与认知呢?这么说吧,我在北大工作已经二十年,工作环境和内容已经非常熟悉了,也应该比较舒服了。可问题是,我人还未老啊,心一直也很年轻的。所以,我相信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时候需要挑战自己,走出舒适区;是时候重新开始,重新出发。就这么简单,真的。熟悉我的师友都知道,这其实就是我的秉性。我人很正统,名实之间似乎很分裂;表面很开放,其实非常传统;虽然一直在追求安全感,但是从小就不安分,内心始终渴望新的环境、新的挑战、新的自己和新的梦想。
请您谈谈大学以来,对您的职业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的几所大学?最重要的几部代表作?以及最不变的原则信仰?
吴小安:哈哈,这些问题更是励志啊。对我职业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学有很多,如果举出三所,应该分别是厦门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北京大学。
厦门大学是我读本科、硕士时代和留校任教的大学。在那里,我求学和工作了前后9年整,充满了青春与生命激情的回忆。在厦大,我真的可以说是天马行空、自由任性了9年;在五老峰中、芙蓉湖畔、上弦场和厦大海滩,苦闷求索了9年;当然,也在图书馆和教室,默默认真读了9年书。那时候,人很穷,似乎只有成天泡图书馆读书这一条道,似乎成天追问“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等类似哈姆雷特式的青春苦闷与呻吟。不是不想谈恋爱,而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啥原因,没人瞧得上呗,连一眼都不给看的,丢脸啊。
幸运或不幸地,读书便成了青春苦闷的最终庇护。那时候啥书都看,小说、历史、哲学、诗歌、政治等等,都喜欢看,而且都没人管自己,而且任我自由自在地看。说来惭愧,对于上课,我是基本不做笔记的,也不追求考试高分的。如今回想起来,这点尤为难得,让我一直放飞,得以做自己。幸运的是,我心里始终有梦想,始终对于自己现状不满意,始终想通过读书深造改变自己。所以,我一直没有脱轨,没有偏离正道。应该是善良和本分拯救了我。如今回想起来,如果不是这些基本面对冲,还真不敢设想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是我作为访问学人和攻读博士学位的大学,对我的职业、人生意义深远,不仅因为我写了一本国际学界普遍认可的英文专著,而且因为自己整个人突然自发地变得开阔了,自觉地变得自觉和自律了。不知这是回归呢,还是幸运。也许正是在厦门大学9年不受约束、宽口径的读书与批评精神,让我在1993年9月赴阿姆斯特丹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立马获得了荷兰导师的青睐 。导师看了我的第一份读书报告后,认真对我说,放弃原来的研修计划,并为我专门量体裁身,重新制定了博士课题研究计划。
导师先给我开了十几本东南亚研究,特别是马来西亚研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殖民主义的专题著作,每2~3周精读一本书,然后定期到她家里讨论,之后再布置下一次读书作业。如此3-4个月高强度训练后,某一天导师说,你已经读了这么多的书了,每本书也写了读书报告,现在你该提交一篇10~15页左右论文,把所读书目主题,分门别类做个总结,指出相同与不同之处,好与不好在哪里,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知道,这又是非正式的“考试”。
三个星期后,我提交了一篇作业论文。导师看了,很满意,连说好,如同每次看了我的读书报告一样很开心。她亲切地对我说,已经给阿姆斯特丹大学写信了,大学校长办公室给予我4000荷兰盾(当时为2万人民币)研究经费,资助我去英国伦敦从事至少3周的研学活动。实际上,我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总共待了5周。我第一次对于做档案与图书馆研究有了一个摸底式的探索体验。然后,我再次回到阿姆斯特丹做图书馆研究,并用2个月撰写了博士研究申请。这个阶段的训练准备,我深刻感受到课题准备与可行性论证到底意味着什么。
博士研究期间,我分别赴伦敦3个月、马来西亚1整年、新加坡2次3个月、闽粤侨乡和耶鲁大学各2个月,从事田野调查。这令我懂得了课题研究系统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方法与原创性研究过程的实质意义。田野调查之后,我花了1年时间阅读整理与分析资料,形成论文第一稿,再之后又用1年时间文献阅读与整合提升。此两个阶段写作过程,令我进一步明白专业学人与非专业学人研究之间最大不同又是什么。
博士毕业后,我分别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做了2年博士后和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6个月的客座研究,期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修改与出版。这两份研修经历最刻骨铭心的感受是:其一,通过无情大幅砍掉自己博士论文的百分之六十,自己超越了作为学生的过去,明白了国际高水平学术专著与博士论文的显著区别。其二,通过博士论文出版,迅速走出了博士研究的阴影,迅速启动了寻找新研究方向的学术探索和及早迈入新境地的耕耘播种。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职业成长生涯中,这其实是学生到学人成长的必经蜕变,虽然过程很长、很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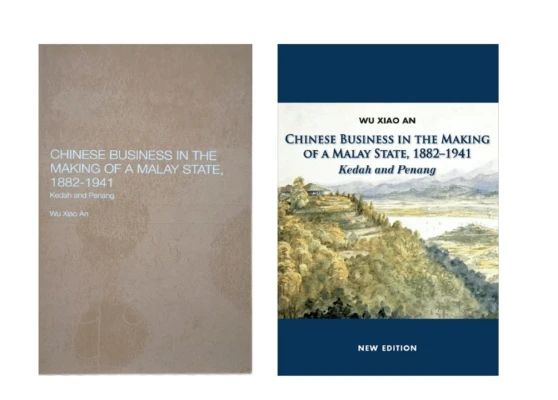
吴小安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的专著
第三所对于我影响最大的大学,无疑属于北京大学了,不仅因为北大是中国著名学府,也不仅因为我写了一本中文代表作《区域与国别之间》(已经第四印)。对我而言,入职北大是从零开始的,也是文化再适应与自我蜕变。这是个人职业转换轨道、成家立业与中国社会经济急剧转型高度重叠的时期。对内,北大对于我自身成长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外,北大对于我继续尝试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会。在北大近20年期间,我分别受邀赴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中国台湾和澳门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十几所大学客座研究,如此才让自己不至于原地踏步、停滞不前。如今回想起来,北大对于我的学术成长是非常有益的,幸运的同时,当然也一直是心怀感恩的。
至于最不变的原则信仰,普世的大道理应该是没有的。如果一定要回答,那么我个人深切体验是:只有认真地做自己、做好自己,只有专业地做事情、做好事情,只有与机构、专业、国家和世界与时俱进,只有养成终身学习的态度、终身学习的能力和终身求新求变的准备,或许我们会变得相对理性、平和与富有好奇心,才不会被时代被动地抛卷,或者不会让自己温水地内卷,或者不会让自己温柔地被内卷。
您最近出版了几部在学界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如诗集《燕寨集》《学术志:田野、星空与飞燕》《学人记:大地的思想与行走的历史》,等等。通常这种类型的著作都是学者退休之后的系列总结,而您则不同,是在正当盛年时,如同下饺子般集中出版的,令人有些不可思议。您能否谈谈上述这些著作与作为职业学人到底有什么关联?
吴小安:哈哈,这些问题很有意思。这些彼此之间是相通的、共生的,而不是无关的和点缀的,更不是不误正业的。不过,彼此之间的边界与主次到底在哪里、尺度怎么把握,却是每一个学人需要时刻保持高度清醒与自觉的。
先说诗与诗集。我始终相信,除了承受苦难,人生的意义应该是为了追求欢乐与尽情歌唱;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是自己热爱的诗人,尤其是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难得的是,步入中老年之后,有人依然葆有一颗诗心。与大家一样,大学和研究生时代,我曾经跃跃欲试写过点滴的诗;留校任教后,我发誓这辈子不再写诗了,而且这份誓言谨守了28年。有意思的是,从2018年开始,我又陆陆续续写诗,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我被迫再次发誓,把自己的诗歌结集出版后,从此封笔,不再写诗。
有意思的是,在加盟华侨大学后大半年的日子里,我还是再次失信了,不争气地继续写了20多首诗。理性审视,其实我始终是以学人身份写诗的,而不是以诗人身份歌唱的。我从来不愿意自己成为诗人,实际上始终在与自己写诗的冲动做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说诗歌对于我有特别意义,那么可能更多地在于赋能、救赎和升腾。或者说,葆有一颗诗心,令自己始终守护着作为一位纯粹学人的边界,在某些特别的日子里,尽量让自己不至于沉沦,至少不能沉沦太久;不至于庸俗,至少不能过于庸俗。生命里,我需要这种感觉。
再说《学术志:田野、星空与飞燕》和《学人记:大地的思想与行走的历史》。虽然分别由科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出版,实际上这是姊妹篇构成一套书。前者由《田野集》、《星空集》和《飞燕集》构成,后者则包括《大地的思想集》和《历史的文化集》。
为什么是《田野集》?小时候,我对田野非常熟悉,捡粪、放牛、拾柴火、淘猪菜等各种农活儿都干过,主要的活动空间就是田间与山野;当年考大学就是为了能够跳出农村,摆脱田地的束缚。上大学后,青春年少,不免苦闷。求索中,读古典神话时,发现大地之子安泰之所以力大无比,竟然是因为始终脚踏实地、拥抱大地;我又开始自省,对大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国外读博士,做博士论文一定要到海外研究场域和相关的档案馆,实地调查系统收集第一手资料,名曰“田野调查”,对田野进一步又有了远方的、异国他乡的和科学神圣的维度。
我的田野调查为期两年,包括不同国家和城市的《田野集》短篇札记很杂,长篇札记都是1200—1500字,是最不容易整理的,应该都是有专业价值的记录,也是时代的历史记录。记录既是对研究进程的回顾与审视,又是对生活与远方的观照和想念,还有对跨国、跨文化的体验与反思。
田野与星空之间是飞燕,之所以命名《星空集》,既是因为《田野集》,又是因为《飞燕集》。《飞燕集》还有一个私人的原因。小时候,我就喜欢燕子;大学时,读泰戈尔《飞鸟集》很入迷;在燕园待久了,便越发喜欢燕子了;离开燕园后,愈发想念了。所以,便是《飞燕集》了。
为什么是《大地的思想集》与《历史的文化集》,则更简单:其一,对学人而言,我始终相信,本真与纯粹,不只是性格与底蕴,而且是源泉和资质,孕育深刻丰富和无限可能性的基因和动力。其二,历史与文化的关系,我是用了很长时间才开始拥有些许清醒和自觉的。很长时间以来,如同很多学人一样,对我而言,历史就是历史,是与其他社会科学是不搭界的,遑论与文化的关联;反之亦然。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智识误区,无辜限制和扼杀了很多学人的灵性与创造力。
最近您率领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代表团出访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三个国家,请问您可否分享一下这次特别出访的感受?我们还得知,您即将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项目客座,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新使命双重视角,请谈谈您的个人愿景?
吴小安:第一个最直观、最深刻的感受是世界变了,变得与5年前我在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荷兰等地客座时,明显不一样了,而且很难逆转。在很大程度上,百年大变局明显在加速演进,局部国家和地区间的冲突和战争牵动了全球政治经济与人类社会神经。这是结构性层面。人民普遍受伤,社会更加撕裂,民粹主义与社会焦虑感、距离感与未来不确定性,等等,在日常生活交往中,感受很深切。
另外一个最深刻、最强烈的感受是中国更迫切需要深化全面改革开放,特别是官方层面和民间层面并举的开放交流,特别是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层面的开放交流。对于我个人而言,很多朋友都已经退休或者提前退休了,以前建立的长久合作交流关系需要重新开始。正是上述大的背景考虑,让我决定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客座7个月,不仅因为那里的东南亚研究是全世界最顶尖的,也不仅因为我个人近几年透支厉害,自己需要赋能充电。当然,导致赴康奈尔大学客座访问还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其一,2023年,我受邀为“光启通识文丛”写一部小书,并且已经与商务印书馆签约了,必须按时交稿,需要找时间静下心来闭关读书写作,先部分地完成作业。其二,决定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客座是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只是25年前在耶鲁大学待了2个月,相比欧洲读博研究(荷兰、英国)、东南亚(至少6年多)、日本(约2年)和大洋洲(新西兰2次,6个月)等大学研究经历相比,无疑是非常欠缺的。我需要弥补与世界最重要的智识板块直接交流互动的空缺。
作为全球中国的新一代学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区域国别学人,您认为最基本的共同点是什么?最大的不同点又是什么?
吴小安:中国式现代化是全球中国的因,全球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果;反之亦然,两者相辅相成,都是当代中国历史、也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历史变迁。我相信,作为全球中国的新一代学人,包括文科生和理工科生,应该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伟大经历者和生力军。专门地,全球中国的学人,则指新时代研究中国的新一代学人,不仅是为中国而研究中国的中国学人,而且是为世界而研究中国的新一代中国学人,同时还包括研究中国的外国学人。换言之,全球中国的新一代学人,学科的边界更加交叉与外延拓展,学人的视野更加多元和国际化,研究的内涵更加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区域国别学人则是专门研究世界区域和外部国家的专业人士,既是因应全球中国发展的战略需要,又是因应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区域国别的学人,不仅需要立足于某单一学科的厚实基础之上,而且需要拥有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关怀;不仅需要立足于国别与专题厚实个案基础之上,而且需要拥有区域整体框架和全球视野的理论自觉与人文关怀。特别地,区域国别的中国学人,不能为区域国别而区域国别,同时需要立足中国、需要吸收中国学的学术传统进行区域国别研究。
如果非要寻找全球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历程之间的最鲜明特性,或许可以简要归纳为四个特性:即时代性、中国性、现代性与全球性,或者说是这些特征要素的融合和融通。全球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共同的鲜明特性则是中国的特色元素,现代化是这样,全球中国也是这样。
最后,您能否给读者介绍一下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院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里的特色优势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结合起来研究?
吴小安:海外有6000万华侨华人,华侨华人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独特视角。华侨大学是全球唯一一所以华侨命名的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是华侨大学“十四五规划”重点打造的“3+1”特色优势学科中的“+1”(机械工程、化工、工商管理是华侨大学最有名的三个学科)。研究院拥有全球中国与华侨华人、亚太区域与华侨华人、比较移民与华侨华人、侨乡文化与华侨华人等六大研究方向群,一座800平米专业图书馆、一座600平米的华侨文物馆、一个国务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福建基地以及一份《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目前,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有教职工30余人。预计到2030年前后,我院专职科研人员将达到50~55人。
研究院“强调一个结合、两个关联的辩证统一”。什么是一个结合?顾名思义,就是华侨华人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什么叫两个关联?其一,如果做华侨华人研究,一定要关联区域国别的大框架、大背景。其二,如果做区域国别研究,一定要关联华侨华人这个专门主题。
研究院曾分别受邀为《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和《清华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的“区域国别”专栏组稿4篇和5篇论文,学界反响不错。2024年7月1日,得益于自己是《剑桥全球移民史》第二卷篇章作者的天时地利优势,研究院牵头与商务印书馆签署了《剑桥全球移民史》英文版两卷本(2023)中文翻译出版合同。这是继20年前我主持的两卷本大型翻译合作项目《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商务印书馆,2010年;汉译世界名著版,2013年)之后,由我再次领衔组织的重大学术翻译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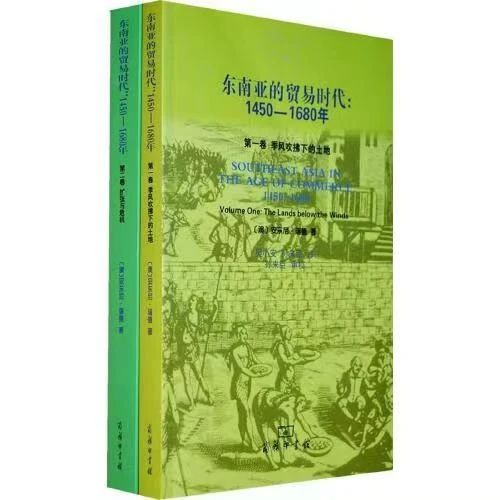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中译本
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研究院对内分别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签署了长期合作交流协议,对外分别与马来亚大学人文暨社会科学院、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正式签署了研究交流合作协议,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相关院系达成了未来加强深度合作交流的意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