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刘清扬评《卡苏蓬先生的世界》|英国的“神话学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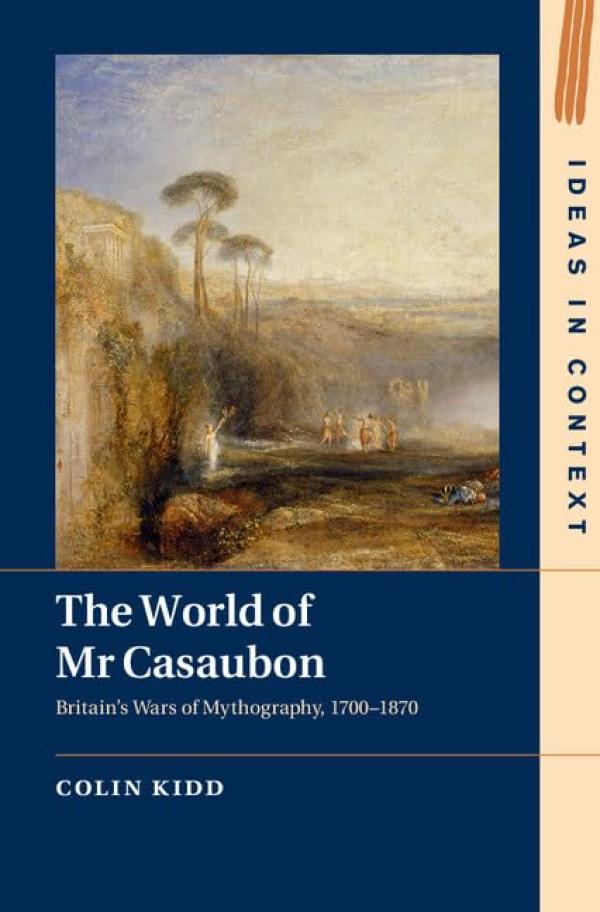
Colin Kidd, The World of Mr Casaubon: Britain’s Wars of Mythography, 1700-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2016, 248pp
从文学作品到思想史:乔治·艾略特的宗教学背景
我们很少有幸能够接触到一个由小说(或者其他文学体裁)引出的思想史作品,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科林·基德(Colin Kidd)的这本《卡苏蓬先生的世界:英国神话战争,1700-1870》(Colin Kidd, The World of Mr Cassaubon: Britain’s Wars of Mythography, 1700-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便是其中一例。这部思想史作品由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80)1874年出版的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引入。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牧师卡苏蓬先生(Edward Casaubon)意以通过历史考据完成一部伟大作品,用于解释古往今来世界上所有神话传说的原理,被称作“一切神话的解”(the key to all mythologies)。然而事与愿违,偏执古怪的脾气以及慵懒和关注琐碎细节的工作态度,让他疏于动笔,最后成为一部未完成的手稿。
是否有人会接续卡苏蓬先生的未竟事业,我们不得而知,但基德在他的作品中告诉我们,这一手稿所要完成的事业——通过考察世界上流传神话(包括亚伯拉罕宗教的创世神话),找出一个共同存在的神话叙事从而构建一个新的解释系统——并非小说作者的异想天开,而来自于艾略特生活的智识背景。尽管艾略特的小说读者可能认为她无意呈现卡苏蓬先生神话史所在的学术争论漩涡之中:在他们眼中,刻画卡苏蓬先生的迂腐与穷酸的文学形象应当是艾略特小说的写作意图。那么,基德是怎么在文学形象上建立与作者艾略特所在时期的知识史、神话史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究这些神话叙事和解释系统是如何在启蒙运动——这一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宗教信仰瓦解,科学精神发扬的时代——产生并发展的呢?
在本书中,基德首先讲到了自己作为思想史学家,意图重构神话学争论展示启蒙运动时期这一争论的本质。首先,他意图考察艾略特的智识背景,并与其1872年所著的这部《米德尔马契》所联系起来,从而发掘艾略特意图通过小说来呈现的宗教哲学界中的辩论。玛丽安·埃文斯(艾略特的本名)成长于一个圣公会低派家庭,宗教家庭背景与激进神学的社会背景使她能够接触到利用神话学的基督教护教学说(apologetics)。1846年,埃文斯翻译了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 1808-74)的《耶稣传》,1854年又翻译了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72)的《基督教的本质》(中文学界所熟知的青年马克思的重要思想来源)。这些元素反映在了年轻的卡苏蓬先生的侄子威尔·拉迪斯劳身上(Will Ladislaw):因此基德认为,艾略特在描绘拉迪斯劳时就在描绘年轻的自己(pp.20-22)——有意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里艾略特刻画了一个有激进思想的年轻男子作为自己的文学代表形象,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性别研究的有趣课题。
关于卡苏蓬先生本人,基德发现了艾略特的知识来源中一些作品也为她提供了灵感。最直接的灵感在于“卡苏蓬”这一名字同名的逃往英国的胡格诺人文主义者以撒·卡苏蓬(Isaac Casaubon, 1559-1614)。讽刺的是(多半是艾略特有意为之),这位卡苏蓬先生所持的观点与小说中的卡苏蓬牧师完全不同:以撒·卡苏蓬在与天主教学者的辩论中,用缜密的文本批判方法指出,旧约时代埃及异教中关于基督降临的线索不过是早期被柏拉图影响的基督教学者所虚构伪造的(pp.9-10)。由此,基德通过第一章对艾略特智识背景的重构,揭示了她借着对文学形象的刻画(卡苏蓬、拉迪斯劳等人)展现了自己对当时的宗教哲学辩论图景的理解:德意志人本主义在传入英国后获得了许多激进青年拥趸,强调耶稣基督的神迹以及其代表的神性只不过是一种神话传说,努力将耶稣的人格进行还原,同时也指出神话的本质是一种出于人们精神需求的自然崇拜。这种理论挑战了圣公会神职学者们的护教学道统,但是英国护教学试图有效地内化这种挑战,在承认宗教的自然崇拜性质的同时,指出了这些原始宗教实际揭示了基督教神学本身的真理,以及这些异教最终预表基督福音的降临。
卡苏蓬先生的蓝图:早期现代异教神话中的“一神论”记忆
然而,基德可能有意限缩探讨范围:因为本书的主题仍然是英国的“神话学战争”。从第二章开始,基德更多讨论了十七世纪中后叶到十八世纪初英国的神话学研究,以及这些研究是如何构造不同叙事而完全融入教派争论中的:新教派别攻击天主教无法脱胎于罗马异教传统就是很好的例证(p.35)。根据他的观察,无论是我们所熟知的彼得伯勒主教、思想家坎伯兰(Richard Cumberland, 1631/32-1718,参见Jon Parkin, Scienc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Restoration England,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99, p.14),还是近一个世纪后的会众派(Congregationalist)神学家乔治·瑞德福德(George Redford, 1785-1860),他们都意图通过考察巴比伦、腓尼基、罗马等异教神话学,清除其中“奇幻与荒谬的添油加醋,并神话式幻想”(fabulous and absurd additions, or mythological fancies),得到一个关于真实的原始历史的可靠描述:例如印证了大洪水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真实存在,因为这一事件的叙述体现了各个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共同历史记忆(pp.46-48)。但如何解释这种宗教与民族之间历史记忆的不同呢?教会学者们注意到了大洪水之后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生儿育女分散到世界各地之后,尤其是巴别塔的毁灭之后,各个原始民族的语言出现混乱,大洪水前的先祖时代的历史记忆在描述上因此也出现了差异,先祖挪亚的一神信仰也因此经过了“宗教的腐败”,逐渐演变成各种多神教或拜物教(pp.32-34; 209)。
因此,为了解释各种神话版本的变异,一种“由原始一神教堕落为多神信仰”宗教-神话史叙事形成了。但是以下问题有待考察:这种叙事如何融汇不同民族中间流传的不同版本的创世神话呢?在这些神话式的历史叙述中,如何能够从不同的多神教和拜物教的仪文中观察到先祖一神教的影子呢?于是,基督教护教论中(apologetics)发展了一个神话史研究原则,被称为“双重教义”(double doctrine):神话史学家假设多神信仰的外表下隐藏着“隐微”(esoteric)的哲学思辨,这种思辨指向一种一神信仰或者反映了原始的先祖一神论残余(p.36)。对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解读,另一些教会学者则批判了这佐证圣经历史真实性的方法。即使像一些人所推测的那样,如同人类理性的普世性可以获得神所赐予的自然法知识一样,神学真理不仅会启示给犹太人与之后的基督徒,也会启示给多神信仰的外邦人;但是,正如著名的苏格兰长老会牧师查莫斯(Thomas Chalmers, 1780-1847)所认为的,新约中所记载的外邦人抛弃偶像崇拜并信仰基督福音的真理这一事实本身告诉我们,一切在异教神学中寻求逻辑上与基督教真理的一致性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没有必要的(pp.62; 64):因为基督教真理是自足与自明的,我们不需要在多神教和拜物教神话学中的“类真理”(quasi-truth)寻找基督教真理的佐证。因此也就不可能对异教神话学进行“去伪存真”的工作:一切看似有联系的多神教预表也只不过是“时间错置”的(anachronistic)牵强附会(p.71)。
这种对“一切神话的解”的质疑并不局限于在教会内部,基德似乎更感兴趣的是,启蒙运动时一些激进的宗教怀疑论者对这种利用罗马异教神话辩护基督教真理做法的批判。随着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在十八世纪,罗马历史中重大事件、神话传说(尤其是荷马史诗)的书写时间可以被确定,甚至神话传说中所记载的故事(特洛伊战争),也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天文学方法、人口学推测方法等)被确证为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6/27)就是这种通过科学方法研究神话叙事历史性的典型代表(pp.81-82)。由此,对古罗马异教的讨论占据了启蒙运动时期关于神话学与基督教圣经历史关系的辩论。
在这个辩论中,护教学者(以威廉·沃波顿William Warburton, 1698-1779 为代表)坚持“双重教义”原则,强调对罗马神话进行隐微解读,挖掘其中的理性主义哲学成分从而证明与先祖到摩西的一神论、基督教真理之间的逻辑一贯:虽然罗马异教立法者以来世报应确定法律的权威和神性,由此与摩西不同;但是这些立法者与摩西均通过秘传的方式保存了一神教理性主义真理。同时,以安东尼·科林斯(Anthony Collins, 1676-1729)及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 1670-1722)等人为代表的自然神论者与“自由思想家”(freethinkers)将罗马多神信仰被赋予了新的理性意义,认为努马(Numa Pompilius)与西塞罗等政治家所理解的公民宗教作用隐藏着一种巩固公民政府,压制理性发声的政治意义。由于政治神学(而权威从来认为罗马多神宗教是一种统治工具)通过祭司的权威压迫一切哲学思辨对真理的渴求,哲学家只能发展一种隐微的哲学书写方式传递其教诲(pp.87-89; 关于古典时代的隐微写作,参见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8)。罗马神话的政治性和现实隐喻性,由此证明了这些神话的传承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正如牛顿所确证的那样。另一方面,科尼尔斯·米德尔顿(Conyers Middleton, 1683-1750)以及吉本(Edward Gibbon, 1737-94)等人则认为基督教传入罗马后的发展则是完全挪用了罗马异教文化,与犹太-基督教的一神论脱节,甚至天主教的敬拜与仪式传统都完完全全复制了罗马异教(p.94; 关于沃波顿与米德尔顿的辩论,参见Tim Stuart-Buttle, From Moral Theology to Moral Philosophy: Cicero and Visions of Humanity from Locke to Hu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Chapter 4)。这种对天主教的攻击广泛地被用于新教学者的作品之中。
然而,基德认为,米德尔顿似乎逐渐走向了一个更极端的地步,质疑宗教改革能够从受到罗马异教影响的天主教那里恢复一个纯粹理性与哲学的基督宗教的努力(p.95)。面对同一本马可(马尔谷)福音,新教神学家同样要面临这样的问题:耶稣驱鬼的事迹是靠着神的儿子的权柄,赶走现实存在的堕落的和敌对的属灵实体?这些属灵实体是否就是多神崇拜中的各个神灵?还是说,他神奇地治好了仅仅患精神病的病人?这样的象征意味不能说不对基督教神学要义构成了挑战(pp.98-99)。就连我们所熟知的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 1711-76),也参与了批判沃波顿发掘异教神话中的正统神学的努力:异教产生的社会背景下生活的人们缺乏一种理性官能对自然观察中的种种现象进行解释,当然也就因着恐惧屈服于一种多神信仰(p.106)。这似乎也被牛顿的“科学”结论所印证,同时也见证了一种与先前坎伯兰等人不同的神话-宗教史叙事:古老的多神异教被断定为早于犹太-基督教统治着人们的信仰生活,其后逐渐被一神论宗教所取代。
东方文化中的犹太-基督教线索:启蒙运动中的宗教学论战
在关注到了神话史被护教学家与启蒙时代对这种神话学滥用的批判后,基德在第四章进行了案例分析。无论艾略特是否有意参考,雅各·布莱恩特(Jacob Bryant, 1715-1804)的《新系统》(A New System, or an Analysis of Ancient Mythology)都可以被视作是卡苏蓬先生的一种原型。作为一个对词源学略知一二的学者,布莱恩特不亚于同时期的“现代”学者:用自己所熟知的文化背景把握一些十八世纪的文化新发现,包括近东、印度及中国的神话故事。基德认为,布莱恩特所说的“希腊文化的错误中残存着一致性”就是卡苏蓬所想要找到的“一切神话的解”的原型(p.116)。作为布莱恩特的忠实读者(自称读过三遍《新系统》一书),威廉·琼斯(Sir William Jones, 1746-94)虽然批判了布莱恩特过于依赖以考据兴趣和语义学附会猜测为基础的还原主义,但是他的词源学研究仍然认同布莱恩特的某些结论,“印欧文化”,包括在神话学和语义学存留相似源头的古希腊与古雅利安文化——被认为是含米特文化——则发源于挪亚的二儿子含,而并非发源于三儿子雅弗。但是在琼斯与他的门徒弗朗西斯·维尔福德(Francis Wilford, 1761-1822)所进行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在寻找印度教神话中关于洪水与挪亚方舟的线索时,一位班智达(pandit)将挪亚(对应印度教中的Satyavrata)与他的三个儿子一样的人物附会入《莲花往事书》(Padma Purana)中,被称为Sherma、Charma和Jyapeti,于是造成的假象成功的欺骗了维尔福德(pp.122-23)。
但是这种东方主义考据并没有停留在象牙塔中,基德认为,这些宗教研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衍生了实际政治意义。第五章,基德讨论了和英国政治论战中有着更密切关系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基督教批判,沃尔尼(Constantin François de Chassebœuf, Comte de Volney, 1757-1820)、杜普伊(Charles-François Dupuis, 1742-1809)等人的作品传入英国后与本地的怀疑论激进派相结合,形成了一股摧毁政治-宗教既有建制的力量。1793年至1822年间,沃尔尼的《大毁灭》一书(The Ruins: or a Survey of the Revolutions of Empires)就有十一种英语翻译版本出版,甚至包括威尔士语版本。同时圣公会高派的教士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激进潮流,批评宗教激进派在沃尔尼的影响下发展出渎神倾向,并煽动一些未受教育的人们接受他们的激进观点(p.147)。
那么,沃尔尼等“启蒙先贤”们是怎么阐述他的激进观点的呢?先于沃尔尼与杜普伊,伏尔泰(1694-1778)已经质疑了旧约历史的古早性:既然迦勒底与古中国文明都已被批判历史学家证明早于犹太信史文明,那么这些东方古代文明,由于所处时间更加接近创世年代,记载的真实性就应当高于犹太教文献。不仅如此,古代中国的传说记载,作为纯粹用作道德教化的文本,一些反直觉的传说更少一些,由此更接近记载真实的历史情况(p.134)。杜普伊则认为整部圣经记载的历史故事都充斥着对古近东神话的借鉴甚至抄袭。如果说有一种“一切神话的解”,那么就是古人对天象奇妙的兴趣以及对自然现象的崇拜。由此衍生出了各种不同解释的版本,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的本体来源于太阳,而基督教本身来源于太阳崇拜;福音书中记载的故事,甚至从旧约伊甸园的神话开始,莫过于喻示着天体星象的变化和生命周期。三位一体也有其神话根源:印度教崇拜的三大神梵天、毗湿奴、湿婆,作为创造者、保护者和毁灭者,对应基督教上帝的三个位格(pp.139-40)。沃尔尼则提供了更多证据证明祆教、佛教等原始宗教对基督教的直接影响。
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旧约先知书中,先知被上帝托梦一样,沃尔尼在《大毁灭》一书中也称帕西人(Parsees, 帕西人指的是阿拉伯征服后,移民至南亚次大陆上的信奉祆教的波斯人)大祭司在梦中声称上帝所传给摩西的与犹太人被掳归回后犹太教神学体系的建立没有关系,因为作为居鲁士大帝所释放的民族,犹太人在“恢复”摩西宗教的过程中,必定带有波斯原始宗教,也就是祆教的印记(pp.142-43)。对这些法国自然神论与怀疑论者的批判,英国的高派神学家法柏尔(George Stanley Faber, 1773-1854)仍然站在“补充证据”(corroborative evidence)的角度进行反击,认为如果没有一种大洪水之前先祖时期的共同记忆,自然神论者所认定的基督教比附借鉴的元素也无法产生:也就是说,在亚当与挪亚的隐喻之中,三位一体的奥秘就已经隐藏,逐渐变化成各种异教形式(pp.163-64)。这样,一个神话史问题逐渐回归到了一个“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pp.148; 151):而护教学者并未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并坚持一种容易被人认为是“时间错置”的隐微主义观点。
现代人类学的开端:考古发现与神话学叙事转变
当神话学问题成为一个考据历史真实存在的问题时,更多的可信证据的发掘并断定其年代便成了必要研究过程:十九世纪人类学与考古学新发现补充了这样的证据。同时,围绕着上述“鸡-蛋问题”的神话学研究并没有止息。十八世纪的人类学猜想已经在杜普伊、沃尔尼等自然神论者的批判中可见一斑:十八世纪的人类学探究宗教如何产生于人类社会,并给出了来源于对自然界未知现象的崇拜的结论,而发展健全和完善的现代人类学学科则分享这一问题意识。布莱恩特已经为这一人类学探究提供了线索,发现了挪亚式人物和大洪水传说普遍出现于近东神话中,但是并没有解决人类学对宗教起源探究的本身问题:布莱恩特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当然拒绝给予一个非宗教解释。十九世纪的神话学家们(包括法柏尔)通过调查更多族群的神话传说(包括毛利人和托克劳人),得出了更精确的人类学结论:原始族群中的洪水传说都指向了他们对一种“鱼神”的崇拜,例如在非利士人的大衮(Dagon),甚至是挪亚也被幻化成了一个生活于大水之中“半人半神”的崇拜对象(p.178)。有趣的是,这里法柏尔仍然沿用圣经旧约中的说法将大衮视作非利士人的神。然而由于一些近东考古成果的最近发现,学界更加相信大衮是叙利亚地区(也就是亚兰人)的主神。
基德注意到,除了“鱼神”之外,十九世纪人类学发现原始宗教中共同“古蛇崇拜”元素更能融入护教学叙事中(pp.180-81)。作为一个令原始人类恐惧的对象,蛇的崇拜代表了人从与独一上帝之间亲密关系的生活来到了堕落状态(Fall):正如乔治·赫尔顿(George Holden, 1783-1865)所惊叹的那样:“人类竟然能够对如此可憎与令人反胃的生物致以对神明一样的崇拜,这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蛇是如此的在人类群体中招致反感,以至于我们仅仅能在一些传统描述中发现它在人类堕落中所起的工具性作用;但事实上,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原始文明都对其进行过宗教崇拜!”(p.187,转引自George Holden, A Dissertation on the fall of man, London, 1823, p.160)对护教学家来说,这些证据印证着基督教的“堕落”神学叙事——世界宗教都分享着一种关于“原罪”的记忆。
反过来说,既然所有人类文明的神话都分享着同样的“古蛇崇拜”以及“鱼神崇拜”的话,异教崇拜才是所有人类信仰生活的原始形态。由此,一种脱离基督教护教学的人类学研究也就在十九世纪应运而生了。在观察到古印度的眼镜蛇崇拜与古埃及的蝮蛇崇拜后,托马斯·因曼(Thomas Inman,1820-1876)猜测到蛇,这一遇到突发事件时挺身昂首的动物,可能是原始文化中“菲勒斯”的代表,表现了这些族群对男性生殖活动的崇拜。自此,包括所有异教和基督教中的神话隐喻都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原始人类的生殖崇拜:新近发现的柱状图腾外表不但是原始部族对先祖形象的想象,更是一种对生生不息的部落传承的一种崇拜;蛇、方舟等物象,甚至三位一体这一被基督教认为不可理解的奥秘,都被用一种生殖崇拜的角度解释——无论是圣父、圣子、圣灵还是梵天、毗湿奴、湿婆形象都仅仅是对“菲勒斯与两个附件”的引申(pp.197-98)。这样一种“多神论起源说”便被给出了一个世俗人类学的科学解释,也逐渐使基督教护教学的“一神论起源说”黯然失色:圣经,和其他多深宗教文本一样,本身被接受并诠释为一种神话学叙事。同时,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发展以及丰富证据成果,增进了人类学的宗教神话理论的解释力和可信度。于是,基德展现了一个人类学科学,由十九世纪从神学发端,为了讨论“一切神话的解”的问题逐渐“世俗化”的思想图景(pp.200; 207; 220)。
后记: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理性和宗教?
我们所生活的当今世界中,“多神论还是一神论才是人类信仰生活的原初形式”这一问题似乎已经淡出了公共讨论空间。接受了“理性破除宗教迷信”的这一主流历史叙事后,宗教作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或许已经抽象地等同于那一切唤起我们内心理想的意识。在理解了启蒙运动时学者们关于历史与神话叙事和理性关系的争论,我们或许会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这一教科书式概念产生新的体会。
传统的教科书观点认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见证了科学理性代替宗教迷信,成为了获取真理知识的必经之路。“对理性的崇拜”似乎意味着对一切关乎人类历史的创世神话进行摈弃。这是传统的“辉格解释”对早期现代,尤其是十八世纪思想发展的反思结论(对“辉格史观”的经典批判,参见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然而,“辉格史观”不仅代表一种历史观点,还代表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也被应用于神话学研究上。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认为,辉格思想史通常在发现了一个历史时期下的“不合理的”材料或一段叙事,也无法寻找出一种适用于当时书写语境的“合理性标准”后,将这一发现拒斥为非理性的、由理性堕落的、原始的与未经修饰的历史材料而丢弃在一边(Quentin Skinner, “Interpretation, Rationality, and Truth” in Vision of Politics, Vol. 1, Cambridge, 2002, p.38)。这样的“辉格方法”则成为了十八世纪一些神话研究学者本身所采取的——尽管就像前文所述,他们的再诠释也存在着政治行动的意图:破坏教会中高派的主导地位,并与之争夺教会职位等。像我们在米德尔顿与休谟的论点中可以看到,在观察到原始神话中诸多违反自然规律与理性的记载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原始先民没有理性能力解释自然现象,或者反思和质疑那些他们所听到的神话传说(pp.105-107):这样我们就在神话与宗教史研究领域中发现了“辉格方法”。而这种宗教史的研究方法,正是理性在启蒙时期发现了自身的最好例证。
但是,作为历史学家发现了神话史中的非理性从而在思想行动上拒斥这种非理性,仅仅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方面,无法还原十八世纪纷繁复杂的思想潮流如何由具体的论战和不同动机与意图呈现:基德主要关注的,则是布莱恩特等人所代表的一种思想潮流,即出于维护基督教义的真理性和权威性,对神话书写和流传史做出再诠释。这种思想潮流是在论证与对话中发展和实现的。正是通过从看似非理性的,不符合十八世纪学界共识甚至生活常识的一些迷信观念中,寻求一种可以和这些当代的理性共识对话的观念,护教派神学家找到了其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桥梁。如同沃波顿对西塞罗的讨论那样,这种看似非理性与逻辑矛盾的情况,则通过“隐微写作”的理论使其合理化了起来。而沃波顿寻求这种古典时期的“秘传元素”,将其视作永恒理性以此佐证基督教思想与古典理性的联系,正与卡苏蓬式护教学的论证策略不谋而合。
基德试图告诉我们,卡苏蓬先生所感兴趣的领域正是现代人类学在启蒙运动中的形态——而这些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则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的光辉创造:研究各个民族不同版本的创世神话中的共同之处,以推断这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同研究对观福音之间书写借鉴的关系一样,从而摘取这些原始宗教中所秘传的理性与一神论成分。因此,启蒙时期同时见证了“理性主义”是如何从反思与分析远古神话传说中诞生的,也见证了护教神学家这一相对“保守”的阶层,是如何通过这些文本训练达到现实政治要求的。
对“理性宗教”的追求造就了这样两批人:其中一批人成了后世所公认的“理性主义”的旗手;而另一部分人,在发现人类学批判方法摆脱了现实的护教意图的控制后,便只得通过回归不断重构神话史叙事,来为基督教护教论服务。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