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对话丁帆(上):“风景”会戴着历史审判者的眼镜“看人”
政邦茶座>>
一直想邀请著名学者丁帆老师做客政邦茶座,理由很简单,他既是学者、作家,更是批评家、思想家,有很多问题希望与他一起“吹毛求疵”地聊聊。
丁帆老师刚刚出版的《消逝的风景》,自称是“最满意的一本”,让人既看见“城市的角色”,更感受到“人文的重量”。而由他主编的《江苏新文学史》,12编30卷约1000万字,在日前开幕的第3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亮相,被称为“绝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学术工程,也绝不意味着一个省份的文学研究,它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中国新文学历史的一个样本,一个缩影,一个投影,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半壁江山。”
政邦茶座嘉宾:丁帆 学者、批评家、作家。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第五第六届成员、国家社科项目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著有《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文学史与知识分子价值观》《知识分子的幽灵》等,新著《消逝的风景》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丁老师好,一直想和您做一期对话。您这两年新作连连,每次读来总是让人“一念旋起”,仔细思索之后,却又期待下一本新书,寻找最佳时机,直到这次看到您的《消逝的风景》。一直以来,您给人的印象是笔耕不辍,佳作不断,新书不断,为什么会说“这是出版的这么多书之中,我最满意的一本”?
丁帆:像我这样的人,写作半个世纪了,形成了一种惯性,只要闲下来,不写手就痒,就这么一点爱好,如抽鸦片一样,是有瘾的,
2024年我计划/预计出版七八本书,均为这五六年来所写的学术论文结集和随笔散文集,当然,主要还是学术论集居多。除了去年底商务印书馆的那本《文学与价值》外;尚有商务印书馆正在重新付印中的我的第一部学术书籍《中国乡土小说史论》,这是“中华当代学术辑要丛书”之一种;译林出版社的《译林评论》和团结出版社的《序跋集》(不含自己书籍的序跋)也在编辑付印中。还有一本《批评的灵感》,则是介于学术研究与散文创作之间杂交文体的文章结集,我称之为“学术随笔”,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疫情期间,困在家里,则是我以前一直在梦中设想的一种身陷囹圄、心无旁骛的写作环境,从章太炎到陈独秀,再到瞿秋白,其中自白式的自传,都是他们在牢狱里的佳作,只有在这种语境中,作者才能静下心来,深刻地反省内心深处想表达的真实情感和思想。当年我编辑《金陵旧颜》时,还责怪陈独秀的旁骛太多,耽误了真性情的写作,他的开篇之作就是那篇自传体散文《江南乡试》,语言极其生动,也极有烟火气,可惜神龙见首不见尾,多想看他的自传体散文延续下去,却再无下文了。瞿秋白则更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书写他一生做文人写作品理想的破灭,一个共产党人在大义凛然就义前,说出了人性深处的思想,并非“多余的话”,堪为真正的烈士。鉴于此,我权当瘟疫这个恶魔将自己关进了囚笼,静心屏气地写了30万字的散文。
我分别给《中国作家》和《当代》杂志开了散文的专栏,也给《收获》《人民文学》等杂志投了一些散文随笔,其题材就是描写我一生中所看到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主要是想表达风景背后历史纵深处的人文思想,从城市到乡村,我试图寻觅到一种剖析社会和人性的入口,冀望显示出画面背后许许多多读者能够看得见的隐喻。
高明勇:“最满意”主要体现在哪?
丁帆:《消逝的风景》就是我想在城市风景的历史遗迹中,试图让读得懂的读者去读到历史背后的一种“呻吟”,从而认识历史和今天的自我。我说是“最满意的一本”,是指在这本散文集中,至目前为止,是最满意的一本,那是因为从编辑到装帧,从开本到纸型,再到封面设计,都是我很满意的。但是,其中也还是有些遗憾之处,那是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无法控制的那些被删去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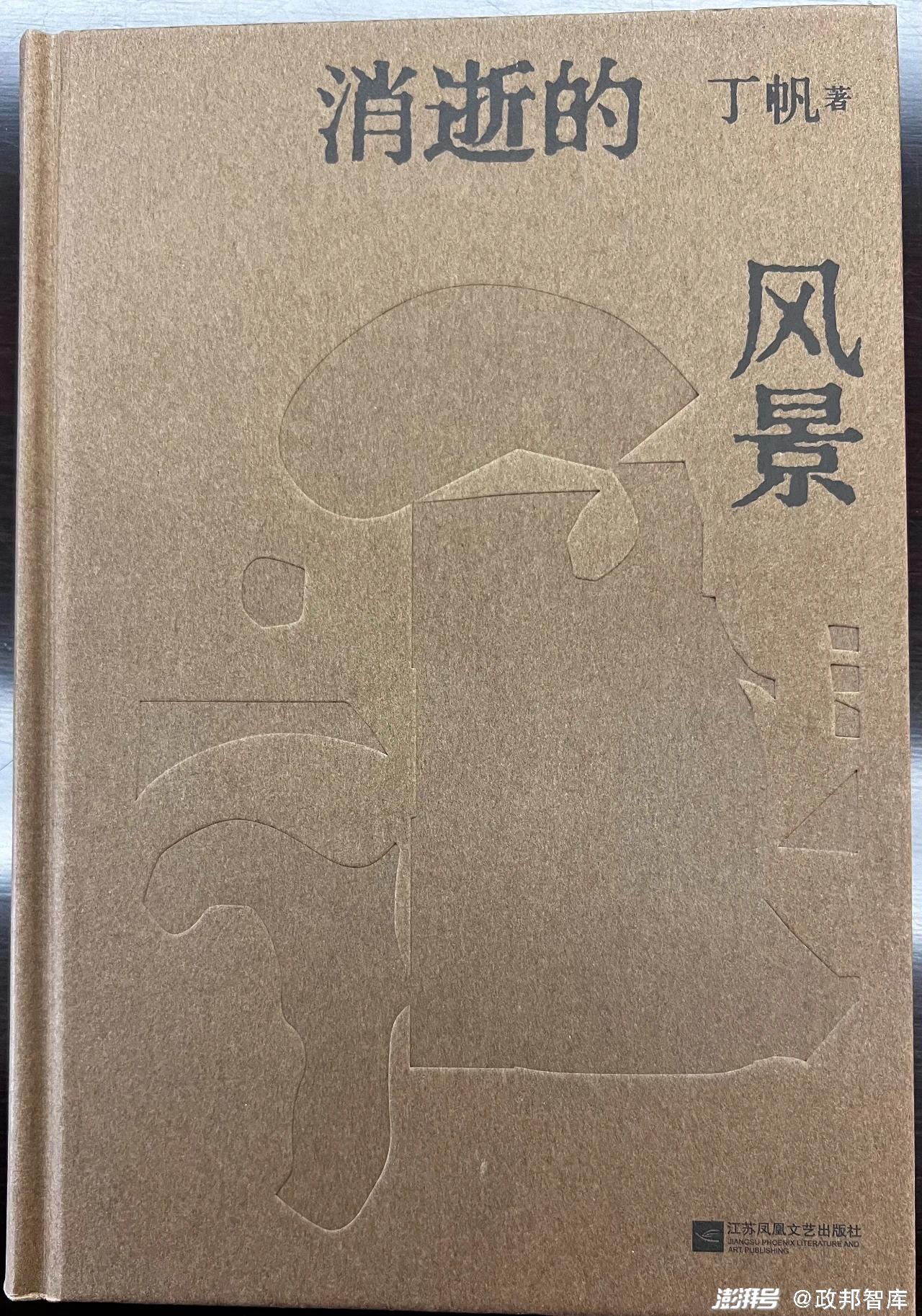
当然,作为作者,都是在期待更满意的下一部作品问世,我更期待的就是在《当代》杂志专栏上发表的散文作品,结集后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乡村风景》,感谢我的“老东家”,感谢社领导,感谢《当代》杂志徐晨亮主编的厚爱,感谢各位评委,他们还授予我“拉力赛”的年度散文奖,这是对我的散文写作最有力的鞭策。
高明勇:您说自己起笔写这本《消逝的风景》,灵感来自伍尔夫的《伦敦风景》,具体是指哪个细节、哪个故事,或者哪句话、哪个观点吗?
丁帆:是的,不仅仅是伍尔夫,许多著名作家都在写“城市风景”,伍尔夫出生并生活在伦敦,她这部不长的散文随笔集虽然并不是很优秀,但却很有特色,它以描写伦敦码头、牛津街、西敏寺和圣保罗大教堂等地理风景,作为她对英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的桥接视点,看起来是写街头风景,笔底却是充满着现代哲学意味,她这本书的细节和故事并不引人入胜,所以影响不大,我只是借用她书名的寓意而已,因为此书的原名叫《南京风景》,后来我怕效颦,才改成了《消逝的风景》。其实,更令我佩服的是乔治·奥威尔的那本非虚构的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这不是他拿手的政治讽喻小说,却更有人间烟火气,故事和细节都很生动,读来受益匪浅。而现代主义大师波德莱尔所写的那本《巴黎的忧郁》,也让我感触颇深,他试图用“一种诗意的散文,没有节奏和音符的音乐”来描写巴黎这个“城市风景”中的阴暗和丑陋,可见散文的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更是它的灵魂所在。
高明勇:其实这种情愫在您之前的创作中也是若隐若现。
丁帆:对,三十多年前,我写第一部散文随笔《江南士子悲歌录》(再版时改成了《江南悲歌》)时,是以人物肖像画为描写中心的,直到《先生素描》,我都是将人的描写放在第一位的。然而,风景描写更是我期待的描写对象,倒不仅仅是梭罗的那种具有超前意识的“生态自然”吸引了我,而是在我儿童时代开始看到的城市风景和乡村风景,触发了几十年后的回忆,从风景中寻觅到“我故我在”的主体意识,风景画面背后“自我”的发现,才是写作的真实动机。巨大的时代“隐喻”,让我时时都想动笔,虽然它们在我童年的脑海里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象,但当时是惘然的,是没有自觉意识的。后来开始喜欢观赏西方的油画,心智有所启迪,其风景画和肖像画背后透露出来的人文意识,往往是超越画家技巧和故事的人性释放,于是,追寻风景背后人文意识中所包含的历史况味和现实意义,才是我写作最有激情的冲动。城市风景和乡村风景的描绘,便成为我近十年来散文随笔由人物素描转向风景描写的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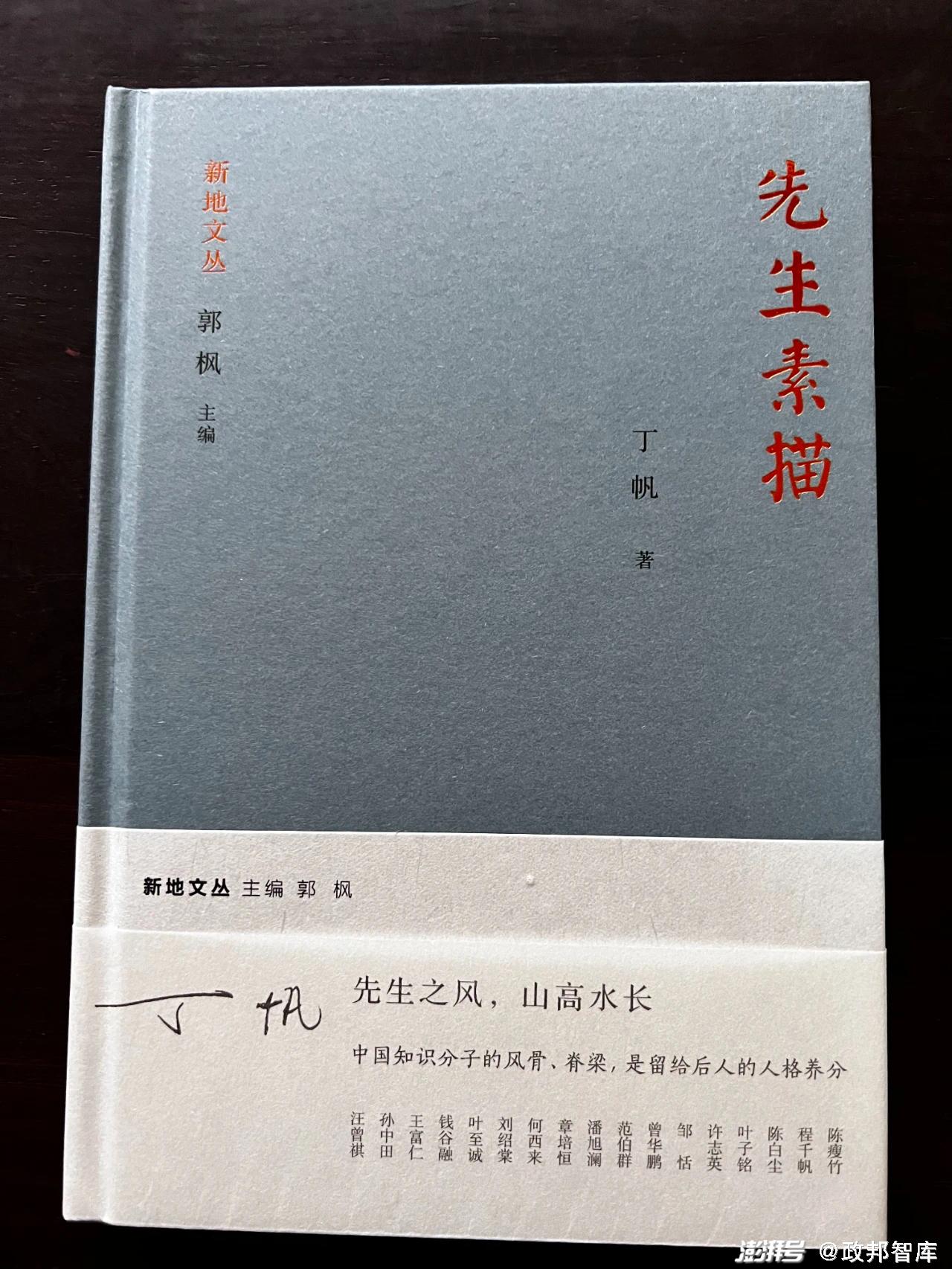
高明勇:您所选取的童家巷、光华门、豁蒙楼等这些“风景”,其实就是一些南京的“地名”,或“地理符号”,您在写作时有自己的“风景”选取标准吗?还是说主要是与自己有交集、印象深的“风景”?
丁帆:是的,我笔下的风景,都是在我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地理符号”,然而,其符号背后的历史与现实的隐喻,却是我更看中的东西。当然,无论是城市风景,还是乡村风景,都是按照自己生活在南京和宝应两地的时代顺序来构筑非虚构风景画面的,在《消逝的风景》中,里面提到的地名,如今依然还存在于南京的大街小巷之中,但是,它们早已成为面目全非的地名遗址了,甚至连一点旧颜都没有留下。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京出版社编写一本《江城子:老南京》一书,将民国时期文化名人描写南京旧景的实录重现出来,后来南京出版社再版此书时,又加进了几篇文章,成书时改成了《金陵旧颜》,那是再恰当不过的历史旧景的文字再现,对照南京旧时的老照片,其风景画和肖像画,活脱脱地将旧日时光里的老南京生活,用蒙太奇的长镜头,还给了历史,让人伫立在风景和人的图像中,真切地体味到沧海桑田中“我从哪里来,欲到哪里去”的哲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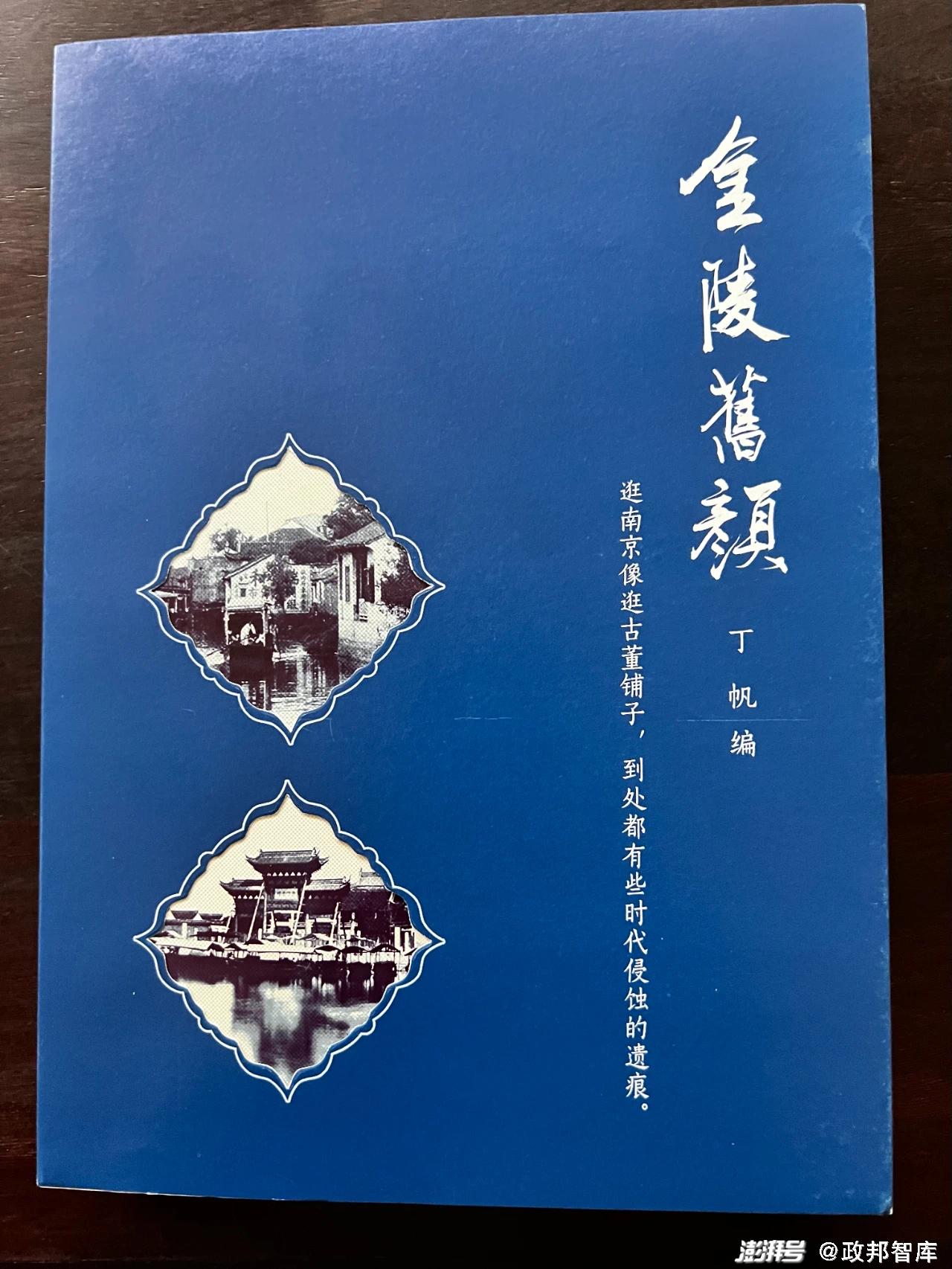
风景分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两种不同的风景在每一个人的眼里,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绪:前者似乎是纯客观的,但其中也隐藏着不为人所觉察的主观意念;而后者则是纯主观的,但是其中却有各种各样观景的视角。这些写风景的书籍,只是我个人对世界的一种生命的认知和体验,是我眼中城市和乡村的感官书写,也许,它们在别人的眼里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了,写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景,那才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天赋和职责。
高明勇:印象中,“风景”在您的写作中是一个高频词,比如在您的那本《玄思窗外风景》中,《你看风景,风景看你》《风景:人文与艺术的战争》《在风景移动中的速度写作》……为什么会这样?
丁帆:的确,正如英国艺术史家西蒙·沙玛在他那部煌煌巨著《风景与记忆》中所说:“只有了解风景传统的过去,才能澄清当下,启发未来。”“所有的风景——不论是城市公园,还是徒步登山——都打上了我们那根深蒂固、无法逃避的迷恋印记。”因此,“风景”一词在我所有的书籍和文章中,是一个高频词,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我年轻时试写小说中对乡村风景描写的眷恋。当然,这个高频词也成为一种无意识,反反复复出现在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中,因而让我提出了中国乡土小说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三画”理论。其中,为什么会把“风景画”置于首位,原因就在于风景不是死去的原始和自然,而是活着的历史,意即它就是历史的见证者,所以,你看它,你就成为了历史的主宰;而它看你,才是戴着历史审判者的眼镜,看着人类一切善恶行径的最后报应。所以,风景和人,是互换的被看对象,所有的喜剧和悲剧的生成,都饱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风景巨大辐射。
高明勇:在您的“个人词典”里,如何定义“风景”?
丁帆:在我的“风景词典”里,我曾经说过:风景的自然属性也是有着两种形态的:其一是客观的、不加任何人工修饰的、原生态的自然风貌,这就是如今活在后现代文明生活环境中被“机械化”了的人,为了摆脱文化的困扰而寻觅追求的那种情景和情境。其二是人类为了攫取、褫夺、利用大自然而对其进行的改造、破坏或美化过的风景。当一个旅游者的目光分不清这两种形态之美丑的根本区别时,也就是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已然失去了他们的歉疚感,在麻木,甚至理所当然地在风景欣赏快感中获得大自然给予的“馈赠”。大自然风景之痛,人类能够倾听得到吗?即使能够听到她的哭泣,你会触摸到她的痛感吗?你会“像山那样思考”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一个人身处喧嚣的都市水泥森林之中,失去了与大自然的亲和力后,生存的意义就少了一种原始的野性,这大概就是梭罗所要寻觅的自然野性吧。当然,另一种声音此刻就会强烈地抗议:难道大自然的美景不就是为人类服务的吗?我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态主义者,但是,我反对那种无节制地糟蹋自然资源与风景的人类卑鄙行径,我们要倾听自然的哭泣,擦拭山湖的泪珠,抚慰她们的心灵创伤。这也许就是人类与自然无法解决的悖论,但是不知道这个悖论的存在,无疑就是人类的悲哀,因为我们的耳朵已经听不到“自然”的哭泣和呐喊声了。
高明勇:能否这样理解,您所说的“风景”,不单纯是文学/文化的意义,更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思索?
丁帆:任何自然的风景背后,都离不开观者“内在眼睛”的解读,我们将用什么样的目光去看风景就显得十分重要了。风景的社会属性同样是有着多种多样的形态。同样的景物,在不同的人群之中,她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感觉,这种差别之大,或许是与各人的生活经历与审美欣赏习惯有关,或许就是与各人的世界观和生存观休戚相关。我看作优美的风景,你看出的则是丑陋,他看出的却又是 一个可利用的物体。殊不知,看风景是要怀有一颗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的,离开这个原则,你就没有资格去欣赏自然赐予你的美景,你对自然美景的占有应该只是精神层面和哲学层面的,而非物理性的践踏与侵害。(未完待续)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